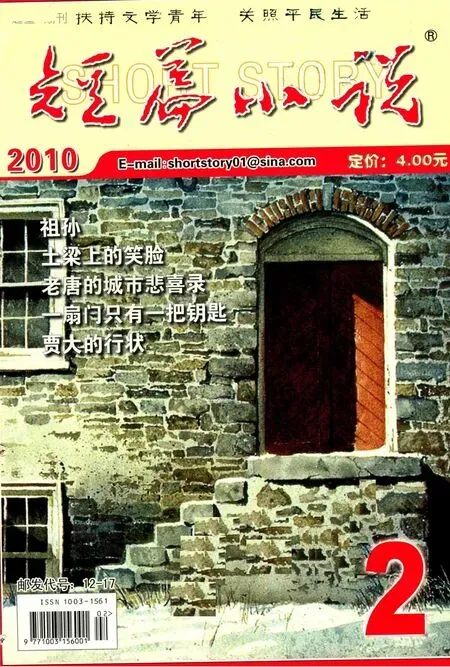河南女人
◎王 妍
我的第二个孩子小同生下来时不到五斤,且肤色呈紫、气息微弱,大夫建议立即住院治疗,于是便从妇幼保健院三楼的产科转到了一楼的新生儿科。作为产妇,我自然是不能东奔西跑地为孩子买奶粉、奶瓶,配合医院治疗,只能乖乖地躺在病房里输液。怀胎九月,却生出来这么弱小的一个孩子,我内心惭愧,但也只能把一切交给丈夫。丈夫既要在新生儿监护室里照看小同,还要按时到三楼给我送三餐、打开水,还要抽空填饱自己的肚子,忙坏他了。

我那时特别能吃,一天三顿总是感觉饿得慌,丈夫干什么都慢腾腾的,给我去买饭总是叫我等了又等,郁闷得我想死的心都有了,于是没出息地在床上悄悄抹泪。
记得第三天上午,丈夫从一楼跑到三楼陪我坐了一会儿,我催他下去看着孩子,说自己不要紧的,催了几遍,丈夫慢吞吞地说没事儿,我觉得奇怪,大夫不是说保温箱前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人吗?丈夫说有人替他照看。
我更奇怪了,骂他开什么玩笑,我们在城里没一个熟人,能托付给谁?万一坏人偷偷把孩子给抱走了怎么办?丈夫说真的没事,一个很好的大姐替自己照顾呢,人家主动要求替换他的,说看他日夜熬着实在太累了就帮帮忙。我说哪来的大姐啊,丈夫说是一个河南女人,家里也有孩子在住院。
我一听急了,起身就往楼下走,憋着一肚子气说你不看我去看,哪里来的女人你都随便相信,现在的人有多复杂难道你不知道吗?丈夫这才动身,我俩快步赶到新生儿监护室,六个保温箱里有四个睡着接受治疗的婴儿,我们的孩子在最左边,丈夫一眼看到孩子在里面,舒了一口气,悄悄骂我多事,虚惊一场。
第三个保温箱前面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正朝我们微笑着。这就是河南大姐,这些天没少给我帮忙。丈夫指着中年妇女对我说。我脸上挤出一点笑容,礼节性地点点头。河南女人长相平凡,胖胖的身材,脸蛋圆嘟嘟的,腮边分布着几十颗雀斑。她说话语速很快,可能是接触了几天的缘故,丈夫竟能听懂她的话,他们叽叽咕咕地聊着。
我被她面前的三号保温箱吸引住了,直勾勾地打量着保温箱里的孩子,保温箱里的婴儿实在太小了,和她的孩子比,小同简直就是大孩子了。那孩子什么都没穿,淡紫色的小身体在玻璃里面显得有些吓人,孩子的头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红皮土豆,没有头发,一缕淡黄的汗毛一样的东西伏在小脑瓜上,也没有眉毛,眼睛紧闭,嘴巴像成人小指甲盖那么大。小肚子却圆鼓鼓的,小胳膊小腿干柴棍一样仰叉着。
我把脸贴在玻璃上细看,是个女孩。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婴儿,这个样子应该乖乖待在娘肚子里才对,不知道因何跑了出来,能活下来吗?那些扎在她小小肢体上的各种塑料管和鼻子上的氧气管,像一团透明的乱麻将她团团捆住了。再看我的孩子,比那女婴大多了,穿着纯棉内衣,在保温箱里睡得很熟。看过以后我放心了,一会儿便爬到三楼安安心心去坐月子了。
丈夫送饭间隙,我问起河南女人和那个袖珍婴儿,丈夫来了精神,碎嘴婆娘一样滔滔不绝地说起了那个女人——孩子不是河南女人生的,孩子的母亲和我一样在这家医院的某张病床上躺着坐月子。孩子父母都是河南人,早年来做生意,现在已经在本地落了户,河南女人是孩子的大妈。
我不耐烦了,因为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个女婴为什么那么小就早产了,她能活下来吗?丈夫绕了半天才说孩子不是早产,够月份,孕妇怀孕前一直跟着丈夫用破牛毛毡熬沥青给别人修补漏水房顶,两口子一直到孩子六个月时才得知熬沥青对胎儿有害,所以孩子生下来只相当于正常胎儿六个月大小,二斤七两重。
我第一次知道牛毛毡可以熬沥青,也是第一次听说熬牛毛毡这活儿存在着这么严重的危害性。这时丈夫嗅着手背说手上有一股臭味怎么也无法洗净,这些天守着给孩子喂奶、洗尿布应该是由河南女人帮忙干的,知道他是乘机向我表功。我装作不明白把话题绕开,让他看我临床的一个产妇,那女人比我小一岁,肥胖异常,顺产生了一个七斤半的女儿,她家人四五口正围在床边看她哺乳,场面蔚为壮观。
那女人竟然当着那么多人将白晃晃的奶子擎在手里往孩子小嘴里喂。因为是初次哺乳,孩子噙不住,折腾一阵后哭了起来,气得那女人用拳头擂着自己的奶子直骂狗奶子。丈夫贼贼的目光扫了一眼,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立刻去楼下看小同去了。
丈夫第二次上来时说,你知道河南女人多长时间没睡觉了?我说一夜一天?两夜一天?两夜两天?丈夫一直摇头,卖够了关子才吐出一句十五天,而且说是十五个白天带着夜晚。丈夫大多时候老实,但有时也会吹吹牛,所以他的话我总是一分为二对待。我笑眯眯地看着他,眼神平和,更深处却埋藏着质疑,这可能吗?十五个白天夜晚不睡觉,还是人吗?就算是人,那也是机器人,而且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
丈夫见我质疑他的话,忙辩解说自己没说谎,说河南女人这些日子从没好好睡过一觉,实在困得不行了才去监护室外的小床上稍稍眯一会儿。我说她家就没个替换的人?娃娃的爸爸呢?丈夫说刚才还来了四个人,但看看就走了,没一个真正顶事儿的。
我说那孩子吃得少,大小便也少,也不哭闹,其实很好照看,有个人在那里看着就是了。丈夫使劲摇头,说,你说得轻巧,一条命呢,谁敢大意,昨晚河南女人的一个妹妹来了,说是替换姐姐,结果你猜怎么啦?我说妹妹照看了一夜孩子,让姐姐美美睡了一夜。
丈夫大笑说妹妹替换姐姐在板凳上坐到十点就嚷嚷困了,对姐姐说我们两人你先守前半夜,后半夜我替换。妹妹出去睡了,姐姐趴在保温箱前实在太累就打个盹儿,怕睡得过死,一会儿起身走走,一会儿用凉水洗洗脸。另外两个婴儿转到普通病房去了,监护室如今只剩下丈夫和河南女人,他俩便不断地说话,用这种方式度过了漫长的夜晚。
我听了心里有点微微的醋意,说你倒是找到伴儿了,一对男女,深更半夜的聊什么呢?丈夫瞪圆布满血丝的大眼,说你个小心眼,我们还能说什么?女人五十多了,儿子都娶上了媳妇,当我妈都够格。我讨个没趣,讪讪地转移了话题,说河南女人既然儿子都结婚了,那眼看就是抱孙子当奶奶的人了,我放心了,你们好好配合,彼此照顾吧。
丈夫接着刚才的事说那个妹妹说好后半夜和姐姐交班,但她一睡就再也不醒,还打鼾,惊天动地的声响隔着玻璃门都挡不住。过了十二点,丈夫提醒河南女人去叫妹妹来当班,她摇摇头说算了,让她睡去吧,她那样子你也看到了,哪是真心实意来替换我?整晚坐在婴儿保温箱边的凳子上眼巴巴地看着里面的孩子,河南女人实在太累就找人说说话。丈夫一来,河南女人有了说话的伴儿,自然很高兴,于是叽里咕噜不停地说。从她的嘴里丈夫得知婴儿的母亲已经出院回家了,她本已生了两个女儿,希望生个儿子,所以偷偷怀了这个。谁知还是女孩,而且有病,回去这些天连个电话都没有,看来是狠心把孩子丢这里了。
过了几天医院通知河南女人,说孩子可以出院了,已经住了两周过了两个疗程,可孩子还是那样,再住下去没有意义了,还是去大一点的医院看看吧。河南女人慌了,连忙打电话叫孩子的父亲过来商量。下午一个男人来了,他神情畏缩地凑到保温箱前草草看了一眼孩子,脸色温温地叫嫂子看着办。嫂子生气了,和他吵了起来,他们吵架完全用的河南话,叽里咕噜一串串的词在两人之间乱蹦,丈夫这个自诩能听懂河南话的人也傻眼了,一句都听不清。最后那个男人气呼呼地走了,河南女人坐在椅子上喘粗气,也气得不行。
监护室又进来了三个婴儿,人一多就有点挤,河南女人谁都不看,就对着我丈夫诉苦。原来孩子的爸爸找大夫咨询过,大夫说你孩子这样去哪儿看都是白看,只能放在保温箱里等她慢慢长大。可一直这么住着也不是事儿,因为长期用药会损伤内脏,再说这么一直住下去医疗费很惊人,半个月已经花了两万多。孩子爸爸的意思是就这样拉倒算了,孩子看好的希望不大,他是准备来抱孩子回去的,但被河南女人给骂走了,河南女人告诉他接下来的花费她承担,如果看好了这孩子就是她的。
那个男人哑口无言地走了。一个大包袱就这样甩给了河南女人,河南女人怎么这么傻?我对丈夫说,人家亲生父母都觉得没希望要放弃,她怎么还要坚持而且自己掏钱?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一天没有好几百不行。丈夫说我也觉得她傻,可又觉得她不傻,是怪。
第六天,医院通知我出院,我离开产科病房住进了儿科病房,在儿子病床上躺着等待他出院。病房里有三张床,里面那张住着一个姓张的女教师,表面看笑眯眯的,但暗地里不断跟男人斗气,我们都看出来了,而且她的亲妈和她婆婆好像也有矛盾,都是围绕坐月子的事发生的。
上午,河南女人进来对丈夫说了句什么后就匆匆走了,丈夫望着她消失的背影告诉我她出去吃饭,要我帮忙看看孩子,还说打开水的时候帮她捎一壶开水。下午,丈夫对张老师一家说起了河南女人以及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可怜孩子。张老师亲妈很惊讶,说她还一直以为是女人的孙女呢,丈夫健谈的毛病又犯了,将河南女人的事情从头讲了一遍。张老师亲妈啧啧地感叹说真没看出来,这性子急躁的女人还是个善心人呢,不容易,生身父母都放弃了她还坚持,还准备自己掏钱,傻呀,现在拉扯一个孩子多累,再说她已不年轻了,何苦呢?不划算,张老师的婆婆提着一桶饭来了,听完后也摇头。
接下来几天,河南女人照旧日夜守在监护室,有时实在太累,就到监护室外面摆着的一张床上打个盹儿。第十天我儿子出了保温箱,抱回病房放在床上,让他开始适应保温箱外的环境。孩子一来,晚上床位就紧张了,我和儿子占了床,丈夫没地方睡觉了,河南女人指着门口那张床说那是她的床位,一直盘踞在那里的一个胖子不情愿地离开了。
我们才知道那是河南女人孩子的床位,胖子是另一个病房的家属,这些天他竟然一直理直气壮地睡在这里。河南女人晚上来了却不睡,指着床告诉我丈夫让他晚上睡这里,丈夫得宠一般高兴,坐在床上直乐。我说她凭什么对你这么好?丈夫说难友嘛,同一战壕里爬了整整十天十夜呢。
第十五天早上,医院通知我们出院,丈夫办完手续,要离开时我们才知道孩子还有一次疫苗要下午注射。怎么办?我们总不能现在回去了下午再赶来吧,因为老家远在乡下,雇车得一小时,我们决定等到下午打了针再回去。
十点钟,一个护士抱着一堆被套床单进来,对我说这里要住新病人了,我慌忙将孩子抱在怀里,护士将我的零碎用品一件件往窗台和小桌上丢,丢得乱七八糟的。我抱着襁褓团团转,丈夫出去一时没回。很快一个年轻媳妇抱着孩子进来了,紧接着是护士进来扎针。在孩子娃娃的哭声中,护士冷冷扫我一眼说这孩子是肺炎,你家孩子是新生儿,你要是怕孩子感染就离远点儿吧。
我身上顿时冒出一层冷汗,这时河南女人进来了,她的孩子昨夜也出了保温箱住在一个单间里,这会儿来取忘在这里的一双鞋。她不看别人,目光飞快地扫到我,立刻知道了我的困境,朝我点点头,说跟我来,我那里地方大。
我迟疑地说你孩子刚出保温箱,大夫的嘱咐我们都听到了,大夫说孩子太小尽量不要接触外界,我们去合适吗?河南女人过来替我拎起行李说走吧,俩小孩在一起住了那么些日子,没事儿。我几乎是在她的推搡下进了那间幽静的特设病房。里面有两张床,小女孩躺在里面那张床上,被子盖得严实,看不到她的影子。
我第一次和河南女人单独闲谈。通过这些天见面打招呼,我已能稍微听懂她的话,加上她有意放慢语速,我们凑合着交流起来。其实半个月来通过丈夫的口,我对她的情况已经知道得差不多了,同时内心的疑问也积攒了很多。
一开口她却给我讲起了我丈夫的事,说孩子住进保温箱第二天时护士叫给孩子喂奶,丈夫冲了一点奶粉往孩子嘴里塞奶嘴,努力了一会儿后慌了,说为啥我孩子不吃?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她上前一看孩子正酣睡,瞪一眼丈夫气冲冲地说他睡着了你看不到?睡着了自然不会吃东西。我丈夫被她顶得哑口无言。一会儿孩子醒了他拿起奶瓶要喂他,河南女人说奶早就凉了你还给小孩喂?晚上丈夫开始给孩子洗尿布,洗了一遍又一遍,可水还是黄糊糊的,河南女人弯腰一看乐了,原来他将尿布投进水里不知道展开了洗,大便裹在里面出不来,河南女人说她当时气得真想拿脚踹我丈夫屁股。
没想到还有这些事儿。我跟河南女人说丈夫平日是个大少爷,什么家务都不干。这样的男人得调教,不能给他惯出毛病。她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点头说这话不假,女人千万不要把男人伺候得像大爷一样,结婚这些年我也渐渐感悟出了这道理。
说着说着话题就说到了她男人身上。她说我男人老实,和你家男人一样,但人好,儿子当年就是他拉扯的,我只管喂奶,别的事儿都是他操心。我惊讶地说换尿布、擦屎擦尿也是他?是的,她笑得露出一颗有点歪斜的门牙,老实男人对女人心实。
接着说到这个二斤七两的孩子。她掀起被子给她喂奶,小孩好像比最初见面的时候长大了一点,看着不叫人那么揪心了。她先兑了奶粉,量很少,只是我儿子用量的三分之一,然后捋起胳膊倒一点奶水在胳膊上试试温度,再将孩子脑袋扳过来给她喂奶。十五天的时间我儿子已经明显长大了,小脑袋圆乎乎的,睡觉时脸上浮现着甜甜的笑,可那孩子的脑袋还那么小。
那孩子会吃,噙住奶嘴缓缓吸吮,动作轻微,速度极慢,慢到我看不出奶瓶里奶水有减少的迹象。河南女人不急,趴在那里眯眼看着孩子吃,她的背影完全给了我,她后背结实,屁股圆墩墩的。想起这些天她一人撑着照顾孩子,我问她累不累,要是别人早就趴下了。她嘿嘿一笑说我怎么不累,我又不是铁打的。我哑巴了,是啊,人都不是铁打的,你到底咋想的,人家父母都说不治,你干吗还留在这里不走?她一拧屁股转身看我,神色停顿一下后说那个女人没有良心,二十多天了连个电话都不打。我想好了,孩子一出院我就带走,带回河南,我养,我就不信养不活她。她的口气像在吵架,唾沫星子喷在了我脸上。我不擦,认真打量她说你带回去谁照顾,你又不能一直守着她。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不能当正常孩子养的,可能需要付出几倍的精力和时间来照看。
我想好了,我先照顾三个月,稍微大点我男人就能照顾了,他细心,我放心。我呆了,一个男人哪有时间照顾孩子?她说他不用干活,专门在家看孩子,再说他那人性格内向不愿出门。那你家不干活怎么挣钱?生活咋办?我出去挣钱,她调皮一笑,我性子野坐不住,喜欢跑来跑去地工作。你干什么工作呢?我心想她这个年纪还能干什么,现在很多工种只要年轻人。我跑保险,她抿嘴一笑,专门跑车险,一天挣一两百一点不累,我这人干啥都高兴,我觉得人活着哭是一天,笑也是一天,人要是成天笑着,日子就过得很快,一眨眼一天就过去了。她呵呵笑了,我跟着也笑了。喂完奶她出去吃饭,让我帮忙照看孩子,其实那孩子没有什么可照顾的,不哭不闹,大小便极少,她衬的那点卫生纸几小时换一次。
小同醒了,小嘴巴叼住奶头一个劲吧唧吧唧吮吸,还不满意地哼哼。看看小同再看那小女孩,我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不真实,是在梦里出现的一幕。在小同的对比下,那个小女孩显得更加弱小,她躺在被子下面悄无声息,感觉那被子是空空地铺开那里的,这样的孩子该怎么拉扯呢?我不由得担忧起来,一方面担心小生命能否战胜死亡活下来,另一方面为河南女人担心。就算孩子活下来了,可要把她照顾到长大成人需要付出远超一般孩子的精力。她做出这个决定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了一番思考?河南女人不在,我过去掀起被子近距离望着孩子,她皮肤上的血管细得像丝线,呼吸时鼻子像薄薄的蝴蝶翅膀在缓缓翕动……我眼前一阵模糊,想起河南女人为她不分日夜地守在保温箱边苦苦熬着,不由得喃喃道,你可得活下来啊,无论如何都要活下来。
这么想着,我眼前恍惚看见这孩子真的长大了,转眼上学了,很快走上社会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站在我眼前,她管河南女人叫妈妈,可有一天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知道这个女人不是亲妈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当她知道了自己是怎么被这个女人日日夜夜守着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又会怎么想?她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报答这个女人呢?想到这些我忽然觉得这孩子根本就无法报答河南女人,真的,什么样的孝心能抵得上她眼前所做的这一切呢?
下午我们给孩子打了疫苗就出院了,河南女人帮我们拿东西一直把我们送出楼道,看着我们上了出租车才进去。
七个月后的一天,丈夫去城里帮朋友接车,回来很高兴地说你猜我遇上谁了?我猜了一大圈儿,他才不耐烦地说那个河南女人还记得吗?记得呀,不但记得,心里还时不时想起呢,替那孩子担忧,甚至有时回忆起在医院那些苦闷日子,都觉得像做梦一样不真实。
我眼前一亮,赶紧问是不是见着河南女人了?她怎么样?那孩子怎么样?丈夫呵呵笑着,说不是她,是遇见了那孩子的父亲。他现在不熬沥青了,承包了城里的一条街道在铺砖呢。我问了孩子,他说他嫂子带回河南去了,孩子长大了不少。别的我不好深问,不过可以肯定那孩子的一条生命是留住了。
我不甘心地追问一些琐碎事情,比如,具体长大了多少,现在体重多少,一顿能吃几勺子奶粉,会笑了吗……想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可是丈夫摇摇头说他知道的也就这些。我一想也是,大男人之间聊天,不是太熟能问得那么详细吗?这时丈夫忽然记起来了,说哎呀呀,今儿给人帮忙办小车上户的时候我忽然弄清楚了那河南女人在干什么工作了,原来她是在保险公司帮人排队呢。现在买新车的人多,车辆入户要办保险,可办保险很麻烦,好多人都在那里排队,于是就有了专门干这个的。河南女人一大早就去排队,看看排到跟前了,那些赶时间的客户就拿着资料顶替她,立马办了。排一个队能挣一百,完了她又到后面开始排队,平均一天能做成两三笔生意。哦,现在还有这职业。我眼前不由得现出一个略显肥胖的身子,挤在长长的队伍里耐心等待着人流一点点往前移动,她泼辣爽朗,干这个应该不困难。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河南女人,她还是那个样子,脖子下面的扣子扣得一粒不差,脸上笑着,嘴里叽里咕噜着什么,说些什么呢,因为语速太快我听了半天一句都没听懂。我问她孩子好吗?会走路了吗?我说我家小同已经满地跑了。她点点头,有些调皮地给我做了一个小孩走路的姿势,迈着小小的步子,一步一步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