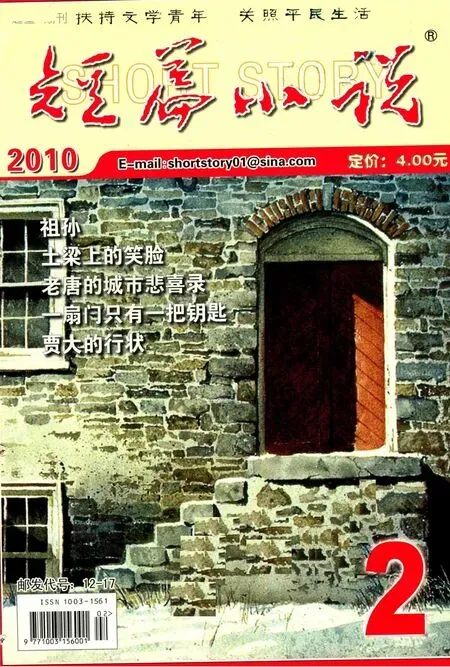刘老汉的晚年生活
◎阮鲁闽

一
刘老汉一大早就醒了,洗了一把脸,跟老伴说出去转转,看看会不会碰到以前的老哥们儿。
刘老汉没有睡懒觉的习惯,这也是他几十年养成的。
以前在工区生活的时候,刘老汉每天早上起来,脸没洗就先到后山转转,然后再下山回家洗脸吃饭,他感觉这样一天下来心里踏实。
过去工区后山是一片原始杂木林,那片原始森林就像一道绿色屏障,守护着工区几十年,整个工区一二百口子人喝的水全靠它。20世纪90年代末被场里卖了,当年就砍了,当时工区里的老工人抱住树不让砍,去找场里的领导说理。场里的领导说,把山卖了好给下岗的工人发买断的钱,不卖山哪来的钱啊?
树被砍了,刘老汉就很少再上后山转了。自从伐木场工人下岗后,工区里年轻人陆陆续续都走了,去外地讨生活,原来上百号人的工区就剩几个老人留守。三层楼十六间房子就刘老汉一家住,一间间都锁了门。
刘老汉闷在家里。刘老汉唯一开心的日子,就是每隔五天到离工区不到一里的干山去赶集。日子也就这样一五一十地过着。
那天,老伴儿怕刘老汉憋出病来,就对刘老汉说:“明天干山集,去集上转转散散心吧。”
刘老汉就来到干山集赶集。
二
名叫干山集,其实连个正经街道都没有,就是一个小山村,村中只有一条路,路两旁挤满了高矮不平的土墙房、木板房,村里人便称这条路叫街道。
也不知道从何朝何代起,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方圆三里五村的村民,都喜欢把家里吃不完的东西,或是瓜果,或是青菜,用篓子背,用竹篮挑,聚集到这儿来,买的买,卖的卖。有的人家里如有个红白喜事什么的,也都在这一天送送帖子,捎个话什么的。一到八九点时间,人们便都回去了,集也就散了,像早晨的露水一样,山里人叫它“露水集”。
就这样一个小干山集,这两年眼睁睁瞅着热闹起来。原因是从县城伸过的高速公路,擦着村边过,人也仿佛一下多了起来,一到逢五、逢十路两边搭篷摆摊,叫买叫卖,说拉弹唱,算命占卦,沸沸扬扬,再加上那煎炒烹炸的油香味熏得空气都油腻腻的,好一派升平世态、繁华景象。
三
刘老汉在集上转了一圈,也没有什么东西买,就转悠到村东头。
老林头的酒店就在村子的东头,紧挨在路边。说是酒店,看那房屋摆设却实在简陋,一间木板钉的房子,靠里面左墙角垒了一个锅灶,旁边还有一个烧木炭的火炉子,上面坐着一个铝锅,这是专门用来烫酒用的。另一个墙角用木板钉了一个长桌,算是柜台。柜台里面摆了好几坛酒,酒呢,不是白酒,也不是啤酒,而是米酒,用糯米做的。山里人喝米酒能当饭吃,一到秋后,山里人每家每户都做几坛,封起来,逢年过节,或办个红白喜事什么的好待客。柜台外面摆了几张木板钉的桌子,这便是酒店了。
老林头年轻的时候便会做酒,是和他父亲学的。他父亲可是远近有名的做酒高手。在农村,有的人家是用稻谷蒸酒,也叫谷烧酒,做的是白酒。老林头白酒、米酒都做,他用的都是上好的糯米。用糯米酿的酒,不管是白酒还是米酒,喝到嘴里润滑,不像谷烧酒喝到嘴里辣喉咙。酿酒可是有诀窍的,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第一道工序是蒸米,蒸米的时候关键是火候要掌握得好,蒸太熟出酒少,蒸太浅酒味出不来,也就是酒精度数上不去,这便是手艺活。
老林头要做酒的时候,先把糯米放水里泡几小时,这个空闲时间,找出蒸笼、笼布洗刷干净备用。老林头时不时地在水里抓起一小把糯米放在手心里,用大拇指慢慢捻揉,等到大拇指上有粉状物出现,就说明糯米泡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把铺好笼布的蒸笼放在锅里,盖好锅盖开始点火,等锅里的水烧开了蒸汽上来了,老林头就用漏瓢捞出泡好的糯米均匀散在蒸笼里,再盖上锅盖。等蒸汽上来,再撒上一层米,盖上锅盖。蒸糯米的时候,烧的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等到最后一道糯米上汽后,老林头就会掀开锅盖拿起一根竹筷子插试一下,竹筷能一下插到底就说明糯米蒸好了,然后把蒸好的糯米倒在一个竹篾编的簸箕里凉透,然后使粬。使粬便是关键的关键了,使多少粬要拿得准:粬使得多了,酿出的酒烈,喝多了会醉人,伤身;粬使得少了,酿出的酒非但没味,还容易变酸,放不久。他做酒一般是十斤米兑一斤粬,一斤米兑一斤半水。所以他酿造的酒不浓不淡,味道格外醇厚香郁。糯米酒如果放上个三五年,那就更好了,一开坛盖,便会有一股酒香冒出来,若打出来盛在透明的玻璃杯里,绿酽酽的。喝惯米酒的乡下人,一看这酒的颜色便知这酒的年份。他还有一个秘方轻易不用,据说是他父亲临终时传给他的,就是把做好的糯米酒滤净后,重新装在一个坛子里,再把一只杀好的鸡放入坛子里,鸡要干,不能有水。封好口,埋在地里,几年后再挖出来,鸡肉连同骨头都融化在酒里,这酒能舒筋活血,可以治百病,女人坐月子吃这酒最好,大补,就是茅台、五粮液都不换。
常来这小店喝酒的有两种人,一种是赶集的买卖人,这号人一到晌午头散集的时候,不管是摆摊的还是挑担的,货一出手,腰里便有了几个钱,就到这店来要壶米酒,再来点猪头肉、花生米什么的,坐上个把小时,既休息了身子,又填饱了肚子,再挑着空空的担子往回走。一种是等车的、下田做活的,经过这里,递过去块把钱,接过两碗米酒,直着脖子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下去,用手背抹一下嘴巴,掂起行李或扛上农具就走,保准一天不口渴,还耐饿。
四
在众多的顾客里,有两人与众不同,他们逢集上午不来,而是下午来,一坐就是一下午,不到日头落山不回家,很像城里人泡茶馆。
一个是七十来岁须眉斑白的老人,个头不高,背有点儿驼,一双细眼老是眯着,透着一脸的喜相。老人姓田,人民公社时当过大队长,酒量不大,坐半天也喝不上两壶酒,酒壶旁边摆放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姜丝辣椒丝炒的田螺。
老田端起碗来喝上一口,细眼一挤,嘴能吧唧半天,品摸滋味。品足品够了,说一句:“老林头,好酒,地道。”然后打开塑料袋,伸进两个手指在塑料袋里捏起一个田螺送到嘴里咂几下。老林头听到夸他,忙说:“好多年不做啦,手都生了,明年您再来尝尝我做的鸡酒,那味儿才叫好。”
爱和老田一桌喝酒的,是住在干山集西边的老张头。这人六十多岁,方脸宽肩,连胡子眉毛都硬扎扎的。他酒量很大,但从不多喝。每回来总是带个大饭盒,不是炸蛋就是卤大肠什么的,装得满满的,有时还变变花样。他一来,就从胳肢窝拿出饭盒,“啪”往桌上一放,“噌”一声往老田头面前一推:“老哥,你尝尝。”然后才冲老林头一点头:“先来一壶热点的。”
刘老汉第一次来到老林头的酒店,看到老田头和老张头聊得热乎劲儿,说到称心快活处,俩老头还仰着脖子哈哈笑一阵,好不亲热。
以后刘老汉每个集日都去,就坐在旁边的桌子独斟独饮,听到他们那开心快活的笑声,羡慕得很,便也耐不住想过去凑个热闹。
几次下来,也许是时间长了,刘老汉跟老田头和老张头也熟了,他们邀请刘老汉一起坐,刘老汉比较随和,很快就你尊我大哥我称你老弟地坐在了一起。
现在的农村也没有多少人,年轻的都去城里打工赚钱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孩子,老田头和老张头都是留守老人,和刘老汉一样。
以后,刘老汉也跟着下午去,刘大娘就说:“人家赶集都是上午赶集,你怎么下午赶集?”
刘老汉说:“下午有伴儿。”
老伴儿见他每次回来都是乐呵呵的,还哼着小曲。见他活得舒坦,便也不再说什么。
五
这天又是个集日。吃罢晌午饭,刘老汉把一个沉甸甸的饭盒装在一个布袋里,一手拎着来到酒店。
老田头、老张头还没来。见刘老汉进来,老林头便要去筛酒。
“先别忙,等他们兄弟来了一块筛。”刘老汉摆摆手。说着把布袋里的饭盒掏出来轻轻放到桌上。
老林头头一回见他带这玩意儿怪稀罕,问:“您老哥的福气,家给弄点啥好吃的?”
刘老汉细眼一眯:“有啥好吃的,就是点三鲜水饺。”老林头一听就明白了,他这是给老张头带的。
上个集他们在这儿喝,老张头说闲话:“要是弄点三鲜水饺来配酒就好了。”
三鲜水饺就是用虾米、香菇、油摊的鸡蛋掺在一起做馅包的水饺。没想到刘老汉把这话记在心里。
那次回到家里,他对老伴说:“下回给我包点三鲜饺子带着下酒。”老伴都听愣了,以往想给他弄点菜让他带去下酒,他都不要,这还是头一回,就高高兴兴地给他和了一团面,包了满满一饭盒。
刚凑在一桌的时候,每回喝酒,豁达爽朗的老张头总是死活非让他吃不可,好像你不吃他的就看不起他,弄得刘老汉心里过意不去,总想找个机会回敬他。那一天,老张头一说,刘老汉就当回事了。他知道自己老伴儿会做。
那天,刘老汉打开饭盒,老张头见是饺子,忙用两个手指头夹起一个放到嘴里,扬起脸嚼了一阵,吧唧一下嘴说:“是三鲜,是那个味,嗯,好东西,多年没吃到了。”
刘老汉看他吃得那样有味道,心里乐了,两眼一眯:“嗨,早先不认识你,从现在开始,我每次都带三鲜饺子,让你吃个够。”
“那多不好意思啊?”老张头客气地说。
“没啥,用我们老家的话说,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刘老汉笑着说。
六
刘老汉有一段时间也没来。
那段时间,连续下雨,下得天都快塌了。工区后山那片杂木林砍了头尾还不到七年,山上流下来的泥石流就把工区房子冲没了。
过去伐木场盖房子选择不是依山就是傍水。那年连日突降特大暴雨,没日没夜地下了一个星期,引起山洪暴发,泥石流把工区整个三层楼的房子冲倒了,山也开裂了,裂了一道一米宽的口子。据上面的地质灾害专家看完现场后说,是后山的木头砍得太厉害了,新栽的杉木根系浅,把不住土,雨一下土就顺着水流走了。
那晚,刘老汉一直睡不着,雷一个接着一个在房顶上轰隆隆滚着响,震天动地,震得窗户咯吱响,就像打炮。刘老汉眼皮一直跳,感觉会出什么事,会出什么事呢?刘老汉也猜不到。
一道闪电,刘老汉发现房间里亮晃晃的,是房间进水了,水浑得像黄河水。
刘老汉拽着老伴儿就往外跑,刚跑了几步,刘老汉又松开老伴儿的手返回去,手里拎着一个箱子再跑出来。
房子边上有一个高坡,刘老汉就拽着老伴儿的手往高坡上跑,刚跑到坡上,刘老汉就看到一股洪水从山上冲下来,就像黄河决口一样淹没了整排房子。
房子冲倒了,无家可归。
房子没了也不能睡大街上吧?刘老汉就在村里租了间农民的房子住。
“干了一辈子伐木工人,末了连个家都没有了,还要租人家农民的房子住。”晚上蹲在租住的农民家的黑屋里,听老伴儿唠叨着,刘老汉也是一脸的无奈。
想起当年,刘老汉带老伴儿来福建的时候,在上海转车,老伴儿第一次看到地板光滑得能照人,跟镜子似的不敢迈脚。仰着头望着高高的大楼问:“咱那里也是住楼吗?”
刘老汉说也是楼,是三层楼,跟这个不一样。
刘老汉跟李大炮不一样,李大炮第一次跟他媳妇说,住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七
大柱下岗后,也去了城里,一家人租了一小套房子住。
大柱说:“爹,你们也一起去吧?”
刘老汉说:“你们去吧,我在这里给你们看房子。”
大柱去城里住,就带了穿的衣服去,家里的东西都锁在房子里,钥匙交给刘老汉。
那场洪水从上面一直冲下来,把大柱的房子也淹了,房子里的东西也被冲没了。
刘老汉在城里安顿下来后,就跟老伴儿说:“明天干山集,我要回一趟干山,以前约好每个集日在老林头的小酒店碰面,以后回去就少了,我要去跟那些老哥们儿说一声,去道个别,他们还不知道我搬家呢,再包点水饺带去,老张头爱吃。”
刘老汉来到老林头酒店,只有老田头一个人在,没有看到老张头。
“怎么就你老哥一个人?”刘老汉边问边拿出饭盒。
“上个集差你没有来。”
“前几天搬家了,城里买的房子孩子们给弄好了,非要让去城里住,以后跟老哥儿几个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还是国家工人好,国家不会丢下你们不管。”
“看来老张头今天也不能来了。”
正说着,老张头来了,一进门就高声说:“嗨,今儿可叫你老哥等急啦。”
老田头说:“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老张头照例拿出饭盒,打开来,是四条半斤来重的炸鲫鱼,圆墩墩的,黄灿灿的,诱人。把饭盒“噌”地往桌上一推,说:“要不是叫你们老哥也尝尝鲜,我今天也真不想来了。昨晚发烧,打了两针,躺了一个早上,晌午时,我那个在城里上班的小儿子买回来几条鲫鱼,说给我补补身子,我看活蹦乱跳的,挺新鲜,便想着哥儿几个,带了几条来给哥儿几个尝尝。”
“这些年,在老哥的这个酒店认识了几个老哥们儿,也是缘分,今天就是特意来跟几个老哥道个别的。”
“住城里好,到处亮堂堂的,哪像农村,一到晚上就到处黑灯瞎火的。”
“在乡下待了一辈子,习惯了,我还是喜欢在乡下,要不是工区房子冲了没地方住了,说什么我也不会去。”
“说得也是,在哪里住习惯了,冷不丁换一个地方还真不舒坦。”老林头说。
“可不是,小儿子也在城里买了新房子,前阵子非要拉我去住几天。白天孩子们都去上班了,就剩我一个人在家闷得要命,跟关在鸟笼里差不多,想出门走走,又谁也不认识,连个说话的都没有,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待不住了。”老田头也深有感触地说。
“以后哥儿几个有到城里,就到我那里去,到家里吃个饭,认认门儿。”刘老汉说。
“这些年,有你们哥儿几个陪着,我感觉日子过得挺好的,就是以后喝酒少一个老哥哥了。”老林头低着头说。
老林头的一对子女也都在城里打工,也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早就想接他去了,老林头就想,在乡下待习惯了,尤其是离不开这个小酒店,当年多亏了有老林头这个小酒店。
当年老林头老伴儿生了一场大病,人没救过来还欠了一屁股债。当时老伴儿说别花那个冤枉钱了,活多大岁数都是命里定好的。老林头坚决不同意,砸锅卖铁也要治,借钱也要治。用老林头的话说,钱没了可以再挣,人没了可就再也找不回来了。虽然人最后没有救过来,老林头难过但不后悔。
后来,老林头就开了这个小酒店,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
再后来,老林头先是认识了老田头、老张头,后来又认识了刘老汉。每隔五天一个集,这些老哥哥就会来酒店陪他。
“今天你们都放开来喝,一切都算我的,就算为老哥哥送行。”老林头笑哈哈地说。
那天老林头说,人一旦有了盼头,日子就过得充实,就有希望。
“是啊,人要活得有盼头,日子过起来就有希望了。”刘老汉一路上念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