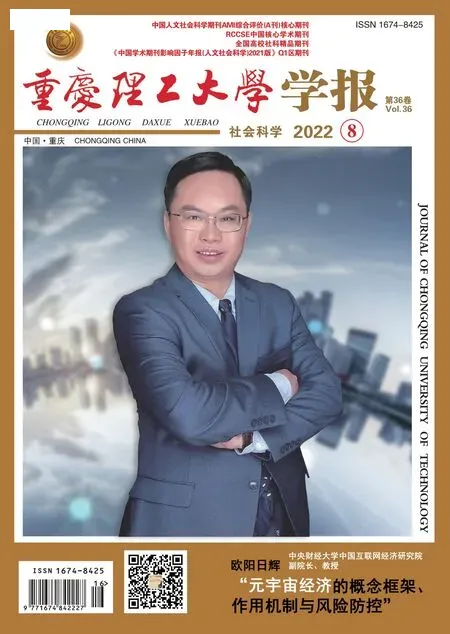“p但我不相信p”为何荒谬?
——从言语行为视角看摩尔悖论句
王 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2488)
摩尔悖论指“我不相信正在下雨,但实际上正在下雨(I don’t believe it’s raining,but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这个房间着火了,但我不相信(There is a fire in this room and I don’t believe there is.)”(1)“我不相信正在下雨,但实际上正在下雨”,这个句子出自摩尔(G.E.Moore)的文章Moore’s Paradox(文章标题由编者所拟),收录于G.E.Moore:selected writings一书第207-211页[1]。“这个房间着火了,但我不相信”,这个句子出自维特根斯坦1944年写给摩尔的信,收录于Wittgenstein in Cambridge:letters and documents 1911—1951一书第365页[2]。G.E.Moore:selected writings的编者鲍德温(T.Baldwin)推测,摩尔的本篇文章是对维特根斯坦这封信的回应。以及与其形式相同、内容不同的一系列句子所引发的问题。本文将引发摩尔悖论的句子称为摩尔悖论句。虽然后来的摩尔悖论句发展出众多变体,但本文仅探讨上述类型的摩尔悖论句及其相关问题,即形式为“p但我不相信p”的摩尔悖论句。一直以来,摩尔悖论句被认为具有某种“荒谬性(absurdity)”,众多学者对此种荒谬性的产生原因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其中,言语行为被认为是导致摩尔悖论句荒谬性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几种言语行为所造成的荒谬性进行分析,发现对于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存在两个层次的解释,二者中只有一种可以恰当地解释由言语行为引发的荒谬性。
一、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并非逻辑矛盾所具有的荒谬性
在对摩尔悖论句与言语行为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前,首先应排除其荒谬性等同于逻辑矛盾这一可能性,这一点可以从语形和语义两个角度来解释。在语形方面,摩尔悖论句并不具有p∧~p的形式,因此摩尔悖论句并不等同于矛盾式。在语义方面,摩尔悖论句的语义是可理解的,而矛盾式的语义是不可理解的。“正在下雨,但我不相信正在下雨”,从字面上看,这句话表示“我”所指称的主体对“正在下雨”这一事实表现出不相信的态度(2)这个句子的理解者不能将代词“我”等同为自身,理解者需要将“我”理解为指称其他人才能理解该句子。,而“正在下雨,但不在下雨”却无法被理解。
摩尔悖论句的语义能够被理解,这一观点需要建立在一个隐含的预设之上:摩尔悖论句具有清晰的语义。在某些情形中,摩尔悖论句并不具有清晰的语义,例如,当我们听到摩尔悖论句“p但我不相信p”被“我”所指称的人以断定的语气说出时,就无法理解其语义。这种情形所体现出的不可理解性正是摩尔悖论句荒谬性的核心,即,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体现在其不可理解性上。我们可以对造成这种荒谬性的原因加以排除。首先,造成这种不可理解性的原因并不在于摩尔悖论句包含第一人称语言表达式。如果a说出“p,但a不相信p”,并且我们知道句中的a指称说话者,我们就仍然无法理解这个句子。在这个例子中,并不存在第一人称语言表达式“我”[3]68。其次,摩尔悖论句被人说出并不是导致这种不可理解性的充分条件。例如,当我们读出“正在下雨,但我不相信正在下雨”这个句子时,不会认为这一句子不可理解,或者当我们听到演员说出这样一句台词时,不会认为它不可理解。在这两种情况下,摩尔悖论句仍会被按照其字面意义进行理解。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导致摩尔悖论句不可理解的原因在于,说话者自身的因素被纳入对摩尔悖论句字面的语义的理解中,二者结合生成了一种存在怪异之处的新语义,而这一问题对于可理解的摩尔悖论句来说并不存在。可理解的摩尔悖论句拥有固定的语义,人们不会认为说话者自身的因素(如说话者的言语行为)能够影响摩尔悖论句的字面含义。
二、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与言语行为
对于不可理解的摩尔悖论句来说,参与到摩尔悖论句语义构建过程中的主体因素包括主体的言语行为。关于摩尔悖论的早期研究倾向于认为导致此种荒谬性的言语行为是“断定(assert)”。例如,维特根斯坦认为:“‘让我们假设:情况是p但我不相信情况是p’,说这句话是有意义的,但断定‘情况是p但我不相信情况是p’是无意义的。”[2]365摩尔也持有类似观点:“当我们说,说这些话很荒谬时,我们并不意味着仅仅说出这些语词就是荒谬的,而是意味着某种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当人们使用这些句子去断定这些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时,以这种方式说这些句子是荒谬的。”[1]207

但除“断定”之外,还有观点认为其他言语行为也有可能引发这种荒谬性。布莱克(M.Black)认为,“说出(pronounce)”也和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相关,“托马斯说出‘蘑菇有毒’这句话时,他的话‘暗示’了托马斯相信蘑菇是有毒的”[4]25。布莱克将“说出”与“相信”这一心理态度相关联,因此说出“正在下雨,但我不相信正在下雨”意味着前一合取支所暗示的东西与后一合取支字面表达的东西构成矛盾。“说出”与“断定”相比,是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说出”可以仅是一种表达词句的发音行为(phatic act),它既可以伴随语义也可以不伴随语义,但断定不仅包括说话者的发音行为,这些发音还一定要伴随语义,而且说话者还必须对自身利用发音行为所表达的语义表示肯定。摩尔注意到,“在一个人作出的断言所意味(means)(6)句中的斜体为原文中的格式。的东西与所表达(expresses)③的东西之间,存在一个不总被察觉到的重要区分”[4]26,他所指出的是“断定”行为层次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是针对“说出”而言的。“断定”与“说出”所表达(7)此处对某些词语进行加粗,目的在于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表述间的区别。的东西是其字面所暗示的内容,它并不能体现断定行为的独特性,而断定所意味④的东西是说话者对话语内容作出肯定时体现的效力,这种差别也是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相对于以言表意行为(locutionary act)的丰富性。基于不同的说话目的,说出某一话语但并不断定它,说话者或许在利用这句话说谎,运用摩尔的措辞,即说话者并不意味着其所表达的东西。
即使说话者正在执行的言语行为是说谎也不一定会消除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说谎时所使用的语气通常是断定性的,有可能被误认为是断定,但说谎者明显没有肯定其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可见并不能够从语气推出说话者所执行的言语行为。摩尔发现了这一点,他区分了“断定”与“断定地说(say … assertively)”,后者可被视为一种语气。他认为这种语气会产生两种可能的效力,一是表达自己确实相信话语所表达的命题,二是倾向于使听者相信说话者确实相信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前一种效力适用于“断定”,后一种效力不仅适用于“断定”,还适用于说谎的情形。说谎常常发生于交流的语境,听者听到某句话语,首先听到的是语气,而不能直接辨别说话者是否断定语句所表示的命题,如果说话者知道说谎与作出断言的语气是相同的,便可能利用这一点来欺骗听者。如果听者倾向于相信说话者是在作出断言而不是在说谎,即说话者成功实施说谎行为,则“断定”所引发的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就会在此情境中发生。不同之处在于,说谎时说话者并不真正具有相互冲突的心理状态,但听者会认为说话者具有冲突的心理状态。
通过对上述三种言语行为所导致的荒谬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导致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的原因似乎存在两种具有分歧的看法:一是说话者心理状态中存在冲突(例如在“断定”的语境下),二是听者认为说话者心理状态中存在冲突(例如在“说谎”的语境下)。
三、摩尔悖论句荒谬性分歧的成因
上述分析似乎表明,“断定”与“说谎”这两种言语行为的差异造成了对于摩尔悖论句荒谬性看法上的分歧,这有可能是由于二者本质上属于不同种类的言语行为。“断定”总体上可被视为一种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作出断言时,说话者表达了一种断定性的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体现为对话语所表达的命题表示肯定。而“说谎”总体上是一种以言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无论谎言的内容是什么,所有说谎行为的目的都是干预听者的心理,使听者倾向于认为说话者相信谎言的内容。但对言语行为种类的划分并不能解释为何会出现上述分歧。首先,以言行事行为与以言取效行为的界限本身是不清晰的,上述划分很大程度上是牵强、大致的。其次,言语行为并不能完全决定是否会产生荒谬性,如果说话者在说谎,但听者识破说话者在说谎,则“说谎”这一行为并未实现其效果,在摩尔悖论句的例子中,表现为任何一方都不会觉得荒谬,说话者虽然在说谎,但荒谬性消失了。 “断定”与“说谎”只是两种典型的会导致摩尔悖论句荒谬性的言语行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言语行为与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相关,诉诸某种言语行为本身的特征来解释摩尔悖论句荒谬性成因上的分歧是不恰当的。
真正造成此种分歧的并不是各种言语行为的特性,而是说话者是否被判定为真诚的,对此进行判断的主体既可以是说话者也可以是听者。以“说出”“断定”“说谎”这三种典型的言语行为为例,只有“断定”必然包含真诚性这一预设,判定其真诚性的主体是说话者,那么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才有可能由说话者心理状态中的冲突所致。但是,尽管说话者本身是真诚的,听者也可以质疑说话者所作出的断言的真诚性。这种质疑虽然是允许的,但并不影响将荒谬性的原因诉诸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同时,这种质疑使得将荒谬性的原因诉诸听者判断的可能性完全排除。而“说出”与“说谎”并不必然包含真诚性预设,因为说话者本身不必真诚或必不真诚,而听者也可以拒绝认为说话者是真诚的。但如果听者将说话者判断为真诚,则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就可以被理解为由听者的判断所致。由此可见,言语行为本身的特性并不足以说明摩尔悖论句荒谬性的分歧性解释,真正导致这种分歧的是判断者对言语行为的解读。
摩尔对“意味”和“表达”的区分已经指出了这种分歧的成因。“意味”涉及说话者与话语之间的关系,“表达”涉及听者与话语间的关系,前者与说话者的思想有关,后者与话语的言外之力有关。在任何言语行为中,如果说话者意味的东西与作为话语的摩尔悖论句所暗示的内容相符,则荒谬性由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引起。如果说话者意味的东西与作为话语的摩尔悖论句所暗示的内容不符,或无法确定说话者意味的东西与暗示的内容是否相符,就会使听者认为荒谬性存在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中,但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否如此是不确定的。摩尔在论述摩尔悖论相关问题时多次使用“暗示”一词,来表示不同言语行为表达的话语所共有的效力,这种效力促使听者根据所听到的信息对话语的意义进行解读。布莱克总结了摩尔对“暗示”一词的用法:“(1)说话者使用表达式E,(2)除非相关命题pE是真的,否则人们通常不使用E,(3)听见说话者使用表达式E,人们通常会相信pE是真的,(4)说话者知道上述所有情况。”[4]26其中相关命题pE并不是指表达式E字面所表达的命题,而是使用该表达式所表达的会话蕴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例如某人说“哎呦!”时暗示“我感觉疼”。表达式E与相关命题pE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语言交流中的约定,它并不是必然的,一个人可以在自己不感觉疼时说“哎呦!”,但这句话会作出“说话者感觉疼”的暗示。当听者根据话语所暗示的信息解读说话者所表达的内容时,他并不能直接掌握说话者的意图,可供听者解读的信息是一些话语的外在标志,例如语气、句式、用词,以及语境提供的信息。布莱克认为:“当我们用断定的语气说出‘牡蛎是可食用的’,我们所用的语气,以及所选用的系动词(‘是’,不是‘可能是’或‘可以想象是’或者任一其他可用的系动词)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真诚’(这一态度)的惯用标志。”[4]31因此,听者便能够从以上标志所暗示的东西推测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在摩尔悖论句的情境中,听者可以推测出说话者至少真诚地肯定前一合取支所表达的命题,因而这种肯定态度与后一合取支所表达的倾向相冲突。如果说话者并不意味着其话语所表达的东西,从而导致其说出摩尔悖论句时并不拥有相互冲突的心理状态,听者也会推测说话者拥有冲突的心理状态。
四、摩尔悖论句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荒谬?
从内容上看,对摩尔悖论句荒谬性的两种解释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合,如果说话者认为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由说话者心理状态中的冲突引发,而荒谬性也确实由此引发,则两种解释便可合二为一。但如果说话者并不拥有冲突的心理状态,则诉诸听者判断的解释便成为对荒谬性的正确理解。因此,对话语和心理状态间关系的探究成为解释摩尔悖论句荒谬性的关键。对于“p但我不相信p”这一真诚的话语来说,如果要将其荒谬性归于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则需要探讨如下两点是否同时成立:“我不相信p”这种字面表达是否反映说话者对“p”具有否定的心理倾向?真诚地说出p是否反映说话者对p具有肯定的心理倾向?
当说话者使用“我不相信p”这一表达式时,并不一定表明说话者对“p”具有否定的心理倾向。维特根斯坦考察了“我相信”这一表达式的用法,他认为:“但若‘我相信事情是这样’表明我的状态,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断言也表明我的状态。因为符号‘我相信’并不能表明我的状态,至多只能提示我的状态。”[8]227该观点表明,当我们说“我相信”时,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心灵中存在相应的信念,但如果“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确实表明我拥有相应信念,则该表达式可以与“事情是这样”互换。但维特根斯坦并未详细阐明“我不相信”这一表达式的用法。从语言形式上看,“我不相信p”既不是说话者对自身信念的表达,也不是对自身信念的报道(8)罗森塔尔(D.M.Rosenthal)认为[9],在口头表达中,人们通常用“正在下雨”“会下雨吗?”等表达式来表达自身相信、好奇等意向,而用“我相信正在下雨”“我想知道是否会下雨”等表达式来报道自身意向。此处对词语加粗的目的在于提醒读者注意上述表述间的区别。,我们也无法从“我相信”的使用方法推出“我不相信”的使用方法,因为“‘我相信’与‘我不相信’的关系既不是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关系,也不是反对关系……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我相信’与‘我不相信’是两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不能被通约为第三种更为基础的实体”[10]17。因此,我们无法从“我不相信p”这一表达式中获得关于某主体心理倾向的确切信息。
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答案也是否定的。首先,真诚地说p指说话者说p时意味着p,即说话者说p时想要表达的语义为p,这可以表明说话者所表达的思想为p。根据弗雷格的观点,语句所表达的思想是命题,它是心理态度的内容,不是心理态度本身,我们无法从说话者表达的内容中推出其心理状态。其次,摩尔认为“通常来说,人们不会作出一个正面的断言,除非他们不相信反面是真的”[4]26。他的观点很符合直觉,根据这种观点,说话者真诚地说出p表示说话者不相信非p。但根据上述提及的语言游戏间的差异,我们无法从对非p的心理倾向推出我们对p的心理倾向。同时,行为主义的观点也为语言与心理间的关联提供了辩护。通常认为,信念是导致行为的原因之一,我相信p会使我说表示p的句子,但同一行为可能具有其他原因,我们无法从行为反推说话者的信念,所以不能由此判定说话者的心理倾向。此外,也有观点从概念形成过程的角度进行了反驳。某人在正常情况下用确信的语气说出p表明其断定p,如果人们频繁地断定其所不相信为真的命题,则“信念”概念就不会是目前的样子[11]11-12。这一观点预设了心理状态是概念形成的基础,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心理状态的含糊性与私人性,如果不借助语言的清晰规定,便难以将不同个体的心理状态统摄于同一概念之下。
根据以上解释,似乎无法将摩尔悖论的荒谬性真正归结到说话者的心理层面,这一解释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使用方式并不依靠与个体心理状态间的联系而得到确定,其必须得到公认才能保证沟通的可能。个体心理状态是一种私人对象,它无法成为语言的基础,只有将语言本身当作某种心理状态的标志,才能保证语言的用法具有稳定性。基于这种看法,将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诉诸听者的判断更具优势,话语对心理状态的暗示可被归结为语言使用的惯例,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即为说话者违反语言使用的惯例的结果,例如说话者在说出“我不相信正在下雨”的同时不能以断定的语气说出“正在下雨”,因为按照布莱克的观点,这种语气的使用惯例是暗示自己“相信”话语内容。无论布莱克对惯例本身的描述是否正确,他从语气、用词、句式等最为直观的语言特征入手的方法是恰当的,这些因素是交流中最先被观察到的,以此为基础规定语言的用法相对于以个体心理的共性为基础规定语言的用法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共识。同时,“相信”等心理动词与言语行为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固有的,而是由于规定而建立的。在语言学习的情形中,某人或许会学到“我相信p”可以和直接断定p互换,这种用法包含在“相信”一词的特点中[12]20,二者间的联系作为一种语言使用惯例得到传授。“信念”等心理动词的用法也并不预设相应心理实体的存在,“信念的完整现象,即人们所拥有的那种信念,只有当像我们这样的生物进行信念归属(belief ascription)的实践时才存在”[12]20。由于“相信”一词的用法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具有不对称性,当我们将信念归属于第三人称主体时,我们通过对其行为的观察完成信念归属行为;而将信念归属于第一人称主体时,我们将第三人称的信念归属标准应用于第一人称的情况[12]20-21。上述信念归属的实践表明能够被语言描述的心理现象也是依靠规定而存在的,决定心理动词意义的是其用法。认为摩尔悖论句的荒谬性是由说话者心理状态中的冲突引发,这种错误看法产生的原因在于语言使用的惯例在长期实践中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常识,影响着我们的直觉,这会误导我们认为语言使用惯例所暗示的某种心理状态是说话者真正的心理状态,或这些惯例的形成至少要以个体心理状态为基础,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个体心理本身就是无法用语言衡量的,二者是两种不同质的东西。
五、余论
以上解释仅表明当摩尔悖论句与言语行为结合时,将其荒谬性解释为由违反语言使用惯例造成是恰当的,并不代表任何语境下的摩尔悖论句都适用于此解释。言语行为所导致的荒谬性仅反映出摩尔悖论句在语用层面的问题,体现了语言与其使用间的矛盾,但摩尔悖论句所引发的某些问题与语言使用无关。例如,作为思想的摩尔悖论句虽然也可用语言表达,但其矛盾出现在思想领域本身,而不是由语言造成的。不被说出的摩尔悖论句也会引发荒谬性,但其荒谬性显然不能诉诸语言使用惯例,因为上述语言使用惯例是指交际过程中的语言使用规则。因此,被言说和被思考的摩尔悖论句所拥有的荒谬性存在质的不同,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