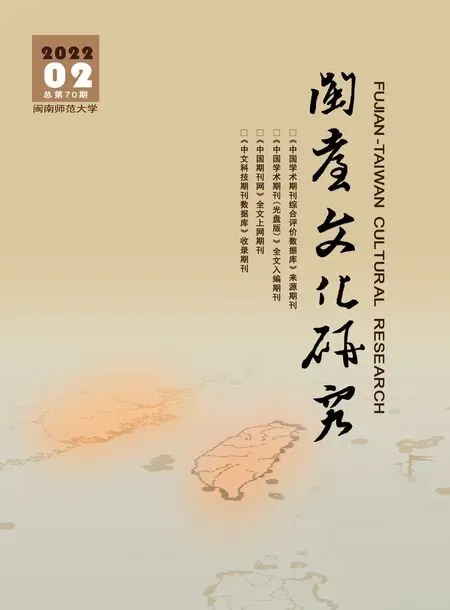后殖民批判与性别政治:20世纪台湾女性剧场艺术论
刘 丽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漳州 363000)
台湾女性戏剧的出现,与世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无关系,从《一间自己的屋子》(英国伍尔芙,1929)、《第二性》(法国西蒙·波伏娃,1949),到《女性的奥秘》(美国贝蒂·弗里丹,1963)、《性政治》(美国凯特·米利特,1970),在貌似司空见惯的社会里,启发女性对男权社会意识的怀疑和批判,从而引发了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社会地位较之前显著提高,女性不再是“坚守炉台、忠贞贤惠、养老育幼、服侍夫君”的“男人附属品”,不在于“通过激发男人的勇敢和侠气而达到英勇、崇高乃至美”(巴霍芬),或“陷入圈套、扮演起并非由她们自己而是由男人所决定的角色”,也不是“堕落的夏娃”“破坏性强的女人”(如莎乐美、鲁鲁、朱迪斯、希尔达·汪格尔)[1],更不应是旧秩序下披着贞洁、母性“光环”的牺牲品,而是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人”而存在。在这种社会思潮下,一群成就斐然的编剧、导演在台湾脱颖而出:她们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自觉地从“女性立场”出发,思考现代社会女性的身份、地位、角色等问题,最先发声的是李曼瑰。1975年3月8日起,李曼瑰的《瑶池仙梦》在南海路艺术馆公演17场,探讨家庭中父亲教育的重要性、妇女的影响力等问题,邀请妇女界领袖担任演出委员,让她们真正成为“三一剧艺社”的中坚,推展妇女剧运,计划开办妇女编剧班,举办妇女戏剧创作征选活动,在每年的妇女节、母亲节、教师节,公演与妇女生活和问题相关的戏剧。但在经受父权制、阶级压迫及异族殖民统治下,台湾女性遭遇的性别、阶层、民族歧视,比男性更甚,反抗也更烈。1996 年5月4日,在台湾大学学生会及全省大专女生行动联盟的带领下,台北火车站的“抢攻男厕”运动引起当局与民间的重视,抗议行动终获成功,街头行动剧的出现,与台湾开始重视女权议题关系密切;2003 年5 月,高雄开展第一届台湾女性艺术节,台湾地区女性主义者举行许多街头抗争表演,呼吁“个人的即政治的”。相对而言,周慧玲、魏瑛娟、戴君芳、吴幸秋是1990年代以来台湾女性主义戏剧的代表,透过剧场,尝试剥除、瓦解社会强加给女性的各种羁绊。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身体与性向
随着后殖民主义[2]的兴起,许多剧场工作者自欧美学成返台,将西方剧场理论、实践应用于台湾剧场,在表演中运用多媒体、幻灯片等手法来处理性别问题及新式的人际关系,女性剧场则强调后殖民主义、性别及族群问题,女性主义领域的后殖民主义戏剧,重点在于批判传统“父权制”“男权中心主义”偏向,推崇性欲解放、性向自由。1995年8月,在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争取和使用剧场式面罩的策略下,儿童青少年性交防治法正式立法。在法律制度的抗争之外,女权运动者积极参与公众活动、政治及政策的制定,1996 年彭婉如案发生后,“台湾妇女团体联合会”成立,12月以街头剧形式在台北新光三越百货前面的马路旁,演出一幕女性被强暴的戏,在抗争队伍接近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的广场时,她们齐声尖叫、夹杂哨音,表达对父权制度的愤怒,女性主义者演出以社会政治为主题的表演,也运用政治策略及戏剧效果,对当局施压,以期改变现状。如莎士比亚的妹妹们剧团演出的《我们之间心心相印——女朋友作品1 号》,表现女性主义、女同性恋、性欲与性压抑等多元主题,以女演员脱去手套、假发、卸妆的表演,表现女性探索自我的历程;《天亮以前我要你》(周慧玲导演)跨越性别、文化、爱情的藩篱,《当我们谈论爱情》(魏瑛娟导演)里,女演员模仿玩偶,女性身体被物化,《牡丹亭》(戴君芳导演)以性别伪装,探讨女同性恋的爱情故事。台湾妇女联盟的女性主义者提倡“禁止将未成年少女卖为娼妓”的法律,抗议者在励馨基金会集合,以戏剧隐喻和剧场演绎的形式向立法团体施压,立法院讨论此法案期间,励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义工坐在旁听席,脸上戴着白色面罩,面罩眼角边挂着一颗大大的红色泪珠,形成强大的视觉压力。
周慧玲执导的创作社剧团,强调剧场原创精神,以“艺术创作”为优先考虑,尝试不同的创作组合方式,以激发创造力。在《记忆相簿》里,舞台设计参考罗伯·威尔森(Robert Wilson)、皮娜·鲍什的风格,舞台上洒满照片,打彩色强光的透明玻璃屋,强化了剧中人难以忘却的记忆。《天亮以前我要你》里,认为女性不是“偶像”“图像”“客体”,性别认同有更多可能性(如双性主体、女同性恋主体)。故事场景设置在纽约,以规避保守的台湾,剧中人是四位台湾旅居美国的知识分子,分别是摄影师(女同性恋)、电影导演(异性恋女人)、服装设计师(男性)、画家(男同性恋),圣诞夜聚会中,画家与电影导演暧昧,在服装设计师追逐“美国梦”的迷茫中,借由电影导演的行动,打破一夫一妻、异性恋及性别的二元性,表演从开玩笑演变成对激情和虚无主义的挑战,混淆了性的探讨和移民的欲望。黎焕雄、魏瑛娟受邀导演两个插曲,周慧玲意在戏剧的多重性中融入不同风格,黎焕雄以非写实、奇幻式的剧场风格表现性别认同的难题,在虐待狂与被虐狂之间,“在这拥有特殊灯光变换的一幕中,四位演员身着黑色紧身皮裙、裤子、胸罩及内裤,以性虐待的黑色幽默之化装技巧来呈现他们的想像性别及性认同。”[3]魏瑛娟导演一位角色向母亲坦承男同性恋身份的场景,在四分钟里,演员使用肢体语言,表达“出柜”的难以启齿,强化“女人不是商品和物品”“女人不是男人交换的财产”等观点。
女性主体的觉醒,在20世纪的台湾剧场里,始于“身体”与“性向”的自由,但未仅仅止步于这两者,而是不断挑战性禁忌,反抗“父权制”。
二、反抗“父权制”:挑战性禁忌
20世纪的台湾小剧场,不断寻求新的表演方法,采用行动、姿态、道具、服装等不同的戏剧元素,大胆描绘跨越性别、性、同性恋等问题,企图追求性别彻底的平等。在剧场里,呈现女性反抗性骚扰、性压抑、性欲表现等主题,如质疑女性着装暴露被性侵的合理性,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有选择穿着的权利,有权为自己而打扮而不是为了取悦男性,此外,反家暴、反性交易、防止性虐待、争取同等薪资、女性平等工作权、女性参政,也是台湾女性主义者关注的话题。300余名抗议者采取街头表演的形式,参与以行动剧“女人走出衣柜”为发端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将印有“贞洁”“免费佣人”“嫁男人、生子”“好太太好妈妈”字样的纸衣柜推倒、践踏,行动剧展示“长期以来处在男性威权压迫下的女性角色,包括雏妓、女学生、年长女性、职业妇女及女同志。演出的高潮出现在带领着示威群众的‘父权天使’突然间变成一只‘恶魔’,而所有的女性则团结起来对抗这可怕的恶魔。”[4]并将被视为“污秽、肮脏”的卫生棉丢向天空,穿透政治性建筑物(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将示威行动演变成一种仪式,以性禁忌转喻政治禁忌,迫使父权体制看到这些“存在”但“视而不见”的问题,女性戏剧演出造就直接或间接的结果,其深远的影响通过不同形式体现出来。
1992 年魏瑛娟编导《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在下冰雹》,是一出关于同性恋题材的荒诞喜剧,“无论魏瑛娟是把蔡政良的角色赋予男/女双性特色,或是兼备同性恋/异性恋倾向,反正她都不着痕迹地打碎了传统性别(以及性偏好)两极化的模式,玩她自己无偏见、无歧视的游戏,而且出之以气定神闲、幽默风趣,更重要的是不必沉痛控诉,也无意紧张地说教。”[5]《文艺爱情戏练习》中,女同性恋角色固然令人讶异,男同性恋在黑暗中换穿内裤的动作,在狭窄的空间里,演员在月色、路灯中若隐若现,大胆挑战男同性恋恐惧症。一些作品打破戏剧与舞蹈之间的界限,表演者的肢体动作取代台词,来诠释戏剧主题,如1996 年1 月,《我们之间心心相印——女朋友作品1 号》在咖啡馆剧场B~Side 演出,“除了节目单以外,作品完全没有文字,连任何有约定俗成之意指的语言都消失了。”[6]三个一起成长的女孩,在友情之外,发现关于同性之间说不出口的“爱情”,彼此吸引、猜忌,又害怕彼此,而情欲又让给她们发现家庭、校园、社会里的各种人际关系,以看不见的力量向自己施加压力,令观众甚为震撼,有“集体治疗”的功效,“三个女人逐渐剥除身上衣物、头上饰物、有形无形枷锁,好一幅独立自主而又彼此扶持的女性解放图像。”[7]《随便做坐——在旅行中遗失一只鞋子》受进念二十面体(Zuni Icosahedron)艺术总监荣念曾之邀,在香港首演,一桌、二椅与两位演员,在20分钟的舞台剧里,以两张金色衬垫的椅子代表父权,盖着蓝色桌布翻倒的桌子,和桌脚上一双小小的血红色旧女鞋代表女性在父权制压迫下的痛苦,使用中国传统戏曲手法和音乐,黑色背景的中间,挂着灯光明灭闪烁的幻灯片和一张图片,两位短发女演员的手脚被红绳子缚住,不停地在两张桌子上挣扎,像玩偶一样移动,在她们的整个身体被红色绳子绑住的过程中各掉了一只鞋子,裹脚“代表了中国父权社会下其中一个残忍的旧俗。”[8]戏剧批判了保守的婚姻制度,这种体制强化了男人的地位时,同时降低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当我们谈论爱情》里,以意大利式即兴艺术喜剧、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美式使用罐头笑声的闹剧等多重风格,身着内衣的两位男演员和一位女演员,用绘成衣服模样的板子遮在身体前面,演员像小狗和玩偶的动作一样移动,他们的口语和肢体语言与戏服、玩偶式姿势一起,制造出幽默和间离效果,反对将女性身体视为引起性欲的物品。讽刺的是,表演要结束时,男人们讨论女性角色的死亡,听不到女性的看法,事实上是两个“男人”在谈论爱情。《文艺爱情戏练习(二版)》分五幕,每一幕都有演员二重唱,角色A(男)、B(男)、C(女)、D(女)没有名字,以演员的间离动作、幽默对白、性别扭曲的服装,打破性别二元性,模糊性别身份,第四幕中,两位男演员互换内衣,让观众感受其亲密关系及男同志情谊。《蒙马特遗书—女朋友作品2 号》以邱妙津在蒙马特自杀前的遗愿为基础进行改编,演出一开始,舞台上散落着几张纸,三位女演员俯卧在地板上,想要接近纸张,六位白色衣服的女演员转向观众,一边朗读纸上文字(女同性恋日记、书信中的故事),一边撕碎它们,这些散乱的纸张象征着女同志的遗愿和书信。演出以黑白布幕为背景,黑色背景与白色衣服形成对比,营造孤独、肃穆的气氛,以多位女演员演出相同的女同志角色邱妙津,探讨爱、欲望、背叛、自杀、死亡等问题。[9]魏瑛娟使用多种手法,将女性故事搬上舞台,让观众了解女性并非男性的附属物,而是独立的主体。“‘莎妹剧团’对女同性恋的认可程度,超出常规尺度的开放表演,令戏剧同行惊讶的同时,毫无疑义地成为前卫剧场代表,这从剧团应为名称中的‘Wild Sisters’亦可窥出一斑。通过处于制度和固定模式之外的女同议题,将艺术变革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起来,从戏剧实验走向女性先锋,女戏剧人完成了由艺术而社会的角色转换。”[10]借助女性社会地位及种种束缚,魏瑛娟在剧场里实践了她的理想,对女性处境的反思,是她一贯的作风。
三、性别政治:解构与影响
1995年3月,临界点剧象录演出《玛莉马莲》(改编自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大有在女性主义思维主导下打破传统传统禁忌的企图。当然事出非关色情,因为真正以色情为号召的牛肉场脱衣秀在台湾是早就公开存在的。”[11]从“甜蜜蜜”到1994年、1995年9月两次“台北破烂生活节”的小剧场演出,暴力、S/M倾向使临界点剧象录的表演,前卫且另类。台湾渥克演出的《查某喜剧——速克达玛丽1993》《肥皂剧》《带我到地方》《痴情目莲花》这些戏,关注同性恋、异性恋题材,“都有女性主义瓦解父权体系男强女弱僵化形象的意图。”[12]1995年5月至9月,“四流巨星艺术节”上,16个周末演出16部小剧场作品,共演出59场,观众达2184人次,演出主题涉及同性恋、女性主义,甚至裸体登场也屡见不鲜,《桌子椅子赖子没奶子》《野草闲花》《带我到它方》《爱死》《幸福拥抱我》《在爱不爱之间,我们……》《青蛙王子的三个女朋友》等[13],“实现了拥抱弱势团体,表露出从边缘向中心反扑的态势。”[14]这些主题曾在1980年代“有限度”地演出过,如《毛尸》《夜浪拍岸》,当时的台湾,探讨“同性恋”议题尚属禁忌,作为“同性恋”“艾滋病携带者”的田启元,不仅在剧场里讨论,而且以反叛的姿态,从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入手,公开挑衅台湾社会体制,以狂躁不安表现台湾受政治压抑的现实,以“同性恋”作为幌子,矛头直指专制政治,而到了1990年代,“同性恋”议题在剧场已司空见惯,艺术手段上表现得更为张扬、恣肆。
与女性解放运动共生的是,女性政治觉悟的觉醒、性开放、服饰标准的变化,以及对庸俗价值观的解构与颠覆:女性不是“生育工具”“商品”“花瓶”“玩偶”,剥除长久以来的“性别标签”,打碎长期以来的“性别壁垒”,女性就是“她自己”,从而重新建构女性主体意识。而这一影响,在21 世纪不仅方兴未艾,且益趋明朗,如吴幸秋执导的《孽女·安蒂岗妮》(2001),类似于“环境剧场”,在台南安平古堡中室外演出时,观众坐在草地上,安蒂岗妮坚持埋葬弟弟,不接受异性恋婚姻的标准,被国王克里昂处死,以其纯真的性格及坚强的毅力,对抗虚伪丑陋的政权,而在戏剧形式上使用跨文化元素,演员以闽南语演出,使用歌仔戏、美国现代舞、希腊歌队、传统说书、中美结合的玩偶等多种形式,并出现像面包傀儡剧场一样的大玩偶,身着中国传统服饰与台湾地区巫师服装,克里昂西式外衣与中式小丑服并列,与歌队一位女性的南方客家服饰形成对比。剧末,安蒂岗妮像鬼魂一样徘徊在古老城墙上,撑着一把台南美浓纸伞,随着音乐从右到左移动,表达对传统父权道德观、殖民主义的反抗;周慧玲导演的《惊异派对》(2003),批判男性视女性为性玩具的观念,提出“女性身体并非生殖工具”的观点,以真人大小的充气娃娃作为性别化物品形象,黑色长发白皮肤,穿着黑色丝织短睡袍,充当其中一位男角色的性伴侣对象,剧中没有女性,只有四位男性角色,指出男性将女性视为被动图像、仅止于性玩具这样的观念;戴君芳执导的《柳·梦·梅》(2004),改编自昆曲《牡丹亭》,结合剧本的文学性与西式后现代表演,在一小时的舞台时空里,将柳梦梅遇到杜丽娘魂魄至柳梦梅挖开杜丽娘坟墓呈现出来。一女性演员分饰柳、杜两角,以女性主义姿态演出女性阴柔气质和伪男性阳刚气质,让观众欣赏性别表演,隐藏着女同性恋的爱情欲望。
四、结语
20世纪的台湾女性剧场,勇敢面对“女性身体”,跨越“后殖民主义”“父权制”的迷思,以“身体”来刻画角色的“精神世界”,在反抗父权制、挑战性禁忌的边缘多方试探,探索剧场的种种可能性,这样的戏剧实践,对演员、观众来说,是相当前卫、大胆的挑战,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从女性解放的层面上来说,相对于西方“贫穷女性”“种族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等议题来说,台湾女性戏剧主要探讨本土中产阶级女性、女同性恋,题材相对偏狭、简单,这并非剧场里特别的“傲慢”,而是蕴含着李曼瑰、周慧玲、魏瑛娟、戴君芳、吴幸秋等人的生命体验,也是她们从事女性戏剧的基础。经济独立决定思想独立,以“小剧场”为主要演出场地的台湾女性剧场,辐射范围不够深广,发出的声音也比较微弱,离成为“主流剧场”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从剧场革命到社会革命,促进女性彻底解放、自主的路,这种“真正的改变”,仍任重道远。
注释:
[1][美]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陈永国、傅景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194页。
[2]“后殖民主义”是相对于“殖民主义”而言,后者强调殖民者对国家主权、军事、政治、经济上进行侵略、干涉,前者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的控制。
[3][4][8][9]段馨君:《凝视台湾当代剧场:女性剧场、跨文化剧场与表演工作坊》,永和:Airiti Press Inc.,2010年,第102页,第91页,第117~118页,第120~121页。
[5][7][12]李幼新:《小剧场与社会禁忌——我在小剧场里什么也没看到》,《中外文学》1996年第24卷第12期。
[6]王浩威:《激进与伦理:小剧场的内部民主》,《中外文学》1996年第24卷第12期。
[10]苏琼:《性别表演视角下的舞台剧照解析》,《戏剧艺术》2019年第4期。
[11][14]马森:《台湾戏剧:从现代到后现代》,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0年版,第27页,第106页。
[13]陈梅毛:《从不良的体制中卯力干起——从四流巨星艺术节谈起》,《表演艺术》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