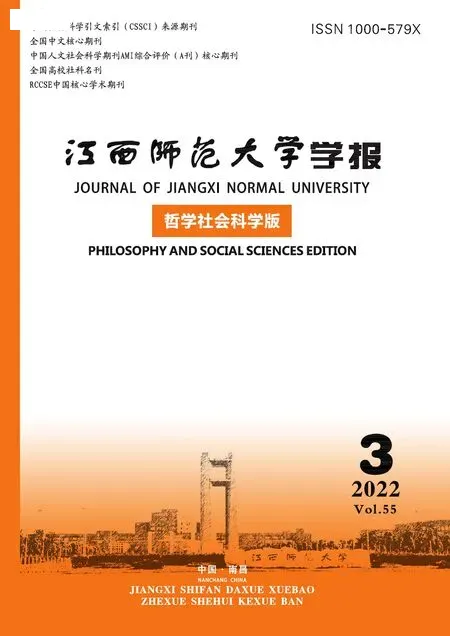赣籍进步青年与五四运动
张蓝天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五四运动,不仅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史上具有开端性意义[1](p503),而且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识群体开始整体主动走上中国社会舞台[2]。晚清民初,省界意识构成“合群”之先声。五四时期,学生依托地缘的聚合为一值得瞩目的现象,如《新青年》办报初期的皖籍群体[3]、民初北大初建与改革中的江浙学人[4]、五四期间以新潮社为代表的山东籍群体,以及以曦园为代表的湖南籍群体等等[5](pp372-373)。而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在京学生领袖,还是地方运动的响应,江西籍学生群体也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既有关于江西地区五四运动的考察,或着眼于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发生、运作及影响等史实的概述与重建,或着眼于个别赣籍人物在运动中的表现与作用,或强调“五四”的后续效应:五四青年向革命青年、五四学生团体向党团组织的转变历程(1)相关研究参见殷丽萍:《五四运动在江西》,《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李健:《论南昌的五四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曾辉:《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5期;晓农:《五四运动中的“江西三只虎”》,《党史文苑》2006年第13期;齐悦:《段锡朋与五四运动》,《同舟共进》2018年第11期;陈维裕:《五四运动的闯将——罗隆基》,《兰台世界》2006年第23期;王伦信:《“五四”时期中学生社团活动写实——两册极为珍贵的袁玉冰学校日记》,《教育评论》2007年第3期;于海兵:《革命青年的修身与自治——以〈袁玉冰日记〉为中心》,《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于海兵:《五四时期地方学生的革命之路——以南昌改造社及其团体生活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具有相当借鉴意义,但对五四期间活跃在京城或故土的赣籍进步学生群体的行为选择及文化性格之专门考察仍较缺乏。而随着《袁玉冰日记》(2)《袁玉冰日记》(手稿),原名《中华民国八年学校日记》,实际上专为袁玉冰个人日记,手稿见“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尚未影印出版。等一手地方性材料的出现,进一步的细致刻画成为可能。本文以五四运动中的江西籍学生为观察对象(3)长期以来,关于“五四”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新文化运动以来有阶段性内涵的五四时期,后者则主要围绕着1919年5月至6月从学生界扩展至工商界、从北京拓展至全国的集体行动,本文将兼顾以上两种界定,以“事件史”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观照五四时代的整体性意涵。,通过分析赣籍进步学生群体的身份特征及社会、时代定位,并与其他群体进行对比,进一步考察五四运动与地缘网络、地域文化的关系,探讨五四在一代青年个体生命世界中的位置。
一、五四运动中赣籍青年的参与特征
在北京,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赣籍青年学生不在少数。1916-1917年之间,许德珩、张国焘、王造时、彭文应等青年学生纷纷从家乡来到北京(4)其中许德珩、张国焘于1916年来到北大,王造时、彭文应1917年来到清华。。这批赣籍青年多就学于北大、清华、京师高等师范、北京中国大学等院校,日益受到新思潮的吸引。1918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为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回国游行,虽然游行目标最终未能达成,但成为学生集体行动之预热。此后,许德珩、张国焘等学生领袖和不少在京同乡积极投身组建学生团体、联络各地同侪、开通爱国之风气等活动。不仅积极参与筹办“学生救国会”、《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团体,并且逐步和九江的方志敏、就读上海的程天放等赣籍学生及各地进步青年建立联系[6](p21)。这一过程中,“心地热诚”的江西较早留美官费毕业生、北大新闻系赣籍教授徐宝璜,在编辑出版、新闻教育方面也给予颇多指导[7](pp43-44)[8](p32)。在五四运动前夕,赣籍学生领袖在集会上积极发声,连夜做准备;游行的当天,更是身先士卒,不少因此被捕。为争取游行目标实现、扩大影响,这批赣籍青年在北京学联、全国学联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多地掀起五四运动的高潮,充分展现青年学生的爱国热忱,得到社会各界进步力量的肯定和支持[1](pp240-255)。相比湖南、山东籍学生,赣籍进步青年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但其中一些重要代表在运动的组织与领导上发挥着骨干作用,还有数十人在京参加五四游行、杂志筹办和民众讲演。赣籍进步青年走出书斋,加入反帝救亡运动,形成一股颇有生气的力量。
就参与运动的特征而言,首先可以赣籍青年集中加入的《国民》杂志社为例。1918年10月,在蔡元培、徐宝璜和李大钊等学者的支持下,《国民》杂志社成立。在199名社员里,江西籍25人(表1),仅次于湖南籍的53人,位列第二,其中不少人担任主要负责职务。如许德珩就当选编辑员,张国焘任总务股干事,段锡朋任评议部部长。此外,该社还有大量的赣籍社员,如胡致、吕日奎、张广鸿、余芾堂、刘正经、陈剑翛、萧赣、游嘉德、谢馥南、陈泮藻、陈颖春、龙石强、曹天颐、于檉培、刘克俊、汤润、邹怀葛、龙沐仁、钟灵秀、孙镜亚、杨传荃等[8](pp9-14)。这些社员大多通过旅京江西同乡会等乡谊纽带[9],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

表1 国民杂志社社员籍贯统计(5)统计自《国民杂志社社员名单》,少数人物籍贯信息暂缺。《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14页。
此外,《国民》杂志社具有较为鲜明的针砭时政、反帝爱国色彩,这虽是时代形势使然,但也离不开该社赣籍负责人的思想导向作用。和《新潮》主要从文学改革入手、反对谈论政治不同,《国民》杂志主张公开谈论政治,刊登大量进步政论文章。许德珩于1919年初发表《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一文,反思辛亥以来的政治局势、国民态度、学人风气,对“夫学问所以为己也,求学问所以为国也,今乃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大加抨击,旗帜鲜明地主张:“本其爱己之心以爱国,本其爱国之心以爱世界、爱人类、爱公理、爱和平,务求其所以屈服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屈服之道。”[10]由于办刊理念相距甚远,许德珩处处求与《新潮》立异,甚至在得知《新潮》推崇白话文后,主张使用文言发表文章[11](p34)。这一办报策略看似极端,却恰恰出于以许德珩为代表的赣籍青年的爱国热忱,也使《国民》杂志影响日益扩大,为五四运动准备更为充分的舆论基础。
赣籍青年反对纯粹的书斋之学,在具体行动中既沉稳克制,又能灵活应变。五四前夕,邓中夏、张国焘等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秉持“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宗旨,吸引了不少上述赣籍积极分子,如许德珩、陈宝锷、刘正经、罗运磷、陈泮藻等。他们通过街头讲演,鼓舞民众爱国救亡的情绪。以许德珩为例,无论是五四前的联络布置,还是五四游行前夜书写宣言、制作标语,均可见其心细如发之一面。但他同样能在情境需要时,发挥过人的演说能力。有人称:“当一个案子难于通过时,他(许德珩)登台演说,能泪如雨下,颇具煽动性,这样,一个案子十有八九可以通过。”[12]五四集会前夜,他清醒地认识到学生行动的多重意义,“对外要表示民气,对内要引起社会一般人注意”[13](p303),兼顾顺应情势与主动作为。而他作为学生游行的首要积极分子遭到逮捕,在面对京师地方检查厅的审问时,又能够应对自若、讲求斗争策略,声言游行不过出于同学们“不谋而合”的集体情绪[13](p304),置对方于道德不利之地位。
段锡朋的人格形象则更为生动,罗家伦回忆称,段平时其貌不扬,“总是穿一件蓝竹布大衫,扇一把大折扇,开口就是我们庐陵欧阳公的文章气节”[14],但在当选为学联会负责人后,他又展现出处事灵敏、讲求策略的一面,不仅“登台言说条理清晰,富有感染力”[12],且与同乡陈剑修、许德珩配合紧密,善于引导和运用民众情绪,将五四运动集体氛围推向高潮。5月底,段锡朋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南下联络各地学生。时在武汉的曾省斋就对其演讲能力印象颇深,提及当时三位南下代表(留日学生代表王次甫、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湖南学生代表徐庆誉)中,“段君的一席话,尤为慷慨激昂,淋漓兴奋,激荡爱国情绪激荡至最高潮”[15](pp90-91)。赣籍进步青年的突出表现既与时代大环境有关,也离不开对地方历史文化记忆的接续,这种地方历史感和自觉的责任意识补充和丰富了江西五四学人行动伦理的思想资源,是省籍群体自我塑造的潜在观念之一。
地方上的五四运动中,赣籍青年同样表现不俗。五四运动在江西得到迅速热烈的响应,彰显出进步学生群体对直接参与五四爱国运动、投身实践的极大热情。5月6日,北京学生罢课消息传到九江,九江各校当即联名致电政府,声援北京学生[16](pp1-2),并积极联络商界、政界等力量,在初期增强自身的社会支持。不少就读这些地区的学生或通过地方报纸编纂发行,或利用寒暑假时间返乡宣传,进一步传播爱国进步思潮。江西其他地区如萍乡、上饶、横峰等地,也涌现出大批进步青年积极参与这一运动。
江西五四运动持续时间较长,表现出极强的韧劲。同年12月,福建省发生日本侨民持械伤害中国学生之“闽案”,江西地区再次发起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声援福建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善后和约方案。直至翌年5月“五四”“五七”等纪念日时,江西学生运动依然热情不减,有关“赣人爱国热之耐久”[17]的报道频见报端,可见学界行动的成绩为全国所瞩目。
学生讲求运动的策略方法,维持良好秩序,从而减小社会阻力,这是其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五四讯息传来后,南昌、九江城内多所学校就开始了相互联络,多数进步青年对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和约定抱有相当尊重,认为“须学生会停止罢课宣言到校,方可上课,盖不可少之手续也”[18](1919年12月13日)。罢工罢市时,学生与商界、工人取得较好配合[19],青年学生行动力、精神面貌给世人留下了良好印象,“学生秩序整齐、举动文明,赣人称颂,报纸上一则曰爱国,一则热忱,再则曰可敬可爱”[18](1919年5月13日)。
不同的社会格局、地域文化传统,对其他地区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同影响,此点主要体现在来自不同文化地理大区青年的行为特质差异上。
赣籍青年与同一文化地理大区(6)胡兆量先生等将中国划分为10个文化地理区,分别为华北文化区、东北内蒙古文化区、华东华中文化区、华南文化区、西南文化区、西北文化区、新疆文化区、藏文化区、港澳文化区、台湾文化区,其中华东华中文化区包括吴越、上海、安徽、江西、两湖地区。参见胡兆量《中国地学通鉴(文化地理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70-466页。内部的其他省区有很大的相似性,不过与吴越地区文化性格也存在些微差异。以浙江籍的罗家伦为例,其虽然在五四期间积极参与了学生游行及救助被捕学生等活动,但很快地对“群众运动”产生深刻的怀疑,认为首要应养成“专门学者”[20]。其徘徊于学术与政治、救亡与启蒙之间,带有江浙传统文人的气质,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调和折衷色彩。同为江浙籍的毛子水虽然参与游行,但“觉得没什么意思,天也晚了就回学校宿舍了”,对于学生会决定集体罢课,他也并不赞成[15](p6)。1919年休学在苏州家中的北大学生顾颉刚尚纠缠于新旧家庭伦理之间,对北京的五四运动并未记载,且因《新潮》刊发信件需请《新青年》审查核定,而大感不满,认为“自当本期良心之觉悟而发表之”[21](第1卷,p45),折射出其注重个体主观自由、力主调和论的立场(7)顾颉刚在日记中称赞章士钊认为“竞争之结果,必归调和”的观点“若在吾心中发出”。参见《顾颉刚日记》,1919年1月11日,台北:联经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这与江西籍学生的性格特质形成一定反差,在一定意义上也揭示出地域间学风、士风与文化心理的差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进步学生与地域文化的纽带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并无高下区分之意,各地五四运动的发展也与政局、代际等各种因素的紧密互动,展现多元样态。
二、赣籍五四青年之养成
赣籍进步青年是五四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且具有特质的群体力量。他们如何选择参与五四,五四又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具有何种意义?这值得结合地域视野进一步追问和探讨。
布迪厄曾指出,行动者身上体现出的惯习或性情倾向(disposition),受相应“社会结构在身体层面积淀”影响,是“生成策略的原则”,这种原则“能使行动者应付各种未被预见、变动不居的情境”[22](p19)。由此,笔者选择从年龄、出生地、学校院系、五四时期主要活动、人生归宿几个方面,简要梳理了这批赣籍青年的身份特征及个体生命史。
笔者共搜集33位赣籍人物,年龄跨度为1890-1904年(除1885年出生一人),尤其集中于1896-1897两年间,达11人(8)样本总数为33人,其中10人出生年数据暂缺,1896-1897两年间出生人数近一半。。与老辈学人不同,这批青年虽亦接受过传统教育,但时间不长,较早受到新式教育的影响。他们在京参与五四运动时多为23-24岁左右,正值人生观、价值观初步形成,最具青春热情的年龄段,他们成为五四时代富有生气的主力军之一,似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赣籍青年多在二十岁左右才来到北京,他们在家乡的童年、少年时期就已接触到近代化因素,而这也是这些五四青年生命史的前置场域。
这些进步青年出生地的分布并不均衡。江西省位居内陆,相对闭塞、变迁缓慢,但近代以来,部分地区如九江、南昌,因区位因素相对优越,较早开始修筑铁路、引入近代企业,从而走在近代化的前列。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中,以李烈钧为首的革命党人驻守九江、南昌一带,“民主共和”话语逐渐深入人心,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这些有助于该区域近代教育的发展。
来自南昌、九江地区的进步青年有8名。其中,许德珩的经历颇具代表性,他曾在九江中学堂受到留日教员引导,获得初步的思想启蒙;早期在主张讨袁的李烈钧部就职、亲见孙中山等人的经历,更对其进步观念产生了极大影响[11](p9-10)。
另有12名青年来自以萍乡、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地区。历史上的庐陵地区,社会经济相对发达,人文传统颇为深厚,有开一代文风的欧阳修,还有忠鲠不屈、气节刚烈的文天祥。明清以来,兼重自身修炼与经世化俗的“江右王学”的盛行,都成为这一地域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23](p156、p213)。近代以来,赣西地区虽不及九江、南昌发展之速,但由于水路便利,手工业、商业较为发达,随着铁矿开发、铁路修建,近代化因素也日渐渗入。在湘赣交界处,官府统治力薄弱,部分地区械斗成风、地方势力强大,在清末民初更演化为若干底层起义。传统士风与初兴新学并存、刚烈气节却与反叛精神结合,成为赣西社会多元而又充满张力的地域特征。
五四运动的效果与演说的氛围、乡音等亦密切相关[24]。由于这两大块片区地处南北交通要冲、风气开通较早,九江地区主要使用江淮官话,赣西地区的赣语亦多受北方方言的影响[25](pp11-12),来自这里的进步青年在北京五四场域中,不会因为乡音而感到较大困扰,叠加其性格和行动能力,往往拥有较强的公众言说能力,避免了不少来自南方地区学生群因乡音浓重而难以进行街头演说、甚至与同侪发生矛盾等问题。
相较而言,来自江西其他地区如赣中、赣南的五四青年相对较少,仅就出生地而论,相对封闭落后、以山区为主的赣南虽有8人,但考察他们的经历,其中大部分人因家境尚可,较早赴南昌等地考学,最终来到北大,案例的个体性较强,与本省内的亚区文化直接关联较弱。总体而言,赴京五四赣籍青年以九江、南昌地区、赣西地区为主,在诠释相关人物行为特征上更具代表性。
江西地方上参与五四运动学生代表的身份和行为特征与之亦有颇多共性,以36名江西本省参与五四运动的进步青年为代表,可以进一步探讨地域因素的影响。
这36名青年的年龄跨度约为1890-1905年,尤以1899-1902年为多,达13人(9)样本总数为36人,其中9人出生年数据暂缺,1899-1902三年间出生人数近一半。,虽然与在京赣籍青年同为“五四”一代,但平均年轻3-4岁,他们响应五四的活动场域主要在中等学校,如省立一师、省立二中等。
出生地方面,来自南昌、九江地区的人数同样最多,达13人,再次印证江西内部的地域差异。这一人群的主要变化是赣东地区人数的增加,共9人,而前批33人中仅有1人。这与原为广信府的赣东地区经济发展、文教有相当基础有关,也离不开当地位居平原、临近江浙及南昌所造就的开放区位。清修《江西通志·舆地略》记载,广信“自永嘉东迁,衣冠避地,风气渐开”[26](p265)。大部分年轻学生可承受赴南昌就读中学的奔波和花费,少数出身贫寒者如方志敏、邵式平等,也获益于开通区位及相对发达的地方基础教育,较早受到新思潮影响,其中不少选择以家乡作为此后革命活动的基点。来自这一地区的进步青年来到南昌、九江等地就读及参与学生运动,日益拓展其横向联结,也为进一步加入革命性社团组织做了铺垫[27](pp202-203),由此更印证了基于地缘因素的影响。
三、中心与边缘:赣籍五四青年的内部分异
通过聚焦五四时期赣籍进步青年群体,有助于勾连起学生群体的横向互动,亦能进一步透视中心与边缘的异同。就赣籍青年在五四运动中扮演角色和发挥作用来看,主要可分为组织召集型学生领袖、自省践履型进步青年两种类型;而北京与江西的空间分异,学生群体内部学生领袖与来自基层乡镇的理想青年的行为选择、人生走向分异,亦构成了“中心-边缘”之多重写照。
组织召集型学生领袖指五四时期已在学生组织中担任较高职务者。在北京参与五四的赣籍进步学生代表中,许德珩、张国焘、段锡朋、罗隆基等发挥了骨干作用,共同推动了五四学生集体游行的发生与后续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如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九江,早年在家乡参与讨袁起义,具备了一定的进步革命观念。1916年来到北大后,许德珩深受蔡元培、李大钊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与日益危急的国际形势的刺激,于1918年组织发起“学生救国会”、主持筹办《国民》杂志,并于该年暑期与部分代表南下联络各地爱国学生团体,为五四运动奠定组织、宣传的初步基础。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界群情激奋。3日晚,许德珩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以《国民》杂志社的名义,主持召开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北大全体学生大会,并被推举连夜起草反帝爱国宣言。次日反帝爱国学生游行中,许德珩更是主要领导者之一,并因此被捕。获释后,他作为北大代表参加“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继续开展对军阀政府的抗争,再次前往天津、上海等地,发动工商业界声援学生运动[11](pp36-37、pp63-69)。可以说,许德珩的宣传组织工作对于五四运动的展开发挥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
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的张国焘,不仅参与《国民》杂志的筹办,同时在李大钊影响下,与邓中夏、罗章龙等组织平民教育会,初步探索“社会革命”的理想。五四运动中,张国焘作为北大学生会干事、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组织若干讲演团和讲演小分队,宣传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的黑暗罪行[28](pp46-53)。其出色的讲演组织能力以及宣传鼓动的激情,对五四运动中集体情感之沸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段锡朋1896年生于江西永新,目前所见与其直接相关的一手史料并不多,但通过他人的回忆,亦可勾勒他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据罗家伦描述,当学生游行被捕系列事件扩大,形势严重,众议纷纭时,“书诒(即段锡朋,引者注)挺身而出,以沉毅、勇敢而热忱的姿态,突现于全体北大同学和整个北京专科以上学生之前”[29](pp66-67),其沉稳与随机应变的性格给时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段锡朋主持北京学联会,向政府提出全体学生自行检举呈文,带领全体学生上书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提出“拒签合约,惩办国贼,力挽蔡、傅,拒绝田应璜”等六个条件,不仅赢得民众同情,而且表达学生爱国决心。5月底他继续南下串联,发动工商界,并任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会长[12]。对于五四游行之后稳定事态、扩大影响起到重要作用。
江西安福人罗隆基则是清华学校的五四运动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后,罗隆基密切关注进步思潮,一度对马列主义很感兴趣,“经常去北京大学听文科学长陈独秀的演说”,甚至“曾经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一文抄写并张贴在学校的走廊上,被人戏称为‘罗疯子’”[30]。五四前夜,他号召清华同学响应爱国示威游行,积极参与北京学联和清华讲演团。他在声援北大同学继续斗争的活动上表现尤为突出,也为北大主导的反帝爱国运动注入兄弟院校的支持。
在江西当地,学生领袖如傅兢仁、钟祥鹭、丁伟、熊式一、李凌鹤、邵祖平、熊韫华、刘子池等也在号召和运筹方面展现出较出色的能力。运动爆发后,这些积极分子借助在学生群体中已有影响,迅速起到组织召集作用。5月18日,丁伟、钟祥鹭等组织学生游行,并带头要求面见议会长、陈诉学生要求[31],临时负责江西学生联合会具体事务,保证与京沪地区的同步行动。5月25日,南昌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邵祖平、卢任华当选正副干事长,丁伟为正评议长,熊式一、李凌鹤、刘子池则分别任南昌学联省立一中代表、评议员、交际部长、编辑部长等[32](p90),这不仅使南昌地区五四爱国运动的开展逐渐正规化,同时也带动全省其他地方学生联合会的发展,推动学界联合的步伐。此外,这些学生领袖都有较强的演说和鼓动能力,这对号召广大学生、表达学生诉求而言至关重要。南昌学联开会时,钟祥鹭等学生代表面对二百余众发表演说,报告上海抵货情况、痛诋玷辱国体之行为,“类皆痛快淋漓”[33]。除组织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外,李凌鹤等学生代表还积极组织办报,将标语传单寄回家乡[34](p7),使反帝爱国情绪进一步散播开来。
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些学生代表也在接洽各地学界、社会各界中表现得相当活跃。一方面,李凌鹤代表南昌学联,注重与九江学界的互联互通[35],另一方面,江西学界也时刻关注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及全国学联的成立发展动态,讨论会上众人均认识到:“吾赣至沪交通极便,届时如无代表出席,岂不赧然有愧?”[36]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责任。卢任华、熊韫华、李凌鹤等也被选为参会代表赴沪奔走[37][38]。在反对部分巨商偷贩米谷出口东洋的斗争中,傅兢仁、刘子池、李凌鹤作为学界代表,多次与商会接洽,并督促其他各界履责参与[39][40],促使学界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一股蓬勃力量。部分学生领袖在这一过程中面临开除学籍、家庭阻挠等威胁(10)在1920年5月领导罢课风潮中,李凌鹤、傅兢仁等十名学生被开除(《民国日报》,1920年5月15日);丁伟则受其叔强制,离开南昌,返校无期,参见《袁玉冰日记》(手稿)(原名《中华民国八年学校日记》,1919年12月26日。,其付诸的努力值得重视肯定。
自省践履型进步青年则指五四时期尚未成为既有学生组织的领袖角色,但富有自省意识,且在积极响应时局、践行学生运动中进一步求索救国救民方案的学生群体。
这主要表现为在江西本地参与运动的进步青年,如袁玉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袁玉冰在1919年留下的日记手稿,成为观察与其类似的进步青年彼时心态的宝贵材料。从日记可见,他一直有读报习惯,密切关注时局变化,5月6日他即得知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及北京学界运动讯息[18](1919年5月6、7、8日),国耻招致巨大的悲愤情绪,也促使其将个体与整体情感联系起来,投身学生领袖组织的大量活动之中。五四期间,袁玉冰担任学生会文牍、游行警告团纠察员等职务,参与请愿游行、抗议议员秘密加薪、集体罢课、筹建实业工厂、维持米禁、组织演说团等行动[18](1919年5月12、31日,6月6、14日,11月23日,12月6日)。寒暑假期间,他返回泰和老家,传播北京、日本及南昌等处学界风潮[18](1919年7月9日),扮演沟通省城与边缘地区的中介角色,使五四新风吹进相对闭塞的江西乡村。其时尚在赣东北读书的方志敏亦回忆称,当爱国运动波及到弋阳时,“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其“废寝忘食的去做”抵制日货、游行讲演等活动,甚至“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41](p14)。邵式平也强调五四对人的冲击和唤醒作用,“当我做学生的时候,真是走到哪里就恨到哪里。在家乡,则恨恶霸地主豪绅;在县城,则痛恨贪官污吏,恨和他们一道害国殃民的遗老遗少;在南昌,则痛恨军阀官僚……因此‘五四’运动一来,我便成了激烈的爱国主义者”[42](p2)。邵式平与方志敏同在弋阳高小( 前身为叠山书院) 读书时,情同手足,志同道合,共创“弋阳九区青年社”,后同入“江西改造社”[43](p58),五四期间其与方志敏共同作为弋阳高小学生运动领头人,大大拓展江西五四运动的广度。
如果将五四运动作为这些青年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进一步将之放置在长时段的生命历程中,在江西本地参与五四运动的青年与在京赣籍群体人生归宿也有所不同。
在京进步学生代表多投身教育研究事业,如许德珩、张芷宾、陈宝锷、王造时等,少数如张国焘走向背叛革命的歧路。地方进步学生群体中,家境一般的基层青年大多投身革命,甚至为之付出生命,如刘肩三、邹秀峰、罗石冰、袁玉冰等。反倒是五四时期已身为学生会领袖者在此后热情渐消,他们或转向学院式研究道路,如钟祥鹭、李凌鹤、石廷瑜等;或泯然众人,如丁伟;或走向共产革命的对立面,如涂振农、刘子池等。可能有以下三方面解释:
其一,赴京五四赣籍青年、在赣学生领袖大多家境较好,不少在五四运动结束后选择赴英美等地留学,如在京的段锡朋、刘正经、陈泮藻,南昌地区的熊式一、李凌鹤、熊韫华等,对于此后的国民革命相对隔膜。与之不同的是,那些家境一般甚至堪称贫寒的五四青年,如方志敏、黄道、罗石冰等,正逢投身国内革命的机遇。以南昌为中心的赣北、赣东地区与湖南、上海紧密相连,也是初期工农运动开展、革命力量与军阀拉锯的前线阵地[45],身处当地的五四青年不能不受到影响。
其二,学生领袖通过先赋条件和后天政治与教育经历的累积,在社会系统中占据优位,一定程度上影响其行动选择。在京赣籍青年虽有因地缘结合的组织和行动,但并未形成宗旨鲜明的行动团体;江西本地学生领袖也因承袭既有的组织架构和行为惯性,缺乏变革的动力。如南昌学联主席丁伟多次运动同学投票,并借助与省立二中校长的亲缘关系,谋求连续当选,学生领袖群体呈现出相对封闭的倾向。既有学生领袖的话语权力不能不说已引起来自基层乡镇却相当有志气理想的青年之不满,如袁玉冰即对学生领袖拉票、甚至与政客勾结的行径颇为疑虑[18](1919年3月13日、12月29日)。他们则将五四激情与此后的革命理想相结合,较早组建旗帜鲜明地以彻底改造社会为诉求的团体,如江西“改造社”,在改造社的影响下,南昌市及全省各地的进步学生纷纷创办多种进步社团[44](p42),与此后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相结合,走上革命之路。
其三,在京赣籍青年参与五四的场域主要为大学,他们所接触的思潮、群体也更为广泛。而以“爱国救亡”这一总体诉求为目标的五四运动,本就是一场统合不同取向青年的事件,在如此大规模的青年学子集体情感相互激荡的环境中,他们参与五四的选择本身,并不一定意味对社会改造激进方案的认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来自地方市镇、注重反省践履的群体,在行动和理想的选择上反而更为慎重,为响应五四运动,数人只手掀起波澜,更需付出切身的努力,而这一过程本身在思想上的震颤也应相当剧烈,他们对五四精神的诠释方是从心灵改造出发、延续到此后的现实实践之上。
由此可知,在五四大潮中积极融入集体固然重要,但深入内心的反省和落脚到行动的变革,更是“五四”精神生发出长远和不竭动力的关键。如来自基层的江西本地进步青年袁玉冰,既始终重视“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的修身传统,带动了一批换阅“日谱”[46](p182、p196)、互相砥砺的有志青年,通过刀刃向内,经历真正触及心灵的变革;又在面对学界与社会各界联合失败、学界内部领袖分化、筹办实业工厂遭遇顿挫的现实时,投身组建新的行动团体[18](1921年12月11日)。其在五四集体情感沸腾的大环境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自省意识,其审慎态度正是出于对人生价值、理想抉择的高度尊重。这一点在同样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五四进步青年,如毛泽东、恽代英那里,均得到呼应。
四、结语
江西的地域历史文化是涵养赣籍进步青年性格作风的独特资源之一,江右王学、庐陵文风、民族气节等精神品性与众多赣籍进步青年注重直接行动、沉稳克制而又灵活机变的特点不无关联。而这种对于地域的认识并非向壁虚造,作为乡土社会的中国,地缘、血缘纽带向来为人们所重,尤其是近代以来,传统的乡土认同扩充至省域认同、与社会改造理想紧密相连,虽然不乏地域分歧、甚至刻板印象(11)如袁玉冰即记录其老师认为“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及浙江之西南等处的人,都是诚实”,而认为江西与江浙有一定不同(《袁玉冰日记》,1921年5月15日)。,但更证明地域文化意识已然是时人普遍思维架构之一,以地域历史传统自任、振发先贤精神也反过来形塑了赣籍青年学生的精神世界。
进一步深入赣籍群体内部时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份特征和人生走向亦不尽相同。“五四”作为一个时代分界点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进步青年在因应时势和主动作为中走上了历史前台,在追求理想的热烈情绪、反叛强权传统的行动上已彰显出与他们老师辈不同的特质。但是在众声喧哗的近代中国社会,影响五四青年选择的因素毕竟太多,“五四”在青年个体生命史中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响需要具体对待。
五四运动中赣籍进步青年曾经做出的努力值得铭记,他们作为故土远行人,地域文化和个体生命前史,对于他们的性格倾向和后来的行动选择不乏影响。而近代以来民族救亡情感的高涨、五四时代总体社会文化氛围变革的洗礼,是他们参与五四运动更为直接的重要因素。总体言之,赣籍青年也是五四进步青年的缩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