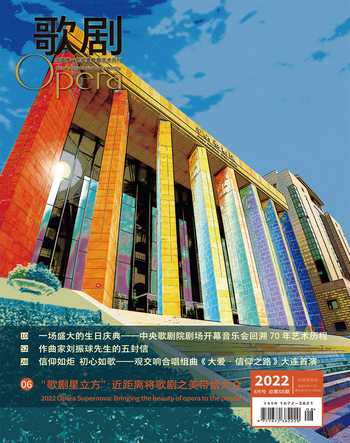论西洋歌剧的民族性(14):回顾与借鉴(下)
黄奇石
(接上期)
(六)中国民族歌剧的成败得失:
欧洲之外,就世界大范围内尤其是亚洲来看,中国歌剧起步并不算晚,大约在20世纪初叶(一二十年代之交)就进入萌发期,与美国音乐剧产生的时间几乎是大体相同的。
之后,稚嫩的中國“歌剧之花”经历了三四十年代的成长期,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了一场激烈的“土洋之争”,“东风压倒了西风”。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民族新歌剧进入了繁荣期。
新中国成立后至今的70年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歌剧也一直在发展变化着。其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与近十年——
前三十年中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民族新歌剧的“繁荣期”(其中包括“文革”十年的“荒芜”);
后三十年中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新世纪的头十年为歌剧的“多元期”;
近十年民族歌剧再度回归,可视为“复兴期”。
1.“繁荣期”的得与失:
“繁荣期”民族歌剧最突出的特征是:革命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故又称为“红色歌剧”。在1950年代中期“土洋之争”中,1956年毛主席《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阐明了“洋为中用”的原则:用西方的方法,创造中国自己的艺术。一锤定音,促进民族新歌剧进入以《白毛女》为典范的“繁荣期”(又称“黄金时代”)。
“繁荣期”的不足是:
其一,“土派”占优,“洋派”噤声,由此失去了向西洋歌剧更深入学习的可能;
其二,“土派”占优,又产生歌剧“戏曲化”的偏向。歌剧要学习戏曲,但不能“戏曲化”。否则,变成了戏曲,也就失去了歌剧本身的特质。
同样,歌剧创作借鉴戏曲的“板腔体”,也不能“生搬硬套”,而须“化开化用”,如《白毛女》中的《恨是高山仇是海》、《洪湖赤卫队》中的《娘的眼泪似水淌》,都是“化用”“板腔体”的典范。否则,所写的音乐就会显得陈旧,失去新歌剧比旧戏曲的最主要的特点与优势——“新”。
更何况不少民族歌剧并不釆用“板腔体”手法,如《草原之歌》《刘三姐》,采用的是藏、壮族民歌作为音乐素材(前者多用西洋“咏叹调”等手法,后者则用的是“节歌体”)。
2.“多元期”的得与失:
按照“百花齐放”的方针,歌剧从“一元”走向“多元”是好事,是有利于歌剧艺术的繁盛的。
1980年代,“歌剧之花”从“文革”十年的“一片荒芜”中挣扎出来,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复苏局面。歌剧界不少人甚至乐观地认为,歌剧复兴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然而,在整个社会“崇洋”之风盛行时,“土”的“一元”已日见式微,“洋”的“一元”占了上风。又由于“洋腔洋调”不受老百姓的欢迎,歌剧复苏的风光不再。到了1990年代,歌剧便迅速跌入低谷。
“多元期”的不足与教训是:抛弃了《白毛女》为代表的民族新歌剧所开创的道路,随风起舞,又将已走向衰落的西洋古典歌剧奉为“圭臬”。与此同时,对美国音乐剧趋之若鹜、群起效仿。代表性的论调是某教授最遭歌剧前辈们诟病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让开《白毛女》等的“大路”,占领西洋大歌剧与美国音乐剧这“两厢”)。
笔者对此“高论”是十分不以为然的。当时曾应《舞台艺术》杂志之约,撰有《中国歌剧之梦》一长文,文末的结论是:“要想在中国复兴西方已经走向衰落的古典歌剧,就像要在西方复兴中国同样走向衰微的京、昆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方歌剧之梦。”(此文后某报刊连载过,应者寥寥。)
正因为“多元期”并未将中国歌剧带出困境,反而使之跌入低谷,人们又开始反思,想找出其中症结与出路。近十年来,尤其是2015年文化部下大力气复排《白毛女》以来,情况迅速改观,民族歌剧又再次强势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70年歌剧发展的跌宕起伏,似乎走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一个辩证发展的全过程。历史辩证法是无情的,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真令人感慨系之。
关于民族歌剧的重新回归,因刚起了个头,众多新作能否传世甚至成为“经典”,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扭转了方向,“洋腔洋调”势头受到抑制,使歌剧重新朝着“民族化”的正路上走了。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现在普遍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这就是毛主席当年批评过的“好吹不好批”。新作还没怎么样呢,便吹得天花乱坠。为何如此?
说好听的话,上下都高兴;要是批评的,便会得罪一大片人。于是,不少剧评,通篇除了被人称为“廉价的吹捧”外,实在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文字,更差的甚至极尽吹捧之能事,“把肉麻当有趣”。自我感觉良好,却是令人厌恶。
这里,我想借毛主席的话对当事者提醒一二:
其一,“实事求是”。好与不好,“一分为二”。要明白:多看到不足,不足才会克服;少吹嘘成就,成就依然存在。一出戏首演,大都只是半成品。要不然,怎会有“十年磨一戏”之说?
其二,“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凡事不可走极端,古训“过犹不及”是有道理的。走极端,就容易片面,好像一提“民族歌剧”,就只是某单一品种,就只能“一枝独秀”。如此一来,岂不有违“百花齐放”的方针?
其实,“民族歌剧”并不是狭窄的概念,而是宽泛的、兼容的。它如同大江大河,汇聚万水千山;它如同大洋大海,只有“海纳百川”,方能“有容乃大”。
明于此,就知道所谓的“民族歌剧”只是区别于外国歌剧,实际上就是“中国歌剧”。我们之所以强调其“民族性”与“民族特色”,也只是为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与外国歌剧相区别而已。况且,中国本身就有56个民族、56种花,岂能是“一枝独秀”而非“百花齐放”的?
除此之外,抓民族歌剧需注意之处还有不少,如:歌剧是艺术而不是新闻、民族化不等于戏曲化、写革命写英雄切忌“假大空”、歌剧舞美讲究写意简朴而切忌奢华(豪华舞美极易变成“豪华垃圾”)等等。诸多问题,均不可掉以轻心。
这让我想起剧作家、词作家“乔老爷”(乔羽)在其文集的“题辞”写道:“不为积习所弊,不为时尚所惑。”上述种种正相反,既有“为积习所弊”,也有“为时尚所惑”。
歌剧界的诸多毛病,很多年前,以贺敬之同志为代表的歌剧老前辈们就大声疾呼过,如批评“盲目崇洋,妄自菲薄”,如提倡“歌剧要走民族化道路”,如阐明“新歌剧与外国歌剧比,它是中国的;与旧戏曲比,它是新的”等等。
然而,时至今日,以“洋歌剧”为标准的“崇洋”之风依然甚盛;用“板腔体”作为民族歌剧的“不二法门”仍大行其道;名为“艺术”实为“捞钱”的恶习依然猖獗……
其中,既有大肆捞钱的“聪明人”,也有不明事理的“糊涂人”。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不是“明白人”。人称“明白人不用说就明白,糊涂人说了也不明白”。板桥先生名言:“难得糊涂”。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当今歌剧界,既有与板桥先生一样“装糊涂的”,也有不少“当事者迷”,是揣着糊涂装明白。明白邪?糊涂邪?天晓得。
但说这些,恐怕也都是既明白又糊涂的“多余的话”。还是回到正题。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歌剧发展的成败得失,应得出怎样的结论?结论有正、反两点:
一、成与得都在于“民族化”;
二、败与失都在于“西洋化”。
这个结论,也许有人会不赞成。如果回顾一下中国歌剧近百年的发展脉络,就能看得更加清楚,就不会认为上述结论下得过于武断了。
【附录】中国歌剧的源头及分期小议
中国是有几千年歌舞传统的国度,在东方文化圈,唐宋以来直到近代,一直处于中心位置。《尚书》中所记载的尧、舜、禹时代祭神时,“拊石而歌”“百兽率舞”,便是上古的歌舞。《诗经》中的绝大多数篇章“大小雅”“十五国风”也大都是“载歌载舞”的。
这种歌舞传统,一路沿袭下来,到了战国末期,《楚辞》中屈原《九歌》已经就加入了戏剧的因素,尤其像《湘君》《湘夫人》与《山鬼》等篇,说它是湘楚古风的“歌舞剧”也不为过。由此,我认为,先秦时代中国的音乐戏剧——歌舞剧就产生了(当然,这一判断还需要更多的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这“双重证据”加以证明)。
然而,自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将戏曲起步定在唐末的“参军戏”之后,中国音乐戏剧的上限至多也只上溯到唐宋了。狭义的音乐戏剧——“戏曲”的起源无妨可以这样界定,而广义的音乐戏剧——“歌舞剧”则需要再上推一两千年以上。几乎可以说,它与古希腊悲剧产生的时代是大致相同的。不同的是,古希腊人偏向于“说与唱”(歌队合唱),古先秦人偏向于“歌与舞”。
断言中国先秦没有音乐戏剧,不像西方很早就有希腊悲剧,这如同历来文史界一直认为中国上古没有“史诗”,只有像《诗经》中搜集的那样短小的诗篇一样,都是并不可靠的旧说。后一旧说,一直到产生于神农架的长篇史诗《黑暗传》被发现,才打破了。我希望,王国维关于中国古典音乐戏剧产生于唐宋之际的旧说,也会有更充分的证据将它打破。(这不怪王国维,他说的只是“戏曲”。)
就广义的音乐戏剧而言,上古歌舞剧滥觞也好,唐宋戏曲雏形也罢,我认为其源头都出自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华夏先民们的创造。两大江河文化是从远古、上古至中近古一脉相承的文化源头。
那么,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音乐戏剧——中国歌剧,其源头又在何处?
歌剧究竟是“舶来品”或是“土特产”?过去,大都认为是舶来品,因为中国历来只有戏曲并无歌剧。歌剧是从西方引进的。后来,开始有异议了,认为中国民族歌剧特别是以《白毛女》为代表的“红色歌剧”根本不是“洋面孔”而是“土面孔”,怎会是外来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国的,完全是“土特产”。(最近中央歌剧院一位中戏毕业的老导演说,他坚决反对歌剧是“舶来品”的说法,有充足的证据可破除此说。近来还有年轻一代的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民族歌剧就是从歌舞剧演变而来的,其渊源久远。)
“舶来品”有不好的(如鸦片),也有好的(如马列主义);“土特产”也有不好的(如“小脚”“长辫”等),也有好的(如中医、武术、烹饪等)。思想与文化艺术领域对“舶来品”的模仿与效法,搞出来的都是“假洋货”,包括“假马列主义”,为害不浅。“洋为中用”,对“舶来品”加以消化,化为中国的,方为正道,就像毛主席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一样。对于西洋歌剧这种“舶来品”,也应作如是观。
至于所谓歌剧的“源头”,也需依事实方能说清楚。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歌剧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品种的,不是“一元”而是“多元”。那么,其源头恐怕也不会是单一的。
20世纪上半叶,从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到《扬子江暴风雨》,从沦陷区上海的《孟姜女》到大后方重庆的《秋子》,再到革命圣地延安的《白毛女》,从内容到形式都各不相同、差异很大。其中有偏“洋”的,有偏“土”的;有偏流行歌的,有偏民歌与戏曲的。
由这种实际而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什么?歌剧的源头应是“多元”的,主要是“洋的”与“土的”两大源头。偏“洋”的歌剧源头自然是“洋”的,偏“土”的歌剧源头自然是“土”的。这样区分,我想比较符合实际,估计连作者们都不会反对。
源頭已定,那么,从其近百年流变的脉络,又该如何划分其萌芽期、成长期、繁荣期呢?
早在1920年代前一两年,黎锦晖的从“学堂乐歌”脱胎出来的儿童歌舞剧就萌生了。一般都将它当作中国歌剧的萌芽。萌芽自然是幼稚的。
如果说,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歌剧的萌芽期,1930年代则是歌剧的成长期。
1930年代一部关键性的歌剧是田汉、聂耳的《扬子江暴风雨》,其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与“五四”以来革命歌曲风格的音乐已树立了中国现代歌剧的主要模式,并初步开拓出“红色歌剧”的主流形态。其中数首歌曲如《大路歌》,沉郁、坚韧、不屈不挠,唱出了民族的心声,一出来便广为传唱。然而,该剧却常被某些论者贬为“话剧加唱”而不屑一顾。其实,它和黎锦晖幼稚的儿童歌舞剧比起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大踏步前进了。
二三十年代被忽略的,还有第一次大革命时广大农村产生的小歌舞剧。当时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全国各地打倒土豪劣绅的小歌舞剧产生不少。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各红色根据地所产生的小型“红色歌舞剧”数量更多,如井冈山就有不少。(以上两种,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至今搜集到的甚少。)
这里须要加以区分的是,抗战造成的“根据地”“沦陷区”与“大后方”的三区分立的局面,促使“成长期”的歌剧也在这三个区域各自艰难地成长着,但占主流的是根据地的“红色歌剧”。其他两个区域也有歌剧,但都是支流,数量有限,质量也不高。
随着革命的发展与抗战的胜利,到了1940年代初,毛主席的延安“讲话”不仅掀起了延安文艺运动,开创了文艺的新时代,具有划开新、旧文艺的划时代意义。“讲话”也极大推动“成长期”中的中国歌剧产生质变。从延安秧歌运动发展出来的歌剧“奇迹”——伟大的新歌剧《白毛女》诞生了。它一出来,便成为“经典”,宣告中国歌剧走向成熟,即将进入“繁荣期”。“繁荣期”出现在新中国开国之后。
从“萌芽期”到“成长期”,经过了二三十年;从“繁荣期”到“多元期”又经过了四五十年,再加上近十年的民族歌剧回归的“复兴期”,中国歌剧发展的脉络及其得失是清晰的。
三、歌剧的未来
我们回顾过去、针砭现状,都是为了开拓未来。实际上,人们在观察现实的同时,早已把希望的目光更多地转向未来了。
(一)是什么决定歌剧的未来?
这里要谈的,主要不是世界歌剧的未来,而是中国歌剧自己的未来。
“来者难巫”,连古人都知道未来是难以预测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谈“歌剧的未来”呢?
未来固然难以预料,也不等于绝对没有踪迹可循。这个“踪迹”不在未来,而在过去。当我们回顾了西洋古典歌剧400年的发展史,也许会明白其兴盛衰落的症结所在;当我们回顾了中国歌剧近100年的发展脉络,也许会明白其成败得失的根源所在。
这个“症结”与“根源”,简单一句话,就在于是否走自己的路、是否发展自己的民族歌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圈内”人士都能够看清这一点的,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而对过去的认识这种不一致,势必会影响到对歌剧未来的认识。因此,对此有必要加以阐明。
近三四十年来,有一种声音喊得很响:“和世界接轨”。反对的声音是有的,但似乎很弱,而且大都是现已老去的创造民族歌剧“黄金时代”的元老们。他们在世纪之交发表过不少呼唤民族歌剧的文章,批驳了否定《白毛女》道路的种种“奇谈怪论”,“其言也切”“其声也激”,被称为“世纪末的呐喊”。其中《红珊瑚》的作曲之一胡士平同志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要想与世界接轨,先要与中国的老百姓接轨”;“要想走向世界,先要走向中国”。
这个分歧,实际上就是“民族性”与“世界性”不同主张的歧见:主张“与世界接轨”者认为必须拿出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才行。这种作品当然需要“洋人”能接受、能欣赏,偏“土”的怎能办到?主张“先与老百姓接轨”者则首先要求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才行,“洋腔洋调,死路一条”。中国老百姓不接受,世界各国观众也未必看得上。
多年来有一句常被引用的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先不管这是不是鲁迅说的,只说此言是否具有真理的普遍性?
诺贝尔文学奖是最享有世界盛誉的吧?你只要翻开获奖评语,就会发现:有相当多的获奖作品的评语都把表现“民族生活”与“民族精神”作为评奖的重要理由。抛开评语中常有的偏见与谬论不谈,仅就“民族性”这个理由,就值得肯定与赞许。至少它从文学的角度,印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所具有的真理的普遍性。
文学如此,同属于文化艺术的歌剧会是例外吗?我们回顾西洋歌剧四百年的发展历史,似乎还没有找到例外。道理很简单,抽象的“世界性”是不存在的,“世界性”存在于“民族性”之中。
由此不難推断:歌剧的未来不在于“世界性”而在于“民族性”。
然而,对于“民族性”也必须有个比较全面、准确的看法,否则弄不好极容易滑到狭窄民族主义泥坑里去,故有必要加以辩证。
(二)民族性辩证。
辩证之一:民族性的二重性。
正如本编中一再阐述的,“民族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二重性:有正面的、积极的“民族性”,也有负面的、消极的“民族性”。正面的、积极的“民族性”是把表现民族的生活与斗争的思想内容与民族的艺术形式尽可能完美地结合起来;与此相反,负面的、消极的“民族性”则把没落的反动阶级的思想内容与陈腐的艺术形式结合起来,用“民族性”伪善的外衣包裹着反民族、反人民的货色。
仅以瓦格纳歌剧为例,他的作品中既有呼唤德国统一、抵抗外族入侵、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歌颂人民民主、反抗暴君专制等积极的一面,也有依附皇权、崇尚教会与神学甚至反犹主义等消极的另一面。
当然,二重性本是事物的属性,非独歌剧的民族性才有,更非瓦格纳及其作品所独有。
辩证之二:民族性的选择。
我们当然选择民族性积极的一面,扬弃民族性消极的另一面。然而,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
这首先要有正确的历史观。
正确的历史观从哪儿来?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哲学)的学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观点: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人民性应成为民族性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内容。同时,历史又是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新旧社会的更迭充满了曲折与反复的斗争。歌剧作者也必须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斗争并勇敢地加以反映。
很显然,当代中国的民族歌剧应该反映、歌颂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漫长的历史阶段,有勇气、有历史担当的歌剧作家,要敢于表现这种斗争。
这就像许多西洋古典歌剧的作者们一样,表现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复辟与反复辟的生死搏杀,如梅耶贝尔的《新教徒》、瓦格纳的《黎恩济》、普契尼的《托斯卡》。甚至贝多芬唯一的一部歌剧《费岱里奥》也应属于追求民主、反对暴政这一类题材,而不应仅视为“善与恶”之争。
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唯物的,又是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是它的另一重要观点。
因此,正确选择民族性还要有历史辩证发展的观点。要知道,民族性属于过去、属于历史、属于传统。忘记过去、忘记历史和传统,便不知如何創造未来;而迷恋过去、死抱历史和传统不放,便会故步自封、裹足不前而走不到未来。二者同样都会失去未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毛主席十分欣赏这句话。同样,一切艺术包括歌剧也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可能停留在原点。
这让我想起东西方古代哲人几千年前曾经发出的慨叹。东方的哲人叹道:“逝者如斯夫!”(孔子);西方的哲人叹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这许多哲理性的声音,启迪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民族性”。我们主张走《白毛女》为代表的民族化道路,却也应该懂得,中国未来的歌剧再也回不到《白毛女》了。时代不同了,反映时代的歌剧岂能够相同?
未来歌剧只能往前走,走未来的、新的路。它也必然会呈现出新的、不同于过去的风貌。
辩证之三:民族性的表现。
解决了如何选择积极的“民族性”,还有一个如何表现的问题。
那么,如何表现积极的民族性呢?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艺术哲学”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个法则将是我们正确表现积极的民族性的又一把钥匙。
一切音乐戏剧,都是由矛盾构成的:音乐的强弱、节奏的快慢、动机的对抗,以及和声的多寡、对位的参差错落……无不充满了“对立统一”;戏剧人物的正反、善恶、冲突、转化,也无不充满了矛盾冲突。一出戏,就是一个矛盾斗争的全过程:一头一尾,必须前后呼应,戏如何开,也就如何收;矛盾双方,你来我往、强弱胜负、喜怒哀乐,经过一番跌宕起伏,矛盾一旦转化了,戏也就结束了。
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也就没有戏,没有歌剧,更不存在歌剧的民族性。
那么,当代中国歌剧最主要的弱点是什么?
肯定有诸多不同的看法:剧本、音乐、导表演,还有舞美等等,哪一项都会有毛病,都可能不尽如人意。
依我之见,最主要的弱点就是缺少戏剧性:剧作者不善于写戏,作曲家不善于写戏剧性音乐。唱词可能写得很漂亮(真正人物的、矛盾的、动态的唱词也不易写好),音乐也可以写得很美(现在很动听的音乐也不多了),但整出戏演下来,就是不好看、不抓人。原因何在?在于“没戏”。俗话说:“没戏,一切白搭!”
任何时代的音乐戏剧,成功的大师巨匠们,都很懂得“戏”,都讲究戏剧性。未来歌剧也是如此,但这还不够,它还会有新的变化与发展,产生新的面貌、新的样式。
(三)未来歌剧将会是什么样?
人类最初的音乐舞蹈是结合的,“载歌载舞”。对此东西方几无二致,至今非洲的原始歌舞仍然如此。这都是有文献与实物可以作证的。
近代以来,西方舞台艺术走向“分离”,搞纯歌剧、纯舞剧、纯话剧。又因“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盛行,东方纷纷“效颦”,于是“分离”样式成为舞台艺术的主流形态。
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洋歌剧本身也一直在变。意大利本重“声乐”(“美声”),德国人加重了“器乐”(“乐剧”),到了法国人手里,“歌、舞、乐”已经又重新结合起来了。20世纪初叶,美国人的音乐剧把非洲的原始歌舞与欧洲的轻歌剧结合起来,又是“歌、舞、乐”融为一体的。它与法国歌剧“歌、舞、乐”的结合不同,演员是将“歌与舞”集于一身的(尽管还达不到中国戏曲“唱、念、做、打”——京剧大师梅兰芳后来加了个“舞”——集于一身的高难度)。当然,这种结合,不是往回走,回到过去,而是往前走,走自己新的音乐戏剧之路。
由此可见,从现代音乐戏剧——歌剧(也包括音乐剧)的发展趋势看,除了内容要表现时代生活与斗争之外,形式上“歌、舞、乐”结合乃是未来歌剧的一种必然形态,是大势所趋。
实际上,西方那种“分离”的做法,并未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广大乡村的老百姓是并不认同的。农村的老大娘看了民族舞剧或芭蕾舞剧,表示很不解,说:“台上那些个姑娘长得都很水灵,怎都是哑巴?”话剧与戏曲、歌剧同在广场演出,话剧台下人没几个,也许还没台上演员多。老乡们都一拥而上看戏曲与歌剧去了。问其原因,答道:“唱戏唱戏,听的就是唱。光说不唱有啥看头?”这就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传入的、近代西方“分离”出来的话剧与舞剧,经过了上百年的沧桑巨变,在有着上千年古典音乐戏剧——戏曲传统的中国广大乡村,仍未真正地扎下根来。
无论是西方现代音乐戏剧——歌剧、音乐剧的发展趋势,还是东方广大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亿万观众群体,音乐戏剧二三百年“分离”的形态已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必将走向融合。
“大梦谁先觉?”“东方睡狮”已经醒来,中国正在崛起。一个未来的音乐戏剧中的“歌、舞、乐”与“音、诗、画”融为一体的歌剧新形态正在到来,也必将到来。谁抓住了先机,谁就将获得未来歌剧的第一批成果。(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