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戏剧的年轻化
整理:钟海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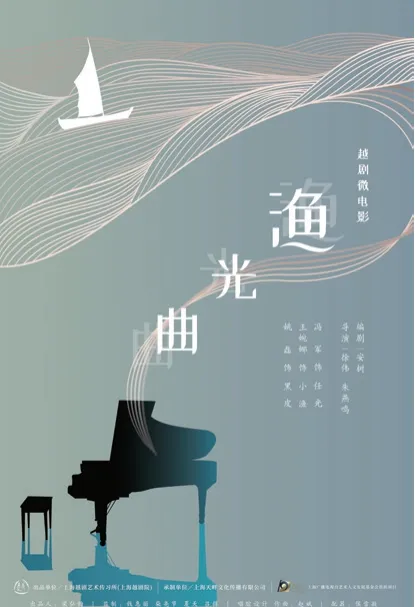
越剧微电影《渔光曲》(供图:上海越剧院)
红色戏剧知多少
杜竹敏:首先,红色题材反映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一部分,对于这段历史的抒写、再现,是构成国家和民族完整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不应该把红色戏剧单独割裂来看,应该和大家喜闻乐见的古装题材、古代题材、现实题材、现当代题材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戏剧的谱系。
我们常说,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那么历史从哪得知?通过教科书我们可以获得全面、系统的相关知识。但它是书面的、平面的,条目式的,相对比较枯燥。而文艺作品,包括舞台的呈现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了解历史的途径,而且它是生动的、立体的,历史中的人物也是有血有肉的。
其次,红色题材不单单是历史,更多承载的是一种精神。尤其是经典红色题材作品,京剧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沪剧的《芦荡火种》,越剧的《忠魂曲》等,这些题材在今天的舞台上不会觉得陈旧,我们依旧会被这些故事感动。2021年我参与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的策划和导演工作,电影节上有位嘉宾是意大利著名影评家马可·穆勒。他几十年来致力于向西方世界、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他说,几十年前接触到中国第一部文艺作品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瞬间迷住了,从此竭尽全力地传播中国文化。
李世涛:在当前的文化环境中,如何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创造中西方观众都能接受和认同的戏剧语言,红色戏剧是非常重要的途径,同时对于我们寻找自己的文化定位以及增强文化自信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请裘隆、朱燕鸣两位谈一下自己的红色戏剧创作情况。
裘隆:我的创作经历,一部是讲述秋瑾故事的《鉴湖女侠》,另一部是讲述陈延年故事的《新生》。另外,改编自《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好八连》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虽说没有经历过红色的年代,但是通过饰演剧中的角色,看历史资料,自己感觉和他们真的是越来越接近。
朱燕鸣:我参与了两部越剧微电影的创作,一部是讲述向警予故事的《她》,还有一部改编自电影《渔光曲》,讲述任光创作《渔光曲》的故事。在创作之前我刚好看了电视连续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就这部剧正好是说向警予、任光这一辈20岁左右革命先驱,在青年时代远赴法兰西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路,并最终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看了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很振奋,被点燃了。从他们身上我其实看到一些与当今“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的交集,比如都生于世纪之交、社会变革之时,都比较有主见、有行动力、有比较明确的理想抱负。《她》的主角向警予21岁就创办了男女同校的新式学校,跟现在年轻人大学毕业就创业有相似之处。她28岁时已经是无产阶级女权运动的领导者,为了广大女性谋福利,这些都很感动我,让我想去了解她、走近她。
李世涛:请杜老师讲讲你今年重点关注的几个红色戏剧作品,为什么关注它们?
杜竹敏:2021年是建党百年,也可以说是红色戏剧创作的大年,回顾上半年看的舞台作品,90%以上都可以归到这类,包括歌剧《晨钟》,京剧《红色特工》,昆曲《自有后来人》,越剧小戏《桃花雪》等,沪剧《陈毅在上海》《早春》,淮剧的《寒梅》,评弹《战无硝烟》,话剧《浪潮》《前哨》,舞剧《努力餐》。每个剧种曲种都没有缺席建党百年庆祝活动。
今年文艺创作中优秀作品很多,各有各的突破,各有不同的好的地方。我印象最深刻的两部,一部是电视剧《觉醒年代》,另一部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简称“《电波》”)。我们已经从一个更真实的、更人性化的层面理解红色题材,它不再是只有牺牲,它是有泪、有欢笑、有情感、有温暖,也有壮烈或者惨烈的一面。为什么说《电波》是一种现象,因为它引起了文艺圈以外的全社会的关注。连我身边很多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的从事经济、法律的朋友都来问我有没有《电波》的票?这两个作品是一个现象,对于我们红色题材的理解和创作可能进入了2.0时代,这和我们近年来在这方面的探索有关,是从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
李世涛: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浪潮》,是上海剧坛在建党百年之际最受关注的剧目之一,我特意留意了一下,这个戏的主创(包括编剧和导演)是一群年轻人,这个戏在演出之后反响很好,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年轻人写《浪潮》写得那么新鲜,角度很独特,却能够引起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情感共鸣。所以,任何一个时代,人对于美、崇高、独立、爱的追求其实是一致的,我们内心最真、最纯粹的追求和信仰是永不过时的。
红色戏剧是怎样锻炼的
李世涛:红色戏剧在舞台呈现上有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现代科技手段在舞台上的应用。在过去,这个问题是有些争议的—舞台必须要用这个技术手段吗?相当于 “这个电影故事必须要用3D吗”?但是,在《浪潮》《电波》等作品里,这样争议暂时平息了,因为它的技术手段和演员表演紧密贴在一起的。
杜竹敏:走进《浪潮》的剧场,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水的应用。它有个非常大的水池,5个上上下下的平台,时而造成非常压抑的感觉。最后一个恢弘的画面,是5个平台像一个天梯一样,5位烈士一步一步走上去,非常震撼!我们在表现手法和手段上越来越多元,完全不亚于国外非常美的音乐剧、舞剧、歌剧。
大家一般觉得淮剧是乡土气比较重的剧种,更适合表现农村题材,但是《寒梅》让我非常感动。那天晚上看完戏回来晚了,睡不着,就写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叫《一个人如果失去信仰会变成什么样》。叛徒李丙辉被迫交出党员名单,他把他的灵魂卖给了魔鬼。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作品,它对我们普通人都有警示作用,不仅仅追求崇高,也要避免平庸,怎样坚守我们的灵魂。这部作品在人性的探讨上又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朱燕鸣:《浪潮》舞台设计中的水舞台和钢架结构的中性装置和演员的表演配合得很好,形成非常好的效果。《电波》的舞美也是这样,不是单独做一个装置,它与演员的表演产生互动的关系。还有整体视觉、光影效果是那种低饱和度的色调、深沉的油画质感,局部的有意味的红色比如主人公的红围巾等又会在这种对比中很出挑,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此外,它将影视化的蒙太奇效果运用在舞台上,比如会运用像闪回镜头一样的舞台处理,还有慢镜头效果,又比如在舞台叙事里用到平行蒙太奇的效果。田沁鑫的《狂飙》的舞台很像Es Devlin给摇滚乐队Wire的演唱会做的舞美设计,也很适合这个剧的风格,剧中人物设定也很像“摇滚明星”,田汉像“明星偶像”一样感召、带领着一群有抱负的年轻人,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展现了那一代青年人的激情和理想。
李世涛:问裘隆一个问题,在扮演红色戏剧题材英雄角色或者革命烈士角色时,相比其他题材的人物,最重要的是哪方面?
裘隆:接到任务以后,我特意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我努力往影视的感觉去靠,《新生》里很多地方的年轻感、活力感,从影视中得到借鉴。陈延年有一段话是:“我们的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出来的。”这个话是当年陈延年的原话,我们在演出过程中最怕是说错了几个字,因为在中文里,同一个字说的语调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这对演员来说有时候是一种比较大的压力。饰演革命题材人物戏的时候,不但要了解他的历史真实性,如果有影像资料,我们会去找他的习惯性动作。举个例子,像毛主席经常有一个叉腰的动作,包括朱德同志等都有这样的动作,早期的领导都是这样的。
李世涛:杜老师能否从你的角度谈谈,为什么红色题材在今天年轻化成为特别强烈的呼声?这背后是不是有观众对于戏曲新的期待?
杜竹敏:二十世纪从五六十年代开始,有非常经典的京剧以及各个剧种的经典留下来,但是进入八九十年代后,红色经典的创作和诞生进入了新的低谷期。在新时代,我们的娱乐方式、接受信息文化的手段多元化之后,也认识到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不可轻视的。
也可能是前辈的创作太高山仰止了,导致今天的创作者会有一种戴着手铐、脚链跳舞的感觉,会有束缚。当代艺术工作者和观众有自我意识,希望创造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我们的作品,就像刚才裘隆说的,他希望自己塑造的陈延年是独一无二的。一旦有了这种追求,我们就会主动去反思。也许有人会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年轻化”。但我觉得年轻化的背后更准确的表达是一种共情化,或者感情真实的表达,因为“年轻”这个词是一种状态,它不是一个年龄阶段,80岁、90岁的老艺术家也有理念非常年轻的,他们有年轻的精神和奋斗,年轻是一种适合时代的表达方式,这是更为准确的表达。
李世涛:年轻化成为一个强烈的呼声并不是偶发现象,我们怎么去重新发现自己的文化、怎么重新塑造自己的戏剧形象?
杜竹敏:在红色题材作品中发现跟今天生活的联系。《电波》的编剧罗怀臻老师曾经说他一开始是拒绝这个题材的,因为太经典了。后来他找了很多关于李白的历史资料。采访过程中,他对我说“你看,这样一杯咖啡,这样的阳光,可能就是当年李白最希望、最渴望的生活。如果没有他在黎明前的牺牲,我们今天能够喝到这杯咖啡吗?”我突然感觉心颤了一下,觉得我找到了历史那么遥远的人物和今天生活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他们当年的延续。所以说,年轻化就是要找到历史的延续,找到共情、共鸣的点。
李世涛:编剧在塑造人物时也是这样,不要先自己给自己戴上一个镣铐,其实镣铐都是自己找的,像今年热播的电视剧、戏剧、出圈的舞剧,都给当下的创作者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个参考是什么?就是你只要去写人物最真实的情感反应,观众是买帐的,当代年轻人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救孤式的情节在今天的观众很难找到共鸣,这种情境相对来说比较极端。但是有很多东西是年轻观众很普遍遇到的,比如信仰的选择、人生的规划、跟家人的关系。
朱燕鸣:《法源寺》里的谭嗣同做了一种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极端的选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可以逃走,但是他没有选择逃走,他毅然选择了赴死,他还这么年轻,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选择呢?因为他希望“以死明志”,通过他的决绝的牺牲去唤醒更多的人,牺牲在那个时代是有它的特定意义和价值的,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是有我们中国儒家“士”的精神在里面的。《法源寺》这个剧的表现形式上用了中国戏曲常用的方式,就是自报家门、自我表白,这种戏曲传统的舞台程式有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有限的剧情时空里快速地交代剧情和人物。谭嗣同在“自报家门”的时候说:我是标准的官二代,这种语言表述方式把年轻人一下子就拉近了。还有谭嗣同对佛祖释迦牟尼的理解,他说“我觉得他是个革命者”,这个观点也很有趣,有一种自己的解读,这种方式也马上拉近了年轻群体。
李世涛:舞台技术手段对表演影响主要是表现在哪些方面?
裘隆:演员可以不用任何景,但是定点光或者一束侧光就能表现,你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突然从一个光明的世界回到内心世界,作为体现,只要演员的表演恰当,观众一眼就能看明白。当然,演员本身也要懂一些舞美设计的意图。如果有些观众觉得这个戏不好看,也可能是演员和舞美没有彻底融合,很多成功的作品,像《电波》,我最喜欢在电梯里那段,所有演员在晃动。只要表达正确,观众一眼就能看明白你要表达什么。
杜竹敏:红色戏剧的创新,它包括了舞美形式上的创新、内容题材上的创新,也包括音乐上的创新。我和著名唱腔设计陈钧老师聊到《好八连》的时候,他觉得越剧什么都能唱,如果哪一天音乐剧的唱腔不能适应现代题材,那是我们唱腔设计的问题,是我的音乐有问题,而不是这个作品的问题。戏剧本身是年轻化的,是以观众需要为指向的。
李世涛:年轻化是一种状态,红色故事有它独特的魅力,也有它独特的价值,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审美,当我们意识到过去的审美表达已经无法跟今天观众的期待产生共鸣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要做出调整,而不是要求观众去调整。不论是什么题材或者类型的戏剧,都需要创作者怀着诚意去跟观众交流,而不是强行说教,剧场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千万个人在那里一起呼吸、千万颗心在那里一起跳动。当下戏剧舞台上涌现了许多年轻化的红色戏剧,但也不能否认很多红色戏剧是僵化的,是脱离了时代的。正因为此,红色戏剧的年轻化是一个可以持续讨论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