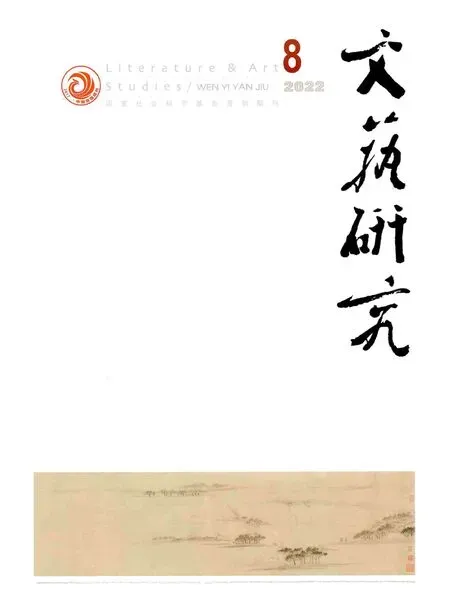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诗歌对芝加哥诗派的选择与接受
吕周聚
从1912年开始,美国文坛上出现了一场著名的新诗运动,其主要构成部分除了意象派诗歌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诗歌流派——芝加哥诗派,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韦彻尔·林德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1869—1950)是主要成员。他们活跃在美国中部大城市芝加哥,作品发表在当时著名的《诗刊》上。他们关心下层人民生活,歌颂现代都市文明,热衷诗歌朗诵,以轻松幽默的笔触书写对现代生活的感受,在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的作品通过美国人在中国创办的英文报纸《大陆报》同步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文坛也开始关注芝加哥诗派。20世纪30年代初,徐迟、施蛰存等人开始翻译介绍芝加哥诗派的作品,使该诗派开始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产生影响。对芝加哥诗派与中国现代诗歌之间的密切关系,学界尚未系统梳理与研究。本文旨在考察芝加哥诗派与中国现代诗歌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后者对前者的选择与接受,分析芝加哥诗派对中国现代都市诗、朗诵诗和轻松诗的产生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纽约、芝加哥逐渐成为繁荣的现代化大都市。诗人桑德堡身处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为美国社会的繁荣而欢欣鼓舞,写下了大量以现代都市生活为题材的诗作,桑德堡因此被称为“工业美国的诗人”。此类作品收入《芝加哥诗集》(,1916)、《烟与铁》(,1920)等诗集中。刘延陵早在1922年就撰文介绍桑德堡的多部诗集,认为其写作取材于农民和工人生活,作品中“发电机的声音,舂谷的声音,与工人们的笑声,谈话声,机器的轰轰之声,都混合着响”。
1933年,《现代》第3卷第1期刊载由施蛰存、徐霞村翻译的桑德堡《支加哥》《钢的祈祷》《嘉莱市长》《南太平洋铁路》《夜间动作:纽约》《工女》《特等快车》《帽子》《夜》等诗作,同时,施蛰存撰写了《支加哥诗人卡尔·桑德堡》一文,对桑德堡其人其诗进行介绍。自此,芝加哥诗派开始正式进入中国文坛。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多篇介绍桑德堡的文章发表,《芝加哥》等诗作有多个中文译本,足以说明其作品在中国文坛受到的重视。桑德堡的诗歌以美国现代都市为表现对象,给彼时的中国读者带来陌生、新奇的感受。1933年秋,徐迟翻译了芝加哥诗派另一位诗人林德赛的《圣达飞之旅程》(《现代》第4卷第2期),同时附了一篇文章,简单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及其代表作《支那的夜莺》《刚果河》和《圣达飞之旅程》等,这是中国文坛第一次译介林德赛及其作品。徐迟认为,莎士比亚、华兹华斯、雪莱、拜伦等诗人已经过时,“从二十世纪的巨人之吐腹中,产生了新时代的二十世纪的诗人。新的诗人的歌唱是对了现世人的情绪而发的。因为现世的诗是对了现世的世界的扰乱中歌唱的,是向了机械与贫困的世人的情绪的,旧式的抒情旧式的安慰是过去了。新诗人兴起了美国的新诗运动”。徐迟概括了美国新兴诗歌运动的基本特点,强调诗歌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美国当时已进入工业化社会,因此诗歌也要与都市、工业紧密结合起来。
1934年10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推出了美国文学专号。在解释为何要系统介绍历史最短的美国文学时,编辑者给出的理由是:“在各民族的现代文学中,除了苏联之外,便只有美国是可以十足的被称为‘现代’的。”也就是说,施蛰存是以“现代”为标准来选择译介对象的,这成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美国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施蛰存认为,美国独特的社会环境是一切新生事物的摇篮:“美国是达到了作为二十世纪的特征的物质文明的最高峰。电影,爵士音乐,摩天建筑,无线电事业,一切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造成的空前的供献以及空前的罪恶,都不约而同的集中在北美合众国的国土上。”显然,施蛰存发现了美国文学与物质文明、现代都市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对美国文学给予高度评价。在同一期上,施蛰存还刊发了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文,对美国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将当时的美国诗歌概括为六种不同类型,其中一类就是“城市诗”。谈及芝加哥诗派时,邵洵美认为桑德堡是“城市诗的前驱,商业美国的代言人”,并指出现代都市生活对诗人创作的影响:“机械文明的发达,商业竞争的热烈,新诗人到了城市里。于是钢骨的建筑,柏油路,马达,地道车,飞机,电线等便塞满了诗的字汇……所以新诗人的文字是粗糙的;题材是城市的;音节是有爆发力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随着新文化的中心在20年代中期由北京南移,上海逐渐成了中国作家生活创作的基地。相似的生活背景,使得芝加哥诗派的都市诗激发了中国诗人的创作,施蛰存、徐迟、路易士、陈江帆等都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以现代都市生活为素材的诗歌,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施蛰存这样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诗歌:“《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的现代的诗形。”在这里,施蛰存定义“现代的诗”的核心标准是“现代”,这与他对美国文学的理解一脉相承。施蛰存对何谓现代生活还做了具体说明:“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嗓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显然,施蛰存所理解的“现代生活”,主要是现代都市生活。他指出,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农村生活存在着巨大差异,认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感情差异,使得现代都市诗与传统田园牧歌有着本质不同。现代都市生活为都市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现代中国也会孕育出自己的都市诗。这一看法,在30年代也为很多人分享。例如,柯可就认为,“新的机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都明摆在我们的眼前,而这些新东西的共同特点便在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感觉。于是感觉便趋于兴奋与麻痹两极端,而心理上便有了一种变态作用。这种情形在常人只能没入其中,在诗人便可以自己吟味而把它表现出来,并且使别的有同经历的人能从此唤起同样的感觉而得到忽一松弛的快乐”。在施蛰存的推动下,《现代》从第4卷开始大量刊发都市诗创作,一直持续到第6卷第1期他不再担任主编为止。作为主编,施蛰存影响着刊物发表诗歌的取舍标准,使得《现代》成为发表反映现代生活的都市诗的重要阵地。此外,在《现代》杂志的带动下,许多刊物都开设了“都市诗”栏目,都市诗创作热潮开始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出现。这些中国的现代都市诗与芝加哥诗派大多有着内在关联,《芝加哥》一诗中的许多都市意象都出现在中国诗人的笔下,而芝加哥诗派对都市的复杂态度也在中国现代都市诗那里得到了呼应。
桑德堡较早在诗歌中反思美国19世纪中后期开启的工业化进程,指出工业化既带来都市的繁荣,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他甚至将芝加哥描绘为“邪恶的都市”“不正的都市”“野蛮的都市”。这使得芝加哥诗派都市诗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揭示现代都市的罪恶,这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初到都市的诗人来说,参差不齐的摩天大楼、五颜六色的街灯令人目不暇接,种种诱惑让他们骚动不安,于是发出这样的感慨:“嚣骚,嚣骚,嚣骚,/嚣骚里的生疏的寂寞哟。”很多中国诗人都表达了面对现代都市时所感受到的陌生、隔膜、孤独与迷惘。在陈继武的眼中,“都市是人间罪恶的鬼窟,/都市人是着了魔的幽灵”,现代都市生活造成了人的异化,使人沉醉于肉体的享乐,失去了灵魂。在吴汶笔下,都市人花天酒地、群魔乱舞,使得都市成了“妖都”,舞厅里的跳舞甚至成了尸舞。诗人锡金看到了都市里的荒凉,到处是大减价的旗帜,路边一片片钉上十字封条的店门,巨幅彩色广告上张贴的白纸黑字的告示互相映照,呈现了一派萧条景象。诗人夏舒雁则看出了都市生活的贫血,听到了它心脏跳动的加速,“满街是熬不住的叹息/满街是挡不住的灾难”。这些作品的主题都与桑德堡的诗作类似,呈现了现代文明的罪恶与黑暗,批判都市生活中的腐化堕落及贫富悬殊等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桑德堡在批判现代都市的罪恶的同时,也在热情地歌颂工业化和城市化,他对那些嘲笑芝加哥的人回敬以嘲笑,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芝加哥比作“高大重击手”,浑身充满力量;现代化的机械“像一个与荒原搏斗的野蛮人”,“建筑着,破坏着,翻造着”,呈现出无尽的创造力;在命运可怕的重负下,都市“像一个青年人似地轰笑着”,“轰笑着青年人底骚乱的,嘎声的,喧嚣的笑声;半裸着体,淌着/汗,自负着是宰猪场,器具制造所,小麦的堆积地,铁道纵/横的玩弄者,国家的运输所”。诗人在关注现代都市中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时,歌颂现代都市文明,为充满活力、富于朝气的现代都市人而骄傲。无独有偶,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人陈梦家也为现代都市歌唱,与《芝加哥》的拟人化手法类似,他同样将现代都市比作一个不会瞌睡的疯子,表现其旺盛的创造力与生命活力。此外,陈梦家描写劳动者的方式,没有像左翼诗歌那样,着重表现他们的苦难或控诉社会的不公,而是歌颂他们是“灿烂世界”和“幸福花园”的建造者,是“创始的功臣”,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于是,现代都市不再是罪恶的地狱,而是成了人间的天堂:“这儿才是新的世界,建筑的天堂,/不住的嘈杂,一切圆轴的飞转/一回一回旋进了那文明的大圈,/你听阿,那高声颂扬着的歌唱!”与那些批判现代都市的诗歌相比,《都市的颂歌》不仅表现出都市高速发展的现代景象,而且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现代精神,是一首真正站在现代立场上的都市诗。此诗深受胡适的赞赏,他在评论中指出:“你的长诗,以《都市的颂歌》为最成功。以我的鄙见看来,近来的长诗,最算这篇诗最成功了。”
现代都市不同于传统都市的地方,还在于出现了大批现代化的新生事物,都市里的光、电、声、色刺激着诗人敏感的神经,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这些题材使诗人产生新的灵感,被反复书写,成为都市诗中凝聚诗人情感、思想的重要意象。于是,纷繁出现的都市意象成为20世纪30年代都市诗的一个重要标志。陈江帆写过一批以现代都市为表现对象的诗作,在他的笔下,海关钟、繁华的市港、小小的公寓、车站旁的钟楼等现代意象大量出现,不仅呈现出现代都市的生活景象,而且承载着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诗人一方面为都市的扩张和发展感到自豪,表示“都会的版图是有无厌性的,/昔时的海成了它的俘虏;/起重机昼夜向海的腹部搜寻,/纵有海的呼喊也是徒然的”,为有崭新的百货店而兴奋;另一方面也为都市的病态而叹息,感慨“属于唱片和手摇铃的夜,/减价的不良症更流佈了,/今年是滞销之年哪……是末代的工业风的音调呢,任蜂巢般地叫唤着,/也已失去它创世纪的吸力的”。诗人反复咏叹“今年是滞销之年哪”,表达了对都市陷入经济萧条的无奈与惆怅。很明显,30年代中国现代都市诗中的意象与桑德堡笔下的都市意象如出一辙,既呈现出现代都市生机勃勃的社会景象,又揭示出现代都市的病态特征。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以现代都市为表现对象的诗作,这类作品的出现,一方面来源于上海所提供的都市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则与芝加哥诗派的影响密切相关。桑德堡等人的诗作对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诗中出现的大量趋同的意象上,更表现在对现代都市的精神认同上,即不是简单地否定伴随现代都市出现的各类丑恶现象,而是同时肯定和歌颂现代都市的新气象、新发展,将现代都市生活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美好目标。
芝加哥诗派不仅影响了中国现代都市诗的写作,而且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朗诵诗运动的出现有着内在联系。桑德堡、林德赛曾在美国各地旅行,朗诵自己的作品并咏唱民谣,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研究者指出:“这派诗人中的两个人——卡尔·桑德堡和伐切尔·林赛(即林德赛——引者注)是美国诗歌史上最有成就的朗诵家。桑德堡用吉他伴奏,二十年代长期在全国巡回演出。他又是一个民歌咏唱家,他的朗诵会夹唱夹诵,名噪一时……林赛的伴奏工具很特别——他朗诵时拍击手鼓。他的诗吸收了爵士乐的特点,节奏效果强烈。关于他的朗诵之魔力,有近乎传奇的记载。”林德赛将爵士乐引入诗歌,创作出一种说唱结合、具有强烈节奏感的作品,他在朗诵时敲击手鼓,有爵士乐队伴奏,有时还邀请观众和他一起朗诵副歌部分(如代表作《威廉·布施将军进天堂》中就有副歌部分),现场气氛热烈,很受观众欢迎。在他们的影响下,朗诵诗遂在美国文坛成为一种流行的诗歌文体和诗歌表演方式,诗人甚至可以通过举办诗歌朗诵会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到了“二战”时期,朗诵诗在欧美各国流行开来,演化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诗歌运动,中国的朗诵诗运动也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芝加哥诗派中,林德赛是最具影响力的朗诵诗人。同为芝加哥诗派重要诗人的马斯特斯曾撰文评论美国诗坛,认为林德赛之所以在美国诗坛具有卓越的地位,并非因为他怪僻的性情,也不是由于他具有精细分析的能力,“只是因为他是唯一能创造环境的天才,然后他给此环境一种回响,一种声音,一种生气勃勃的空气,一种特异的性质”。中国诗人较早注意到林德赛的朗诵诗,并有意识地通过介绍其创作,救治早期新诗缺乏音乐性的弊病。刘延陵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撰文介绍林德赛,指出诗人强调诗与音乐的合一,“他步行周游美国东部,到处把诗唱给人听以换取食宿,所以有‘游行诗人’‘乞丐诗人’的称呼”。徐迟则认为林德赛不是诗人而是职业的演讲者,“他在美洲巡行着,作教育的演说,同时背诵他的诗”。徐迟有感于中国新诗缺少音乐性,选择着重介绍林德赛的朗诵诗,并详细介绍其朗诵技巧:“林德赛的诗是有音律的。是诗歌,是可以引吭而歌的。在《Congo之河》与《圣达飞的旅程》两诗的边旁,他用较小的字说明着读他的诗的时候的声音的法则。例如读Rachel Jane的莺鸟之声,需用‘美妙的低声,或朗读,或歌唱’的方法念那九行的小诗的。而黑人的行句上的读法是‘大声的或用如铜的低声部音’的法则。汽车驶动的读法是‘渐渐的快而渐渐的高亮’。这些他都特别加以注语的。”林德赛在诗句旁边用印刷小字说明朗读一首诗的不同部分时的声调和表情,给朗诵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导。他讲究朗诵技巧,其朗诵三分之二是说,三分之一为唱,说唱结合,同时吸收了马戏团音乐、黑人灵歌、流行歌曲、民族和钢管乐的有益成分,演出效果生动,“把音的效果参杂到诗歌里去——未始不是使诗歌对于一般读众更能接近一些的方法,它对于后来的广播诗剧更不无影响”。徐迟所翻译的林德赛《圣达飞之旅程》无疑提供了朗诵诗创作的模板,使中国诗人可以借鉴林德赛的作品与朗诵方法来创作、朗诵自己的作品。
与林德赛类似,桑德堡同样以朗诵诗知名,其诗歌热情奔放,打破了传统诗歌的写作模式,采用口语进行创作,将诗与散文的句子混合在一起,大量运用排比、并列和重复的修辞手法,不讲究音部和音韵,这种句式能够抒发作者强烈的感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鼓动力,非常适合朗诵。徐迟的朋友,诗人严文庄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现场观看桑德堡的诗歌朗诵。在给徐迟的信中,她描述了自己到路德教大学体育馆听桑德堡演讲的经过,详细地描写桑德堡的穿着、神情和声音,认为诗人用整个灵魂朗诵《芝加哥》,“这是街头上狂呼着的桑德堡的孪生,涂着阴影,捕着迷雾,爱好着领略着音字中的蓄意”。从信中可以看出,严文庄很欣赏桑德堡的诗歌朗诵,她对诗人朗诵现场绘声绘色的描写,使徐迟也能间接了解桑德堡的朗诵特征,加深了其对朗诵诗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国诗人对林德赛、桑德堡等人朗诵诗的翻译介绍,最初并非有意识地在中国推行朗诵诗,而主要是通过借鉴朗诵诗的形式来解决中国早期新诗存在的散文化问题。中国早期新诗的散文化倾向严重,许多诗人片面地追求自由而忽视诗歌的韵律,从而导致新诗只能默读而不能朗诵。穆木天、徐迟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原本试图借鉴美国的朗诵诗救治中国新诗散文化的弊病,探索新诗发展的路径,没想到却暗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政治需要,朗诵诗先是与左翼文学提倡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发生关联,后来又成为宣传抗战的一种重要的文艺形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2年9月,穆木天、蒲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创办《新诗歌》,大力提倡诗歌大众化,除采用民歌、民谣、小调等形式创作之外,还倡导朗诵诗创作。诗歌大众化运动是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1935年“左联”的解散,左翼文学的发展也告一段落,朗诵诗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相对有限。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抗战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为了让全国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了解抗战、参加抗战,诗人开始意识到,“必须在抗战的实践中,把诗歌朗读和诗歌大众化紧密地连系起来,这一种朗读工作,才真正能完成他的任务,也就是说,必须在诗歌大众化的实践中,把诗歌朗读的工作执行起来,才真能使诗歌朗读运动,收到他的真正的效果”。谷夫就特别指出,朗诵诗在宣传方面具有独特的力量,“因为朗诵诗用于宣传的力量,不是新闻纸,演说,演戏,图画等所能做到的,于是在国防文学中朗诵诗也用崭新的姿态出现了”。正是抗日宣传的推动,使得朗诵诗在广州、武汉、延安、重庆、昆明、上海以及香港等地蓬勃发展起来。
徐迟、穆木天、冯乃超等人在抗战时期大力提倡“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的朗诵诗运动。这一时期,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标注为“朗诵诗”的作品,其中高兰的朗诵诗影响最大,特别是他的《我们的祭礼》,在1937年10月19日在武汉举行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集会上由著名电影演员王莹朗诵,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从此,许多诗人走出象牙塔,走上广场、街头,表示“去,朗诵去!/别再坐在房里尽发呆,/站起来,/走出门去,/门外有万千的群众在等待,/等待着你,把喉咙放开”,“展开咱们朗诵的诗歌,/全民的抗战里有你也有我”。不过,对于大部分诗人而言,朗诵诗是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他们大多不了解朗诵诗的特点和要求,不了解朗诵诗的受众对象,写出的作品不受欢迎,无法产生应有的艺术效果。
为了解决朗诵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当时很多研究者开始以芝加哥诗派的朗诵诗为模板和参照,从理论上总结朗诵诗创作的规律。朱自清就曾撰文专门介绍美国的朗诵诗,认为广播诗剧(朗诵诗)要让广大的听众听得懂,这也会对印刷的诗产生影响,“教作者多注重声调,少注重形象”。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桑德堡、林德赛等人的朗诵诗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日常口语、俚语进行创作和朗诵,自然能够被一般观众(读者)接受并产生良好的朗诵效果。杜若也指出,“朗诵诗,与其说是写来看的,不如说是写来诵的,既诵,则许多不便于‘诵’的文语上的语法,应极力避免;同时,还得从口语里学习他们的精华,提炼成为诗的句语。其次,为便于诵,更得强调诗里的音乐性,对音节给以更大的注意”。这就概括了朗诵诗的语言特点——口语化和音乐性。施蛰存通过研读《芝加哥》,发现了桑德堡诗歌中的土语与节奏之间的微妙关系,“他底音律,也和他底题材一样,是非传统的诗底音律。那是与他底土语及五弦琴不可分离的。用读普通各种英诗的方法来读他底诗,它们诚然不会给你音节,但倘若你能够用那比普通英语更慢的美国中西部土音来吟诵呢?自然,它们会都是很和谐、很美的诗”。正是在芝加哥诗派的启发下,施蛰存发现了土语在朗诵诗创作与朗诵中的重要性。穆木天也有类似的思考,他认为朗诵诗创作者在抗战期间必须考虑听众的文化水平,不应该使用知识分子惯用的语言进行写作,指出“朗读诗,必须考虑到朗读的条件。他不借用音乐的帮助,但是,他必须是大众的情感的大众口语的表现”。
这方面思考的集大成之作,是徐迟1942年在桂林集美书店出版的《诗歌朗诵手册》。该书通过介绍欧美、苏联的诗歌朗诵创作,分析朗诵诗的基本特点,介绍怎样选择朗诵诗、如何分析朗诵诗,讨论诗的“翻译”(从印刷品“翻译”成朗诵诗)、朗诵诗的语言和声调等具体问题,探讨朗诵者的造型、感情、口技、眼睛等技术因素,成为指导当时朗诵诗创作的普及性著作。徐迟这本著作主要分析的对象和例证,正是桑德堡、林德赛等人的朗诵诗创作。徐迟在谈到如何把一首印刷品诗“翻译”成朗诵诗时,特别强调诗歌语言的重要性,即要把死文字“翻译”成活的语言,尤其强调要把国语诗“翻译”成方言诗,因为许多人只能听懂方言,而听不懂国语。他还指出用活的文字来塑造活的形象,通过活的形象来呈现诗人的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打动观众(读者),才能产生应有的朗诵效果。《诗歌朗诵手册》为当年的朗诵诗创作与朗诵提供了理论支持,著名的朗诵诗人高兰当时曾热情地向读者推荐这部“关于诗朗诵的杰作”,对推动朗诵诗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上述关于朗诵诗语言特征的讨论,推动了当时的朗诵诗创作质量的提高,使文坛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朗诵诗作品。陈方在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写了朗诵诗《纪念“七·七”》,控诉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鼓动老百姓积极参加抗战,表达了对抗战胜利的美好希望。全诗共五节,句子短促明快,节奏感强,具有强烈的鼓动力和感染力。作者为了给朗诵者提供便利,增强朗诵效果,还学习了林德赛的创作方式,特意在诗后附有说明:“读时,首节柔和而亲切,宜稍慢;二节低而缓;三节坚决;四节昂扬,末节宏亮,宜稍快。”高兰的《给绿林好汉》以“绿林好汉”的口吻回忆八年前兄弟九人歃血为盟、誓死抗日的壮举。为了加强诗作的地方色彩,获得较好的朗诵效果,高兰大量运用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如“多么亲切啊!朋友/你‘贴着柳子’,/咱也‘上过绿’;/你是绿林的好汉,/咱的青纱帐在长白山边”。土匪使用的黑话不仅符合主人公“绿林好汉”的身份,而且富有地方色彩和艺术感染力。当然,我们也须看到,当时发表的朗诵诗数量众多,但优秀作品较少,很多作品流于标语口号化,突出了政治主题,忽视了朗诵诗的艺术形式,语言没有做到大众化、口语化。以拽棲的朗诵诗《汨罗江》为例,该诗抒写屈原怀才不遇、投江自杀的故事,渔翁、牧童和屈原三个人物先后出场,但他们的对话都使用知识分子的语言,把渔翁、牧童写成了和屈原一样的知识分子,自然也就难以产生朗诵诗应有的艺术效果。
尽管中国的朗诵诗运动受到桑德堡、林德赛等人的影响,但中美两国的朗诵诗还是有着较大差异。从思想内容和创作目的来看,芝加哥诗派的朗诵诗主要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进行写作,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通过与观众的感情发生共鸣来打动观众;他们的诗歌朗诵带有商业性质,借助诗歌朗诵解决温饱问题。而中国现代诗人的朗诵诗主要站在大众、国家的立场进行写作,服务于全民抗战的现实政治,通过朗诵诗向民众宣传抗战思想,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从文体形式的角度来说,桑德堡、林德赛等人的朗诵诗继承了惠特曼自由诗的特点,语言口语化,并以吉他、手鼓等乐器伴奏,节奏鲜明,有感染力;而中国的朗诵诗则融合方言、民谣等民间语言形式,富有节奏感,感情真挚,呈现出民族化、大众化的特征,它可直接向听众朗诵,也可用于舞台表演,为抗战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朗诵诗既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也是芝加哥诗派影响的产物。对美国朗诵诗的译介,一方面为中国的朗诵诗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早期新诗散文化的倾向。正像朱自清所说的,朗诵诗构成了新诗辩证发展的动力:“朗诵诗的提倡更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朗诵诗虽在散文化,但为了便于朗诵,也多少需要格律。所以散文化民间化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这正是所谓的矛盾的发展。”
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语境下,中国诗人除了创作朗诵诗宣传抗战外,还创作出了一批轻松诗,以轻松幽默的语言对当时社会的各种乱象进行讽刺批判,为严肃的文坛带来别样的风格。这类轻松诗的出现,也与以桑德堡、马斯特斯为代表的芝加哥诗派有着内在关联。
芝加哥诗派继承了惠特曼诗歌的传统,诗作充满乐观情绪,语言轻松幽默,马斯特斯的《匙河集》()是这类创作的代表。诗人假托美国中部一个小城的死人们给自己写墓志铭,以悼亡诗的形式为各种各样的小人物写了214首诗,呈现他们卑微的一生,充满讽刺与幽默,格调轻松活泼。中国诗人同样很早就关注这类轻松诗创作。在20世纪20年代,刘延陵就称赞《匙河集》是美国新诗发生以来最有名的诗集之一。朱复的评论文章对马斯特斯及其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匙河集》轻松幽默的特点来自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讽刺与批判。吴风则指出,马斯特斯犹如一个人类的辩护士为他的事主辩护,“承认他的罪案,而却以人类那种在善与恶,美与丑之间无止境的挣扎的忧愁和辛酸的讽刺来为他辩护”。直至40年代,中国文坛仍保持着对马斯特斯的热情,珠还撰文介绍马斯特斯并高度评价《匙河集》:“他的技巧完全是对维多利亚式的矫饰的反叛,文字质实无华。他的深厚的同情,使他能洞悉一切人的最深痛苦,而他的冷酷的判断,使他能对一切丑恶不存姑息,就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乃成为一个民族的史诗。”可以看出,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以马斯特斯为代表的芝加哥诗派轻松诗创作是中国诗人长期关注的对象,为这一诗歌体式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打下了基础。
在20世纪40年代,一批中国诗人开始大量创作轻松诗,并着手从理论上研究这一文体。马凡陀于1949年编译了《现代美国诗歌》(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一书,选译了包括林德赛、桑德堡在内的28位诗人的作品,并重点介绍了轻松诗。他表达了将“light verse”译为“轻松诗”时的顾虑,坦言“这个名字恐怕会受到人们反对的,但也不知道该怎样翻译才适合。许多‘轻松诗’在内容上看来,是毫不轻松的,甚至是十分严肃的。那末说它们的形式上‘轻松’吧,似乎也不尽然,有许多有严谨的格律”。他还指出,从“游戏笔墨”“讽刺诗”“通俗诗歌”“民间歌谣”等角度并不能涵盖“轻松诗”的全部意涵。杜运燮则较早看到了轻松诗与打油诗的区别,并概括了其基本特点:“美国艾布拉姆斯编的《文学名词汇编》这样说:‘轻诗(即轻松诗——引者注)使用平常说话的语气和宽松的态度,欢快地、滑稽地,以至怪诞地处理一些题材或者带有善意的讽刺。’《英汉辞海》的解释是,‘这种诗体主要是为了取乐和给人助兴而写,常具有机智、优雅和抒情的美的特点。’着眼点是轻快性,机智、风趣,目的主要是逗趣,给人愉快。我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读奥登诗时接触到的。我喜欢他的那种轻松幽默,带有喜剧色彩,内含微讽的手法,觉得可以很容易用之于写讽刺诗,加入严肃的内容。”杜运燮与马凡陀对轻松诗的理解和界定虽有差异,但都看到了轻松诗运用反讽、悖论等现代手法来表达诗人对社会现实人生的严肃思考,其语言形式虽轻松、愉快,但思想内涵却严肃、沉重的特点。
尽管杜运燮声称自已是通过奥登接触到轻松诗的,但他对芝加哥诗派的轻松诗并不陌生。唐湜在评论杜运燮的《诗四十首》时,一方面指出他的两首轻松诗所存在的问题——人物的刻画不十分深,不十分有力;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我们由此出发,去代替小说刻划人物去,让我们的市民、农人以歌谣的亲切外衣挂在群众的嘴上”。值得注意的是,唐湜提出了解决中国轻松诗创作弊病的办法,认为诗人应以芝加哥诗派的轻松诗为样板加以改进:“美国的马斯脱(即马斯特斯——引者注)有一册《匙河集》,描写匙河镇上的各式各样人物,辛辣又深刻,还有哲理味的结语,是一个好榜样。美国新诗人对人物的素绘特别有兴趣,这在写作未来的资本主义史诗是一个很好的准备,现在已有人在尝试写作机械世纪的史诗了,那是卡尔·桑德堡,他的《芝加哥》在某些方面继承了魏尔哈仑歌颂新文明的精神,而在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人物诗的新传统。在匆促的都市生活里,读小说似乎是太烦重的工作,那么,这种写人物的轻松诗就是最好的体裁,好像是小说的大兵团里派出来的轻骑兵。”显然,在40年代的评论家看来,马斯特斯、桑德堡等人的诗作,足以成为中国诗人学习的榜样。芝加哥诗派运用反讽、悖论等表现手法,以轻松幽默的笔法表现严肃内容、揭示美国社会问题的诗作,对杜运燮、穆旦、马凡陀等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既表现在题材风格上,又表现在艺术形式上。
如前所述,《匙河集》假托死人给自己写墓志铭,用俏皮风趣的语言呈现人物的一生,让死亡这一沉重的主题变得轻松幽默。例如,《霍特·普特》一诗让富翁比尔·皮尔索和穷鬼“我”安静地睡在一起,表面上看两个人都破产了,但前者的破产成了捞取更多财富的手段,而“我”的破产则是以被判绞刑为代价,两人生前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死后却躺在了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杜运燮也采用类似的手法从事创作,在《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中,诗人以死者的口吻来写下自己的遗嘱:“给我一个墓,/黑馒头般的墓,/平的也可以,/像个小菜圃,/或者象一堆粪土,/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有个墓,/只要不暴露。”这份遗嘱提出的要求非常卑微——希望死后给他一个“黑馒头般的墓”,语气却严肃庄重,二者之间产生反讽张力,使读者能在轻松的语句中感受到浓郁的人生悲剧,既控诉了战争的残酷,也呈现出生命的卑微。在战争环境中,死亡时刻伴随着人们,杜运燮的《林中鬼夜哭》化身死去的日本兵发表对死亡的看法,表示“死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终于有了自由”,“啊,你们都要原谅会哭的死人,有一天我们也许要使你们惊叹”。在这里,诗人将“死”与“最有意义的时候”“最快乐”联系在一起,创造出反讽效果,传达了谴责战争的沉重主题。在《老人》中,作者则以老人的口吻表达对死亡的理解:“他喜欢我被你们抛弃,/孤独地与他行走,/因为他可以更早占有我。//虽然知道,我将要喜爱他,/过于喜爱你们!/因为他才是最长久的朋友。”这首诗以豁达、幽默的语气书写对死亡由怕到爱的复杂心理变化,带有浓郁的哲学意味。
中国现代诗人从马斯特斯、桑德堡等人的轻松诗中,学到了反讽、悖论等能够产生幽默效果的艺术表现手法,把沉重的社会话题以轻松的笔触呈现出来。在战争年代,国统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很多人敢怒而不敢言,为以讽刺、批评见长的轻松诗创作提供了舞台。例如,杜运燮在名诗《追物价的人》中,将物价比作抗战时期的红人,很多要人、阔人都捧他、提拔他,而主人公“我”则不得不努力赶上他,不能落伍:“虽然我已经把温暖的家丢掉,/把祖传的美好田园丢掉,/把好衣服厚衣服,把肉丢掉,/还把妻子儿女的嫩肉丢掉,/而我还是太重,太重,走不动,/让‘物价’在报纸上,陈列窗里,/统计家的笔下随便嘲笑我,/啊,是我不行,我还存有太多的肉,/还有菜色的妻子儿女,她们也有肉,/还有重重补丁的破衣,它们也太重,/这些都应该丢掉;为了抗战,/为了抗战,我们都应该不落伍,/看看人家物价在飞,赶快迎头赶上,/即使是轻如鸿毛的死,/也不要计较,就是不要落伍。”这首诗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受到很多评论家的好评。袁可嘉就认为,这首诗“采取了颠倒的写法,把人人痛恨的物价说成是大家追求的红人,巧妙在于从事实的真实说,这句句是反话,而从心理的真实说,则句句是真话。由此形成的一种反讽效果是现代派诗中特有的”。通货膨胀是社会的毒瘤,但在那个病态、荒诞的社会中,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不正常则成了正常,诗人反话正说,深刻揭示出国统区社会的腐败与黑暗,堪称轻松诗的经典。马凡陀在这一时期也以轻松诗创作知名,其《古老的故事》《发票贴在印花上》《人咬狗》等作品运用反讽、悖论等手法创作而成,不仅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具有耐人咀嚼的意味。但从整体上看,《马凡陀的山歌》中的大部分作品是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创作的讽刺诗,有些近于打油诗,通俗有余而诗味不足,诚如他自己所言,写作讽刺诗只是开玩笑而已,难登大雅之堂,“没有什么耐人寻味的价值,更难和一些严肃的诗相比”。由此来看,他的大量政治讽刺诗只得到了轻松诗的皮毛,并未得到轻松诗的真谛,这也正是唐湜认为马凡陀在人物描写上没什么成就,需要重点学习马斯特斯、桑德堡创作的原因。
芝加哥诗派的轻松诗以描写人物见长,受此影响,穆旦、杜运燮等诗人也采用类似手法创作了一批语调轻松、具有强烈讽刺性的人物诗。抗战时期,大批农民走上战场,成为抗战的生力军,但在旧式军队里,他们却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穆旦的《农民兵》就以反讽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农民兵形象:“不知道自己是最可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当富人和猫狗正在用餐,/是长官派他们看守着大门。”士兵虽然在名义上是“最可爱的人”,但在长官眼里却“太愚笨”,连猫狗不如,这中间的巨大反差所造成的反讽效果,不仅写出了农民兵可怜的命运,而且揭示出“长官”“法律”的丑恶嘴脸。杜运燮在《一个有名字的兵——轻松诗(Light Verse)试作》中,也塑造了农民兵的形象,“张必胜的一生,/做过两次人:/一次在家里种田,/另一次是当兵”,他因为脸上长麻子而被人叫“麻子”,母亲告诉他要好好干活才能讨到老婆,他听母亲的话,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比别人做得好,因此获得了“铁牛麻子”的名声。可正当娶老婆的理想马上要实现时,他却被抓了壮丁,“麻子就变了‘张必胜’,/不久又变成‘张麻子’,/张麻子很快又出了名,/因为他有一副傻样子”,他学不好立正,排长调他当勤务兵,可第一天就摔掉一个茶壶,第二天又忘记说“报告排长”,于是被派到厨房当伙夫。在厨房他找到了用武之地,“大伙儿猜拳喝酒,/他在旁边剥花生米。/大伙儿要去找姑娘,/他说他还要筛一筛米。//被服发得破旧,/麻子是不会说话的,/草鞋费被吞掉/也喷不出个‘他妈的’”。他上了三次火线,第一次丢个大拇指,第二、第三次都被打中了腿,在野地里躺了十天十夜,腿上长满了蛆,身旁的草都吃得精光,最后回到了队伍,腿被医生锯掉,活了下来,但在抗战胜利三个月后,他却被人发现死在路旁。诗人以轻松的语言生动地刻画出一个滑稽的农民兵形象,表现其质朴勤劳的性格特点,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控诉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无尽苦难。此外,杜运燮的《阿Q(轻松诗试作)——根据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写的》则是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的改写,诗人抓住原作的主要情节和细节,用诗的形式将阿Q这一人物形象及其精神胜利法生动地呈现出来,语言幽默风趣,读来别有一番风味。
综上所述,以桑德堡、林德赛、马斯特斯为代表的芝加哥诗派在诗歌题材和文体形式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他们创作的都市诗、朗诵诗和轻松诗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世界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30年代,徐迟、施蛰存等人将芝加哥派诗人的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中国诗人根据自己的诗学趣味和社会需求选择接受了芝加哥诗派的不同影响:施蛰存、徐迟等人接受了其都市诗的影响,上海成为诗人主要表现的对象,他们的创作不仅揭露和批判都市的罪恶,而且歌颂都市的繁荣发展,赋予中国新诗一种全新的现代气质;穆木天、徐迟等人接受芝加哥诗派朗诵诗的影响,本意是要借鉴朗诵诗的韵律、节奏改变中国新诗散文化的倾向,后来却切合了抗战的现实政治需要,创作出具有强烈宣传鼓动效果的朗诵诗,为抗战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杜运燮、穆旦、马凡陀等人则接受了芝加哥诗派轻松诗的影响,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批判国统区的黑暗与腐败,对现实人生进行深入的思考。正是在芝加哥诗派的影响下,中国诗人一方面拓展了中国现代诗歌的题材范围,另一方面探索了新的文体形式,创造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动了中国现代诗歌的繁荣发展。
注释
①㉖ 严文庄:《卡尔·桑德堡的一幅肖像》,《现代诗风》第1册,1935年10月10日。
②㉓㊶ 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诗》第1卷第2号,1922年2月15日。
③㉔ 徐迟:《诗人VACHEL LINDSAY》,《现代》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1日。
④⑤ 编者:《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导言》,《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⑥ 邵洵美:《现代美国诗坛概观》,《现代》第5卷第6期,1934年10月1日。
⑦⑧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
⑨ 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第1卷第4期,1937年1月10日。
⑩⑯ 卡尔·桑德堡:《桑德堡诗抄:支加哥》,徐迟译,《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
⑪ 宗植:《初到都市》,《现代》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
⑫ 陈继武:《都市人》,《诗经》第1卷第6期,1936年4月1日。
⑬ 吴汶:《七月的疯狂》,《现代》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1日。
⑭ 锡金:《都市的夜》,《诗林》第1卷第1期,1936年6月1日。
⑮ 夏舒雁:《罪恶的都市》,《诗地》第1期,1947年1月1日。
⑰ 陈梦家:《都市的颂歌》,《新月》第3卷第3期,1930年5月。
⑱ 胡适:《评“梦家诗集”》,《新月》第3卷第5、6期,1931年3月。
⑲ 陈江帆:《都会的版图(一作新堤)》,《现代》第6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⑳ 陈江帆:《减价的不良症》,《现代》第6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㉑ 赵毅衡:《诗朗诵在美国》,《诗刊》1981年第3期。
㉒ Edgar Lee Masters:《美国诗坛的复兴》,张露薇译,《文艺月刊》第5卷第6期,1934年6月1日。
㉕ 杨周翰:《论近代美国诗歌》,《世界文艺季刊》第1卷第3期,1946年4月。
㉗ 穆木天:《诗歌朗读与诗歌大众化》,《穆木天诗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页。
㉘ 谷夫:《朗诵诗运动》,《学习》第1卷第6期,1939年12月1日。
㉙ 冯乃超:《诗歌的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14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㉚ 锡金:《朗诵去》,《时调》第3期,1937年12月。
㉛ 高兰:《展开我们的朗诵诗歌》,《时调》第3期,1937年12月。
㉜ 朱自清:《美国的朗诵诗》,《时与潮文艺》第5卷第1期,1945年3月15日。
㉝ 杜若:《关于朗诵诗》,《战时艺术》第5期,1938年5月1日。
㉞ 施蛰存:《支加哥诗人卡尔·桑德堡》,《现代》第3卷1期,1933年5月。
㉟ 穆木天:《诗歌的形态和体裁》,《穆木天诗文集》,第385页。
㊱ 徐迟:《诗歌朗诵手册》,集美书店1942年版,第40页。
㊲ 高兰:《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高兰编:《诗的朗诵与朗诵的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㊳ 陈方:《纪念“七·七”》,《浙江潮(金华)》第18期,1938年7月7日。
㊴ 高兰:《给绿林好汉》,《文艺月刊》第4卷第1期,1940年1月16日。
㊵ 朱自清:《抗战与诗》,《新诗杂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页。
㊷ 朱复:《现代美国诗概论》,《小说月报》第21卷第5号,1930年5月10日。
㊸ 吴风:《关于马斯特斯》,《中国诗坛(广州)》光复新版第1期,1946年1月15日。
㊹ 珠还:《关于马斯特斯》,《益世报》1947年2月12日。
㊺ 马凡陀:《鲁迅先生的轻松诗》,《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10月19日。
㊻ 杜运燮:《自序》,《杜运燮六十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㊼ 很多人将W. H. 奥登视为英国诗人,由此探讨杜运燮所受英国诗歌的影响,实际上奥登于190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25年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书,1939年又移居美国,1946年加入美国国籍。从这一角度来说,也可将他视为美国诗人。
㊽[55] 唐湜:《杜运燮的〈诗四十首〉》,《新意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6页,第56页。
㊾ 杜运燮:《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1946年2月25日。
㊿ 杜运燮:《林中鬼夜哭》,《诗四十首》,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第21页。
[51] 杜运燮:《老人》,《诗四十首》,第65—66页。
[52] 杜运燮:《追物价的人》,《诗四十首》,第107—109页。
[53] 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7页。
[54] 马凡陀:《轻松与严肃的诗》,《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10月10日。
[56] 穆旦:《农民兵》,《新诗歌》第4期,1947年5月15日。
[57] 杜运燮:《一个有名字的兵——轻松诗(Light Verse)试作》,《诗四十首》,第115—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