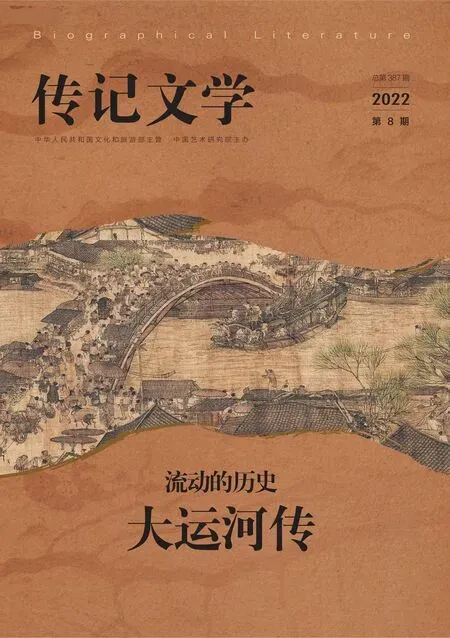赵清阁先生未了的遗愿
陈子善

1948年的赵清阁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若要说女作家,汉代的蔡文姬,唐代的鱼玄机、薛涛,宋代的李清照等,虽都已流芳千年,也只是屈指可数。明清以降,闺阁诗人固然为江南文化增添华彩,真正女作家群起、争奇斗艳,却要到“五四”新文学勃兴之后了。冰心的《春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萧红的《呼兰河传》,直到张爱玲的《传奇》,不仅当时风靡一时,后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日益显赫。但是,查《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还有一位赵清阁,1949年之前的著作竟有27 种之多,还不包括与老舍合作的话剧《桃李春风》等。就数量而言,已超过了上述任何一位女作家,却长期被冷落。当然,作家文学成就之大小不能以创作数量为标准,但这样一位笔耕如此之勤奋而命运又很坎坷的女作家,近年来对她的研究虽然已有所开展,仍然薄弱得很,与她的文学贡献还很不相称。这是我撰写这篇回忆文字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我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多年,与前辈女作家多少也有些接触。通过信的有冰心、杨绛先生,见过面的有陈学昭、罗洪先生,陆晶清先生住在上海,却未能拜访,一直引以为憾。因我研究郁达夫,画家兼作家的郁达夫侄女郁风先生,自然也来往不少。请益最多的,北京是赵萝蕤先生,上海就是赵清阁先生了。我已回忆了不少交往过的文坛学界前辈,但女作家除了写过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的张爱玲,还没有写过别位,这是不应该的,该写一写赵先生了。
至于为什么起了“赵清阁先生未了的遗愿”这样一个题目,文末自会揭晓,且容我慢慢道来。
我是怎么认识赵清阁先生的,如是主动写信向她请教,地址何来?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来自她的老友施蛰存先生。施先生文人雅兴,在20 世纪80年代初一连好几年自印贺年片分赠友人学生,分别印过女画家陈小翠和赵先生的国画,施先生都送我,而今他精印的陈小翠《仿赵承吉采菱图》还在我的书橱里,赵先生的那枚《泛雪访梅图》却不知哪里去了。因此,我有可能向施先生打听到赵先生的地址。二是我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包子衍兄很熟,而赵先生当时已是包兄的前辈同事,我也可能向包兄打听到赵先生的地址。到底来自何方?却已无法记清。
不管怎样,我约在1986年2月初给赵先生写了第一封信。这封信她老人家似未收到,但她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并在同年2月23日写了回信:
陈子善同志:
大函收悉。的确记不起您来过信,但最近自《香港文学》上看到您的文章,因此名字熟稔。
方宽烈先生来沪,愿惠访,自当欢迎。届时请兄电话联系,375019,一般均在家。匆复,祝春吉
赵清阁 二.廿三
她在信中明确告诉我,她未收到我的第一封信。“最近在《香港文学》上看到您的文章”,具体应指我为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1985年10月第10 期策划了郁达夫遇害40 周年纪念专辑,并发表了《墙内开花墙外红——郁达夫作品在香港》等文。以及同年12月第12 期上有我的《〈郁达夫文集〉未收郁达夫作品目录补遗》,赵先生在这一期上正好也发表了散文《母亲》,我们有同刊之雅。我写此信是通报赵先生,香港的文学史料研究家方宽烈先生将来沪,拟拜访她,但方先生后未成行。

赵清阁1986年2月23日致作者函
赵先生这通短简是从上海长乐路1131 弄1 号202 室发出的,当时她正住在那里。而现存她给我的第二封信已寄自吴兴路246 弄3 号203室,这是她的新住地,是当时新建的高知楼。记得246 弄3 号的住户,还有501 室的孙大雨先生、1001 室的王元化先生,好像复旦大学原校长谢希德先生也住在这幢楼里。作为3 号203 室、501 室和1001 室的经常到访者,我对这幢楼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有幸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在赵先生、孙先生和王先生那里接受教诲。一个下午拜访三位肯定来不及,往往是拜访两位,如果谈的事多,就只能拜访一位了。
赵先生给我的第二封信就比较长了,照录如下:
子善同志:新年好!
卅日来信及附件均收到。
《联合报》廿七日的,您竟这样快就看到了,不知是否直航寄来的?我恐怕月中才能见报,估计是从香港转递。最近该报又为春节约稿,我则以投递不便而踌躇。不实行“三通”,交流是困难的。


赵清阁1989年1月3日致作者函
秦贤次先生我不认识,去年他莅沪,有所闻。可惜未获一晤。这次他为我写简介,殊为不易。
四十年代我编的一本女作家小说散文集《无题集》,去年湖南文艺出版社要去重印,改名《皇家饭店》,但以新华书店预定印数不足,至今尚未付梓。除非我愿自购千余册。我未同意,因我无法为此摆书摊。只好听之。
梁实秋纪念文集,经济效益也不会高,恐出版难。出版社若能着眼长远效益,社会意义就好了!建议你和北京三联书店试恰(洽),请他们从统战角度考虑接受。(拙作纪念梁文已收入我的一本集子,又略作修订。)
谢谢您复印的拙作。耑此,顺颂冬安
赵清阁
一九八九.一.三
信中所说的“《联合报》廿七日”指1988年12月27日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的赵先生的一篇文章(应是她的散文《文苑坎坷记》,已收入她自编的最后一本散文集《不堪回首》),我把剪报寄给赵先生,引发了她的一通议论。但她误解了,我之所以那么快看到,是因为正好有位台湾友人来沪,从飞机上带来的。秦先生指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他1988年10月来沪参加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首届学术研讨会,即信中所说的“去年他莅沪”。赵先生在“联副”发表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简介”应出自秦兄之手,故赵先生称之为“殊为不易”。
不过,此信的重点是赵先生所编的《无题集》的重印和拙编《回忆梁实秋》入选她的大作两件事。抗战胜利后,赵先生从重庆回到上海,应主持晨光出版公司的赵家璧先生之请,主编一本现代女作家作品选,而且,赵先生“不愿选取女作家的旧作,而要求她们写出新作”,尽管“组稿相当困难”,赵先生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终于大功告成。1947年10月,赵先生主编的《无题集》由晨光出版,收入冰心、袁昌英、冯沅君、苏雪林、谢冰莹、陆小曼、陆晶清、沉樱、凤子、罗洪、王莹和她自己共十二位当时在海内外的女作家的小说、散文新作,以第一篇冰心的《无题》题目作为书名。这本《无题集》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唯一一本女作家新作合集,颇难得。而袁昌英的《牛》、陆小曼的《皇宫饭店》和赵先生的《落叶无限愁》等也都成为这一时期女作家创作中的名篇。四十多年后,又是赵家璧先生建议重印《无题集》,赵先生才在致我信中写到此事,并为印数不够而犯愁。此事结果还是令人欣慰的,书名改为《皇宫饭店》的这部小说散文集,在赵先生给我此信九个月后,终于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印行了。
此信所说的最后一件事与我直接相关。我那时已踏入梁实秋研究领域,正着手编集《回忆梁实秋》一书。我知道赵先生和梁实秋交往不少,梁实秋逝世后写过回忆文章,故拟收入拙编以光篇幅,赵先生同意了。她先后写了两篇回忆文章,一篇为刊于《文汇报》的《忆梁实秋先生》,另一篇为连载于《团结报》的《隔海悼念梁实秋先生》,她提供给我的是两者的合并文,仍以《隔海悼念梁实秋先生》为题,也收入了后于1989年10月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她的散文集《浮生若梦》。但她在信中建议把《回忆梁实秋》书稿送北京三联书店一试,我却没有照办。为求出书快,交给了吉林文史出版社,结果印出来的《回忆梁实秋》竟漏印我的“编者前言”,引起了海内外读者的误会,但木已成舟,后悔莫及。

赵清阁1994年2月22日致作者函
赵先生此信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细节,即所用信封是旧信封拆开反过来重新粘贴而成,这件小事当然可以看出赵先生的节俭,而另一方面,这旧信封大有来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信封,寄信人署“刘”,我推测应是当时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刘麟先生。这是我为写此文重检赵先生来信的一个小小的新发现,可见当时现代文学馆与赵先生还是有联系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现存赵先生给我的信共四通,另两通都写于1994年,而且越写越长,谈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第一通是1994年2月22日写的:
子善同志:
新年收到大函,甚谢!
承告台湾三民书局情况,至感。散文尚在编辑修订中,一俟竣事,再定夺出处。台湾印刷好,出书快,大陆已有不少作家在台出书,如肖(萧)乾、蛰存、朱雯等,但他们都是在买(卖现)成翻译,不像散文,虽系纯文学,也难免反映现实中有所犯忌,为此不无顾虑,唯恐触犯两峡(岸)!“联合”似乎超脱些,拟与痖弦通信时一问。
去岁台北开了一次“四十年文学会议”,乃联合报主办,你参加否?不知其时限如何框局?听说颇有笑谈。你如公(果)主持图书馆工作,于文学研究必大有裨益。
大陆大事宣传严肃文学,而出版社仍着眼市场效益,对散文、诗歌、戏剧不予接纳,其实并非读者不欢迎,乃新华书店售货员不欢迎也。因此,热衷文学事业的人宁肯自费印书,自己叫卖,为之啼笑皆非!我老矣,也该搁笔了!
专复,顺颂
新春安吉
赵清阁
94.2.22
在这封信中,赵先生所说的“散文尚在编辑修订中”,当指她的散文集《不堪回首》,后来于1996年4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赵先生送了我一本,扉页题字如下:
子善同志正之
赵清阁赠 96.11.4 病中

赵清阁赠本文作者的散文集《不堪回首》
信中写到她认识的大陆老作家肖(萧)乾、施蛰存、朱雯等在台湾出书,写到当时的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他跟我也有很多联系,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认真负责的编辑家。还写到1993年12月在台北举行的“两岸三地中国文学四十年学术研讨会”。此会是大陆和台湾文学界首次在台湾召开学术交流会议,由痖弦先生策划操办,大陆的王蒙、刘恒、李子云、吴亮、程德培,以及当时在海外的刘再复、黄子平等位都参加了。赵先生虽然年高,仍十分关心中文文坛动态,关心两岸文学交流,所以在信中特别提及。她所问的“不知其时限如何框局”,我当时无从奉答,现在才突然想到,或为1953年台湾三报联合版改名为《全民日报、民族报、经济日报联合报》,到1993年正好是四十年之故?至于她所说的“听说颇有笑谈”,我未与会,就不得而知了。


赵清阁1994年3月22日致作者函
赵先生在此信中还对当时一些老作家出书难,出版散文等集子尤难的不正常现象提出批评,发出感叹,这些观点也曾在她公开发表的《著书·出书的感慨》等文中表达过,至今读来仍心有戚戚矣。
一个月以后,赵先生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此信最长,既谈她出书的事,也谈她生活上的困扰:
子善同志:
上月来信收悉。谢谢你对我结集散文《往事如烟》的鼓励,你是我的散文读者知己,所以错爱,深感欣慰。但散文无市场价值,加之我素无出版社关系熟人(非“关系户”),因而迄未找到出版社。原拟交台湾,三民书局表示:他们以两峡(岸)尚未关系正常,故对作品可能要作修改。修改我不介意,但如何修改?我不得知,万一有所歪曲,岂不又生麻烦?92年《联合报》曾转载我发表于《香港文学》之关于苏雪林一文,而文中妄加她“反共”字句,我函询痖弦,他也不知何人所为。这种改、增,对苏、对读者影响都不好。因此在台出书议不敢轻率,大陆已托端木蕻良设法推荐,不成功,就自费印出,为的今年八十又一,结束文学生涯!虽今倡导精神文明建设,鼓吹严肃文学,恐亦难能落实也!
拜托一事:阅报你校有发明电视眼镜应世,但未讲何处出售,拟请一询。我近年患白内障,(秋天开刀),视力日衰,唯一电视的文娱生活又不愿放弃,能得此眼镜,获益非浅!
你还研究现代文学否?近得重庆出版的《卅年代中原诗选》,颇感惊喜:①诗歌这一冷门文学竟还有人愿出,②看到久已佚名,被人遗(忘)的诗人诗作,难能可贵,③本人自己毫无记忆的诗作居然看到,感触万端!如你需要,便中来舍,当赠你一本。我买了几本。不易呵,应该支持。
即颂
文祺
赵清阁 94.3.22
当时我一定知道了赵先生将把新写的散文结集《不堪回首》(原题《往事如烟》),写信向她谈了我的期待,她才会在这封回信中把我称为“散文读者知己”,其实我是完全不敢当的。关于是否在台湾出书,赵先生在此信中进一步详谈了她的想法,老人家的态度认真而谨慎,最终,她自编的最后这部《不堪回首》散文集还是交给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而她因白内障导致观看电视不便,希望我帮她代购“电视眼镜”,此事我已了无记忆,但愿当时没让她失望。
此信最后一段,赵先生让我分享了她的喜悦。1993年8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诗人周启祥主编的《三十年代中原诗抄》,这本诗集现在几乎无人提及了,却是一本颇具特色的新诗选本,是现代文学作品整理和研究“地方路径”的一个生动范本。书中除了收入徐玉诺、于赓虞、陈雨门、姚雪垠、苏金伞等知名的河南作家的新诗,大部分是名不见经传的河南新诗人的作品。其中女诗人仅三位,第一位就是赵清阁先生。所以,她完全有理由“颇感惊喜”,为居然还能看到“自己毫无记忆的诗作”而“感触万端”!书中共收入她的《别离曲:寄金芝姊》《新生:献给关心我的朋友》《春的咒诅》《净歌》四首新诗,且录她19 岁时所作的较为短小的《春的咒诅》,以见其早年诗艺和倔强刚烈性格之一斑:
春来了吗?——我不相信,/这生活怎的依然是萧瑟低沉;/呵!我已是死了一半的人,/不能感受这阳春的温馨。
春来了吗?——我不相信,/过去的美好何以不能追寻?/呵!今日我是如此的颓废,/失掉了这人间的春深。
我将祈求着大地的陆沉!/让这恶浊的人间同归于尽;/春呵!连你也要埋没在内,/请不要再向我故作骄矜。
赵先生与我通信当然远不止这四通,但当下只检出这四通,只能对这四通略作诠释。值得庆幸的是,还检出赵先生写给我的一纸毛笔字,照录如下:

赵清阁书赠作者的《杜诗集句》
杜诗集句
浮生一病身,惨淡向时人。
江城带素月,披豁对吾真。
子善同志雅嘱
庚午中秋赵清阁书于上海
庚午年是1990年,该年中秋是10月3日,赵先生应我之请,写下了这首《杜诗集句》。字写好钤章时,赵先生一不小心,把闲章“不甘老病”钤倒了,不得不重钤了一次。于是,这幅《杜诗集句》上就留下了一正一反两方“不甘老病”,颇有趣。记得赵先生把这幅字寄给我时,还在信中自嘲了两句。字笺保存下来了,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
当时收到这首集句,我有点意外。原以为赵先生会手书自己的诗作或抄录前人之作给我,没想到她会写集老杜句的小笺给我。转念一想,这是她当时心情的自然流露,也说明她熟读杜诗并深有感触。《杜诗集句》首句出自老杜的《奉送十七舅下邵桂》:“绝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第二句出自《寄张十二山人》:“艰难随老母,惨淡向时人。”第三句出自《听杨氏歌》:“江城带素月,凉乃清夜起。”最后一句出自《奉简高三十五使君》:“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被赵先生这样一集,焕然一新,成了一首传达她自己所思所感的五绝了。中秋夜集“江城带素月”句无疑是恰切的写实,而“披豁对吾真”句更是赵先生一生真诚待人的写照。
赵先生曾自述:“我自幼喜爱旧体诗,但年轻时仅写些新诗,偶尔习作旧体诗词。”她喜爱杜甫,与老杜的诗沉郁深邃、气象万千有关吧。40年代后期,她在沪参与编辑《文潮月刊》,发表过友人梁实秋的《杜审言与杜甫》等文,恐也有点关系。这首《杜诗集句》,我不知道赵先生是否还书赠别人,但“浮生”这个词,她一用再用,她晚年的第三本散文集不就题名《浮生若梦》吗?书前的序诗里也有“浮生”句:“砚贮相思泪,笔志师友情。浮生若梦幻,处处风雨声。”她还把晚年所著四本散文集的书名都写进一首七绝中:
沧海泛忆往事真,
行云散记旧风尘。
浮生若梦诗文泪,
不堪回首老病身。
昨立春偶得七绝一首,句中嵌进余之散文集书名,尚觉自然贴切有意趣。
虎年新正赵清阁于上海
《不堪回首》出版于1996年,两年后的1998年正是“虎年”。她在该年2月18日“立春”日写下这首带有自传色彩的七绝,一年之后就谢世了。把自况意味甚浓的《杜诗集句》和这首七绝联系起来读,我们或许更能体会赵先生晚年孤身一人,回首前尘旧痕时的苍凉心境。
追忆赵清阁先生,有件事要不要写?我颇费踌躇。这件事读者也许能猜到,即赵先生与老舍先生的恋情。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新史料的陆续出土,此事可说已完全水落石出。当年我登门向赵先生请益时,已经听到一些关于她和老舍的风言风语,但我是后辈,前辈之间的事,特别涉及两位我尊敬的作家的私密感情,我是没有资格发问,更没有资格说三道四的。我一直认为经历了那么多惊涛骇浪的赵先生他们那代人的追求、困扰和情感煎熬,后人是很难理解的,更不容后人胡乱猜测和亵渎。所以,去拜访赵先生,我一直恪守这条原则,绝不唐突。只有一次,很巧,赵先生房中正好悬挂着一幅老舍的字,具体内容已记不真切,赵先生见我站着端详良久,就问:“你没有见过老舍的字吗?”我连忙回答:“确实首次见到老舍先生的真迹,很荣幸。”赵先生笑笑,招呼保姆倒茶了。此后,老舍再未进入我和赵先生之间的话题。不料,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还是与之相关了。
1999年2月3日是老舍百岁冥诞,1998年下半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就开始筹备纪念活动,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当时在纪念馆工作的傅光明兄率摄制组来沪,拟采访一些文坛前辈,以赵先生与老舍的关系,当然是首选。傅兄找到我,要我先代为预约。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得有次拜访赵先生,闲聊中不知怎么谈起巴金老人把他的大批藏书和资料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我就脱口而出,建议赵先生也可这样做。赵先生听了似有不悦,不置可否。我一看苗头不对,马上转换了话题。所以,我对赵先生与现代文学馆的关系微妙是有所觉察的,虽然正如前述,她与刘麟先生还保持着通信,刘麟先生的《无声的对话》一文还披露了赵先生与他关于冰心老人以往书信的四通信札。但既受傅兄之托,那就尝试一下。
此事结果,可想而知,失败了。这次为写这篇回忆,我特向傅兄核实,他2022年3月8日的答复如下:“1998年10月20日,兄给赵先生打电话,后回复我说‘赵先生要看明天身体情形再定’。弟开始在兴奋中期待,次日,兄电话告知‘婉拒’。”赵先生具体怎么“婉拒”的,我的日记未记,现在更记不清了。我1998年10月21日日记的相关内容则是这样的:
中午至感恩苑见傅光明及现代文学馆摄制组,同席还有王为松、雷启立和唐晓云,由唐赏饭,畅谈老舍和文坛往事。下午陪同傅光明等至华东医院访柯灵,听柯灵谈纪念老舍百岁冥诞的感受。
赵先生当时确在病中,“身体不舒”固然是实情,不愿接受现代文学馆采访,尤其不愿对文学馆来人谈论老舍,恐怕更是实情,所以只能“婉拒”。一年之后,她就与世长逝了。未能留下关于老舍的谈话录像,确实令人遗憾。但若设身处地为赵先生想,她又怎么谈呢,能说些什么呢?如此说来,我毕竟还是唐突了。不知赵先生是否会怪我“多事”,徒增她的烦恼。不过,我们以后还有联系,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我2009年主编《现代中文学刊》以后,先后发表了老舍和赵清阁研究者史承钧、傅光明等位发掘“舒赵之恋”史实的文章,因为我认为这对研究这两位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情感历程是不可或缺的。今年4月发表的最新一篇《老舍写给赵清阁的一首情诗》(史承钧作),公布了老舍作于1941年2、3月间的一首五言古诗手迹,赵先生一直保存至离开人世,不妨转录如下:
童年弱且贫,事事居人后:邻儿有彩衣,默默垂我首!及壮游四方,营营手到口;文字浪得名,笔墨惭深厚。中岁东海滨,陋室安妻丑;方谓竟此身,书史老相守。血腥起芦沟,仓促西南走。大江日夕流,黄鹂啼翠柳,逢君黄鹤楼,淡装明无垢;相视俱无言,前缘默相诱!灯火耀春暮,分尝一壶酒,薄醉情转殷,脉脉初携手!幽斋灯半明,泪长一吻久!先后入巴峡,蜀山云在肘:辛勤问暖寒,两心共臧否,天地唯此情,此情超朋友!日月谁与留,四载荷连藕,我长十六龄,君今方三九。桃源春露秾,鸳鸯花下偶,缓缓吹东风,花雨落窗牖!愿斯千里缘,山河同不朽,世世连理枝,万死莫相负!
一九四一年于渝
2021年9月28日至12月26日,上海博物馆举办“高山景行:受赠文物展”。文物展结束前夕,我赶去观看,还认真看了两遍,结果越看越生气。

老舍写给赵清阁的五言古诗

赵清阁与老舍合作的剧本《桃李春风》
必须把时钟转回整整三十年前。1991年年末的一天,我有幸应赵清阁先生之邀,参加她向上海博物馆捐赠所藏字画的小型仪式。大概她知道我对现代作家艺术家的字画有浓厚兴趣,所以在捐赠仪式前通知我,邀我参加。我当然是受宠若惊,求之不得。那天下午到场的除了赵先生本人,还有上海博物馆的几位负责人,都是文物鉴赏方面的专家,记得有馆长马承源先生、副馆长汪庆正先生等,还有谁,已记不住,而唯一的年轻人就是我。记得赵先生捐赠的字画,除了扇面,都已装裱,一轴又一轴,满满放在一张大桌上,工作人员一轴一轴徐徐打开,让大家观赏,赵先生还不时在旁解说几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么多名家真迹,真觉得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饱了眼福。后来,我在1992年5月23日济南《作家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专页》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观赵清阁捐献字画有感》,引录关键的一段:

赵清阁绘赠翻译家罗玉君的岁朝清供图



冰心题赠赵清阁的《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赵清阁题赠施蛰存的《长相忆》
她这批历经战乱和“文革”劫火终于幸存的近现代名家字画我是首次见到。除了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沈尹默等书画大家的精品外,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鼎堂(郭沫若)、老舍、田汉、赵景深等现代作家的书法作品。鼎堂1943年为赵清阁书写的一幅扇面,工整的蝇头小楷,风格与后来的完全不同。而老舍书写的一幅扇面,内容为《忆蜀中小景》五绝两首,极有可能还是老舍的佚诗。更为难得的是徐志摩夫人陆小曼在40年代末写的一幅扇面,用娟秀的正楷书录了徐志摩诗《这年头活着不易》(个别字句有出入),可谓别开生面,因为扇面上题写新诗是很少见的。
以上都是我的亲眼所见,真实记录。仪式结束后,上海博物馆方设晚宴感谢赵先生,我叨陪末座。看得出来,赵先生那天很高兴。在宴席上,不记得是马馆长还是汪馆长主动表示,为感谢赵先生的慷慨捐赠,上海博物馆将把这些珍贵字画编印成书,以为纪念。赵先生虽然连说不必,但脸上还是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这个情景虽已时隔三十年,却仍然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也因此,我那篇小文的结尾特别写道:
听说上海博物馆有意把赵先生捐献的字画编印成册,以广流布,这是令人欣喜的好消息,我期待着此书早日问世。

赵清阁所藏巴金译著《门槛》
万万没想到,等啊,等啊,一直等到1999年11月27日赵先生逝世,这本纪念图册仍杳无音讯,不见踪影。我后来去看赵先生,不敢再提此事,怕她不高兴。但我觉得,赵先生虽然大度,虽然从不再提此事,当她离去时,如想起这桩未了的心愿,还是会感到遗憾的吧?
更没想到的是,在赵先生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字画三十年后,上海博物馆举行受赠文物展,又把赵先生的捐赠遗漏了!就参展的现代作家的捐赠而言,文物展展出了郑振铎捐赠的汉代人物画像砖、巴金捐赠的董其昌行书诗册、夏衍捐赠的纳兰成德(展览原件为“成德”)手札长卷,还有陈从周捐赠的陆小曼东山骑归图轴,唯独没有一件赵先生的捐赠,众多“高山”之中就缺少了赵先生这一“山”。我前前后后仔细看了两遍,确认确实一件没有之后,在展厅里徘徊良久,大为惊讶之余,不禁悲从中来!赵先生竟然缺席,难道她的捐赠水准不够,不值得展出一二?与董其昌、纳兰成德等相比,赵先生的收藏也许比不上,但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沈尹默等的字画,哪一件比陆小曼的差?陆小曼自然应该展出,即便是陆小曼的字画,她写给赵先生的徐志摩新诗扇面,才是独一无二的呢!
在我看来,赵先生捐赠的这些名家字画,不仅是她历经劫波的幸存,是她与文坛画苑前辈和友好交游的真实见证,也是珍贵的文物、特殊的文献,很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可供深入研究的价值。当年,赵先生把它们捐赠上博,一定是经过了郑重的考虑。不实践诺言把它们印出来,也不把它们展览出来,实在是辜负了赵先生的一片苦心、一番诚意啊!
而今,赵清阁先生、马承源先生、汪庆正先生都已谢世,不知还有几个人知道这件往事。我作为一个当时在场的见证者,有责任把这段史实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
最后,我忍不住发问,赵先生未了的遗愿,何时才有可能实现呢?
注释:
[1]参见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53 页。
[2]严格说来,我以前曾两次写过赵先生,一是本文第五部分将要引述的短文《观赵清阁捐献字画有感》,二是另一篇短文《赵清阁三提张爱玲》。后者已收入拙著《不为人知的张爱玲》,商务印书馆2021年5月初版,本文就不再重复了。
[3]赵清阁先生的《泛雪访梅图》作于1966年,“辛未早春”(1991年)“题赠”作家马宗融之女马小弥。2022年5月在杭州西泠印社拍卖公司“巴金的朋友圈·马小弥上款及旧藏现代文学珍品专场”拍卖会上拍出。
[4]赵清阁:《怀故旧,思悠悠:〈无题集〉重印后记》,《皇家饭店:现代女作家小说散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 页。
[5]参见赵清阁:《著书·出书的感慨》,《不堪回首》,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8 页。
[6]赵清阁:《春的咒诅》,周启祥等编:《三十年代中原诗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0 页。
[7]赵清阁:《茅盾谈旧体诗词》,《不堪回首》,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 页。
[8]赵清阁:《诗代序》,《浮生若梦》,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插页二。
[9]这首七绝手迹初刊赵清阁著、沈建中编:《长相忆》,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正文第3 页。
[10]关于“舒赵之恋”,近年海内外出版的相关著作如下:一、赵清阁编、史承钧校订:《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书中收录老舍致赵清阁信四通,写于1955年4月25日的第一信,原稿老舍自称“克”,称赵“珊”,为《呼啸山庄》中恋人苡珊和安可夫的简称。二、傅光明著:《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书中收入韩秀谈“舒赵之恋”的信多通。三、洪钤编:《中国现代女作家赵清阁选集》,台北秀威资讯科技公司2016年版,书中《编选者后语》以知情者身份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集中讨论了“舒赵之恋”。
[11]参见刘麟:《无声的对话》,《文学的思念》,西苑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2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