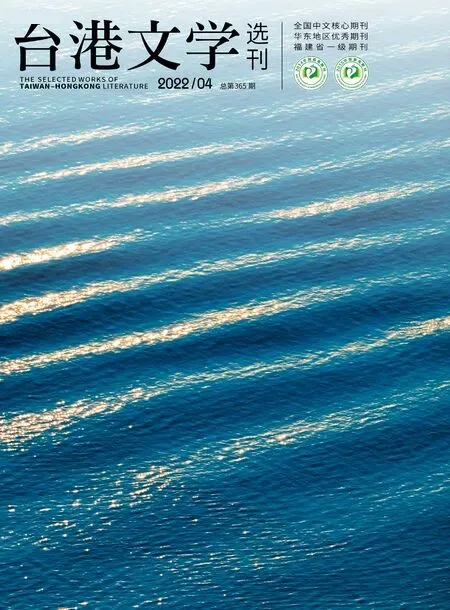一部拓荒性巨著
——我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 李尚财(中国福建)
夏志清先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大家。
从1961年出版至今,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一部作品,能够在出版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被翻版并流传,已足够证明其生命力之顽强。尤其文学理论著作更为难得。有几本文学理论著作50年后还能一看呢?虽然,《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颇受争议,但即便是夏先生最极端的反对者,也不能完全无视他的某些贡献与真知灼见。他的诸多理念与见解,早已春风化雨,融入到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肌理与血脉之中。自其之后,中国任何文学史家重整现代文学史,均很难绕过这部奠基之作。
我曾不止一次暗自琢磨,为什么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是他?不,确切说,为什么只有他能够将《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得如此不同凡响?寻思了一番,认为这个人也只能是他!舍他其谁呢?时也命也运也。彼时,夏先生虽然年纪尚轻,却已学贯中西,对中西文学的生成与差异了然于胸,又恰巧站到了中西文化交合的特殊站位上,他几乎成了不二人选。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历史选择了他为中国文学发声。
1948年,时为北大英文系青年教师的夏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三年半后(1951年)获得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博士即将毕业时,由于不计划回国教书,又没能进入美国高校任教,他不得不开始打起“零工”。尴尬的是,出国前虽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但他精攻的是欧美文学,如今却因为“就业”需要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学。他打的第一份“零工”,是协助同校政治系教授饶大卫编写《中国手册》,负责《文学》《思想》等版块内容的编写。他由此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这个令他感到非常诧异。自此,他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也悄然结下了缘分。1952年,他以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为选题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报并获批为期3年(每年4000美元)的补助资金。三年无拘无束的生活,他阅遍了各种渠道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国文学著作。他的中西文学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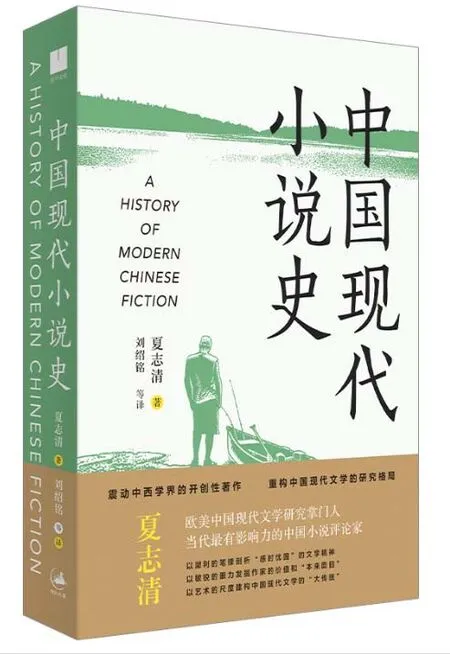
由《中国现代文学史》改成写“小说史”,是因为夏先生在通览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之后,“实在觉得新文学小说部门成就最高,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此后多年,再就业,辗转多所大学教书,从中国哲学教到英美文学,从先秦诸子讲到欧美名著,课目跨度大——虽为“生存”所需,却为他的批评事业建构了更加深邃广阔的学识背景。十年铸一剑。1961年3月,夏先生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自此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被学界誉为“一部拓荒性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成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文学的一本“教材”级的作品。夏先生也由此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王际真因对鲁迅颇有研究,看过小说史《鲁迅》专章后,认为夏先生对鲁迅的看法与众不同,对他的才学与眼界大为佩服,并认为,夏先生的“英文造诣也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更斯两位大师媲美”。
经王老先生的举荐,夏先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他长期引领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中国作家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推手。
我读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2005年3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版本,也是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个版本。早就对这本书有所耳闻,尤其夏先生推广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文学成就早已传为文坛佳话。换句话说,这几位作家能够在国内、国际上“火”起来,形成“沈从文热”“张爱玲热”“钱锺书热”,正是由于夏先生的助推。如果不是夏先生的发掘与论证,他(她)们是否将永远埋藏在历史的故纸堆中了呢?有可能。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喜欢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我们应该要感谢夏先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对媒体说:“如果沈从文1988年没有去世,他肯定获诺奖。”马所披露的信息之真假已无法印证,但沈先生在国际文坛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却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先生对沈从文的评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最杰出、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对张爱玲的评价是“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他评价钱锺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
《中国现代小说史》全书十九章,其中十章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等。这些用“专章”体现的作家,便是夏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其他各章以“综述”的形式处理了分量稍轻的作家,同时概括了各个时期形成文学史的若干要目。夏先生不仅将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列入“专章”,甚至给予了他(她)们不逊于鲁迅、茅盾、老舍等“主流”大家的评价。可以说,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后来能够被纳入到新时期文学研究领域的视野上来,同夏先生的“专章”助推有直接关系。
我在书店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当即就感觉到了它的“不一样”。我首先被它的视野所震惊,夏先生显然将作家与作品搁置到世界文学的大盘上,纵贯古今,横跨中西,引入了诸多古今中外文学实例进行比较,形成相互阐明的功效;其次是,在上述这一视野的参照之下,作者的行文倍显自信且不失权威,不论批评还是赞许,敢于下评断;再者是,文本清新、灵动、雅正,对作家某些弊病的点评,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不失率真,涉笔成趣,严谨又不失轻松,严肃却不死板,具有理论文章难得的可读性。直令人感慨“文学史”还可以这样写呀?这与我之前看到的国内文学史著作都不一样。通过夏先生的视角,仿佛飞鸟掠过群山——一览众山小,中国文坛的泰山北斗,其优点与局限性全都显现了出来。鲁迅怎么样,茅盾好不好,老舍什么特色,张爱玲为什么好……他(她)们的优势与局限是什么,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好,一一道来,下的评断令人信服!就连钱锺书看后,也不禁盛赞其“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我认为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能够不同凡响,有如下几方面因素:一是他的“站位”。他身处异国的站位,使之可以抛下一切思想包袱,用更超脱、纯粹、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谁写得好就是好,谁写得不好就是不好,敢于推翻价值、确立价值,完全遵照自己内心的判断与文学审美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对作家进行重新“排位”,为作家画像、为文学立传;二是他的天资与才学。如果说站位使他“敢说”,那么具备这个才学则使他“能说”,解读文本的功底深厚,艺术感觉敏锐,个人见解强悍鲜明。他具备做好这件事情的能力;三是率真的性情。敢说、能说还不行,还要愿意说。他不仅说了,还心口如一,说得很彻底。正是这些因素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独特品格与魅力所在。我由此也喜欢上了这本书。
因为喜欢,十几年来我时常将它从家里、办公室来回带,翻开哪页看哪页,随手翻开都能看下去。出差如果只能带一本书,那就带上它,感觉耐读。我也知道一个人整天抱着一本“文学史”很不好,可是我就是喜欢它,而且百读不厌。每每翻阅,总能从中领略到夏先生的智慧并收获某种启示。它几乎成了我文学上的“圣经”。
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不难看出夏先生的文学主张。他推崇文学要有独立的品格,终归以“文本”的艺术性、思想性论高低,作家始终要站到文学的本位上来,保持具有穿透迷雾的眼力、发出“真声”的能力,在“人的文学”上用力,“借人与人间的冲突”来探讨那些“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这也是夏先生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作家应当从中受到启示。评论家亦然,应当少一些“媚权”吹捧,真正将才情用到“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上,去发掘、论证、提携你的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锺书!从而真正与作家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国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催生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创造出堪与世界水准相比的一座又一座文学高峰,为人类文明贡献宝贵的文学遗产。
夏先生一生著述颇丰,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有同样被奉为经典的《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另有多种评论、散文、随笔集。2013年12月29日,夏先生在美国纽约安然去世,享年92岁。一代饱学中西的文学史大家就此陨落,一颗智慧卓越的头颅停止了他对文学的思考,但是他和他的论著留给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