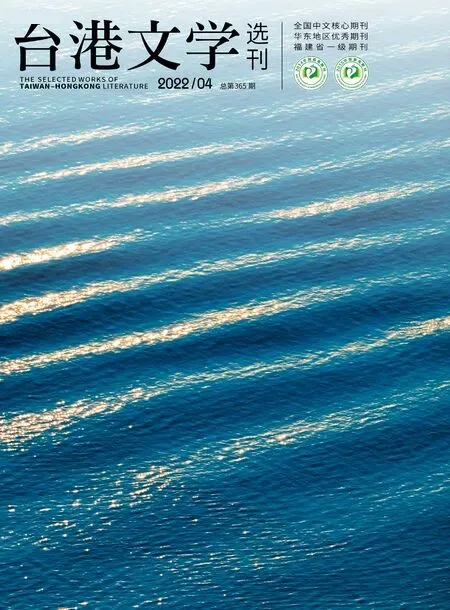马语者(外二篇)
■ 申 平(中国广东)
那匹黑马,已经闯入他的梦境好几回了。黑马瞪着一双愤怒的眼睛,前蹄刨地,嘴巴嚅动,好像在对他说着什么。可是他听不清,也听不懂。他非常奇怪,这匹马是从哪里来的,曾经跟他有过什么恩怨。他半生养马无数,但是对这匹马却一点印象也没有。
他隐约觉得,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果然,他就接到了侄儿的电话,说今天拍马场出事了,马群“炸群”了。平日那些温顺的马儿,忽然变得狂躁不安。也不知道是哪匹马带头嘶鸣一声,马群立刻就像接到命令似的,开始向四面八方奔突逃窜。这倒不怕,山谷四周都有围栏呢。可怕的是它们竟然疯狂冲向那些“拍客”,撞倒的撞倒,踢伤的踢伤,现场一片混乱。
黑马!
他的脑子里立刻打了个闪,把这事和梦里的黑马联系在了一起。他一边开车往拍马场赶,一边就在分析判断,难道,这匹黑马它是神马,是特意前来提醒我什么的?
出了城,走高速又走乡道,一路上都可以看见他为拍马场做的广告。他为拍马场付出的心血和成本,由此可见一斑。眼看“拍马事业”蒸蒸日上,他终于可以回到城里,遥控指挥了,怎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事故呢!
前面的山谷,就是他花重金打造的新景区拍马场了。景区围绕“拍马”这一中心,兼营骑马体验、马术表演等许多服务项目,平日里人气很旺,今天却冷冷清清。他不由着起急来。
侄儿正在景区门口等他,他下了车,开口就说:黑马!咱的马群里有多少匹黑马?
侄儿瞪着眼看他,好像没反应过来:黑马,黑马咋了?
肯定是黑马带头作乱!他说,走,带我去看马群!
二人走进山谷,直往山的最里面走。那里,就是养马的地方。路上他们经过拍客平台,他不由站住,详细询问出事的情况。
“拍马”,是他一手创办的新兴行业,就是把越来越没什么用处的马匹收集起来,放养在这山谷里,专门供摄影爱好者拍照。不是那种一人一骑摆姿势拍照,而是要营造万马奔腾的场面。每天,都有各地拍客来到这里,买票入场,等时间一到,上百匹马儿就在马倌的驱赶下,居高临下从山谷里冲出来,声若巨雷,气势宏大,令人震撼。马群还会冲过一片水域,马蹄下水花四溅,那些拍客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门票再贵也要来拍。
现在他们走进了马群,开始审查黑马。黑马有十几匹,他一匹匹地看,希望能有一匹和梦境里的一样,但是没有。他最后对侄儿下令:把这些黑马都处理了吧。
处理掉黑马以后,马群还真的平静了几天。但是这天夜里,那匹黑马却又重回他的梦境。这一回,它显得更加愤怒,前蹄刨地迸出了火花,它的眼睛里充满讥讽,身上的颜色也开始不断变化,一会黑,一会红,一会花。紧接着,就如放电影一般,他的梦里又出现了许多马匹,一会是声势浩大的战争场面,无数战马载着战士冲锋陷阵;一会又出现了农村的场景,马儿在卖力地拉车犁田……最后竟然出现了他的拍马场,拍客在排队买票,然后他们举着相机、手机,追逐着马群拍啊拍。黑马嘴巴嚅动,好像在斥责他,但是他还是一句没听懂。
早上醒来,他感到头痛欲裂,忽然意识到大事不好,急忙命令侄儿,今天不要开放拍马场了。可是侄儿却说:票已经卖出了,如果停业,要赔很多钱。最后,他还是被金钱打败了。
这一天,他亲眼目睹了马群“炸群”的情景:随着一声巨大的嘶吼声响起,一匹匹马儿突然变成了一支支利剑,纷纷射向四面八方。更有几十匹矫健的马儿,扬鬃奋蹄,山呼海啸般朝着拍客冲来,那些人一时间倒倒爬爬,喊爹叫娘,屁滚尿流……
这天,他惶恐不安地处理完“后事”,很晚才睡。刚一闭眼,就看见那匹黑马又来了。这一次,它的鬃毛都竖起来了。他慌忙俯身下拜,连连道歉,大声说马神啊,我知道你是马神,求你放过我的拍马场吧。不错,我确实是在依靠马群赚钱,可是我对马群也不错啊!再说我的本钱还没收回来啊!他看见黑马高昂着头颅,居高临下轻蔑地看着他,后来它又开口说话了,而且这一次他竟然听懂了,只听黑马说道:你们人类,真的是太自私、太贪婪了!你们想尽花招,究竟想把我们马族,压榨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他打了个激灵,突然醒了。恍然间,他好像明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明白。第二天,他咬牙做出决定:关闭拍马场,还马儿自由。
原载《西部》2021年第3期
入选2021年《小小说选刊》第12期
虎 鞭
老胡的家里,珍藏着一条虎鞭。
但是他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他有这个宝贝。因为,他一直无法确定这条虎鞭的真伪;最主要的,是直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当年他买下这条虎鞭,到底是属于上当受骗,还是助人为乐。
那个文质彬彬的小伙子,以前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有时候,他笑容满面地来了,带着大把钞票,要赎回那条虎鞭,还说着感激的话儿。有时候,他是得意洋洋地来,说你这个傻老帽,贪财鬼,你以为你花钱买了个啥,那就是个化学材料合成的玩意,你还真当宝贝了。你这土鳖,不骗你还能骗谁!
三十多年以前,有一次老胡去市里出差。在汽车站等车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忽然走到他的面前,先是向他打听什么事,接着就跟他攀谈起来。年轻人穿戴整齐,但是神情却有些忧郁,他说:我的爷爷当年是抗联战士,他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打仗的时候,曾经打死过老虎。虎肉吃了,只留下一条虎鞭。您知道吗,虎鞭那东西长得可神奇了,上面长满倒刺,龟头那里,分成三股叉……
老胡听到这里,紧绷的神经有点放松。因为他还真的听人说过,老虎之所以生育率低,就是因为虎鞭上生有倒刺,交配时母虎疼痛难忍。可是真正的虎鞭他没见过。
年轻人继续说:我祖上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就留下了这条虎鞭,还是挺值钱的。不瞒您,我出来闯荡,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大叔,您能不能帮我个忙,我把虎鞭先寄存到您这里行吗?
寄存?这东西能有多大,还用寄存?老胡的心其实已经开始动了。
也不是寄存,是……保管吧。我落难了,大叔您能不能多少给我点钱——我可不是卖,更不是骗哈。等我渡过难关,将来有钱了,我会去找您,再把东西赎回来。当然我要是没钱,不去赎,这东西就归您了。您看行吗?
开玩笑,我们根本不认识,你去哪里找我呀?
这不难。第一我看您就像个好人,我信任您;第二呢,我要记下您的身份证号码,还有您的住址和单位。有了这个,还怕找不到您吗?
唔……那你的虎鞭在哪里,我看下。告诉你,我可是学过医的。
啊,那您懂呀,那就更好了。走,我们去那边没人的地方。
于是,那条虎鞭,正如传说中一模一样的虎鞭,就展现在老胡的面前:在一条肉筋上面,伸出一根灰褐色的肉棒,上面真的长满倒刺,龟头那里不是圆的,也不是扁的,而是分出花朵般的三股叉来。老胡一边细看,一边在脑子里飞快地转着,想着应该怎么办。偏偏这时上车的时间快到了,他就咬了咬牙,怀着赌一把的心态,掏出身上仅有的150元钱(相当于现在的1.5万元)说:如果你不嫌少,就先拿着……
那个年轻人面露难色,很犹豫的样子。
老胡说:我真的只有这些钱了,你嫌少就算了。
年轻人叹口气说:那好吧。接着他就看了老胡的身份证,记了名字、号码和地址。
一晃十几年过去,年轻人并没有来找他。唯一知情的老婆说你肯定上当了,但是老胡不信。他经常翻出那条虎鞭打量,怎么看也不像是人工做的。后来有了网络,老胡就开始不断去网上搜索,去看真正的虎鞭到底长啥样。可是网上的图片五花八门,像的不像的都有,这越发把老胡整糊涂了。时间久了,就像他把虎鞭压箱底一样,他渐渐也把这事也压到了记忆深处。偶尔想起,受骗的感觉虽然越来越强,但却依然抱着几分幻想。有一回老婆拿这事说他,他立刻恼羞成怒,大吼大叫,仿佛被人揭了癞疮疤,吓得老婆再不敢提了。

胡振德 画
一晃又十几年过去,老胡渐渐老了。这日,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说到了虎鞭,说那东西长得如何神奇,如何有滋阴壮阳的功效,又如何值钱,随便一条也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老胡终于忍不住说:你们说虎鞭呀,我手里就有一条。
啊!你有虎鞭?哪里来的?朋友们立刻惊叫连连,就好像不认识他一样看着他。
老胡乘着酒兴,不慌不忙地说:这虎鞭,是我祖上留下来的。我爷爷当年是抗联战士,他在深山老林里打仗的时候,打死过一只老虎。虎肉吃了,只留下一条虎鞭。
哎呀,那可是宝贝呀!众人都艳羡地说,老胡,那你可发达了。能不能拿出来给我们开开眼啊?
没问题!老胡说,他感觉到,也的确到了让虎鞭得见天日的时候了,顺便也让人鉴定一下。众人便约好,第二天还来喝酒,看老胡的虎鞭。分手的时候,老胡明显感觉到,大家看他的眼神充满敬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呀。
老胡得意洋洋回家,就去柜子里找他的虎鞭,可是居然没找到。不对呀,明明就是放在这里的呀,搬了几次家,难道又放到别处去了?他问老婆,却遭到抢白;又问自己,记忆却很模糊。这一天,老胡把自己家里的犄角旮旯都翻遍了,可是愣是没有找到那条虎鞭,那条曾经让他梦绕萦怀的虎鞭。
被猫叼了?被狗吃了?被老鼠啃了?被老婆扔了?都似乎不可能,又都似乎有可能。
老胡最后瘫坐在地上,浑身冒汗,他真想抽自己的嘴巴。这么多年都没说,为什么现在犯贱要说呢!你老都老了,还要撒谎,往自己脸上抹粉,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在一瞬间,老胡觉得自己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恍惚间,他甚至无法确定,那件事是否真实发生过。那个年轻人,还有那条虎鞭,是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原载《辽河》2021年第2期)
东坡与司马
“乌台诗案”尘埃落定,苏东坡终于回到了久别的京城。
第一个宴请他的人,是司马光。那时候,司马光已经取代王安石,做了宰相。
“子瞻,你这几年受苦了。”司马光说,脸上充满对他的同情。
“没什么,没什么!”东坡笑一笑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我不去黄州,怎会有《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呢!”
“也是。”司马光说,“你还年轻,受点磨难不是坏事儿。”
“你还年轻”,这四个字让东坡心里一颤。他抬眼看看对面将近比他大20岁的司马光,看看他那张因夜以继日编纂《资治通鉴》而变得沟壑纵横的脸,不由一阵心疼。
“子瞻啊,”司马光好像还不习惯叫他的“东坡”雅号,这个和他父辈一样年纪的人,无论对他的父亲,还是对他和弟弟苏辙,都有一种心灵相通的亲切感。在这京城之中,有两个人他最为敬重,一个是在科举考试中发现了他和弟弟的欧阳修,另一个就是眼前的司马光。司马光其实对他更为重要,因为在更为高等的“制科”考试中,作为主考官的他,再次把他们兄弟二人直接推向皇帝身边。
“是这样,”司马光说,“你现在这个正四品的起居舍人职位对你来说,还是太不相配了,我准备马上拟奏,建议你为中书舍人,随后还要你做翰林学士知制诰……”
“恩公,这……也未免太快了吧。”东坡的一颗心突突突地跳起来。
“一点不快。”司马光说,“你知道这是谁的意思吗?”
“谁,难道是高太后?”
“非也,这是先帝神宗皇帝的意思。高太后说,神宗皇帝简直太喜欢你了。每当拿起筷子吃饭时,他都要问:苏轼又有新诗出来没有?”
“啊,是先帝呀!”东坡不由得热泪盈眶了。
“当然,我这样不遗余力推荐你,也有我的目的。”司马光目光炯炯看着苏东坡。
东坡不由满饮一杯酒说:“恩公,你有用得着苏轼的地方,只管开口便是。”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司马光接着便开始滔滔不绝,纵论天下。
东坡很快就听懂了,司马光是要全盘否定王安石,他要把王安石做过的一切,一点不留,统统纠正过来。他希望自己能够公开站出来,大力支持他。
东坡心中,立刻压上了一块千斤巨石。这倒不是因为他刚刚见过王安石,与他吟诵唱和,相知恨晚,而是从事实出发,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也不是毫无可取之处。人生经验告诉他,对任何事情,彻底肯定或者否定都是不对的。
“恩公,”东坡耐心地听他说完,开始小心翼翼地说,“我想先问您一句题外话,您与王老相公,真的就那么势如冰火,不共戴天吗?”
“嗯?”司马光愣了一下,他以探询的眼光看着苏东坡,等待他的下文。
“依我看,你们这两位老相国,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忧国忧民之士,都有经天纬地之才,只是你们的治国理念有所不同罢了。”
司马光的脸色骤然阴暗下来,对此东坡已经察觉,但是他感觉自己的舌头有点不受自己支配:“我说话您老千万不要生气——我觉得介甫变法,出发点还是好的,当然有的必须纠正,比如‘青苗法’;但是我觉得有的还可以保留,比如‘免疫法’……”
忽听砰的一声响亮,东坡被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糟了!只见对面的司马光,此时早已满脸涨红,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颤抖着一只手指着他,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
“恩公,您怎么了?你不要生气嘛!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还不行吗!”东坡有点慌乱地起身,过去要扶司马光,却被他一下子推开了。
“苏轼!”司马光终于说出话来,“你……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如此器重于你,你却把我和那祸国殃民的老匹夫相提并论!他是个什么东西,连你的父亲都说他是‘囚首丧面’,专门写《辨奸论》骂他。可是你……竟然在这里替他说好话,还要我保留他的害人之法,你……真是气煞我也!”
东坡没有想到司马光的反应会如此强烈,他知道自己又惹祸了。唉,你怎么就管不住你自己的嘴呢!他真想打自己的嘴巴一下。
“恩公,我只是提个建议而已,并没有别的意思。您老兼听则明嘛!”
“你不要说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能不能公开彻底地站在我这一边,和我一起把那老匹夫的余毒肃清。能的话,我不计较你刚才说了什么。如果不能,那么你就必须承担后果,为那老匹夫付出代价!”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清楚了。东坡心里,犹如翻江倒海。在一瞬间,他很想为了自己的个人前途,向对方服个软,道个歉,但是他的嘴巴依然不肯听他指挥,他说出来的话竟然是:“恩公啊,您老为何这般逼我,我不过是说了句公平话而已呀!”
只见司马光的脸由红变紫,眼睛里已经喷出火来。他猛地一下掀翻了桌子,大声吼道:“苏轼啊苏轼,可惜我对你的一片苦心呀!什么都不用再说了,你……走吧!”
这时东坡的火气也上来了,他站起身,给司马光鞠了一躬,径直就朝门外走去。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向性格温和的司马光,那个充满智慧、小时候就知道砸缸救人的司马光,性格竟会如此偏执,如此听不得不同声音。算了,你爱咋地就咋地吧!
东坡想着,大步流星走出了司马府。他转过身来再看,突然发现这座来时还感觉无比亲切的宅邸,现在却变得那么陌生,那么冷冰冰。他知道自己以后不会再到这里来了,他和司马光的师生情、忘年交,到此就戛然而止了。
“司马牛,司马牛!”东坡不由得大喊起来,惊得门楼上的燕子纷纷腾空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