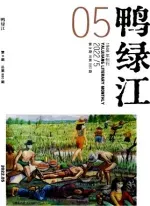代表
程多宝
1
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三十多前的那个初秋,天气是一副想找人“嗨皮”的嘴脸,我却碰到了一件烦心事。这事,其实说不上烦,就是有点绕,一绕就是好多年,如今想起,心里还有些酸溜溜的。
那年,我好不容易考上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一家乡镇民政所的干事。我们那个乡镇,地处素有“将军县”之誉的江西兴国县,我上班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民政所所长免不了一番语重心长,那意思是说,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会后,所长估计我一时半会儿还没有理解到他的用心良苦,特地留下了我。虽说我是个大学毕业生,考上这个岗位看似光鲜,其实我自己心知肚明,多少也带有毕业分配的那种性质,但毕竟——我对兴国县情哪有多少了解?那时候还是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一时还没有什么“上网”一说,如果哪个冒出来“上网”这么一句,江西老表们肯定以为是下河捕鱼之类。好多乡镇级别的单位,办公时用的多是油印机。配发的386 电脑还是新鲜货,敲起键盘来咚咚地响,仿佛身旁站着老头老太太戳着拐杖。再加上民政系统的事情特多,打交道的要么老弱病残,要么功勋卓著,方方面面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好在我热情高涨,若是工作累了,哼唱几首武打片插曲放松放松。那个年月,《少林寺》《霍元甲》热浪刚走,金庸古龙梁羽生如日中天,我对自己的歌喉很是嘚瑟,居然收获粉丝N 位。久而久之,我在那个乡镇居然小有气候,以至于后来的乡镇联欢晚会,只要我放开歌喉,难免嘚瑟得有点儿飘。甚至我还没有想到,有些在县城上班的姑娘,都想着法子绕着弯设法打听我。
那年秋天,即将隆重召开党的十三大,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参会的党代表要从基层的党组织开始选举,名单再一级级地往上呈报。那些红色的选票海一般浩瀚,每一朵浪花都是那么神圣与光荣,组织填报与统计工作哪一项都容不得丝毫差错,所以我一大早就猫进了办公室,即使腰酸背疼也浑然不觉;实在不行,我就一边敲着电脑一边哼着小曲解乏。直到那台386 电脑的键盘极不耐烦,我才停了下来,准备歇上一会儿,嘴里的小曲还是没有停摆。
尽管我起了身,好像那种键盘的敲击声还在。这就怪了,我一个侧脸,键盘无动于衷,这是哪里闹出的响声?茫然四顾才发现,敲拐杖的声音是从门口那里过来的。于是,我一回头,真的看到了一根竹制的拐杖,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渐行渐近,皱纹一层层推开波浪似的脸庞,泛着浅浅的笑意。
哦,是领救济的,还是……我想起来,问了一句,“老人家,您是党员吗?”
对面的那个人摇了摇头。
“是想打听选举党代表的事?”
她先是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头,停了一会儿,又坚定地点了点头。
好在选举党代表这项工作是一级一级向上呈报的。在我们乡镇这个口子上当选的党代表,哪能都去北京人民大会堂?这可是有比例限制的,他们有的是去省市开会,更多的只是去县里开会。这事也不需要保密,反正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着,让老人家看看那些当选人的照片也没啥关系。直到安顿老人坐下,我才知道,老人想看到的那个人,比她自己岁数还要大。
“那——不得快八十岁了?我们乡镇符合选取条件的党代表真的没有这个年龄段的。”我安慰了一句,正想找个理由打发呢,不想老人自报家门,说自己姓胡,“小同志,你就叫我胡老太,好不好?就当……你是我的大孙子,行不行?”
我后来才知道,胡老太这么多年没有结婚,但凡见到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年轻后生,心里忍不住母性泛滥,话一出口,就想喊人家一声大孙子,或是大孙女。
我喊了她一声奶奶,说是手上有工作,您老人家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改天到了星期天,我在办公室等您,问清楚到底您想找的那个人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胡老太脸上的皱纹一时抻平了不少,身子与那根拐杖快要走出门口的时候,不想却慢慢地转了身子,“大孙子,我这次来只是顺嘴一问,那个人的音信,怕是没个指望。还有,我想与你比一下,行不行?”
“比什么?胡奶奶,我与您都不认识啊,我俩之间有什么好比的?”
“比唱歌。听人家说,你的歌唱得好。可我觉得,你比不过我这个老婆子。”胡老太有了些羞涩,“要不,今天我俩就比一段。这么些年,我还真的没有找到对手,山上的树木还有竹林,天上的云朵与飞鸟,它们听过我的歌,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
“你敢不敢?”这次,胡老太来了劲,走过来的几步,似乎手里的拐杖成了累赘。
2
怎么可能?我一个年轻大学生,再怎么说,与您这个岁数的一位老太太比赛唱歌,赢了还是输了,传出去让人怎么说呢?这时,我听她说起了一些家长里短。原来,这位胡老太多年独居,既不识字,也没有地方戏班子开唱的底子……这样,我更不忍心与她较真。
就在我愣神的时候,胡太太开启了歌唱模式。还别说,虽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可是那个嗓子真有些天籁之音的模样: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
夜打灯笼访贫农。
……
如此一来,眼前的这位胡老太真的不同凡响,让人刮目相看。
难怪我们所长说,咱们这儿可是“将军县”,别看那些个七老八十的农村老头老太太,他们要是拐杖地下一戳天上一捅,没准儿就是上下两个大窟窿。
一番打听,听到她所在的村干部们介绍,我这个年轻后生不得不对老人家肃然起敬。原来,她是胡家冲的一位幺姑,往年这个季节,天凉了,还没到秋收的时候,农活儿有了些清闲,她每年都要出山,到乡镇走上几趟,据说最远的到过县城,有一次差点去了省会南昌。说来说去,还是那件事,就是想着让我们各级民政组织出面,帮她寻夫啥的。“男看鼻子女看嘴,一生富贵少是非。你没见过他,我不怪。他那个人,长得真的好看,看了一眼就忘不了。他那么能干,打起仗来不怕死,又有文化,还命大福大。说不定,刚解放那会儿,他就成了党代表啦。就是现在,他要是还在世上,我74,他76,说不定他真的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好几次的代表大会,他也有资格参加呀……”
这时,我好歹听出来一个大概:1931年秋,这位胡老太,不过十七八岁的花季的一位村姑,与一位叫小马的红军战士,就在她现在所在的那个胡家冲订了婚;只是后来,这位未婚夫不辞而别,倒是这些年时常托梦回乡。每个梦境里,少不了两人都在对唱,而且小马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改口,还喊她“小燕子”……
这都多少年了?56 年了啊,我的胡奶奶。
我还知道的是,我前面几任同事,好几个让胡老太折腾烦了,但凡看到胡老太上门,多是点头客气一下,借口手里有急事要办,瞅空闪人。也难怪,谁要是让胡老太缠上了,哪个又能帮她解开心结呢?
倒也理解,20 世纪30 年代的兴国县交通闭塞,既没信件,更没电话,何况老人家说的,还是“苏区”那个年代的事。
3
久而久之,胡老太寻夫,依旧无望。
其实,我也听说了,包括我们所长在内,那些年,我和同事们还真把这个事当作一项工作任务,查资料走访啥的,青灯黄卷N 遍,硬是把全县烈士家属走访了一遭。
结果不出所料,对于胡老太来说,只能是一次次叹息,之后还是一副痴心不改的劲头。
这以后,每到这个季节,胡老太仍旧出山,找上门来的次数一年比一年来得稀,拐杖一声声地比以往敲得还要重。每次接待老人家的时候,她总是忘不了主动教我唱歌,几乎成了“保留节目”。她会唱的,只能是一些与“苏区”有关的歌。那些歌子挺筋道的,让人热血沸腾一往无前,可毕竟不是时下流行风,也不是小青年的“时髦菜”。
我只有苦心相劝:“苏区”为了中国革命,牺牲太惨重了,失踪、失散得太多;你一口咬定那个小马没有死,说不定京城当了大官,会不会隐姓埋名啥的当了负心汉,我们真的也不好帮你推测。胡奶奶,说话要有证据,你手头——有什么线索吗?
“当然有了!当年,他给过我定情信物。这都多少年了,哪个晚上,不在我的床头?这些年,我夜夜枕着,睡觉前,摸一遍,喊一声他的名字,心里那个恨啊,非要把他的魂魄喊散了。”那应该是记忆里的最后一次,胡老太上门找到了我,“大孙子,你帮我想想,都是黄土埋到脖颈的人了,我不想带进棺材。没想到当年他这么一走,真狠心,我能不恨他吗……”
直到有天,胡家冲通上了电话,我第一个电话打过去询问的时候,听到村支书汇报说,胡老太身子骨脆了,一直卧在家里,几乎出不了远门;好在给她老人家落实了“五保户”待遇,吃穿有了保障,只是有些遗憾,老人心里牵挂的“烈属”待遇,申报材料一直弄不齐全,没多少说服力,村里一时犹豫着不好决定,也没有往乡镇上报。
于是,我只身下乡前往。在那间又黑又矮的屋子里,看到了那只枕头里包裹的信物。
一张快要磨破的油纸布,包裹得严严实实。一层层解开,再慢慢地摊开:一本《共产党宣言》,内夹一张照片:一位手捧马克思银像的青年人,穿着红军军装,戴着八角帽,身材笔挺,长相蛮酷,像是当时某部战争影片的男一号。
“帅哥啊!看看您的小马哥,那个鼻梁,多挺啊。”我这么一说,胡老太一惊,让我小声,别让屋外的一个什么人听见。
其实,哪有呢?只是门前的一阵过堂风,还有的是山林与竹海探出了头,竖着耳朵想听点什么动静,又好像是为她鸣上几声什么不平似的。
停了会儿,我看她用手拢了拢垂曳的几绺银发,往门外望了一眼:我当年,长相哪里输他?大孙子,你不晓得,胡家冲这一带,方圆多少里,哪个不晓得我,人称“小燕子”呢?
见我把这些信物轻手轻脚地一一塞进公文包,又给她打了张盖了公章的收条,胡老太抹了抹眼角,可能想着还要唱上一曲,算是感谢或是拜托的意思。我看出来了,胡老太的感激方式只剩下歌唱,别的她也没有,就像是当年的苏区老百姓送别亲人红军长征之际,排着队临江而歌,高唱“十送红军”的那种神情。只可惜,老人家像是浑身漏了气似的,实在没什么气力,哼出的歌子断断续续,有好几处还唱错了歌词,像是拉风箱似的。好在不一会儿,胡老太硬是凭着记忆,中途又给找了回来。
我说:“胡奶奶,咱以后再唱,今天咱先省点力气。您敞开讲,我认真听。哪怕……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也信您。”
“真的,你信?本来,我就是他的‘小燕子’嘛。”断断续续地,我总算听清楚了,两人间的白云苍狗,尘封几十年之后,仍然让我这个晚辈潸然泪下。
4
最初的小马,是被她的山歌吸引过来的。那天,两个人只是一个对眼,她就在心底烙下了人家那张脸。原来,小马也有一副好嗓子,看他一身军装的精气神,听他歌声里的那种豪迈劲,即使雾褥云被绳床瓦灶,似乎这世上就不存在“苦累”二字。一开始,他们只是喊着小名,或者就是乳名。她,没有名字,在他的嘴里,只是一声声小燕子;他,当然有了大名,只不过她只知道姓马,一口口的都是小马哥,往心里喊的那种亲切,像是被天上的闪电一句句地电上了似的,让她的心直到现在还微微战栗不已。
其实,哪怕岁月真的熬成了她手里的一把梳子,几十年下来,一天天就这么梳过来梳过去:这么多年的回忆,也只是见过三次面。
那个小马比她大两岁,读过私塾,喜欢看书。小马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在她的眼里就是大道理,听起来心里热乎得不行,一会儿随他漂洋过海,一会儿随他九天揽月。是啊,小马哥才是我们老百姓心里的大代表,他代表着我,也代表着他自己,更代表着千千万万天下的受苦受难的人。小马告诉她:“我们抛头颅洒热血要捍卫的中央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初次尝试……”
“你说的,我都懂。以前不懂,现在真的懂了。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是你,是我,是我们所有的穷人苦人难人可怜人,对不对?”当年的她,那个小燕子一点就透,多聪明啊,多善解人意啊。可是,到了后来,她担心极了,又哭又求的,可是小马摇了摇头。她懂了,这是一匹千里马,心里的疆场只能是山河、家国与天下。
“就不能,不走吗?要么,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你要解放天下穷人,你的小燕子,也是穷人啊。”那一次,胡老太说,她哭得伤心极了,简直是不想活的那种。
家里人不放心了。长辈们说小马舍得下性命,真的是一条汉子,他代表的就是我们,我们这个家族不能忘了人家小马。只是,小马可以闯天下,但是先得订一门亲;这么帅的男人,又有一肚子学问,将来打下了天下,得有多少女子追随?说不定啊。凡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管怎么说,咱先说好,得让我们胡家有个念想,先订一纸婚约,千里马跑得再远,咱胡家人手里得有根缰绳,好歹也能拴住人家的马腿。
得知小马出山闯天下,她悄悄地跟了一截子路,话没多说,只是塞给了一卷私房钱。那是她的一双手换来的,砍柴、采药、织布……即使再辛苦,心里有了盼头,那也不会再苦,嘴里的曲儿如一只只欢快的小鸟,满山满坡地飘,风儿与白云也绊不住。也不知等了多久的一天,她等来了小马从似乎遥远的天边寄来的一封信。信上的意思是:实在是对不住啊,他认定了这条道,绝不回头,身子骨难免朝不保夕。毕竟,他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他们两个人……
胡家的人,哪个猜不出来?小马要成气候了,分明是想退婚嘛。她怎会同意?还有的,她怎么不知道:苏区“扩红”的势头,烈火干柴旺着呢,满眼的星星之火,直往天上喷的那种气势。十个大男人,九个想当兵。直到解放后的一天,她收听村上的广播喇叭时,这才提心吊胆:那年月,兴国县总人口23.18 万,有5.5 万人参加红军,牺牲烈士达2.32 万人,全县每4人中有1 人参加红军,每10 人中有1 人为革命牺牲。红军长征之后,他们县连同周围一带遭到敌人疯狂报复,很多地方成了“无人村”,国民党当局对外称为:“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
只是,她当时不便外出寻夫,就是哭着闹着跟上队伍也走不远啊。小时候,她裹过脚,就算是小马哥拽上了自己,当上红军游击队啥的,一旦行军,还不成了累赘?
于是,她铁了心,决心要把那间小屋守成暖暖的窝啊,筑成美美的巢啊,死心塌地等着飘落在外的小马,说不定哪天醒来,眼前站立的这个大活人真的天外飞仙;海水枯了石头烂了绝不悔改,即使族人盈门陆续逼婚——好几次,她急了,没办法了,也没理由了,实在是没招了。哭泣的声音,一阵阵地和着山风呜咽,最后还是摸了摸心窝窝,那个小马依然还在,热乎着呢。……终于,解放那年,村口过大兵,好大岁数的一个女人了,她的心儿怦怦跳,直想往外蹦。那天,她铁了心,没命地往队伍丛林里钻,又一次次被那些与小马哥头顶上戴着一样五角星的解放军战士们或推或送,一开始有的是笑,到后来好多当兵的真的哭了。她急了,她能不急嘛,这是把多少年的煎熬,当成这么一次机会赌上一把啊。年轻的胡老太,就是小马哥嘴里的那只小燕子,她把小马哥的那张照片别在头巾上,见到队伍里那些岁数大的当兵的,就没命地哭喊:“马儿啊,你慢些走!你这么狠心啊,你死到哪里去了。你一个大男人,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我不管你是谁的代表,我是你的小燕子,我不会飞走,我在等你啊,你听到了吗?我的马儿……”
5
一回回梦境出现的场景,经过我好多次试探性的启发,胡老太这才一口咬定:对,就是延安,有宝塔的那个山头。没错,那个地方,电影上我看到过的。大孙子,奶奶谢谢你,还有你带的那些报纸。
以前的好多次送别,我给过她一些报纸。我知道,胡老太不识字,好在报纸上有图片,看到穿着军装的那些人,她就感觉亲切,一次次地把他们贴在墙上,端着一盏煤油灯,一次次地照着,想在一张张的字里行间找寻那个让自己魂牵梦绕的马儿。
我知道了,胡老太认定的地方,就是我说的那个“抗大”。
幸好,第二年,我们乡镇五谷丰登,再加上民政工作得了好几块牌匾,上面终于拨了笔款子,促成了我的延安之行。直到查遍了“抗大”资料,疑似胡老太述说的那几届学员花名册,别说马儿,牛儿也没影呢。
“会不会改了名?”我只能这样安慰。诚然,在“将军县”这一带,当年为革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牺牲得多了海了,但的确有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革命需要隐姓埋名;还有的,建国之初,那些从革命老区推着小车一路寻夫的女人,也有一些在城市居住下来……
好在,没隔多久,延安那家博物馆寄来一封挂号信,里面塞了几张照片,一看,就是新近翻印加洗的。
“就是这匹马,看你——往哪里跑!一二三四五六,第六排,最后一排,站在边角的这个……”胡老太只是扫了一眼,右手食指没有拐弯,直接摁住了其中一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像是一时间拴住了那条奔腾万里的马腿肚子,眼神突地一下,好似接通了电。
那天的她,特地拐进了里屋,等到再一出来,当着我的面,焕然一新呢。胡老太的小脚舞动着,立马有了一阵风,还特意换了件新衣:粗布浅灰色大衣襟褂子,是当年定亲时小马的“彩礼”,与小马军装的颜色一个样;还换了一双新新的千层底布鞋,一左一右的两只鞋帮上,彩线绣出“马踏飞燕”的造型……
让我不解的是,胡老太像是要举行什么仪式似的,她特意梳了头,还用梳子蘸了水,一遍,又是一遍。
“老天有眼,快六十年啦。乖乖儿,你这个天杀的,看你往哪里跑?一个甲子,没了。”那一刻的胡老太,仿佛一株干蔫了的花儿,沐浴了一番阳光雨露之后突然枯木逢春,嗓子脆生生的,似乎还想唱一出似的。
只是,胡奶奶,您要打听的那个人,已经改了名。作为一名乡镇民政所的办事人员,我必须要提醒这么一句。
“改啥名,都是我的马儿。我是他的小燕子,就是哪一天,飞不动了,入了土,成了一把灰,照样也是他的人……”我不知道,那天的我,是如何告别胡老太的。
6
好些个日子,尽管我心里念着胡老太,可就是不敢再去那间屋子。有好多次,县里的民政局局长也急,电话里几次催促我,最好尽快给老人家一个答复。
是啊,局长怎能不急呢?当年,局长就是那个对我语重心长的乡镇民政所所长,如果刨根问底,局长要是知道了胡老太的那种无望的痛,肯定比我要伤心多了。
好在接下来,延安方面又追过来一封信:胡老太的“马儿”,连同他所带的一个排,在太行七分区的一次 “反扫荡”突围战中,无一幸存……
想了想,征得局长的同意,我又一次上了门,哭着告诉了胡老太。我原以为,老人风烛残年了,会撑不住。没承想,那天的胡老太,脸上没有让我看出来一丝痛苦,甚至我告别下山的路上,还听到了她一路送行时为我唱的歌谣。
这封延安来信不久,不到一个月的一天,村里电话过来了:年近八旬的胡老太悄然辞世,村里一时没人发现。
我不知道,那个孤寂的夜晚,她的梦境里有没有马蹄声碎?有没有燕去燕回?有没有情歌回荡?
或许有吧?因为山风,这些年一直告诉了我……我还了解到的是,胡老太曾有过遗愿,她拒绝死后立即下葬,她要停棺山林松涛之间,直到组织上找到“马儿”,两人相守,在这间小屋的后面同穴合葬。
我的报告递上之后,局长打了几通电话,最后的回复十分简洁:胡氏就此安葬,遗物上交省民政厅,存档烈士博物馆。2022 年秋,我到龄退休。
7
干了半辈子的民政工作,虽说我后来工作调动离开了兴国县,可冥冥之中还是忘不了胡老太。
适逢举国上下喜迎党的二十大召开,闻说有个专为校外辅导员举办的“红色之源”旅行团,行程里有江西兴国县这一站,我立即报了名。在一家新建的烈士纪念馆内,解说员刚一开始讲解,恍惚间胡老太仿佛就在眼前,一声声唱着歌儿。这时,我知道的是:胡氏辞世之后,老屋因为年久失修,村委会拆除房屋时,在土墙的一个夹层缝隙里发现了这样一封信。信是油布纸包着的,虽然年头久了,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
透过橱柜玻璃,我看到开头的那行字,墨迹娟秀如初:
我的小燕子:
……
如果你再也等不到我,那么这首歌,就是我梦里吟唱的恋歌……
忽然想起来了,当年的胡老太,曾经一句句地教会了我唱这首歌;还有呢,好几次我下山的时候,背后飘过来的不正是她唱出的这支曲调,尽管音量渐渐地减弱:
最后一碗米,
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
送去做军装,
最后老棉袄,
盖在担架上,
最后亲骨肉,
送他上战场。
……
可是,我一时有些迷茫:按理说,小燕子本人,一生中并没有见到这封信。那么,她怎么知道,这首塞进土墙壁里的歌儿,是小马儿离别之时,千万次梦境里,留给她下半辈子的一曲恋歌?
还有啊,这以后,前往这家烈士陵园的那些后来者,比如说我的学生们孩子们,如果我这个校外辅导员在你们面前教唱这首歌时,说不定会唱出一脸的泪水,你们……能不能听进自己的心灵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