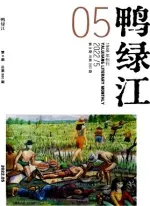纸笔何安
高 方
某一日午夜梦回,再难入睡。辗转反侧之际忽然想起这些年与纸笔为伴的日子,想起我在书房、在教室、在食堂,在许许多多地方写下的那些文字。
前电脑和智能手机时代,我的文字都是写在纸上的,稿纸、大方格、大笔记、大白纸,还有随手扯下的教案、便笺、台历页以及应急时摸到的毫不规则的碎纸片。从小到大,我从没有过买不起本子的日子,但很多时候我更喜欢纸张粗糙的背面,喜欢笔尖触及时比正面更为滞涩的手感,以及无须侧耳就能听到的沙沙声响。
也许是因为很容易受到外物的触发,不时就会心有所动,我养成了随身携带纸笔的习惯。更多以电脑为笔的今天,我也没有真正疏离真实的笔墨,就算有时忘了带纸,笔也是一直在的,有时应急,还能分给别人一两支。我常和人开玩笑说:“知识分子,身上哪能没有笔呢?”
笔,我通常是带两支,一支黑的,一支红的,有时也会多些,放在一个挺括有型的牛皮笔袋里。这个笔袋是十几年前在一家手工皮具店买的,一起买的零钱包早就废弃不用了,它却一直陪着我,去了很多城市,常常是除了放笔也放U 盘和一支无色的唇膏。这个笔袋从买了就几乎天天扔在包里,用到今天几无破损,它用实力向我证明了皮革的韧性。大约也是因为它,最近这十几年的印象里,除了专门赴宴会换个小些的手袋,其余时间我总是背着大包,去上班或是去其他地方。
包里的纸,有时是一个极薄的软皮本,有时干脆简易到三两页横折又竖折到巴掌大小的A4 纸。本子还好,有软皮护着,纸就不行了,用的时候经常已经有了黑色的折痕和其他污渍。好在我不介意,它在我眼里就是白的,仍旧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这样随意的纸张时常能够派上用场,有时却也让人出糗。
读硕士的时候去找导师请教毕业论文的写作。大夏天的,要坐两个半小时的火车,嫌热,不想背大包,就习惯性地折了几张白纸塞进我小小的的帆布月牙包。我清楚地知道,老师讲的要点和精髓是一定要记下来的。
隔着宽大的办公桌,老师坐在主位,我坐在客位,手边是一杯老师亲自给我泡的茶。老师开始讲,我掏出“认真”准备的纸张开始虔诚地记录,却发现他突然停住了话头。老师侧过身,在他左手边的书本堆中努力翻找了一阵,然后抽出一个本子说:“这个给你吧!”那是一个厚度超过1 厘米,开本大约略小于B5 纸的皮面记事本。我诚惶诚恐地双手接过,向老师道谢。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谢意是真的,不情愿也是真的——我不缺本子,我只是不想在这种天儿里背着个大厚本儿在两个城市之间来去。
那个本子我差不多算是捧回去的,因为我小小的月牙包根本无法安放它的庞大。好在回去的火车上我偶有所得,写了篇我和学生之间的小故事。要是手边没有这个本子,我还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再后来,我又拿它记了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日记。
我没有在交通工具上写字的爱好,但有时有了感觉就会写一点、记一点。在从湛江徐闻去海口的船上,注目碧蓝的波浪,我心中默念着苏轼的名字,写下了《蹈海行》的第一句话:“凌波蹈海,我只为一人而来。”平素的公交车上适合看风景,看不到风景的地铁就比较适合记下零碎的感受,当然前提是要有座位。有座位真的很重要。还是读硕士的时候,家和学校之间的旅程要一次次地经过呼兰河,会看见四季的景色,也会不时想起萧红,于是《车过呼兰河》就诞生于某一次旅途。笔在手中,纸在膝上。
送女儿上大学,去时三个人,回来只有我一个。安顿好女儿,留下先生再陪她一晚,我要赶回去上第二天的课。返程的高铁要走六个半小时,一个人坐在列车上,想想十八年来一个小娃娃和我自己的成长,不免心绪起伏意有所动。那一次身边没有纸和笔,我就断断续续在手机上写下了近两千字的《从此,空巢》。也许因为情真意切,许多读者说写得好。《从此,空巢》是我唯一一篇在手机上定稿的作品,断断续续是因为有时思绪飘得太远要及时拉回来,有时还要取出纸巾拭干涌出的泪水。
有一年从苏州离开,飞机升上云海,我的心思却还停留在地面。习惯性地摸出笔,却发现纸在行李袋里,而行李袋在行李舱里。我抽出机组为乘客准备的清洁袋,写了正面,又写反面,一个袋子用完,又去后舱的架子上“自助”了几个。也许是因为在飞机上,想法飞得太快,写的时候就用了很多草字和省笔,结果等我到家整理的时候,麻烦来了,有些字句我已经不认得了。
我开始慢慢“破译”自己亲手写下的每一个字,大体还算顺畅,但是有一句七个字怎么也认不全。后来还是女儿反复看,然后试探着问我:“你写的是不是‘珍珠成土石犹在’?”是的,我说的是一千多年前太湖里的珍珠和太湖石。我一边疯狂点头说“嗯嗯嗯”,一边张开双臂想抱她,她小鹿一样躲闪着跳到一边说:“你高兴大劲儿了,可别把我的腰搂折了!”这篇文章就是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细雨沧浪亭》,原稿有四千多字,发表的时候生生忍痛截到了报纸要求的三千字。
我曾教过十几年的写作课,学生们做课堂训练时我也和他们一起写。在或大或小的教室里,我们或是一起做同题分享,或是我出题他们写、他们出题我来写,反正还算年轻的女老师很“心机”地赢得了许多由衷的钦佩,也带动了很多人。那之后许多年,还有学生在给我的信里说,总会时时记起我带他们在大操场的草坪上写作课和现场训练的情形。我回信说,现在不敢了,人不在教室是要被算作教学事故的。我忘了问,那些沾惹了芳草气息的文字,他们是否还留着,我也不记得我自己当时写了什么。
大约二十年前,有一次考英语四级,我监考,早早到考场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只等着到点开门,学生入场。考场在一楼,开着窗,我站在讲台上傻傻地看向窗外,看到那些从春到夏次第开放、次第凋零的花树。我取出纸笔,伏在讲桌上,写下了一篇只有六百字的短文《看花的感悟》。我至今还记得文章的结尾:“其实我们谁不知道呢,花儿的心里只有蜜,露珠更不是花儿的眼泪。”那时电子邮件还是新生事物,办公电脑和家用电脑都还没有普及,编发此文的编辑后来专门写纸质的书信给我,问还有没有类似的“又短又美又隽永”的文章给她。很遗憾我没有,也很遗憾后来跟她断了联系。
前些天去教务处参加一个实验室项目的答辩,我没背包,只掐着几页纸和一支笔,在会场外面等待依次进入。等的时间有点长,教务处的五间办公室我串了三间,问完了想问的问题实在没事干,就坐在茶几前面开始写字。屋子里的小姐姐看到了,起身,费劲地把一张桌子正中的两大摞材料抱走,说:“高老师,你到这儿来写吧!”我在人家办公室完成的就是《四月春花开》,感慨一下我们大东北四月里并行的雨雪和鲜花,以及由岁岁荣枯而生发的一点点感喟。这篇文章写在教务处的办公桌上,也写在会序单和我汇报材料的背面与正面空白处。
我特别感激自己与纸笔相伴的积习,因为有了它,坐在街边就写了《坐在街边》,坐在楼梯间就写了《坐在楼梯间》,我还在煦暖的日子坐在大明湖畔的柳色里、西子湖畔的荷香里涂抹过文字。那些极不情愿参加的没营养的会,也让我在会议记录本上记了些与会议无关的内容。读硕士、博士的时候,等餐的间隙我还在食堂的饭桌上写过一些文字,在人间烟火气最足的地方写最没有烟火气的故事,那些男子都是眉目清雅疏朗俊逸,那些女子都是白衣胜雪飘飘欲仙。只是现实中,我那件灰色羽绒服的袖口早就被蹭得和那些饭桌一样油汪汪地闪着亮光。
我最多的文字当然还是写在我的家里,在书房,在阳光晃眼或是阴雨绵绵、大雪纷飞的日子,在架上书香和案头花香的陶染中。当女儿寒暑假回家偶然兴起侵占我的书桌时,我就只好移师到她的房间,一边假装耐心地询问这个可不可以动、那个要放到哪里,一边把她桌上的东西收好,给我自己腾出一块放纸笔或是放电脑的地方。有时我嫌麻烦,干脆坐到餐桌前,开始或继续我未曾完成的文稿。
我笃信文字的神性与圣洁,所以我和我的纸笔都可以毫不挑剔地随“遇”而“安”,而且一定会继续“遇”,继续“安”。心有所归,笔有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