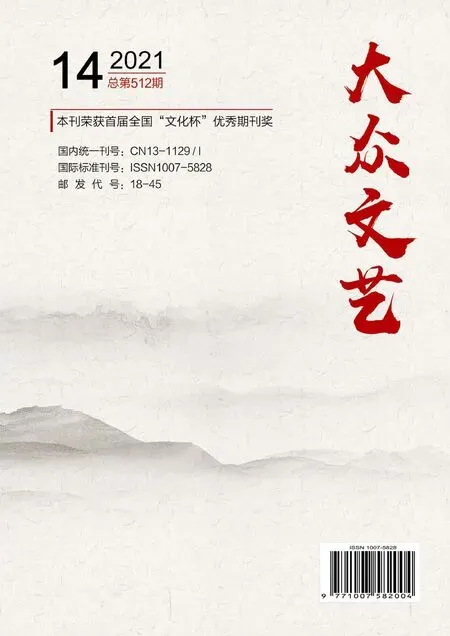浅析《孔雀》的人物形象及文化意义
——以弟弟高卫强为例
谢伊琳
(深圳大学,广东深圳 518000)
由顾长卫执导的电影《孔雀》讲述了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南古城安阳一个五口之家的故事。影片用分段叙述的拍摄方式,展示了故事三位主人公(哥哥、姐姐和弟弟)不同的成长隐痛,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其中作为叙述者和亲历者的弟弟高卫强,在影片中的叙述篇幅最短,如他所言“沉默得像个影子”。毋庸置疑,影片中对姐姐浓墨重彩、肆意飞扬的刻画,吸引了众多观影者的注意力,对影片的探讨,多停留在以姐姐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视角及哥哥作为特殊残障人士的生存处境上,更凸显了弟弟在影片内外的沉寂。这固然与影片送审时弟弟故事内容的删减不无关系,也侧面说明了平庸而弱势的群体游离于关注之外的社会现实。
《孔雀》中的姐姐是一个清醒的追梦者,她的自由意志,对理想的追逐和现实的反抗赋予角色极高的艺术价值。相比之下,柔弱寡言的弟弟显得黯淡。但笔者以为,这绝不意味弟弟这一人物形象的失败与无用,反之,对高卫强的形象塑造,更加贴合现实生活中的普罗大众。我们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和弟弟一样普通,于观众而言,弟弟因真实而更加复杂。因此,对弟弟的解构不能仅停留在其单薄短小的影片叙述篇幅中,而是应该把他放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多方场域进行剖析。本文将结合威尔海姆·赖希的精神分析学理论,通过分析弟弟在成长历程中受到的压抑,联系身处的社会、学校和家庭环境,还原其真实的成长隐痛,以获得对特定时代下人性弱点与个体幻灭的集体反思。
一、家庭的弱者
“权威”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这是由于物质生存资料的有限离不开人为的组织形式。发展心理学认为,个人权威主义人格的形成,与其早期的家庭结构、教育密不可分。在权威主义家庭中,父母对孩子施予严厉的管教行为。只有孩子的表现被父母们认可时,才会得到关注、爱护乃至酬赏;父母们强调顺从的重要性,并严厉地制止孩子的敌意表现,这构成了权威主义家庭的雏形。赖希认为,尽管父母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干什么,实际上却执行了权威主义社会的意图。
(一)经济权的缺失
《孔雀》讲述的五口之家,成员间有着俨然的等级秩序。父亲和母亲掌握经济权和话语权,患有脑疾的哥哥是全家关注的重心,叛逆的姐姐紧随其后,而最懦弱寡言的弟弟处于全家的底层,像一面无言的镜子折射出家庭其他成员的生存状况。
少有人注意到弟弟在家庭中的身份定位——在校学生,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王沪宁在《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一书提道:“在阶级社会里,经济权力就是阶级权力,就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在经济领域中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在影片中,哪怕是患有脑疾的哥哥也换了几份工作,有着不算稳定的工资,毋论其他家庭成员。而弟弟自始至终都只是家庭里一个小心翼翼地“依附者”,他的吃穿住行强烈仰仗着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经济权力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弟弟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权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家庭,经济发展远没有达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地步,尽管一家五口吃穿不愁,但影片对高氏父母的镜头刻画,大多停留在他们生存资料的挣取上,如造煤、腌制食材等。处于青春期的弟弟,按常理,本应获得家人特别的爱与关注,却被精神匮乏的家庭环境所牢牢压制。作为缺乏收入来源的学生,他成了家中的“被奴役者”,以获取某种平衡。在影片的前半场里,他帮姐姐跑腿、买书,照顾哥哥洗澡;影片的后半场他则放弃了劳动权,企图通过满足妻子张丽娜的性欲,来换取自己的生存资源。
弟弟并非没有抗争过。他的第一次离家出走(养老院工作)和第二次离乡出走(扒火车逃离小城),都是为了脱离这种依附状态的挣扎,试图用经济的独立换回个人的尊严。但他失败了,不健全的人格和孱弱的心理状态,于内于外都无法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离家出走”的失败收场,表明弟弟寻回自我意志行动的永远破灭。
(二)竞争与失败
家庭资源的有限,往往使得多子女家庭的儿童存在内部的竞争关系。赖希认为,同一家庭的儿童之间在和父母关系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强烈的爱与恨的情感关系上。在《孔雀》这部影片里,高氏父母因为愧疚,对患有脑疾的哥哥百般疼爱,甚至要求另外两个孩子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利。在这里,导演设置了“分糖”这一取巧的情节,用细节把哥哥对家庭其他两位成员生存空间的挤压表现得生动细致:糖一共106块,除以五,每人二十一块,哥哥拿到了多余的一块糖;之后,父母、姐姐和弟弟又各分了哥哥5块糖。
以《孔雀》里的兄弟关系为例。与普通家庭相比,哥哥对弟弟的压制无疑有着明面上的绝对优势,反映在日常生活里的各个方面,包括拎包、洗澡等;而处于劣势的弟弟对哥哥的对抗则隐秘得多,其对哥哥的两次反抗行为(一是跟随同学用伞柄殴打,二是深夜投老鼠药),都是在遭遇学校同龄人的辱骂和欺凌后,为了重拾尊严而进行的不得已的反抗,并在之后受到了父母的惩罚。由此可见高氏三兄妹的家庭地位排序。高氏父母居于顶端,是权威的代表。而哥哥在家庭里,仰仗父母的偏爱。但是,这不等于哥哥拥有真正完全的自由,这体现在他即便喜欢陶美玲,也依旧要顺从父母的安排,和农村来的金枝结婚。尽管姐弟都服从父母和哥哥的权威,但弟弟同时还听从于姐姐的指使。在这一家庭结构中,弟弟无疑是等级阶序的底层。对权威主义家庭观及其影片中同一家庭儿童相互竞争关系的探究,表明了家庭对个体意识塑造的巨大作用和在其面前个人意志的渺小无力,以致泯灭个性。两次反抗行为遭受的惩罚象征了弟弟和哥哥在家庭内部竞争中的落败。
(三)暴力与性压抑
西方权威家庭是西方社会源远流长的父系家长权威文化的主要社会载体,却不限于西方国家。赖希认为,权威社会借助于权威主义家庭而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进行再生产。尽管《孔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小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趋势已有抬头,出现资本的雇佣关系(如姐姐帮人刷瓶子),但集体意识残存的权威主义家庭模式依旧延续着它的作用。影片对此有多处刻画,观众注意到父亲这一角色对弟弟自觉人格的压制作用。在这个五口之家里,与母女间隐秘而含蓄的角力相比,父子间的压制模式由于男性的生理特征混入了暴力成分。而在片中,弟弟处于青春期的独特心理,也使得这份压抑掺杂了性萌发和性压抑的成分。
以弟弟为例。作为学生,他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其次是家庭内的辅佐性劳作。和学习无关的事务,则被视为“异物”加以驱逐。影片中的一幕,弟弟在学习,父亲坐下来递了杯牛奶,并叮嘱道,“现在社会,没有知识是万万不行的,你一定要好好学”。接着检查弟弟的作业,并在发现女子的裸体肖像画后,痛斥其“流氓”,随后把弟弟拖拽出家门,并大喊“邻居们快来瞧,我家出了个流氓”。这是弟弟承受来自父亲的第一次暴力。后来父亲拎礼物上门帮弟弟找工作,却被突如其来的狗吓了个趔趄,面对儿子的嘲笑,他回以狠狠的一巴掌——这是第二次暴力行为。两次暴力的本质缘由不同,前一次是由于弟弟不服从管教,后一次则因为弟弟对父亲权力的嘲弄。如果说第一次,弟弟是带有“自由意志”的反抗,那么第二次就是“顺从的反抗”,他对父亲的嘲笑,是特定环境造成的亲情情感压抑的表现。他厌恶父亲,但最终变成了父亲——麻木和逆来顺受。弟弟的青春期性心理同样受到了压制。他对“性”抱有天然的好奇,这体现在他偷偷绘制女性裸体画。同时,他也对自己萌发的性意识怀有羞耻和恐惧心理,表现于他帮姐姐购买性启蒙书籍时的慌张,以及惧怕被父亲发现。肉体的暴力和精神的性压抑成为弟弟自卑懦弱的心理诱因之一。
二、社会的弱者
弟弟高卫强是五口之家唯一的在读生。和哥哥、姐姐相比,他承受的社会压力来自学校的同龄人。影片中描写了哥哥给弟弟送伞的事件。在观众看来,亲人送伞本应是温情的体现,发展到后来竟成了血腥事件,与那个年代下的大众价值观分不开关系。
“揭发”,原指将坏人坏事揭露出来。这种揭发对人类情感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孔雀》的导演选择把这种破坏力量演绎出来——弟弟同班同学的两次检举行为。第一次是哥哥送伞,弟弟因为残障的哥哥而不敢出声,一位同学站起来喊,“我认得他,他是高卫强的哥哥”。后来弟弟请朋友果子假装公安人员来送伞,第二次的检举没有正面刻画,但可以从后来弟弟被欺凌的事件看出——有人在班级里揭发了弟弟的行径。两次揭发行为,使得弟弟在班集体中的地位跌落到底层,直接导致了他的退学。除外,影片也体现了邪恶的大众道德对亲情的伤害。两次送伞中,送伞者身份的变化,昭示了群众的普遍价值观——前者是残障的亲哥哥,后者是在公安局工作的假哥哥。弟弟及其同班同学对两者前后的不同态度,既体现了时人的价值取向,也表达了对亲情不敌体面地位的社会现象之讽刺。班集体是一个群体,这种观念像毒蛇般将弟弟缠住,迫使他归顺大众,为了重拾尊严,他选择了象征权威的公安人员的“哥哥”来为自己撑腰;事情败露后,弟弟遭到集体的欺负,暗示失去“权威”庇护的弟弟重新回到了弱者的行列。
《孔雀》中的三姐弟,都直接或间接地面对了来自群体的暴力。哥哥被工友压榨捉弄,因此他不停地更换工作;姐姐厌恶自己的生活环境,因此她选择和小王结婚;而弟弟,在遭到同龄人排挤时,第一反应是想通过请“哥哥”再次送伞以求挽回自尊,重新回到集体中去。当这种方法失效,他只能仓皇逃跑。原因是,在三姐弟中,弟弟的力量最为薄弱。他的学生身份注定其必须和排斥他的集体朝夕相处,也剥夺了他更换所处环境的可能性,他想工作,只能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未成年的弟弟丧失了学生身份,也不能为成年人的世界所容。因此他成了三兄妹中唯一逃离家乡的人。
三、反抗与幻灭
暴力与性压抑以独特的面貌在回乡的弟弟身上扭曲地成像。这既指弟弟的“断指”,也指其与妻子张丽娜扭曲的婚姻状态。
影片没有解释弟弟“断指”的经历,并非剪辑的原因。电影剧本一开始就省略了他这段在外的经历。笔者猜测,从他三缄其口,家人绝口不提的态度看,应该不是意外受伤导致的结果,而倾向于认为,弟弟扒火车逃离家乡后,卷入了某暴力组织争斗的漩涡,“断指”既指明了弟弟身上的暴力倾向,又昭示了他在争斗中的失败结果。社会和家庭对弟弟施予的压制,终究以这种惨痛的形式宣泄出来。有学者认为,弟弟这段人生经历的空白,和他回乡后因这段经历带来的转变,为人物增添了真实感和深刻性,吸引了观众去“填空”。笔者以为,弟弟离乡经历的隐去,可以看作是其所处环境对外部世界的隔阂和漠然,这座暮气沉沉的北方小城有着它特定的社会规则,大部分居民遵循这个规则生活。和高氏父母一样,小城居民对小城外的世界了无兴趣,也无心过问。他们小心谨慎,安于现状,编剧时空线的刻意收束和限制,强化了安阳故步自封的小城特点。
与年长的离婚妇女张丽娜的结合,及其“吃软饭”的举动既是弟弟遭到性压抑后的发泄,也是弟弟对周围环境无声的妥协,影片后期的他闲时除了带孩子,就是和街边的老人下棋。哪怕遇到对方悔棋,也只说一句,“中,你替我下吧,不跟他玩了”。弟弟并非没有过抗争,无论是在哥哥的水杯下药,找果子假装公安人员送伞,还有两次出逃,都是他在走投无路之下的绝境反扑。遗憾的是,反复的失败磨灭了他的斗志。我们在影片后期的弟弟身上看见了死寂和虚无,弟弟的结局证明了个人力量在权威这座大山面前的渺小,也点明了特定时代下恶劣的社会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尽管影片因艺术效果之外的缘由删减了弟弟的部分情节,但细心的观众仍然可以在电影中看见弟弟完整的生命线。弟弟与哥哥,一弱一强,他们同为家庭的一员,命运却截然相反,这种强烈的反差加强了影片的嘲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相较简单直率、充满理想色彩的姐姐,弟弟的形象要更为耐人寻味。他是时代的多棱镜,在他身上折射出家庭、学校、社会的多重面貌,以及权威力量生发的对普通个体的毁灭力量。弟弟的悲剧是必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尚未发展成熟的幼苗在狂风骤雨下悄无声息的死亡,是真实而深刻的写照。与此同时,弟弟高卫强在影片后期自我放弃式的“虚无主义”,使其富含的形象意义被掩盖在姐姐耀眼的自由意志之下。部分观众谴责弟弟的懦弱无能,以为他的人生悲哀完全是咎由自取,却忽略了作为一个心理、生理尚未成熟,经济、生活高度依赖他人的少年学子,他其实是影片中最需要包容和爱护的一员。影片中的高氏家庭,极度缺少爱的话语表达,本质是其爱能力的丧失。高氏父母本身没有自由意志,他们的意志就是当时社会意志的具象化。无论是扯下了姐姐蓝色降落伞的母亲,抑或是骂弟弟“畜生”的父亲,他们都代表了影片中一种无形的集体的道德力量。
对弟弟的关注研究最初缘于他身份的特殊——家中幺儿,校园学生,法律定义上的未成年人。编剧和导演赋予弟弟别样的观察视角,使我们明白弟弟的压抑和痛苦来源于一种特定时代的隐痛。观众与弟弟,有如结尾的主人公与孔雀,在观赏剧中人的同时也照见了自己,而后者则以痛苦的呈现方式,生动地传达了个体在压抑环境下寻找人生定位的徒劳,同时,弟弟一角对人性层面普遍弱点的映射也启示了我们对自我灵魂的不断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