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的散文家
——评苏沧桑散文集《所有的安如磐石》《纸上》
孟繁华
在消费文化统治生活的时代,越是高端文化越鲜有人问津,散文、诗歌的命运大抵如此。新时期以来,诗歌还有过辉煌的纪录,它开启了新的文学时代的功绩,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受到它深刻影响的几代人,都铭刻在心。那是他们不能忘却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因此而富有,因此可以月明风清地生活在别处,与这个红尘滚滚的时代界限分明。但散文似乎还没有这般幸运,这个古老的文体因体式的限制,既难革命又难先锋,因此,在这个“争夺眼球”的时代便很难被瞩目被热捧。于是,散文的寂寞也就是它的创作者的寂寞。当然,文学本来与热闹无关,它一如高山流水只待知音。但我发现,只要走进这个古老文体的深处,其四射的光华绚丽无比。
苏沧桑是一位散文作家,她生活在南中国的湖畔竹林边,执笔为文二十余年,有多种文集问世并获过“冰心散文奖”。这部《所有的安如磐石》,被称为是“散文中的天籁之音”,是苏沧桑十年磨一剑的散文精品集。文集分五辑:分别命名为“它”“我”“他们”“眼前”和“远方”。这些命名和它的内容,基本在昭示一 个声音,那就是书的扉页提示的“像祖先那样,依从心灵的声音休养生息”。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说法来分析的话,这是“反现代的现代性”——现代的步伐一日千里,GDP的数字不断攀升,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公路街道拥堵不堪……现代化将我们世代梦想的物质丰盈幻化为现实,同时我们也终于尝到了它酿造的如影随形的苦果。于是,反省或检讨“现代”的一厢情愿,就成为苏沧桑散文一个锋芒锐利指向的一个方面。这倒不是说苏沧桑如何用理性方式直指“现代”的要害,而是通过她的文体形式和情感方式,以不同的具体形象,类似《诗经》中“兴”的 表现方法,“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托“草木鸟兽以见意”。比如她写竹、写水、写地气、写树、写米、写地痛,这些外部事物一经她的表达和讲述,就不仅仅借景抒情、抒怀状物,她要表达的是与现实、与我们有关、切近而紧迫的问题:她写高尔夫球场的地:那里“湖光山色、绿草如茵、沙坑果岭,无论是球场的景致还是球道的长短、难度,都是设计者精心设计、刻意雕琢。可它的宿命,生来就是挨打”。但是这还不够:
最痛的,是果岭边的地,可谓伤痕累累,因为球近果岭了,但还未上果岭,就要用切杆,杆头往地上切,做砍头一样的动作,瞬间,一大块草皮飞起来,被斩首的草粘在铁竿头上,绿色的黏液像血。敏感如我,常有种心悸的感觉。(《地痛》)
与其相比较的,是——
…… 儿时学自行车摔到农田里,那沁人心脾的泥腥味……翘檐的老屋……后山的小溪、映山红和一座座老坟……外塘姨婆家海泥鳅的无比鲜美,沙子炒蚕豆让人心碎的香,刚出锅的小葱炒土豆,鸡鸭狗打架……黑白照片里母亲的纯美……上学路边一丛比太阳还艳的野菊花……毛竹搭的戏台……母亲亲手做的嫁衣……异乡街头飘来的家乡海鲜汤年糕的味道……泛黄的手写书稿……黑板上熠熠生辉的词语——淳朴、诚信、正直、坦荡、理想、快乐……(《地气》)
“现代”就这样将诗情画意和田园风光永远地变成过去。“战胜自然”“改天换地”的口号实现了,但是,在这远非理性的观念和道路上,我们真的找到了我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了吗?在苏沧桑的比照下,我们看到的只是触目惊心的沧海桑田。
当然,这还只是“现代”铸就的外部事物。在财富和金钱成为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时候,社会道德的跌落便是它结出的另一个畸形恶果:
三十年后,我的孩子,和无数孩子一样,带着手机,背着沉重的书包和家长一万个不放心的叮嘱和眼神,走在放学路上。野兽般的汽车,狼狗般的电瓶车,等在校门口的杀人狂,骗子,拦路勒索的校园小霸主,富含各种有毒物质的各种零食,一路风险,一路忐忑,一路风声鹤唳。(《放学路》)
因此,苏沧桑虽然处江湖之远,但她“位卑未敢忘忧国”。她曾在书的后记中表达过她近年来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最近这一个十年,我表面平静,内心汹涌。 夜深人静时,我清晰地看到自己以及和我一样匍匐在大地上的动物们、植物们、人们的生态堪忧——离最初的朴实、纯真、安宁、诗意,越来越远;离一种安如磐石的幸福感,越来越远。”因此,她的这些篇章,充分表达了她对公共事务积极介入的热情,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和优秀作家应该具备的品行和坚持的最高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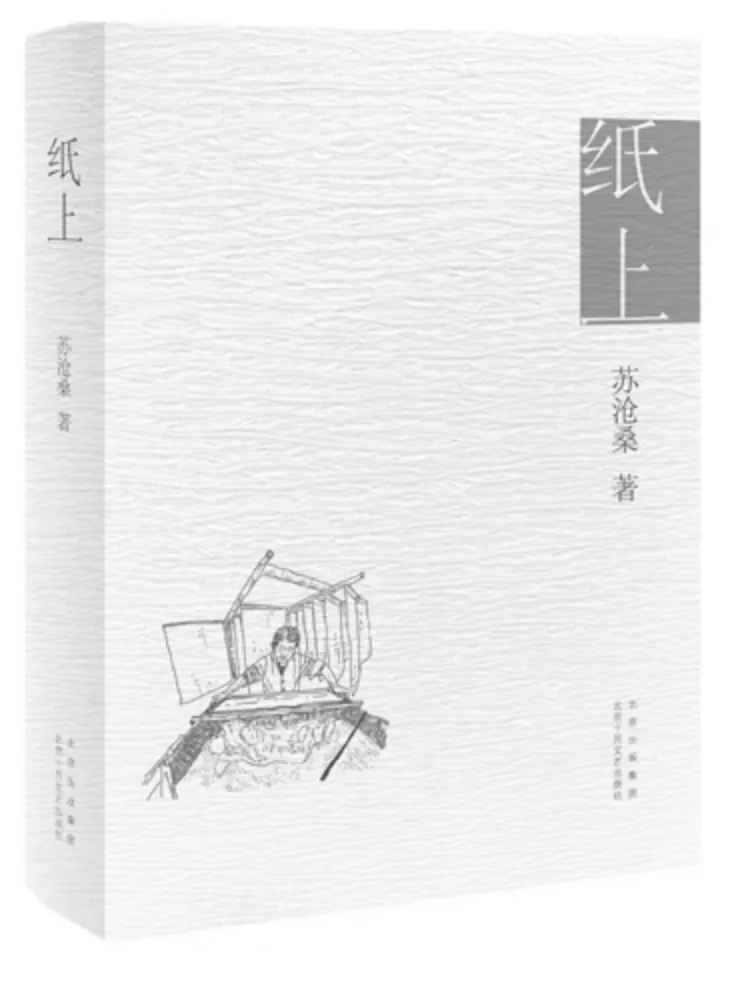
但是,作为一个散文作家,特别是一位女性散文作家,苏沧桑当然不是专事社会文化批判的职业斗士。这也诚如著名作家张抗抗在本书序言所说,沧桑写的是她的“痛与梦”。她更多的散文还是写她亲历的人与事,写她的梦幻和理想。在她的作品中,她写保姆、女儿、朋友、父亲母亲、写犯罪的少年、写梅家坞和种满庄稼的花园、 写人心的善和人间的暖意;写渴望“像仙女一样”地生活,当然也写异国情调他乡异客:“自由飞翔”的“我”“依从心灵的声音休养生息”的“他们”、那看似 “走得很慢”,也许是“走在最前面的”“眼前”事物,以及与信仰和普遍价值有关的“远方”想象等,在苏沧桑的笔下飘渺而柔美,端庄又俊逸。
苏沧桑散文的书写对象,大多应该是诗的题材,特别是题目,极富诗意。从她的散文中可以明显感知,她有良好的传统文化修养,尤其是古典文学的功底。她对传统文学中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显然格外属意;当然,她也热爱梭罗的《瓦尔登湖》、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因此,她的文章既有传统中国士大夫的风雅意趣,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既有国事家事天下事,又有风声雨声读书声。但是,究其沧桑散文的最大魅力,还不止是书写的对象或遣词用语,最重要的还是她的真情实感,她的这些文字是从心底流出的文字。有幸邂逅《所有的安如磐石》,眼前浮现的作家苏沧桑便是——“休提纤手不胜兵执笔便下风华日”的形象。相信她苦心经营种下的这些文字,“深浅不一的疼痛与忧伤”,一定能够实现她唤醒哪怕一座仍在沉睡的“珊瑚礁”的真切期待。
在延安时代,文艺家们曾开展了“走向民间”的活动。这个活动在阿瑞夫·德里克看来,对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对他们实现思想情感和话语方式“转译”的重要举措,让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话语方式都转向人民大众一边。通过这一活动,延安的文艺家们解决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自然也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全员动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总目标上,文学艺术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传统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下的文学创作。民众动员的时代过去了,但是,生活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的真理性并没有成为过去。多年来,苏沧桑不断地走向民间,汲取了大量的文化营养,逐渐形成了个人相对稳定的书写对象和审美趣味,创作了大量受到广泛好评的作品,在生活中,她找到了一条适于自己的创作道路,用她的话语形式和讲述对象,发现了另一个我们不熟悉、已经远去却还存活在当下的历史,这是活的化石,是散落在民间的历史脉搏的有力回响。这就是《纸上》。
这些作品在结集前曾先后发表过。《纸上》曾在《人民文学》头条重点推出、《新华文摘》转载,《跟着戏班去流浪》《与茶》《春蚕记》《牧蜂图》《冬酿》《船娘》等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刊出,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这些作品,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如朱中华与古法造纸;邵云凤、沈桂章与春蚕;潘香、阿朱、赛菊等与戏班;黄建春等与“茶”;沈建基与养蜂人;灵江叔等与酿酒;虹美等船娘们。内容是“非虚构”的,笔致是散文。
当我们阅读其中一篇作品的时候,觉得别致但也没有多大的冲击力,但是,当集中阅读这些作品时会猛然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江南在苏沧桑的作品集中被塑造出来。
《纸上》写的是富阳一个古老村落里唯一坚持古法造纸的传承人。“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元书纸是富阳竹纸的精品,是富阳传统手工制纸品的代表。富阳在唐末宋初开始制造竹纸,工艺技术随时间推移渐趋成熟,生产的竹纸质地优良、洁白柔韧,微含竹子清香,落水易溶、着墨不渗、久藏不蛀,成为书写公文用的首选纸品。朱中华是造纸世家,家族最辉煌时,曾有八个纸槽五十个工人。到了朱中华这里,他的愿望就是造出世界上最好的纸,让会呼吸的纸、让纸上的生命留存一千年、一千零一年、更多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愿望。这个愿望看起来诗意无限,背后隐含的却是无尽的艰难。人们多关注的是纸上的字、纸上的画,谁的印章。却没有人关注一张纸本身,也没有人关心一种纸的消失、一门手艺的失传将意味着什么。作者以诸多现场细节,观察、讲述了古法造纸人朱中华和继承他志业后代的不易。 作者说,为了写《纸上》:“为深入体验、采访,我踩着泥泞,冒着严寒,顶着雾霾,忍着病痛,亲手触摸在水里泡了四十多年的六十多岁捞纸工的手。那双手的触感让我震撼,仿佛摸在一块没有生命的橡胶上,橡胶上层层叠叠结着白色的、厚厚的老茧和没有一丝血色的旧裂痕。《纸上》试图挖掘记录现场所有的气味、声音,将笔尖深入纸的每一层肌理……在近两万字中,解剖一张纸的前世今生、它与主人公命运的深刻联系、它的传承与未来。”《纸上》洋溢的不是盎然的诗意,而恰如这古法造纸的历史一样少有欢欣。
《跟着戏班去流浪》是我更喜欢的一篇作品。题材浪漫,写得也浪漫。戏里戏外真真假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不同的场地,不同的观众,自然也有不同的遭遇。不明白戏班流浪人生的作者和戏班人说:“演戏多好啊,我从小就想当作戏人。”但赛菊的一句“太苦了呀”大家就都不响了。流浪的戏班本质上是苦中作乐,他们是中国民间的“大篷车”;还有那常年徜徉在湖光山色间的船娘,表面看,她们就生活在诗意间,或者说她们本身就是诗意的一部分。但没人知道的是,她们每一天过的是“眼睛的天堂,身体的地狱”般的日子;还有那养蜂人,辗转在天山、伊犁河谷、果子沟、赛里木湖,这是何等的浪漫诗意。但是,一旦需要转场,火车说走就走,途中就如现代性一样不确定,于是,吃饭、上厕所都成了问题,如果火车开走了,要么你“扒车”去追,要么找火车搭车去追;下了火车还要找马队驮蜂箱,一波三折的仍是故事的主体:马失前蹄,车翻了,受惊的蜜蜂疯狂乱窜,一头大马竟然被惊慌失措的蜜蜂活活蜇死。翻车要人命,蜜蜂受惊也会要人命。这是生活,但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作者追逐的养蜂人,居然是一个年届七十的诗人。他将养蜂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幻化成生活的诗篇。诸如此类,《纸上》描述的人与事,恰如东边日出西边雨,让人喜忧参半悲喜交加。但生活的本质不就是这样吗?苏沧桑在自序《春天的秒针》中说:“三年多来,‘我’深入‘他们’的生活现场,亲身体验捞纸、唱戏、采茶、养蜂、育蚕、酿酒、摇船,截取鲜活的人生横断面,深度挖掘其间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文化意识、文化自信,抒写新时代新精神,讴歌中华民族山水之美、风物之美、传统之美、劳动之美、人民之美。”这是作者走向民间的真实体悟。
《纸上》所有的作品,都来自作者的亲历。这不仅使作者与她的书写对象有了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联系。同时,她也发现了另一个不一样的、我们不了解的江南。过去,我们理解的江南是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或者是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或者是苏东坡的《望江南》,在文人墨客的眼里,江南被描摹得草长莺飞花团锦簇,风光无限诗意无限,江南就这样成了人间天堂。这是诗人的江南。苏沧桑的不同,她是透过历史构造的诗意江南,在民间、在生活中看到的另一个江南。这个江南同样诗意无限,它与历史、与风物风情、与华夏文明息息相关。但是,维护、传承、光大这一文明的人们,不可能在花前月下,在茶肆酒楼完成。他们要在生产实践中、在劳动中完成。于是,苏沧桑的散文,承继了一个伟大的主题,这就是劳动的主题。“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我们在理论层面,从来不否定劳动的意义和劳动者的价值。但是,许多年以来,在我们的文学中,还有多少劳动者的身影被歌颂,还有多少劳动者的形象被塑造?当苏沧桑将这些默默劳作的“人民”跃然纸上时,我们才发现,我们与这样的形象已经久违了。
这是苏沧桑走向民间的发现。这个发现不止是对民间生活的发现,同时也是对民间美学的再发现。民间美学就是前现代美学,前现代美学的审美对象是自然、乡村和劳动,美的观念是建立在自然原生态基础上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怀旧、乡愁等与前现代相关的离愁别绪,为什么乡村美学在中国是如此的强大甚至不可撼动。审美对象的选择,也隐含了作者对某种审美对象的拒绝。对乡村的意属,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当然,我们不可能将苏沧桑的选择愚蠢地认为她在倒退或复古。事实是,她书写的那种生活方式或生产方式,于今天来说,是只可想象难再经验的过去。但是,这些场景或前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她用文字构建起来的另一座“博物馆”,让后来者也能够了解甚至直观这些“陈年旧事”,并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历史。过去的事物在生活中可能失去了实用功能,但它在生活中并没有消失,它还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我们的心灵和精神世界,那是我们的文化血脉。苏沧桑身体力行,用她的纤笔一支,抚今追昔,用文字打造了一座非遗博物馆,实在是难能可贵。当然,她的努力有了令人鼓舞的回响,她曾获得了许多奖项。十月文学奖散文奖授奖词说:“她在纸间供养中国江南最后的蚕桑,蚕声如雨,笔落成茧。一个民族星云闪烁的记忆,耕织社稷的文明初心,一带一路上的远方与乡愁,她以蚕桑之事织就对世界的整体性想象。它是桑间地头行走的辞章,是千年蚕事女儿心与文心在当代田野的相会,一曲灵动幻美、文质皆胜的非虚构农事。以美文的形式抵达如此宏大深邃的主题,苏沧桑外,罕有人及。”这样的评价,苏沧桑当之无愧。
2021年7月5日于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