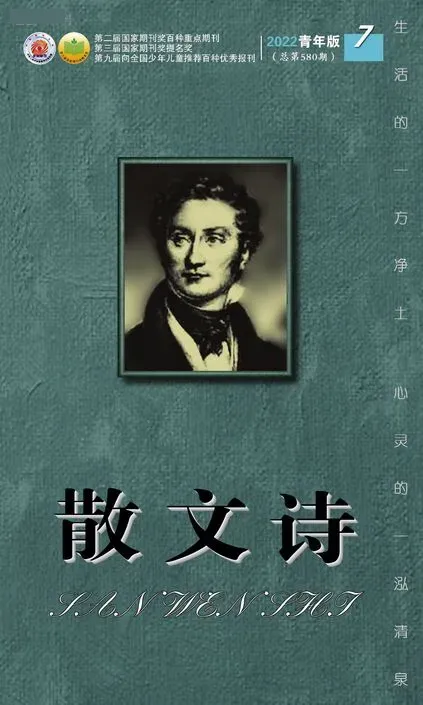花儿朵朵
龙小龙
喇叭花
吹吹打打的日子,在乡村依然盛行。
吹奏中,乡村小路变成了水泥公路。路上行走的牛车变成了汽车。来来往往的故事,从张村到王村,从赵姓到钱姓,从贫瘠到富裕。
吹奏中,阴霾的天气越来越少。
云朵晾得很高,天空像一床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色床单,久久凝望,便会望见曾经在床单里安详的睡眠,星星点灯的呓语。
炊烟散开成巨大而透明的白纱巾,传递徐徐香风和鸟鸣,勾起谁的欲望。
牵牛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歪扭的浅浅足洼,都走远了。
喇叭花蹲在角落,或者路边。
她的眸子依旧单纯,明澈如露,穿着白的、紫的连衣裙,咬着牙,不吱声。
喇叭花,是谁家长不大的小女儿。
梨 花
夜,只属于感觉和听觉。昨夜,风在泼墨,起笔落笔,尽在视野之外。
偶尔发出潇洒飘逸的刷刷声。
天亮张开眼一看,山川却比想象中轻灵许多,树木枝干只是一些轻描淡写的勾勒。
大地,潦草,蓬松。显示另一种沉重。
越过漫长的寒冷,本该放下一冬的宿疾了,而人们弯曲的身体暂时还习惯性地弓着,仿佛依然怀念着身下取暖的火盆。
那些泛青的色调被半透明的白笼罩。
无边的静寂,就像一只巨大的玻璃杯,空荡。
离我最近的一棵梨树——
像我的老父亲,站在辽阔的田垄,顶着一场茫茫大雪,等着我。
南瓜花
南风吹过几遍,爬满青藤的桑树一低头,树下的岁月,便成了雨季。
而风声越来越密。
不说飞舞的风筝曾经让多少仰望失魂落魄。
也不说静谧中却平白无故地扰乱一池湖水的絮语。
许多想法,只能在纸上兴叹。
南瓜花在绿色深处兀自吹奏,它只想把日子奏得黄亮亮的,抹上富贵的色彩。
敞开思念的小村。
主角永远是渐渐枯萎的南瓜花,宛如远行的南方小姐妹。
一位远在异国他乡的闺密。
当稔熟的、小巧玲珑的身影模糊于视野尽头,总会令人怅然,感觉像薄雾笼罩。
卷曲萎缩的阳光下面,刚刚受孕的南瓜,打着一颗相思结。
小村里,谁家失声啜泣,如看不见的流水。
玫瑰花
她们集体失踪。
从春天的花园中消失,顺便带走了戒指和香水。
带走了我准备一冬的虚词。
随后,却又集体出现在公众视野。
比如闹市区,影剧院,咖啡屋,某个青春靓丽花枝招展的娱乐节目中。
我注意到这个夜晚,天空被一道不解人意的河流劈成了两半。
我的屋顶月亮不知所踪,炉灶里的火焰黯然失色。
此岸,温度骤然下降;彼岸,季节大幅升温。
此岸西风盛行;彼岸东风沉醉。
玫瑰成为一种暧昧的颜色,一个令人欲罢不能的魔咒。
当艳丽的花朵离走后,大地尽是芒刺,却又拔不得。
一拔,手就痛。一拔,心就疼。
也不知这种滋味,是谁发明的?
虞美人
读懂了往事。
读懂了小楼昨夜凋落一地的东风。
读懂了一轮薄如纸片的故国明月斜挂天空。
读懂了绵延不绝的一江春水。
读懂了掠过宝剑寒光闪烁的锋刃时的那一抹血红。
就读懂了她低头的羞涩与抬头的娇媚,泪光婆娑中,尽是对尘世理解的百般滋味和恩怨情仇。
就读懂了为什么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绽放一枝拿不起,也放不下的花朵。
湿淋淋的露水中,总有铁马滚滚而过。
宏大,隐约,遥远,惊雷一般。
可曾留意弓箭上的纹身,刀柄上的流苏,飞舞长空的水袖。当伟岸与婉约并存,生命定然结出刚柔相济的佳话。
英雄美人,江山落幕。
隔岸。某个瓷瓶里反复插播一曲荡气回肠的挽歌。
格桑花
寒风的皮鞭未收敛,霜雪的铁锤未放下,兽群的撕咬未停止。
但正是命里注定相逢的刁难,铸就了我所尊崇的人格魅力。
摧不垮,压不灭,烧不尽。
这种于苦难中磨练出来的品质,才是最朴素的坚韧,最本真的个性。
有娘就有家。有格桑花的地方,就是羊群和马队眷恋的家。
我喜欢,这开满胜利和幸福之花的家园,在莽原上燃烧着不灭的灯火,举着缤纷的旗帜。
彰显苍穹之下的伟大。它,才是高山的脊梁。
用简单的颜料和瘦弱的身体,用嘹亮的长调,一寸一寸地托起牧人的希冀,给青草大地赋予了穿透性和无限的张力。
并与哈达一起,把自己献给心目中的英雄,献给干净的白云和无私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