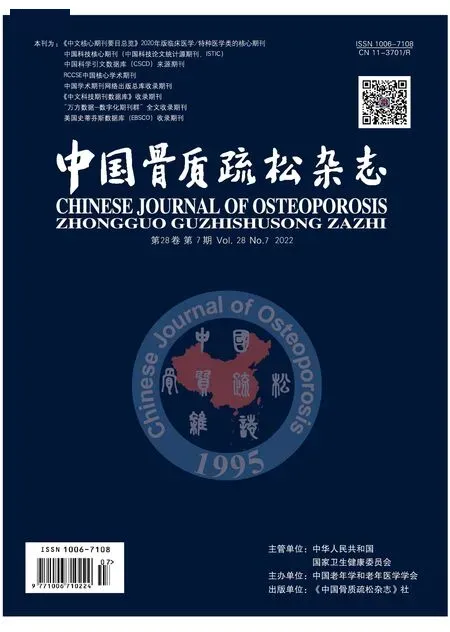OSTA在中国各级医疗机构骨质疏松筛查中的应用进展
付赛 赵宇 王世浩 刘树华 张桂鑫 黄宏兴 万雷*
1.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 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 510375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一种以低骨量、骨组织微结构破坏,导致骨脆性增加、骨强度及骨密度下降,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1]。初期因无明显的症状容易被忽视,其中疼痛是骨质疏松症最常见、最主要的临床表现,当人体骨量丢失>12 %时可出现骨痛,而骨折是骨质疏松症最严重的并发症[2]。OP可以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任何年龄都可以发生,但多见于老年男性和绝经后女性。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3]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 40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70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 06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3.50 %),与2010年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上升了4.63 %。流行病学调查[4]显示,我国50岁以上人群OP患病率为19.2 %,其中男性占6.0 %,女性占32.1 %。有研究[5]对2010年-2050年我国50岁人群脆性骨折发生率及费用进行预测,2010年大约有233万例脆性骨折发生,花费约94.5亿美元;到2035年,脆性骨折发生的年数量和费用将翻一番,到2050年将增加至599万例,花费约254.3亿美元,防治费用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然而,骨质疏松症是可防可治的,早期筛查和干预可以降低OP带来的危害。因此早期识别与筛查出OP高危人群,减少OP及其并发症的发生,有益于我国对于OP的防治和诊疗工作的开展。
OP的筛查工具众多,检测仪器包括双能X线吸收仪(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定量超声(quantitative ultrasound technique,QUS)等,筛查量表工具包括WHO骨折风险评估工具(WHO 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FRAX)、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l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OSTA)等,其中DXA是诊断OP的“金标准”,但因其价格昂贵、执行操作复杂、需专业人员操作,难以在我国各级医院普遍开展。QUS虽具有安全、无创、无辐射、设备轻便等优点,但因其检查操作相对复杂、对操作人员的技术要求高、耗时长、存在一定人工误差,故在使用方面受到限制[6-7]。FRAX主要是一个评价骨折危险的工具,能有效识别骨折中、高危患者,可用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防治,但其存在一些缺点,如:某些骨折危险因子缺失及易受继发因素的影响[8]。而OSTA主要根据年龄和体重筛查骨质疏松的风险,作为医疗机构和民众自我测评的筛查工具,具有简便、高效的特点,可快速识别出骨质疏松症高风险人群。
目前我国在各级医疗机构中的OP筛查均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缺乏昂贵的OP检查设备,缺乏适合本地实际状况的调查评估工具;另一方面社区卫生机构与大型综合医院之间缺乏信息沟通。由于各种因素限制,虽然OP的诊断依赖DXA骨密度检测,但其仍未能作为OP的普查工具。然而对骨质疏松症的筛查刻不容缓,有必要利用简易工具在各级医疗机构开展风险筛查,而价格便宜、操作方便且具有较高灵敏度和特异度的筛查工具便体现出优势[9-11]。在由黄宏兴教授等人牵头制定的“基层医疗机构骨质疏松症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1)”[12]中,OSTA被推荐作为OP风险评估的初筛工具。本文拟对OSTA在中国各级医疗机构骨质疏松筛查中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1 OSTA概述
OSTA是由Koh等[13]基于对八个亚洲国家绝经后妇女进行的研究,具体为收集多项骨质疏松危险因素并进行骨密度测定,从中筛选出11个与骨密度具有显著相关的风险因素,再经多变量回归模型分析,获得敏感度和特异度最佳的2项简易筛查指标即年龄和体重,从而得出用于评价亚洲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危险性的工具。OSTA指数计算公式及分级如表1。

表1 OSTA指数计算公式及分级Table.1 Calculation formula and classification of OSTA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治指南(2011年)》[14]明确将OSTA量表列为初筛量表之一,建议当OSTA指数<-1时应进行骨密度测定。在亚洲绝经后女性无BMD检测条件的地区,推荐OSTA作为骨质疏松症风险初筛工具,可用于OP风险的自我评估。此外,在Kung等[15]与Lynn等[16]的研究中,他们同样认为OSTA指数可以作为早期筛查和评价骨质疏松的简易指标。在成都社区中进行的一项涉及15 752名40岁以上健康女性的研究[17]中发现,OSTA对预测低骨密度或骨质疏松症很有用。也有研究[18]显示OSTA的灵敏度为96.3 %,特异度为6.3 %,AUC为0.710,由于OSTA的灵敏度较高,在筛选工具当中使用起来最为简便,适合筛检基层人群。有研究[19]将其与DXA测定的OP诊断标准对比,OSTA评价骨质疏松症风险的灵敏度、特异度以及诊断符合率均较好,可作为OP的简易筛查工具。因此使用OSTA不仅可以鼓励患者和临床医生更积极地评估OP风险,而且可以提示风险人群进一步测量骨密度,进行早期干预,预防骨折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尽管OSTA工具简单、易于操作,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杜娜等[20]对412名绝经后健康女性受试者进行实验得出,OSTA诊断骨质疏松的敏感性一般,不建议单独作为早期骨质疏松筛查工具。在一项关于OSTA指数和FRAX联合诊断2型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症的研究[21]中表明,两者联合应用可提高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弥补单一工具预测效果较差的缺陷,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OSTA和QUS的联合,有助于发现患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这可能是诊断骨质疏松的另一种方法,特别是在无法进行DXA测量的地区[7]。因此,将OSTA、其他筛查工具和OP危险因素相结合,可能会提高准确性。因此建议结合其他危险因素或筛查工具进行综合判断,以便提高筛查的准确率和预测效果。
2 在各种疾病患者中的应用
2.1 OSTA评分在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筛查中的应用
老年性骨质疏松症(senile osteoporosis,SOP)一般指老年人70岁以后发生的OP。我国65岁以上人群中OP患病率达到32 %。《中国老年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22]对于≥65岁女性和≥70岁男性推荐直接进行骨密度检测,然而结合我国老年人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DXA无法普及的医疗环境,OSTA用于老年人OP风险筛查仍具有意义。
曹硕等[23]的研究表明,OSTA对于SOP患者的筛查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与DXA结果有一定的相关性,提示OSTA作为老年女性原发OP患者的筛查工具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国内有研究[24-25]分别在杭州(共11 540例,平均年龄70岁)和上海(共3 284例,平均年龄73岁)的基层社区利用OSTA进行骨质疏松症筛查,显示OSTA指数能有效筛查出所在社区老年人患骨质疏松症的高危人群,验证了其有效性,研究者建议在社区老年人中推广使用OSTA筛查工具。
2.2 OSTA评分在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筛查中的应用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P)是最常见的代谢性骨病。OSTA本身即是针对亚洲PMOP危险性进行评价的方法[26]。在绝经后妇女中使用OSTA筛查骨质疏松风险已被证实是更经济、有效的方法,且推广应用中优于其他更复杂的骨质疏松风险筛查工具[27-28]。
Fan等[29]将2 055名年龄≥45岁于北京社区居住的绝经后女性纳入骨质疏松筛查研究,结果显示OSTA的AUC范围与FRAX相似(均>0.72),均能可靠预测PMOP。另外在规定阈值内,这两种工具在仅遗漏7.2 %~8.6 %患者的情况下,可使需要测量BMD的病例数量减少37.6 %~42.4 %,证明OSTA可作为鉴别北京汉族人群PMOP的可靠而有效的工具,尤其为缺乏DXA的医疗机构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另一项中国香港社区招募的722名绝经后妇女的研究中,得出OSTA是一种廉价有效的方法,不仅可以有效评估OP风险,还可促进在发展中国家适当和更具成本效益地使用骨密度测定的方法[30]。
2.3 OSTA评分在预测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的应用
OP是绝经后女性的常见疾病,其发病有明显的性别差异[31]。胡健等[32]对我国5 745名50岁以上体检者进行骨密度测定评价OSTA筛查老年性骨质疏松效果的研究中发现,OSTA可用于50岁以上人群OP筛查,且更适合用于女性,建议OSTA最佳干预值为-1.7。然而,吴秀云等[33]发现OSTA不论在男性还是在女性人群中,均有较高的敏感性,具有一定的筛查价值。国内有专家指出在60岁以上男性健康体检者中发现OSTA指数有助于OP的早期筛查。何燕萍等[34]发现OSTA指数评价老年男性OP风险的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均较好,可作为男性诊断OP操作方便的简易筛查工具。在中国香港地区基层人群中也验证了OSTA可以预测老年男性OP[15]。Huang等[35]在四川省人民医院10 000多名体检人群中,利用OSTA有效地筛查出了老年男性群体中OP和骨量低的患者,可节省1/3的DXA检查资源,表明OSTA在老年男性OP筛查中的应用也是有价值的,值得在各级医疗机构推广。
2.4 OSTA评分在骨质疏松性骨折中的应用
骨质疏松性骨折系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受到轻微外力或通常不会引起骨折的外力时发生的骨折,亦称脆性骨折(fragility fracture)[36]。费琦等[37]指出OSTA指数在预测PMOP和新发疼痛性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方面可能是一个简单有效的的临床筛检工具。因此使用OSTA有助于及早识别有PMOP风险的妇女,并指导预防和治疗,应用前景广阔。另外OSTA量化的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危险程度与臂踝脉搏波速度(baPWV)等因素显著相关。baPWV的临界值为1 676 cm/s可能是预测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的潜在可接受标志物[38]。然而,在一项横断面研究[39]中发现,在临床实践中,OSTA在骨折方面虽然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OSTA不足以有效预测新发疼痛性骨质疏松性椎体骨折(PNOVFs)的风险。而FRAX可能是确定中国老年男性PNOVFs高风险的有效工具,截止值为2.9 %。
2.5 OSTA评分在其他疾病合并骨质疏松症中的应用
临床和流行病学证据[40]表明,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与OP有关联。T2DM和OP经常共存,并且都受到年龄的影响[41]。一项研究[42]称20 %~60 %的T2DM患者会发展为OP患者。T2DM患者胰岛素分泌不足会影响钙沉淀[43],同时血糖控制不佳又会抑制骨形成,从而诱发骨质疏松[44]。OSTA指数可以作为绝经后糖尿病患者髋部骨密度预筛的良好指标[26]。Tang等[45]的研究也表明OSTA适用于对我国绝经后女性T2DM患者股骨颈部位骨质疏松的早期筛查。
另外,在合肥进行的一项探讨OSTA指数对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患者骨质疏松的预测价值的研究[46]中,结果显示,在320名老年RA患者中,OSTA指数与BMD密切相关,且相关程度远强于年龄或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3 结语
OP是人体退变和代谢改变的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类骨病。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对各级医疗机构受众人群的OP筛查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经在我国进行的大量实验验证,OSTA具有高灵敏度、简单易操作、易于被医务人员及被筛查人群接受的特点,有较广泛的适用度。在与相关工具结合应用时其灵敏度和适用性可进一步提高。
在分级诊疗政策深入过程中,OSTA可定位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基层医院进行OP初筛的工具之一,有效筛查出需要进行BMD检测的高危人群进而向上级医院推荐,从而做到对OP的早发现、早干预。在上级医院诊疗前进行OSTA等工具筛查,可以节省医疗资源、明显提高成本效益。以此契机建立起各级医疗机构间的沟通、合作,可提高OP筛查效率、明确分类诊断、规范治疗以及便于各级之间的双向转诊,使筛查、诊疗、随访管理的过程更高效。
OSTA在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中用于筛查OP是有价值的,然而对此我国暂未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最佳干预阈值[47],且研究均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经济发达城市进行。因此对于未来OSTA筛查OP风险的研究方向,应着力于深刻探讨其在中国基层医疗机构骨质疏松筛查中的适用性,开展多中心、大规模、涉及中小城市的研究以完善最佳干预阈值标准,推动包括OSTA在内的简易筛查工具在各级医疗机构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