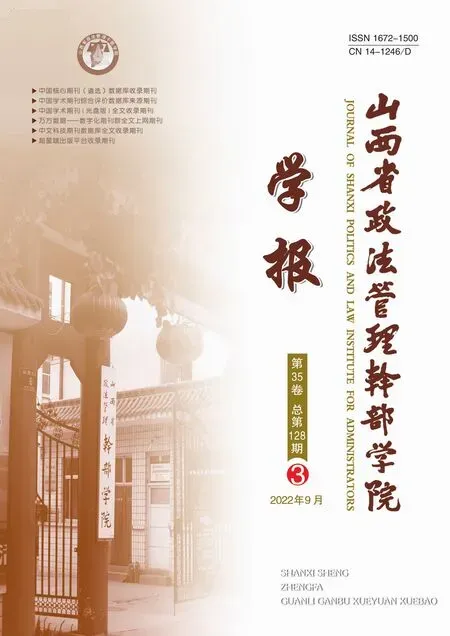分居期间法定财产制的立法选择
周旭诚,张 挺
(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一、问题的提出
婚姻法语境下,分居一词的指向包括自然事实、法律事实与法律制度。[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中的“分居”一词指向的是自然事实,但针对财产制的讨论,应以法律事实为前提。因此本文语境下,分居是指引起夫妻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发生、变化或消灭的法律事实,而对自然事实意义上的分居以“分别居住”称之。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一千零六十五条分别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和约定分别财产制。遗憾的是,上述条款均未提及分居期间夫妻财产制的特别安排。单从文义解释出发,当夫妻双方就婚后夫妻财产制没有特别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应适用法定婚后夫妻财产共同制。尽管立法如此清晰,但判例仍存在分歧。此外,分居期间适用法定财产制,虽然可以保持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制的稳定性,但也会在子女抚养、家事代理权等细节招致解释困境。参考比较法,意、法、德等国家针对夫妻分居均规定了特别财产制。由此可见,夫妻分居期间适用共同财产制的做法尚存商榷的空间。
二、分歧的司法判例
(一)一般做法——夫妻共同财产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公布的49起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中的案例(七)涉及在夫妻分居期间,由一方取得的财产的归属问题。本案中,被告辩称涉案房屋是其在分居期间完全用个人的财产购买的,应属于个人财产。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法官经过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为夫妻共同财产”;(1)《最高人民法院公布49起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之七:李某诉孙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最高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针对2016年指导案例66号《雷某某诉宋某某离婚纠纷案》作出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我国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没有建立非常态下的特别夫妻财产制,对夫妻分居情形,仍坚持共同财产制……”;(2)《雷某某诉宋某某离婚纠纷案——指导案例66号的理解与参照:婚姻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离婚时”含离婚诉讼期间与离婚诉讼前》(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2016年)。申请人王某与被申请人马某某离婚纠纷案中,法官针对分居期间的子女抚养费给付指出,“对于婚内子女抚养费一项,因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婚姻存续期间并无各自取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书面约定,故被申请人马春生在二人分居期间取得的抚养子女的费用亦属夫妻共同财产”。(3)(2016)辽08民再82号。针对分居期间财产归属问题,法官大多采取了上述个案中的判决思路,并未对分居期间的夫妻财产归属作特别处理。
(二)特殊做法——夫妻分别财产制
但在部分案例中存在不同观点。如2016年江苏省高院发布的家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中的案例五,在对本案的点评中存在以下论述,“在夫妻关系正常的情况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一般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生活时则另当别论。此时,夫妻各自控制和支配着自己使用的那部分财产,与夫妻分别财产制或离婚后各自的财产关系相似”;(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2016年江苏法院家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之五:杨甲、杨乙诉杨某抚养费纠纷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成年子女可以要求父母一方支付抚养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年)。汤某诉徐某离婚纠纷案中的法官评析道,“如果夫妻双方存在分居关系,且系因感情恶化或感情已经完全破裂而分居的,那么在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个人财产……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的夫妻分居,主观上夫妻间已经丧失了共同生活的愿望,客观上已经结束了共同生活的状态,从而失去了建立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基础和条件,夫妻双方的经济关系已经中断,夫妻一方的财产收入已不以双方相互依存为前提,所得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分离状态,形成了两个独立的经济生活主体。虽然双方仍是夫妻关系,但这只是身份关系而已。”[2]
综上所述,最高院指导案例尽管确认存在夫妻分居的法律事实,但由于立法未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因此仍适用共同财产制;也有部分法官认为,分居期间的夫妻财产状况发生变化,仍适用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不妥,应允许分别财产制的适用。
三、共同财产制的适用困境
(一)缺乏合理性基础
根据《民法典》,婚姻关系成立后,如无特别约定,夫妻间即形成夫妻共同财产制。就其合理性基础,存在几种学理观点:一是家庭贡献说。我国从1950年婚姻法开始就实行了共同财产制,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就应该是推定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相等;[3]在传统家庭结构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承担了较多的家事劳动并牺牲了其参与社会劳动的机会,而另一方参与社会劳动获取货币报酬。此时,承担家事劳动的这一方的劳动成果并没有以货币的形式呈现,但其确实创造了社会价值,从事社会劳动的这一方也从中获益。此时,出于保护从事家事劳动的一方当事人的需要,需要对其家事劳动加以评价,也就是将其的贡献反映于夫妻共同财产制中。二是家文化说。中国传统社会历来以家庭为本位,重身份关系的调整,轻财产关系的规范……在夫妻关系上,也更容易接受夫妻一体主义的观念,认为夫妻在人身上既然不分你我,在财产问题上也应不分彼此。[4]《礼记·昏义》中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由此可见,我国传统中婚姻的首要目的是家族延续与祖先祭祀,是家族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的。[5]三是共同生活激励说。从制度的功能上看,夫妻财产制度有利于婚姻和家庭生活,能够为夫妻双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各项经济活动或非经济活动提供经济上的激励。[6]
而上述合理性基础在分居期间均难成立。首先,分居期间当事人双方生活各自独立,各自承担家事劳动与社会劳动,彼此也不从对方的家事劳动中获益,因此毋须通过共同财产制评价家庭贡献;其次,由于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观念的勃兴,婚姻双方越来越被视为两个具有独立思想和感情的个人的契约联合。[7]现代婚姻中传统家文化日渐式微,而更具个人本位色彩;最后,分居期间不存在正常家庭生活,此时也不再需要夫妻共同财产制为家庭生活提供物质激励。
(二)具体解释困境
1.子女抚养问题。分居并不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在夫妻分居期间,子女一般与其中一方共同生活,由该方直接抚养,并由其直接承担子女日常开销。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一般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一方以自己的收入抚养子女可以视为另一方的共同抚养。此时,非直接抚养方就可利用夫妻共同财产制逃避其抚养义务。为落实父母双方抚养义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三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拒不履行抚养子女义务,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尽管该条并非直接指向分居期间的子女抚养,但分居期间也属本条规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居期间父母双方形成直接抚养、非直接抚养两种抚养形态,子女可基于该条请求非直接抚养方在分居期间本应支付但尚未支付的抚养费。(5)(2021)陕0728民初956号;(2021)湘0381民初161号。本条尽管保障了被抚养人的抚养费请求权,但仍未解决前文所述的理论困境:一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即便是分居期间的个人收入)承担抚养费,可视为另一方的共同抚养。既然子女所享受的被抚养利益来源于直接抚养方与非直接抚养方的共同抚养,又怎可认为非直接抚养方没有尽到其抚养义务呢?
此外,司法实践中子女抚养费问题一般由父母协商解决。父母双方关于抚养费的相关约定应当理解为共同抚养义务人之间关于该义务的内部分配。[8]因此,分居语境下,本条看似规定的被抚养人的抚养费请求权,实则以被抚养人为媒介,允许直接抚养人向非直接抚养人针对其已支出的抚养费用请求补偿。诚然,上述处理最终使直接抚养方得到救济,但直接抚养人却非抚养费纠纷的适格原告。实际救济对象与法定权利主体设置的分离会致使程序成本增加。相反,一旦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一方以其个人收入所支出的抚养费就不被认定为共同抚养。一方面,被抚养人要求非直接抚养方支付抚养费就不会出现前文所述的理论困境;另一方面,针对已经支付完毕的抚养费,直接抚养人也可基于类似无因管理的原理而取得直接的请求权。
2.无权处分问题。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处分共有不动产或动产的,应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在法定夫妻财产制下,共同共有财产构成夫妻财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共同生活中,时常出现一方单独处分共有财产的情况。一方面,如果当事人处分财产时不征得共同共有人同意,会导致无权处分风险,影响交易安全;另一方面,如果要求当事人就日常生活中的各个处分行为均征求共同共有人则会过于繁琐。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家事代理权”可以解决这一矛盾。
我国现行法未针对分居期间建立特别的法定财产制,若无特别约定,分居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财产也属于共有财产。这就导致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处分其分居期间取得的财产也属无权处分。就分居期间的家事代理权,相关域外立法例可供参考。《德国民法典》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在结束同居关系而自愿分居时,家事代理也随之停止;日本法规定,依据判例,在分居的情况下,如果妻子为了维持生活,处分了丈夫的财产或借了必需的款项,也不在日常家事的需要范围;英国法也存在类似规定,在夫妻没有同居关系的阶段,妻子会丧失表意代理权。同样,我国家事代理权条款中的表述是“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对该条进行反面解释,即夫妻一方不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当然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因此,虽然我国没有明文规定分居期间家事代理权的变化,但由于分居期间不存在正常的家庭生活,家事代理权条款也就丧失了发挥空间。
在夫妻共同财产制下,一旦丧失家事代理权,夫妻双方即便处分其分居后取得的财产也需事事征得其法律上配偶的同意,否则将产生无权处分的风险。问题就在于目前没有建立分居期间的特别财产制,导致婚姻当事人一面针对其在分居期间取得的财产无法获得完整的所有权。
四、非常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可能性
林秀雄教授认为,世界各国之夫妻财产制有共通的倾向。以分别财产制为原则之国家,于夫妻离婚之际,将本来分别所有,分别管理之财产,适用共有之原理;而以共同所有制为原则之国家,将共同财产范围,尽量限定于职业所得,而扩大夫妻独自之财产。因此,今日各国之夫妻财产制,严格言之,既非单纯的分别财产制,亦非单纯的共同财产制。[9]因此,我国在立法上设计分居期间的非常态夫妻财产制时,可以参考同为采取“共同所有制”原则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设计。
(一)比较法经验
依据非常法定财产制是否需要当事人请求或法院宣告而实施,各国家、地区立法例可以分为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与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模式。而针对分居这一特殊的婚姻关系存续状态下如何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各国存在不同立法例。
1.意大利。意大利法中分居期间的非常法定财产制规定具有以下特点:(1)分居期间当然适用分别财产制;(2)分居须经法院宣告;(3)分居不必然进行共同财产分割;(4)分居状态结束无需宣告。《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夫妻被宣告分居的情况下,财产共同状态将被解除。这是因为由于在夫妻分居的情形下,法定共同财产制的实施已不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再适用普通的夫妻财产制,即使当事人并无其他约定,也转而适用分别财产制。[10]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分居的法条表述为“被宣告分居”。由此可见,尽管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实施无需法院宣告,但作为其前置要求的“分居”仍需法院宣告方才成立。
根据意大利民法,分居分为合意分居与裁判分居。无论是裁判分居还是合意分居,都需要司法力量的介入,意大利法律基本上不承认未经过法官裁判的事实上的分居的效力。在实行法定共同制的情况下,分居不必然导致共同财产的分割,但是分居期间应当实行分别财产制,家庭成员的扶养费用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和法官裁判决定。分居的终止可以不经法官的介入,用与分居状态明显不符的行动,比如用和解来表明。[11]
2.法国。法国民法针对分居期间的非常法定财产制规定具有以下特点:(1)分居期间当然适用分别财产制;(2)分居须经法院宣告;(3)分居时须进行共同财产分割;(4)分居状态结束须经相关机构确认方产生对抗效力。《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分居即引起分别财产。夫妻分居时得对分居开始前的夫妻财产进行清算分割,夫妻各自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于分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夫妻分居后自愿恢复共同生活的,财产仍然分开,但若夫妻订立其它财产规则的除外。
法国采用裁判分居制,规定夫妻分居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经由法院审查并宣告分居,因此,法律对夫妻一方提起分居的法定情形作了具体规定,夫妻一方向法院提出分居请求,得按与离婚相同情形及条件提出。据此,夫妻一方提出分居的法定情形应与离婚同。在法国,离婚包括两愿离婚、接受中断婚姻关系之原则、夫妻关系变坏无可挽回以及因过错等四种情形。[12]当夫妻分居终止,恢复共同生活,婚姻关系得以维持时,为取得对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应经公证文书确认或经向户籍官员提出的声明确认,并在结婚证书与夫妻双方的出生证书备注栏内作出记载。[13]
3.德国。德国法中分居期间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具有以下特点:(1)分居期间适用分别财产制须经法院判决;(2)分居毋须法院宣告;(3)分居时不进行共同财产分割;(4)分居状态结束毋须宣告。德国法中,分居对夫妻财产关系的效力,包括对分居期间的扶养费、家庭生活用品的分配、住房的使用、财产的增值归属,但不涉及夫妻财产制的变化问题。夫妻分居期间如果没有特别规定或者约定,婚姻财产的增值仍属于双方的共同财产。[14]在分居期间未达三年的不解除原夫妻财产制,如果无特别规定或者约定,婚姻财产的增值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必须达到分居满三年的才可提起诉讼,要求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在判决生效时始实行分别财产制,从而中止共同财产关系。[15]
按照德国法的规定,分居由当事人双方或一方依其意愿在事实上实行,无须申请法院判决宣告。德国法界定的分居是指夫妻双方之间家庭的共同生活已不存在(客观要件),并且可看出一方因拒绝过婚姻的共同生活而不愿恢复家庭的共同生活的(主观要件),夫妻双方即为分居。即使夫妻双方在婚姻住宅内分居,家庭的共同生活也不复存在。即只要夫妻双方之间事实上不存在家庭的共同生活,不论双方是分开住所居住,还是在同一住所内居住,均构成分居。允许因夫妻双方的同意或夫妻一方的意愿而实行事实分居,但却没有规定司法分居。关于分居的理由,该法仅概括性地规定分居的理由为:一方滥用其权利或者婚姻确已破裂的情形下,夫妻一方可以与其分居生活。[16]
综上可知,在上述三个大陆法系国家就分居期间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立法例中,显然,意大利与法国的立法思路属于一类:针对分居期间夫妻法定财产制的变化,均规定了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因此,两国针对分居的认定采取的是司法分居主义,仅承认经法院判决的分居,不认可事实状态的分居。一方面,德国立法例规定的是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分居期间并不当然地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但另一方面,德国针对分居的认定采取的是事实分居主义,即承认事实上的分居状态,而毋须经法院判决认定。
(二)我国现行法中的非常法定财产制
非常法定财产制具有以下特点:(1)适用该财产制需要特定的法定事由。在未出现或未发生这些事由之前,夫妻按照法定财产制或夫妻双方约定的财产制执行;(2)可通过当然适用或申请适用启动非常夫妻财产制;(3)非常夫妻财产制的适用结果具有唯一性,即分别财产制。[17]
我国非常法定财产制的雏形初见于《物权法》第九十九条,后于《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具体化。在征求意见稿中,出现了针对“因感情不和分居”的特殊财产处理。但值得注意的是,法条中并未将“因感情不和分居”作为启动财产分割申请的单独条件,只用于确定“重大事由”的发生时间。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一时间限制没有存在的必要,“重大事由”并非仅出现在上述期间内。[18]最终,《婚姻法解释(三)》成稿中,并未出现“因感情不和分居”的表述,而是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夫妻关系存续期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也沿袭了上述规定。但仍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婚内请求分割财产的法定情况要求过于狭窄,夫妻分居并不能单独引起财产分割请求;另一方面,尽管条文规定可于婚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未规定财产分割后夫妻采用何种财产制形式。显然,我国现行法中尚未建立完整的非常法定财产制。
五、非常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方案
(一)分居期间的确定
我国立法尚未建立宣告分居制度,但承认事实上的分居状态,并将其作为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依据。由此可见,目前针对分居成立问题,我国与德国立法思路较为一致,认可事实上的分居状态,而毋须经法院宣告。
我国现行法上的分居须满足三个要件:“因感情不和”“分别居住”及“满两年”。其中“因感情不和”与“分别居住”均与分居期间起算点的确定密切相关。根据文义解释,“分别居住”应当“因感情不和”而起,因此,在时间先后上应当感情不和发生在前,分别居住发生在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如此解释会排除嗣后感情不和的情况。笔者认为,从判断夫妻感情破裂、婚姻关系非常态化的角度,无需排除此类情形。
为了解法条适用的实态,笔者以“分居”“二年”“两年”“离婚”为搜索关键字,“法院级别—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程序—一审”“文书类型—判决书”“审结日期—2020.01.01至2021.10.13”为筛选条件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案例,并从中筛选出法院基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第四项判决离婚的案例,对案例中的分居期间计算时点及分别居住事由进行统计,结果如表一所示。

表一 分居期间起算时点及分别居住事由
根据表中数据,已统计案例中与法条表述“因感情不和分别居住”严格符合的案例,即分居期间起算点为“一方离开共同住所之日”且分别居住事由为“双方感情不和”占比59.1%。但也存在部分案例中的分别居住事由并非“双方感情不和”(被告离家、一方被羁押、一方旅居国外)。针对这部分案例,法官将“双方断绝联系之日”作为分居期间的起算时点。由此可见,法官认定相对灵活,不要求“分别居住”事实由“感情不和”引起。
另外,针对“感情不和”要件,陈某与张某离婚纠纷案中的法官解析指出,“如果被告已经离开原居住地两年,达到了分居两年以上的要求,那么则需要审查其是否系因‘感情不和’导致的分居满两年。这里的‘感情不和’可以包含两种情况:一是被告因与原告感情不和而离开原居住地,进而双方分居两年以上;二是虽然被告不是与原告感情不和而离开原居住地,但离开原居住地后不与原告联系已经两年以上,这虽并非直接的感情不和,但被告既然已经两年以上不与原告联系,亦说明原被告之间的感情已经非常淡漠,乃至达到了夫妻感情破裂的程度,故此种情形也符合了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条件”。[19]由此可见,实务中认定“感情不和”并不严格要求夫妻双方之间存在积极冲突,消极淡漠的关系、断绝联系也足以认定夫妻“感情不和”。
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分居期间毋须考虑“分别居住”要件与“感情不和”(包括消极的断绝联系)要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某时点一旦同时符合以上二者,即可作为分居期间的起算时点。
(二)分居期间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具体设计
为确保夫妻财产制的稳定性与交易安全,前文所述各国立法例中均没有出现事实分居原则与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组合。在分居的成立与分居期间非常法定财产制的适用两者之间,司法机关至少针对其中之一具有判断权。针对分居的成立问题,既然我国现行法采用事实分居主义,就应将司法判断权后置,即采用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
1.可申请财产分割宣告期间要件。德国法要求夫妻之间至少分居三年,一方方可向法院申请宣告适用分别财产制。在事实分居主义国家,由于分居毋须法院宣告,因此分居状态的形成基本由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决定,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有必要设定一定的持续期间作为当事人提起非常法定财产制宣告请求的要件,从而保证双方当事人在提起宣告请求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分居关系。而德国法对此持续期间的要求为三年,并且夫妻双方为了和解而短暂地共同生活,并不构成对推定婚姻破裂的分居期间的中断或停止。[20]
参考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的规定,分居满两年即可被视为感情破裂的依据,法院可据此判决离婚。由此可见,我国法上分居期间满两年即可认为夫妻间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分居关系。而针对分居期间是否可由于短暂共同生活而中断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依法律规范之目的,一定时期的持续分居是推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然而夫妻双方因客观原因或甚至为和解所为之短暂的共同生活,并不能使夫妻分居的期限中断,因为它不能掩盖夫妻双方感情已经破裂的事实。[21]
综上所述,我国法上允许当事人请求进行非常法定财产制宣告的期间应为两年,并且该两年期间不因短暂共同居住而中断。应从符合分居标准(感情不和与分别居住)之日起开始计算,直到申请宣告之日满两年,当事人方可提起。
2.分居期间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在夫妻分居期间,虽已不存在共同生活关系,但仍需满足一定期间要件,方可申请宣告非常法定财产制。因此,以非常法定财产制宣告为界限可将整个分居期间分为两段。
针对宣告前双方当事人取得的财产,假如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仍会出现前文所述的由于家事代理权丧失而导致的无权处分问题。然而,德国法规定的一般法定财产制不会出现该问题。德国法中规定的法定夫妻财产制为财产增加额共同制,其原则是配偶双方各自的财产不成为共同财产,而是继续归各自所有。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仍是取得财产一方的财产。但是,如果婚姻因离婚等原因而解除,就将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增加额加以均衡。[22]因此,在分居后非常法定财产制宣告前,夫妻双方仍适用财产增加额共同制。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为共同财产制的背景下,分居后非常法定财产制宣告前的期间内财产增加额共同制有其适用的空间。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夫妻财产关系的稳定性,暂不分割财产有利于夫妻关系的恢复;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在处置分居后非常法定财产制宣告前取得的财产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不存在无权处分的风险。而在非常法定财产制宣告后,夫妻间即形成分别财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