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献·数字人文:我的学术研究三期
王 贺

承乏《传记文学》“学人自传”栏目邀任作者,不胜荣幸,但老实说,我一直心怀忐忑,未有勇气动笔。正如该栏目第2 期揭载的房伟教授的自传所云:“与前辈相比,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也未到总结工作的年纪,只能将从事学术工作的经历心得写出一些,供大家批评指正。”郜元宝教授撰述《在失败中自觉——马上自传一至七》(《南方文坛》2004年第3 期)时,亦有如此按语:“在一次小型聚会上,谈起最希望读怎样的文章,我说是当代人思想学术的自传,像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或胡适《四十自述》之类。有朋友问我现在谁还有资格写那样的文章,我说可以写的人应该不少吧,要什么资格?……现在,抱住一个大题目乱啃一气的文章太多,要么口吐预言,作杞人之忧;要么手握真理,勒令天下人屏息侧耳倾听,还这派那派闹个不休,真肯谈谈自己的文章却越来越少了。无边的热闹中透着彻骨的寂寞。”如此看来,似乎也不必畏手畏脚,以自己缺乏资格而却之,或可斗胆一试,虽然怎么写、写什么,也绝难达到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或胡适《四十自述》那样的高度。
如入宝山——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因缘
受过完整的学术训练的近代学人,回顾其学术生涯(如吕思勉、钱穆、陈垣等自学成才者,当属例外),泰半自入读大学时代开始,然而到了今天,我们似乎很难再将自己的学术起点追溯到大学一年级甚至更早的时候。不过,我仍感激那段蹒跚学步、胡乱读书、狼吞虎咽、信马由缰的烂漫时光,特别是老师们对我的包容和宽容无似,让我在其书斋、研究室里可以就近请益、畅所欲言的愉快情形,真是终生难忘。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在《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的“后记”里,写下了这段话:
我还要向从高中阶段开始,指导我阅读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近人著作的王芝盛先生,牺牲自己的宝贵休息时间、无偿地为我辅导功课的张军喜先生,以及父执陈旺元先生、杨宗贤先生,大学时代的章琦、王百玲、刘养卉、王文棣、刘朝霞诸位先生,硕士论文指导教授邵宁宁先生、师母王晶波先生,博士论文指导教授陈子善先生、师母王毅华先生,致以无限谢忱。感谢各位师长,没有因为我的平凡、无知、虚荣和青少年时代的自命不凡、孟浪之言,而视我为顽劣不堪、不可救药之徒,仍然无私地接纳了我、包容着我,时常予以鼓励、扶持,给我谆谆教诲,让我知道,全世界所有的秘密,都在书里;能有机会读书、写书,乃是此生最幸福的事。
大学时期,我也有机会多次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学习。先后聆听过多位先生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文艺理论方面的课程,也认识了许多小伙伴,有北大本校的,有校外的;有本科生,也有硕士、博士,大家一心向学,彼此之间真诚、坦率的交流很多,对我也很照顾,令人十分怀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后来很多人都没了联系方式,渐次相忘于江湖,只有目前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谢俊兄,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如果说之前的学习都是学徒期必要的训练,那么,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也许勉强可以算作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吧。从大学毕业、2008年公开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弹指一挥间,也已经有14年了。那篇论文和同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都是我本科毕业论文中的一部分。写成之后,有老师提出来,由其安排发表,当下大喜过望。而今看来,和一般的本科毕业论文一样,论题太大,论述也颇多空泛之词,真是幼稚到骇人而不自知。不过,这一发表行为本身,对我确实也是一种鼓励,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心投入接下来的硕士阶段的学习。
硕士三年,学习时间虽然很短,要上课、修学分,但更多的时间,我的确是在学校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度过的。在邵宁宁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阅读近现代西北报刊上,试图作出一点新的研究。等硕士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在《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现代中文学刊》《诗探索》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献整理成果和以此为据所作的文学史研究论文。也为钱理群先生任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撰写了西北现代文学史这一部分的内容。至今,关于西北现代文学史方面的专题研究论文,已发表十余篇。有朋友曾多次建议我将此结集出版,列为其主编的丛书之一种,但我一直都提不起劲,因为在我的理想中,关于近现代西北的古典写作、校园文学,乃至学术思想的研究,都很重要,而目前这方面基础资料的搜集,还不足以支撑相对宏观的研究,而在没有完成这几部分的研究之前,简单地出版一部论文集,似乎意义不大。

本文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合影。前排从左至右:陈子善、张为刚、陈建华、本文作者、殷国明;后排从左至右:文贵良、郜元宝、罗岗
实际上,对我而言,展开西北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不仅是渴望填补这一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形成的“空白”,讲述来自边地的“无声之声”,扭转将延安及邻近解放区的文学研究等同于西北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做法,更多的是想讨论和分析这样一些问题:从文学和文学史的角度看,西北的“现代”是如何发生的?是北京、上海等地传入的结果吗?“在地”的士人、新文化人、普通民众分别作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在“冲击—回应”“影响—被影响”“接受—被接受”等既有的分析框架之外,我们该如何发现、分析、描述“在地”的“现代”历程?又该如何从清中后期以来西北诸地内部的文学、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中,清理出一条相对较为清晰但又足够丰富、辩证的线索,既可观照、叙述西北的“现代”及“文学”之史,也可用于反思作为总体史的近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仅依靠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运用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区域史和区域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等可能也还不够,尚需参考人类学、社会学、全球史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因为这些学术思想上的困难,我在作硕士论文的时候,并未选择这方面的题目,而是研究了丁玲出版的第一本书《在黑暗中》。这篇论文答辩时,老师们评价很高,但从今天的角度看,仍然是失败的,可以说是雄心有余而具体论述不够坚实、细腻的例子,为此,后来我改写并发表了其中的部分章节,且主要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重新解读了其中的《暑假中》等重要文本,试图修正、挑战学界关于丁玲早期写作乃为“同性恋”书写的定见。当然,有的研究者并不同意拙见,认为我的研究仍然暴露了“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已作专文进行回应。
另一方面,未选择西北文学史研究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也是由于那个时期,学术界对这一选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还远不如今天,几乎使人望而却步。很难想象,在那时候研究一个不太知名的“在地”的西北现代作家、作品、社团、刊物等,会有发表的可能。也因此,我这方面的早期研究,是以曹禺、于赓虞、陈敬容、牛汉等重要作家与西北文学之关系的重新研究作为开始,直到后来才有学力、也敢鼓起勇气,触碰另外一些学界不太熟悉的研究对象、议题,如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西北的“通俗小说热”等典型文学现象,尝试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已逐渐增多。虽然研究力量仍以现居西北诸地的学者尤其青年一代研究者为主,一些研究恰如前引郜元宝教授的评论,似是“抱住一个大题目乱啃一气”,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扎实、认真的关于西北报刊的专门研究,及对一些“在地”的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颇具参考价值。西北现代文学史研究终于不再是一片“不毛之地”了。
术业有专攻——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及其他
话说回来,在学习和研究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我也逐渐意识到了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除了前辈学人的著述给予我无尽启发,解志熙先生和陈子善先生先后给予了我许多指导。在一篇访谈中,我也曾经这样回答提问者:
我接触“文献学”比较晚,是从大学四年级才开始的,也不很系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从那以后,到硕士一年级、二年级,解志熙老师先后给我们开过《张爱玲研究》《沈从文研究》《1937—1949年文学史》等课程,每门课都是以他刚刚撰写完成的专题研究论文、著作为基础开讲,他是很自觉地用“文献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史)。我从那时候学习“文献学”的东西,一开始纯粹就是好奇,并没有所谓的“冷门学科”或边缘学科的意识,然后比较系统地阅读了近代西北报刊,整理了一些作家、学者的集外文,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专题研究,还初步梳理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史。但更深入地学习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是在跟陈子善老师读博以后。除了陈老师给我们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专书导读》等课程,他的文章、著作,包括私下里的谈话,时常都给我很大的启发。
不太清楚其他同辈学者是如何学习和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但对于我而言,大致上即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首先是在两位先生的帮助下,细读既有的现代文学文献论著,并对其研究历史、经验、方法等问题,不断地作出总结和检讨;其次,为了弄清楚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究竟和现代文学研究、历史研究有何关系,其特殊性何在,应该如何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等问题,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的学问领域,拥有自己专门的研究框架、分析工具和独立的方法论,乃将思想和研究的触角又伸入古文献学和西方文献学(语文学)、东洋文献学等相关学问领域。
在前一方面,我先后发表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等十余篇长短不一的专论,面世之后,也引起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讨论,但后一方面的工作尤其吃重。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古文献学和其他相邻的学问领域的概念、分析工具,对于研究和整理现代文学文献,是一笔极为丰富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体会,但与此同时,如果将这些概念和分析工具,全部不假思索地用于近现代文献、当代文献的研究,似乎又有不足。
以“辑佚”而言,古今文献学的研究差异就非常明显。古人多针对一佚书而展开搜求其佚文、重订其编次、复原其文本等方面的工作。但对于现代文献研究者而言,因为印刷和出版技术的革新、学术观念的变化、文本编辑和呈现方式的差异等,许多时候,我们只是针对一个作家、学者的文集、全集而进行补遗,我们的工作对象并非真正的佚书、佚文,顶多是集外文。而且,古人是针对子书和经学、史学的重要著作进行辑佚,但我们所置身的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却缺乏足够的“历史化”和“经典化”,对于哪些作家是重要作家、哪些作品是重要作品,值得辑佚(包括进行校释、考辨等),都还缺乏足够的共识。这样一来,不少这方面的文献整理成果,就变成了“捡到篮里都是菜”,对这些新作品、新文献的研究,也仅仅停留于相对比较初步的阶段,即整理、校勘、注释,钩沉历史背景,作一报道或缕述而已。
在发掘新文献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虽然注意多方开拓其源,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疏忽“常见书”(含常见报刊等)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清代辑佚学的覆辙,而其精细程度、整体格局、学术贡献等又远不能与此相较。为此,我曾先后写就《“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常见书”与现代作家、学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记〉为讨论对象》《“常见书”中的于赓虞诗歌研究资料》三篇文章,希望提起学界对此一问题足够的注意。
至于整理这些资料并予重刊之时,出现的问题就更多了。数种专门发表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刊物所载新发现、整理的文献资料,就其报道的资料本身而言,当然有一定之价值,但就其整理工作本身的质量而言,真让人一言难尽。目力所及,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迄今为止仍只有《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于赓虞诗文辑存》、《冯至作品新编》、《废名集》、《穆旦诗编年汇校》等有数几种。由于“文献学转向”的发生,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并无这方面的准备、积累和训练,便从事某一“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工作,使人闻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喜者,在源源不断的现代文献,由是可以为研究者重新广泛利用;所忧者,在其整理体例、章法、规范、质量耳。
更关键的是,除了这些偏重实践的探讨,理论方面的思考也未有尽期。仍以“辑佚”为例,自古文献学学术传统沿用至今的“佚书”这一概念,也有一定的局限,不足以概括近现代文献存佚的实际样貌。为此,我也以一些具体的个案讨论过近现代“佚书非佚”等现象,以期为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探索,奠定一定的基础。
不过,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范围实在太广,可做的工作也极其之多,个人目前的研究实在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在其所辖版本、目录、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及文献编纂、庋藏等诸领域,尽管我多多少少都作过一些专门研究,也提出过一些自以为新鲜、重要的研究议题,但与其实际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相比,与其庞大的总体样貌和开阔的研究格局相比,都还远远不够,有待进一步深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和许多前辈学人的学术目标一样,我们共同的理想,乃是使现代文学文献研究不再是现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附庸,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领域,使之拥有其应有的学术尊严。尤其是念及诸如编纂一部年谱,早已是胡适、姚名达、内藤湖南等中外学人著述之林中不可或缺的一片风景;而探讨某一版本的《荷马史诗》的一个残章,更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再看我们的现代文学与文献研究领域,在各种评价方面,在硕博士生等未来学者的培养计划、论文写作及评审规程等方面,是否能够允许出现这样的作品,何时才能形成这样广泛的共识,委实费人思量。我也常想,为了使学术研究葆有现实关怀精神(我们对学术如何济世的理解,和近代学人相比,而今似乎狭窄到只认“议政”一途),为了永不消逝的“当代性”的追求,我们难道要永远拒绝承认现代文学已经正在且必将“经典化”“历史化”这一发展趋势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将文献研究作为自己的起点,或一生情有所钟之学问领域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文献研究也教会了我如何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等视野之外解读、利用文献,从更加多元的角度理解和研究现代文学史。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以穆时英文学为中心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主义”的重新研究(这也构成了此后至今我的另一研究重心),其中对穆氏生平著述的考察、新文献的发掘与整理、重要文本复原问题的讨论,等等,也都运用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和方法。
在博士后研究阶段,因工作需要,我又开始转入整理和研究当代文献。这方面的专论如《历史与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室(1949—2019)》《当代资料室的日常运作与学术生产(1949—1990):书籍史的视角》等,是从制度史、书籍史角度对当代文献资料庋藏、流通、再生产等问题的研究。其间也实际参与了一项大规模当代文献数据库的开发计划,为我的“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操、实作的机会。另外还有一些当代文献整理和专门研究的成果,因头绪甚多、事冗时仄、迄今尚未定稿,只能待其定稿之后再请学界先进、同仁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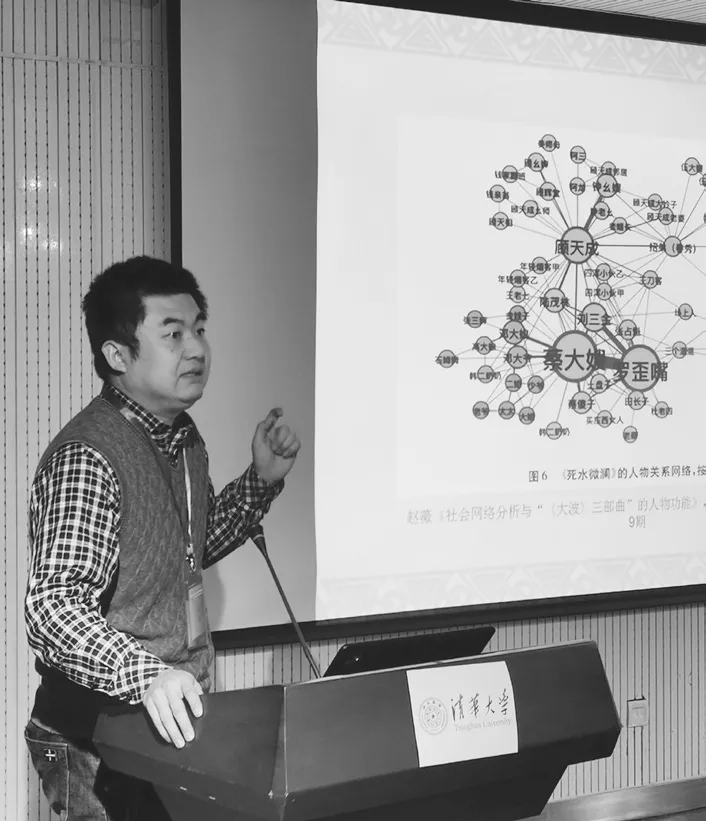
本文作者在清华大学作学术报告
大道多歧——“数字人文”研究试探
大概在2015年前后,因“数字人文”研究在中文学术界逐渐引起关注,受此思潮影响,我也对这一新兴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进行学习和思考。此后相继发表了《从“研究资料集”到“专题数据库”》《“数字人文”如何与现代文学研究结合》《“数字人文”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追寻“数字鲁迅”:文本、机器与机器人——再思现代文学“数字化”及其相关问题》等系列论文,并完成了《数字时代的目录之学》(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21年版)、《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两部专书。
或是我的既有论述未能深刻阐明“数字人文”的内涵,或是由于个人的学术轨迹是由文献学进入“数字人文”所致,许多师长、朋友因此就认定“数字人文”是文献史料“数字化”或“数据库学术”的代名词。但必须再一次声明,这其实是误解:首先,进入“数字人文”,未必得通过文献学。其他许多人文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也都是从自己所在的学问领域出发,逐步进入这一跨学科的领域;其次,作为专门学问领域的“数字人文”,虽然也有质化研究(请恕我借用这一社会科学术语),但更重视量化研究、分析,如果仅仅是一般性地利用互联网和数据库中的文献资料,作文献研究或其他方面的研究(如文学史研究等),而缺乏一定的数据挖掘、分析、可视化等,似乎也很难称得上是“数字人文”研究。
我的这些论述,因为是立足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首次探讨“数字人文”研究取向如何展开等议题,在其发表、出版之后,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也同时引起了一定的争议。这其中既有较具学理性的批评(尽管仍不乏误解,如将“数字人文”等同于“数据库学术”);也有学者认为我给现代文学研究开了一个很坏的头,是明示读者从此以后不必再细读、研读纸书,是放弃“人文性”、径直遁入“元宇宙”的不智之举。不过,我深信,只要是细致、完整地阅读过我的上述论著的读者,应该不难发现:在“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的关系上,我主张两者为互补关系,而非前者取代后者;在“数字人文”可能提供的新视野、新方法、新思路之外,我同样也讨论了其可能的局限性、目前已显露出来的若干不足及今后亟须处理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数字学术”所需的、必要的学术训练之外,我曾多次强调传统人文学术研究技艺如基于纸质文献的阅读、写作和思考的重要性,是从事人文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训练,指出我们不能为了查资料而读书,而应该多读“常见书”、将其从头到尾全部读完,人文研究尤为需要耐心、细致、细腻的批评与诠释;在“数字人文”如何积极参与当代社会、文化生产,帮助我们想象更为良善、美好的人类文明等方面,我也深以鲁迅所言为然,不敢奉“数据主义”(Dataism)为圭臬,仍愿意做一个道地的人文主义者,因为“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虽然理念、目的不能代替方法、手段,更不能保证结果,但作为融合了数据科学、统计学和人文学术等多个领域的“数字人文”,力图为数字时代的人文学术研究蹚出一条新路这一理念,是不必怀疑的。至于其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因其还在方兴未艾阶段,现在还无法作出预测,但不尝试一下,我们怎能知道其是否有效呢?对我而言,要学习的数字工具、方法还有很多,而更难的是,怎么将这些工具、方法,恰如其分地运用于现代文学研究当中,作出新的观察和分析,而非是花拳绣腿的“概念学术”,或是为创新而创新的“贴牌学术”。

王贺著、王静编:《数字时代的目录之学》
在我的提议下,在学校、学院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下,我目前所服务的大学也在2020年成立了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之初,我们也作了一些发展规划,如招聘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开发数字人文平台、增设数字人文学科等,但放眼海内外,既擅编程、又能专精于某一人文学术领域的合适的研究者,实在凤毛麟角,因此其进展也可以想见。
这一切,都让我想到现代作家、学人台静农的著名集句:“人生实难,大道多歧。”我也时常以此提醒自己,虽然一腔孤勇、属意探索“数字人文”,但也要避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甚或完全地放弃传统人文研究。也正如我在《数字时代的目录之学》等论著中所言,新学术的滥觞固然可喜,但旧学术的发皇,也同样是今时今日人文学者的使命所在。恐怕不能我们每一代学者,都以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尚未完全完成,我们都是“过客”“中间物”,所为只是“过渡时期的学术”等作为自己的“正当”理由。
我个人也由衷地期待未来学术环境能够更好一些,学术工作能够更加纯粹一些,压在我们身上的事务性工作能够更少一些,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可以安心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专心地著书立说。不敢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至少不必汲汲于治生、发表、项目、评奖和“帽子”,等等,以作出世界范围内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第一流的研究。
也许,如此说法不免高自标置之嫌。但每逢深宵独处,徜徉于中外经典著述之林,耳闻目睹许多前辈学人的虚怀若谷、雅意殷殷,同辈学友的志趣相投、声应气求,未来学者的勤勉有加、训练有素,仍不由不对人文学术的远景憧憬不已,某虽鄙陋无似,敢不勉旃?
注释:
[1]南江涛编:《嘤其鸣矣:青年学者说文献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版,第8—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