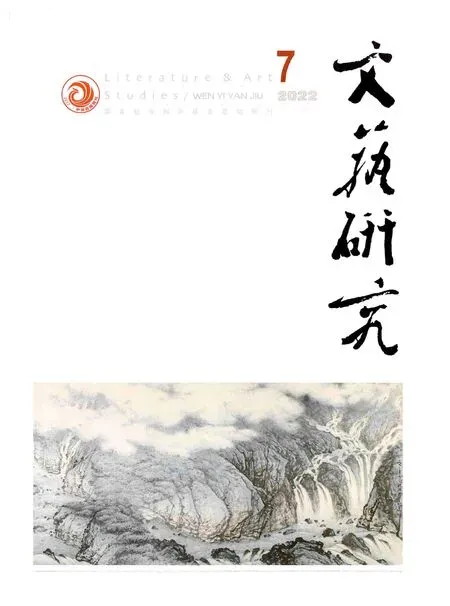以一人之思摄一时之思
——王国维《壬子三诗》稿本考论
彭玉平
王国维在壬子岁末曾将本年在日本京都所作三首长诗合编为《壬子三诗》一集,以记一时之思。此集为合罗振玉手写《颐和园词》石印本原稿与王国维手抄《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蜀道难》二诗而成,并未单独付刻。今检王国维致诸人信,皆未提及此集,而知悉此事的罗振玉在与他人信函或自撰《集蓼编》中也未明确提及,故知者寥寥。曾关注王国维《壬癸集》并笺释过《颐和园词》的黄永年,也直言“《壬子三诗》有无印本我虽不清楚”云云。
最早公开提及此集的应是赵万里。他在1927年所撰《王静安先生年谱》壬子年下记云:
二月,作《颐和园词》,罗先生见而激赏之,为手写付石印……而以夏秋间所作《送狩野博士游欧洲》及《蜀道难》二首附录于《颐和园词》后,署名“壬子三诗”。
赵万里曾任王国维助教,深受王国维信任。王国维殁后,其手稿由赵万里整理并陆续经手捐献给今国家图书馆,此《壬子三诗》即为其一,故赵万里能略知本末。不过,此后如储皖峰《王静安先生著述表》、姚名达《王静安先生年表》、神田喜一郎《观堂先生著作目录》、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等均未列此集。胡逢祥编《王国维著译年表》,于癸丑年下“文”首列《颐和园词后记》,并括注:“校补入《集林》二十。又名《壬子三诗序》,手稿藏国图。”所谓“校补入《集林》二十”乃就《颐和园词》等三诗而言,而《壬子三诗序》并未收入《观堂集林》,也未编入《王国维全集》第14卷“诗文”编,故此序至今尚为王国维集外之文。今检国家图书馆藏书目录,果然有《壬子三诗》稿本。王国维生前编定的诗歌专集,除了此前的《静安诗稿》和此后的《壬癸集》,便是这本《壬子三诗》了。而且,《壬子三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次年成编的《壬癸集》之雏形。王国维晚年回顾平生所作诗歌,曾说:“余所作,惟《颐和园词》《蜀道难》及《隆裕皇太后挽歌辞》,差可自喜。”在王国维一生写作的众多诗歌中,其拈以自喜的不过三首,两首即收在这个小集中。同时,作为王国维东渡日本后编的第一部诗集,此集带有易代之初特殊的时代和情感特点,故其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一、《壬子三诗》的创作与编定
《壬子三诗》,顾名思义,就是壬子年作的三首诗之合集。从创作时间而言,《颐和园词》最早完成,作于1912年阴历二月中旬;《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脱稿于八月十六日(9月26日),次日王国维致信铃木虎雄说,“狩野先生欧洲之行,本拟作五排送之,得数韵后颇觉不工,故改作七古,昨已脱稿”,成稿时间很明确;《蜀道难》成诗最晚,完成于该年11月上旬。1912年11月9日,王国维将誊写版《蜀道难》寄给缪荃孙,附信云:“近日作《蜀道难》一首,咏匋斋制府事……谨以誊写板一份呈览,字画模糊,恐不宜老眼,然字句太多,无法录呈也。”两日后又将同一誊写版寄铃木虎雄。誊写版制作简单,费时亦少,因知《蜀道难》一诗必撰成于本月上旬。可见,三诗的完成时间在1912年4—11月。
三首长诗写就,王国维即拟编《壬子三诗》小集。三诗以创作时间为序,但非并列关系,而是以《颐和园词》为主,余二诗为“附录”,故《颐和园词后记》也可视为《壬子三诗序》(胡逢祥《王国维著译年表》)。此后记因未为诸种王国维集收录,故知者寥寥,兹据国家图书馆藏《颐和园词》手迹经折装本录文如下:
壬子二月,侨居日本京都,旅食多暇,因成此词。罗叔言先生见而激赏之,因为手写付诸石印,此其原本也。其后字句略有改易,如“方治楼船凿汉池”,改“因治”;“后宫并乏家人子”,“家人”改“才人”;“东南诸将翊王家”,“翊”改“奉”;“岂谓先朝营暑殿”,“暑”改“楚”。凡易四字,并将夏秋后所作《送狩野博士游欧洲》《蜀道难》附录于后。是岁所作长歌共三首,因名之曰“壬子三诗”云。岁除前十日,国维识于鸭川东畔之寓居。
“壬子三诗”作为集名即来源于此。“岁除前十日”指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公历1913年1月26日,距三诗全部完稿不过两个半月。按序中所述,王国维之所以将此三诗合为一编,是因为壬子年所作长歌仅此三首。
这部名为“壬子三诗”的诗集,卷首并未署集名,只是题篆文“颐和园词”四字,后记也书于该诗之后、《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之前。按一般著述常规,应该或书于《颐和园词》之前,以作为诗集之总序;或书于《蜀道难》之后,以作为诗集之后记。可见,王国维编集颇为随意,不过,他以《颐和园词》为正编,以《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蜀道难》为附编,也体现了对三诗轻重的考量。
二、王国维《颐和园词》与铃木虎雄《哀清赋》
细致寻绎《壬子三诗》之编订,“是岁所作长歌共三首”只是王国维编集之一因,且非主因。此前他编订《静安诗稿》,乃合长、短诗为一编,《人间词》甲乙稿和《壬癸集》《履霜词》也都未究心于篇幅长短,何以《壬子三诗》独将三首长歌合为一集,而短诗不与?这其中应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笔者发现,此三首长诗虽各有主题,但都与哀悼清亡有关。王国维对清亡之事的述论,大致包括历史事实的陈述、背后原因的探讨和清亡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1912年5月9日,王国维致信铃木虎雄云:
《颐和园词》……此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至于全国民之运命,与其所以致病之由,及其所得之果,尚有更可悲于此者,拟为《东征赋》以发之,然手腕尚未成熟,姑俟异日。
陈述清亡史实方面,一篇《颐和园词》已见梗概,而后两方面的内容,原拟以《东征赋》出之。1912年5月31日,王国维再次致信铃木虎雄云:
前从《日本及日本人》中见大著《哀清赋》,仆本拟作《东征赋》,因之搁笔。
王国维原拟用《颐和园词》与《东征赋》完整表述自己对晚清灭亡的过程、何以灭亡的原因以及清亡对国家民众的影响之所思所想。《颐和园词》重在描述爱新觉罗一姓的末路,尚未及其余。他在读到铃木虎雄《哀清赋》后,觉得自己未及表达的方面铃木虎雄此赋已言之殆尽,于是搁笔。故欲了解王国维对清亡之事的整体之思,除了探究《颐和园词》的主题之外,尚需对读铃木虎雄《哀清赋》。
王国维在居东后不久就开始创作《颐和园词》,初衷即在于勾勒晚清从衰落到短暂中兴终至灭亡的历史过程。当时国内的基本情况是中华民国已经建立,孙中山虽短暂出任临时大总统,但权力很快就为清王朝原重臣袁世凯窃取。此诗以颐和园与清廷的关系为主要视角,缕述清朝走向衰落的过程。1860年,在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之际,“仓皇万乘向金微”,咸丰帝从圆明园逃向热河,随后圆明园被烧毁,结果“一去宫车不复归”,次年咸丰帝在热河惊惧而亡。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所谓“觉罗氏一姓末路”,这个末路的起点便从咸丰帝出逃热河开始。接着慈禧登场,开启所谓“同治中兴”。因为重用左宗棠、曾国藩等人,清王朝很快平定了外忧内乱,慈禧的“西宫才略”被众口称誉,营造和扩建颐和园的宏大工程也在这种中兴气象的掩盖下开始了。一个富丽到极致的颐和园,加上“是时朝野多丰豫”,使慈禧的享乐之心和政治威望臻于极致。然而不久,同治帝的遽然去世、甲午海战的失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等接踵而至。在庚子之变的再一次“仓皇”中,慈禧携光绪匆匆西走长安。而此前因为慈禧反对戊戌变法,朝廷内部矛盾愈趋尖锐。“两宫”返京不久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仓促登基。摄政王奕劻承光绪遗旨罢黜了袁世凯,袁因此在家乡赋闲近三年。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被清廷诏请,再度出山,从湖广总督做到内阁总理大臣,接着又代孙中山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王国维“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云云,即指此事,袁世凯事实上成为清廷末路的终结者。最后王国维以颐和园的物是人非结尾,感慨道,“应为兴亡一抚膺”,走笔至此,可谓沉痛苍凉之至!
此诗写了咸丰、同治、光绪三位帝王的去世和稚龄宣统的仓促登基与旋即被废,而贯穿其中的核心人物则为慈禧太后,颐和园作为与慈禧关联最紧密的处所而被擢拔为题目。慈禧先是协助咸丰帝处理公务,继而垂帘听政于同治、光绪二朝,临终扶持宣统帝登基,执政长达48年。王国维“五十年间天下母”云云,并非称誉其政治威望,只是勾勒一种客观历史罢了。慈禧事实上是“觉罗氏一姓末路”的全程主导者。诗中虽也涉及内忧外患,并曾一度把矛头指向当日顾命大臣、今日新朝之主袁世凯,但造就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也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此诗之所以名“颐和园词”,无非是想通过一园之兴衰冷热来展现清王朝虽偶有起伏但终归灭亡的过程。不过,正如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信中所述,他的重点是“略具”清王朝走向末路之“事”,是以线性叙事的方式勾勒晚清历史,至于面对这一历史的深度思考,则限于叙事之体未暇充分写入,这引发了王国维续写《东征赋》的冲动。
王国维未写就的事外之思,《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蜀道难》固有涉及,但不免夹杂在其他主题之中。而铃木虎雄的《哀清赋》,在王国维看来,则相当集中地展现了自己《颐和园词》的未尽之思。
铃木虎雄《哀清赋》向被冷落在中国和日本相关学术史研究的视野之外。此赋1912年春初刊于《日本及日本人》杂志。1928年11月,铃木虎雄《业间录》由日本京都的弘文堂书房出版,“附录”部分收有此赋并序。铃木虎雄回忆当时创作及与王国维交流的情形说:
我听到清帝退位(退位是壬子二月十二日)消息后作《哀清赋》(二月十八日起稿),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登载,王君读它以后寄给我的信如下……
铃木虎雄此赋与王国维《颐和园词》的创作大致同时。王国维读到铃木虎雄赋的时间在1912年四月十五日(5月31日)之前,此时罗振玉手书印本《颐和园词》也已告竣。王国维以慈禧与颐和园之关系为核心写清亡,于一园之兴废见一朝之兴亡,属于纪事体史诗。因为此诗是按照时间顺序连贯叙事的,故留给思考兴亡原因及社会影响的空间便极为有限,这才触发了王国维别作《东征赋》。可以说,王国维对《东征赋》寄寓的情感力度和思想深度,皆在《颐和园词》之上。但不过一个月的时间,王国维便因看到铃木虎雄之《哀清赋》中辍了写作计划,因为他觉得《哀清赋》已将自己所欲言者言之殆尽,故不烦另撰。而我们则可通过《哀清赋》一窥王国维之所思所想。
铃木虎雄在《哀清赋》前撰有小序,略述其创作宗旨,序云:
序曰:神圣登极,四十五年二月旬有二日,皇天降丧于有清,清帝辞位,举其冢宰袁某,假拟万机,从约朔南,改建政府,肇造国会,俾以殷荐民主于皇天。昔在帝尧,禅舜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荐贤让德在下。”三代之所同。然而国无君长者,自古来未之有也。惟夫满清,以异种临区夏,睿哲代兴,湛恩庞鸿,贤德在下,未轶唐虞。一旦变起荆湖,秣陵失守,四海响应。君为独夫,释乾纲而不张,委民政以自治,是非常之大变也。何则?内恃暗昧,外侮文明,宗臣倾夺,巨室窃权,先阀阅之得丧,而后亿兆之休戚也。是以边警频至,境无敢死之将;军饷将赋,廷有匿赀之臣。以十九省之大,三百岁之渥,而不能抗于锄耰棘矜木兵竿旗之众,楚人一呼,可怜运移,亦必至之势矣。呜呼!山岳崩颓,草木凄怆,举目有风景之异,孰其致之?社鼠城狐。嗟乎狐鼠,不独自祸,亦覃及于城社,世之为显臣者,可不鉴焉哉。作《哀清赋》。
参读1912年5月9日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可以推知,王国维拟写的《东征赋》,应想在《颐和园词》缕述清末历史的基础上探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清王朝何以走向末路,即“致病之由”;第二,清王朝覆没后的处境,即“所得之果”;第三,清王朝灭亡后对整个国民之影响,即“全国民之运命”。而铃木虎雄关于清亡的整体之思,也大致类此。下面拟结合《哀清赋》之序与正文,略作阐释。
先说何以要“哀清”。在铃木虎雄看来,有清三百年总体“未轶唐虞”,而其承上古禅让之法,辞位于民国,则不失君子之风,宗旨在“俾以殷荐民主于皇天”。如此“睿哲代兴,湛恩庞鸿”之圣明朝代,至“楚人一呼,可怜运移”,此其所以可哀者。
次说清王朝衰亡之原因。“内恃暗昧,外侮文明,宗臣倾夺,巨室窃权,先阀阅之得丧,而后亿兆之休戚也”,这是铃木虎雄在序中归纳的清亡原因,要在王朝的封闭自守以及宗臣巨室的窃权争利。在正文中,铃木虎雄说得更为详尽,他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大臣专权卑污,贪图名利,以至于民心涣散。“民涣散而乖离兮,臣淟涊以夸衔”“据显位以专权兮,跨沃土而置庄”,即针对这一现象而言。第二,皇族内部肆意争夺,形成内乱。“夫二邸之倾夺兮,驾八王之猖狂。迨柳樊之未成兮,酿祸乱于萧墙”,即指此。第三,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的兴起。“盗贼起于山东兮,君臣顾其仓皇。锄耰棘矜兮,首唱湖峡”“青丝白马兮,席卷建业”,即指此。一个朝廷,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是其衰亡不可挽回的根本原因。
再说清亡导致的结果。清王朝虽有十九省之大、三百年之渥,但由于内忧外患深重,一旦辛亥革命兴起,则不敌“锄耰棘矜木兵竿旗之众”,江山为之易色。此就朝廷而言者。在正文中,铃木虎雄将清王朝“所得之果”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将帅与宗室无能自私,不讲道义。“民心一去兮,疆臣坐懵”“厚赏虽悬兮,纳款弃甲。皕百岁养士兮,无一义人”“咨宗室亦懵腾兮,托阃寄愈狐疑”“非贾韩之佞柔兮,则桧伦之莽卤;先一身之安危兮,忽王室之薄祜”,即指此。将帅不知对策,大臣忘却道义,先求自身安全,不计国家安危,这是清廷政治导致的恶果。第二,危急关头缺乏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贤士,导致清室孤儿寡母无所依托。“憨孤儿与寡妇兮,孰其托以盐梅”“或勤王而倒戈兮,或讨贼而缓鼓;咸是羊质之城虎兮,谁敢中流之砥柱”,即指此。第三,灾祸接踵而至,终至民国代清而兴。“遭要劫之觱沸兮,让共和之祥休。名虽美而实丧兮,大憝兴而炰烋”“举一人而司群后兮,熙百揆以通舆谋;何今日之辞位兮,与前典之不侔”“嗟一旦之雍熙兮,化千年之寂寞;去万乘之尊位兮,就二王之宾列”,名义上颇有气度的禅让,并没有为逊清王室赢来起码的尊重。而“仰父颜以睢盱兮,牵母衣而夷悦;彤庭阒以无人兮,绣扆嶷而徒设”“閟玉殿以瞑坐兮,掩朱扉而哽咽;循景山而徙倚兮,禽鸟噭以哀别”“临太液而容与兮,柳荷晘而欹折;芳苑日以苔积兮,曲池时渐水渴”等,更是渲染了辛亥之后逊清王室的悲凉处境和宫廷苑囿的寂寞之状。

铃木虎雄《哀清赋》与王国维《颐和园词》呼应最切紧的,应主要是对袁世凯的尖锐批评。《哀清赋》序所论虽广,但直接提及的反面人物只有“冢宰袁某”即袁世凯一人,其余所谓“宗臣”“巨室”“城狐”“社鼠”,不过笼统言之,这实际上是把清亡的关键原因归于袁世凯。正因为慈禧所用非人,导致如袁世凯一类的奸臣当道,加速了王朝走向末路。赋文中“哲妇既不悟兮,懦王又邃处”“嗟信师昭之谋图兮,不知操卓之诡随”“起先皇之逆仇兮,支大厦之败颓;借巨盗以管钥兮,忘伪忠之奸回”“固出尔之反尔兮,虽百悔无奈何”等,皆主要指袁世凯。而王国维《颐和园词》“独总百官居冢宰,共扶孺子济艰难”“虎鼠龙鱼无定态,唐侯已在虞宾位”“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时顾命臣”等,也无一不指向袁世凯。二人堪称桴鼓相应。
将清亡之关键原因归诸袁世凯,在当时乃寓居京都的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共同看法。1912年7月明治天皇去世,不久乃木希典大将即切腹自裁,以殉天皇。对此,寓居日本的罗庄在《海东杂记》中评论道:
居东二年,最令人惊心动魄者,为乃木大将希典殉明治天皇一事……盖其时有权奸秉政,如吾国袁氏者,其心叵测,恐嗣君为所诱惑而动摇国本,故效古人尸谏……伯父、王姻丈及家大人皆叹仰不置。
“伯父”即罗振玉,“王姻丈”即王国维,“家大人”即罗振常。可见,当时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皆视袁世凯为权奸。王国维居东诗歌,凡涉易代之篇,批评锋芒也都或明或暗指向袁世凯。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中,王国维更直接指出,清廷最致命的错误就是辛亥以后,“庙谟先立帅,廷议尽推袁”,使得袁世凯权倾一时。正是这个清廷的代表胁迫清帝退位,稍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民国总统。历史在一个人手中竟然如此翻云覆雨。
王国维在《颐和园词》中隐约而言的百官冢宰、新朝主,在铃木虎雄赋中则直接变成了“冢宰袁某”。而在《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中,王国维也直接点出了“袁”。《颐和园词》中的“虎鼠龙鱼”,即是《哀清赋》中的“城狐”“社鼠”。可以说,铃木虎雄与王国维的批评矛头都是主要针对着袁世凯的,《哀清赋》是如此,《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的后半部更是以袁世凯与隆裕为双线。王国维《颐和园词》《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二诗,点染着其对清朝覆没的悲悼、对袁世凯的批评及对清亡后皇室的张皇处境和国家社会之凌乱局面的忧思。可能是王国维觉得这些零碎而分散的议论缺乏力量,所以才拟撰《东征赋》畅说其意,后来他意外读到铃木虎雄《哀清赋》,觉得思路、判断与自己大体相合,于是便毅然搁笔。
值得注意的是,铃木虎雄何以对晚清历史如此熟悉,何以能有如此精准的评判?从1912至1913年间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可知,铃木虎雄在京都与王国维、罗振玉等过从甚密,多有诗歌和学术、文献交流。由此推断,铃木虎雄从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处获知清末史事以及他们对清朝灭亡的淋漓悲情和相关议论、判断,也是十分自然的。这大概也是铃木虎雄能道王国维心中所欲言而未及在《颐和园词》中所尽言者的原因。
三、《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与《蜀道难》之哀清
就哀清主题而论,《颐和园词》与次年初撰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可以彼此衬合,而《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之哀清则若隐若现。
狩野直喜曾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前后在中国留学,其友人藤田丰八时在东文学社任教,狩野直喜从藤田丰八那里知晓了王国维的名字,但缘悭一面。一直到明治四十三年,狩野直喜与内藤虎次郎等到清学部调查敦煌遗书,才因着罗振玉的绍介而与王国维结识,据说当时他们交流了关于元杂剧的研究。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与罗振玉东渡日本,即应狩野直喜等人力邀而去,舟至神户,狩野直喜与东京、京都的友好亲来码头迎迓,狩野直喜并为之卜宅于京都。居东期间,王国维“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与狩野直喜住得相近,“常常来往”。从王国维赠诗“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结回心胸”,可见两人交往之频和相谈之切,譬如关于哲学的话题就曾在他们之间展开。狩野直喜说:“聊天的时候我偶尔提到西洋哲学,王君苦笑说他不懂,总是逃避这个话题。”王国维赠诗中“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似乎与这一话题有关。如此,从北京初识的相谈甚欢和离别时“巾车相送城南隅”的深情,到京都再聚时择邻卜居、夜阑话旧,再到赠诗狩野直喜西渡并坐待归来,两人交谊之密切和深厚在异国友人中确实是少见的,这大概也是王国维在诗歌中不仅谈故国、谈两人交谊,也谈对日本时局的担忧的原因所在。他们“夜阑促坐”的交谈,应该既广泛也深入。
1912年8月,狩野直喜拟往巴黎和伦敦查访敦煌文献,王国维以诗送之。初以五排作之,因觉不工,遂改作七古。诗凡66句。前8句以自己治学的“苦泛滥”“随所攻”与狩野直喜之“肸蚃每与沂泗通”相对照,极言狩野直喜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心契。最后18句兼写日本国“尚功利”“乏风节”“困鲁税”“出燕说”等不良现象以及为狩野直喜送行之意。或许是因为在日本赋诗而有批评日本之意,所以铃木虎雄索此诗拟刊登日本杂志,王国维有点犹豫。这与铃木虎雄拟荐《颐和园词》刊载《艺文》杂志,王国维回复“毫无不可”形成了明显反差。
王国维送狩野直喜诗的中间40句,可分为五层:第9—20句回忆京城初见情形,既写相见之欢愉,也写清末朝政松弛、官员无耻,士风与学术皆趋堕落;第21—24句写当年京城一别后不久即“市朝换”,发生了易代之变;第25—32句写自己在辛亥之后兵戈满眼之际仓皇东渡日本;第33—40句写寓居京都后与狩野直喜聚谈之乐以及兴衰之感;第41—48句则具体写“回首神州剧可哀”之义,这才是与哀清主题相关的部分,所占篇幅不足全诗的八分之一,兹录诗如下:
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姑苏台。兴亡原非一姓事,可怜惵惵京与垓。
这是王国维与狩野直喜谈及清亡之事时的感慨,不仅可与《颐和园词》对读,也可与稍后而作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互相参证。王国维直言与狩野直喜“谈深相与话兴衰”“忧时君为三太息”。以此而言,狩野直喜在王国维去世后回忆两人交往说“我从未听到他谈政治”,应该并不符合事实。何况狩野直喜读过王国维《颐和园词》,称赞其中“满含燃烧着的忠义之情”,知道王国维对清亡的深沉感叹。可惜今存狩野直喜致王国维信五通,皆未涉此诗,而王国维致狩野直喜信也仅存两通,皆为王国维从日本回国之后所作。若有两人京都往返信函存世,我们或可了解他们更多的探讨。此8句所述,要点有三:第一,王国维感叹古代的忠节传统在清亡后渺无踪影;第二,感叹清亡与内部政权的松弛密切相关,乃有一个逐步衰落的过程;第三,清亡不只是皇室、皇族的沦亡,更重要的是全体国民从此陷于灾难之中。第一、第二点王国维在《颐和园词》中已有简略表述,第二、第三点则是其拟作的《东征赋》的核心内容。“良医我是九折肱,忧时君为三太息”,王国维因为饱阅世事,对自己的政治判断力十分自信。曾经在1910年与狩野直喜一起结识王国维的小川琢治说:“读王君的遗稿《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中‘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一联,我才知道早在革命时,他已坚决地选择了一死。”小川琢治未免联系得过于直接,但至少看到了王国维在清亡后满怀的悲凉之意。
从内容的关联性来看,王国维送狩野直喜之诗虽有与《颐和园词》呼应之处,但只是以彼此谈论话题的方式嵌入诗中,所占分量不多,送狩野直喜诗更多的内容与两人的交往经历和彼此谈论的其他话题有关。
“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这是王国维对清亡后没有出现像文天祥、谢枋得一类节士而深感遗憾甚至屈辱的慨叹。谢枋得宋亡后矢志为遗民,而文天祥则是为国捐躯的英雄。其实“节士安在”之叹,只是大概言之。在王国维看来,尚书端方或可视为清朝之文天祥。因为端方是入川被杀,故王国维以“蜀道难”为题,赋诗纪念端方被杀一周年。此诗极言端方的博学多才和多舛命运。“铁官将作议纷纶,诏付经营起重臣。又报烽烟昏玉垒,便移旌节上荆门。”端方在四川、湖北等地联合反对皇族内阁将铁路收归国有之时,受命出任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因川中议论最为汹涌,故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川,结果在资中被革命党人杀害,首级被砍下携至武昌。“即今蛮邸悬头久,枯骨犹闻老兵守”“首在荆南身在蜀,归魂日夜西山麓。”王国维对当时革命党人不肯归还端方首级表达了极度不满。

总之,《颐和园词》以慈禧为中心带出清亡始末,《送日本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则在叙写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交往的过程中兼及清亡之事,《蜀道难》是在辛亥革命的背景下聚焦端方个人命运。三诗都与哀悼清亡有关,故被王国维合为《壬子三诗》一集。
四、《壬子三诗》的层次
值得注意的是,《壬子三诗》在三首长诗之外,还附录了《柯凤笙京卿劭忞岁暮怀人诗四首》《沈乙盦方伯曾植秋怀诗三首柬太夷》,又沈曾植《寄叔言》一首,凡八诗。柯劭忞诗所怀四人分别是罗振玉(字叔蕴)、王国维(字静庵)、刘廷琛(字幼云)、郭恩孚(字蓉汀)四人,沈曾植的《秋怀诗》三首是写赠郑孝胥(字太夷)的。
王国维何以在自己的诗集之后附录柯劭忞与沈曾植的诗呢?前言三诗组合成集,已形松散;再附他人八诗,未免松散更甚。如果再考虑到此八诗乃是癸丑年(1913)之作,则“壬子”二字也难副其名。王国维素来心性严谨,这其中必有值得考索的原因在。
王国维因罗振玉之介而结识柯劭忞,时在1909年。今检王国维书信集,仅存1917年12月21日致柯劭忞一札。《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影印柯劭忞致王国维手札十通,亦是王国维从东瀛回国后在沪、京两地所作,内容多关《新元史》之编刻、请其指导其子、日常宴聚等事,而无关癸丑年寄诗京都之事。
王国维后来在柯劭忞《蓼园诗钞》五卷刻本(1925年自刻本)此四诗题上眉批:“凤老前寄初稿,稿略,字句略有异同,又第四首全异,附注诗间。”王国维的语境比较模糊,如“凤老前寄初稿”,受者为谁,并不清晰。其实这四首诗是寄给罗振玉的,罗振玉又将其抄示王国维,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收录罗振玉致王国维信函696通,其中第9通即为罗振玉手书此四诗以赠王国维者,王国维又抄写一份附于《壬子三诗》之后。柯劭忞寄赠此四诗的时间一时难以确考,大致应在癸丑(1913)冬。崔建利《柯劭忞年谱长编》于此年记云:“是年冬,有《岁暮无憀感伤存没作怀人诗四首》,思念时在青岛的刘廷琛、在日本京都的罗振玉和王国维、里居潍县的郭恩孚。”柯劭忞此四诗的创作时间和寄奉罗振玉的时间应比较接近。崔建利在这段文字下还依次列出柯氏分致刘廷琛、罗振玉、王国维、郭恩孚四诗,与罗振玉抄赠王国维的罗振玉、王国维、刘廷琛、郭恩孚的顺序略有不同,而王国维抄录则一依罗振玉之序。不知是柯劭忞寄赠时因为受赠者是罗振玉而改变了顺序,还是罗振玉抄示王国维时作了调整?
罗振玉东渡日本后至少在1912年8月前后,与柯劭忞失去联系,以至于要在致宝熙信中询问柯劭忞的去向。此后不久方得与柯劭忞通函,不少往返函件仍然通过宝熙中转。两人通函的频率并不高,以至于罗振玉在致宝熙信中有“凤老近相见否,久无信来何也”之叹。今存柯劭忞致罗振玉信,从1912年末至1913年末,仅得两函,其中并无一字涉及赠诗之事,或函件缺失者尚多。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与罗振玉居东时,国内友朋来信,彼此互相传看是常态。如1915年春,罗振玉收到缪荃孙来札,即将原札转王国维一览并附信云:“缪先生函奉览,竟不知其作何语也。”“缪函阅后,求送绶公处一看。”一信由罗振玉、王国维、董康(字授经)三人先后阅过,可见这一时期王国维寓目罗振玉接函,也是常例。王国维据罗振玉钞本柯劭忞四诗另抄入《壬子三诗》,同样有着这样的背景。
虽然在1904年阴历四月上旬,王国维于其主事的《教育世界》第7期“肖象栏”中刊登过“中国历史学家沈子培太守曾植”照片一帧,但那主要是因为罗振玉的关系。1902年初,沈曾植就离沪外任了,王国维与沈曾植当时只是神交而已。而在壬癸年之前,王国维依然无缘结识沈曾植。1914年8月2日王国维从京都致信时在沪上的沈曾植,尚以“踪迹暌违,未得一奉几杖”为憾。这足以说明《壬子三诗》编竣之1912年岁末,王国维与沈曾植尚缘悭一面。1915年二月七日(3月22日),罗振玉致信沈曾植云:“月内王君静安送眷回国,届时当晋谒左右,渠久仰名德,深以得接謦欬为幸,想长者必愿与纵谈也。”王国维自己也说:“乙卯春,归国展墓,谒方伯于上海。”(《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弁言》)王国维是1915年春从日本回国去海宁扫墓经沪时,才第一次拜会沈曾植,这一次会面,王国维向沈曾植请教音韵之学,而沈曾植则赞许王国维“善自命题”(《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弁言》)。明乎这一背景,则知沈曾植数诗亦为寄呈罗振玉者无疑。事实上,在1914年8月2日王国维致沈曾植的信中,已直接说出由其致罗振玉信而获读《秋怀诗》之事。王国维信云:“每从蕴公处得读书疏并及诗翰,读‘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之句,始知圣贤仙佛,去人不远。”信中“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即为沈曾植寄呈罗振玉其柬郑孝胥《秋怀诗》三首之三中的句子,而此二句也同样是近九个月前(1913年11月18日)罗振玉收到沈曾植诗札“讽咏不下百回”者,可以想见当初罗振玉接奉沈曾植信,与王国维展读共赏的情形。在王国维致沈曾植的这封信中,除了上引“道穷”二句外,另有两处提及“愿在世无绝”之句:
现蕴公次子福苌年未及冠,天资英敏……能继先生志事者,当在此人,此亦先生所云“愿在世无绝”之一事也。
先生……但使闲燕之间,心之所感,随笔书之,自数字、数十字以至数百千字流传世间,当有振发聋盲之效,此亦“愿在世无绝”之一事也。
如此一信之中,三复其诗句,足见王国维阅读沈曾植之诗的特殊感受,其抄录并附《壬子三诗》之后,不亦有故乎!而在近三个月前的1914年5月5日,王国维已先将此三诗转刊于《盛京时报》上,并在诗前评曰:“顷读沈乙庵方伯《秋怀诗》三首,意境深邃而寥廓,虽使山谷、后山为之,亦不是过也。”在引录沈曾植三诗后,王国维再次对第三首中的“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表达了极度推崇之意。一诗二句四度引用,足见其青睐。
“辛亥国变,予避地海东,乙厂尚书书问屡通”,这是罗振玉追忆寓居日本后与沈曾植往返通函之密。今检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正录有不少沈、罗往返之函,可证罗振玉非虚言也。总而言之,此八诗乃柯劭忞、沈曾植寄赠罗振玉,罗振玉出示王国维,王国维遂合抄柯劭忞、沈曾植二家诗附于《壬子三诗》集后。这意味着,现存罗振玉著述虽然并无只字提及《壬子三诗》,但其实他是知悉王国维此编,并支持王国维将柯、罗之诗附录集后的。
1914年,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书成,曾手录嘉兴沈曾植《奉怀一律》(即《寄叔言》)冠简首,并录胶州柯劭忞《岁暮怀人四之一》即赠自己的一首次于后。罗振玉跋云:
予性孤冷,少交游,自江湖长往,与世益疏。惟子培方伯、凤荪京卿时时诒书海外,勉共岁寒。去岁知予将考订殷虚遗文,先后赠诗,均及兹事。所以期于予者至厚。此编告成,爰录之简首,以志予之樗散放废,尚能勉力写定者,其得于二老敦勉之力为多也。
王国维与罗振玉分撰《殷虚书契考释》序、跋,在甲寅(1914)冬十二月,知罗振玉跋所云“去岁”,乃指癸丑年(1913)。而《壬子三诗》编定则在壬子(1912)冬,由此可知,《壬子三诗》后附柯劭忞、沈曾植八诗乃后来补入,与三首长诗的编定并非同时。据考证,沈曾植将《秋怀诗》三首出示郑孝胥,时在1913年九月二十五日(10月24日),次日,郑孝胥在海日楼以和诗三章示沈曾植。1913年十月中旬(约11月12日前后)沈曾植致信罗振玉云:“近日万念灰冷,病余睡醒,惟以梵䇲遮眼……录奉短篇,聊当寤语。”信后依次附“奉怀”罗振玉的诗一章和《秋怀三首柬太夷》。其实沈曾植分赠郑、罗二人之诗,在创作时间上隔了近二十天,赠郑者前而赠罗者后。1913年十月二十一日(11月18日),罗振玉收到沈曾植手札和附诗后复函云:“拜读赐章,欢谢不可言状……《秋怀》四章,合山谷、后山为一手,一句一拜倒,至‘道亡诗亦尽,愿在世无绝’二句,讽咏不下百回,恨不得尽观近制,亟付手民也。”读此信可知,王国维后来在《盛京时报》对此四诗“虽使山谷、后山为之,亦不是过也”之评,应是与罗振玉共读时的公论。罗振玉“《秋怀》四章”云云,乃是将沈曾植寄呈之诗并称“四章”。以此可知,王国维将沈曾植四诗抄录一过(抄录顺序与沈曾植信中附诗顺序相反),附于《壬子三诗》集后,必在1913年11月后半月或之后,此时距《壬子三诗》编定的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1913年1月26日),已有十月之久。由此可知,《壬子三诗》虽然所录有11首诗歌,但其实以《颐和园词》为正编,以《送狩野博士直喜游欧洲》《蜀道难》为副编,以柯劭忞、沈曾植各四诗为附录,实际上有三个层次。
五、《壬子三诗》附录柯劭忞、沈曾植八诗之意旨
王国维将柯劭忞、沈曾植诗附于《壬子三诗》之后,盖以其一人之思摄合多人之思。先看附录的柯劭忞怀王国维之诗:
历历三年事,都归一卷诗。秦庭方指鹿,江渚莫然犀。管邴君无忝,唐虞我已知。文章零落尽,此意不磷缁。
王国维在此诗后面题“静庵”二字,因知是题赠给他自己的。此诗在批评当时民国政府颠倒黑白、不辨奸邪的背景下,以历史上操守清凛的东汉管宁、邴原分比王国维与罗振玉,称赞他们辛亥之后东渡日本,清节凛然。柯劭忞怀罗振玉诗也有“衣冠非夙昔,风义自平生”之句,极言罗振玉以风义自守而甘做东瀛之客。对辛亥后飘然隐居青岛、潍县的刘廷琛、郭恩孚,柯劭忞也赋诗表达了敬意。总之,柯劭忞的这组怀人诗结合辛亥后四人避地之事,略写遗老情怀。王国维将柯诗附于《壬子三诗》之后,亦有深意存焉。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亦云:
先生又尝评柯凤荪学士《蓼园诗钞》云:“义山而后,学杜者惟后山,二千年后乃得蓼园。”推崇可谓备至。又于沈乙盦先生诗,亦必手自钞录,而尤爱诵其《秋怀》及《陶然亭》二诗。无事时,辄讽咏不已。此二老外,其他则少所许可矣。
此“《秋怀》”诗即附录于《壬子三诗》之后的四首组诗,可见在王国维生命的最后十五年,至少就诗歌而言,柯劭忞与沈曾植都是其心追神想的典范。但赵万里所引王国维评柯劭忞的文字,略有讹误,原文见王国维跋中华书局1924年4月铅印本《蓼园诗钞》五卷:“古来学杜得其神髓者,无如义山、后山,一千年后乃得蓼园。三复此编,当知此言非溢美也。”赵万里盖耳闻王国维之言,而未及核对此跋,只是略撮其意而已,并误“一千年”为“二千年”,不过,也传达出了王国维对柯劭忞诗歌的赏爱之意。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回到上海,与柯劭忞交往亦多。1923年王国维入京后,与柯劭忞联系更为密切。1924年甲子之变,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据说罗振玉与时为溥仪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柯劭忞相约投河自尽。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诗“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二句即谓此事,所谓“北门学士”便指柯劭忞。可见除了诗歌趣味之外,两人政治态度亦相当一致。
柯劭忞、沈曾植二人应是罗振玉与王国维交谈时频繁涉及的人物,故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扉页专门抄录二人之诗,以鸣谢“二老敦勉之力”。大概是受到罗振玉影响,王国维对当时诗坛的赏评也持“南沈北柯”之说。
癸丑(1913)二月,在种种政治势力的逼迫下,隆裕皇太后率清帝溥仪正式宣布退位,民国政府由此获得了政治上和体制上的完全合法性。对于遗老来说,这一易代之变一时难以接受。沈曾植、郑孝胥都是当时沪上遗老的代表,故两人之“秋怀”亦深度相似,而沈曾植更深刻了解罗振玉,故将简郑之诗抄录寄罗,亦借以表惺惺相惜之意。王国维总评沈曾植三诗“意境深邃而寥廓”,盖也别有体会。沈曾植诗之一借秋景起兴,以秋叶之萧条、秋虫之喑哑、秋宵之无力、秋啸之寂寞,来写“天人目共眴,海客珠方沉”之寂寥惊恐和怀才不遇之意;之二以“贵己不如贱,鬼应殊胜人”起笔,暗喻当时魑魅魍魉当道,世界无序无常;之三从南宋“四灵”说起,言漂泊江湖,“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此二句为罗振玉剧赏,讽咏不已,盖写出遗老鼎革后孤独之怀耳。合观三诗,要在表现易代之后失序之时势以及萎靡甚至绝望之心情,弥漫着对清王朝的追念以及对民国政府的不满。王国维评此组诗曰:
于第一章,见忧时之深;第二章,虽作鬼语,乃类散仙;至第三章,乃云“道穷诗亦尽,愿在世无绝”,又非孔、孟、释迦一辈人不能道。以山谷、后山目之,犹皮相也。
“忧时”乃就辛亥革命后国体变革而言,“鬼语”乃笔墨怪诞,从忧思中宕开一路。“孔、孟、释迦”之语则极言其能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类似“无我之境”。《人间词话》云: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故不同矣。
尼采原话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其血写下的。用血写,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王国维认为李后主与宋徽宗虽同为亡国之君,但宋徽宗词尚不离乎个人身世,而李后主词则如释迦牟尼和基督一样以承担人类罪恶的胸襟看待和承受家国灾难。不离乎自身,乃“有我之境”;关合众生,乃“无我之境”。前者境小,后者境大,王国维的价值评判非常明确。这样来看,王国维对沈曾植《秋怀诗》三首之三的宏阔之境评价极高,认为道出了一个群体特别是遗老群体的共同心声。
郑孝胥收到沈曾植赠诗后,作有《答乙盦短歌三章》,情韵略似,而意趣更为消沉。其对世道之不满、悲愤甚至求死之心,较沈曾植诗更为强烈,觉得自己不过鬼世人形、枯寂存世而已。《壬子三诗》附录的最后一首诗乃沈曾植寄赠罗振玉的《寄叔言》:“二酉山深是首阳,千秋孤索耿心光。十繇郑说文能补,六太殷官府有藏。梦里倘逢师挚告,书成不借广微商。残年识字心犹在,海水天风跂一望。”此诗用典甚多,要在以“二酉山”之典赞赏罗振玉辛亥后隐居日本京都,考订殷墟甲骨遗文,抉发千年前之文明。盖甲骨书契,乃新近出土、“先儒未闻”,故可资考订以补上古史者甚多。末二句期待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一书早日撰成,“故悬知公之疏通知远,足以质鬼神而俟后圣”,必是为中国文明史“发一殊采”之伟业。
相较于沈曾植赠郑孝胥诗,《寄叔言》别开一途,主要表达对罗振玉从事甲骨文研究的重视和期待。沈曾植、罗振玉等人于易代后“万念灰冷”之时,沉潜于学术,未尝不是在隐居避世。此诗虽不如赠郑孝胥诗那么沉痛,其实也是心曲旁通。可见王国维以柯、沈八诗与其三首长诗在情感、思想、神韵上的契合而都为一集,乃以一人之思摄合诸人易代后的一时之思也。
余论:从《壬子三诗》到《壬癸集》
《壬子三诗》编定于1913年1月26日,但至今尚未发现王国维欲将其付梓的文字记录。大约在1912年末,罗振玉致王国维信云:“便中为录诗稿付装,不拘多少。”从时间上来考察,此时王国维尚无编辑《壬癸集》之念,故信中所谓当与《壬子三诗》有关。可见无论是王国维还是罗振玉,皆无将此集付梓之念。孙敦恒说王国维将此三诗“署名《壬子三诗》印行”,擅加“印行”二字,未免出语唐突。陈永正说王国维将《壬子三诗》“散发给诗友”,似也缺乏证据。
王国维对《颐和园词》当然是满意的,但这种满意仅限于对晚清走向衰落直至灭亡的历史轨迹的勾勒,而对清王朝覆灭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尚未及系统探讨和表述,所以王国维的“满意”其实是不彻底的。铃木虎雄《哀清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王国维《颐和园词》言之未尽的遗憾,但毕竟是异邦他人文字,能否在思想和情感上与王国维精准契合也是值得推敲的。拟想中的《东征赋》固然因看到铃木虎雄《哀清赋》搁笔已久,但隆裕皇太后的突然去世,却再度唤起了王国维续写《颐和园词》未尽之思的冲动,于是便有了完成于1913年2月下旬的《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王国维在《壬子三诗》编定后不到一个月便完成此诗,就清亡主题的共性而言,理当汇为一编,但硬性放在一起又不合适,毕竟后者是跨年之制了。大概是王国维心有未惬,故在此诗完成后,有意扩大编辑范围,将壬子、癸丑两年之诗合编一集。1913年2月24日,王国维致信缪荃孙就提及“拟将至东以后诗编成一卷付之排印”之事。此一卷之诗即传世之《壬癸集》。1913年6月27日,王国维致信铃木虎雄,已明确告知《壬癸集》“次月上旬可以装成”。如此,编成《壬子三诗》与起意编辑《壬癸集》之间,相距不足一月。这说明《壬子三诗》编成不久,付梓意义很快就被王国维否定了,而转以《壬癸集》代替。如此,《壬子三诗》便像化石中的生物一样,冻结在历史地层中了。由王国维致铃木虎雄信可知,他其实是想把《壬癸集》作为暂时中辍诗歌创作的一个标志,故而将居东之诗悉数收入,不再遴选。
然而,王国维并未完全搁置《壬子三诗》。《壬癸集》编成于1913年5月,印制出版于同年7月上旬。当年11月下半月左右,王国维从罗振玉处先后获睹柯劭忞、沈曾植之诗后,还是将其悉数抄录在《壬子三诗》之后。而且,他在晚年尚对助教赵万里特地提及此集。这说明王国维对此集萦怀难忘。因为有了《壬癸集》,《壬子三诗》固然无需出版,但对王国维来说,却是思想和情感历程中的珍贵“鸿爪”。
① 黄永年:《说〈颐和园词〉兼评邓云乡〈本事〉》,《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页。
②⑤[33][59] 冀淑英、张志清、刘波主编:《赵万里全集》第1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第16页,第13页,第16—17页。
③ 储皖峰:《王静安先生著述表》,《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姚名达:《王静安先生年表》,《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1927年10月;神田喜一郎:《观堂先生著作目录》,(日本)《艺文》1927年第8、9号;赵万里:《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赵万里全集》第1卷,第62—70页。
④⑩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11页,第511页。
⑥ 王国维《壬子三诗序》即明确说“壬子二月”成《颐和园词》,参见国家图书馆藏《壬子三诗》稿本。
⑦⑧⑨[11][17][22][23][24][29][34][44][49][51][74][75][76][77][78] 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第44页,第56页,第54页,第53—60页,第55页,第56页,第54页,第674—675页,第491—492页,第61页,第61页,第61—62页,第46页,第46页,第48页,第60页,第60页。
[12] 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第53页。按,编者将此信置于5月9日信之前,应是将王国维落款的“四月十五日”按公历计算,不应先“搁笔”而后“拟为”《东征赋》。
[13] 本文所引《壬子三诗》诸诗,皆据国家图书馆藏稿本。
[14] 铃木虎雄:《追忆王静庵君》,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5页。
[15] 本文所引铃木虎雄《哀清赋并序》,皆据鈴木虎雄『業間録』(弘文堂書房,1928)360—363頁。
[16] 罗庄著,徐德明、吴琦幸整理:《初日楼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
[18][20][21][25][27]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追忆王国维》,第292—293页,第294页,第294页,第295页,第297页。
[19] 参见罗振玉:《狩野君山博士六十寿序》,罗继祖主编,王同策副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10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694页。
[26] 此后王国维与狩野直喜彼此通函,也不时涉及对政治之看法,参见《王国维书信日记》,第674、675页;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编:《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579—2580页。
[28][35][37] 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编:《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第2572—2580页,第481—497页,第596—597页。按,今仅存诗歌而未附信。
[30] 小川琢治:《回忆王静庵君》,《追忆王国维》,第299页。
[31][41] 萧文立编注:《雪堂书信集》乙集(未刊稿),第25页,第16页。
[32][36] 崔建利:《柯劭忞诗集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第152页。
[38] 崔建利:《柯劭忞年谱长编》卷六,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71页。
[39] 1912年7—9月罗振玉致宝熙信云:“柯凤老何在?求便询徐梧翁见示为荷。”(《雪堂书信集》乙集,第6页)
[40] 如1913年12月10日罗振玉致宝熙信中即请其转致柯劭忞之信,柯劭忞也有请宝熙代寄致罗振玉信者(《雪堂书信集》乙集,第10、17、15页)。
[42] 王宇、房学惠:《柯劭忞致罗振玉手札廿三通》,《文献》2001年第1期。
[43]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王庆祥、萧文立校注,罗继祖审订:《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45][50][58] 许全胜整理:《罗振玉与沈曾植书函》之十七,《历史文献》第1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页,第167页,第167页。
[46][47]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5卷,第125页,第125页。
[48] 罗振玉《海宁王忠悫公传》云:“公居海东……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蓼园学士……”(《追忆王国维》,第7页)
[52][53][64][65] 王国维:《东山杂记》卷二,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第107页,第106页,第107页。
[54] 罗振玉:《海日楼绝笔楹联题咏·跋》,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96页。
[55] 罗振玉手书沈曾植、柯劭忞二诗及跋见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95—96页。
[56]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88页。
[57][70] 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388页,第388页。
[60] 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录:《观堂题跋选录(子集部分)》,《文献》1981年第4期。
[61] 罗振玉《祭王忠悫公文》云:“十月之变,势且殆,因与公及胶州柯蓼园约同死。”(《追忆王国维》,第70页)
[62]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筼诗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6页。
[63][73] 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第144页。
[66] 王国维著,彭玉平疏证:《人间词话疏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9页。
[67] 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页。
[68] 郑孝胥:《答乙盦短歌三章》,郑孝胥著,黄珅、杨晓波点校:《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50页。
[69] 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三种》,第98页。
[71] 萧文立编注:《罗雪堂书信集》(未刊稿),第5页。
[72]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