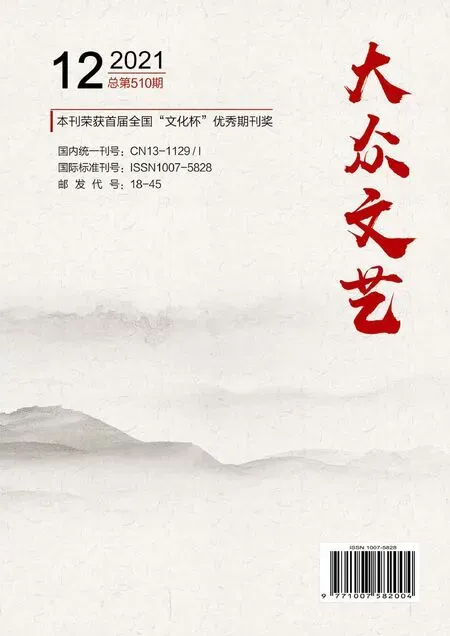编年叙事与地方记忆
——纪录片《渡口编年》系列的叙事意义
黄宝富 马卓敏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321004)
叙事主题是内容在思想层面的高度凝练,它往往通过特定的人物、地点和时间来表达,其显著特征则是具体。而对纪录片的叙事来说,“所谓‘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这除了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之外,还有对生活的思考、评价以及作者的情感、理解和认知”。《渡口编年》系列由《贺家》《陶家》《周家》《故乡》四部组成,导演郭熙志立足于自己的生命体验,又以大生命意识的视野,试图透视在这变迁的二十年间,被主流话语边缘化且忽视的生命,是如何像草一样生长起来的。在叙事主题上,影片以“编年”与空间的双重影像,在主题层面传达出文献价值和真实意义。
一、“编年”叙事中影像呈现的“文献性”意义
中文的“纪录片” 一词,译自英文词源“documentary”,其本意便是“文献资料”,故文献性是纪录片的本源属性。在《渡口编年》系列中,导演郭熙志以社会转型所提供的“危机时刻”作为创作原点和契机,以故乡和悦洲作为社会横截面,以“编年”叙事激发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积蓄的时间能量,为在时代洪流中未立住脚跟的“小人物”做传。正如史学家保尔·汤普逊所言,“与正史、官史不同,文献愈是私人、地方和非官方,就愈难以幸存”。而该系列纪录片,正以其跨时代的见证性,为当代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影像文献”。
(一)客观与“厚描”:新历史主义叙事中的时代缩影
“厚描”作为人类学中描述民族志的方法,被强调为一种符合民族志解释性特点的“微观描述”,“我们想找到过去的躯体和活生生的声音,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找到这一切——那些躯体早已腐朽而声音亦陷入沉寂,我们至少能够捕捉住那些似乎贴近实际经历的踪迹。”《渡口编年》系列在新历史主义视阈的观照下,将被现代历史划分到边缘地带的人群的境遇及其生活空间,作为被主流宏大叙述所搁置与忽略的“微小事件”展开厚描,以此记录下带有大量私人化与当代性的影像材料,以作为描摹时代缩影的原始素材。
艺术创作者在现实主义观念的投射下,以社会转型所赋予的“危机时刻”作为纪录的契机,以故乡作为现代历史洪流中的锚着地,打捞与记录沉沦在历史之海中却有价值的事物。该系列纪录片的创作时间为1998年到2018年,在时间跨度上经历了由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之后二十年后的历程,该阶段可谓中国社会在以发展作为转型目标上的阵痛期。如果说由主流叙事宏观铺陈的以发展为关键词的时代缩影,是中国这一母体在阵痛期后顺利分娩的婴孩,纪录片系列通过将主流叙述聚焦于新生儿的目光回望至母体的方式,给予其关爱与敬意,并展现被迫与母体割舍的以“弃儿”为主体的时代印象。而该系列作品的客观性,也主要体现在其试图为过往存像,建构与还原中国社会的真实在场,在“孕育与阵痛”时的真实景象。
与主流叙述所构建的,以“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表达相伴生的,则是对逝去的往昔时代的怀念。在《故乡》中,导演故乡的地理空间格局,首先为怀念的展开提供了基础情境。其故乡大通古镇在自然地理空间上分为三部分,而每部分又随着时代变迁分化出不同的社会功能:空间一是位于江心的和悦洲,它是导演的出生地。该地因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进行移民迁镇,现呈半荒废状态;空间二是与其隔江而望的大通古镇主体,镇上有菜市场、鱼市、理发店等较为完整的生活系统,基本可以同时满足本地住户的生活需求与外来游客的观光需求;空间三则是横亘于两者间的长江与古渡。在影片中,导演怀着吊古之情多次乘渡船徘徊于两岸间,承载旧有生活方式的和悦洲已破败为废墟,对岸被时代发展“收编”的大通古镇则不断旧貌换新颜。两者在影片中的并置,成为时代发展以“扬弃”为实质的时间指涉。
(二)细观与“抓取”:时间叙事中的现实记录
“记忆之场意味着两个现实层面的交叉,其一是有形的层面,他可触及、可感知,扎根在空间、时间、语言和传统中,而另一种则是纯粹象征化的,它可以被反复阐释。两者间存在某种共性,将有形物与象征物同时囊括。”记忆的场域,在长达二十年的编年体长河中展开叙事,但却通过时间之河的细观与“抓取”有形之物,并在影像结构与视听层面赋予较为纯粹的象征意味,使其在作为现实回忆时更具可考性与思辨性。
以和悦老街废墟为联想能指,留存于记忆中的已逝去的时代和生活方式,导演通过当下时空发掘与构建有形的意象流,觅得往昔踪迹。在影片《故乡》中,导演于2014年拍摄了一家位于大通古镇,且内里仍是榫卯木结构老屋的理发店。画面中,收音机里传来的喑哑的戏曲声,掀起了旧生活的一角珠帘。刻有“查姓老墙角”的石碑,则叩响了历史的院门。导演以微微摇晃的手持特写镜头,传达出其初入历史处境的欣喜与紧张,伴随其脚步,镜头一一记录下横挂在已层层剥落的砖瓦墙上的老物件:老式木制电箱、木制插座、皇历……此处是导演通过生活符号序列,对理发店作为生活场景进行的白描。在此基础上,导演又分别以长达近五秒的近景,定格理发店内已层层脱落的皮椅,墙上灰尘沉积的木算盘,桌上带锁的老式木箱与墙角整齐堆放的蜂窝煤饼。在导演带有审慎与忧思之情的画面里,这些旧物宛如被赋予了生命意识,以其静默彰显存在。而理发店这一空间,也因其成为历史与当下交互共生的“地方”而被赋予档案性。
除了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有形的“标记”之场,导演还在影片中通过蒙太奇组接而形成象征层面的记忆之场。在片子的结尾,导演使用了带有共性的剪辑法。当剧作接近尾声时,导演会在被摄对象已离世的事实后,承接一段其生前站在渡口前拍摄的历史影像。贺国平与陶礼贵都是患癌去世,他们的人生在影片中分别落幕于公墓前与病榻前。然而在此之后,导演都先承接了一段他们生前的形象,即站在风声呼啸的渡口边,再以照片定格。而在《周家》的影片末尾,周鑫结婚生子,生活趋于稳定,周家老屋的废墟也成为和悦洲景区的一道“风景”,但导演却在此后承接了一段幼年周鑫左右手分别举着父母遗像,站在渡口边的个人印记。
诚然,在被摄对象已离我们而去或生活的阴霾已逐渐淡去时,导演的此番剪接是残酷的,但笔者认为导演的首要也是本质目的在于追忆逝去的采访对象并向其致敬,而更深层的目的是在将看似迷雾逐渐淡去的当下代入一种紧急状态,即时刻警醒人们不要遗忘那些曾站在时代变迁的渡口,试图搭上驶向发展的渡船的这群人。这群在现代化进程中或被遗忘,或被抛下,或被前进脚步所制造的时间幻觉裹挟的个体,是活生生真实存在且在如野草般努力生长的。呼呼作响的江风或许淹没了他们的声音,但无法抹去他们的存在。而他们,才是历史进程中真正值得拥有话语权与书写价值的大多数。而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最后作为定格呈现的图片视角,并不等同于影像中观众所看到的视角,这似乎也在暗示与警醒观众,历史在呈现与书写上具有多面性,应以思辨的思维,审慎对待影像文献提供的视角,努力寻找那不止一个的生命真相。
二、空间叙事中影像纪录的真实性意义
邵培仁在《媒介地理学》一书中说,“空间是媒介传播环境中的材料与景观”,空间作为叙述环境,是纪录片展现的内容之一,而如何来表达内容以及如何将空间和叙事构筑在一起,则属于叙事的范畴。纪录片《渡口编年》立足故乡这一地域性空间,以构成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作为探寻社会真相的窗口。以记忆中的乡土空间,作为生发集体记忆的沃土,由此在现实与记忆的互文中构建记录真实。
(一)家国共生:地方叙事中的社会本相
人类社会由无数以不同标准划分的社会单元组成,在《渡口编年》谱系中,导演以故乡和悦洲作为叙事展开的基本社会单元,通过二十年的连续“在场”,为观众呈现大量有别于正史和官史的,带有私人性和当代性的影像系谱,由此成为社会转型的见证者与社会“真相”的存留者。在创作谈中,导演将其意图追寻的社会实在比作“看草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其实质则是关乎生命的真谛。只是这个样貌过于平凡,且被科学定义为某种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要求的自然规律,因而容易被人忽视。
诚然,并不是所有生命内在都能被镜头所记录,在以导演自我溯源为主体的《故乡》中,导演试图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回忆邻人的境遇。在影片第一段“和悦·死”中,导演总共回忆了十一位曾与自己同住在浩字巷的邻人。这些被讲述对象,多受过封建意识的“教育”或伤害,且家庭命运往往与国家兴衰同构。如与导演同住在三道街上的九姑,枞阳老桐城县人,听说上过金陵女子大学。其夫曾是国民党高官,江北普济圩修建的国府督办。二人育有一子,名为桐举,是个弱智。1949年九姑家准备乘军舰逃离大陆。发船前,九姑忽然发现儿子不见了,便慌忙下船寻找。等找到儿子,轮船已载着其夫走了,去了台湾。在挨斗风波中,面对持棍人要其下跪的胁迫与台下高呼的“认罪”声,她总是头不低,且不断地站起……
纵然只是对邻人某段生平的简单口述,被抑制的生命却仍在释放鲜明的能量,且在不断更迭的历史背景中被赋予某种独特的当代性。而家庭作为构成社会的最小单元,成为导演得以从多角度窥见生命本真的棱镜。作品系列也因此看似生发出多条寻找生命意义的思维线索,它可以是时代变迁中一条老街上的故事,可以是“父辈”的奋斗史,也可以是“子辈”的成长史,只是这三条线索被有机的交织在家庭叙事中,以看似不明就里的方式渗透在家庭及个人的命运走向中。正如导演在访谈中所说,“无论有多少种概括,我想有一点能确定:这是一个不讲逻辑的故事,但你可以触摸到时间,像用手抚摸到生命中坚硬的柔软那样具体”。而这种看似不讲逻辑,实则彰显生命本体的叙事意图,则是打破时代前行所制造的时间幻觉,从而探寻社会现实的“第一步”。
(二)族群记忆:乡土叙事中的符号连续性
共同记忆在社会区域的集体建构中,因为共通的生活场景、乡愁符码和时代事件,烙印在人们的内心观念与惯例行为之中。在纪录片中,被摄对象们基本是导演的同乡,其记忆显现于乡村陈述的文化发展性中,具体表现为对童稚生活的美好回忆,以及对乡土的无限眷恋。比如最后一部《故乡》的故事展现之中,导演有意选取从事不同工种,但在精神上与前三部被摄对象共享底层性的知识分子,以丰富与共享一致性的主体记忆,在各自的言说中进行沟通和交流,以生成和构架“同乡”的心理图式。
“尽管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上汲取力量,但也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回忆”。观众在观看同为安徽铜陵籍的盲人诗人章和信,坐在家中的木桌边,桌后的墙面上悬挂着年画,年画左侧写着“新世界”,右侧写着“旧山河”,章和信则就在这新旧共聚一堂的堂屋内,用乡音自在地吟诵着其诗作《沃土》:“我的沃土是太阳底下晒着的黑夜许多复苏的记忆从身边爬起便是些灼目的花草夜越黑花儿也就越鲜艳……”作家黄复彩则靠坐在街边的老墙下,对着手机念着其早已拟好的“遗嘱”,希望将其枯骨一把火烧了,扔到长江中,让他的灵魂顺江而下,回到故乡的江岸,并一头深深扎进岸边的土里,因为那是他拥有无数童年记忆的地方。在聚会的饭桌上,书法家余飙也操着乡音,情绪激动地吟诵着黄复彩的“遗嘱”,仿佛魂归故里也是他的心愿。
导演则以镜头展现了他坠入童年之梦的奇遇与祈盼,在正式开启对成长历程的溯源前,导演以从湖边漫步回忆往事的镜头,突然跳切到其只身伫立于一座荒废瓦房前的场景,模拟其在回忆的引力作用下,突然跃入梦中的奇遇。循着蝉声,镜头缓慢右摇对准叶片上的一只幼蝉。导演在将镜头向幼蝉推进的过程中使用了慢速摄影,画面出现如时间凝滞般的短暂抖动与虚化,仿佛人晃神时的状态。该画面在持续了不到三秒后,镜头突然上移恢复常速,仿佛导演从刚才的晃神中突然回过神来。此时,仍是导演的手持镜头,画面晃动,但值得注意的是镜头的机位明显降低了很多,较之前更贴近地上的植被,仿佛在模拟孩童行走在林中的视点。结合刚才由晃神到回神的镜头设计,导演似在经历一场有意识的穿越性质的梦境体验,即重返记忆中的童年。在《故乡》结尾处,导演则以多个手持长镜头,完整记录下盲人栽树人王惠民上山栽树的行走过程,且镜头时常对准王惠民行走的双脚与贴地的搞头。盲人王惠民在上山栽树过程中,数十年如一日以搞头贴地而行的行走经验,和以锄头植树的原始耕种经验,则是人与土地产生联结的最初方式,因此成为被摄对象们以乡土经验为代表性集体记忆的根隐喻。
在纪录片《渡口编年》系列中,导演遵循“直接电影”现场拍摄的非虚构美学原则,不干预、不介入、不影响生活原生态的发展过程,让摄影机成为静默记录的事件“旁观者”,但是,当镜头进入具有私密性、隐私性的家庭空间,有限内景的封闭性和压迫性,促使被摄对象与创作者之间又具有了情感上的对话性和共鸣性,“私人化”的影像表达却具备了人物形象的普适性和社会价值的公共性,因此,从叙事艺术的审美视角切入纪录片文本,就是从“作者”二十年“拍什么”没有变、“怎么拍”有所变中观照到纪录片不加修饰的“描写生活”的叙事风格,能够感悟到作为“民间记忆”的纪录片作品非同寻常的社会学意义,能够体验到纪录片导演内心世界深处的乡愁情结以及对于普通生命个体的人文性关怀。当众多纪录片导演“凝视”被宏大叙事忽略的普通大众在社会变迁中的生活、挣扎和拼搏,社会基层鲜活的生命形态,才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