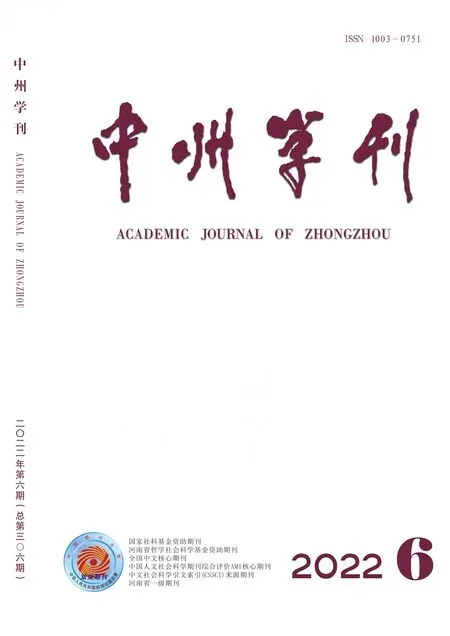“情”“义”相须:孔子情理关系思想新解
贾 伟 玮
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长久以来关注的核心议题。与西方一些认为理性和情感彼此相互冲突的哲思不同,儒家伦理主张情感与理性不可分割,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与平衡,而这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就是“义”的根据。蒙培元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是‘情理’之学。”梁漱溟先生也说:“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智,而以感情为其根本,但却不远于理智——此即所谓理性。理性不外乎人情。”梁先生认为儒家伦理具有“因情而有义”的特质,“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此番论述极为精辟,只可惜未见梁先生深入阐发。学界关于儒家情理关系问题研究的成果虽丰硕,但落脚到儒学开山孔子上仍有待补充。《论语》通篇未见一个“理”字,且前贤多对孔子“情”与“仁”“礼”之间的关系探幽发微,对“义”提及不多。有感于此,本文拟对孔子的“情”“义”范畴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梳理与探讨,并以此视角来思考,以期能丰富儒家情理关系问题的研究,并能对相关问题研究做出补充。
一、从对神鬼的“畏”“敬”到人际的“爱”:孔子对“情”的伦理转化
何谓“情”?“情”是一个形声字,青声,从心。“青”,《说文》谓“东方色也”。东方为“木”,草木之色青,故“青”又代表“春生”,有美好之义。由此可见,“情”字从“心”从“青”,指人心、人性的萌发和外显状态。在介于孔孟之间的郭店竹简出土之前,“情”字很少出现于传世文献及出土资料当中,且作为“情感”义的“情”字也极少见到。《论语》中“情”字二见:“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均为“情实”的意思。而在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情”字出现了20次,且最重要的含义是表示人的情感,可见其对情感的重视是空前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先秦儒家重要文献,《性自命出》重情思想的来源无疑是孔子。
虽然《论语》中的两处“情”的字面意思是“情实”,且未形成像后世儒家那样清晰的性情对举的思想,但实际上,孔子是极重情感意义上的“情”的,只不过他多用具体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词汇或字眼来表达“情”。孔子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不清楚父母的年纪,在因父母长寿而感到欢喜的同时,也要因其年事渐高而感到担忧和惧怕。孔子评价《关雎》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此诗抒发快乐但不是没有节制,表达悲哀但不至于伤痛。《论语·先进》载“颜渊死,子哭之恸”,弟子颜渊短命早死,孔子痛哭,并说:“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形容那感觉就像老天要了他的命一般痛苦。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只有道德高尚的仁者才能真正正确地抒发好恶的情感。他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迁怒,不贰过”,等等——《论语》中所刻画的孔子,恰恰是一位少言“情”字而又时时处处重“情”的思想家形象,而孔子所重的“情”,便是人的真情实感,即与外物接触而形成的与人的生命体相关联的情感体验或心理状态。可以说,孔子的“真情实感”之“情”恰恰是“情实”的引申义,被后儒继承发展之,在先秦便形成了重情的传统:《性自命出》言“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孟子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心”来体认各种情;荀子之“情”从属于“性”,《荀子·正名》里就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意思是人生来便有的未加修饰的自然秉性中的好、恶、喜、怒、哀、乐便是“情”。
此外,作为真情实感的“情”具有三个特质:一是实然性。“情”首先是真与实的,是一个存在于人伦日用之中的实然概念,无善恶价值。二是情境性。因为“情”是经由接触外界事物而引起的情感体验或心理状态,因而人在面对不同的情境时便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就像孟子所讲的突然间看到“孺子将入井”时,人所产生的是“怵惕恻隐”的情感,而非“羞恶”“辞让”的情感。三是差异性。即面对同样的情境,不同的人所产生的情感也会不同,比如,宰我与孔子有关“三年之丧”的辩论,面对父母的离去,孔子认为那种悲恸之情至少要三年才可平复,但宰我认为只需一年即可。由于“情”具有的实然性、情境性以及差异性特质,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情”便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个体的特殊情感如此,影响民众至深的社会情感更是如此。
殷商时期,社会情感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畏”。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天道天命开始。”“情”的初始意涵与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的宗教文化背景直接相关。商代一年也叫一祀,因为各种祭祀活动按照一定的顺序举行完毕的周期刚好是一年,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祭祀,最重要的情感就是对于鬼神的情感。并且对于认知能力和生产能力尚处于低级阶段的远古人类来说,“星坠,木鸣,国人皆恐”,自然界的“斗转星移”“寒暑更替”,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聚散分合”,都会让人们对具有无限威力和不可掌控的天(帝)以及其他未知的力量产生困惑、焦虑和畏惧,从而进行祭拜天地、奉神事鬼的宗教活动,祈祷福佑以及祈求赎罪避祸,人之“情”得以慰藉与纾解,日常生活与政治结构也可处在一种相对安然有序的状态当中。
到了西周,社会情感则集中地表现为民众之“敬”。西周灭商,面对商纣王“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的喟叹,周人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予以回应。“以德配天”的做法,说明周人在保留了对“天”的畏惧之情的同时,也看到了人自身的责任与义务。继而作周礼,来规范人(主要是王权贵族)的衣着穿戴、仪容仪表与行为举止,以建立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维护氏族社会生活的有序与稳定。《礼记·礼运》中说得很清楚:“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舍礼何以治之?”制“礼”实为治“情”,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规范下,人之“情”主要表现为“敬”,敬天、敬德、敬“礼”。相对于商朝,西周外在的祭祀仪式已经相对弱化,但人内在的以德配天、敬鬼神的情愫得到强化。时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有很多,但作为社会情感来说,“敬”是最重要的。
相较于殷周之“情”,孔子之“情”更加生动与鲜活。因为孔子在继承发展周礼的同时,认识到了人的主体性价值,从而对“情”进行了转化发展。一方面,孔子把以前传统的以神鬼为本位转化为以现实的人为本位,以人与人关系的调解为主要思考对象;另一方面,在孔子之前,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置和买卖奴隶,从不把奴隶当人看,孔子以人的现实生活为本,其思想有面向包括奴隶在内的一切人并建立共同的人道标准的倾向,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歧视与相残。因此,孔子之“情”是根植于人的个体生命中普遍认同的情感,其主要表现为“爱”。孔子之学通常也被称为“仁学”,《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曰:“爱人。”“仁”是沉浸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对他人的“爱”之真情。方东美先生称:“儒家之‘德’透露亲切而和谐的关系。”此所谓和谐关系即“仁”之可以“化人为亲”,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结会促进社会伦理秩序的和谐。“情”是“仁”的核心依据,也就是孔子所言道德生命的内核。
孔子之“仁”离不开“情”,孔子所重之“礼”也与“情”不相离。林放请教孔子何为礼的根本,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朱熹《论语集注》引范氏(宁)曰:“俭者物之质,戚者心之诚,故为礼之本。”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隋书·高祖纪下》曰:“礼有其余,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杨伯峻《论语译注》译“易”为“仪文周到”。意思是说,仪文周到、奢华只是外在表象,真情实意才是深层本质。并且可以看出,当个体情感与礼制产生冲突时,孔子关注个体情感之真甚于礼制规范之严,关注情之“爱”甚于“敬”,说明礼的本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人情的笃实及其应然秩序,礼的形式要服从于情感的真实。
孔子对人的内在情感世界进行开掘,将“情”作为根植于人的生命体的基础、实体和本源,使人文世界的代表由三代“神本”之“礼”转向了春秋季世安放于人的内在世界的爱人之“仁”。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孔子发现,原来的周礼是覆盖人跟天交往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失去了对天的“敬”,周礼只能作为外在规范而徒具苍白的形式,逐渐走向崩坏的境地。孔子以“仁”释“礼”的实质是援“情”入“礼”,也就是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自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和值得注意的是心理情感原则,它是孔学、儒家区别于其他学说或学派的关键点”。

二、从“神本”到“人本”:孔子对“义”的理性发掘


在前述母体之上,孔子发展出儒学之“义”。孔子喜《易》而“韦编三绝”。《帛书·要》载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孔子重《易》之“德义”而后其“祝卜”,这是对《周易》进行的理性解读与哲学改造。《帛书·要》载孔子曰“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孔子将人之德行仁义与《周易》之福、吉相连——君子观天地之象,然后推至人伦之则,人便拥有了普遍的主体性。而“义”则被看作是天、地、人三才中人之范畴的伦理正义、规范原则:《易·说卦》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易·系辞下》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意思是说仁义之于人道就相当于阴阳之于天道、刚柔之于地道。人的思想意识始于天道、地道,终于人道,由于“人能弘道”,人因而获得了道德主体性,人道最终指向人之仁义道德。如此一来,德与福相连相生,《周易》的卦爻象占获得了新的解读,为儒家践行“义”而获得福佑的思想生发提供了土壤。换言之,德行仁义代替了古时祈祷占祝于鬼神,成为人们积善成福的新途径。这不仅是哲学思想的创造,更是文化与传统的更新;这不仅奠基了儒家价值范畴体系的初步建立,更意味着其价值范畴可以由天上神灵法宝下落成为人间的法则。


其一,应然性。孔子说“义者宜也”,义的本质即规定性、适宜性与恰当性。“义”首先规定了一种“应当”,是必须遵守的刚性原则。《论语·里仁》中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什么是必须、务必要去做的,也没有什么是一定、绝对不能做的,只要是合适的、恰当的就是符合“义”的,就是对的、可以去做的。《论语·卫灵公》曰“君子义以为质”,“义”是孔子强调的君子道德人格的必备条件。


其四,审美性。孔子说:“义者宜也。”“义”不仅是道德的、理性的,而且是得宜的、得当的,是在一定的价值判断与理性节度之下的合理行为,体现着人伦关系当中知分寸、懂进退而达到的和谐有序、恰到好处的审美境界。清段玉裁注“义”说,“義,从羊,与善、美同意”,“义”字在其产生之初便具有了善与美的意涵。《论语·阳货》载:“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虽然“勇”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也必须有“义”对其进行裁制,否则便会产生为盗作乱的结果。“义”是其他诸德的“标尺”,使诸德适度且合宜。《论语·述而》载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是“义”的应有之义,是衡量情境、事理以求不偏颇之宜,在“共学”“适道”“与立”和“经权”四个层次中最难把握。不偏颇之“宜”即为“中”,要求根据主客体、主客观条件综合权衡下的无过无不及,就像孔子所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
其五,合理性。所谓合理性,就是与理性相合。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是人际交往中必须遵守的制度规范,是社会理性的外在表现。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对自我情感、自我感性欲望的约束,弘扬的是社会理性精神。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义是礼的精神内涵,无论是在主观上认识道,还是在客观上认识万事万物之理,都离不开“义”,因为“义”是人在主客观相统一之下做出价值判别的理智能力。以礼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体现的正是人之为人的理性。孔子所说的“人”是具体的、鲜活的、有真情实感的,除了具有生命存在的价值之外,还具有“异于禽兽”的人格特质,能够通过外在“礼义师法”或者内在道德自觉来完成理性对感性的约束。这一点后来被荀子揭示得更加明确,《荀子·王制》曰:“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义”是人贵于禽兽的关键因素,是理性的要求对感性欲望的节制,体现了先秦儒家所共有的理性致思。孔子之“义”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德之为德”的原理,充分彰显了人作为主体的理性之美。
三、“情”“义”的张力与统一:“义”本于“情”而节“情”

1.“情”为“义”始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人们的情感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呈现出从对鬼神的“畏”“敬”向人际间的“爱”的流变,“义”的观念也存在一个由“神本”向“人本”的转化过程。真实的情感和心理状态是孔子“义”观念的生成本源和伦理起点,“义”观念的转变也正是孔子通过对原始宗教情感的价值转换来完成的。
同时,孔子又对人的孝亲情感进行了开掘。人的道德情感是自然情感与社会情感的有机统一。孔子发现,以“孝”为核心的血缘亲情便是由自然延伸到社会的原发性情感,是儒家家庭伦理走向社会伦理的关键因子。“义”作为人伦日用之纲,生发于家庭血亲之间的亲亲之“情”。

其二,人们普遍具有的“报”的心理情感,也是“义”之生成基础。“报”是报答、回报的意思,《诗经·蓼莪》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对子女有生育、养育、教育之恩,对孩子予以关爱与付出,大多也成为孩子的榜样,子女对父母行孝道便是出于自然亲情之爱与感恩之心的“报”的体现。《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报本反始”即受恩思报,不忘自己的生之所自来,并与自己的生之所由遂相统一,是根源于孔子最为重视的深厚的血亲之“爱”的情感向生之始、性之初的一种升华。前面已经提到,经由孔子改良的祭祀,其对象已经由天帝鬼神变成了自家祖先与逝去的亲人,目的是借爱与敬等真诚情感的发用而尽一己之德,意义在于报本反始、崇德报功,即《论语·述而》所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义”由产生之初“人鬼两相安”的意涵,到孔子之时发展为“人道之所宜”;换言之,即为“人人两相安”。《论语·阳货》载,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一年就可以了;孔子虽然坚持“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的礼制原则,但对宰我的回应是“女安则为之”。“宁戚”、心“安”则为。喜怒哀乐等情感发用合度无憾才能安,“安”是“义”要达到的内在心理情感状态,正所谓“心安而理得”。孔子的用意,一方面是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做出退让,另一方面则是为礼做出的新的价值探寻。“义”作为“礼”之内质,在新的历史境遇下为礼提供弹性与创新性,这是孔子面对社会现实做出的思考。
2.“义”为“情”节
作为实然的、随境遇变化的、具有个体差异性的“情”,在其进入人的群体社会道德生活时便会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如虚假的“情”、或过或不及的“情”等,都会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与混乱;“义”作为一种理性的判别力,一方面能够判别真情与假意,另一方面能调节“爱”的范围与程度,是端正思想行为的规矩,也是提高道德修养的必要环节。

在辨识排除了虚情假意后,哪怕是作为人道之肇始的真挚情感,也必须受到规范与节制,否则其流弊就大。因为“情”虽真,但也有哀乐、喜怒之分,人在不同的情感状态下会做出不同的行为,所谓《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里“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好与恶、爱与恨,是人所普遍具有的对立情感,处理不当便会失衡失序。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可以说,“爱人”是儒家仁学处理人我关系的第一准则。然而,孔子的“爱”是有差等的,并且隐含着恶或恨。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存在需要爱和值得爱的人,也存在可憎、可恨的人,还存在一些既不需要爱也不值得恨的人。如果将“仁”作为第一伦理规范推扩到一切人都可使用的范围,那么仅有爱的原则,便不足以应对各种复杂的现实状况。孔子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也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具备仁德的人,是具有公心、不以个人私情为主的,能够公正地做出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仁者”不仅知道如何去爱,也应懂得如何去恨;既能好其所当好,也能恶其所当恶。只有“仁者”能做到爱与恨的统一。这里的“能”与“察”便是价值判别的理智能力,是“义”的价值导向作用的凸显。

然而,在孔子高倡“泛爱众”的整体基调下,“义”对“仁”的节制作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受业于孔门后又“非儒”的墨子,便将孔子的有差等的、能恶的爱,“膨胀”为毫无差别的、一刀切的“兼爱”。被孟子及时发现后骂其“无父”,并高举“义”旗,将“义”提高到与“仁”横向并列的地位。《孟子》载:“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
孟子的“义”,是为自己的不善感到羞耻、为他人的不善感到厌恶以及有所不为、有所不爱,是对“爱人”之情的理性节制与平衡。这与荀子的“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异曲而同工。
四、“情”“义”相须:情理的融合与平衡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