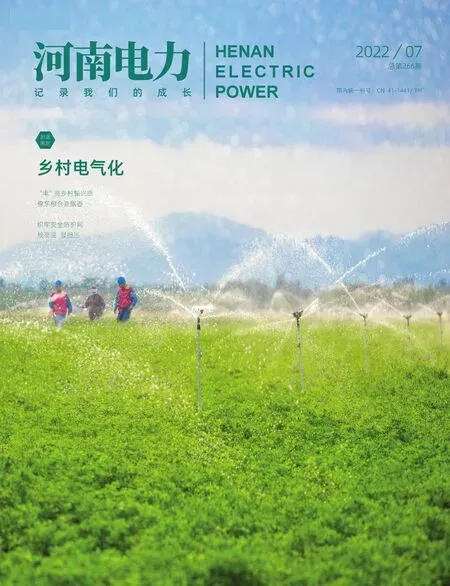关于电影的记忆
文_乔 桥 图_赵亚楠
20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于一个豫北农村。小时候,我是村里同年龄的娃娃头儿,精力充沛体力旺盛,调皮捣蛋的事没少干。每天一放学,常常是领着小伙伴儿们从村子的这头一口气飞奔到那头,或者拿了弹弓,溜到村边的树林子里,和护林的老大爷捉迷藏,把才长得半大的青枣儿偷来做子弹打知了,抑或一起隐蔽在一个角落,瞅见谁家的女孩子路过,就一起用小石子儿往她身上扔,再者上到树顶上掏鸟蛋,到村南的河里摸鱼捉虾……似乎一刻也闲不下来。
回想当时,能够让我和伙伴儿们停下来喘一口气,安静地待上一两个小时的,似乎只有电影了。
那时的电影,很多还是黑白片子,色彩显得单一了些,但因为稀有,人们热情不减。附近的十里八村,谁家有了喜庆的事情,都以能够出得起钱放一场电影而自豪。观众也很捧场,会早早去占位置,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讲,只要有电影,哪怕不吃晚饭,也会早早地赶去,往往是深更半夜回到家,才想起当天的作业还没做。
那个时候,能看电影已是意外之喜,新影片更是少有,大多是一部影片反复播放。尽管如此,甚至有时候能够提前打听出片名,有的片子看过了不知道多少遍,但也是必去的。有好多电影,我和小伙伴儿都把部分精彩的台词背得滚瓜烂熟,玩儿的时候,也往往是模拟战争题材片子的某些情节。在当时,我实在弄不明白,那个神秘的白色幕布为什么让我们如痴如醉?


生活就是那么富有戏剧性。高中毕业后,我因为字写得好,被乡里的电影院聘去写海报。我的那帮伙伴儿们也兴奋异常,在他们看来,自己终于在电影院有了熟人,一个能够帮他们弄几张紧俏的电影票,甚至有时候能开开“后门”,让他们享受一次免票的人,我的威信也一下子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实,那个电影院更像是一个破败的大仓库,天花板吊得特别高,老式的吊扇在上面飞速地旋转。你不能看它,因为总感觉它摇摇晃晃的样子似乎要趁你不注意掉下来,看一眼,就会胆战心惊。地板上是一排排硬木做的椅子,每次观众入场和退场都会噼里啪啦乱响一阵。几扇木制的窗户也已经合不拢了,白天放电影时总有几缕刺眼的光芒从那里射入。漫长的夏季里,电影院里充斥着汗酸味和体臭味。但是,梦幻竟然就在这样的地方神奇地制造出来了。
那时的电影院都是当地首屈一指的繁华之地。一旦有新片子上演,电影院门前便人头攒动,电影票更是供不应求。印象中电影票最难买的要数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了,那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武打片。连着几天,电影院门前总是人山人海。那时候,人们几乎没有排队的习惯,所以身强体壮的大汉往往被委以重任,负责到窗口购票。小小的窗口前伸满了攥着零钱的手臂,如果谁能够从大汉们的缝隙间抢购几张票,肋骨往往会疼上好几天。而这个购得票的人往往会得到同伴们的感激,合伙把他的票钱给凑出来。有时,人们推推搡搡过了分寸,打起架来也是常有的事。
如今,电影无论是拍摄还是制作手段都与过去不同,先进技术更是层出不穷,效果常常让人倍感惊喜,电影院也变得金碧辉煌,各种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带来的观影体验与过去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全家团圆时,一起去影院看场电影,也成为很多家庭的一致选择。
但是,午夜梦回,我还是会怀念儿时的电影,怀念那时的电影院。那些关于电影的记忆存留在我脑海深处,代表的是一段岁月,是年华逝去时的一种情怀,是对过去的认可,也是面对未来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