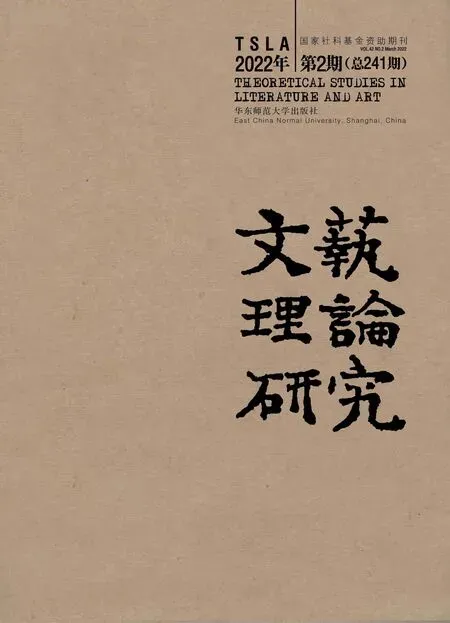从“可知的儿童”到“难解的童年”
——论儿童问题与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
赵 霞
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当代化进程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启动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进程。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学科经历了从学术地位到研究格局的巨大变迁。短短几十年间,儿童文学研究从弗兰西莉娅·巴特勒(Francelia Butler)所说的“局外”(excluded)状态起步,迅速建构起自身的理论批评体系,并日渐成为西方文化批评的话语焦点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问题既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关切,也在根本上推动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持续分化、深化。与此同时,正是伴随着理论和批评的演进,儿童文学层面的“儿童”不但作为一个基础的观念,更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以及一种深刻的批评精神,不断得到创造性的发掘与建构。理解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演进,“儿童问题”是基础问题,也是根本问题。
一、 儿童文学批评与有关儿童的知识论
“一切儿童文学批评,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与儿童有关的意图表达。”(4)凯琳·莱丝尼克-奥贝斯坦(Karín Lesnik-Oberstein)在其知名的《儿童文学: 批评与虚构的儿童》(’:)一书中提出的上述论断,指明了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某种基本属性。如果说现代儿童文学的文类发展始终与“儿童”观念的历史紧密缠结,现代儿童文学批评则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通过揭示儿童文学内含的这一“儿童”概念的性质、内涵等,论证儿童文学独特的文类身份,廓清儿童文学合法的艺术与文化内容。19世纪初,英国作家莎拉·特里默(Sarah Trimmer)在其创办的《教育卫士》()杂志上发表的童书评论,作为现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滥觞,其贡献之一即是突显了“儿童”观念之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意义。认识到由于儿童是有别于成人的个体和群体,因而有物质和文化方面的特殊需求、要求,进而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考虑如何落实、体现这种需求和要求,是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起点。
但这个起点本身,恰恰包含了巨大的复杂性。正如当代批评家M.O.格兰比(M.O. Grenby)与金伯莉·雷诺兹(Kimberley Reynolds)在其合作主编的《儿童文学研究手册》(’:)序言中所说,作为儿童文学前缀的“儿童”一词一经提出,便带来了更复杂的问题: 这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儿童”,究竟是“哪个儿童”?是“文本中的儿童”还是“作为读者的儿童”?“如果是指后者,究竟是其阅读反应有待探究的真实读者,还是叙述建构的隐含读者?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过去的童书文本,其真实读者又是谁?是此书针对的原始读者、当下读者还是二者兼有?这些儿童的年龄段如何?年龄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吗?年龄、代际意味着什么?”(4)事实是,与儿童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密切相关的“儿童”一词,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儿童文学批评的巨大难度。“在有儿童书籍以前,必须先有儿童。”(Townsend1)同样,为了理解和界定儿童文学,首先必须理解和界定它所对应的“儿童”。
因此,从现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诞生伊始,其理论的探究就对应于一系列有关儿童的知识论。这个儿童,既是生理和心理的儿童,更是文学和文化的儿童。
早期儿童文学批评深受儿童教育传统和观念的影响,对掌握上述“儿童”知识论怀有一种朴素的雄心。这一时期儿童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将儿童视为教育规训的对象,并从这一教育和规训的角度,理解、要求一切与儿童有关的文化事务,包括儿童文学。莎拉·特里默本人即是约翰·洛克教育学说的信徒。洛克在《教育漫话》中精细规划的完美孩童,正是特里默在其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致力于认同和传播的儿童观念。在《教育卫士》的书评部分,特里默确立了现代儿童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和职能: 通过揭示儿童应该(适合)读什么,不应该(不适合)读什么,来划定“儿童”身体及其精神的边界;这个边界,同时决定了儿童文学的边界。特里默对其“儿童”对象的宗教、政治及文化边界的认定高度明晰,这种明晰性,也是早期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她的反对幻想的儿童文学批评观,在18、19世纪的西方儿童文学界影响深远。一方面,认为儿童应有专为他们提供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作品,这类作品应从传统的教育读物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又认为儿童不适于接触虚妄的幻想,认为现实生活和理性规则才是儿童最恰当的精神养料。在特里默亲身创作的《寓言故事》(又名《知更鸟一家的故事》)里,我们清楚地见证了这种文学观念内含的矛盾: 它既是一个想象的童话故事,又不断地反对、解构着自身的想象。
如果仔细辨认,这一文学观所对应的,其实正是启蒙主义时代得到重新发现和界定的新儿童。在洛克的《教育漫话》里,在卢梭的《爱弥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儿童的身影。《教育漫话》和《爱弥儿》对于儿童生活巨细靡遗的观察、总结与管理、安排,与莎拉·特里默、玛丽亚·埃奇沃思等18、19世纪作家笔下生活和道德轮廓分明的儿童,以及特里默批评中依照宗教、政治、道德等规范精雕细刻的儿童,实为同一。这个儿童,既被赋予空前充分的关注,也被施予空前严格的管控。
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当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上述传统儿童观念及相应儿童文学艺术边界的重新认知与划定。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西方儿童文学的创作和阅读早已越出特里默设定的边界,反过来促发着儿童文学领域新的批评思考。20世纪30年代,两部著名的儿童文学研究著作的出版,奠定了儿童文学批评语境下“儿童”一词的新内涵。1932年,哈维·达顿出版了首部系统的英语儿童文学史研究著作《英格兰童书: 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同年,并非专事儿童文学研究的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出版了儿童文学领域知名的理论著作《书,儿童与成人》。这两部著作对英国及欧美儿童文学发展史的梳理,奠定了20世纪西方儿童文学史述的基本线索与价值观,其中对于儿童文学的幻想及荒诞艺术的高度肯定与张扬,则代表了儿童文学批评观念历史性的转折。在《英格兰童书》中,达顿将荒诞无稽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爱丽丝镜中奇遇记》认定为儿童文学从教育主义走向“自由想象”(liberty of thought)、从道德训诫走向“纯粹欢乐”(the pleasure itself)的艺术革新与精神转折的标志。(263—269)这一观念在C.S.刘易斯的《论儿童文学的三种写作方法》(“On Three Ways of Writing for Children”, 1952年)一文、科妮莉亚·迈格斯等的《批判儿童文学史》(’, 1953年)、珀西·缪尔的《英语童书: 1600—1900》(’:, 1954年)以及约翰·罗威·汤森更富影响力的《英语儿童文学史纲》(:-’, 1965年)等著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进而成为当代英语儿童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立场。在《书,儿童与成人》第一卷,阿扎尔专辟“当想象力遇见理性”一章,为儿童文学中与荒诞幻想有关的阅读快感正名,同时指责儿童文学传统中理性对想象力的扼制。“我们难道不想被带到更遥远的地方,游走在犹疑不定半梦半醒的灵魂中,飘荡在无法识别真实和虚幻的自我、无法分清现实与梦幻的奇妙领地?”(阿扎尔198)这一呓语式的抒情,表达的是与特里默的时代截然不同的儿童文学艺术主张。在这里,幻想、荒诞与现实、理性分庭抗礼,文学想象不再只是作为现实生活的投映或寓言,而是拥有了另一片自由的空间,一个“犹疑不定”“半梦半醒”的“奇妙领地”。
对儿童文学来说,幻想与荒诞是重要的艺术话题,但绝不仅是纯粹的艺术问题。承认幻想、荒诞在儿童文学艺术表现世界里的合法性、合理性,甚至是优越性,一方面大大拓展了这一文类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承认儿童拥有幻想和荒诞的权利,承认儿童的身体和精神世界里存在与此密切相关的特殊维度。与相对可见的现实世界和相对可知的理性生活相比,幻想世界的神秘未知与荒诞世界的不成逻辑,赋予童年另一重现代面貌与现代内涵。太阳底下有了阴影。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重新打量一个孩子及其代表的童年世界。儿童喜欢阅读什么样的文学?儿童如何阅读文学?更进一步,成为一个阅读中的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批评者们从作家、作品、阅读活动等不同角度,尝试提供更丰富、准确的解答。罗杰·兰赛林·格林的《故事讲述者》(, 1946年)、吉奥弗瑞·特里沙的《课外读物》(, 1948年)等著作,一方面试图从个人和集体阅读经验的视角,为更准确地理解儿童的阅读及阅读中的儿童提供新的注解,另一方面则从这一新的儿童理解出发,提出对于儿童文学的文学标准和艺术要求的新认识。李利安·H.史密斯在其影响深远的《欢欣岁月》(1953年)一书中回应安妮·卡洛·摩尔对传统童书的批评,认为过去的许多童书“之所以常常会得到成年人的褒扬,是因为它们折射着成年人对社会问题的真诚关注,而并非因为它们本身的主题是对童年自发地关注”(35)。她进而向儿童文学批评提出了确立新的批评标准的要求。
对儿童文学文学性的日渐关注,以及对于其文学表现空间、价值的重新认定,带来了当代儿童文学批评观念的两个重要标志。第一,认为儿童文学应以儿童为艺术表现的中心,从儿童的目光、视野、角度出发,反映儿童及其生活世界的情状。第二,认为在追寻上述文学表现的道路上,儿童文学的第一要务不是教育儿童,而是娱乐儿童,不是用成人的意志塑造儿童,而是要创造属于儿童的欢乐。后来儿童文学批评界熟知的“教育/娱乐”(Education/Entertainment)二分法,随之产生。1963年,玛丽·斯维特的《从启蒙读物到阅读的欢乐——印刷发明至1900年的英格兰童书史》(:’)一书,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分野。当儿童开始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当他(她)在文学的世界里被赋予充分的欢乐权利,儿童作为文化个体的内涵和广延,也得到了新的拓展。教育儿童的文学观念并未就此退场——事实上,任何场合,儿童依然被理解为有待教育的个体和群体——但在儿童文学的批评中,首先是面向儿童的文学乐趣、文学技法等问题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突显。与此相应地,探讨、理解儿童“真实”的文学趣味、阅读倾向、接受特点、接受能力等,成为了儿童文学批评的重要话题和内容。
这里的“真实”一词,隐含的命题是多重的: 第一,过去儿童文学所认识、面向和书写的儿童,并非“真实”的儿童,或者说,是由成人规定和操控的儿童,这其中,儿童自身的真实特点及诉求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认可。第二,“真实”的儿童,或儿童的“真实”状况,在儿童文学的表现世界里是客观可知的对象,是可供儿童文学创作参照的第一蓝本。第三,儿童文学应该致力于理解、反映、书写这个“真实”的儿童,进而为儿童建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世界。为了把握这个“真实的儿童”(the real child),20世纪70年代,一种朴素的儿童阅读研究在儿童文学批评界蔚然成风。从尼古拉斯·塔克的《儿童阅读小说的反应》(“How Children Respond to Fiction”, 1972年)、迈尔斯·麦克道维尔的《儿童小说与成人小说的本质区别》(“Fiction for Children and Adults: Some Essential Differences”, 1973年)等文到调查报告《儿童阅读的趣味》(’, 1975年)、玛格丽特·米克等编写的《儿童阅读模式》(:’, 1977年)、阿瑟·艾坡比的《2—17岁儿童的故事观》(’:, 1978年)等,相关研究揉合了其时风靡的儿童心理学(尤其是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接受理论等学说,对操作实践的关注远大于理论本身的建构企图。研究者们怀着良好的愿望,致力于勾勒、描画儿童文学背后那个独立、独特的“儿童”,同时揭示文学阅读在儿童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是现代儿童文学批评史上将儿童文学移近儿童主体的重要努力,其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极大地推进了现代儿童文学艺术观及其儿童观的进步。
二、 “不可知”的儿童与“不可能”的儿童文学
在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上,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一方面,试图更准确、深入地把握儿童文学艺术世界的批评努力仍在继续。以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童话的魅力》(1976年)等为代表的研究,不但为人们打开了理解儿童文学虚构世界的新通道,也进一步确证了童年幻想的现实价值。另一方面,对主要局限在教学和阅读实践层面的儿童文学理论水平与批评现状的不满,促使一批研究者致力于推动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研究专业与学科的建制。
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一般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起,儿童文学研究的专业身份和学科地位才开始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可。1970年1月,英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艾登·钱伯斯与其妻南茜·钱伯斯共同创立了英国首家儿童文学专业研究刊物《讯号: 童书研究方法》(:’)。同年,由艾克塞特圣卢克斯学院教师西德尼·罗宾斯创立的《教育中的儿童文学》(’)杂志在英、美两地同时发行。也是在这一年,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成立,由时任法兰克福大学儿童与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的克劳斯·多德雷尔任会长,并于1971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了首次大会。1971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成立儿童文学分会,并于当年举办首次研讨会,这是当代欧美学术界开始承认儿童文学学科地位的一个标志事件。1972年,在弗兰西莉娅·巴特勒的推动下,美国首个儿童文学专业学术刊物《儿童文学》(’)创刊。此前西方学界涉及儿童文学评论的刊物,多为面向图书馆及大众阅读服务的期刊,包括1963年创刊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会刊《书鸟》()杂志,主要也以介绍地域儿童文学作家、作品、出版状况等为主。上述三种学术刊物的创立,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一门专业学科的新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学术土壤。其后三十年间,它们成为了儿童文学专业研究与交流的重要园地,并见证了这一研究队伍的迅速壮大及其研究视野、能力的迅速拓展。这一阶段,通过汲取、借用文学研究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资源,并将其迅速转化为儿童文学的批评话语和方法,研究者们不断发现、发掘着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文本的巨大理论潜力。至1980年代,以英美学界为主导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已经全面步入新的理论话语时代,并且开始迎来杰克·齐普斯称之为儿童文学批评“革命”的阶段(Zipes205)。
这一批评“革命”的冲击力,或许超出了当时整个儿童文学界的想象。1984年,女性主义作家、批评家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出版了著名的《彼得·潘案例,或论儿童虚构文学的不可能性》(,’)一书。该书基础是罗斯在法国索邦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出版和进一步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野。原本正在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中变得日益坚固的当代儿童文学观及其儿童观,在此书中遭受了根本性的摇撼与质疑,其结果是,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理解儿童文学及其背后的儿童问题。西方儿童文学批评自此步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后罗斯”时代。罗斯以《彼得·潘案例》一书,对当代儿童文学写作及批评所持有的“真实”的儿童观念,以及儿童文学试图理解、代言这一儿童的努力,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儿童虚构文学是不可能的。这并非因为它不能被创作(这么说就太荒唐了),而是因为它紧握着一种不可能性,又不敢将其道出——那就是成人与儿童之间不可能的关系。”(Rose1)罗斯所说的这一“不可能的关系”,乃指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作家试图代表儿童进行的各种文学表述,因其成人身份与儿童身份之间不可消除的隔阂,而成为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表述。作为西方儿童文学经典的《彼得·潘》以及围绕着它形成的全部儿童文化合集,共同塑造了一个永恒的儿童形象,但在罗斯看来,这个儿童恰恰是非儿童的,甚至是儿童的否定。“《彼得·潘》写的是儿童,却从未真正朝向儿童讲述”(1),其中那个不愿长大的孩子,与其说是“真实”的儿童表达,不如说是成人愿望中的儿童。最终,这部“不可能”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西方经典儿童文学的书写传统,仅仅成为了成人对于儿童的欲望投映。尽管J.M.巴里、刘易斯·卡洛尔等儿童文学作家的恋童倾向一向是学界讨论的话题,罗斯却并非仅在狭义的“性”的意义上使用“欲望”一词,而是借它指称“成人施诸儿童的一种投资形式,以及作为这一投资的结果,成人向儿童提出的要求。这一要求将儿童固定下来,保持在一个确定的位置。”(3—4)在罗斯看来,一切成人创作的儿童文学,无不是成人对儿童的想象、挪用、侵占和固化。“如果说儿童虚构文学在文本内建立了一个儿童的形象,那么其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文本外的那个儿童,后者恰恰是不容易掌控的。”(2)由于从根本上看,儿童对成人而言是不可知的,“儿童虚构文学的背后并无儿童”(10),因之,儿童文学也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文类。
罗斯的女性主义背景在《彼得·潘案例》一书中显露无疑。某种程度上,她是将女性主义中的激进批评挪用至儿童文学的语境。儿童与成人的身份对立,等同于罗斯笔下女性与男性、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身份对立。在后来的批评中,这种“儿童-成人”的二元对立遭到了进一步的批评。然而,对于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而言,其最重大的意义并非指出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身份分裂——对于儿童文学中成人代言者的意识,实际上由来已久,诚如莱丝尼克-奥贝斯坦所说,儿童文学批评的核心,也是该领域内以及围绕它展开的一切争论的核心即在于,“儿童文学是成人为儿童写作的文学”(3)。《彼得·潘案例》的意义在于,通过提出儿童“不可知”与儿童文学“不可能”的激进论断,拷问儿童文学语境下一种“‘可知’的、一元的儿童读者观念的假设”(Lesnik-Oberstein4-5),进而激起人们关于这一代言行为有效性的反思,并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儿童”以及与之相关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复杂性、多层性、甚至是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儿童虚构文学源于这样一种观念: 儿童和世界是可知的,其可知的方式是直接和无缝的。该观念将儿童的天真与一种原始状态的语言和(或)文化紧密关联,并使它们彼此依赖。这一观念影响了迄今为止的儿童文学写作以及我们对儿童文学的看法。”(9)罗斯将这一观念的源头上溯至18世纪以来欧洲现代儿童文学的全部发展史,以及以洛克、卢梭为代表的现代儿童观思想。
《彼得·潘案例》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走向新转折的突出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儿童文学理论家彼得·亨特就指出了“儿童文学”的命名中“儿童”与“文学”二词间的彼此重塑、相互矛盾及其谐调关联的难度。(“The Mayne Game”10-11)1984年,彼得·亨特发表了知名的《儿童主义批评》一文,以“儿童主义”一词强调儿童文学批评重新理解儿童、走近儿童的必要性。(“Childist”44-46)加拿大儿童文学理论家佩里·诺德曼在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定义儿童文学》一文中,也强调了“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统一概念的界定困难。(“Defining”184)在诺德曼随后的批评中,这一针对儿童文学及其对应的儿童概念的反思,贯穿始终。事实上,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已开始有意识地将当代童年研究(尤其是法国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童年史观)、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资源引为己用。这一过程中,儿童文学逐渐确立起了一个重要的当代研究观念,即关于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建构性的意识。《彼得·潘案例》正是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观念从“本质的儿童”(the essential child)转向“建构的儿童”(the constructed child)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代表性的研究文本。
然而,从《彼得·潘案例》开始,有关儿童的知识论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下开始遭遇空前的危机。当现代儿童观念的坚固性遭到摇撼,现代儿童文学在艺术和文化上的合法性也面临新的质疑。在罗斯看来,由于儿童问题的“不可能”解决,现代儿童文学迄今为止的艺术进程其实只是技法的进步,究其儿童观念的实质,则并未发生真正的革新。罗斯之后,一部分学者继承其激进姿态与思想,致力于通过揭示当代儿童文学及其儿童观念的“伪儿童”性质,质询、批判儿童文学的写作与批评。莱丝尼克-奥贝斯坦的《儿童文学: 批评与虚构的儿童》是其中影响最广的著作之一。作者将罗斯的激进方法由儿童文学艺术进一步延伸至批评领域,认为不但儿童文学、整个儿童文学批评同样建基于一个“可知的儿童”的虚幻观念。该书追溯了儿童文学及其批评语境下“真实儿童”观的由来,进而质疑了这一“儿童知识体系的边界”(Lesnik-Oberstein142)。由于当代儿童文学批评赖以建基的这个普遍、可知的“儿童”概念本身是不存在的,因此,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也是一项“不可能”的活动。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莱丝尼克-奥贝斯坦带领英国雷丁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团队出版了一系列批评论著,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苏珊·霍尼曼在其《难解的童年: 现代小说中不可能的表征》(:)一书中,则将罗斯的批判由儿童文学拓展至更广泛的一般文学领域,通过解读亨利·詹姆斯、马克·吐温、威廉·戈尔丁等作家笔下的儿童,探讨文学作品中童年表征普遍的“不可能性”,以及它所揭示的文学和文化问题。
关于儿童“不可知”与儿童文学的“不可能”性的批判,带来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观念的巨大振荡。如果说其时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文化建构性质正在得到日益普遍的认可与不断深入的探究,那么以罗斯、莱丝尼克-奥贝斯坦为代表的“不可知”论与“不可能”论,则向批评界进一步提出了以下观念的反思。第一,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儿童观念,是否总是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对现实儿童的某种概化、约减?假使一切儿童只能以观念的形式进入我们的文化书写和认知,那么,如何认识、看待这一儿童的观念,如何赋予它相对于现实的合法性、合理性?第二,更进一步,儿童文学中所谓“现实”或“真实”的儿童,在文本之外是否真实存在?换句话说,儿童文学中看似虚构的书写,是否反过来决定着儿童存在的真实面目?这也是为什么罗斯说“儿童文学不应被理解为对于儿童(童年形象)价值与观念变迁的消极反映。相反,我将它视为我们建立自我与语言、形象之间关系的核心途径之一。事实似乎是这样的: 对儿童形象来说,并非儿童第一,形象第二,而恰恰是为了形象的欣然完满,才有了最适合的儿童代表。”(Rose138-139)这可能意味着,儿童文学的虚构之于现实童年的面貌,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儿童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儿童文学的观念也并非孤立的亚文类观念。罗斯等人批判中的那个“可知”的儿童,远不只与儿童有关,它还揭示了我们社会文化和观念中的某种普遍疏忽与缺失。“童年同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索引词汇,它掩盖了儿童以及我们都身处其中的这一切的多样与复杂。”(10)就此而言,儿童文学的“不可能”论除了揭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问题,对于包括成人在内的整个社会和文化生活来说,还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诘问和反思中,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关于“何为儿童”“何为儿童文学”等基本命题的认识和解释,经历了意义重大的丰富与革新。
三、 儿童与儿童文学的再定义: 作为一种方法和精神的“儿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入了空前蓬勃的发展时期,其主要的表现,一是研究队伍与论著出版巨量增长,二是研究话题与研究领域迅速扩大,三是学科身份与学术地位显著提升。这一时期至今的儿童文学研究出版物,覆盖儿童文学的艺术研究、文化研究、教育应用、图书馆服务、阅读推广、创作指导、市场出版等各个领域,论域广泛,论题多元,并且以其强大的学术延展性和生长力,逐渐引发整个学界关注。但另一方面,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又无时不怀着为“儿童文学”及其赖以存在的“儿童”观念重新正名的焦虑。事实上,从《彼得·潘案例》出版起,关于儿童的“不可知”论与儿童文学的“不可能”论的讨论,就构成了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有影响的儿童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彼得·亨特的《儿童文学》(’, 2001年)、杰妮特·梅宾与尼可拉·J.沃特森合作主编的《儿童文学: 方法与界域》(’:, 2009年)、金伯莉·雷诺兹的《儿童文学简论》(’:, 2011年)、帕特·平森特的《儿童文学》(’, 2016年)等,均将罗斯、莱丝尼克-奥贝斯坦的“不可能”说视为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中,如何重新理解、界定当代视野下的儿童与儿童文学,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罗斯的批判在现代儿童文学及其儿童概念的坚固性上敲出了第一道显而易见的裂缝,其统一性一经打破,随即激起了理论界极大的探究热情。研究者们开始从各个可能的视角、方向、层级等,发掘儿童文学语境下童年概念的“未知”内涵。在这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潮流中,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以降单纯、天真的童年观,迅速分裂为另一个充满多元维度与统摄难度的复杂对象。
首先,童年不再意味着依照特定社会文化规约配给的特定隔离时间与空间,而是融入广大的生活世界,并且成为其中普遍、基础而重要的社会文化符码。菲利浦·阿利埃斯与尼尔·波兹曼都认为,现代童年的观念始于某种将成人与儿童相“隔离”的努力,不论这种隔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抑或媒介的途径。某种程度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则不断地质疑、打破、消解这种“隔离”,以期恢复儿童与完整的生活世界之间的丰富关联。一方面,通过重新探讨儿童文学题材、手法等的禁忌和边界,恢复童年日常生活的真切与复杂,同时也是恢复日常生活中儿童个体的丰富与生动。另一方面,通过揭示儿童文学叙事背后的宏大文化讯息,揭示儿童意象更广阔的文化蕴涵与深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克劳迪·纳尔逊的《女性伦理与英国儿童小说: 1857—1917》(:’, 1991年)、B.L.克拉克的《校园故事的性别重建》(:, 1996年)、R.S.特瑞兹的《唤醒睡美人: 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 1997年)、克里斯蒂娜·巴希莱卡的《后现代童话: 性别与叙事策略》(:, 1997年)、B.L.克拉克与玛格丽特·伊戈内主编的《儿童文学与文化中的性别》(,,,:’, 1999年)、克莉丝汀·维尔奇-斯蒂伯斯的《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话题》(’, 2002年)、约翰·斯蒂芬斯主编的《男性之道: 儿童文学与电影中的男性气概书写》(:’, 2002年)、肯尼斯·B.纪德的《塑造美国男孩: 野蛮故事与男童学》(:, 2004年)、盖尔·伊彤的《儿童传记读物中的女性形象》(-:, 2006年)、劳伦丝·塔莱拉赫-维尔马斯的《维多利亚时期童话与奇情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塑造》(, 2007年)、维多利亚·弗拉那甘的《儿童文学与电影中的易装现象和性别化的身体》(:-’, 2008年)、安妮特·瓦那梅克的《儿童文学与通俗文化中的男孩: 男性气质、异斥与虚构的儿童》(’:,,, 2008年)、凯瑞·马兰的《儿童小说中的性别困境》(’, 2009年)、乔·萨特利夫·桑德斯的《规范女孩: 理解经典孤女故事的源头》(:, 2011年)等著作的出版,通过持续、深入地探讨儿童文学中的性别建构话题,为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贡献了成果最丰硕、影响最突出的理论分支,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儿童一词及其可能性的想象与理解。此外,从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神话学、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重视角对儿童文学所做的大量探讨,不断揭示出“儿童”一词多层的政治文化内涵,以及儿童在此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身份建构。由此,儿童不再仅是一个独立的形象,而是成为了一个结点,一张网络,牵连着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其次,对于儿童与成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发生了某些重大和本质的转变。传统的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模式在儿童文学研究中早已开始遭到质询。20世纪90年代以来,艾丽森·卢里的《别告诉大人: 反抗的儿童文学》(’-:’, 1990年)、约翰·斯蒂芬斯的《儿童小说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 1992年)、彼得·霍林代尔的《童书中的儿童性》(’, 1997年)、约瑟夫·佐那多的《发明儿童: 文化、意识形态与童年故事》(:,,, 2001年)、佩里·诺德曼的《隐藏的成人: 定义儿童文学》(:’, 2008年)、大卫·拉德的《阅读儿童文学中的儿童》(’:, 2013年)等著作,不断深入成人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儿童文学文本深处,探讨儿童存在于其中的面貌、方式等。这一过程中,儿童背后成人声音的各种形态不断得到揭示,但与此同时,该成人声音的稳固性、权威性也在不断遭受新的质疑。事实上,“成人也跟儿童陷于同一话语之中,不断地与之对话(书写/阅读它),正如儿童卷入各种‘成人话语’一样”(Rudd, “Theorising”369)。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向儿童文学中“成人/全知-儿童/可知”的观念模式提出的批判和指责,正是当代儿童文学批评重新出发的起点。与此同时,运用新的批评方法,人们对于儿童文学所呈现的童年精神世界的理解,也抵达了新的深度。凯伦·科茨的《镜子与永无岛: 拉康、欲望与儿童文学中的主体性》(:,,’, 2004年)、玛丽亚·尼古拉耶娃的《儿童文学中的声音、权力与主体性》(,, 2010年)等著作,从精神分析等角度揭示经典儿童文学文本及传统童年观念中深藏的文化符码。透过这类研究,人们进一步看到,在儿童文学的文本内,成人的控制力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稳当。儿童文学不只是关于儿童的文学,它还暗藏着一座成人精神的深渊。

至此,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语境下的“儿童”早已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基础观念,而是同时成为了切入儿童文学乃至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儿童研究领域取得的大量成果,进一步加强了“儿童”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资源在文学研究中可能发挥的独特功能。可以说,正是围绕着儿童问题,诞生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批理论成果和批评方法,后者进一步为从儿童话题、视角等切入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灵感和支撑。一方面,从一个持续打破传统想象的“不可能”的儿童观念出发,通过不断探问、揭示“儿童”一词的难解内涵,儿童文学研究既打开了儿童文学文本及其艺术的深广世界,也建构着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难解的儿童”的观念同时包含了与一切边缘观念及其文化反诘力有关的丰富隐喻,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也成为了当代文化批评的基本词汇之一,为我们反观、重思历史和当下现实中的各种文化霸权、偏见、裂缝等,提供了生动的脚本和图鉴。
更重要的是,“儿童”问题的思考及其演进,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确立了至为重要的一种批评精神;或者说,它本身就是这一精神的重要符号。在现代儿童文学诞生迄今的大部分历史时间里,由于儿童被认为是一个在知识、经验、能力方面均低于成人的群体,所以形成了有关儿童文学的一种传统而普遍的成见,即“儿童”与“文学”的结合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是在以一个经验、知识、技能和复杂性都有限的读者群体为对象的书籍中,还是在该读者群体身上,构成‘文学性’的那些天然(或者说文化的)价值和质素,都难以得到维持”(Hunt,’2)。诺德曼认为,这种成见与我们对待儿童的态度有很大关系,而这种态度自儿童文学诞生伊始就深植其中。很长时间里,童年主要被定义为“一件不足(being less)之物: 经验不足,见识不足,理性不足,责任感不足,能力不足。它几乎总是由作为其对立面的成人衍生出的变量来定义,而这个变量几乎总是指向一种缺失的状态”(Nodelman, “Preface”3-4)。直至1968年,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弗朗西斯·科曼在其主编的《当代美学研究》一书序言中,仍将儿童的阅读快感认定为“缺乏鉴赏力”的“最低级的快感”(Coleman17)。“结果就是,儿童文学也是一种缺失的文学——比如,性的缺失,黑暗的缺失,复杂和宏大的缺失——一种说得较少的文学。”(Nodelman, “Preface”4)
然而,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界朝向“儿童”问题的持续、深入的探求,带来了儿童与儿童文学边界不断的重新划定。这一过程中,传统儿童文学观念里代表“不足”和“可知”的儿童意象,逐渐被另一个丰富、复杂、难解的儿童所取代。人们发现,关于儿童的“不可知”论非但没有导致儿童文学的终结,反而促生了儿童文学及其批评致力于重新理解儿童的新征程。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为儿童的“不可知”,所以上述理解和探知的进程本身变得艰难漫长,永无止境。如果我们还记得罗斯的不满和指责:“儿童虚构文学的存在基于以下观念,即一个孩子,就在那里等着我们向他讲述,而且这种讲述是简单易行的”(Rose1),那么时至今日,在西方儿童文学的批评与创作观念里,承认儿童的难解性以及用文学的方式抵近它的难度,正在成为一种日益受到重视的意识。作为一种主要由成人承担创作和批评角色的特殊文类,儿童文学一方面不可能彻底取消成人立场,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打破、挑战成人对儿童的“知情”能力与权力。这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内含了阿多诺主张的那种文学的自我否定性。这种自我否定不抹煞儿童文学的存在,却赋予它永不安定的精神与灵魂。在“可知”和“可能”的边线外,总有些童年的地界是“不可知”的,总有些关于童年的书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不可知”与“不可能”的意识,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Rud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6)。正如大卫·拉德所说,关注儿童文学的“不可能”状态,“最终是为了坚持浪漫主义儿童形象的另一些零余: 一个对象,因其以某种形式处于普遍语言体之外,或者难以被称谓,[……]或者在被称谓时,其反应是未知的”。(Reading33)这一“零余”的观念显然不只与零余者有关,它将进一步促使我们“重观自我,重估文辞,以期更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加诸自身及他者的各种武断限制”(Honeyman151)。
就此而言,“儿童”问题也揭示了儿童文学及其批评固有的政治性蕴涵。经由它,人们意识到,我们关于儿童、成人乃至一切日常生活和文化的观念,都充满无处不在的皴皱和裂缝。或者说,这些皴皱和裂缝本身就是观念和认识的必要构成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或许是,在一切解构性的裂缝和罅隙中,语言、文化和个体仍然被体验为相对连贯、整一、有意义的存在。近三十年间,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尽管深受解构主义理论及思想的滋养和影响,却始终不曾走向彻底的解构。作为近半个世纪来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最重要、最先锋的批评家之一,也是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界最早运用解构主义理论解剖儿童文学的学者之一,佩里·诺德曼始终坚持,“语言之外还有世界——一个语言与之交流的世界,哪怕它永不能被准确或完整地描述。我相信,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着真实的儿童。我们用语言描述他们的方式,确会对他们产生真实的影响”(87)。事实上,当我们身处的后现代世界普遍质疑着各种稳定身份的观念,人们似乎日益想要抓住些坚固和持久之物——童年正被视为这样一个锚碇。(Rud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12)经历“不可知”论和“不可能”论的诘问之后,儿童文学开始被更多地视作虚构与现实、成人与儿童、文学与生活之间彼此交往、相互塑造的通道。而对儿童文学中的这个“儿童”的反复追问和思考,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朝向这一形象的不断指认、辨识、质疑、纠错,促使我们(包括儿童读者)建立起对于自我、他人及包括儿童文学自身在内的一切对象的更完整、丰富的认识。这一认识的过程,借用西方知名童话研究学者杰克·齐普斯一部著作的题名,乃是一个“无尽的进程”(relentless progress)。
①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肇始于19世纪初,以莎拉·特里默在其编写的《教育卫士》杂志上发表的系列童书评论为代表,其突出特点是以教育为中心的儿童文学批评观。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1932年哈维·达顿《英格兰童书》的出版为标志之一,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开始从教育中心转向文学中心,这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当代进程的起点。参见Thomson, Stephen. “Substitute Communities, Authentic Voices: The Organic Writing of the Child.”’:. Ed. Peter Hun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77-98.
② 1970年代,美国康涅狄格大学英语系教师弗兰西莉娅·巴特勒不满于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贫瘠现状,呼吁更多文学研究者关注儿童文学批评,并于1972年创立了美国第一份儿童文学专业学术刊物《儿童文学》。创刊号上,巴特勒以“The Great Excluded”指称儿童文学学术事业,这个命名在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界广为人知。其中,“Excluded”是巴特勒对当时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现状的基本判断。
③ 特里默强调,童书应当“在满足儿童好奇心的同时,灌输宗教、忠诚和良好道德的教诲。”这其中,文学想象的功能主要是引起儿童的兴趣,“宗教、忠诚和良好道德的教诲”才是最终的目的。(Trimmer63)她之所以反对幻想,正是因为儿童故事的幻想对其教诲目的可能造成损害。
④ “教育/娱乐”(Education/Entertainment)二分法是20世纪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的一种基础批评思维模式,以教育中心或娱乐中心的标准判定儿童文学的价值。很长时间里,西方儿童文学界关于儿童文学文类身份属性与文学价值的探讨,始终绕不开该二分法的两极论争。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日益走向开阔多元的理论与方法,这一二分法思维不断经受质疑与反思,并逐渐淡出主流研究的视野。
⑤ 例如,杰妮特·梅宾与尼可拉·J.沃特森在其主编的《儿童文学: 方法与界域》一书绪论中指出,(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事业的独立,是1970年代以来的事情。(Maybin & Watson1)金伯莉·雷诺兹在其主编的《现代儿童文学导论》一书绪论中谈到了现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从1970年代的起步期到21世纪初的发展。(Reynolds,’1)帕特·平森特在《儿童文学》一书中也认为,“197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才真正开始被视作一门‘体面’的学术科目。”(Pinsent11)。
⑥ 关于20世纪70年代以英语儿童文学界为代表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发展进程,参见赵霞《思想的旅程——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理论观察与研究》第一、二章。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
⑦ 该书英文题名,’中的children’s fiction一词,这里译作“儿童虚构文学”,在西方批评中是相对于非虚构儿童文学的一个基础门类。因英语fiction也有小说之意,儿童虚构文学又以小说为主要文体,children’s fiction在中文语境下有时也译作“儿童小说”,但此译法的涵盖范围不及“儿童虚构文学”。尤其罗斯书中重点探讨的《彼得·潘》,其主要文体身份是童话。在英语语境下,童话是children’s fiction的一种,两者并无冲突。但如将children’s fiction译成“儿童小说”,则不能完全涵盖书中所论,且易造成误解。因此,这里取“儿童虚构文学”的译法,尽量保留其原意。
⑧ 2010年秋,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界广有影响的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第3期发表了《彼得·潘案例》出版25周年的纪念专栏。大卫·拉德与安东尼·帕弗立克在该专栏的《儿童虚构文学的(不)可能性》一文中指出,罗斯的著作是1980年代前后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边界拓展进程中的代表成果之一。参见Rudd, David, and Anthony Pavlik. “The (Im) 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Rose Twenty-Five Years On.”’35.3(2010): 223-229.
⑨ 例如,1975年起,作为西方儿童文学重要学术刊物的《儿童文学》开始更多地关注童年文化研究。该刊1975年出版的第4卷,引人注目地探讨了包括阿利埃斯童年史研究在内的童年文化话题。1976年,该刊发文关注儿童文学中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问题,至1980年代,种族主义、男性霸权等话题成为了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1982年第3、4期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先后开设“儿童文学的结构主义方法”“女性主义批评与儿童文学研究”等专栏,探讨相关理论及方法在儿童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价值。
⑩ 参考: 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沈坚、朱晓罕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Coleman, Francis J. “Introduction.”:. Ed. Francis J. Coleman.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1-23.
Darton, F. J. Harve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Grenby, Matthew O., and Kimberley Reynolds, eds.’:. London: Red Globe Press, 2011.
保罗·阿扎尔: 《书,儿童与成人》,梅思繁译。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
[Hazard, Paul.,. Trans. Mei Sifan. Changsha: Hunan Juvenile and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2014.]
Honeyman, Susan.:. Columbu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unt, Peter.’. Oxford & Malden: Blackwell, 2001.
- - -. e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 -. “Childist Criticism: The Subculture of the Child, the Book and the Critic.”43(1984): 42-59.
- - -. “The Mayne Game: An Experiment in Response.”28(1979): 9-25.
Lesnik-Oberstein, Karín.’:. 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ybin, Janet, and Nicola J. Watson, ed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Nikolajeva, Maria.,.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0.
Nodelman, Perry. “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8(1980): 184-90.
- - -. “Preface: There’s Like No Books About Anything.”’. Ed. Sebastien Chapleau. Lichfield: Pied Piper Publishing, 2004.3-9.
- - -.:’.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insent, Pat.’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Reynolds, Kimber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 -, e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Rose, Jacquelin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84.
Rudd, David.’:.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 -.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Ed. David Rudd.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3-13.
- - -. “Theorising and Theories: The 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Ed. Peter Hun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356-74.
李利安·H.史密斯: 《欢欣岁月: 李利安·H.史密斯的儿童文学观》,梅思繁译。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年。
[Smith, Lillian H.:’Trans. Mei Sifan. Changsha: Hun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2014.]
Townsend, John Rowe.:-’(5).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90.
Trimmer, Sarah.1.1(1802).
Zipes, Jack. “Neue kritische Ansätze zur engl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Kinderliteratur seit 1980: Eine Bestandsaufnahme.”:. Eds. Hans-Heino Ewers, et al. Stuttgart and Weimer: Verlag J.B. Metzler, 1994.2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