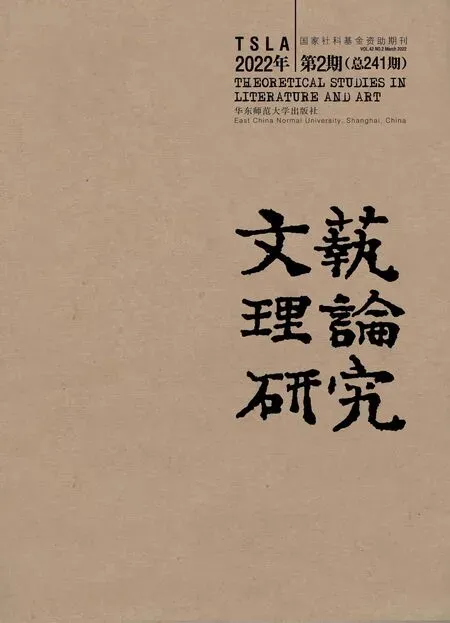论民初小说批评话语中的“自述”与写实
罗紫鹏

在该文发表之前,评论界很少使用“自述”一词分析小说作品。在该文发表之后,虽然当时学界对小说的写实问题、价值问题已有较深入的探讨,但凤兮所谓的“自述”一词,亦鲜有学人延用。凤兮所谓“自述”与今日学界所说“自述”自不相同,而其自己使用时也并未作详细的概念界定,但他所讨论的小说“自述”及“写实”问题却是五四时期学界评论小说的一个焦点,当时小说界的创作状况及新的小说理论的引入在其论述中亦可见一斑。
一、 “自述体”小说概念的提出
凤兮在其文章中对“自述体”的介绍及内涵的说明非常简短,总体而言,他认为:
当世竞言写实派,实则写实即自述体,惟作自述体者不尽为写实派耳。何以言之?自述体不论其书之主人为自己、为他人,而所写必即身遇之实。写实派虽不以自身写入书中,然因所写为身遇之实,不啻令读者见著者当时观察之状,则与以他人为书中主人之自述体,无以异也。
我所见之自述体小说,当然亦分两种作法,即或以自己为书中主人,或以他人为书中主人。此种自述体小说,甚足表见小说家个性。而我国两种作法之比较,以自己为书中主人为多,且于人物多修饰,自述反不能写实,可诧也。故吾有自述体不尽为写实派之语。(“我所见之自述体小说”14)
即,凤兮将“自述体”定义为: 以自己为主角或以他人为主角而对身遇之事所做的实录。他将写实包含于“自述体”,认为写实与“自述体”的区别就在于“自述体”还包括出于作者主观原因而不能写实的部分。因此,表面上看凤兮是在谈“自述体”小说,其实他是在讨论小说的“写实”问题。他所谓“自述体”一词,其中虽有自己对小说的独特理解,但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当世竞言写实派”,而他也要加入讨论的行列。
盖自晚清以来西方小说及小说理论不断引入,中国学界对小说的讨论也遍及小说价值、小说题材、小说类别、小说语言等诸多方面,而对“写实派”“写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则在五四之后迎来了高潮。虽然在20世纪10年代,不少小说亦题为“写实小说”,但在20年代“写实”才真正成为重要的论题被学界集中讨论,而1922年吴宓在《中华新报》上发表的《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与沈雁冰在《文学旬刊》发表的《“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君: 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次讨论的高潮。但其实在吴、沈两文之前,不少学人已在文章中介绍过西方的“写实主义”,如郑振铎的《写实主义时代之俄罗斯文学》(《新中国》1920年第2卷第7—8期)、愈之的《近代文学上之写实主义》(《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期)以及沈雁冰的《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1920年第9期)等,这些文章虽全是对西方文学流派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实则已经开启了对国内小说所属流派及写实与否的评判与“清算”。1921年,在北大任教的德国文学教授欧尔克曾作题为“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教育价值”演讲(《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第821期),这是外国教授在课堂上宣讲小说流派及写实主义价值的直接证据。而在1922年之后,亦有诸如《谈写实主义》(蒋豪,《雪片》1924年第2期)、《写实文学论》(木天,《创造月刊》1926年第1卷第4期)等诸多文章发表。所有这些文章都表明当时文坛及评论界对小说创作的“写实”要求。可以说,当时的学界一致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写实,应该依照西方小说理论中所谓的“写实主义”去关照、反映时下的个人命运及中国社会,而这也间接推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严肃小说的创作。
除了敏锐地觉察到文坛的热点话题而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外,凤兮对写实问题的感发还基于当时小说界的基本状况。他所说的“自述体”,其参照对象就是当时文坛极流行的通俗化旧式小说,而这也是当时诸多学人讨论小说“写实”问题的现实背景。
按照凤兮对“自述体”的阐述,晚清以来带有“自述”性质的小说有很多。既有“捏造”一位主角以第一人称来叙写自身经历的,也有将自己“化入”全书来描摹、揭露社会现实的,像闻名于世的“四大谴责小说”就均带有“自述”的特点。而受“四大谴责小说”的传播与流行影响,在小说界兴起的所谓“社会小说”“狭邪小说”等皆有“写实”及叙述自己及自己周边人事的特征。如《花月痕》《海上繁华梦》《九尾龟》等小说均以浓重的笔墨刻画清末的旧式文人,其人物之众、酬接之多、场景之清晰、线索之明确,如果不是亲历其中的人,很难有如此真切的描绘。又如,在时间上较为靠后的《歇浦潮》,虽然于1916年底才开始在《新申报》副刊上连载,但无论写法,还是“自述”的性质特点,与《海上繁华梦》诸篇都极相似。正如凤兮在其文中所说:“徐枕亚自为《玉梨魂》中之何梦霞,能不讳其中国不许有之情,意尚可取[……]姚鹓雏自为《恨海孤舟记》中之赵秋桐,及《夕阳红槛录》中之某某(偶忘其名)。两书皆写所谓雅人雅事,不免将自己写作此宗人矣。”(《我所见之自述体小说》14)此外,包天笑、周瘦鹃等大部分通俗小说家也都擅长并创作了不少“自述体”的小说。像毕倚虹的《人间地狱》,陈小蝶也曾评价说:“书中人名皆隐托。柯莲孙是他自己,恋人秋波,则是会乐里的乐弟[……]而包天笑、姚鹓雏、郑丹斧(杭州人)都成了书中的次要主角。”(陈定山195)
由此可见,当时的小说家在作品中“实录”个人见闻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以描写现实为目的的作品在晚清以降的小说界是较流行的一种创作范式。这类作品或是以小说主人公为中心的短篇单线叙事,如《玉梨魂》;或是以小说主人公经历为主线的多人物多线长篇叙事,如《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或是将“自我”隐去的多人物多视角长篇叙事,如《歇浦潮》《孽海花》。它们有的题为“社会小说”,有的题为“写实小说”,有的甚至题作“黑幕小说”“言情小说”,但在“写实”的特点上却是一致的。而凤兮也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才将其统括来讨论,并总称为“自述体”。
因此,凤兮所谓的“自述体”是针对晚清民初的小说作品情况所作出的论断,其所指就是描写事实的现实主义小说,不管这事实是作者亲历还是道听途说,不管小说的主人公是“我”还是“他人”。“自述体”是对小说创作手法的一种评价,这种评价与当时大部分评论家的观点一样,以“写实”为最高标准。
二、 “自述体”的表现与局限
用“写实”或“写实主义”来讨论小说,其实是在对小说进行一种价值评判,是在用新获知的西方小说理论去评价、引导当时的小说创作。从晚清开始,小说价值就被反复讲述和强调,到郑振铎、沈雁冰等刊文介绍西方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及写实主义等概念时,小说的价值是再次被强调和突显的。“自述体”的论述是对强调“写实”的应和与肯定,也是基于写实标准的一种价值论断,这种价值论断一方面正是五四时期小说理论的具体呈现,另一方面也同时展示出写实小说及“自述体”概念本身的局限。
虽然五四时期西方各派文学理论均有引入,但文坛学界始终无法摆脱“小说工具论”的束缚。小说的地位之所以不断提升,之所以不再是“或有可观的小道”,原因就在于学界不断证明其具有“熏、染、刺、提”的作用;而一部分知识分子愿意投身于小说创作的队伍,除了稿酬的吸引,还在于其对“小说能够改良社会”的认同和想象。而能够充分发挥“工具”作用影响社会现实的小说,无疑就是充分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社会小说,也即凤兮所谓的“自述体”小说,或者说写实小说。
不但吴宓在《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中称:“吾国之新文学家,其持论乃常以写实小说为小说中之上乘、之极轨,而不分别优劣,并言利弊。惟尊写实小说而压倒一切,其余悉予摈斥”(吴宓286),旧派小说家王钝根也说:“小说之中,实以社会小说为最有意义,最有价值。吾既以小说为业,在义当作一长篇社会小说,警醒世人,庶几稍尽天职。”(王钝根4)《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歇浦潮》等小说就是作者通过“自述”描摹社会人生,对其中弊端进行批判,以警醒世人,呼吁改良。可以说,“写实”就是文人幻想的参与社会改良的方式,是知识分子通过对自我及所属阶层的剖析与描绘而收获的“意义”。小说家意欲通过“自述式”的写实来实现其改良社会的责任,而这也正是当时的小说界所热切倡导的。梁启超当初提倡“小说界革命”,就是希望小说家能改变传统小说中的“绿林习气”“状元思想”,能够像西人小说一样有益于社会。而自小说地位上升之日起,小说与社会的关系就被反复提及,如苏曼殊称“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苏曼殊165),又称“小说者,乃民族最精确、最公平之调查录也”(苏曼殊166),也即小说“描写现实的要求”与小说的“重新被估价”是同时发生的。吴沃尧在小说中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九死一生笔记”(吴趼人2),张春帆说《九尾龟》“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漱六山房1),冷泉亭长亦在其《后官场现形记》的序言中说“爰据近二十年来之闻见所得,笔临摹之,借镜社会,慰我故人”(冷泉亭长1732)。晚清以来,凡讲求“写实”的小说多半是拾掇自己的经历见闻而成,不管其书是第一人称叙事,还是另设主人公,又或者是串珠式的全知叙事,其所撰内容皆不出凤兮所谓的“自述”范围。
凤兮在文中提及“自述体”时,所举的例子是《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尾龟》《泪珠缘》等十余部作品。按照其写实的标准,这些作品都是依照自己的经历见闻描摹现实,其区别只在于是否以“自身为书中主人”。然而这些作品并不完全能够实现描摹现实、改良社会的工具价值,反而较多地表现出创作上的缺陷。
因为“自述体”要求“写实”,所以时时处处可以见出“真人真事”,这不禁会勾起时人的好奇心,并使许多读者做起小说的“人物索隐”来。而在“人物索隐”风行的情况下,撰稿者在创作时会更逼近现实,甚而形成“揭秘”的恶趣味,如在五四之前盛行的“黑幕小说”就是实例。此类小说直到1918年《中华教育界》《时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相继刊出《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时才略有收势。而清末民初学界的“索隐”风气对写实小说的流行来说,亦是一剂催化剂。“索隐派”本是《红楼梦》研究的一大流派,此派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中的各个人物乃现实中某人之化身。而晚清以来,盛行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本就喜欢模仿《红楼梦》,加之受到“索隐派”研究的影响,这些小说的作者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通过“隐喻”的手段去记录人物,甚至直接依照“索隐”的框架去构建作品大纲,这就导致小说中的角色多有“影射”,个别“影射”之人竟至一目了然。
如《孽海花》中的陆菶如、庄小燕分别影射陆润庠、张荫桓,至于金雯之于洪钧,庄寿香之于张之洞,李莼客之于李慈铭等,则几乎人尽皆知。1916年,望云山房出版的三册本《孽海花》就直接附录时人所撰的《〈孽海花〉人名索隐表》《〈孽海花〉人物故事考证》,可见曾朴所撰多为事实。又如,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中也曾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的影射:“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濂、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苟细绎之,不难按图而索也。”(蒋瑞藻284)则其中所述大事件与大人物的“真实性”,与《孽海花》的情况大抵相同。此外,又如署名“旅生”所撰的《痴人说梦记》一篇,该作品言及康梁变法与孙中山革命,其中的角色宁孙谋、魏淡然、黎浪夫即为康、梁、孙三人之化身。而若给《歇浦潮》一书列“人物索隐”,首先可以确定的就有方凯城(喻袁世凯)、方振武(喻袁克文)等人。以上这些作品,作者均未以自己做“书中主人”,但其实直接以自己为主角进行“写实”的作品也有不少。如凤兮谈及的张春帆之《九尾龟》、陈蝶仙之《泪珠缘》,此外还有毕倚虹之《人间地狱》等均以“自己”为主角来“描摹现实”。虽然这类作品因多是作者自己的经历,许多人物的身份略加隐藏,不易查究,但若经熟悉时人掌故者细细考察,其“人物索隐”亦不难得出。
所以,凤兮所谓的“书之主人为自己”与“书之主人为他人”这两种情况均有“人物索隐”可作,而这也更说明了当时写实小说存在的价值与现状。即,这些小说或是为揭露与警示的责任而作,或是为自我的阐释与剖析而作,其“文艺高度”总离不开“写实”的要求,其写作经验也总少不了“索隐”的习惯。追求小说的社会功用必然会带来“征实”的要求,而“征实”便避免不了“自述”,也就避免不了“人物索隐”。
但是过多揭黑式、索隐式的创作无疑引起了读者及评论界的反感,同时也并没有体现出其作为“写实小说”的裨益社会的价值。在这一点上,凤兮的“自述体”表述并没有给出自己的观点,而只是认为以自身为“书中主人”时不能客观写实,有“极力铺张自身”的缺陷。但吴宓却直击这类小说艺术价值上的不足,他在《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一文中将写实小说分为三类:“(一)则翻译俄国之短篇小说,专写劳工贫民之苦况[……](二)则如上海风行之各种黑幕大观及《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三)则为少年人所最爱读之各种小杂志,如《礼拜六》《快活》《星期》《半月》《紫罗兰》《红杂志》之类。”(吴宓285—286)其中第二、三类与凤兮所讨论的“自述体”内容基本一致,即他们都认定当时文坛流行的各类言情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等是时下国内写实小说的代表。但吴宓指出这些小说的弊端在于“徒抄一种实境”,“以不健全之人生观示人”,故不能直达艺术的较高境界。而沈雁冰则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沈雁冰39—42),他直接否定这些作品是“写实小说”,并同时否定其可能存在的社会价值。
从凤兮到吴宓再到沈雁冰,他们讨论的都是小说的写实问题,但对盛行文坛的通俗小说的评分却是逐级递减的,这种递减关系与新旧文学家不同的文学观念相关。凤兮显然是站在旧文学家阵营的,他在“自述体”的表述中关注的是“写实”能达到什么程度。而当时也正因评论界对写实的过度强调,才有了更多揭黑式与索隐式作品,也就出现了更多吴宓所谓的弊端。
凤兮将写实小说完全包含于“自述体”中,对写实小说的概括过于随意,对“自述”与“写实”的辨析也不甚清晰。任何小说体现的都是作者的经历见闻或心境思想,都可以说是作者的“自述”,写实小说自然也不例外。按照凤兮的观点,没有小说不属于“自述体”,就像焦菊隐所说:“小说里,永远有作为解说者的作家身分存在着,即或它是自述体。”(焦菊隐143)
但是“自述”与“写实”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般来讲,“自述”更多的是一种叙事方式,而写实则是一种艺术表现类别。所谓“自述”,常常是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故事,或者倾吐“我”的心理活动。其实,当时文坛已经出现以“××自述”为题的小说,如怜侬口述、曼殊撰文的《阿侬自述》,明道所撰的《某女士之自述》等,这些小说无论在叙事手法上还是在题目名称上,都更明确地交待了小说的“自述”性质,即向内描述心理、倾吐心事,而非向外描写社会现实。在现代小说理论的话语中,“自述体”小说就是倾向于描述人物心理而非社会实事,可以说恰恰是写实派的反面。正如有的学者认为:
便于这种自我大表露的书信体、日记体、自述体小说的出现与流行,则使心理小说有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形态的心理小说,我们可称之为心理倾诉小说,它们往往以自述的形式来倾吐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柳鸣九45)
不过这种理论在急于验证小说社会价值的民国文坛,显然是普通的评论家所望不到的。
当然,凤兮也言及“自述”与“写实”不同,即“以自己为书中主人”的情况。但属于这种情况的,不少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绛纱记》,徐枕亚的《玉梨魂》等。不过,凤兮所言“自述”不在于界定作品是作者的“自传”,而在于强调“自述”(写实)所呈现出的艺术效果,是否因“过多修饰”,“反不能写实”。另外,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谈及吴双热的《孽冤镜》时,也用了“自述体”(范烟桥275)的评价;而包天笑1926年在其小说《空门忏语》中亦曾言:“至于书中人物,我恐妙师自述过于真实,略加改易。或者自述供状之原本,亦非真姓名,未可知也。此小说为自述体,加以点缀描写及一切背景,以求合乎小说体裁。”(包天笑13)但因为这两篇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中的人物,所以范、包二人是用“自述体”来指认小说的叙事手法,与凤兮对“自述体”的表述与理解并不相同。
大体而言,凤兮将“写实”等同于作者的“自述”,是因为当时的确有许多作家在用纪实的方式描述自己的见闻经历,“自述体”的表述是时下“索隐式”小说过多的缘故,而非凤兮完全出于主观故意的误解。他用“自述体”概念去品评小说作品的优劣,其实是探讨在写实的标准之下,时下流行小说所呈现的社会价值。只是“自述”一词的能指与他真正表述的内涵并不完全吻合,所以他划分的“以自己为书中主人”和“以他人为书中主人”这两种“自述体”小说类别并没有被其他学人所接受或延用。
三、 “自述”概念呈现的小说理论问题
如上文所言,凤兮等人关于“自述体”、写实小说的表述存在很多缺陷。但他在传统小说理论方面仍然有所突破。这种突破不仅仅在于他将古代小说批评中对小说的结构、炼字、伏笔、人物刻画等内容的评点转变为对小说写实的要求,将古代小说中的“警世”论调转变为对小说价值的深入探讨,还在于他与其他评论者一样敢于尝试运用西方的文学观念、运用全新的批评话语。特别是,其对于自述与写实的思考反映了小说理论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如小说内容的虚实问题及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
(一) 虚与实的问题
凤兮之所以认为“自述体不尽为写实派”,是因为“自述”时对“自己”多有修饰,下笔往往不能客观。这种过分强调写实的态度,是和当时大多评论家一样过分追求小说工具价值的结果,也是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小说内涵的结果。
俞平伯曾言:“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虚构原不必排斥实在,如所谓‘亲睹亲闻’者是。但这些素材已被统一于作者意图之下而化实为虚。”(俞平伯435)但晚清民国时期的许多评论家并不了解现代小说的真正含义,一部分学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小说观念里。现代的文学观念常把“虚构”当作评判小说的一个标准,倾向于将虚写的内容归为“小说”,而把实写的作品定为散文或其他文体。然而在传统的观念中,《列异传》《神仙传》这类虚幻不实的作品是“小说”,文史考证类的札记也是“小说”。像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的“九流绪论”一节中就将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等内容均归为“小说”,而以“观代”的小说观念来看,《颜氏家训》《梦溪笔谈》之类均不能划归为“小说”。同时,现代观念所认为的“虚构”,在古人眼中也不一定就是“虚构”,否则近人也不会批判迷信、提倡科学。“虚构”不是传统小说的特质,“小道可观”才是。古人将今日所认为之“小说”归在史部和子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小说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缉琐语”三派,其反映的正是传统小说的形态与本质。即,所谓的古代小说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古人对经历见闻的直接记录和书写,是按照古文的规则将轶闻琐语纂辑成篇,或辅正史,或助谈笑,但却非靠着自己对历史人生的观察和体悟而进行的阐述和表达。可以说,古代小说有相当一部分只是记录、辑佚,是对世间传闻的整理,运用的是史学的方法,而非文学的手段。传统的小说观念及创作习惯,加上晚清以来流行的小说助益社会改良价值论,使得写实一时成为部分小说家和评论家的最高追求,继而遗漏了小说的虚构特质。
作家在撰写所谓的“自述体”小说时,过分修饰自己固然不可取,但忽略了虚构与写实的区别同样使得这些作品无法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前文提到,按照写实的标准,许多小说具有索隐式的特点,其结果就是许多读者及评论者会去如实索隐、还原小说中的现实人物。也就如俞平伯在评述《红楼梦》研究之“索隐派”与“自传派”时所说:“索隐、自传殊途,其视本书为历史资料则正相同,只蔡视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俞平伯435)他们关注的似乎只是史料,而看不到小说真实的文学价值,或也因此,胡适才会认为《红楼梦》的价值并不突出。
而就作品而言,忽视了虚构,其文学价值也就如吴宓在《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中所说,是“徒抄一种实境,不能为小说”(287),是“有悖文学之原理”(286)的。吴宓将人生分为实境、真境、幻境三种情况,他认为写实派小说需由实境而历真境,最后达到幻境,才能真正取得创作上的成功。
凡作小说者,皆必首先观察人情之实境。或凭经历,或由读书。所得既多,乃悟人生之真理。是即真境也。然此真境虚空渺茫,欲以晓示于人,则必假设一种幻境,以显明之,而予人以己之观察理解之所得。故幻境虽幻而最真,与所有之实境皆不同。以其由凝练陶冶而出者也。凡小说家皆必遍经此三种之步骤。(吴宓286)
即,纪实不是小说家的最终目的。小说家应该在现实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思考以求真,通过重新的创作再化真为实,艺术真实才应该是小说家的追求。但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大多缺乏这种“化实为虚”“化实为幻”的能力,他们以“身遇之实”为素材的作品完全遵循着写实的意旨,以自己为主人公的小说也不过是将自己的形象进行随意的美化。对见闻体悟的归纳与升华,对实事的重构与转化,在小说作品中极少有“幻境”式的呈现。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小说家自身才力不足的因素,有刻意追求小说社会价值的因素,也有因报刊连载而潦草撰写、快速发表的因素。但不管怎样,这些作品的不能虚构与当时对“写实”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其价值构建也是在“写实”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
然而,当写实超出了小说所能承受的范围,如专门揭露“黑幕”、搜罗别人隐私,甚而可以按图索骥,制作“时人索引”时,小说应有的社会价值便会被削弱。虽然也有像吴宓一样的评论者看到了这些小说的“写实”特点,但清末民初所谓的“黑幕小说”“狭邪小说”仍不免被新派文学家所诟病,如沈雁冰就不但痛诋这些作品是“劣作”,甚而对吴宓是否真正读过这些作品表示怀疑,认为吴宓所谓“抄袭实境”的话,“去针砭时下专做‘此实事也’而其实不尽不实的‘小说匠’,却是很有用的”(沈雁冰42)。不过,由于对小说社会价值的一再强调,这种揭露与写实的习气一时难以消除,因而凤兮所谓的“自述体”小说便在文坛不断出现。
可以说,在现代小说概念逐渐形成的晚清民初时期,小说文本的虚实问题也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讨论重点。学者在抬高小说地位、借重小说的功用价值之后,也开始探索小说的本质,认识到小说不是“抄录的实事”,而应该是“虚构的真实”。凤兮虽然不能像吴宓等新派学人一样揭示真正的文学真实,但他毕竟看到了当时小说中存在的虚实问题,这对于之前的小说评论来说也算是一种进步。
(二) 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
凤兮虽然将写实派概括为“自述体”,但其实想要强调的是“自述”与写实的不同;其论述的侧重点在于“以自己为书中主人”时,作者描摹现实、进行“自述”的创作水平及能力。他想要区分的是: 作者是将自己作为小说的主要角色去讲述事实,还是借其他角色去演述事实,即在“自述体”的表述中,凤兮间接涉及的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是凤兮在文章中提出并予以解答的问题。他认为写实的作品都属于作者的自述,但实际上,即便不是写实,作品中的架空、虚构、想象也无不显露着作者的思考、观点与心理。作品与作家作为文学的两大要素,是文学中联系最紧密的两个主体。可以说,作品就是作者倾吐自我的窗口,在作品的细微之处总可以寻找到作者观念的影子,作品内容无不是作者的“自述”。就连凤兮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概许多小说家,间必有自述之作,隐显可辨。即看似不关自己者,其因必得于所遇,而以理想衍为结构,以成自然派之艺术。所惜者,自述体小说中,竟无如迭更司之《大卫考伯菲而》(即《块肉余生述》),遑论易卜生作《社会柱石》后之作《群鬼》哉!此中国小说家与欧西小说家个性之大别也。”(《我所见之自述体小说》14)只是,他将作者演述理想一类的作品称为“自然派”,与他认为的“写实派”又有所不同。
即关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凤兮还是基于写实小说来谈的。他并未脱离写实小说去谈作者的问题,他其实摒弃了非写实小说,如侦探、武侠、历史等类型,或许在他看来,这类带有虚构性的内容,既然大多不源于作者的见闻,那么就不能用“自述”来界定,自然也就不会去探讨其中是否表现了作者的思考、观点与心理。而某些作品并不能真实呈现作者的状态,他将原因归为作者的主观失实——作者对自己的矫饰。但其实当时已有不少人认识到作品即使以“我”来自述,“我”也不能与作者等同,如韵秋女士就对“这个‘我’是作者的自称,这篇小说中的事迹便是作者的自道”(韵秋女士7)提出质疑。同时,过于强调作品是作者见闻及内心的呈现可能会导致作者中心论,会忽视作品文本、忽视读者的阅读,但这一问题对当时聚焦于讨论小说价值与写实问题的小说界来说还为时尚早。
关于这一问题,凤兮只谈及时下文坛“自述体”小说很多,却并未分析原因,而当时的评论界也未给予说明。实际上,这也是探查作者与作品关系的重点。凤兮在谈论“自述体”时,没有指出当时的许多小说家都是文坛新秀,有不少人是刚刚迈进小说界进行创作的。盖晚清民国时期是小说撰稿者急剧增长的时期,其中大多数人称不上是小说家,只能算小说写手。也正是因为他们在写作手法及艺术技巧上不成熟,他们对社会体悟的不深刻,他们处在创作初期,所以只好从描写、剖析自己开始,只好通过“自述”向成熟的创作阶段逐渐迈进。
当时带有自述式倾向的原创作品有很多,除了前文所举的《孽冤镜》《九尾龟》《人间地狱》等长篇小说之外,大众流行的通俗刊物如《礼拜六》《半月》《游戏杂志》《小说月报》等发表的作品也极多“自述体”,通过自述以尝试创作的小说家亦不在少数。如周瘦鹃的许多“言情小说”虽然对男女主角的身份描写常常不着痕迹,但多为自己的映射,所谓“紫罗兰”轶事更被时辈传为美谈;又如陈蝶仙的“自传体写情小说”,韩南曾在其《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中就此专门进行论述,他所举的例子是陈蝶仙写于1912年前后的《黄金祟》和《娇樱记》(韩南209);又如《申报·自由谈》的早期主编王钝根,他同样写过“自传体”小说《家庭地狱》,该文用第一人称完整倾诉了“我”的家庭不幸,其中还有大段篇幅与其所撰《钝根随笔》相同。此外,还有女小说家吕韵清,她同样喜欢在小说中将自己的经历添置在角色身上,如她的《返生香》《石姻缘》等作品都有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而秋瑾所撰的自传体弹词小说《精卫石》,亦是将自己的经历与理想“实录”于作品之中。
这些例子均说明,清末民初的小说界存在着普遍的创作冲动,小说家渴望通过小说来演绎自己,并希冀进一步表现时代、改良社会。只是由于他们创作手法的稚嫩与不成熟,导致其实现小说价值的愿望受挫,使其产出的小说作品大多只能在“自述”的漩涡中挣扎。
此时的小说创作不再只是讲述故事或抒愤、怀古,创作者普遍具有用小说改良社会、表达自我的意识。小说作者开始认识到“创作”本身,但这种创作意识的觉醒并不一定就能产出好的小说作品,创作成绩的打磨也需要一个过程。如凤兮自己也谈道:“以严格言,我国非无创作小说,惟足当创作而无愧者,盖亦鲜矣。且我国创作小说,只短篇而止,长篇则未之前闻也。”(《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14)
因此,在“生产”小说之初,小说家便因写作习惯与才力的影响,撰写出许多颇具自传性质的作品,但这也正是他们进行“创作”的开始。正如吴宓所说,小说创作是一个由实求真,由真入幻,最后归于艺术真实的过程。而中国古代小说,严格来说有相当一部分都不能算是“创作”,而只能算是撰写的文章、记录的琐语、编纂的旧闻。在晚清以来的学人逐渐推翻旧有小说评价标准、重新审视并梳理中国小说时,小说被依照西方文学的标准进行归类和评述。小说被分成短篇和长篇、白话和文言等体裁,被分为言情、社会、侦探等类型。古人没有立志做小说家者,亦无所谓“创作之理想”。而小说从被要求助益社会改良之日起,小说作者便开始了“有意识的创作”,这是古今小说主要的区别之一,也是中国小说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此时,作品大多在撰写之前已先有了立意和宗旨,小说撰稿人在下笔之前已经知道要写一个什么故事,要表达一种什么思想或道理,甚至可以预见主要的读者与受众是谁。他们在作品题目之前往往标注“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等不同的类别,即对作品的意旨已作了“规定”。像《申报》《时报》《礼拜六》等报刊的小说撰稿者常常撰写“滑稽短篇”,虽然所述仅为一件小事或假设虚构的某个场景,但却在行文之前已明确了自己的表达意愿,故该作品乃是作者独立“创作”的结果,并非简单地将某事某人记录下来。立意确定之外,此时的小说不再是史传性质的作品占主导,而是言情、武侠、侦探及社会小说等内容成了创作的主流。
因此,在小说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在小说依照价值前提、写实原则对现实进行的描绘中,其最初的尝试多半是自述式的,这符合作者的创作心理,也适于小说的撰写规律。凤兮在自己简短、粗疏的评论中,将写实派概括为“自述体”,其虽然忽视了小说内部的虚构问题,忽视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区别,但仍反映出民国时期小说评论者对作者客观描述自我的要求,反映了对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朴素认识。虽然不如吴宓、沈雁冰等新派学人对西方文学理论的辨析明确,但至少在写实小说及“自述体”的问题上,凤兮等评论者既能够欣赏旧式通俗小说,又积极地追问、探讨了小说文本的“写实”问题。
总体来说,“自述体”一词是为了探讨小说的写实问题而提出的,是主要针对清末民初的旧派小说作品所作的论断。凤兮能注意到“写实”之中的虚构、看到“作者在作品中的自我呈现”,这是他较之旧派“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等小说创作者的进步,也是“自述体”一词的价值所在。但他对“自述体”的界定却又是宽泛而不准确的,他将小说的写实问题放在“自述体”的概念之下讨论,使得对小说创作流派的讨论纠缠于对小说叙事方式的讨论。关于写实派、写实小说的争论,发端于晚清民初一系列致力于刻画现实的狭邪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社会小说的失实与粗陋,发端于对这些小说水平及真正价值的评判。但从凤兮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争论并不一定是从新派学人那里开始的,也可能是从更能欣赏“自述体”小说的普通评论者那里开始的。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小说批评话语中的“自述”与写实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写实代表着小说创作要沿着工具价值导向继续往现实靠拢,“自述”也要求作品内容要忠于客观的现实与自我。但除此以外,“自述体”这一并不准确的表述也似乎给创作者指出了一条新路,即在不属于写实的那部分自述里,创作者或许可以幻想、构筑出全新的文学世界,并最终达到艺术上的真实。
① 此外几部为徐枕亚的《玉梨魂》,姚鹓雏的《恨海孤舟记》《夕阳红槛录》,周瘦鹃的《玫瑰有刺》《玫瑰小筑》,包天笑的《电话》《天竺礼佛记》,刘半农的《假发》。
② 如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曾说:“《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胡适518—519)
③ 王钝根的《家庭地狱》小说发表于《半月》杂志1923年第3卷第3期。这篇小说所述的大儿夭折、归乡安葬之情节与其在《钝根随笔》(《新申报》1919年4月24日第4张第2版)中所述几乎一样。
包天笑: 《空门忏语》,《申报》1926年12月1日。
[Bao, Tianxiao. “Confessions in the Buddha Hall.”1 Dec. 1926.]
陈定山: 《春申旧闻》。北京: 海豚出版社,2015年。
[Chen, Dingshan.. Beijing: Dolphin Press, 2015.]
范烟桥: 《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魏绍昌编。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68—363页。
[Fan, Yanqiao. “A Brief History of Old-Style Nove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d. Wei Shaocha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84.268-363.]
凤兮: 《我国现在之创作小说》,《申报》1921年2月27日。
[Fengxi. “Current Fiction Writing in China.”27 Feb.1921.]
——: 《我所见之自述体小说》,《申报》1921年3月20日。
[- - -. “Personal Accounts as a Type of Novels That I Have Read.”30 Mar. 1921.]
韩南: 《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
[Hanan, Patrick.. Trans. Xu Xia.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胡适: 《胡适全集》(第26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Hu, Shi.. Vol.26.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3.]
黄霖编著: 《历代小说话》。南京: 凤凰出版社,2018年。
[Huang, Lin, ed.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8.]
蒋瑞藻: 《小说考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Jiang, Ruizao..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4.]
焦菊隐: 《导演·作家·作品》,《焦菊隐文集》第四卷。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22—148页。
[Jiao, Juyin. “Director Author Works.”. Vol.4.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8.122-148.]
冷泉亭长: 《〈后官场现形记〉序》,《历代小说序跋集》,丁锡根编。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1731—1732页。
[Leng Quan Ting Zhang. “Preface to”’. Ed. Ding Xig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6.1731-1732.]
柳鸣九: 《世界心理小说类别的划分——〈世界心理小说名著丛书〉总序》,《柳鸣九文集》第二卷。深圳: 海天出版社,2015年。第44—47页。
[Liu, Mingjiu. “The Classification of World Psychological Novels: Preface to”. Vol.2. Shenzhen: Haitian Press, 2015.44-47.]
沈雁冰: 《“写实小说之流弊”?——请教吴宓: 黑幕派与礼拜六派是什么东西!》,《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魏绍昌编。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39—42页。
[Shen, Yanbing. “‘Weaknesses of Realistic Fiction’: A Question for Wu Mi: What the Hell Are the Exposé and the Saturday School!”. Ed. Wei Shaocha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84.39-42.]
漱六山房: 《九尾龟》。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
[Shu Liu Shan Fang.-. Nanchang: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1.]
苏曼殊: 《小说丛话》,《新小说》3(1905): 165—168。
[Su, Manshu. “Comments on Novels.”, 3(1905): 165-168.]
王钝根: 《温柔乡》,《社会之花》2.1(1924): 1—7。
[Wang, Dungen. “”, 2.1(1924): 1-7.]
吴宓: 《论写实小说之流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严家炎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5—290页。
[Wu, Mi. “The Weaknesses of Realistic Fiction.”. Vol.2. Ed. Yan Jiay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285-290.]
吴趼人: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Wu, Jianre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俞平伯: 《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俞平伯全集》第六卷。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33—436页。
[Yu, Pingbo. “The Textual Research and the Review of Author’s Autobiography on”Vol.6. Shijiazhuang: Huashan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97.433-436.]
韵秋女士: 《言情小说中的“我”》,《最小》8(1923): 7。
[Yun Qiu. “The Narrator ‘I’ in Romantic Novels.”, 8(1923): 7.]
郑逸梅: 《南社丛谈》。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Zheng, Yime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