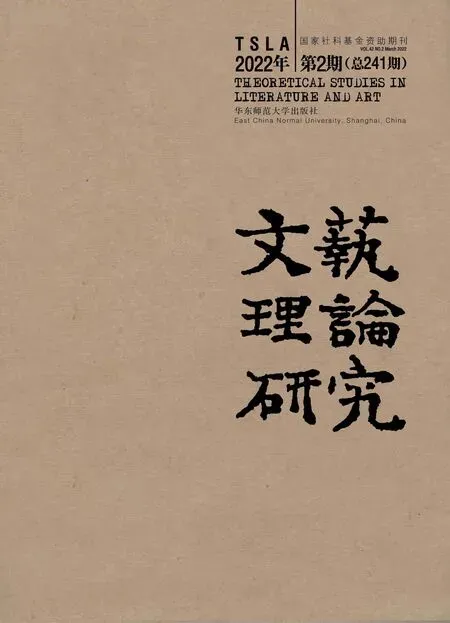晚明禅林诗禅关系的重构与援儒入禅的诗学转向: 以吹万广真为中心
王廷法
明代文学流派众多,文学思想趋向多元化。在三教合一、禅净一体以及中西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有明一代佛教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明中叶以来,阳明心学与佛学桴鼓相应,催生了晚明文学的新变局,文人群体形成了融通儒、释两家的新学风和讲究童心性灵的文学风气,明清之际居士群体、遗民逃禅群体、画僧群体涌现,以及小说戏剧与宗教的交错,深化了佛教文学的解读视野”(李小荣 杨遇青208),在西南巴蜀之境的吹万广真(1582—1639年),是晚明禅林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其文学思想不但与晚明以“文字般若”提振禅林的现状相关,亦受到了儒家诗教观的影响,是“融通儒、释两家”新学风与“讲究童心性灵”文学风气的僧侣文学之典范。
一、 吹万广真的诗禅观: 从“以禅喻诗”到“以诗喻禅”
禅宗自成立之初便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教外别传之旨为极则,秉持“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字禅观。事实上随着禅宗的发展,“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之胶葛从未断绝。《圆悟佛果禅师语录》载:“所以达磨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后来六祖大鉴禅师尚自道‘只这不立两字’早是立了也,何况语言机境种种知解,须是一笔句断始得。”(圆悟克勤769a)以此可见禅宗之于文字禅观的复杂性。而诸如南宋严羽等一众诗论家“以禅喻诗”之说则又参杂其间,为诗禅关系蒙上又一层面纱。晚明三教融合,不少禅师统合儒释之道来看待文字禅,加之禅林模拟之风盛行,以未得为得,未证为证,认虚妄为真实,丧失了文字禅的本来面目。纷繁复杂的“文字禅”因禅林而生,却凝滞一隅,未能结合禅林现状进一步推动文字禅观。吹万广真的文字禅以禅悟为机要,以提振明季禅林衰微之势为目标,不但切中“文字禅”之要害,亦对明末禅林“文字禅”之风予以反拨,从禅宗本身的立场出发予以重新审视。
晚明禅林中的诗禅关系基本上与“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相应,学界一般认为可分两种情况: 其一,诗禅一致说,憨山德清、觉浪道盛等均持是说,认为诗禅不二。如紫柏真可倡“文字般若”(释达观1),认为文字与禅不一不二;《灵峰蕅益大师宗论》曰:“出世之文,迦文为最,治世之文,文宣为最”(释智旭326c),统合儒释之道来看待文字禅,认为是中之“道”决定“文字”。其二,诗禅非一说,云栖祩宏《竹窗随笔》认为诗乃士大夫之所为,非僧人“己分之事”,其言“末法僧有习书、习诗、习尺牍语,而是三者皆士大夫所有事,士大夫舍之不习而习禅,僧顾攻其所舍,而于己分上一大事因缘置之度外,何颠倒乃尔”(释祩宏30b),认为诗禅非一。事实上,从禅林的历史形态出发,我们并不能以“诗禅一致”“诗非禅”之语简单的阐释禅林的诗学观,禅林“诗禅观”的发展变化与禅林的发展现状紧密相连。吹万禅师为提振明季禅林衰微之势,对“文字禅”的态度随着禅林的现状而发生变化,对晚明模拟之风提出批判,以禅悟为机要,力争跳脱“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二者之藩篱,回归到禅林本身重新审视文字禅,体现了晚明禅林禅学本位的诗禅观。吹万广真结合晚明禅林的发展现状,从“以禅喻诗”转为“以诗喻禅”的禅家本色,以禅僧的身份融合“诗”“禅”,转换了诗家与禅家以妙悟为的旨的诗禅关系。
其一,“以诗喻禅”的禅家本色。吹万广真基于对文字禅的理性认知,其诗学观念受此影响,体现了禅家本色。严羽“以禅喻诗”之说在整个明代备受推崇,谢肇淛(1549—1613年)言:“诗话当以沧浪为最”(卷二),尤其“复古派”对“妙悟说”极为尊崇,谢榛(1495年—1575年)论诗曰“诚以六祖之心为心,而入悟也弗难矣”(412),倡“悟入说”。作为禅僧的吹万虽受此影响,但其“以诗喻禅”与南宋诗论家严羽“以禅喻诗”之说显然不同,吹万以禅者的身份借诗喻禅,其要旨在禅不在诗。严羽以禅喻诗,吹万则以诗法参禅,两者一以论诗,一以论禅,取诗禅相通之法互融互用。吹万以禅学为本位,扭转了诗禅关系,从“以禅喻诗”一变而为“以诗喻禅”。吹万认为“诗家法即禅家法”,《勉学说》言:“托诗参禅不唯有好诗,兼有好禅”(释广真514b),以诗为参禅门径,以作诗之法参禅,不但诗有好诗,亦得禅旨。《沧浪诗话·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曰:“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严羽758)其论诗“自家实证实悟”之说正合吹万“参禅须透祖师关,妙悟要穷心路绝”之禅旨,诗禅关系在时代的流变中得以更迭。“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即源自禅宗正法眼藏,认为作诗先要熟读《楚辞》,以之为本,后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及至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吹万论诗言:“顿然悟后再不挨门傍户”,取作诗之法以通禅道,是自唐宋以来“借诗解禅”“借诗悟禅”之后的诗禅交互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体现了吹万挽救晚明禅林缺乏真参实悟的良苦用心。
其二,诗禅一如:“诗中有禅”“禅中有诗”。《沧浪诗话》言:“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27),与吹万禅师“做诗不参禅,不是好诗”之说法几近一致,但作为诗论家的严羽言“妙悟”仍然将“诗”与“禅”分开来看。吹万广真作为晚明高僧,与严羽“以禅喻诗”不同,其在“以诗喻禅”之上,指出诗禅一如,将诗禅等同,认为“好诗”即“好禅”。吹万曰:“真宗运夫笔端,不须学问而显了学问也;好禅道出口头,不须情境而挺特情境也”(释广真541b),“真宗”即参悟之禅旨,诗得妙悟,无学问处显学问,无情境处显情境。吹万为说明诗即为禅,禅即为诗,举白云守端禅师之“禅”与黄庭坚之“诗”为例:
1. 白云守端之禅: 山前一块闲田地,叉手叮咛问祖翁。几度卖来还自买,为怜松竹引清风。此白云端会悟语也,何尝不是诗?(541b)
2. 黄庭坚之诗: 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唤扁舟归去,旁人谓是丹青。此山谷居士诗也,何尝不是禅?(541b)
第一则为法演禅师参白云守端禅师时所作,载于《法演禅师语录·偈颂》,题为《投机》。是偈为七言绝句,押东韵,完全符合诗律,吹万认其为诗并无不当。法演禅师以“诗”言禅,以“田地”比喻妙明真心,言其无人问津而变得荒芜;“叉手叮咛问祖翁”,如同学人向祖师参禅,法演以第三视角创造参禅的情境;颈联“几度卖来还自买”则以学人不识自心,迷于事相,导致“田地”空闲;尾联言“为怜松竹引清风”,以喻中之喻来揭示自性清净心,在清风松竹中蕴含自性清净心,构造了一片淡泊清净、陶然忘机的天然之境。寓禅理于禅境,颇具宋诗理趣,体现“禅即诗”。第二则以画境为真境,不知是人中画,还是画中人,物我一如,了然无碍,活泼泼一片禅机。诗人首联以“烟雨芦雁”起笔,与潇湘洞庭融为一体,将读者亦带入画人如一的境地,天地之间唯有清净自性。在这万物一体的境界中,芦雁纷飞而“我”悠然于潇湘洞庭之上,万径无人而“我”独钓于孤舟之上,夜静水寒而“我”心不在钓与不钓,体现着自心的清净。最后诗人“顿悟”禅旨,明白原来一切皆空,不过“迷头认影”,误入歧途。黄山谷诗仍然体现了宋诗“以事言理”,但理契禅旨,故吹万言:“此山谷居士诗也,何尝不是禅”(释广真541b),体现“诗即禅”。吹万“诗禅”的转换,不得不提及宋代释梵琮《率庵梵琮禅师语录》之言:“诗中有禅,东湖湖上浪滔天,一叶扁舟破晓烟;禅中有诗,手把乌藤出门去,落花流水不相知。”(释梵琮657c)释梵琮一言“东湖”,一言“乌藤”,看似均以物象入诗,但“东湖湖上浪滔天”偏于诗家,而旨契于禅,“落花流水不相知”则无物不禅,偏于禅家之言,而契合诗境。吹万与梵琮所论,倒像是吹万对释梵琮的模拟,只是换了一副面孔。不过吹万至此未休,其最终归宿仍然在于平常心是道。在“诗禅转换”的论述之后,他说:“吾愿诸学人,体是四老,则浸种插秧、饥餐困寝,此夏亦不空过。”(释广真541b)一切归于寻常日用,归于平常是道,认为诗中有禅、禅中有诗是自然生发的,两者契合无间。
其三,诗家的“妙悟工夫”与禅家“顿悟渐修”“见性不留佛”的证禅之道。严羽《沧浪诗话》言:“工夫须从上做下”“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73),“单刀直入”说的是机锋峻烈、棒喝交加的临济宗风,直截了当,非类曹洞绵密回互之风。是言以顿悟为旨,指出悟须渐修。吹万禅师宗临济门庭,亦倡顿修渐悟说,并以之为作诗之法。释广真《吹万禅师语录》载:
从上古人有五种禅,老僧者里只用二种: 顿明自性与佛同俦,然有无始染习,须假渐修对治,令顺性起用,如人吃饭不一口便饱,此是一;见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师,目睹瞿昙犹如黄叶,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师玄旨是破草鞋,宁可赤脚不穿最好,此是一。(480c)
吹万是语持“顿悟渐修”说,认为人人自性清净,本有佛性,然因受习气熏染,“有无始染习”,须以渐修对治。然而吹万并未执着于“顿悟渐修”,进一步指出禅本无修无证,若执着于修证的工夫,则又堕入野狐禅。“见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师”,以“黄叶”“破草鞋”喻祖师禅旨,便是启悟学人无一物可执,无住无为,假名修证。吹万无住无为、无一物可执的思想,正反应了严羽《沧浪诗话》“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57)的诗学主张,“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157),妙在“顿悟”,妙在“真修”,吹万言“真修者,亦非勤亦非忘,勤则近执著,忘则落无明”(释广真481a),是为其诗学的思想渊源,即其援诗入禅的“诗家法即禅家法”(535b)的具体体现。吹万《诗僧传》曰:
盖诗家法即禅家法也,顿然悟后再不挨门傍户。所谓“拈来无不是,用处莫生疑也”,设暗窃古人之句者,如盗狐白之裘;明取古人之义者,似夺和氏之璧。令人知而不能行,见而不敢效也。(535b)
“顿然悟后再不挨门傍户”之说,道出经“顿悟渐修”之法后,作诗须自成一家,摒弃“挨门傍户”的“学诗之路”。然吹万并不认为要摒弃古人所有的“句”“义”,面对“窃古人之句”“窃古人之义”的作法,吹万以禅语答之“拈来无不是,用处莫生疑也”(535b),学人即已识得“顿悟渐修”之法,则拈与不拈古人之句,取与不取古人之义,全在自心,“用处莫生疑”,悟得要旨则无所分别,如清风明月,古今如一,古人用得处,今人亦用得。故吹万所言“无迹可寻”,是事理无碍之“无迹”,而非脱离古人空谈诗法。
二、 吹万的“真诗说”: 以“真参”“真悟”作“真诗”
吹万广真的诗学观念除了与禅林现状与禅学思想息息相关,与诗派迭出的时代亦有紧密联系。其诗学步趋“后七子”谢榛之后,二者同倡“兴、趣、意、理”的四格诗论。同时,李贽、袁宏道等晚明卓异之士所倡“童心”“性灵”之论,与晚明禅林以“真参”“真悟”为旨的诗学共同构成了晚明“求真”的诗学特征。
《诗僧传》中明确指出:“诗之法要有四”“四者: 兴、趣、意、理也”(释广真535c),据笔者目力所及,提出“兴、趣、意、理”四说者,首推“后七子”谢榛(1495—1575年)。更为契合的是,吹万与谢榛对此四者的论述方式如出一辙,兹摘录如下:
谢榛《诗家直说》卷二载:
:,,,。太白《赠汪伦》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陆龟蒙《咏白莲》曰:“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王建《宫词》曰:“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李涉《上于襄阳》曰:“下马独来寻故事,逢人惟说岘山碑。”。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228)
吹万《吹万禅师语录·诗僧传》载:
况诗之法要有四[……]:、、、[……]如册(《游戏三昧》)中友人《山居诗》曰:“彩凤自栖青菉竹,瑞麟惟向紫灵芝。从来隐士居幽处,山色浮光水色奇。”。《春雪诗》曰:“春山不见天花树,一夜殊沙到处明。”。《对桃花诗》曰:“不为东风展笑颜,机含此日露天班。”;《交秋诗》曰:“只有一瓢情不更,四时掬水当衔杯。”。(535c)
谢榛之“诗格”即吹万诗之“法要”。吹万与谢榛之“四格”的先后序次均不相差,只是吹万将谢榛所举诗句换为《游戏三昧》中友人诗句,而“替换诗句”更可证明吹万对“兴、趣、意、理”说的认同。这也意味着“后七子”谢榛诗论对吹万广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吹万广真对于谢榛之说并未全盘接受,而是将“四格”诗法导向了“真参实悟”的参禅之法。吹万所举《春雪偶作》“春山不见天花树,一夜殊沙到处明”,超脱刻画模拟之“实”,景虚而有味,展现雪夜的明净,其意趣颇似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两句,空山无人,春山亦无天花树,然无人却闻人语,无树却有处处“殊沙”,语涉大乘中观之思。《春日对桃花》“不为东风展笑颜,机含此日露天班”,意随笔生,不假布置,蕴藏禅意。此诗后两句“灵云岂是花惊眼,只喜枝头带月圆”(释广真515a)道出唐末灵云志勤禅师因桃花悟道的公案,倒是颇为符合谢榛“阅书醒心,忽然有得,意随笔生,而兴不可遏”的“辞后意”,以“他悟”开“己悟”,意到辞工,不着痕迹。对于吹万广真而言,则体现了他对“千七百则公案”态度,只要“真参实悟”,一大藏经是否“呓语”(释德清786a)都可以平常心看待。《交秋诗》与铁壁慧机《辞世别爵台养元谭公》相类,铁壁慧机《庆忠铁壁慧机禅师语录》诗曰:“沧桑世局几曾催,事主勤王正可为。只有一瓢情不更,四时掬水当衔杯。”(释慧机613b)将吹万禅师体现“禅理”的两句诗化为对谭养元的寄托之辞,化离别之思于“衔杯”。吹万以“兴”引起所咏之辞,将其导向了禅趣、禅意、禅理。吹万的“四格说”以禅为旨的,与谢榛不同。二人一僧一俗,诗学指向虽统一于“四格”,体现的却是吹万广真借谢榛“四格说”以“真参”“真悟”作“真诗”的作诗之法。
其一,吹万认为不论是“古人之句”,还是“古人之义”,都要以“真参实悟”为先,“顿然悟后再不挨门傍户”,以至作诗具备“兴、趣、意、理”四格。“真修者,亦非勤亦非忘,勤则近执著,忘则落无明”,无物可执,至无迹可寻,认为诗家法即禅家法。吹万与谢榛认为作诗不离“书”,可取古人之句,古人之义,化为己用。谢榛曰:“因人之悟,以开己之悟”(476),认为是为作诗之“天机”;吹万则认为只要“真参实悟”,作诗无物不可入,所谓“拈来无不是,用处莫生疑也”,绝非挨门傍户之家,这或许也是吹万被时人称为“山谷”后身的主要原因。吹万认为“烦恼性中有无边华藏世界”(526b),其《语录》载“君(吹万广真)栖幽地任徐徐,满座深藏万卷书”(555b),以此可见吹万对“书”的重视。
其二,观谢榛诗论,重“真”之一字,吹万亦以“真心”作“真诗”,以诗体道,体道归真。谢榛说:“‘太古之气浑而厚,中古之风纯而朴。’夫因朴生文,因拙生巧,相因相生,以至今日,其大也无垠,其深也叵测。孰能返朴复拙,以全其真,而老于一丘也邪?”(谢榛504)其论暗合吹万之言。吹万曰:“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释广真476a),“斯可与言诗,并可与语道”(532b),指出诗在于“道”。吹万在《〈唐诗响韵联珠〉题辞》中认为“世界一希声也”(532a),《诗》《离骚》《十九首》与绝句、律诗源出于“大音希声”的混沌状态,以诗体认大道,回归于“真”。“是中不可说而说,不可闻而闻者,故名真说真闻也”(540b),禅宗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的本来面目为“真说真闻”,吹万将对“真诗”的体认与“真心”结合,认为“学道不离心,离心不见道,认得真心处,豁然通三要”(507a),以“真心”解“真诗”。吹万禅学思想尤重“心”,以心为宗,认为“一心一切心,一法一切法,因法故说心,无法心何有”(505c)。吹万诗歌亦以“得心”为旨,以心为真诗鹄的,《〈缠隐草〉序》言“得之心而寄之诗也”(531b),可见吹万作诗重在“得心”。谢榛《诗家直说》载“握之在手,主之在心,使其坚不可脱,则能近而不熟,远而不生。此惟超悟者得之。”(339)“夫万物一我也,千古一心也”(364)“万转心机,乃成篇什”(355),此中数语无不展现了谢榛与吹万“诗心”相通。
其三,吹万的圆融思想,既体现在吹万“五宗一家”的融通,也体现在其基于禅林之弊的文字禅观,与谢榛“文随世变”不谋而合。谢榛不拘泥于复古,认为“学者能集众长,合而为一,若易牙以五味调和,则为全味矣”(谢榛332),与吹万的圆融思想不二。尤其吹万“力究五宗”,认为“五宗一家”,“沩仰严谨,曹洞细密,临济痛快,云门高古,法眼简明,然五者果可缺一乎?”(释广真484a)主张参究五宗之玄旨透过“大统纲宗”识“活句”。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超越时代的相合之处。吹万的“文字禅”基于禅林之弊,而非单独论“诗禅关系”,即是谢榛“文随世变”的表现。谢榛言:“《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虽其逸诗,汉人尚不可及。今学之者,务去声律,以为高古。殊不知文随世变,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于古,而终非古也。”(1)今人学诗“务去声律,以为高古”,而谢榛认为“文随世变”,今别于古,虽有意于古,“终非古也”,旨契一心,符合吹万的文字禅观。谢榛与吹万同倡“四格说”,甚至可以说,谢榛为吹万的“世外知音”,一僧一俗,因诗学观念展现了僧俗的共通之处。晚明曹洞高僧觉浪道盛之言则揭示了崇尚唐诗的谢榛与身居禅门的吹万广真诗学相同之因由:“唐人之诗,不言禅而可禅,以其意句俱活,不死于法,而机趣跃跃然在言外。”(觉浪道盛719a)一语道破唐诗与禅思之间的妙用神通。
除谢榛外,吹万禅师还受到了“童心”“性灵”文学风气的影响,袁宏道《珊瑚林》对吹万广真撰写《一贯别传》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约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末,吹万禅师至湖广衡州府潇湘湖东禅院开法,至善《行状》载“翁开法堂中,学人二百有余,皆诗赋经论之客”(释广真554c),是时湖广之地“多作竟陵体”(陈子龙415)。袁中道《淡成集叙》载“近日楚人之诗,不字字效盛唐[……]以真人而为真文。观于宗文氏之所集,可以知楚风矣。”(袁中道516)袁氏所言“楚风”重视“言其意之所欲言”的“真精神”不啻于吹万广真“真诗论”的世外知音。吹万《善哉行》言:“指上贻来四句真,大都一字皆隐括”(520c),《〈缠隐草〉序》“余尝读《法华歌》,至‘我亦当年好吟咏,将谓冥搜乱禅定。今日亲闻诵此经,何妨笔砚资真性’之句,不觉精神舒展手足舞蹈”(531b),直言诗要“真”。吹万“拈古人之句,取古人之义”看似与公安三袁反对复古相异,其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都反对“模拟之风”,吹万的“拈古、取古”是在“真参实悟”的基础上而衍发的,与“公安三袁”的“反古”并无多大区别。更为吻合的是吹万禅师与公安三袁均受到李卓吾的熏染。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核心观念便导源于李贽的“童心说”,吹万则将李卓吾“汝与我论道,吾与汝论心”之言与六祖慧能“若真修道人,行正即是道”等而视之。吹万《示灯道善人》曰:“盖道由心也,是心静而为德,受而为仁,行而为义,用而为智,在家善人,舍此别悟,即非道矣,非其道亦失其心矣。故卓吾子曰:‘汝与我论道,吾与汝论心。’六祖云:‘若真修道人,行正即是道,善人体之,则有得步光明藏之美。’”(551b)对李卓吾论“心”之言击节称赞,与谢榛“四格说”一样都体现了吹万诗歌的“得心”之旨。
综上,不论是踵事谢榛“四格说”,还是“童心”“性灵”,吹万强调的都是要以“真参”作“真诗”,对蹈袭之风深通恶绝,以“言其意之所欲言”的“真精神”为“真诗”,提倡“真参”“真悟”,古今之道一以贯之。在诗派叠出的时代,吹万以禅僧的立场道出了诗家的真髓。
三、 艺苑何如法苑长: 忠义菩提与游戏三昧
吹万禅师不止受到了时人诗论的影响,在动乱频仍的晚明,吹万禅师上承大慧禅师“菩提心则忠义心”之说,以“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圆悟克勤713b)的佛禅观念援儒入禅,融通儒释,以忠孝作佛事,展现了自己的忠义菩提心。其诗论于识韵求响之中,受到儒家诗教观念的影响,“诗言志说”深刻影响了吹万禅师的诗歌创作。要阐明的是,禅门的“诗言志”“和声律入佛音”虽有用世之思,但其道最终导归于禅,故而吹万言“艺苑何如法苑长”,乐得游戏三昧之妙,得之心而寄之诗也。
(一) “诗言志说”: 佛门“忠义”观
吹万诗歌除了写禅境、禅理为主,也体现了吹万禅师“诗言志说”的观念,主要表现了佛门以“忠孝作佛事”的忠义菩提心,展现了对抗清将士忠义之举的赞颂。《吹万禅师语录·卷十一》“自序”直言作诗之旨:
卜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山野逃诸法苑久矣,策杖风尘,栖迟岩薮,果独无言乎?言且出而不觉成句,句成而不觉带有咏焉,或长或短,或歌或叹,吾莫知其所以然。无奈侍者集而梓之,罪过罪过。(释广真512b)
观是言可知,吹万禅师作诗显然受到儒家诗教观念的影响,持“诗言志说”。《〈缠隐草〉序》曰:“夫诗何以称也?发圣贤之奥窍,影君子之规模”(531b),可见在吹万看来,诗体现了圣贤君子之志。吹万持“诗言志说”,基于他“儒释合一”的思想。吹万曰:“知儒者,知诗者,知百家诸子者,出为学人,道破关节,一则广圣贤之见闻,一则酬祖师之遗训,始不空过此夏”(550c),认为儒释合一,百家诸子悟透禅观,亦可顿悟成佛。
吹万持“诗言志说”,体现了他对明季时局的关切。吹万曰:“及外之百氏,斯以折冲外侮,应变无穷”(550c),以不即不离、随缘自适的心态面对动荡的时代。吹万《穷通论》曰:
使余之遇通而适也,则扶摇九万非高也,翼摩苍穹非大也,天地只一指耳;使余之遇穷而适也,则深于山林非幽也,巢于一枝非狭也,芥子纳须弥耳。以是观之,得非禅门敌外侮之良将耶?(535b)
吹万是言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轲281)的观念不二,遇通则扶摇直上苍穹,遇穷则隐于山林采薇,是当时士人逃禅的真实写照。如“何缘天禄喜逃禅,索我瞿昙顾命篇”(516b),“淑景春回气不寒,登登山色尽逃禅”(516b),展现了当时的逃禅现象。禅门成为士大夫“抵御外辱”的避世所在。也正是逃禅的“不得已”透射出身处禅门的吹万对时局的关切。“忠义”的主题在吹万诗歌中亦频频出现,如“由来父母勤务施,弹铗鸣兮窥士义”(520b)“戎马卢龙踏未休,渝城烽火动人愁”(519c),吹万禅师身处动乱的明季巴蜀地区,与抗清名将秦良玉、马祥麟等互有交往,其诗中常常表现出对忠臣义士的称赞。如《过花林访秦总戎》:
春江晓灿满林花,溯水轻舟崦影斜。旗鼓远声星斗映,簪缨渊霭玉金霞。定知节度重恩蜀,信有南康再御家。野衲早逢青眼顾,依依犹启入仙槎。(518c)
秦总戎,即秦良玉。从诗题来看当为吹万访秦良玉而作。首句从访花林写起,展现了春江花林的景色,当为巴蜀重新平复的写照。中间两联略写战争场面,以“节度重恩蜀”“南康再御家”,直接称颂了秦良玉的功绩。吹万好似对此仅仅以“道情”视之,以“轻舟”“仙槎”表现自己任运自适,但仍然流露出对时局的关切,对秦良玉忠义之举的感恩之情。除此诗外,吹万尚有《代作贺石柱总戎文》,其文曰“洗荡蔺巢之尘烟,巴水重新月粲,挥灭远塞之臭秽,燕城依旧衢谣”(533b),赞颂秦良玉近平巴蜀,远灭清军的功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明末禅林对儒家诗教观体现了一定的包容性,在动乱的明朝末年,儒释二者在禅林中甚至是并存的。明季脱俗逃禅的现象不绝如缕,同他们自身的处境一样,僧人也试图寻找融合儒释之道的方式,在出世、入世之间寻求平衡,将这样的观念融入到诗歌的创作之中,展现出亦禅亦儒的双重性。
(二) “识韵归响”: 一切法同一切音
吹万禅师为中如居士《唐诗响韵联珠》题辞曰:“殆将龙门积石之源涌于唐海,金波玉浪,大地皆响矣”(532a),“响”之一字对于理解吹万广真的诗学观念至为重要。吹万所言“响”具备“大道”之义,贯穿了禅宗的传心之旨。
一者,吹万认为“响”为东西佛音相汇而生,体现了东西两土佛教文化的共鸣。吹万以禅宗诗集《游戏三昧》悉为源头活水,非“溟海尾闾”之下乘诗歌。吹万所谓诗歌源头,《〈唐诗响韵联珠〉题辞》曰:
伶伦取嶰谷之竹为籥,音律成而鸾凤皆舞;善知童子唱四十二字,厥义串三贤十圣萨埵位。曹子建游鱼山,聆穴中之音而作梵,则东西两土韵响始相协矣。(532a)
是语指出东土之音律源自伶伦取嶰谷之竹以制乐,而佛教则起自善知众艺童子教唱华严四十二字母,至曹植则合东西两土之韵为一,“东西两土韵响始相协”,故此“响”之一字表面关涉佛教吟唱,实际上指的是东西佛音相汇,至曹植东西佛教文化共鸣而生之“响”,借韵律以表征其同。
二者,吹万认为“响”展现了华梵文化相互融通的态势。吹万曰:“或谓诗者,歌咏性情也,何拘拘于响韵哉”,则展现了诗与“响”之间存在另一种关系。从“龙门积石”至唐代近体诗,吹万曰:“怛闼老子,大圣人也,尚美频伽未出之卵,盖重其音也。夫音借韵以成句,续句以成章,章之长短,即言之长短也。是而有风焉,有雅焉,有三颂焉。[……]潜通岁时之气,故音变则声变,律变则气变,所以《毛诗》之后有《离骚》,《离骚》之后有《十九首》,《十九首》之后变辞为绝,敲乐为律,殆将龙门积石之源涌于唐海,金波玉浪,大地皆响矣。”(532a)由音借韵而成句,继之而有风、雅、颂,而有诗、骚、十九首,再而为绝、为律,都是从“音”而来。是说不但阐明“响”之由来是诗歌演变发展的结果,同时认为东西两土之音从源头同为一音,以致借韵成句,终至敲乐以成律诗,东西“大地皆响矣”。故吹万之“响”有存在东西佛教文化相互融通,最终合流的一种态势,远远超越了韵律的范畴。
三者,“响”具备“大道”之义,不论圣贤、君子、骚客、隐逸之士悉秉其“大道”而可“响”。吹万言:“世界一希声也,布而为音,为律,为辞,可令人念兹在兹,咏兹在兹,惺惺成大丈夫相”(532a),认为“响”由老子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义而来,最后具有“大丈夫相”。故其言:“时而击竹唱易水之歌,时而饭牛作南山之韵,时而执爨题问影之诗,时而蹑屏调天衢之句,优哉游哉!诚众甫中之真逍遥也。”(532a)“响”韵已成,而有“道”存焉,如“击竹唱易水之歌”,道出吹万身处禅林而托志于世外的忠义之举,故以禅林“击竹”悟道之举而言荆轲《易水》之寒;再如“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沈德潜9),表现了宁戚生不逢时之叹。以此可见吹万对“响”赋予的“大丈夫之相”。故吹万曰:“善观者不可泥于韵而求义,当于韵而求响,斯可与言诗,并可与语道”(532a-b),“响”具备“声韵”与“大道”之义。吹万《〈缠隐草〉序》曰:“夫诗何以称也?发圣贤之奥窍,影君子之规模,写骚客之清狂,摹隐逸之雅况。所以皎、灵二沙门,打破铁瓮之余,挑商刻羽;欧、苏两夫子开了关钥之后,赓韵联吟。”(531b)从这里可以看出,吹万认为“诗”蕴于“挑商刻羽”“赓韵联吟”的韵律中,当有圣贤、君子、骚客、隐逸之风,不分僧俗皆可为之。
统而言之,“响”实则贯穿了禅宗的传心之旨。北宋末耿延禧为圆悟克勤禅师所作《序》曰:“佛以一音而演说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诸佛此一音,六代祖师此一音,天下老和尚此一音。”(圆悟克勤713b)耿氏言佛之一音展现了禅宗“以心传心”之旨,正是吹万禅师“响”之一字的绝妙注解。“响”正是禅宗“一音一切音”“一法一切法”的体现,只有真参实悟、了明自性才可识得何者为“响”。
(三) 游戏三昧:“得之心而寓之诗也”
有趣的是,不论李贽还是袁宏道,他们虽然倡导“真诗”,但也提出“以游戏之态为文”的“无法说”,吹万亦言其“得之心而寓之诗”的游戏禅道,甚至被时人称为“山谷后身”,戏以“吹苑”号之。吹万《吹万禅师语录·山谷亭记》载:
华仙评诗时,每带《山谷集》中语以似余,众莫之测。次二日长至见访遗笔,卷首则曰:“山谷前身”。询其意,谓余前身乃黄山谷也,复以“吹苑”号之,谓取山谷悟道于木稚花之义,赠其“三绝”,大露山野之丑矣。(释广真526a)
华仙,号曰琼华老仙,自叙为明初进士张伯雍(526a)。此琼华仙人以黄庭坚参晦堂禅师因“木稚花香”悟道,与吹万作比,认为吹万乃一“诗僧”,以“师(吹万)乃宋太史黄山谷后身”(555b)称之,以此讥讽吹万禅师。琼华仙人并有“三绝诗”赠吹万:
其一曰: 山容此日有山灵,我来访客草青青。前身黄谷今犹在,一座明灯一卷经。
其二曰: 竹深云坞树茵苔,我得登临山色开。一笑过溪亲座处,囊收天地古今怀。
其三曰: 君栖幽地任徐徐,满座深藏万卷书。秘著三车开世路,千秋遗业古今图。(555b)
琼华仙人三诗说的正是吹万为山谷后身,尤其第三首言“满座深藏万卷书”“秘著三车开世路”,展现了吹万禅师藏书之多,著述之丰,正合“吹苑”之称。“吹苑”虽是戏称,却道出了吹万以“文字”为禅的一面。不过吹万《阅藏说》对其作出了回应:“倘能十藏经中,拾得眉睫之宝,便可道得禅教不干一句。”(542a)“且禅是佛祖所传之心,教是佛祖所说之法,皆不离一心上体用”(542a),秉持禅教一致、体用一如的观念,认为阅藏不离禅,“诗禅”不一不异。
细绎《语录》,吹万其实是以“游戏三昧”之态而对“艺苑”,《〈缠隐草〉序》曰:“要皆不在诗而在游戏三昧也。游戏三昧之妙,得之心而寄之诗也。”(531b)借用欧阳修“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1021),以称其作诗缘由。吹万曰:
余尝读《法华歌》,至“我亦当年好吟咏,将谓冥搜乱禅定。今日亲闻诵此经,何妨笔砚资真性”之句,不觉精神舒展手足舞蹈,呻之曰:“是先得我心也,得不以山花啼鸟,松声草色而赏吾之般若法身耶?”(531b)
“山花啼鸟,松声草色”皆为自心所现,种种世间之相悉为般若法身。吹万并将是举与寒山、船子和尚相比,言“寒山写溪岫之影相,舡子赋钓竿之浮沉,要皆不在诗而在游戏三昧”(531b)。吹万寄心于诗,并非徒然思虑作诗,故其言“风雅赋颂、兴观群怨之工”“不思而自得”(531b),世人不识自性清净心,故而以“吹苑”号之。
吹万曰:“出有入无,应来化去,莫不以这个东西为药为病,即缚即脱,总教堪忍中。族姓子识得烦恼性中有无边华藏世界也。一山谷居士于我何轻重哉?”(526b)吹万作诗,出入于僧俗之间,不以此“为药为病”,心无挂碍,于烦恼性中识得无边华藏世界,不以“山谷”患得患失。“宋则山谷隐矣,明则吹万显矣,厥隐厥显,何通何塞,厥俗厥真,何增何减”(526b),识得其中隐显通塞、真俗增减事事无碍之理,即识得吹万作诗之道。
吹万以“山谷”作佛事的另一面则体现了其担当振兴济宗的大任。吹万曰:“山谷得法于黄龙南之后晦堂心禅师也,济上之宗时亦盛之;至于我朝,续如悬线,且径山慧祖则无大显之裔矣。山野幸接慧祖未斩之脉,实欲鼎沸济宗也,又安知山谷之愿不如仰山之愿乎?”(526b)吹万之心系济宗法脉,“余(吹万广真)但愿济宗之长,谓我为山谷可,谓我为吹万亦可”(526b),出入僧俗之间,体现了吹万不可不为之缘由,认为黄庭坚参禅“不可不创”,而诗亦“不可不居”,琼华仙人以“吹苑”讥之,不识佛禅境界尔。《讲僧传》曰:“可说者,文字句义也;不可说者,性觉未明也。可闻者,音声语言也;不可闻者,妙明未起也。”(535c)诗与非诗,在于性觉妙明之“真心”,而非诗歌本身。
结 语
吹万广真创建聚云禅系,不但在晚明巴蜀禅林影响深远,其文学创作涉及诗、词、曲、赋、小说等多种文体,《释教三字经》在禅林广为流播,其诗学观念以禅僧的立场融通儒释,对于禅宗诗学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吹万禅师的诗禅观念,力争跳脱“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的藩篱,与禅林现状和禅学思想紧密相关,启发我们在研究禅宗诗学时要深度结合禅宗史、禅宗思想,把握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避免以偏概全。晚明作为特殊的历史节点,烽鼓不息,又兼禅道下衰,禅林急需以真源印心,维系法脉,而高僧大德又心存用世之思,以忠孝作佛事,践行忠义菩提的佛门善举,僧俗交互频繁。在禅门嬗代厘革之际,诸种因素交错其间,故而从禅宗诗学角度对晚明儒释交互的诗学状况予以深入考察是比较困难的。笔者此处也只是浅尝辄止,更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① 聚云吹万禅师(1582—1639年),讳广真,俗姓李,僰道宜宾(今四川省宜宾市)人,对明末巴蜀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称明季巴蜀禅林第一僧。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七月,吹万广真礼月明联池禅师出家受具,后游吴、越、闽、粤,还蜀后驻锡忠州聚云禅院。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去世,世寿五十八,僧腊二十七。吹万广真著述宏富,有《一贯别传》《古音王传》《恣夏草》《说乐正论》《文字禅那》《偏说九辩》《心经诠注》《居士颂》等二十多种。现存《聚云吹万真禅师语录》三卷,《吹万禅师语录》二十卷,《一贯别传》四卷,《古音王传》一卷,《释教三字经》一卷。《释教三字经》在禅林流传甚广。释至善《行状》、田华国《吹万禅师塔铭》、释自融《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释性统《续灯正统》载其生平事迹。
② 周裕锴指出“文字禅”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字禅”即所谓“以文字为禅”,是包容了佛经文句、古德语录、公案话头、禅师偈颂、诗僧艺文等形式各异、门风不同的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狭义的“文字禅”是诗与禅的结晶,即以诗证禅,或就是诗的别称(《文字禅与宋代诗学》3)。本文所采用的文字禅即与诗相对应的狭义文字禅之定义。
③ 吹万广真所举“白云守端之偈”实为法演禅师之《投机》偈(《法演禅师语录》666a)。“黄庭坚之诗”即《惠崇芦雁》,一说为苏轼所作(《苏轼全集校注》5786)。
④ 《全唐诗》作“还应一作无情有恨无一作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全唐诗》7211)
⑤ 《全唐诗》作“歇马独来寻故事,逢人唯说岘山碑。”(《全唐诗》5432)
⑥ “响”作为批评术语在魏晋时期便已引入,但观历代诗论家对“响”的评点,与吹万所言“响”并不一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222—225;《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285—287)。
⑦ 《吹万禅师语录·诗僧传》载:“造其前,揖而问之,不答,但袖出一册,题曰《游戏三昧》。彻读之句句非溟海尾闾也,乃龙门积石也,昆仑也。”(《吹万禅师语录》535b)
陈子龙: 《陈子龙诗集》,施蛰存、马祖熙标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Chen, Zilong.. Eds. Shi Zhecun and Ma Zux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3.]
李小荣 杨遇青: 《中国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研究论纲——从东晋到晚清》,《东南学术》1(2019): 194—212。
[Li, Xiaorong, and Yang Yuqing. “A Research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ese Buddhism: From the Eastern Jin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1(2019): 194-212.]
孟轲: 《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 中华书局,2010年。
[Meng, Ke. Mencius. Ed. Yang Boj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欧阳修: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洪本健校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Ouyang, Xiu. Collected Poetry and Essays of Ouyang Xiu. Ed. Hong Benjia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9.]
彭定求等: 《全唐诗》。北京: 中华书局,1960年。
[Peng, Dingqiu,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沈德潜: 《古诗源》,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
[Shen, Deqi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释达观: 《石门文字禅序》,《石门文字禅校注》,周裕锴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2。
[Shi, Daguan. “Preface to.” Literary Zen from Shimen. Ed. Zhou Yuka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21.1-2.]
释道盛: 《天界觉浪盛禅师全录》,《嘉兴藏》第34册。
[Shi, Daosheng.. Vol.34.]
释德清: 《憨山老人梦游集》。X.73. No.1456。(《卍新续藏》简写为X,册数标于其后)
[Shi, Deqing.. Vol.73, No.1456.]
释梵琮: 《率庵梵琮禅师语录》。X.69. No.1364。
[Shi, Fancong.. Vol.69, No.1364.]
释法演: 《法演禅师语录》。T.73.No.1995。(《大正藏》简写为T,册数标于其后)
[Shi, Fayang.. Vol.47, No.1995.]
释广真: 《吹万禅师语录》,《嘉兴藏》第29册。
[Shi, Guangzhen.. Vol.29.]
释慧机: 《庆忠铁壁慧机禅师语录》,《嘉兴藏》第29册。
[Shi, Huiji.. Vol.29.]
释克勤: 《佛果圆悟禅师语录》。T.47. No.1997。
[Shi, Keqin.. Vol.47, No.1997.]
释智旭: 《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嘉兴藏》第36册。
[Shi, Zhixu.. Vol.36.]
释祩宏: 《竹窗随笔》,《嘉兴藏》第33册。
[Shi, Zhuhong.. Vol.33.]
苏轼: 《苏轼全集校注》,张志烈等校注。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Su, Shi. The Complete Works of Su Shi. Eds. Zhang Zhilie,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汪涌豪: 《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Wang, Yonghao..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谢肇淛: 《文海披沙》,明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Xie, Zhaozhe.. Vol.2.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1609.]
谢榛: 《诗家直说笺注》,李庆立等笺注。济南: 齐鲁书社,1987年。
[Xie, Zhen. Blunt Comments of a Poet. Eds. Li Qingli, et al. Jinan: Qilu Press, 1987.]
严羽撰: 《沧浪诗话校笺》,张健校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Yan, Yu. Canlang’s Remarks on Poetry. Ed. Zhang Jia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袁中道: 《珂雪斋集》,钱伯城点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Yuan, Zhongdao.. Ed. Qian Boch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9.]
张培锋: 《佛教与传统吟唱的文化学考察》。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2016年。
[Zhang, Peifeng..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6.]
周裕锴: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Zhou, Yukai..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