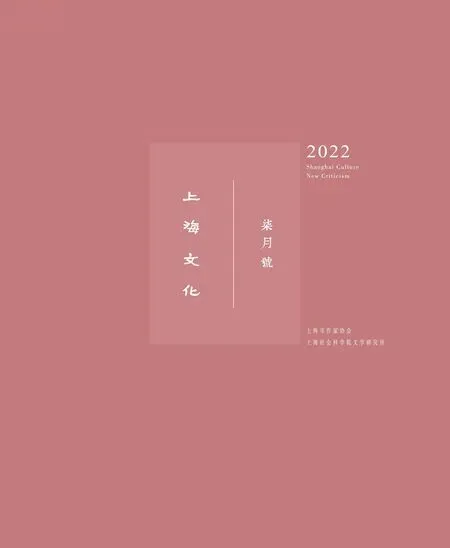窥视,臆想,推开悬疑之门辛丑年阅读小说的零散笔记
李庆西
窥视者被窥视
1953年,罗布-格里耶出版了《橡皮》,两年后又推出《窥视者》,这两部小说在法国“新小说”圈子里都占据重要位置。相比之下,《窥视者》更接近写实主义真谛,是将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剥离开来的一个出色样本。
这部小说以简单叙事造成复杂效果,手法比较少见。说其简单,是仅以一个推销员到海岛上推销廉价手表为故事梗概,并未介入历史与现实的特定语境。那个叫马弟雅思的旅行推销员,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上岛时间意味着销售和赢利),可是时间并非呈现线性过程,整个叙述兜兜转转不断回溯,造成一种复沓效果,其中夹杂着主人公的想象和回忆,有时让人很难分辨眼前的情节处于何种时态。阳光下,镇子中心那座雕像和它周围的铁栏杆投下的阴影,暗示犹疑的路径。当推销员踏入那个阴影的中心,影子构成的那张网便跟着他的脚步挪移,导入种种枝蔓性叙事。
现实的情形嵌入了早年的影像——马弟雅思就出生在岛上,离开这个岛有三十年了,他曾在这里度过自己阴暗的童年。模糊的影像伴随着心有旁骛的叙述,他在咖啡店里窥视女招待的身体,窥视她给顾客斟酒的动作,偷听水手们的闲聊……书中对楼上铺着黑白瓷砖的卧室里的陈设做了详尽描述,切入童年时的可怕记忆。在隔壁糖果店里,他向女店主推销他的手表,人家抽屉里居然也有跟他一模一样的货色,这时候他还没有发现自己“一直游荡在一种失去感觉的幻境中”。
他借了自行车往村子里去,途中见到农妇马力克太太的情形故意写了两遍,之间夹着周围景物和修理自行车的描述。又如第一章咖啡店里的场景,第二章又反复出现。这种重述手法,犹似警匪片中探案人重新播放监控视频,图像定格或放慢放大之后必然发现新的细节。不过,回旋式递次推进更多地表现他的游移状态,令人阅读中不免产生朦胧之感。
记忆和现实都缺乏辨识度,岛上所有的房屋都是相似的,周围的悬崖也都一模一样。这些叙述中穿插了一些意识流式的印象和幻觉。那些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细节都栩栩如生地记录下来,但少女雅克莲之死却是一个叙事空白。绳子,木桩,烟头和岩石上的毛衣,闪烁其辞地透露现场情形。小说虽是第三人称叙事,但一切只缘从主人公的视角。
推销员煞费苦心地从时间上安排自己不在场的说辞,谁知悬崖上早就有人在窥视他……窥视者被窥视,这让人想起埃舍尔的《画廊》。看客成了被看,是一种哲理假设。这里,暧昧的镜像关系意味着窥视的无限可能,一切秘密都不再是秘密。罗布-格里耶不是写犯罪小说,犯罪的桥段只能读者自己去想象和补充。有时候写作就是为了印证想象与实际事物之间的差异,无意义的描述伴随着种种错觉,藉以还原某个真实的存在。
杀手一题
海明威有个题为《杀手》(又译《杀人者》)的短篇,写两个杀手去小镇上刺杀一个叫安德森的瑞典人。其中大部分篇幅叙说他们在亨利餐厅的盘桓与等待,他们来早了,要了火腿和培根煎蛋,在那儿边吃边等。他们掌握的情况是安德森通常晚上六点来这儿就餐。艾尔和马克斯,这两个杀手,从五点进店,等到七点十分,安德森一直未出现。最后两人收起锯短的滑膛枪,“开开心心”走了。其间,他们把黑人厨子和跑堂的小伙子尼克押到后厨捆绑起来,只留柜台上的乔治应付客人。其实客人寥寥,更多的笔墨花费在两个杀手跟乔治的对话。海明威用冷隽的短句写对话,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黑道人物的找茬、耍横和无厘头。这两家伙显然不是职业杀手,不惮亮出身份,还告诉人家他们是来杀谁的。
有一点很费解,他们走后,尼克跑到后巷出租公寓给安德森通风报信。那个重量级职业拳击手躺在床上,漠然地盯着墙壁,没有任何表情。他好像知道这事儿。尼克建议去警察局报案,安德森说没用,眼睛一直对着墙壁。公寓管理员贝尔太太告诉尼克,安德森先生是个好人,而且很绅士。尼克回去报告乔治,两人便猜测,安德森准是在芝加哥(故事中的小镇在芝加哥附近)惹了什么麻烦。尼克感到一阵恐惧,乔治劝他别再想这事儿了。
这个短篇不算很短,译文大约八千字,行文很紧凑,是典型的海明威的电报式风格。说实在,我没怎么看懂,整个叙述真是所谓冰山一角,很难推测那些隐去的部分。人们谈论海明威的含蓄往往举述他另一个短篇《白象似的群山》,那篇当然很有名,但《杀手》这篇被遮蔽的东西更多。我的一位朋友自有他独到的解读,他说这里未必有何深意,艾尔和马克斯不过是两个小混混,冒充杀手来吃霸王餐而已。你看,别的客人买了打包带走的三明治,小说特意交代:“客人付了钱,走了。”艾尔他俩吃了火腿和培根煎蛋,付钱了吗?我又看了一遍,倒是没写他们付没付钱。可问题是,这种低级杀手,出来办事是否也该照规矩买单?我竟犯傻,琢磨半天也不能确定他们是要杀人还是来蹭吃蹭喝。
狩猎的想象
海明威那次去非洲是哪一年?好像是1933年,他跟着一个狩猎旅行团去非洲打猎,在那儿大概待了一个月。他的两个短篇名作《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乞力马扎罗的雪》就是那次旅行的产物,在一次访谈中他专门说到,这两个故事是根据那次游猎得到的“知识和经验”虚构出来的。
这两个短篇都跟狩猎有关,都涉及死亡和男人的勇气,等等。然而,许多专家并未意识到,其中更重要的是对于富人精神生活的窥视或想象。1930年代,海明威已是成功作家,完全摆脱了早年的贫困与窘迫,开始思考财富的意义。但是,他对菲茨杰拉德那种关于财富带来的人生的想象很不以为然。那些真正的富豪,像他写的麦康伯和哈里夫妇,为什么不在纽约或巴黎那种大都市的豪宅里好好待着,偏要跑到满地荆棘鬣狗出没的地方来。评论者或以为是表现了富人精神世界的空虚,这种说法太容易了,好像也没有太离谱。人们自然可以联系到那种狩猎活动的隐秘动机,什么野性的呼唤,寻找原始经验什么的。可是,麦康伯和哈里夫妇走进丛林,带着司机、仆人和厨子一大堆随从而来,这跟原始的狩猎活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即所谓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其实对于世间不富裕的普通人来说,被限制的并不只是物质层面的认知,而是难以窥测财富带来的精神世界的变化。照海明威小说里的表达,他们是想寻找一种重塑自我尊严的机会,因而不惮将自己投入艰险境地,他们渴望的是某种超越现实人生的精神自赎。当然,这种超越现实的想象,还真是离不开现实的财富基础,海明威的故事明显带有反讽意味。问题是,这种想象一旦真的逼近残酷现实,也就剥离了财富的意义。
白夜梦
故事越简单的小说越是不太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只写了两个人物,没有名字的男主人公和那个叫娜丝金卡的姑娘,一起在河滨街道上徘徊了四个夜晚,只是各自诉说自己的境遇和幻想,没有复杂的情节。两个年轻人虽说过得不如意,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惯于描述苦难和邪恶,这回却大不一样,没有一点撕心裂肺的东西。彼得堡朦胧的白夜遮蔽了生活的真相,眼前一切都飘飘忽忽,孤独者泡上了孤独者,带着某种幻想走入对方心灵。
姑娘向“我”表示了爱意,四个夜晚的踯躅总算有了结果,却不意半路杀出前男友。那人去了莫斯科之后一直杳无音信,她以为他把她甩了。现在外出打拼者如期归来,娜丝金卡没有丝毫犹豫,回头亲吻了“我”作为告别,再一回头,便随那人一同而去。
也许,年轻时读到这篇小说,我该和“我”一样怅然若失。可是我很晚才读到它,面对如此简单空乏的爱情故事,我还是习惯地代入复杂的生活经验,还想着能有什么理论可以阐释……我突然意识到这太傻。不知为什么,大师的作品总会让我们觉得深不可测。
亲戚朋友一条龙
索尔·贝娄的短篇一般都很长,《亲戚》这篇差不多有五万字,从头到尾嵌合着当下情境与历史记忆。贝娄擅长横生枝节的叙事,不时另扯一道,却是收放自如。主人公艾嘉·布罗茨基,曾在电视台主持庭审案例节目,后来在兰德公司搞数据分析,现在做金融咨询。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代入了贝娄自己的人生体验,虽然二者身份完全不同。当然,艾嘉也是犹太人。因为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绰号叫“坦克”的表弟出事了,表妹尤妮思就来找他去跟法官说情。艾勒法官是他老相识,果然让“坦克”缩短了刑期。
艾嘉并不是多么在乎亲戚关系,但他不能不顾及尤妮思姐弟死去的母亲莎娜表姑留给自己的美好记忆。其实,“坦克”许多年也不跟他来往,只是遇到事儿才找上来。平时,各自的人生都在不同的朋友圈里,混黑社会的表弟有自己的老大和马仔,说到这儿又不惮其烦地叙说黑道上那些破事。表弟这边刚完,又扯到搞人类学的泽克堂兄,然后又是出车祸的表舅莫迪。然后,又有一位三十年没见面的姑表兄来信求助,此人已是癌症后期,想到“二战”时自己所在部队横渡易北河的辉煌,决意死后葬于当年的战场。虽然他战后只是开出租车谋生,据说在生物学、物理学、史学和哲学几方面都深有造诣,自己深信“他的影响将作为人类的荣耀和尊严而延至后世”。艾嘉不得不大费周折地替他去安排身后之事。
艾嘉的人生本已脱离亲戚关系的连缀,现在又陷入其中。前妻嘲讽他对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过于热心,他却内疚于独享“世界崩溃带来的自由”——按黑格尔的说法,“历史的针脚再次开线,传统的联系再次分崩离析,多少世纪的约束转眼便杳无踪影”。他所面临窘境让人想起贝娄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描述的孤独与迷惘,作为成功人士的艾嘉是另一个晕头转向的约瑟夫。现代人从家族和亲情的樊篱中突围,却又产生无尽的乡愁,而命运永远悬而未决。
读贝娄此作,想起过去杭州人一句老话:“亲戚朋友一条龙,吃来吃去吃不穷。”其实,这话往往是带有嘲意的反语。
克莱采奏鸣曲
读贝娄此作,想起过去杭州人一句老话:“亲戚朋友一条龙,吃来吃去吃不穷。”其实,这话往往是带有嘲意的反语
托尔斯泰名作《克莱采奏鸣曲》发表于1891年,是他“最后审判时期”的作品。这故事比较特别,人物、观念都相当出格。主人公波兹德内歇夫年轻时是个出入花街柳巷的浪荡子,婚后竟成了追求纯洁、高尚的正人君子。可他并不赞美婚姻,相反认为婚姻是骗局,有谓“结婚无非是交配罢了”。他痛恨女性的诱惑,认为女性利用了男人的性欲成了世界的统治者。在他看来,女性的风姿绰约和充满活力都是社会危害。作为官员和贵族,他不能不关注社会堕落的种种问题,故一再申言,“上流社会允许男女接近,简直达到危险的地步”。因而,当音乐家特鲁哈切夫斯基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危机就逼近了。
在家庭音乐会上,他妻子和特鲁哈切夫斯基一同演奏贝多芬的《克莱采奏鸣曲》,那一刻他好像被催眠了,唤起了某种他自己称之“不伦不类的”感情。然后,他放心地去外地参加会议。可是心中的疑虑并没有消除,那天夜里,他从外地匆匆赶回莫斯科家中,看到妻子正和音乐家坐在钢琴前,竟不啻捉奸在床——他愤怒地扑上去,没能摁住音乐家,却把自己妻子给杀了(后来因为法庭裁定他是“被侮辱”的丈夫,被宣判无罪开释)。
这个故事有个第一人称的叙事人,就是火车上一个未作自我介绍的乘客,但小说自第三节开始至末尾第二十八节几乎全是主人公的自述,他在车厢里向几个陌生乘客讲述自己道德理念和家庭悲剧。这种二度叙事在19世纪小说中是一种常见的语态,只是波兹德内歇夫振振有词的冗长言述好像完全成了作者的声音,既是癫狂又是理性的自省,几乎展示一种拉奥孔式的痛苦情境。叙事人被撇在一边,托尔斯泰借助波兹德内歇夫颇为雄辩的言述,将家庭和社会,包括自我,包括艺术,都推向黑暗之处。
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一书对托翁后期作品有专文评述,不知为什么,偏是不提这篇《克莱采奏鸣曲》。
阴影线
康拉德小说《阴影线》的主人公(没有名字的“我”),原是一艘轮船的大副,好像没什么理由就辞职不干了,按书中说法就是年轻人的“任性”(其实他不年轻了)。在新加坡办完交割,他准备搭乘邮船返回英国。就在这时接到航务部门任命,让他出任一艘帆船的船长。在康拉德那个时代,帆船尚未退出远洋航运,老资格的水手都认为驾驶帆船才算得真正的海员。我们的主人公马上改了主意,喜孜孜到曼谷去接管他的船。开头这两节写得比较冗繁,耐心读下去,等到他的船驶入暹罗湾,算是进入主要情节。前两次我读到后边,对前边的铺垫已然淡忘。
原先的船长死在海上,海葬于暹罗湾北纬八度二十分,这是书中描述的一道“阴影线”,现在他们的船很难越过这片水域。十几天了,海上没有风,帆船只是在水上漂泊。除了“我”和船上的厨子,所有的船员都得了热病,仿佛老船长的阴魂缠住了这条船。这些情节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你不能想象下一刻将发生什么——也许小说描述的境况都不如你想到的凶险。康拉德精心营造了那种氛围,然后让读者去胡思乱想。最后,暴风雨来了。熬成鬼影似的船员们一个个挣扎起来,拽紧缆索,操控帆桁,掌舵的“我”忽然意识到,那魔咒终于被解除了。他们在海上行驶二十一天才抵达新加坡港。那道“阴影线”是人生过程的一个坎,小说开头的地方就有这种哲理性陈述,只是不经受海上的一番磨难(也是阅读的折磨),很难领悟他的意思。
双城记,双重主题

随着顺时叙述的情节推移,一切都在演化。狄更斯的描绘不但层次分明,也非常透彻,并不像涂在油画布上的颜料那样完全覆盖了前边的色彩。最后,《双城记》的传奇叙事由西德尼·卡顿的自我献身宣告结束,完成了互相渗透的双重主题:阶级 / 仇恨 / 杀戮,自由 / 平等 / 博爱。一切在在可见。
满地碎屑的悬疑故事
诺曼·梅勒写《硬汉不跳舞》,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隐喻目标。他将故事安排在新英格兰科德角那个名叫普罗文斯敦的小镇,按书中说法,这是当年英国清教徒最初抵达新大陆的登陆点。只是几个星期后,由于某种原因,越洋而来的人们又渡过海湾去了西边的普利茅斯,结果让那儿成了美国历史的起点。在梅勒看来,历史就是一堆散沙。
小说以主人公蒂姆·马登的视角作叙述,这人自称作家,其实是不务正业的嬉皮士。故事开始时,他妻子帕蒂已离家出走二十四天了。那天晚上,蒂姆在“望夫台”酒吧邂逅来自加州的一对男女,杰西卡和伦纳德,因为那女的长得很像他妻子,便凑上去跟他们聊了半天。在随后的故事里,我们知道这两人当晚就出事了。蒂姆第二天醒来,发现自己身上莫名其妙出现了一个刺青花纹,竟想不起是怎么来的,大概是酒精和大麻把脑子搞坏了。随之,加州女人和她的男伴失踪了。蒂姆汽车里发现了血迹,警长雷杰西盯上他了。后边的故事很难三言两语复述一遍,总之蒂姆竭力想理出个头绪,到处找人问询。蜘蛛尼森,斯都迪,哈坡,玛蒂琳,沃德利……还有他老爸道奇,当然还有警长,一个个都相继出场。其中玛德琳是他过去的情人,后来嫁给了雷杰西,而他妻子帕蒂又是警长的情人。世界太小,又是满世界的夹缠不清,其中夹杂着许多往事与回想。说实在,这些意识流破事让我看得晕头转向。
梅勒这个疑案故事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一切探案小说。因为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侦探,蒂姆到处找人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而雷杰西插手其中并不代表警方立场。小说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讲述来剖示案情,由各自的言述一层层揭开包袱皮。但问题是,所有的言述都基于各自的立场与视角,很难说他们的供词是抖落内情还是遮蔽真相,其实都属于所谓“不可靠的叙述”。蒂姆的脑子里根本就是一团浆糊。所有这些,远比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里举述的例子更符合“不可靠”的技术要求。
既然历史是一堆散沙,在梅勒看来,现实也是难以收拾的碎屑。
寻找“快乐的死”
1937年,加缪二十四岁,写出了小说处女作《快乐的死》。也许他自己不太满意,生前未予发表。我过去读到的加缪作品集里都没有这部作品。现在有梁若瑜所译单行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中译本仅八万字,比他五年后出手的成名作《局外人》篇幅略长。有意思的是,《局外人》的叙事结构跟它有些相像,都是分作两个部分,按时间顺序叙述,第一部重点都落在主人公的杀人,第二部则讲述如何因命案而改变主人公命运。对了,两个小说主人公都叫梅尔索(《局外人》译本作默而索,或莫尔索),都是在港口上班的货运员(负责核对提货单之类)。不同的是《局外人》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而《快乐的死》则是第三人称。
平心而论,《快乐的死》写得相当漂亮,文字甚至比《局外人》来得细腻也更灵动。小说开头就是梅尔索枪杀萨格勒斯的场景,被害人坦然面对的神态,似乎表明这其中有什么默契。主人公是通过女友玛莎结识这个坐轮椅的残疾人,后边几章对两人的交往有一种微妙叙述,他们谈论某种人生感受,试图定义快乐与幸福,萨格勒斯俨然以智者的大彻大悟开导眼前的年轻人。但残疾已经使他不可能实现人生的目标。小说没有点明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你可以想象一种共谋关系。年轻的作者将叙述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真是毫无破绽。梅尔索拿到死者的钱财,获得了有经济保障的“自由”,但他并没有获得人生的快乐。小说第二部先是写他去欧洲旅游,然后回到阿尔及利亚寻找快乐,所有的叙事都有贴实的描述,却又给人一种失焦的感觉,那些很有真实感的细节却拼写不出真实的人生,他仿佛迷失在冷漠之中。尽管身边不乏漂亮的女友,他并未沉溺于友谊与爱恋之中。他去什努亚海边独居,或是“有意识的”自我放逐,最后在病中面临死神召唤。
小说有大量的内心活动,却不能让人真正窥识梅尔索这个人物的内心。他没有反省和忏悔,关于快乐的终极思考也比较简单。比起《局外人》,这部小说所描写的人物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过于含混,更像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局内人。
时间,或生命轨迹
科塔萨尔的《追求者》看似长篇结构,篇幅却不长,中译本只有五万多字。主人公约翰尼是吹奏萨克斯管的爵士乐手,在这一行里算是顶级人物,也是一个难以常理揆度的家伙。也许天生秉性不凡,也许是吸食大麻和生活比较混乱的缘故,这人脑子就是跟人不一样。比如在他看来,音乐和自己思考的东西尽可以塞进时间里——从圣米歇尔站上了地铁,坐到奥德翁是一分半钟,他脑子里想着他妻子和孩子,想到妻子拉恩穿着绿色连衣裙的样子,裙子上的丝带和蝴蝶结,想到他家隔壁的迈克,迈克跟他讲述的科罗拉多野马的故事,还有他孩子奏出的每一个音符以及他母亲的祷告……所有这些内容转换成言语讲述,得花多少时间?布鲁诺掂量着,至少一刻钟,可能还更长。因而约翰尼得出的结论是,生命需要找对门路,不应该卡在以钟表计量的时间里。
布鲁诺是巴黎一家报社记者,也是一位爵士乐评论家。在小说里他作为叙事人,以第一人称的“我”讲述自己与约翰尼的交往过程。作为约翰尼的传记作者,他总是担心这伟大而荒谬的人物偏离正轨,可是这约翰尼时不时要弄出点事儿。经常是大麻吸食过量,生病发烧不算,不是将萨克斯管扔在地上踩踏,就是在录音棚里跟其他乐手闹掰。不用说,这人的艺术感觉确实与众不同,对自己出色的演奏并不满意,别人不看好的东西他却视如宝贝。他不太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然,对布鲁诺写他的传记也不满意,他说那是镜子里的他。布鲁诺说镜子是忠实的,他非说还缺了点什么。
布鲁诺不理解他“穷尽一生在音乐中寻求那扇门”的意思,不知道他到底在追求什么。故事大部分是约翰尼在巴黎的生活情景,他小女儿在芝加哥去世后,他和新交的女友回到纽约。再后来,布鲁诺收到那女人的信,说约翰尼死了,看电视时咳嗽了几声就一头栽倒。传记作者对传主人生预期总是落空,这难免让人读出双重荒谬的意味。
科塔萨尔的主题很难归纳,如果说是表现追求的虚无(存在的荒谬?),好像还缺少点什么。用文学评论眼光去阅读他的作品,总觉自己才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