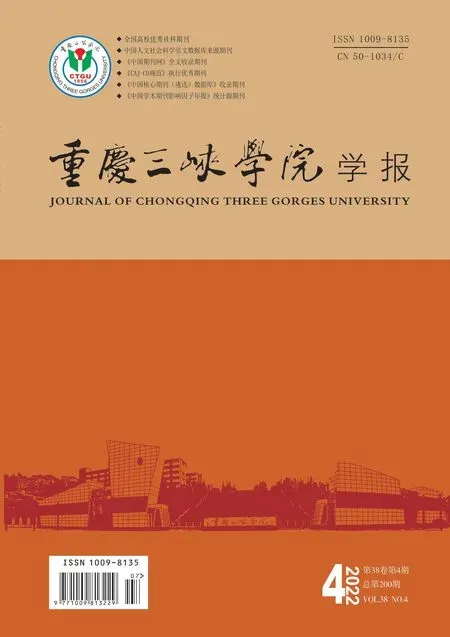乡村旅游生态价值转化机制研究——基于生态文明的思考
吴剑豪
乡村旅游生态价值转化机制研究——基于生态文明的思考
吴剑豪
(福建商学院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福建福州 350012)
我国乡村旅游经过30余年的发展演变,在相应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对于生态资源—生态价值转化也经历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战略安全价值”的认知升华。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旅游生态价值转化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生态农业实物产品溢价、环境调节和功能开发收益、生态保护财政补偿支付、生态资源产权流转增值以及生态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5种模式,通过人本需求和农业多功能属性的内生驱动,发展、巩固农业基本功能,推动三产融合,以“兼业”形式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借助区域公共品牌的信用背书、完善乡村生态旅游产品谱系等外部协调措施提供保障。
乡村旅游;生态价值;转化机制;生态文明
一、引言
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旅游已成为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平衡区域产业结构、对接现代农业产业、实现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有效途径。乡村在景观呈现、人文内涵方面别具特色,依托农林牧渔的产业要素特征衍生出乡村郊野赏景、生态环境观光、古村落(古镇)旅游、乡村民俗节庆节事等旅游形式,同时配套农家乐、渔家乐、森林人家、乡间民宿等乡村餐饮、住宿接待服务,参与田间地头的采摘、果蔬尝鲜、种养活动为主的农事体验、研学教育等活动。乡村生态资源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生产、存续乡土民俗、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及实现乡村治理的资源本底,既是自然要素,也是生产要素,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其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价值功能难以替代。基于乡村地区“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功能叠加,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将生态资源及所处的生态系统环境作为资源要素参与经济活动,在保护“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探索乡村生态资源转化为现实的产业效益,助力乡村旅游经营主体提质增效的市场化发展,释放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红利,促进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基本概念界定
(一)乡村旅游
20世纪90年代城乡协调发展大背景下兴起的乡村旅游,从一开始就担负了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希冀脱贫致富的历史使命。城市近郊或靠近旅游景区的农民凭借特有的乡土风光、农事活动及民俗民间节庆等,吸引城市客源前来休闲娱乐。随着外部社会资本的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呈现复合多元的状态,出现了村民以集体土地、山林、闲置房屋入股引入公司化经营等形式。笔者较认同刘德谦教授对乡村旅游的定义: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地域及农事相关的风土、风物、风俗、风景组合而成的乡村风情为吸引物吸引旅游者前往休息、观光、体验及学习等的旅游活动[2]。乡村旅游的主要产品类型有自然观光型、农事体验型、民俗节庆型、休闲运动型、认知研学型、康复养生型等。
(二)生态价值
人类对于生态资源的利用和认知经历了“资源—资产—资本”三个阶段。首先,生态资源及其生态环境因公共资源的外部性,价值被忽略,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粗放式地开发资源以获得经济发展,甚至出现过度侵占的“公地悲剧”。其次,生态资源具备资产特征的认知始于资源的使用价值被发现并在明晰产权归属之后,资源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参与到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中,形成价值的增长、转化和再循环。最后,资源的资本化典型特征是金融信贷和资本运作,激活沉睡的生态资产转变为活跃的生态资本[3],实现生态资源从零星状分散到集中登记确权、功能价值的资产交易估值以及搭建优质生态资源产品的产权交易平台,进行市场化融资运作,通过金融创新开发生态资源金融衍生品,实现生态资源的货币化循环。生态资源既能够通过交易直接创造价值,也能通过生产高附加值的生态产品获得间接价值。生态资源优势地区还能够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吸引、布局相关产业落地、集群化发展。同时,在政府层面,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实施治污减排举措,建立区域生态补偿政府基金,打造区域公共产品品牌价值等,有效提升生态资源的空间价值。
(三)生态文明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阐述为:建设生态文明就是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4]。生态文明建设被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此后“建设美丽中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土空间开发规划、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淘汰落后产能培养绿色发展产业、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责任追究体制、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及生态补偿制度、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综合治理、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等一系列举措全面铺开,力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响应。
三、乡村旅游与生态价值认知演变分析
我国乡村旅游最初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大背景、零星农户的自发经营探索、政府的推动引导关联密切。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政府部门、旅游业界、民众对生态资源—生态价值转化的认知逐步加深。
(一)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萌芽探索期(1988—1997年),国内学者普遍认同乡村旅游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标志性事件是1988年6月28日,广东深圳举办了首届荔枝节,后续开办采摘园[5]。此后,全国各地效仿以农业节事带动商品展销、招商引资等经贸活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居民收入的提高,也为乡村旅游打下较好的客源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农科村徐家大院为代表的农家菜餐饮经营,后期升级为餐饮、住宿功能的“农家乐”模式,逐渐受到城市居民追捧。1995年5月1日,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也推动了城市游客到农村休闲娱乐、旅游聚会等活动的发展。到城市近郊、风景区周边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成为村集体、个体农户发展非农经济的新思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农民自发经营为主,接待设施较简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类型较简单,村镇道路、停车场、公厕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受限。
第二阶段:起步成长期(1998—2008年)。这一时期,国家旅游局发布了“华夏城乡游”(1998年)、“中国乡村游”(2006年)、“和谐城乡游”(2007年)等宣传主题。乡村旅游经营的主体数量及产品种类都有显著增长。传统农家乐除旅游接待以外,农事果蔬采摘、科技农业观光、乡村美食品鉴、民俗节庆、乡村休闲等产品类型逐渐完备。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6]。同年首批“全国工农业旅游示范点”产生,大大提升了乡村旅游的社会影响力,资本介入乡村旅游市场化经营,出现了“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运作模式,乡村旅游经营单位的设施条件和村镇环境有了较明显改善,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产业呈聚集化特点,依托农村地区的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等农业现代化要素,衍生出“农业+旅游”产业融合趋势。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社会资本介入乡村旅游开发、乡村旅游产品谱系比较丰富,总体呈现三产融合和空间拓展趋势。
第三阶段:快速发展期(2009—2016年)。历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2009—2016年的国内旅游人数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2011年最高达13.2%,呈现高速增长势头。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突破20亿人次,达到21.03亿人次。2016年国内旅游人数突破40亿人次,达到44.35亿人次,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同期获得快速发展。根据农业部统计,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22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4 400亿元,从业人员790万人,其中农民从业人员630万人,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7]。2008年11月,中央政府应对全球金融风暴采取“扩内需、促增长”措施,包括两年4万亿元大规模新增投资,涵盖农村公路、水利、电力、信息网络、饮用水、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文明环境得到明显改善,铁路、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作为各级政府支持乡村旅游业发展的“沉没成本”,有利地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2015年5月,《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GB/T 32000—2015)公布,次月开始实施。2015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提出:“创新农业经营方式,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创建水平。”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旅游提升计划,开拓旅游消费空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乡村旅游人数迅猛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引导较为密集,乡村地区“三生”(生活、生产、生态)融合趋势成为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绿色发展的平衡路径。
第四阶段:调整升级期(2017年至今)。国际经济格局震荡,国内经济增长持续下行,外部投资减退、内需消费疲软,民间投资的部分乡村旅游项目盲目追求规模扩张、贪多求全,导致后续发展资金链断裂,加上疫情影响,客源锐减,行业发展进入洗牌整理、提质升级阶段。“互联网+”、文化创意、“在地化”资源整合、“网红打卡”、融媒直播等要素融入经营模式创新与项目科学运营,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旅游产品供给,拉长了乡村旅游产业链条,调整优化乡村民宿、田园综合体、自驾车旅游宿营地等乡村旅游新业态的空间布局势在必行。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与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的行业发展背景下,乡村旅游需求升级与产品体验改进既互相促进又彼此掣肘,项目商业化严重、经营竞争趋于激烈,风险挑战与发展机遇并存,此外,这一阶段数字技术、智慧旅游赋能乡村旅游带来消费体验显著提升。
(二)生态价值认知深化
自然界中的大气、土壤、山川、海洋、江河、湖泊、森林、沙漠等是人类生产、开发活动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即生态资源。相对于人类的主体地位而言,这些要素作为客体意义上的环境而存在,即生态环境。因此,从空间角度上看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并无实质区别,且优质生态环境的整体系统也是生态资源。人们对生态资源或者生态环境“有价”的认知是在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大体经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战略安全价值”的认知深化(图1)。

图1 生态价值认知深化过程
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源于生态系统中各类型资源自身所具有的功能属性,如土地、森林、草原、水体等为人类开发利用后形成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效用。生态资源的使用价值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外部性、有限性等。例如,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净化空气、延缓全球变暖等功能,同时作为外部性的森林资源也容易因过度砍伐引发“公地悲剧”,付出环境代价和额外治理成本。
在商品经济领域,生态资源具备与其他商品或货币进行交换的属性,表现为生态资源的交换价值。生态资源产品越稀缺,经济价值越高。生态资源交换价值属性客观上也造就了人类对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优化,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生了绿色增长、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等理念。产业资本循环是启动区域条件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钥匙”[8]。生态资源产品经过确认权属、产品价值评估、搭建交易平台等市场化手段鼓励交换价值的实现,通过配额指标交易、资源托管租赁、股权合作、财政转移支付、金融信贷支持等方式实现生态保护补偿和生态资源产品的保值、增值。2004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徐州市采煤塌陷地复垦条例》[9],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人参与采煤塌陷地复垦,复垦后获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此项地方法规有利于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矿区国土综合整治,推动地方产业转型与乡村振兴,并因矿区复垦的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带动区域土地资本溢价。2016年,福建省三明市试点推出“福林贷”金融产品,通过组织成立林业专业合作社、设立村级林业担保基金以林权内部流转,解决了贷款抵押难题[10],激发了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等新要求[11]。站在国家生态安全观的战略高度,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需要领会,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内涵,以系统思维推进工作,尊重自然科学规律,统筹兼顾地开展生态文明治理。
四、乡村旅游生态价值转化机制
在人本需求和农业多功能属性的内生驱动作用下,国内乡村旅游生态价值转化的案例经验可以归纳为5种主要的实践模式:生态农业实物产品溢价、环境调节和功能开发收益、生态保护财政补偿支付、生态资源产权流转增值、生态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等(见图2),并借助区域公共品牌的信用背书、完善乡村生态旅游产品谱系等外部协调措施提供保障。

图2 乡村旅游生态价值转化机制
(一)内生动力
1.人本需求。相较于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生态乡村亲近自然的优越条件成为旅游者逃离惯常环境、暂别“城市病”、体验休闲“慢”生活的出游选择。同时,发展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生计”的有效手段,农户通过开办餐宿接待、从事向导解说、自产自销农产品等“家门口创业、就业”满足家庭增收、脱贫致富的人本需求。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期,农村基础设施、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人居环境得到较大改观,凭借乡村生态条件发展旅游并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生态意识、公共环境意识,由此推动农民参与本乡本土生态环境恢复的积极诉求和农村生态伦理的重新认知。农民作为乡村生态价值的利益相关者,更加重视保护青山绿水,是乡村开展人居环境治理、生态资源保护的价值观认同基础。中国农业文明是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传统农业技术、手工技艺以及基于农事活动产生的岁时节气、民间习俗、神话传说、音乐舞蹈、饮食文化等内涵丰富的文化资源,农业文明传承亟需借助与区域旅游发展的积极互动,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文化的片段特征,使子孙后代能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传承和时代创新[12]。
2.农业多功能属性。农林牧渔业作为第一产业具备多功能属性,从传统种植、养殖的农业基础拓展到第二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农林牧渔服务业、涉农电商、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等第三产业领域。我国新时代乡村振兴突破“三农”发展问题需要第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即推动以第一产业农业为依托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以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农业“六次产业化”[13],该理论最早由日本东京大学今村奈良臣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农业“六次产业化”的重要前提是发展、巩固农业基本功能,在此基础上推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等协同融合,有利于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优化、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促进土地、资金、劳动力、产品、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提高农业附加值,激发乡村经济活力、带动更多就业岗位并增加农户家庭经济收入。
(二)实现路径
1.生态农业实物产品溢价。社会民众对食品安全的隐忧主要源于环境污染、过度施用化肥、滥用抗生素添加剂等对农产品安全的直接影响。某种意义上看,处于萌芽探索期“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乡村旅游农家乐体验中的城市旅游者采摘购买农家自种果蔬、垂钓自助收费应该都算是农产品溢价销售的早期形态。当前,生态农业、有机农业依托乡村地区优良的生态环境以单体农户或以专业合作社联合体、公司化形式发展绿色农业,开展“稻—蛙共养”“桑基鱼塘”“猪(牛)—沼—果(菜)”等立体生态农业循环种养,减少化肥施用和能源消耗、改善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农副产品质量。通过申报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开展地理标志商标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有机农产品国际认证、中国驰名商标认证等推动农业品牌战略、农产品出口和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单体农户、专业农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凭借农副产品溯源标签、品质监控体系及有机农产品生产企业认证授权,建立消费群体对生态标签产品价值认同的基础,接受农业实物产品的高品质溢价,并以此实现生态价值转化收益。浙江丽水的区域公用农业品牌“丽水山耕”通过整合设区市的县域优质农产品、863家企业会员、1 122个合作基地,至2018年11月,旗下农产品覆盖菌、茶、果、蔬、药、畜牧、油茶、笋竹和渔业等产业,产品累计销售额达129.06亿元,产品平均溢价率超过30%[14]。
2.环境调节和功能开发收益。耕地、森林、湿地、草原、水体等资源具备生态系统环境调节、改善局部气候的功能,在应对气候变暖的碳减排进程中,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的碳储备和固碳能力对全球范围内的碳排放“中和”意义重大。通过造林碳汇、草原碳汇、湿地碳汇以及农业减排、农村普及清洁能源、高效立体农业技术等实现农业农村的“碳中和”目标。在此过程中,鼓励林农、牧养户开展森(竹)林养护,草原植被恢复,林业部门通过设立碳通量监测设备,科学监测温室气体排放、碳汇林(草)地的固碳能力,为碳汇交易平台提供具体技术数据,通过碳汇买卖市场化手段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还可以根据建档贫困农户的林地资源条件,进行林木信息采集编码、拍照建档,策划设计单株碳汇扶贫开发项目,即以每棵树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作为基本计价单位产品换算成碳汇量并计算出市场价格,个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可进行购买并发放证书,购碳资金全额进入农户的银行账户,以生态扶贫模式实现林木养护和贫困农户增收的“双赢”。2018年7月,贵州省正式实施单株碳汇精准扶贫项目[15]。此外,直接利用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优质水源地等资源禀赋,结合区域优势产业将生态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纳入生产活动过程中,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有机茶园、包装饮用水、酿酒饮料、渔业养殖、药材种植、食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形成绿色产业集群,获取生态功能开发收益。例如,正山小种红茶原产地在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正山小种”于2010年获评地理标志商标,福建省武夷山市茶产业品牌战略实施带动正山小种茶树种植面积由原来的5 000余亩扩大到1万余亩,年产量从230多吨增至1 000多吨,年产值由8 000多万元增至2亿多元[16]。茶业、旅游业已成为武夷山市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3.生态保护财政补偿支付。部分经济欠发达但生态资源优势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主动放弃污染型产业,压缩了工业发展空间,导致地方经济增长受限,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机会成本、潜在收益等需要以合理方式予以补偿。在现有政策框架内,财政补偿支付作为政府主导的单向使用、普惠性质的生态保护价值实现的直接方式,以纵向生态保护补偿、横向生态保护补偿为主。前者包括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向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使用各级生态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的任务项目考核奖励、资金补偿、政府购买生态管护公益岗位[17]等制度。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包括跨行政区域、上下游流域间地方政府以生态资源保护方与生态资源受益方的角色定位,协商确定生态保护的利益补偿金和治理绩效考核方案。2007年4月,福建省印发《福建省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指出,省财政与闽江流域上下游的三明、南平、福州,九龙江流域上下游的龙岩、漳州、厦门六市政府共同出资建立专项资金,用于闽江、九龙江流域污染整治和项目奖补。2012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之外部分,安徽、浙江两省以新安江流域跨省界断面上一年度水质监测数据为考核依据[18],确定省际横向转移支付划拨方式,筹集流域生态治理专项资金。另外,区域间开展协作互助也是财政补偿途径的积极选项,位于九龙江上游的福建龙岩市和下游的厦门市共建山海协作经济区[19],厦门市和龙岩市覆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闽西)两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厦门市作为经济发达的生态资源受益地,通过“占补平衡”的指标交易、绿色产业转移、支持龙岩市生态资源保护、延长升级产业链条、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红色旅游,建设绿色农副产品供应基地等,对龙岩市实施对口帮扶。
4.生态资源产权流转增值。生态资源归国家所有是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决定的,其产权流转在乡村地区表现为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流转,如农村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承包经营权人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生态资源由于其空间不可分割、公共产品权属特征等因素,各级政府在资源普查、明晰产权、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搭建公共生态产品产权交易平台等诸多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提出,政府需要扮演全域性资源资本化的“做市商”角色,依靠农村传统“村社理性”组织建设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三级市场[20],打通外部资本介入生态资源投资开发途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生态资源价值收益分配社会化。生态产品估值是产权流转交易的重要环节,需要依据生态资源基础数据进行科学测算,兼顾外部补偿和资源开发的代际补偿因素,以公允价值计量生态资源产品和服务的整体价值,避免生态产品价格明显低估、农民利益受损的问题。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依托国有林场探索“森林生态银行”机制[21],将分散林农碎片化经营权、林木所有权集中流转至“森林生态银行”收储、整治,转换成权属清晰的优质“资产包”,通过各产权交易平台策划推介医药、木材加工、旅游康养产业项目招商和林业碳汇交易,提高了生态资源转化为资产、资本的运营效益。此外,国家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自主投资或与政府合作PPP(公共—私营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废弃矿山、无居民海岛等生态修复项目,修复主体在完成生态修复保护任务后,可依法获得自然资源资产使用权,从事文化体育、康养休闲、生态旅游等相关产业开发,获取相应收益。2011年,北京市房山区史家营乡曹家坊村将废弃煤矿区所在的4 700余亩集体林地以70年承包期经营权流转给开展矿区生态修复的北京百瑞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完成生态修复并投资建设文旅景区,带动村民从事旅游服务、发展民宿,村集体财务和村民人均年收入双增长,实现绿色生态产业转型[22]。
5.生态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和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生态系统因蕴含人文因素而具备相应的文化价值,其价值分布范围广泛、内涵深厚、地域特色鲜明。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背景下,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生态反思意义。福建省尤溪县联合梯田的“竹林—村庄—梯田—水流”山地立体农业系统,以山顶竹林留储雨水,形成溪流汇入村庄和梯田,农民在早稻季插秧后间种田埂豆、水田放养鱼苗,改善土壤肥力;收获水稻、黄豆、鱼后放入鸭子、山羊觅食遗落谷粒、田间杂草;梯田景色优美、农家风情浓郁,吸引城市旅游者和摄影爱好者,利用乡村旅游接待实现农户兼业创收。现实乡村空间下的非遗文化资源具有活态传承和开发转化价值,福建省级非遗项目“邵武河坊抢酒节”,源于隋代兵部尚书冯世基公元591年九月初一视察河坊(邵武市洪墩镇河坊村),正值新开垦的稻田大丰收,冯尚书与邵武屯驻军民一同奉祀三国名将赵子龙的“将军庙”,军民争相舀酒,向神像叩拜敬酒,“抢酒节”便沿袭定俗在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此外,扎根乡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融为一体,顺应当代文化消费需求,设计地域文化符号、乡土文化IP品牌成为生态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主要内容。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定居地,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当地盛产白莲、田螺,保留有兴贤书院、朱子社仓、朱子巷、紫阳楼等遗迹,留存有朱子家宴、朱子家礼等省级非遗民俗,南平市近年也积极打造本地文化IP——“卡通朱子”和各类朱子主题文创产品,武夷山市五夫镇发展乡村旅游、朱子文化旅游,实现农业、旅游、文化的协同发展。生态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以农旅文融合形式在生态文明创建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其价值转化形式与时俱进且意义深远,不失为应对环境污染与社会发展时代性难题的对策选择。
(三)外部协调
1.区域公共品牌的信用背书。农业生产种类繁多,受生产方式、光照水热等地域差异以及种养周期、产能限制等影响,实物产品质量控制难度较大,加之农产品在初加工、深加工、流通运输、消费购买等环节受加工技术、地域文化、供需变化等因素制约,农业实物产品在商业品牌市场运营方面存在现实障碍。相较于企业个体层面的产品品牌和企业品牌,区域公共品牌具备政府主导的公共属性和特定地理区域环境的信用背书效应。由于区域公共品牌的管理者、使用者相对独立,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品牌管理者,在引导消费者品牌偏好和保持消费黏性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构建“母—子品牌”准入标准体系和农业实物产品质量体系两个方面。前者以设立国资企业注册区域公共品牌,运行维护区域公共品牌并整合“区域公共品牌+企业(产品)品牌”的“1+N”品牌矩阵形成品牌联想和经营壁垒,造就区域公共品牌的资产价值规模效应;后者主要依托高标准的农产品检验检测监督和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构建,以现有“三品一标志”(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为基础,严格确定产品遴选的品质标准和企业品牌授权使用规则。在营销渠道和宣传推广方面,整合独立分散的企业竞争主体,“线上”电商、网络精准营销,“线下”重点(旅游)城市门店展示、体验销售相结合。区域公共品牌的培育和发展需要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23],以配套公共基础服务、建立健全标准化品控体系、加强政策制度供给等行政职能手段,配合融媒体创新营销方式、发掘公共品牌文化内涵、发布品牌主题宣传片等市场化举措,建构筹划公共品牌统一形象和品牌信用。
2.完善乡村生态旅游产品谱系。生态文明背景下,完善乡村生态旅游产品谱系需要融合生态要素供给和绿色消费需求,从供给—需求两端共同推动、协调发展。结合前文所述的乡村旅游阶段划分来看,乡村旅游的“乡村”并非旅游产品档次低下的代名词,从消费趋势而言,“乡村”辽阔多元的地域特征为践行绿色环保、文化创意消费、产品服务创新等要素与旅游产品融合提供基本空间。乡村生态旅游产品可大致分为生态观光型、文化体验型、生态康养型、休闲运动型和科普教育型(见表1)。随着旅游吸引物增多以及旅游需求变化,乡村生态旅游产品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发展,包括农业文化遗产观光、乡村特色民宿、避暑避寒的气候养生、乡村骑游道、步行慢游道、乡村“非遗”传习、乡村文创体验以及各种主题的教育研学产品等极大完善了产品谱系。

表1 乡村生态旅游产品主要类型
五、结语
乡村性和生态性是乡村旅游生态价值实现的立足点,存在于乡村空间的生态资源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在旅游业角度则是具备作为旅游吸引物功能和旅游活动的空间场域。在生态文明和“两山理论”推动下,回顾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绿色环保的生态消费理念、做负责任的旅游者已成为生态旅游需求客源群体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同时,旅游行业的产品服务供给也在迎合乡村生态旅游需求细分的机会市场。旅游功能开发是附加在农业多功能属性上的产业融合选项,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实现需在重视农业生产能力基础上,以农业为依托,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六次产业化”。生态资源分布和资源所有权属特点决定了在其价值转化途径选择中,政府需进一步发挥在生态资源保护、统筹生态系统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的制度设计和规范区域公共品牌的准入使用等方面的职能。
在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背景下,为应对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现状,政府应鼓励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和乡村青年就地创业,为城市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技术培训、金融信贷扶持、简化项目审批等惠农支农政策。同时,重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配合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转化项目推广,积极开展面向农民的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环境教育,尝试将生态教育成效纳入项目工程验收的指标体系。结合各地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因地、因时、因人制宜,以“跳出旅游,做旅游”的思路,支持生态资源产权流转的农(林、牧、渔)户以“兼业”形式参与乡村生态旅游产品经营,推动生态农产品电商销售、乡村民宿经营、农旅文研学项目、文旅小镇、田园综合体项目等业态升级和复合型旅游产品创新,进一步丰富生态观光+休闲运动+康养度假+研学旅行+文化体验等多元组合、差序开发的乡村旅游产品谱系。在商业资本进入乡村生态旅游开发项目的相关利益分配和尊重乡村社区主体话语权方面,需要避免乡村文旅建设“跑马圈地”“大拆大建”“景区化开发”的旅游项目地产化倾向以及产品设计粗糙雷同、优秀乡土文化浅层化表达、文化需求体验浅陋等急功近利的商业行为带来的利益分配显失公平、乡风民俗“原真性”缺失、旅游者消费体验感差等负面影响。
[1]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
[2] 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J].旅游学刊,2006(3):12-19.
[3] 兰菊萍,刘克勤,朱显岳.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演化逻辑、实践探索与战略指向[J].浙江农业科学,2020(12):2450-2455.
[4]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从荔枝节到高交会、文博会 城市名片记录深圳成长[EB/OL].(2018-07-03)[2022-03-25].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8-07/03/content_19448646.htm.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02-09.
[7] 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22亿人次[EB/OL].(2016-05-09)[2022-03-2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09/c_128968441.htm.
[8] 龚勤林,陈说.基于资本循环理论的区域优势转化与生态财富形成研究——兼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2):97-118.
[9] 《徐州市国土资源志》编纂委员会.徐州市采煤塌陷地复垦条例[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479-481.
[10] 洪燕真,付永海.农户林权抵押贷款可获得性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三明市“福林贷”产品为例[J].林业经济,2018(9):31-35.
[11]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EB/OL].(2020-10-30)[2022-03-28].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0/1030/c117092-31912127.html.
[12] 吴剑豪.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价值链协同创新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6):75-81+114.
[13] 严瑾.日本的六次产业发展及其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128-137+197-198.
[14] “丽水山耕”荣获2018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排行榜区域农业形象品牌类榜首[EB/OL].(2018-12-25)[2022-03-28].https://www.sohu.com/a/284478469_99914229.
[15] “生态+扶贫”贵州单株碳汇项目实现双赢[EB/OL].(2020-05-19)[2022-03-28].http://www.gywb.cn/system/2020/05/19/030487587.shtml.
[16] 正山小种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获评48.04亿元[EB/OL].(2018-07-30)[2022-03-28].http://www.wysxww.com/2018-07/30/content_452012.htm.
[17] 赵翔,朱子云,吕植,等.社区为主体的保护: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的思考[J].生物多样性,2018(2):210-216.
[18] 麻智辉,高玫.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研究——以新安江流域为例[J].企业经济,2013(7):145-149.
[19] 陈发胜,王尚华,章丽清.山海共鸣唱大戏 厦龙合作谱新篇[N].闽西日报,2014-06-09(002).
[20]温铁军,罗士轩,董筱丹,等.乡村振兴背景下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的创新[J].中国软科学,2018(12):1-7.
[21] 黄颖,温铁军,范水生,等.规模经济、多重激励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福建省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经验总结[J].林业经济问题,2020(5):499-509.
[2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第二批)的通知[EB/OL].(2020-10-27)[2022-03-28].http://gi.mnr.gov.cn/202011/t20201103_2581696.html.
[23] 王宇飞,武红.赋能区域公共品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浙江丽水品牌建设的经验和启示[J].中国发展观察,2020(Z1):108-111.
A Study on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Value of Rural Tourism: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U Jianhao
Along with more than 30 year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China’s rural tourism show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corresponding stag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cological resources to ecological value has also experienced the cognitive sublimation of “use value-exchange value-strategic security valu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alization paths of rural tourism ecological value transformation mainly include five modes: premium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oduc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unction development benefits, ecological protection financial compensation payment, transfer and appreci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 property rights, and consumption of ecological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develop and consolidate the basic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and to partially participate i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endogenous drive of humanistic demand and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 attributes, and provide guarantee with the help of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asures such as credit endorsement of regional public brands and improving the products spectrums of rural ecotourism.
rural tourism; ecological valu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吴剑豪(1980—),男,福建长乐人,副教授,主要研究区域旅游发展。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朱子文化赋能福建研学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JAS21198)。
F592.7
A
1009-8135(2022)04-0038-13
(责任编辑:张建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