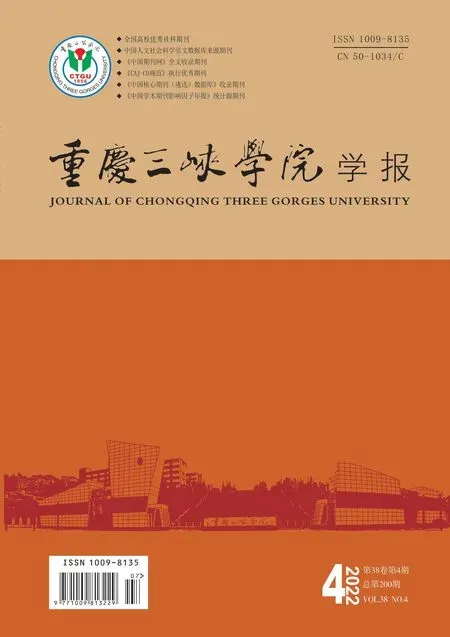由仙人俊逸到逐客悲叹——论杜甫前后赠怀李白诗之变化
丁震寰 于慕清
由仙人俊逸到逐客悲叹——论杜甫前后赠怀李白诗之变化
丁震寰 于慕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35)
杜甫有14首赠怀李白诗,时间跨度达二十年。以永王李璘事件为界,之前杜甫笔下的李白以仙人形象出现,诗歌整体风格为清新俊逸;之后杜甫笔下李白以逐客形象出现,诗中流露出信而见疑的楚骚悲叹。但早在李白的仙人形象中,就已埋藏了楚骚的悲苦之叹。杜甫笔下李白形象及诗歌风格的变化,既是杜甫自伤身世的感慨,也体现了时代政治对诗人、诗歌具体风格产生的影响,暗含着时代整体的诗风发生变革。
杜甫;李白形象;诗歌风格变化;认识过程
李白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被后世称为诗仙。葛景春指出:“最早称李白为诗仙的或许是北宋范仲淹,至南宋杨万里之后,诗仙一词专称李白的现象才渐渐增多。”[1]与“诗仙”并称的是李白豪迈奔放、清新飘逸的写作风格。在唐代许多与李白同时的人也称李白仙人,亦赞许其飘逸诗风。然而,安旗指出:“李白其人及其诗远非‘飘逸’二字可以概括。”[2]纵观李白一生,其潇洒时供奉翰林,落魄时流放夜郎;其诗欢快处纵情歌酒,沉郁时几似《离骚》。伴随着李白生平境遇的不同,其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飘逸”可视为李诗大体风貌,但并不完全准确。杜甫或是较早关注到这一问题之人,其有多首赠怀李白诗,诗中李白的形象及诗歌风格也有着明显不同。
洪迈《容斋四笔》谈到:“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其多。”[3]今查《杜诗详注》等注本,杜诗所涉李白篇目大抵有《赠李白·二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昔游》《遣怀》,其中《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并非单独赠与李白,《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只是记录了同游之事,但都可算杜甫赠李之作。《昔游》《遣怀》则是追念旧友,作此二诗时李白早已故去,其中有怀念李白的成分。最早的《赠李白·二首》约作于天宝三载(744),最晚的约作于大历元年(766),其间跨度达二十多年。通过这些诗篇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杜甫对李白形象及诗歌风格评价都发生了变化。
一、由仙人到逐客
在杜甫笔下,李白最早以仙人形象出现,最直观的是《饮中八仙歌》所写:“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此处李白自称“酒中仙”,既是对贺知章“谪仙人”的呼应,也是对王绩《醉乡记》的化用。王绩《醉乡记》言:“阮嗣宗、陶渊明等数十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4]酒有麻痹神经的功能,让人思维恍惚,从而脱离尘世寻找另一种精神寄托,因此酒常常作为引导人们进入仙境的标志。刘伶在《酒德颂》中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5]在醉梦之中,时间空间产生了错乱,通过错乱的时空感应,构建了异乎现实生活的仙境。李白自称“酒中仙”,既是其爱酒性格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在酒的影响下,李白狂放不羁、飘逸洒脱的仙人形象。酒与仙紧密呼应。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酒是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查《说文》释“仙”:“僊(仙),长生迁去也。”[6]查《释名》释“仙”:“仙,迁也。迁入深山也,故其制字人傍作山也。”[7]由此可知,塑造的仙人形象需具备几个要素,其一是寿命长,其二是独居深山,与人世隔绝。由此又可引申出寿命长是通过喝酒、服食丹药以及求道实现的。酒本身具有药效,饮酒也是养生的一种方式。《汉书·食货志》称:“酒者,天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8]隐居深山与世隔绝,则表现为内在精神的逍遥自得,外在风格的卓然不群。杜甫书写李白的诗中都体现了这些特质。
杜甫笔下李白的仙人形象由炼丹饮酒、隐居求道和超于常人的精神风貌三方面构成。试看其七绝《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此处便写到了炼丹、饮酒。炼丹、饮酒,一则是外在的对仙境的寻觅,一则是内在的精神的豪迈洒脱,二者共同构成了李白的仙人形象。再看老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此六句皆在描写范十隐居环境之清幽,虽未直接描写范十本人,但通过小童的清秀衬托出范十的不俗。而李杜共寻之,最后以“不愿论簪笏”结尾,更是体现了二人在与范十交谈后,不愿再多追求仕途,希望寄情沧海。范十本非俗人,兼居幽处,在杜甫笔下,李白有意寻之,并冀以向范十学习。李白爱道,与元丹丘交情颇深,访道也并非偶然。《赠李白》侧重在李白服丹好酒,而此诗更侧重在李白精神的不羁,向往仙境和幽居。同样在《冬日有怀李白》诗中,“还丹日月迟”和“空有鹿门期”二句也是对炼丹、幽居生活的总结。顾宸《辟疆园杜律注解》以为,此诗当作于天宝四载冬[9]五律卷一。是时,李白早已离开长安,并得道箓入道籍,道家所提倡的炼丹、服药、幽居等思想与诗中还丹、鹿门相印证,也正是李白如今生活的写照,这更深化了李白的仙人形象。至于《春日忆李白》一诗提出的“飘然思不群”,既是对李白诗歌风格的高度肯定,也通过“飘然”“不群”体现了李白超于常人的精神面貌及思维方式,暗含对李白“谪仙人”的呼应。在天宝年间,杜甫通过《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为李白的仙人形象定型。诗歌对孔巢父作了大量描述,称其“钓竿欲拂珊瑚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但最后却告诉巢父“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南寻”句又作“若逢李白骑鲸鱼”①参见《杜甫全集校注》该句《校记》:宋百家本、宋千家本、宋分门本、元千家本、元分类本、范本引洙曰:“一云:‘若逢李白骑鲸鱼’。”宋百家本、宋千家本、宋分门本、元千家本、元分类本、范本诗末引“洙曰”所引“一本”,二蔡本诗末引别本,亦俱作“若逢李白骑鲸鱼”。(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其实无论“禹穴”还是“骑鲸”,指的都是李白仙人形象。“禹穴”当为阳明洞天,张炎兴指出:“(在唐代)阳明洞天是大禹传说与会稽山结合后逐渐道教化的产物,原来意义上作为大禹为治水而得书藏书处的禹穴,经过道教化的洗礼,变成为大禹得长生药方《灵宝五符天文》之处而曰阳明洞天。”[10]“骑鲸”典出扬雄《羽猎赋》“入洞穴,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11]。巢父已有仙骨,故才可能去禹穴或者碰到骑鲸鱼的李白,李白仙骨似乎更胜巢父。由此可知,杜甫诗歌通过对李白求丹、好酒、幽居的外在表象,飘然思不群的内在精神,共同构建了李白的仙人形象。
然而,此时“仙”的李白形象背后,隐藏着其内心的伤悲。李白天宝元年入朝,却在朝中受人妒忌,遭人诽谤,最终于天宝三载请求还山。玄宗也以其“非廊庙器”,亦恐其“言温室树”将其赐金放还。也正是这次放还途中,杜甫结识了李白。尽管这次放还并非玄宗主动,而且李白被放一事还足够风光,不能称得上逐臣。但离开京城后,李白仍有被放逐之感,既宽慰自己享受隐居生活,又流露出对个人身世的哀叹。天宝三载,李白有《沐浴子》,此诗反用《楚辞·渔父》,诗歌开头描绘了一个“沐芳”“浴兰”的高洁士人形象,但因为小人太多,所以渔父告诫士人“处世忌太洁”,最后士人选择暂且“藏晖”与渔父一同隐居。天宝四载,李白《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言:“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泊流离放辽海。”此诗更明显体现出李白向往长安的理想与而今滞留单父的现状间的矛盾。被赐金放还后,李白沉迷道教,从中寻求精神慰藉,但内心多愁苦,感慨自己离开京城。
这一时期杜甫对李白的书写中也暗藏了这种情绪。前引《赠李白》一诗,表面是杜甫劝诫李白,让其好好修仙,炼丹饮酒,实则是感慨李白不能为人赏识,只能虚度年华。仇《注》称:“自叹诗意浪游,而惜白之兴豪不遇也。”[12]再看其《饮中八仙歌》,程千帆解读其中人物称:“这群被认为是‘不受世情俗物拘束,憧憬个性解放’之徒,正是由于曾经欲有所作为,终于被迫无所作为,从而屈从于世情俗物拘束之威力,才逃入醉乡,以发泄其苦闷的。”[13]此说有理。杜甫与李白惺惺相惜,醉眠共被,李白内心向往长安而终不可得的忧愁,杜甫应当有所察觉。只是这时赐金放还,一来李白尚在壮年,二来也足够风光,三来此时李白更沉迷仙道,试图用仙道消解内心痛苦。所以,这一时期杜甫努力用“仙人”形象劝慰李白,掩饰了其中哀伤。这种“仙”与“悲哀”交织的矛盾,正是李白自身的矛盾。当后来李白的身份再度发生变化,其悲伤情绪占据上风,仙道思想已不能调和与掩饰时,杜甫对李白的书写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安史之乱后,杜甫笔下的李白形象由之前的飘逸若仙转向哀愁逐客。李白因参与永王李璘幕府而受到牵连,其后又被流放夜郎。杜甫于759年在秦州,闻李白流放之事,作《梦李白二首》。诗言“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直接道出了李白的“逐客”形象。“魂来枫林青”明显化用了宋玉《楚辞·招魂》的句子,王逸《楚辞章句》称:“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14]将李白屈原并提,进一步深化了逐客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一句,自天宝年间分别后,杜甫再不曾见过李白,时隔十几年,杜甫想象李白不住地搔着自己的满头白发。曾经炼丹、纵酒、幽居访道的仙人已然被愁绪缠身,苍老了许多。此处实则已用逐客形象否定了曾经塑造了李白的仙人形象。这一否定更体现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王嗣奭评价此诗称:“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12]798在诗中有强烈的今昔对比之意,开篇便言:“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此虽是书写李白与贺知章故事,但也是杜甫对李白“谪仙人”形象的肯定。其后老杜将李白如今现状与之前“谪仙人”进行暗比,指出李白现在处境“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鵩鸟用了贾谊《鵩鸟赋》之典故,麒麟则是孔子感叹麒麟生不逢时。贾谊被文帝弃用,贬至长沙;孔子则因为受季氏排挤而离开鲁地,周游列国。这两处用典,皆突出了逐臣形象,与上文所言“放逐臣”相呼应。最后“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以老、病二句想象李白现状,昔日的仙人形象如今已为年老多病的逐臣形象所取代。
唐代与李白同时的人,大多推崇李白“仙人”风骨,较少关注其内心的苦闷和逐客之愁。司马承祯称李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15]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称:“是日也,车出桐门,将驾于曹,仙药满囊,道书盈箧。”[16]3943大抵在中唐时,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才隐约提出李白的“逐客”形象,“又志尚道术,谓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流离轗轲,竟无所成名”[16]6247。放眼唐代,尽管未有人称李白为“诗仙”,但唐人大多以仙人之姿评价李白,李白的“逐客”形象并不常出现,当是杜甫首以逐客称之。
综上可知,大致以永王李璘事件为界,李白自身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前期的赐金放还相对风光,后期则是下狱几死。前期李白尚可通过仙、道求得解脱,后期已被困于网罗。基于此,杜甫对李白形象的书写发生了由“仙人”到“逐臣”的变化。
二、由清新俊逸到楚骚之感
杜甫并非仅仅论述了李白个人形象的嬗变,还发掘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嬗变。人物形象对文学作品风格产生影响的观点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周易·系辞·下》提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17]构建了人物心理、状态与其言辞风格的关系。然而,人的心理、状态并非一成不变,其言辞风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更何况,作家本人并非游离于社会之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也会对作家心态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作家创作。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18]安史之乱后,盛唐王朝发生动荡,李白也因为永王事件牵连遭祸,杜甫笔下的李白形象由仙人转向逐客,与之相配的则是李白的诗风由清新俊逸转向楚骚悲苦之叹。
细查现存14首杜甫怀赠李诗,其中关涉李白诗歌的只有8句,“清新俊逸”几成李白诗歌风格之定论。这8句诗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关于李白诗歌内容的,只有1句,为“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角弓》诗”典出《左传》,《左传·昭公二年》:“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19]此处借指李白寄给杜甫的诗文,大约是叙述二人友情之作。其二是有关李白作诗状态的,共2句,为“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这两句诗写出了李白酒后作诗,才思敏捷。其三是涉及李白的诗歌艺术评价,共5句,为“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通过细化分析,可以看出“冤魂语”与“清新俊逸”之不同。
此处主要讨论《天末怀李白》一诗。仇《注》引赵子栎语:“白于至德二载坐永王璘事而谪夜郎,公在秦州怀之而作。”[12]713杜甫以为李白流放至夜郎必至长沙,过湘江,故而其诗中多用屈原、贾谊典故。《天末怀李白》诗云: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诗言“凉风”点出时间已是深秋,“天末”点出杜甫所在秦州。鸿雁一句颇有深意,“鸿雁”一词大抵有两重含义,其一源于《诗经·小雅·鸿雁》,借鸿雁以比“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的漂泊离家之人。其二源于《汉书·苏武传》,借“鸿雁传书”表达收到他人音信。此处似乎更偏重于第二种意思,即杜甫询问鸿雁如何信息不到。在五律写作中,第二联往往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此联上半句正因不知李白音信如何,故询问鸿雁。下半句却担心秋水上涨,使李白前往贬所之路行走艰难,进而引出真正行路之难的其实是“魑魅小人”。也正因行路之难,所以杜甫才特别担心李白,频繁询问李白书信。第三联代替李白作语,为不平之鸣,亦与屈原暗合。第四联则化用扬雄典故。《汉书·扬雄传》载:“(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遂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乃作书,往往摭《离骚》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8]3515此处借扬雄投诗悼念屈原之典来表达李白也应该悼念屈原。但扬雄所作《反离骚》是批评屈原的,扬雄那时刚走出蜀地,其虽然悼念屈原,但并不能真正对屈原感同身受。而今李白深刻体会了“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的道理,那李白也应该和屈原有共同语言吧。李白善于写诗,其所遭遇的又与屈原一样,杜甫认为他一定可以写出与屈原类似的,富含楚骚之感的作品。查《说文》释赠:“赠,玩好相送也。”[6]494“赠”相较于“吊”更有一种双向的互动,以期求回应,故张衡《四愁诗》云:“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在赠、报之中,使得李白与屈原的关系进一步紧密。正如黄生《杜诗说》言:“不曰吊而曰赠,说得冤魂活灵活现。”[20]也正因为寻求李白与屈原的双向互动,故而李白之诗风也当与屈原相靠近。在杜甫看来,此时李白因自身遭难,其诗歌风格已发生变化,由清新俊逸转向楚骚之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杜甫似乎并未再收到李白音书。杜甫在秦州写下赠怀李白的诗时,李白已经遇赦,可见当时的信息具有滞后性。连李白遇赦这样重要的大事,杜甫尚且难以得知,更何况得到李白的书信呢?另查秦州时期赠怀诗,有“鸿雁几时到”“舟楫恐失坠”这样的疑问句,更确定杜甫此时并未得到李白消息。根据现有文献无法得出杜甫听到或看到了李白流放之后所作的诗歌,所以,杜甫只是猜测李白的诗歌风格发生了转变,而并非肯定,故其用“应共冤魂语”表示推测。
杜甫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李白清新俊逸的诗风与楚骚之叹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在此,有必要对“清新俊逸”与“楚骚之叹”加以论述。“清新”一词最早见于陆云《与兄平原书》:“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为病耳。”[21]此处“清新”大抵指清丽、新颖。“俊”与“峻”通,本为高大之意,后可引申为俊伟、雄健之意。《玉篇》释“逸”:“逸,奔也。”其本意是奔跑,后可引申为奔放。“俊逸”一词实则是雄健奔放。“清新俊逸”指李白诗歌既善于对身边景物进行细微描述,诗歌风格珠圆玉润、婉转悠扬,又能善于发挥想象,上天入地,心鹜八极,诗歌风格汪洋恣肆、纵横捭阖。这两种看似矛盾的风格,李白都能驾驭,甚至将其融会贯通。关于“楚骚之叹”,司马迁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22]王逸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14]2刘勰亦对骚作出评价:“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18]48结合司马迁等人观点,大抵可以对“楚骚之叹”作出解释,即诗人自身所处时代,或诗人自身经历了挫折之后,使用与自身产生共鸣的奇特意象、物象,以表达自身的悲愤情绪。特别是刘勰拎出“酌奇玩华”与“其真其实”的矛盾,进一步指出《楚骚》的特点是依附在真实感情,主要是指悲情基础上的华丽言辞与奇特物象。
通过对“清新俊逸”和“楚骚之感”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俊逸风格的产生源于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楚骚之感”的重要方面也是“酌奇玩华”,通过描绘奇特的物象并与自身产生共鸣,也需要诗人充分地展开想象。在“清新俊逸”的诗歌风格下面,其实已经隐藏了“楚骚之感”。一旦诗人自身经历挫折,“其真其实”的条件得到触发,那么诗人很有可能从“清新俊逸”向“楚骚之感”进行转变。加之其早期作品也多有化用或感慨屈原、宋玉、贾谊之辞。如“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宿巫山下》);“濯缨掬清泚,晞发弄潺湲。散下楚王国,分浇宋玉田”《安州应城玉女作》;“汉朝公卿忌贾生”(《行路难·其二》)。更因为杜甫推测李白会过湘水楚地,在那里会进一步产生与屈、宋、贾的共鸣。种种原因作用下,李白自然会写出与屈原类似的作品,也就可以投诗赠给屈原了。
三、杜甫对李白风格评述变化析因
提及老杜诗歌风格,当下学界皆以“沉郁顿挫”称之。提及杜甫诗论,往往赞颂其“庾信文章老更成”“老来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认为杜甫善于创语,更喜欢雄健之笔。其实不然,杜甫对于清词丽句一样很喜欢,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谈到“转益多师是汝师”提倡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也明确指出“清词丽句必为邻”。杜甫并非反对诗歌辞采华贵,而是反对仅仅追求华辞而忽视内容,仅仅追求柔美而缺乏气度。初唐诗坛一直存在着“江左清绮”和“河朔重质”两种诗歌风貌,在诗歌发展过程中,两种风貌逐步融合,但人们的审美情趣始终未能摆脱齐梁风貌。杜甫自身也有效仿齐梁的作品,《月夜》正是其中之一。王嗣奭《杜臆》称之:“云鬟、玉臂,语丽而情更悲。”[23]42语丽正是齐梁诗歌的特色。吴怀东进一步指出:“写妻子‘香雾云鬟’‘清辉玉臂’,显然纯是想象之词。从写作手法的角度看,此前宫体诗对女性身体的美化描写无疑对杜甫有着启发作用。”[24]由此可知,在唐代诗歌发展过程中,尽管有陈子昂、韩愈等提倡复古并以之成风,但齐梁的“清词丽句”审美观念一直对唐人产生影响。杜甫本人则提出“转益多师”,并不一味赞扬复古,也没有一味推崇齐梁清丽。时代的多元审美风尚兼杜甫善于学习多种审美风格,成为杜甫论诗的基础。
杜甫早期称赞李白“清新俊逸”,后期称赞李白“楚骚之感”,这种评述变化既与杜甫本人的经历有关,也隐含了社会变迁过程中政治、思想等因素对时代诗歌风格的影响。杜甫投奔肃宗后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空参军,后又弃官至秦州,辗转入蜀。在这一时期,他听闻挚友李白亦被贬谪,同为逐客,不免惺惺相惜。这段时期的怀赠李白诗,既有宽慰李白,又有自解之意。《梦李白二首》的“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搔白首”一句与《春望》“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的杜甫形象何其相似。《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莫怪隔波恩,乘槎与问津”,亦是杜甫自我宽慰之语,尽管其中暗含着无奈。葛景春在《杜甫在秦州的李白情结》已论述甚明[25]。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转变,总体说来,这一时期杜甫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悲世”“伤身”①浦起龙评《秦州杂诗》称:“二十首大概只是悲世、藏身之意。其前数首悲世语居多,其后数首藏身语居多。”浦起龙又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七首皆身世离乱之感。”(见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1页、第262页。),在表达方式上杜甫十分注重比兴托物,《初月》《归燕》《萤火》《苦竹》《病马》《铜瓶》等诗,皆作于此时。《离骚》之作,也大抵是如此内涵,“哀民生之多艰”悲世也;“吾独穷困乎此时”伤身也;以香草美人自比,比兴托物也。杜甫秦州所作诗,实则已有楚骚之感。王嗣奭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七歌’创作,原不仿《离骚》,而哀实过之。读《骚》未必堕泪,而读此不能终篇。”[23]112杜甫与李白在忠君爱国的思想上有高度相似性。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称:“东坡苏子瞻《诗话》曰:‘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26]李白亦如此,萧士赟、王琦都称之“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李白诗歌虽不像杜甫那样写实,但从中亦不难窥到其忠君之心。李白少年离开蜀地时写到“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开元后期王大曾邀他隐居,李白写到“建功及春荣”;在李白获释后,其仍想着投奔李光弼从军;直到身死之前所作《临路歌》,依然自比孔子,感叹功业未成。同样的忠君之志,同样的被驱逐经历,杜甫深刻体会到了《离骚》“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思想内涵,并将之付诸实践。他也深知李白之志,加之李白经过楚地,杜甫在怀赠李白的诗中同样寄托了自己的情绪,所以尽管杜甫大概率没能见到李白流放后的作品,其依然认为李白这一时期诗歌风格已发生了转变。
杜甫在诗歌方面始终推崇以李白为标准,并以之为榜样。杜甫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清新俊逸”兼有“屈宋之风”。这一评价主要体现在《戏为六绝句》中。这一组诗内部存在关联,笔者以为此诗当细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前三首诗,简述作此组诗的原因,认为当时人对庾信及初唐四杰的评价有误;第二组为第四、第五两首诗,主要批评了当时那些批评庾信和四杰的人所作的诗;第三组为第六首诗,杜甫告诫了今人“转益多师”的作诗方法。在第二组中,杜甫通过批评他人的诗,点出了自己的诗学思想。试将二诗列于下: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第四首前二句通过疑问“凡今谁是出群雄”指出这些人无法与数公相比,后二句解释了原因,即他们只能写翠鸟落在蓝苕上这样清新的事物,却不能作在碧海中捉鲸这样的豪放之语。言外之意,杜甫看来,优秀的诗歌既清新自然,体察细微之物,还豪放大气,有雄壮之美。这二句是称赞李白,可以用“清新俊逸”一句加以概括。“翡翠兰苕”可称“清新”,此意甚明。“掣鲸碧海”实是“俊逸”。杜甫以鲍照为“俊逸”之典范,《诗品》称鲍照:“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糜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27]“諔诡”是奇异的想象;“糜嫚”是华糜柔嫚;“骨节”指文章骨力、气势;“驱迈”指驾驭文章节奏的手法。其中奇特的想象与文章的骨力、气势也正是“掣鲸碧海”的重要组成部分。鲍照之骨力,后人论述颇多,试举二例,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鲍照诗)气骨渊然,骎骎有西汉风。”[28]陆时雍《诗镜总论》:“鲍照才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壁矣。”[29]此正与李白诗歌风格契合。葛立方《韵语阳秋》明确指出“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擎鲸手也。”[30]更何况李白诗中频繁出现“鲸鱼”意象。景遐东、刘云飞《李白诗歌中的鲸意象及其影响》也指出:“鲸……等意象展示其豪放不羁,豪迈奔放的精神世界,形成李白诗歌壮美的精神境界;这类意象群与月、花、酒等意象群所形成的优美境界交相辉映,铸就李白诗歌雄奇飘逸、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31]胡仔说:“庾不能俊逸,鲍不能清新,白能兼之,此无敌也。”[32]可知,李白具有杜甫所提倡的清新与壮美并存的诗歌风格。
第五首前二句亦是对批评庾信及四杰的当时文人进行批评,认为古人如屈原、宋玉纵然值得喜爱,但今人依然有可取之处。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学习屈宋,希望与屈宋并驾齐驱,但他们只是喜爱模仿屈宋的“清词丽句”,这样的结果也就是再一次走入他们所批评的“齐梁诗风”。由此,大概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当时的诗坛以诗歌与屈、宋类似为极高的审美标准,所以当时的人想要“攀屈宋方驾”。其二,杜甫以为当时人学习屈宋并不得法,屈、宋的思想内涵是善于用比兴寄托的手法关注社会政治及个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命运,实际上是做到了辞采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屈、宋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其语言固然重要,但其内在的情感,作品所流露出的思想才是核心。而学习者只关注到屈、宋的语言层面,并未由语言形式上升到思想内容,只是“酌奇玩华”而未得“其真其实”。尽管杜甫并未专门评价李白诗歌风貌,但其喜爱的“清新俊逸”和“屈宋之风”兼在李白身上得到体现。杜甫对“屈宋”的喜爱,使得他也以屈宋评价李白诗歌。
杜甫对李白评价的转变也与时代引起的诗歌发展变革有关。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产生了巨大的动荡,标志着大唐帝国盛世的结束。盛唐诗人积极高昂的精神风貌被打破,诗歌创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陈伯海《唐诗学引论》指出:“唐中期诗歌转变航向的首要标志,就是把‘言志抒怀’的宗旨换成了‘感事写意’……怀抱的抒述往往由‘事’引起,述怀中就含带‘事’的影子;而记事作品还要加上一个‘感’字,也意味着其中仍有述怀的成分。”[33]具体说来就是诗人更加关注自身处于政治事件下的个人心态与风貌,并对政治事件展开评述。“言志抒怀”更多的是诗人主观怀抱的倾吐,而“感事写意”则更偏向于诗人对客观事物的记录。诗歌从来都与政治紧密结合,诗人从来也不曾脱离社会实际。“感事写意”明显要比“言志抒怀”多了与政治大背景的关系。在厚重的政治背景下,感事写意往往融入了复杂、悲世的情绪。杜甫正是由“言志抒怀”向“感事写意”转变的代表。可以说,时代的变化,王朝的动荡,使整体社会对诗歌风格的审美评判发生了变化。“楚骚之感”本身带有政治色彩。屈原所处的时代也正是楚国动荡的时代,屈原创作《楚辞》的动机既有秦楚之间战争爆发,楚国的不断战败,也有自己在政治斗争中不断被排挤、打压。自安史之乱后,诗歌的航向已逐渐发生变化,《离骚》所蕴含的深刻意蕴与大的时代背景相契合。杜甫提出“楚骚之感”,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紧密结合,甚至也可以说是安史之乱后,盛唐诗风向中晚唐诗风的过渡。在此审美标准下,杜甫依然推崇李白诗。
综上可知,杜甫以为李白诗由“清新俊逸”向“楚骚之感”的过渡,实际上前者是杜甫的确见过的李白诗风格,后者是杜甫推测想象的李白诗审美风格。但后者的推测想象,实则是这一时期杜甫诗歌风貌的特点。杜甫以为李白所处环境与自己类似,应该有如此诗歌风格,而这一诗歌风貌也体现了以杜甫为主导的盛唐诗风向中唐诗风的嬗变。
四、结语
杜甫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评价变化,实则也是自己不同境遇下诗歌风格的转变。李白仿佛一面镜子映照着杜甫。杜甫早期写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在成都较为安定的生活和蜀地风光也使杜甫创作出“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等清新秀丽的诗。现行的杜甫“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很难包含这些作品。在政治环境及个人生存环境的变动下,诗人心态受到影响,进而投射在诗歌创作上。杜甫怀赠李白诗,在其对李白深厚友情的基础上,也充斥着自己内心的沉痛。相似的性格与遭遇,使杜甫赠怀李诗中带着更多的个人意味。在诗歌中,主客关系逐步消解,李白本是杜甫所赠之客,但杜甫其中诸多言语更像是自我心境的剖析。
正因如此,杜甫对李白诗歌风格的评价标准有极强的主观性。李白诗歌实际上是变与不变的结合:其总体的好用比兴的写作手法、磅礴大气的物象、豪迈纵横的语言并未发生太多变化;其年轻时以大鹏自比,直至死前的《临路歌》依然以大鹏自比;其年少时作所《峨眉山月歌》与其年老时所作《早发白帝城》语言风格也十分相同。尽管遭到磨难,被流放夜郎,但李白始终自信,始终期待着重返魏阙,期待着再展宏图。他从来都是一个“得即高歌失即休”的人物形象。
总之,通过对杜甫赠怀李白诗梳理、分析,可以大体看出以李白被流放夜郎为界,杜甫对李白形象及诗风表述有前后两种不同的态度。前期李白的仙人形象中已蕴含了有志不骋的悲苦,后期这一悲苦与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哀怨相结合,凝成身为逐客的“楚骚之感”。在李白形象的变化之中,也暗含了时代诗风变迁的特质及杜甫的自身之情。
[1] 葛景春.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J].中州学刊,2020(10):163-167.
[2] 安旗.简论李白和他的诗[N].光明日报,1982-10-05(3).
[3] 洪迈.容斋随笔[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409.
[4] 王绩.王绩文集[M].夏连保,校注.太原:三晋出版社,2016:221.
[5]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76.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许惟贤,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672.
[7] 毕沅.释名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5:84.
[8]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82.
[9] 顾宸.辟疆园杜律注解[M].康熙二年(1663)吴门书林刊本.
[10] 张炎兴.阳明洞天考[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65-71.
[11] 林贞爱.扬雄集校注[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95.
[12] 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53.
[13] 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M].中国社会科学,1984(5):145-155.
[14] 王逸.楚辞章句[M].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02.
[15]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20:1506.
[16] 董诰.全唐文[G].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 王弼.周易正义[M].孔颖达,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9.
[18]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227.
[20] 黄生.杜诗说[M].徐定祥,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4:133.
[21] 刘运好.陆士龙文集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366.
[2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82.
[23] 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2.
[24] 吴怀东.《月夜》与思妇诗的夺胎换骨[J].杜甫研究学刊,2020(1):1-9.
[25] 葛景春.杜甫在秦州的李白情结[J].杜甫研究学刊,2014(1):1-7.
[26]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话[G]//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195.
[27]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85.
[28] 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338.
[29] 陆时雍.诗镜总论[G]//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1407.
[30] 葛立方.韵语阳秋[G]//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502.
[31] 景遐东,刘云飞.李白诗歌中的鲸意象及其影响[J].福建论坛,2017(9):125-131.
[32]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45.
[33] 陈伯海.唐诗学引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14.
From Being Handsome to Lamenting:On the Changes of Poems Presented by Dufu to Li Bai
DING Zhenhuan YU Muqing
Dufu has 14 poems for Li Bai, which have been written for 20 years. Taking the event of Yongwang Li Lin as the turning point, Li Bai in Dufu’s works appeared as a celestial being before, and the overall style of his poems was clean, fresh and elegant; after that, Li Bai appeared in Dufu’s works as a figure be expelled, and the poems showed poetry’s lament that he was loyal to the king but was suspected as it was in. But as early as in Li Bai’s celestial being’s image, there was the clue of this lament. The change of Li Bai’s image and poetic style in Dufu’s works is not only out of Dufu’s sad emotion towards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but also reflects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s on the poets and the specific style of poetry, implying the change of the overall poetic style of the times.
Dufu; the image of Li Bai; change of poetic style; cognitive process
I206.2
A
1009-8135(2022)04-0085-12
丁震寰(1995—),男,新疆石河子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唐代诗歌。
于慕清(1996—),女,山西榆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唐代诗歌。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