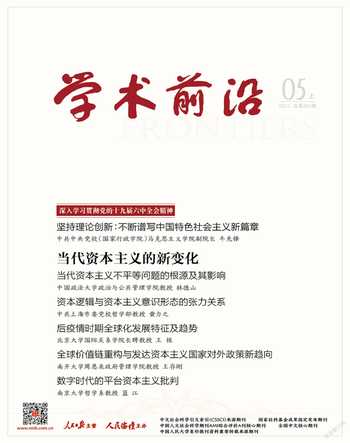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三种形态和实践
【摘要】通常被认为属于自由主义社会的澳洲其实是一个“沉默不言”地符合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中,澳洲有三种社会主义形态和实践方式:乌托邦的社区社会主义、温和渐进的民生社会主义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中,部分地实现民生社会主义是可行的,但是这种民生社会主义也具有巨大的局限性。
【关键词】澳洲社会主义 乌托邦的社区社会主义 民生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10
自由主义理论大家罗尔斯是一个“沉默不言的社会主义者”,[1]其一生都保留了对社会主义的浓厚兴趣。他曾明确说过,拥有财产的民主和自由社会主义这两种政体符合和体现了他的正义理想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澳洲的自由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沉默不言”地符合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在自由主义占上风的时代,澳洲仍然有追求社会主义的政党及其活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社会主义党的成员Jorge Jorquera在2020年Maribyrnong市镇的选举中当选市议员。[2]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这也是他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备忘录和框架协议的思想根源之一。这都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仍然是澳洲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澳大利亚的社会主义这个时代课题是扎根于现实生活之中的。
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人类追求政治经济平等的思想理念。社会主义主张社会拥有、共同享有、共同劳动,其特点为由民主来控制生产资料(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社会拥有”可通过国家拥有、集体拥有、公民持股来实现。在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中,由于各国历史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其形态和实践方式各异,不同于俄罗斯和中国,澳洲并没有大量无土地的农民。澳洲通过立宪建立了联邦政治制度,任何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和发展都受制于这个宪政安排。因此,在澳洲通过暴力来改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完全行不通。澳洲不可能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澳洲只是推行有限的国有化政策,实行部分的社会主义,即共同享有的民生社会主义[3],或小范围的社区社会主义。
目前对澳洲社会主义的研究往往与历史、女权、阶级、种族、环保相联系,但是缺乏对澳社会主义形态和实践方式的详细深入研究,大部分研究拘泥于劳工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分,或劳动党内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分。这些区分对我们理解澳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颇有价值,[4]但是不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澳洲社会主义主要形态和实践方式。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的三种形态和实践:乌托邦的社区社会主义、温和渐进的民生社会主义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并简要讨论澳洲历史政治文化条件对三种社会主义形态和实践的影响以及三种社会主义形态之间的有机联系。本文注重实践中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注重实践,回归民生。
乌托邦的社区社会主义
乌托邦的社区社会主义形态时间跨度超过一个世纪,其主要特征是:以一个社区为基础,民众过着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生活;它是小范围的社会实验,不能进入社会主流;从以白人种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发展为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社区社会主义。早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乌托邦理想主义者William Lane在澳洲殖民地上建立了社區社会主义的实验地,称之为“新澳洲”。他受Edward Bellamy的影响,认为种族矛盾阻碍了社会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因此他主张只在讲英语的白人中建立社会主义。然而,正是他视为“亲兄弟”的白人,有38个人因为不满意他的无能和平庸离开了他,另辟新的社会主义实验园地。[5]
社区社会主义的实验在澳洲历史上层出不穷。在20世纪70年代,澳洲受世界社会主义影响,对外反对越战,对内寻求新的社会主义方式。1975年,有学者著书就详细规划了如何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在澳洲内陆地区打造小社区,实行一种“无政府”、“去中心化”和“环保”的理念,并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新创造”。[6]笔者好友Geoffrey Stokes教授在1975年任南澳政府工业民主指导委员会专家,工作内容就是推动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参与。笔者曾在1988年受邀参观一个社区社会主义的实验地——上百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个深山老林之中。他们只是对外才使用货币,内部并不使用货币,内部之间的劳动帮忙采用记分制。他们过着田园般的宁静生活,社区的财产是公共支配,有一些甚至“共妻”和“共夫”。这种社区的社会主义生活是封闭的、小范围、零散的和远离城市的。它不可能在主流社会中复制其生活方式。但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只要少数人向往社会主义理想,将其财产拿出来让一个小群体的人以民主议事的方式决定如何支配其“公共”财产,这种乌托邦式田园般的社会主义方式就能生存下来。
目前,澳洲城区中也盛行社区菜园。居民在一块公共的土地上种植不同蔬菜,或在自己宅地上种不同蔬菜,然后把丰收的果实放在一个公共场所中,人人按需取之。这种新型的按需分配的社区社会主义往往包括各种不同民族的人群,是以多元文化主义为基础的,并且与环保紧密联系。这种社会主义环保联盟也被称之为生态社会主义。2020年10月24日~25日,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澳洲社会主义大联盟召开了网上会议,讨论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一理念和实践。[7]
温和的、渐进的民生社会主义
温和的、渐进的、非暴力的民生社会主义的推动力来自于工会和工党,其注重民生和社会福利并在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上作了退步,因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暴力剥夺他人的财产来建立一个社会共同拥有的财产制度是不义的。于是,他们主张通过立法方法来推行国有化政策,例如,早在1911年,工党政府立法建立了澳洲联邦银行。1946年,南澳政府收购了私人电力公司,建立了政府的电力公司。工党在推行银行国有化中遭受了几家资产雄厚的私人银行的强烈反对。1948年,25位银行家在悉尼攻击工党是“残酷的社会主义官僚集合体”。1949年12月,工党在大选中惨败。[8]
澳洲社会主义主要体现在“共享”,即全民共享的社会福利政策。失业者每周可领到数百澳元失业金。穷人可申请政府建造的房屋。据统计,2011年,全澳约有30万套政府房屋,约占所有房屋的4%(丹麦的政府房屋占20%,法国的政府租房达到40%,英国的政府房屋高达50%)。在吃住行方面,澳洲人都可以享受最基本的福利,不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担忧。这种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每个穷人都有权享受最基本的福利。
推动民生社会主义的动力来自工会和工党。早期澳洲工党成员有不少来自贫困工人,特别是爱尔兰人。这一特征导致澳洲工党一直有反英的传统。[9]例如工党领袖第29届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具有爱尔兰血统,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澳洲在1999年举行了不承认英国女皇为澳洲国家元首的公投,结果只获得45%的认可,而反对票占54.8%,这一提议以惨败结束。
当然,澳洲工党能否被称为社会主义政党是具有争议的。早在1905年的澳洲工党党章中就有条款主张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1921年,澳洲工党领导以15票支持、13票反对主张限制集体所有制的公司从事“剥削”活动。有人从马克思主义反对剥削的理论视角来断定工党应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不少学者断定工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10]1927年,澳洲工党重新界定了党章中关于争取目标的方法,明确主张采用宪政方法来达到目的,删除了关于建立工人委员会来管理国有企业的条款。[11]到了1970年,Humphrey McQueen认为工党的发展已逐渐远离了普通工人,作为其主要成员的白领工人已慢慢形成了一种小资产阶级心态和生活方式。因此,他认为工党已成为澳大利亚小资产阶级的代表。[12]
不管如何评价澳洲工党的阶级性质——是否为社会主义政党,工党确确实实地在推进和贯彻民生社会主义政策。1904年,澳洲工党领袖克里斯·沃森出面组阁,这是工党第一届联邦内阁,克里斯·沃森总理利用掌权机会来扩大工人阶级权利,在修改仲裁法庭法律中提出应对工会会员予以优待。[13]此项提议在国会中被否决。后来,1906年,以阿尔弗雷德·迪金为首的关税保护派和工党联合,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城乡工人的法律。如1908年颁布的《残废恤金和养老金条例》规定,凡年满65岁本地出生的和归化的英国人,并在澳大利亚居住一定年限后,均可领养老金。[14]
1910年,澳洲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工党领袖安德鲁·费希尔提出了征收土地税,这一政策有利于打破“大地产制”。费希尔政府还颁布了建立联邦银行法案。20世纪初,澳洲工党的两次执政,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为未来澳洲民生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塑造了一个政治“基因”:即通过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来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征税政策来调节社会分配以减少和控制极端的不平等;通过选举来推行民生社会主义政策,把社会财富尽可能地分配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保证任何人享受最基本的生活。
当“共同占有”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目标时,工党就追求“共享”,即一种注重民生的社会主义政策。这种社会主义虽然不彻底,但是它避免了由一个官僚集团来管理国有资产所形成的一个特权阶级的问题,也避免了国有企业低效率的问题。F. W. Eggleston在1920年~1927年之间担任维省议员,负责大型公共设施建设。根据他的亲身经验,他主张尽可能运用市场来提供公共服务。[15]
民生社会主义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笔者曾经访问过一个农场主,他已经70岁了,还努力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然后,他指向一位刚好来访问他女儿的单身妈妈,说她不干活却享受单身妈妈的特殊福利。澳洲人懒惰的声名在外,殊不知,澳洲有些行业的专业人才常常每天工作12小时。此外,近十几年,澳大利亚的福利越来越少,以前读大学免费,现在必须付学费。目前,澳大利亚靠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尚可维持这种福利制度。未来,这种福利制度是否可持续是一个大问题。
有人会认为澳洲这种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优于苏俄的暴力革命。这种评价谴责了暴力革命,表面上似乎很正确,但是却切割了历史现实。稍懂澳洲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英国殖民者曾大规模虐杀澳洲原住民。正是这段残酷的历史解决了原始积累问题,消除了土地问题,为之后的温和、非暴力方式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澳洲温和的、非暴力的改良道路一旦碰到了强大的阻力,它就会停滞。一旦涉及特殊利益集团,推行民生社会福利政策的政府首脑就会被迫下台。1970年代初年,爱德华·高夫·惠特兰总理在国内推行许多激进“社会主义”政策,在对外政策上与中国建交,公开指责美国在越南使用生物武器,在美国和苏联的大国竞争中试图保持中立,与尼泊尔一起在联合国主张印度洋为“和平之洋”等。结果,他在1975年便被迫下台。2012年,陆克文总理对大矿产公司施加了30%的矿产税。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矿产资源理应国家所有,如不能国有化,施加高額税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这种侵犯大资本利益的举措遭到鲁伯特·默多克等媒体大亨的反攻、围打,导致陆克文的民意支持率大幅度下降,工党高层怕在选举中惨败,最终陆克文被“逼宫”下台。由上述两例可见,澳洲的民生社会主义的巨大局限性和基本底线就在于它不能从根本上侵犯资本利益。
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
澳洲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态是激进的马列主义政党所推进的政治社会运动。澳大利亚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10月30日,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1930年代初领导了煤矿工人大罢工和失业工人的斗争。澳洲共产党是一个工人为主体的政党,澳共大部分干部都担任各类工会的领导职务。与中国不同,澳共在农村影响甚微。在农村,澳洲有“澳大利亚乡村党”,在1919年大选中得到了11个众议院席位,在1922年大选中获得了14个众议院席位。相反,澳共和“社会主义工党”未获得任何席位。[16]
到了1940年代,澳共党员人数已达到2.5万人,在大选中得票率占比为3%。1949年,澳共成功地领导了煤矿工人大罢工。为此,工党政府颁布了“全国紧急法案”,冻结了矿工基金,宣布动用此基金支援罢工工人为非法行为,并派军队入驻露天煤矿。罢工坚持到1949年8月15日而宣告失败。[17]1950年4月,孟席斯政府在国会中通过了“解散共产党法案”。同年10月,澳共和10个工会向高等法院提出起诉。1951年3月,高等法院以6票对1票否决了解散法案,认为该法案不符合宪法。尽管当时发生了朝鲜战争,但是大法官认为,澳大利亚并未处于战争状态,不能随意解散政党。[18]可见,澳洲的宪政发挥了保护澳共的作用,当然,后面笔者将指出其宪政也限制了暴力革命的发生。
澳共在1970年分裂為三个小型政党:国家共产主义政党、澳洲社会主义党和澳共(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外,还有托洛茨基派别。澳共政党的分裂导致其在大选中没有拿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议会席位。当时,澳共大约有2000名党员,亲莫斯科的澳社会主义党只有低于1000名党员,亲北京的澳共(马克思—列宁主义)支部只有200多人的党员。[19]
1989年~1991年的苏东剧变也影响了“澳共”的政治命运。随着苏联解体,“澳共”宣布自动解散,其党产由一个民间基金管理,保留和管理澳共的历史文件等。各种共产主义政党纷纷转入加入各种环保组织。1996年,从澳共分离出来的“澳大利亚社会主义政党”重新更名为“澳大利亚共产主义政党”,并宣布其是1921年建成的“澳共”的合法继承人。2001年,几个社会主义政党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同盟,到2010年两个主要的派别合并,但总体来说,其政治影响力远不如以前。
澳洲政府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1991年通过“改制”实现联邦银行“私营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澳洲的“私营化”加速了,包括1993年改制澳航(Qantas)、1995年维省的电网、1997年的国家电信、1999年的墨尔本公共交通、1999年的南澳电网、2002年的悉尼机场等。
激进社会主义运动在澳洲受限于下面几个因素。第一,来自英国的自由传统根植于澳洲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中,民众一般都倾向保守,不赞同、更不支持激进的暴力手段。如前所述,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认为通过暴力来剥夺他人的财产建立一个社会共同拥有的财产制度是不义的。第二,澳洲政府对共产主义政党的暗中控制也影响了年轻人参加共产主义政党。一位朋友告诉笔者,他曾经在1970年代想参加澳洲共产党,但怕被列入黑名单影响就业而放弃。第三,澳洲联邦宪法的限制。澳洲工党曾多次取得政权,但是每次工党执政时试图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推行新政策,总是遇到抵抗而失败。唯一的例外是在1946年工党取得了一点小成功。[20]工党一直抱怨宪法限制其追求社会公正的努力,有些工党成员试图在宪法之外,或废除某些宪法条款,但这些努力往往一无所获。澳洲联邦主义学者Brian Galigan指出,联邦政体并非中立的,它往往限制了政府的权力,偏向于私人资本。澳洲的联邦制度是用来保护自由经济的,它在制度上避免一个强大的政府。[21]在历史上,宪政限制了工党的改革措施和方案,但正如前文所说,澳洲的联邦宪法也保护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生存,澳共通过法律手段避免了政府解散其组织的发生。澳洲的联邦宪法也保护了州的自治权力,因此每个州可自行发展其社会主义的政策。
澳洲激进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但是它在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正是激进社会主义运动逼使工党不断采取更多的民生社会主义政策以获得广泛的选民支持;正是激进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自由党政府在民生社会主义政策上作出退步,以避免暴力革命的发生。澳洲工人权利保障的完善,虽然是在工党推动下完成的,但是背后的巨大动力来自激进的社会主义,因为后者提出了激进的社会主义目标,通过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强迫政府来改善劳工的生活。澳洲人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乏激进社会主义的功劳。
对于目前澳洲民生社会主义的退步,我们也许可以提出下述假设:激进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降低了实施民生社会主义的动力,因此导致了民生社会主义的退步。西方赢得了冷战,但是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冷战结束后,当西方失去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平衡力量,资本主义就疯狂盛行,由此导致了经济上的极端不平等,为特朗普的上台留下了伏笔,造成了目前美国政治的动荡。
澳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可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澳洲社会,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看成是彼此取代的关系是简单化的、不符合事实的。正如前面所说,正是社会主义的推动,迫使自由主义发展和完善了人权机制,特别是保护劳工和贫困人群的最基本需求的社会福利政策和保障机制。一旦自由主义没有了社会主义,它就会变成一个狭小自私的学说;一旦自由主义否认自由价值的公平属性,就无法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健康和强大的自由主义,必须采纳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反之,一旦社会主义缺乏自由主义,它就会产生一个专横的特权阶级,最终走向反面。澳洲进行了一种混合努力的实践: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中,部分地实现民生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而且二者可以融化一种新的混合政治文明。当然,澳洲的民生社会主义有其内在的巨大局限性:它不能从根本上侵犯资本利益!
注释
[1]William A. Edmundson, John Rawls: Reticent Sociali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2]https://www.victoriansocialists.org.au/.
[3]Eggleston早在1934就把国家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国家提供公共服务。See F. W. Eggleston, State Socialism in Victoria, London: P. S. King & Son, 1932.
[4]Don Aitkin, Survey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Scienc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5, pp. 333-335; also see Boris Frankel, "Beyond Labourism and Socialism: How the Australian Labor Party Developed the Model of 'New Labour'", New Left Review, 1997, No.3.
[5]John Kellett, "William Lane and 'New Australia': A Reassessment", Labour History, No.72 (May, 1997), pp. 1-18; also see Geoffrey Stokes, "The 'Australian settlement' and Australian political thought",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04, Vol.39, Issue 1, pp. 5-22.
[6]Margaret Smith and David Crossley, Margaret Smith and David Crossley, The Way out: Radical Alternatives in Australia, Melbourne: Lansdowne Press, 1975, chapter 11 on living styles.
[7]Hans Baer, "Towards Democratic Eco -Socialism in Australia", accessed at https://socialist-alliance.org/alliance-voices/towards-democratic-eco-socialism-australia, on 11 May 2021.
[8][9][14][16][17][18]張天:《澳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35、246、245~247、278~279、335~336、338页。
[10][11]Peter Coleman, James Jupp, H. B. Gullett, P. B. Westerway and Joan Rydon, Forces in Australian Politics,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63, p. 34.
[12]Don Aitkin, Survey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Science,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85, pp. 332-333.
[13]Stuart Macintyre, 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Vol.4, pp. 1901-1942.
[15]F. W. Eggleston, State Socialism in Victoria, London: P. S. King & Son, 1932.
[19]T. B. Miller, Australia in Peace and War,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40-41.
[20][21]Graham Maddox, Australian Democrac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Melbourne: Longman Cheshire, 1985, p. 124, p. 125.
责 编/张 晓
何包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与政治学院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中国乡村政治。主要著作有《民主理论:困境和出路》、《协商民主:理论、方法和实践》、《正义论》(合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