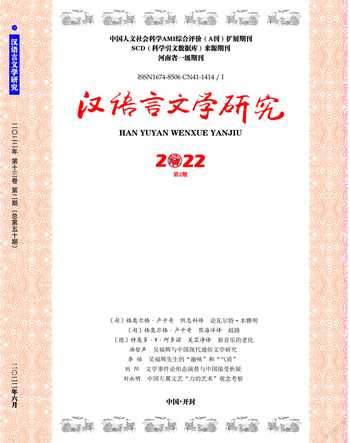贬须臾之道以济天下
摘 要:由于部分学者在辨伪上的卓越表现,古文《尚书》的存废,成为清代学人普遍争讼的焦点。主张不废古文的学者,除了更看重“存古”和“求道”的价值之外,尤其在“理学”和“治道”两面,强调古文《尚书》不可轻易言废的独特价值。庄存与作为该派学人中的“魁硕”,特别对《尚书》中蕴含的家人父子伦理作了独特阐发,强调非天命不敢嗣位、人子当大孝、处人伦之变当法舜等内涵。在皇家伦理惨剧频发的康雍乾时代,他的这些阐发与其皇子师傅的职业和朝廷的现实规制有密切关系,彰显出清代不废古文派学者别样的经世关怀。
关键词:古文《尚书》;尚书学;庄存与;皇子师傅
进入清代,辨伪陡然成为尚书学中的焦点问题,受到众多学人关注,也取得了巨大成绩。经过阎若璩等学者的努力,使得自宋代以来即受到怀疑的古文《尚书》,逐渐被主流学界判定为伪作。但由于《尚书》一经不但是中国的基本典籍,还在国家文教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有关它的真伪,以及连带出的存废问题,即因关涉过多而受到不同立场学者的广泛争论。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其间大致可分为三派:彻底推翻伪古文的、坚持非伪的、明知其伪而主张不废的。①不过,因为辨伪派的主流地位,过往研究多集中在对该派辨伪成绩和方法的研讨,而对主张不废古文的学人,则仅注意到了他们更看重读书“求道”而非“真伪”,但对于所谓“道”的真切内涵及其背后关怀,则尚缺乏深细具体的讨论,故而对此派学人的理解还多存待发之覆。②本文即拟在考察清代诸儒一般论说的基础之上,深入主张不废古文的著名人物庄存与的尚书学著作,以期更为具体地探索此派学人问题意识背后的时代关怀。
一、不废古文《尚书》的理由
主张古文《尚书》不可废的学者,难免有其各自的理由,但仔细梳理,也会发现存在一些普遍关心的焦点。
首先是有部分学者从“存古”的立场出发,认为古书难得,多有采摭缀缉之功,自当存之为贵,如王懋竑即称:“东晋所上之《书》,疑为王肃、束皙、皇甫谧辈所拟作,其时未经永嘉之乱,古书多在,采摭缀缉,无一字无所本,特其文气缓弱,又辞意不相连属,时事不相对值,有以识其非真,而古圣贤之格言大训往往在焉,有断断不可以废者。”③朱彝尊亦有同样看法,“是书久颁学官,其言多缀缉逸《书》成文,无大悖理,譬诸汾阴汉鼎,虽非黄帝所铸,或指以为九牧之金,则亦听之。”①
其次,更为重要的,正如先行研究所指出的,另有部分学者从治学的目的着眼,认为读书原本即为求道,苟道之所在,真伪本可不计。如万斯同称:“夫学者读古人书,在别义理之深浅,而文词之险易其次也。”②颜元称“古来《诗》、《书》,不过习行经济之谱,但得其路径,真伪可无问也,即伪亦无妨也。”③显然在他们看来,文本不过是筌蹄之属,是为得“道”服务的,如果道是真实的,文字的真伪自可忽略不计。
这些学者之所以坚定地不废古文《尚书》,显然他们所关心的所谓“道”或“义理”,在其时代中就不应当是空泛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关涉到他们眼中古文《尚书》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原本与五经中的其他诸经相比,《尚书》即以多载二帝三王治政临民之实事而成为探讨外在治道的重要典籍。故《荀子·劝学》云:“《书》者,政事之纪也。”但时至两宋,经过诸儒尤其是朱子对古文《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虞廷十六字”的发挥,使得古文《尚书》成为建构理学心性学说的重要凭借,《尚书》因此又具有了向内修己的巨大价值。通观清代学人对古文废立的争辩也可发现,他们所倾心关注的,亦不过一为理学,二为治道。如皮锡瑞总结说,古文《尚书》相承不废,其远因有二:一是虞廷十六字,宋儒以为乃道统之相傳;二是除虞廷十六字之外,古文经亦多为宋儒言道学所本。此外,其近因亦有二:一是不废古文,君臣父子多得陈善纳言之益;二是如废除古文,恐对帝胄天孙无以垂戒。④可见皮锡瑞的总结也正落在了理学和治道两端而已。以下则通过其他清儒的论述,对这两方面再分别略作梳理。
李绂指出:“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⑤另据晚清学人张文虎观察,今古文真伪聚讼不休,主要原因有五条。⑥不过,除第一条“理学家以虞廷十六字为道统真传,一旦以为伪,则失其所凭依”之外,张文虎所梳理的其他四条都集中在汉学家具体辨伪方式的不智之上。这种观察显然流于表面,没有照顾到不废古文的学者的核心关怀。不过其第一条看法,却道出了清代学者的普遍担忧。其实早在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之时,即有人忧虑及此,批评阎氏“且得罪于圣经,而莫可逭也”⑦,朱朝瑛(号康流)更明确质问:“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渊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绝矣,而可伪之乎?”⑧其意在揭示,如果此十六字为伪,程朱亦会受到株连,有人即提醒李调元:“微危精一,理学家奉为宿海,若疑古文,则程朱先挂口矣。”①
我们发现,将“程朱先挂口”者,却不仅仅是汉学家。比如,有观察者指出,在当时崇王的学者之中,不论是支持阎若璩的黄宗羲,还是批判他的毛奇龄,表面对辨伪的态度看似相反,却在内里有着相通的目的,李光地称:“黄梨洲、毛大可辈,掎摭一二可疑之端,辄肆谈议,至虞廷十六字亦辟之。学者不深惟理义,徒求之语言文字以定真赝,所谓‘信道不笃’也。”②李绂称:“毛氏素不善朱子之说,其为此书《古文尚书冤词》,亦藉以驳朱子耳,其本意岂诚笃信古文《尚书》也哉!”③可见阎若璩的这一辨伪,虽然一定程度上为清代的汉宋之争点燃了引信,不过在其所处的时代,也同时为程朱陆王之争提供了武器。这显然也是尊朱的学者所不愿看到的。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真伪的讨论根本不会影响古文《尚书》的存立,担心因“伪”而“废”纯属多余。如谢章铤即称:“试平心察之,字句气体之间,何以相悬若此乎?果皆真耶?抑亦有不可信耶?此故不必以强词争也。若其书则萃古来之微言大义,字字若禹鼎汤盘,从来作伪无此妙巧,且言心言性,举宋儒理学之渊源,莫不萌芽于此二十五篇,立之学官,悬为经鹄,盖千百年矣。又有大力者负之而趋,谁能废之?亦谁敢言废之?世俗之《感应篇》《阴骘文》尚足长留天壤,而况所托甚高,所言又甚正哉!”④此亦一家之论,察其立论的背后,还是在凸显古文对理学的巨大价值。
如上所述,除维护程朱理学之外,更多的学者主张不废古文《尚书》,是出于对“治道”的关心。但是他们却并非为普通官吏或儒者而发,而是着眼于帝王的治国理政。如齐召南在向皇帝进呈一己著作时,即明确说:“虽朱子亦尝疑之而不能不奉为经者,其言道粹然不诡于正,其言治犁然足为后代准绳。《大禹谟》精一执中,上绍二《典》;府事歌序,后起箕畴。《汤诰》言降衷恒性。《仲虺》言制事制心。千古圣贤学问之渊源、功德之基本具在,古文不可没也。”⑤点出了古文《尚书》在帝王制心和制事两方面的巨大价值。齐召南的这一看法,在其前辈王植那里也有着几乎同样的呼应:“如《禹谟》克艰之旨、惠迪之言、五子之歌以下,若‘不见是图’与夫‘制心制事’、‘立爱立敬’,以及‘协于克一’,何一非圣人之精蕴,岂后人剿说所能为。‘且其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深沉而切至,高明而矫健’,诚有如陈第之言者乎。”⑥论说虽多,但按其实质,还是不出古文《尚书》对帝王制心、制事两方面的作用。
在另一篇文字中,齐召南将这一意涵表述得更为显豁:“经虽残缺,二帝三王致治之本末具存,天不变,道亦不变,修己治人各充其量,岂有难知而难行者欤?”⑦这里的修己与治人,不过是上文制心与制事的另一种表述。管世铭亦称:“二帝三王修身之精蕴,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今古文所载一也,至谓一句一字皆出于当日史氏之原文,吾非特疑古文,且将疑今文也。”⑧黄廷鉴称:“古文中之心源治法、微言古训,较诸经为切。刘子骏有言‘礼失求之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⑨不论是“修身之精蕴”“治国平天下之大道”,还是“心源”“治法”,都是在强调古文《尚书》对帝王立身、出治的重要价值。而程晋芳则将治人讲得更为具体:“二帝三王之道,莫备于《书》。自天文、舆地、职官、乐律、礼制、刑罚之大者,皆在焉。由其道则治,反其道则乱,得其片言微义,皆足以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而绵翼子孙于世世。要其大旨不过二端:知人、安民而已。”①
因此,他们难免对因真伪而有废立的议论嗤之以鼻,李绂说:“其所收采正文,固当奉为齐治均平之本,攻者不必攻,而辨者亦无庸辨也。”②翁方纲说:“况如六府三事、九功九叙之政要,危微精一之心传,此而敢妄议之,即其人自外于生成也必矣,自列于小人之尤也审矣。”③
古文《尚书》上述的政治功用,必然依赖实现的管道。阮元曾对此有特别提示,他在援引北周和唐代君主与臣子、皇子引《书》以互动的几个例子之后,说:“凡此君臣父子之间,皆得陈善纳言之益。唐宋以后引经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讲筵之益者,更不可枚举。”④可见,这一实现的管道,在于日常的陈善纳言和日讲经筵等君主学习制度之中。与阮元相似,龔自珍在讨论庄存与不废古文《尚书》之时,特别指出庄存与意图通过皇子师傅的身份,将古文中有关修己和治政的道理授与皇子:
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说命》废,“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肄业者。⑤
虽然这篇文字被魏源评价为“斯足以当奇文、大文之目”⑥,但龚自珍却坦承,此文提到的传主“行事之美”是他听庄绶甲(庄存与孙)说的,而庄存与教授《尚书》的苦心孤诣(“公志”),却是宋翔凤(庄存与侄外孙)为他推测的。⑦故其表达的,可能更是当时人的一般认识,这从此文虽然提到多篇古文《尚书》,但实质并没有脱离修己和治人两面即可看出。由于庄存与恰有两部尚书学著作存世,我们正可通过对其文本的追查,来更加具体地探讨其不废古文的具体立场,以及此派学者论说的时代语境及真正关怀。
二、庄存与尚书学的视点
庄存与共有两部尚书学著作,即《尚书既见》和《尚书说》。由于《春秋正辞》的非凡水准,庄存与在后世主要被当作清代公羊学的代表人物。然而在他自己看来,其最为擅长的却是《诗》《书》之学。⑧而且常州庄氏一门,也以尚书学传家,庄存与侄庄述祖、孙庄绶甲,皆传存与《尚书》之学,前后相望,有声于时。⑨与此同时,庄存与两次出任皇子师傅,其著作多为授读皇子的教本,①可正好为我们探讨这些著作的时代意涵提供基础。
《尚书既见》初版于乾隆癸丑(1793),当时并未分卷。道光七年(1827),庄绶甲在整理汇刻其祖遗书时,重新对《尚书既见》进行了编辑,将其内容析分为三卷,并将其父庄逢原新又收集的“零章断句”编为《尚书说》一卷,一并付刊。②《尚书说》共收集21条庄存与论《尚书》的文字,除极个别者外,基本一条论述《尚书》中的一篇。其篇幅有长有短,长者或就《尚书》某篇的一个问题,阐述一己之看法;短者或仅为一句,解释对某个字词意涵的独特理解。因此,我们可以将《尚书说》看作是《尚书既见》的补遗,合并讨论。这两部著作,均为学术札记体,显示出明显的随手笔录、未及写定的特征。③
《尚书既见》的内容,庄绶甲曾有过提示:
今绶甲冥心讽诵,谨条其大旨,弟为三卷。一卷首篇正后儒之误解《禹谟》为再征有苗,重为《书》诬,因以明不攻古文之意;次篇释《盘庚》,而证以二《雅》,因以著以经解经之法;三篇阐《书》之言天、言命、言性至明切,而怪后儒卤莽读之也。二卷皆论周公相武王、辅成王之事,一衷于经与序,以明文武之志事,述显承之艰难,辨成王不能莅阼、周公践阼摄政之诬。三卷皆论舜事父母之道,以孟子之言为本,而证明逸《书》之《舜典》,后述伊尹、周公之遇,皆所以明圣人之于天道也。④
庄绶甲对该书内容的概括异常准确。第一卷共三篇,前两篇主要讨论“不攻古文”和“以经解经”的立场,唯有第三篇在讨论“天”“命”“性”等内容,借以批判宋儒的立论。第二卷,则主要辩论成王年龄非幼,而周公亦不曾践阼摄政,借以维护周公尊王、未曾僭越的圣贤形象。这前两卷的内容,大致可说是在“制心”与“制事”的范围之内。但是第三卷,讨论的却是“舜事父母之道”,此一家人父子间的伦理关怀,似乎并没有出现在上揭诸儒所论及的古文《尚书》的价值之中,因而值得特别予以讨论。综合而言,第三卷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一是非天命不敢嗣。《孟子·万章》篇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庄存与以此为基础,以为天子能命人为诸侯,但不能命人为天子,因此,其人苟无天命,则不得继位为天子。然而,后世对开国之君如舜、禹得天命易知,但对继体之君如启、太甲、成王之受命于天则难知。故有以为自身得天命,而强致之者,庄存与以为“天命不可为而致也”⑤。因此,尧崩,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但天下之民不从丹朱而从舜。舜崩,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而天下之民不从商均而从舜。禹崩,益避禹之子启于箕山之阴,天下之民不从益而从启。庄存与以为,盖天命在舜、禹、启,而不在丹朱、商均、益也。与之类似,伊尹知天命在太甲,虽然因太甲不肖而放之于桐三年,但终迎太甲复位。而反之即使圣德如周公、孔子,以不得天命故,也不得有位,即周公相成王而并不亲践祚⑥,孔子不能有天下,所谓“夫位之不尚于德也,天命之矣”。⑦庄存与如此强调得天命在继位中的作用,显然有其在君王家人父子之间防微杜渐的理由。
二是为人子者当大孝。庄存与以舜为例,讲述为人子者当大孝。尧举舜于畎亩之中,以二女嫁舜,不以天子之贵加舜及其父母昆弟,二女亦不以天子之女之贵视舜及其父母昆弟,当时舜尚未继位,仍为耕稼之匹夫。庄存与认为,尧以舜事于天下,而舜则以尧事于父母,尧派来服侍舜的九男、二女,以及为之配备的百官、牛羊、仓廪,皆成为舜的悦亲爱弟之资。“舜何有焉,而后可以底豫,底豫而后天下化,天下化而后大孝成,舜惟终身于慕父母之诚而已,他不与有也。是故谓之大圣,是故谓孝子之至,是故可为法于天下,传于后世,而为人子之极则。”①庄存与突出舜大孝的努力可见一斑。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庄存与以长篇大论为舜不告而娶辩诬,以维护舜大孝的形象。其结论不过是名告而实不告,反经以合道,圣人之权也。②不过这一论述,还是以庄存与一贯的推原圣人之心的写作方式而出,故略显牵强和迂曲。庄存与并且认为,天子尊养其父,不当以名,而当以其实与其诚,即“养非口体之养,志之养也。《孝经》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是之谓以天下养而尊亲之至也。不惟其物,惟其诚焉;不惟其名,惟其实焉”。同样显示出庄存与对此问题的关注点。
三是处人伦之变当法舜。史载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处于这样的人伦惨境中,舜却能够顺适不失子道、兄道。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终于感化父母及兄弟,而避免了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庄存与以为,“舜果非圣人,而不可以为子矣。春秋以来,不胜书也”。庄存与并推原为何必须要像舜一样对待兄弟,认为虽然天下皆谓舜为圣人,但如果瞽叟独谓舜不孝,则天下莫能自持其说;雖然天下皆谓象为凶人,但如果瞽瞍独谓象为孝子,则天下莫能执象之口而服其心。而舜也明白,能悦天下者,己也;能悦亲者,弟也。悦天下万万,不若悦亲,则己断断乎其不如弟。而就道理而言,舜所顺者父母之天也,而不顺其人;象所顺者父母之人也,而不顺其天。因此,未敢谓舜全得、象全失矣。因此,象之心一日不安,则舜之心终身不著。故舜引咎归己,日以爱弟之道待象。庄存与且谓“兄弟宁校计是非之人邪!是以诗人所刺、《春秋》所讥,皆遭人伦之变而不能如舜之善全之,以为大恶”,人苟不能为舜,则终为残杀手足之不孝不慈而已矣,必无中立之道。并且认为天子待兄弟之法,无有不富贵之者,不当问其仁不仁也。“天下之为人兄者,不可以不善其弟。弟之不仁,兄不可以为仁人也。天子之为人兄也,不可以不私其弟,他人不容吾私,吾弟则必行吾私。无私者,无亲也。天子必有亲,圣人必有亲,人道亲亲,未有不如此而王天下者,不自有虞氏始,以人心为皆有之。”并再次强调“为天子者,慎毋使诸父昆弟怨其尊而不亲也。然后能合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则天下和平之本在是矣”。同时指出,“夫兄弟之恩,不在共富贵,在常相见;不在同政以子万民,在同心以事父母”,③可见,富之以财,不尊之以位,同心事父母,而不共同子万民,依旧是庄存与为天子善待兄弟划出的范围,其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分寸讲究。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庄存与的《尚书》学关怀,实际均局限在君王(尧舜禹)的家人父子之间。揆诸庄存与出任皇子师傅的人生经历,可以肯定,此类论说的对象即为其教授的皇子,其目的即在于规范皇子的行为。其间既包含为皇子指出正面效法的榜样、以及应该重视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在反方向上,提防由于皇子所处的敏感境地,而出现因争位致使父子离心、骨肉相残的人伦惨剧,故而他尤其强调天命在继位中的首要条件性,以及效法舜的大孝与大悌的重要性。在经过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父子相离以及雍正初年手足相残的人伦惨剧之后,庄存与在乾隆朝做这样的强调,就更显得不是无的放矢。由此,我们也可对不废古文学者的核心追求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这当中包含有他们作为经学通明的儒者处在权力核心中所期望发挥的一己职效,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古文《尚书》在此一方面的特别意义。经义不能脱离时代,正是他们的追求,也是经书的价值所在。
为更加深入理解不废古文的学问主张与时代关怀间的关系,有必要对其落实这些关怀的管道作更加具体的追索,下文继续以庄存与为例,对其所出任的皇子师傅一职,继续做些探索。
三、朝廷规制下的现实关怀
庄存与一生,两次出任上书房师傅。第一次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次任职大约至三十九年其提督山东学政、寻调河南学政为止,共7年时间。第二次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①,此次供职的时间大约为5年,至五十一年(1786)原品致休为止。
庄存与第一次入职上书房,教授的是皇十一子永瑆,现有永瑆《送庄方耕师傅授提督河南全省学政序》可证②。第二次入直,教授者为谁,目前史料缺乏,尚待考证。另外,清代宗室有承恩入上书房读书的习惯,据庄氏族谱所记,庄存与亦曾授读过弘旿和永珊。③庄绶甲曾说,庄存与“入侍皇子课读,惟以经术讲授,不负平日所学。具见器重,敬爱日深”④。庄存与入直之时,永瑆方17岁,虽然清高宗一生共育有17子,但大多早卒,此时具备竞争储君资格的仅有5位: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璿、皇十二子永璂、皇十五子永琰及永瑆。而皇四子永珹虽然也在世,但已出继允祹,失去了继位资格,另外最小的皇十七子永璘尚未出生。因此,永瑆此时具有竞争皇位的巨大潜力。庄存与处于这样核心和敏感的地位,以经说来教授皇子,其责任和意义自然不同。
清代的皇子教育,从康熙朝开始逐渐形成制度,历来甚为用心,要求亦甚为严格。皇子六龄入书房,每日卯入申出,一年的假期只有万寿节、元旦等少数几天。⑤并且皇帝还经常以各种方式检查课业,一旦发现问题,皇子与师傅皆会连带受到责罚,《清高宗实录》中多有此类记载,约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师傅不能勤于供职,皇子学业荒疏而受到责罚,如乾隆二十年(1755),皇帝偶行至上书房,不闻读书声,发现师傅多半未到,考核皇子作诗,虽然依韵完篇,但全无精义,乾隆发怒,命将上书房师傅“嵩寿、蔡新、奉宽、程景伊、陈德华、周玉章、梁锡玙、吴炜、张泰开俱著罚俸三年”。⑥再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皇上简阅上书房师傅入直门单,发现自三十日至初六日,所有皇子皇孙之师傅竟全行未到,不由大怒,将上书房师傅“刘墉、胡高望、谢墉、吉梦熊、茅元铭、钱棨、钱樾、严福、程昌期、秦承业、邵玉清、万承风俱著交部严加议处。至阿肃、达椿,身系满洲,且现为内阁学士,毫无所事,其咎更重,均著革职,仍各责四十板,留在尚书房效力行走,以赎前愆而观后效”⑦。一天之后,又将上书房总师傅刘墉予以惩处,“刘墉著降为侍郎衔,仍在总师傅上行走,不必复兼南书房,以观其能愧悔奋勉否”⑧。从此类处罚的力度,也可以看出乾隆对皇子师傅要求之严格。
另一类是皇子言行不当或越轨,则师傅会一并受到牵连。如乾隆十三年(1748),孝贤皇后去世,乾隆甚为哀痛,而大阿哥、三阿哥举止不当,“并无哀慕之忱”,被乾隆责为大不孝,甚为震怒,除明白宣示此二子将来不能继承大统之外,并以诛杀相戒,称“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⑨。并归咎于师傅和谙达平时并未尽心教导,命将“和亲王、来保、鄂容安著各罚食俸三年,其余师傅、谙达著各罚俸一年”⑩。再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礼部司员秦雄褒与阿哥绵德交通,为乾隆发现,除绵德被革退王爵,秦雄褒被发往伊犁之外,“绵德之师傅李中简,不能教诫管束,咎无可辞。该员本系缘事降调,复经赏给编修职衔,仍令在书房行走,今复不能尽职,即著革职,逐出书房”①。
再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八阿哥以己事私自入城,被乾隆发现,除八阿哥及师傅、谙达受到处罚外,乾隆并下谕曰:
师傅为诸皇子授读,岂仅以寻章摘句为能?竟不知随事规劝,俾明大义。而总师傅,则尤当尽心诲导,凡事纳之于善,勿使稍有过愆,方为无忝厥职。今于八阿哥擅自出入一节,漫无觉察,所司何事?②
如果说中国经典原本包含着成学与成人两个面向,那么从以上两类被连带责罚的事例可以看出,皇子师傅的职责重在教授成人,而轻于教授成学,即所谓“随事规劝,俾明大义”,“凡事纳之于善,勿使稍有过愆”。因此,在皇子师傅的选择上,除学问优长之外,首重人品端方。③而在授读上,亦要求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为要,而不以寻章摘句、记诵文辞为贵。可以说,这是从康熙朝上书房制度逐渐形成以来,历代清帝的共同要求。④这样做的理由,自然是由于皇子未来以经略天下为务,不能培养成舞文弄墨的才人学士,故必以培养品德、明白治世之要为尚。正是这样的一种职业要求,使得师傅的职责不仅体现在书房的课堂之上,更深入到皇子日常的行为举止之中。由此,我们再反观庄存与的《尚书》解说,他特别强调的人子问题,即非天命不敢嗣、为人子当大孝、处人伦之变当法舜,就更容易理解。道光朝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就曾对其受学的过程有明白记述:
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闲以伦常大节,责备尤严。⑤
所谓“伦常大节”,在在显示出皇子师傅的着眼重点。皇子的日常行为稍有不轨,师傅则会连带受到责罚,作为内廷供奉,这一职位显然有其紧要却不得不慎重的一面。尤其是在雍正有惩于康熙晚年诸子争位的惨剧而确立秘密立储制度之后,由于并未公开宣布皇位继承者,使得诸皇子至少在表面上变得皆有成为下届人君的可能,因此,皇子师傅的这一职业就更加显得敏感。如嘉庆帝回忆师傅朱珪的授读即云:
其(朱珪)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即稍涉时趋之论,亦从不出诸口,启沃良多。⑥
嘉庆口中的朱珪,正是庄存与的同事。朱珪于乾隆十三年(1748)及第,入庶常馆学习,此时,庄存与正因为第一次散馆考列二等而被罚留馆继续学习三年,因此,二人有三年在庶常馆同学的经历。而庄存与初次入直上书房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朱珪初次入直是在四十一年(1777)⑦,可谓先后比肩。而所谓朱珪“其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这在上揭庄存与《尚书既见》《尚书说》之中,也莫不如此。“非法弗道”,“稍涉时趋之论,亦从不出诸口”,则让我们更能理解为何授读讲说,不论多么牵强附会,皆要借经典发言,而又多从唐虞三代立说的苦心。内廷禁地之中,皇家父子之间,恐怕稍涉时趋,耽误的不光是自己的身家性命,甚至还会搭上皇子的前程。历代典籍中对此类事件的记载比比皆是,对于饱读诗书的皇子师傅而言,怎么可能轻忽以应呢。
因此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皇子师傅同样是戴着脚镣的职业舞者。在这一职业的敏感地位及各种要求的前提下,皇子师傅在必须老成持重、谨言慎行的同时,还必须对未来的人君进行培养教育。有关怀抱负的师傅,必然会想到他肩头的责任,这显然不是培养一名普通童子,而是培养未来可能会对天下负责之人。在这样的处境中,他自然会将经典中一位人君需要明白的重要道理,以及他自己日常所体验到的政治感、现实感,皆加入到对皇子的授读中。当然,这种讲授,一定是借著经典的外衣。
回顾上揭庄存与有关家人父子间的伦理论说,可以发现,庄存与非常强调对亲长孝、对兄弟悌,以舜为例,作了长篇而迂曲的论说。在皇家内部,则尤其强调继位与天命的关系,防止皇子争权夺位,更提前预防由此而来的父子昆弟间的人伦惨剧。在康雍父子相离、手足相残的时代里,以及在乾隆痛责大阿哥、三阿哥不孝的情形下,庄存与此类的论说,显然是有着自己的政治识见和政治考量的,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龚自珍以庄存与的口吻说,“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①,才真正道出了此派学者的关怀所在。
四、结语
《尚书》一经,虽然同样偏重政治方面,但与《周礼》详于具体制度、《春秋》多讲王道礼秩相比,还是以其多存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而别具一格。所谓心法,除宋儒从理学角度所大肆发挥的“虞廷十六字”之外,实际更多是与帝王日常持身修己相关的基本守则,而所谓治法,则更突出帝王治世临民的行动原则。进入清代,由于部分学者在辨伪上的卓越表现,使得古文《尚书》的经典地位有所动摇,随之而来的存废问题,则更将心法、治法这一背后诉求推到了风浪前台。在不同立场的学者的争论之下,我们看到“去伪”与“存古”、“求道”与“求真”之间的巨大裂隙。而像庄存与这样参与时代事务更为深入的知识分子,则更加懂得现实与知识之间的紧张对应关系,他十分具体地为我们展现了不废古文的立场缘由,以及如何将《尚书》中所蕴含的“法”则落实在具体的政治现实和时代关怀之上。除了像一般学者一样,庄存与泛言尚书学在“修己”与“治人”方面的普遍价值之外,特别对其中所蕴含的家人父子伦理做了深入发掘,强调非天命不敢嗣位、人子当大孝、处人伦之变当法舜等具体内涵,以适应其作为皇朝的文化教育官员兼皇子师傅所期望发挥的一己职效。我们发现,他的这些阐发均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认为不过是他不能轻易出口的时趋之论的另一种表达。虽然并不是所有主张不废古文的学者皆能有庄存与这样的政治地位、皆能参与时代事务到如此核心的程度,但我们不可否认,在儒家经典的共同思想语境之下,在科举学优则仕的制度保证之下,知识人实际上对经典中所蕴藏的意涵有着大致相近的理解,而对经典的现实指向,也即能有大致共同的體察,此乃他们群趋不废古文的根本原由。这既向我们展示了清代《尚书》学的复杂面貌,又展现了不废古文学者在超越文本真伪之上的可贵关怀。龚自珍称庄存与不辩古文真伪,是“贬须臾之道”“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良有以也。即使时至今日,在求真与致用、学术与关怀、关怀与落实等问题上,可能同样并不时刻配合无间,依旧是我们在经学研究中继续思考与探索的课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庄存与《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校注(项目批准号:18FZS001)”“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① 如,刘起釪先生在《尚书学史》中即已做此类划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354—381页。
② 近年的相关研究参见:刘仁鹏《阎若璩与古文尚书辨伪:一个学术史的个案研究》,台北县: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吴通福《晚出〈古文尚书〉公案与清代学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张循《“读书当论道”还是“唯其真而已”?——清儒关于伪〈古文尚书〉废立的争论及困境》,《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马延炜《学术与世变之间——晚清古文〈尚书〉辨真的思想史意义》,《船山学刊》2008年第3期;刘德州《晚清〈古文尚书〉“辨真”学兴盛原因探微》,《船山学刊》2020年第2期。
③ 王懋竑:《白田草堂存稿》卷一《论尚书叙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9页。
① 朱彝尊著、林庆彰等校:《经义考新校》卷七十四《书三·古文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3页。
② 万斯同:《群书疑辨》卷一《古文尚书辨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
③ 颜元:《习斋记余》卷三《与桐乡钱生晓城》,《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1页。
④ 详见皮锡瑞著、杨世文等笺注:《论伪〈书〉相承不废,以其言多近理,然亦有大不近理者,学者不可不知》,《经学通论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40—241页。
⑤ 李绂:《穆堂初稿》卷十九《古文尚书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2册,第220页。
⑥ 张文虎《舒艺室杂著》甲编下《书古文尚书考辨后》说:“二十五篇之伪,在今日已坦然明白,立异为高者,乃拾《冤词》《广听》之唾余,欲翻成案,何哉?理学家以虞廷十六字为道统真传,一旦以为伪,则失其所凭依,一也;考证诸儒于伪古文毛举瘢索,身无完肤,欲举东晋以来相传为经文者,而拉杂摧烧之,其事惊世駴俗,其言亦失于过当,遂使不平者反唇相稽,二也;古文《泰誓》出于民间,盖非完帙,马氏已疑之,唐用伪古文作疏,此篇遂废,今采辑残賸,以伪易伪,文辞诡谲,众论不谐,三也;逸十六篇绝无师说,东汉儒者相传古文仅有三十四篇,其余残篇断简十不存二三,《尹告》《武成》郑注为亡,其果见与否皆不可考,而诸儒必谓马郑及见孔壁全文,四也;……伪古文经传萌芽皆在魏晋间,盖王肃忌郑氏名高,事事务为敌,伪古文经传、《孝经》、伪孔传、《孔丛子》,皆其所创。……乃诸儒攻古文者,非府辜于梅赜,即集矢于皇甫,使回护者反有所藉口,五也。”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0册,第321页。
⑦ 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⑧ 见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序》,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序”,第1页。
① 李调元:《童山文集》卷十二《古文尚书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4册,第574页。
② 李光地著、李玉昆点校:《榕村语录》卷十二《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64页。
③ 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古文尚书冤词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2册,第596页。
④ 谢章铤:《赌棋山庄集·文续集》卷二《与伯潜论竹坡(宝廷)〈古文尚书解纷〉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80册,第773页。
⑤ 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三《进呈尚书注疏考证后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0册,第203页。
⑥ 王植:《崇德堂稿》卷一《古文今文辨》,《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4册,第454页。
⑦ 齐召南:《宝纶堂文钞》卷四《尚书集解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00册,第229页。
⑧ 管世铭:《韫山堂文集》卷二《尚书今文古文说》,《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3册,第472页。
⑨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古文尚书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5册,第266页。
①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二《尚书今文释义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43册,第450页。
② 李绂:《穆堂初稿》卷四十五《书古文尚书冤词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32册,第596页。
③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一《古文尚书条辨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第19页。
④ 阮元:《揅经室集》卷四《引书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0页。
⑤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见王佩诤点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页。
⑥ 魏源:《定盦文集手批》,《魏源全集》第12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743页。
⑦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文末附记,见王佩诤点校《龚自珍全集》,第143页。
⑧ 庄绶甲《尚书既见跋》称:“先大父尝自言生平于《诗》《书》之学最明。”见庄绶甲《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1页。
⑨ 庄绶甲《尚书既见跋》称:“從父珍艺先生(庄述祖)从大父讲授,有《尚书驳议》《尚书授读》之著,亦考信于序,有《书序说义》之著。从父尝叹曰:‘《书》所著,盖文武之道,贤者识其大者,世父是也,余则不贤者识其小者而已。’一时学者因目大父与从父为大小夏侯焉。恪守家法,亦不为墨守,如今文、古文,则从阎氏、惠氏之说,大指则无不合揆云。从父于诸兄子中尤好为绶甲讲论,令为《尚书考异》,绶甲又私述所闻为《尚书集解》,以《诗》《书》通《春秋》之大义,冀承先业而未能也。”见庄绶甲《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2页。
① 刘桂生:《从庄存与生平看清初公羊学之起因》,见赵和平等编《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② 庄绶甲:《尚书既见跋》,《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1—402页。
③ 庄存与的大多数著作均未最终定稿,他致仕之后曾有整理自己著作的计划,但因两年后即过世而未能实现。参见鲁九皋《祭庄座主文》,《鲁山木先生文集》卷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78册,第197页。
④ 庄绶甲:《尚书既见跋》,《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1—402页。
⑤ 庄存与:《尚书既见》卷三,道光七年(1827)阳湖庄氏刻本。
⑥ 庄存与以长篇大论反复申论周公未践祚,以驳斥《礼记》周公践祚之说,参见庄存与《尚书既见》卷二。
⑦ 庄存与:《尚书既见》卷三。
① 庄存与:《尚书说·尧典》,道光七年(1827)阳湖庄氏刻本。
② 庄存与:《尚书既见》卷三。
③ 庄存与:《尚书既见》卷三。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九,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丙寅,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版,第23册,第405页。
② 永瑆:《诒晋斋集》卷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32册,第67页。
③ 庄怡孙等编:《毘陵庄氏增修族谱》卷二七上《盛事》,光绪元年(1875)刻本。弘旿,字仲升,号瑶华道人,康熙孙,胤秘第二子,乾隆八年(1743)生,嘉庆十六年(1811)卒。永珊,字远亭,号红玉主人(庄氏族谱作“红屿主人”),康熙曾孙,胤祉孙,弘景第三子,乾隆十一年(1746)生,嘉庆二年(1797)卒。
④ 庄绶甲:《味经斋遗书总跋》,《拾遗补艺斋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12册,第404页。
⑤ 郑仲烜:《清朝皇子教育》,台湾中央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66、217页。
⑥ 《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庚子,第15册,第23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四,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甲子,第25册,第925—926页。
⑧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四,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乙丑,第25册,第927页。
⑨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七,乾隆十三年(1748)六月甲戌,第13册,第208页。
⑩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乾隆十三年(1748)三月丙午,第13册,第89页。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〇〇,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甲戌,第21册,第376—377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八五八,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癸未,第19册,第490—491页。
③ 如乾隆上谕选派新任上书房师傅,即明确要求:“著总师傅等另选人品端方、学问优长之员,带领引见,候朕简派。”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二四,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乙丑,第25册,第928页。
④ 雍正帝谕曰:“皇子课读,事关重大,当教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之要,若徒寻章摘句、记诵文辞,一翰林能为之,非朕所望于卿等者。”见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29册,第203页;乾隆帝谕曰:“尚书房翰林入教皇子皇孙等读书,惟须立品端纯,藉资辅导,原不同应举求名者,仅在文艺词章之末。”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五,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己巳,第26册,第317页;嘉庆帝谕曰:“(皇子)总不得自署别号,竞尚虚文,惟当讲明正学,以涵养德性、通达事理为务,至词章之学,本属末节,况我朝家法相传,国语骑射,尤当勤加肄习。若竟以风雅自命,与文人学士争长,是舍其本而务其末,非蒙以养正之意也。”见《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嘉庆九年(1804)二月丁卯,第29册,第697页。
⑤ 奕譞:《窗课存稿》“自序”,《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⑥ 《清史列传》卷二八《朱珪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27页。
⑦ 《清高宗实录》卷一〇〇八,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月辛巳,第21册,第543页。
①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见王佩诤点校《龚自珍全集》,第142页。
作者简介:辛智慧,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经学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