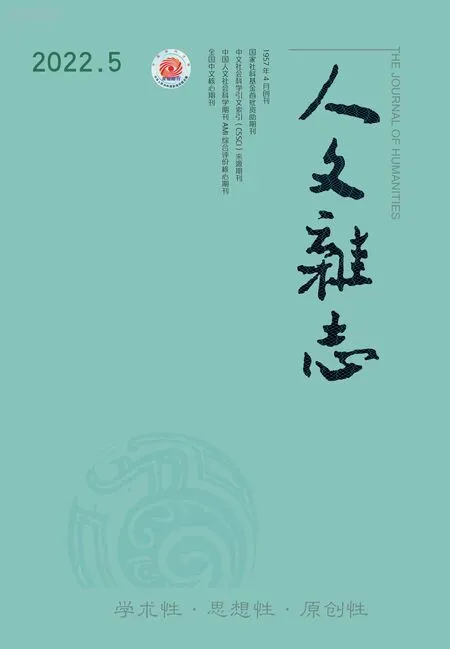古尔纳《天堂》的隐喻叙事与殖民创伤
朱振武 郑涛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2)06-0067-09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 ),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绝大多数普通读者竟然不知道古尔纳是何方神圣。其实,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古尔纳早已被列入重点研究作家之列,中国首个非洲文学研究国家重大项目就辟有专章探讨古尔纳的小说创作。古尔纳迄今共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鉴于他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对文化与大陆之间的鸿沟中难民命运的毫不妥协且富有同情心的洞察”,①而被授予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不错,古尔纳的获奖与他对流散特别是流亡群体的始终不移的深切关怀密不可分,但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流散文学取得突出成就的背景下,古尔纳何以脱颖而出?古尔纳所揭示的非洲流亡群体的身体伤害、心灵创伤和无法平复的殖民记忆,是其他流散作家难以企及的。研读了他的全部小说后,我们就不会再惊讶于其获得诺贝尔奖。古尔纳的《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对流散主题的探究,《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对难民身份的建构,《多蒂》(Dottie,1990)对帝国叙事的后殖民逆写,《天堂》(Paradise,1994)中的隐喻叙事与殖民创伤以及对东非贸易图景的描摹,《绝妙的静默》(Admiring Silence,1996)中对沉默的难民的有声叙述,《海边》(By the Sea,2001)对殖民主义阴影下的难民宿命的预判,《遗弃》(Desertion,2005)中對难民的文化无意识和殖民者的四重遗弃的揭示,《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2011)中对身份认同和共同体意识的彰显,《砾石之心》(Gravel Heart,2017)中对非洲移民的边缘化困境的思考,《今世来生》(After lives,2020)中对流散者的逃离和坚守的书写,都显示出作者古尔纳对殖民主义的深恶痛绝、对非洲难民的悲悯之心、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思考和对人类未来的乐观态度。在这十部小说中,《天堂》的地位稍显特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名字也更有深意。“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不如在地狱里称王”,①《失乐园》(ParadiseLost,1665)中的撒旦这么说道。从文化意象来看,天堂象征着无忧无虑,而地狱代表着无尽折磨,但二者绝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有了地狱作参照,天堂才让人神往。倘若天堂中的生活水深火热,奔赴地狱也许才是明智之举。这种迷惘无奈的流散状态,对殖民问题、对未来的美好希冀与憧憬的隐喻描摹在古尔纳的十部小说中都有体现,而在其最负盛名的小说《天堂》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英籍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是2021年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天堂》是其创作的第四部小说,曾入围1994年布克奖短名单。古尔纳得到高度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所描摹的非洲文学有别于其他任何地区的文学,非洲除埃塞俄比亚外曾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下,其创作整体来说都是流散文学,②这一点是有别于其他任何地区和国家的作家。而古尔纳几十年里始终聚焦非洲流散群体的命运走向、文化认同、殖民伤疤、创伤记忆和未来憧憬。《天堂》这部小说代表着作者对殖民问题和流散问题的阶段性思考。小说讲述了一战时期的东非,奴隶贩卖盛行,主人公优素福(Yusuf)因父亲欠债而被卖给了富商阿齐兹叔叔(Uncle Aziz),跟着他到了一片富庶之地,并遇到了另一个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小奴隶卡里尔(Khalil)。优素福不知道自己是被当作奴隶卖过来的,以为自己到了天堂。后来优素福受尽奴役剥削,又跟着阿齐兹的商队到处游行,一路上目睹了非洲大陆上存在的种种问题。最后他认清现实,萌生了加入“民兵”③的想法。小说以优素福在民兵部队身后追赶的情景结尾,引人深思。与古尔纳其他作品相比,《天堂》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待非洲的殖民问题。小说引经据典,运用了许多隐喻的手法:由动物隐喻揭开殖民化过程,再从名称隐喻探讨殖民对文化身份的冲击,最后通过主人公优素福对奴隶主家中“花园”的向往与幻灭探寻身份认同缺失的根源。古尔纳借隐喻之手,逐渐揭开了殖民者所构建的“天堂”面纱。
隐喻表达了两种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人们认知的本质往往都是隐喻性的。心理学家一般将隐喻分成根隐喻(radical metaphor)和新隐喻(novel metaphor)。其中,新隐喻指喻体和本体之间有明确差异,隐喻的使用者“知道A不等于B,但他只是想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传达一种用别的方法无法传达的信息”。④ 因此,隐喻能体现作者的情感,让作者以讲故事的形式将某些隐晦的信息传递给读者。在《天堂》中,古尔纳用了多种形式的隐喻叙事来讨论殖民问题,如“花园”隐喻、名称隐喻和动物隐喻等。其中,动物隐喻令人印象深刻。古尔纳通过小说中的“他者”讲述有关动物的故事,聚焦殖民化过程,把殖民者的暴力行为和殖民心理间接展现出来,体现了古尔纳强大的文字把控力和对殖民主义问题的深刻思考。
小说中出现的动物隐喻大都与“狗”相关。在伊斯兰文化中,狗或者说犬类,被认为是邪恶的、不洁的化身。在记录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中,关于犬类的记载也大多是负面的。阿齐兹家附近狗群泛滥,狗常常成群结队在附近徘徊,优素福和卡里尔都深受其扰。某天夜晚,狗群再次接近他们的住所,来势汹汹,就像是专为优素福而来。面对狂吠的恶犬,优素福被吓得手足无措,幸好卡里尔及时赶来,用阿拉伯语大声咒骂,驱赶了狗群。这一情景暗示了面对殖民压迫时,优素福和卡里尔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所带来的不同结果。被卖到阿齐兹手上后,优素福一直都是一个沉默的“反抗者”,他拒绝学习奴隶主的语言———阿拉伯语,以这种无言的方式来反抗殖民主义带来的身份枷锁;而卡里尔则恰恰相反,他乐意接受自己的奴隶身份,也学习奴隶主的语言,并劝说优素福学习阿拉伯语,始终以主动的“顺从者”形象出现。但在面对恶犬时,沉默的反抗是无用的,只有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才能获得生机。其中,古尔纳让卡里尔用阿拉伯语驱散狗群这一设计也融入了他自己对于反殖民方式的思考。
此前,优素福也曾梦到它们张牙舞爪地朝自己扑过来。值得注意的是,优素福在这段对梦中恶犬的描述中,用了“slavering”一词。“slavering”作形容词指动物龇牙咧嘴、口水直流的样子,但还可以用作名词,意为“奴隶贩子”。这个巧妙的双关语,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恶犬”的意象,也隐晦地将奴隶贩子与恶犬作类比,凸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狗群被驱散后,稍有收敛,就只在附近徘徊,再没有靠近。但狗群的低吼让优素福无法安睡。为了让优素福平静下来,卡里尔给优素福讲述了一个有关“野兽育人”的故事。
豺和狼把人类婴儿偷走,以犬乳哺育他们,喂他们吃反刍肉,把他们养成野兽的样子。豺狼还教他们说野兽的语言,让他们学习如何狩猎。人类孩子长大后,就让他们和豺狼结合,造出半人半狼的生物。①
其实,这种“兽化”的过程就是“殖民化”过程的缩影。“殖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剥夺被殖民者的姓名。“姓名不仅是称谓符号,更是一种身份标识”,②一旦被剥夺,会造成一种自我认知混乱。而奴隶主会趁此机会重塑奴隶的“奴化自我”。殖民者剥夺他们的姓名后便限制其人身自由,剥夺其人权,强迫其学习殖民者的语言,侵蚀其思想,最后达到将其完全奴化的目的。优素福自踏进阿齐兹家的那一刻起,就失去了拥有自己姓名的权力。阿齐兹始终保持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优素福的对话中几乎都以人称代词称呼优素福,而卡里尔常以“kifa urongo”(斯瓦希里语,意为死骗子)以及其他诅咒语来称呼优素福。此外,阿齐兹作为一名穆斯林贵族,又从事贸易,生活富裕,而优素福由于从小生活困苦,见到这个陌生的繁华世界后便心态失衡,其世界观和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面临这种冲击时,选择负隅顽抗还是缴械投降,是每个被殖民者或被奴役者需要作出的选择。
优素福听完“狼人”的故事后,问卡里尔是否见过“狼人”,而卡里尔表示自己见过,并告诉他,见到“狼人”的时候,跑是没有用的。“如果你跑,他们就会把你变成动物或是奴隶”。③ 作为主动的“顺从者”,卡里尔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副对奴隶身份完全认同的态度,他会学习和使用殖民者的语言——阿拉伯语,俨然是“黑人之躯里住着阿拉伯灵魂”的样子。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奴性外化的人,给优素福讲述了这样一个别有深意的故事。此外,这个故事中“狼人”似乎与民兵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恰好重合,为故事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小说结尾,德国殖民者征召非洲土著人组建了一支军队,以便管理非洲人,并称之为民兵。小说在这部分着重描写了民兵路过时,满地狼藉的景象。“就在苏菲树(sufi tree)树荫外,优素福发现了几堆排泄物,有几只狗已经在如饥似渴地啃食着……它们一眼就能认出谁是食屎者”。① 此处,古尔纳用“狗”来喻指那些被奴化的人,用地上的粪便来指代殖民者留下的遗产。一方面,殖民者用“以非制非”的方式,加深了非洲的殖民程度,这种殖民主义尤其体现在思想上对殖民主义认同,并接纳殖民文化,甘愿成为殖民者的附庸。另一方面,语言和文化是殖民的主阵地,对于个体身份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语言和文化上的吞并直接意味着自我意识的消亡。古尔纳在这里显然是将殖民者留在非洲的遗产——语言与文化视为糟粕,用讽刺的手法体现出他对于殖民主义的鲜明立场。
然而,身处地狱,糟粕也会被视作黄金。优素福在经历了被剥削压迫以及所爱被叔叔夺走后,心中的“天堂”随之破灭,心灰意冷之下才认清了现实。在这片满目疮痍的殖民大陆上,自己已然成了一个“边缘人”。远方的家回不去,阿齐兹的家融不进,自己一无所有,无家可归。就在这个时候,优素福碰到了前来抓获俘虏的德国殖民者,目睹了殖民者强行征召非洲人民加入民兵的场景。他和卡里尔躲在阿齐兹家里,等德国殖民者和民兵离开才敢走到外面。一出家门,优素福就发现了民兵留下的“排泄物”,旁边还有一群狗在虎视眈眈。优素福一靠近那堆排泄物,狗群就急于护食,因为“它们一眼就能认出谁是食屎者”。②这句话显然也是隐喻,暗示的应该是主人公的归宿。最后,优素福“快速环顾四周,目光透出一丝狡黠,随即朝民兵队伍的方向追赶”。③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并没有具体写出优素福最后是否成功加入了民兵。一直极力与殖民主义抗争的优素福,最后却动了加入殖民主义队伍的念头。这与《失乐园》中那句“与其在天堂里做奴隶,不如在地狱里称王”形成互文关系,为探索后殖民时期创伤提供了新思路。
古尔纳在复杂的语言文化环境中长大,母语为斯瓦希里语,但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不得不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于古尔纳而言,英语是殖民语言,这与屈辱和痛苦紧密相连,但后来在英国的生活又让他无法摆脱英语。古尔纳长期浸淫于英语语言和文化,用英语进行创作,这是无奈之举,也是最好选择,因为英语创作的影响力远大于非洲本土语,同时这也是其利用殖民语言来反抗殖民主义的最有效手段。也许如小说中的优素福一般,古尔纳认清了现实。面对话语权的不平等,古尔纳决定用殖民者的语言来阐述非洲被殖民的历史,借此让更多人,包括殖民者,看到殖民对一个民族造成的巨大伤害,也让人们思考语言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正如小说中印度商人加拉信葛(Kalasinga)所说,只有了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才能知道如何“对付”他们。④古尔纳用殖民语言对创伤进行书写,“借用个体叙述对抗宏大历史叙事宣扬的终极真相”,⑤“用不一样的讲述留存多元化的声音”,⑥或许为后殖民时代非洲人民疗愈殖民创伤提供了一种选择。在古尔纳的《最后的礼物》《绝妙的静默》和《砾石之心》等作品中,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这样的隐喻。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是全世界读者最费思量的一件事,最后谁成为幸运者往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而这正是诺奖的魅力所在。从诺奖120年的历史来看,获奖的118位作家总体上说能够服众,但有些作家获奖后才真正出名、才为一般读者甚至相关学者所知晓。可见,諾奖评委会是有他们自己的思考和标准的。值得深思的是,每年的诺奖的确代表了一定时期西方主流社会的价值判断和审美选择,也的确预示着文学文化的一定走向。我们对一种文化现象熟视无睹或不予关注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不能跟着诺奖的判断走,而应该对诺奖作家及相关现象做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和审视,同时还应该做田野调查,按照我们的判断和标准去挖掘世界各地的代表性作家。古尔纳之所以成为中国首个非洲文学重大项目的关注点,原因就在于此。
古尔纳的小说对流亡到欧洲的非洲难民的持续关注和书写正是中国学者关注的对象,而非洲难民的身份寻找和文化认同则是其作品的恒定主题。文化身份是殖民语境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在殖民统治之下,被殖民者不得不长期接受殖民文化的浸染,致使其对自己在本土文化或是殖民文化中的位置产生怀疑,并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重构。古尔纳对西方文学作品了然于心,对西方文化特别是宗教方面的有关典故如数家珍,其《朝圣者之路》《多蒂》和《砾石之心》等作品都运用了名称隐喻的写作手法,在互文、象征、戏仿等方面驾轻就熟。《天堂》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而在名称隐喻方面更是匠心独运。作品巧妙运用人物名字和称呼,体现出小说主人公优素福内心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文化人类学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中仅次于民族的一种重要文化身份”,①而作为一位穆斯林作家,古尔纳的创作自然也离不开宗教这一重要创作题材。
权力等级关系是宗教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一关系多见于对位居高位者的称呼上。任何一个宗教系统都无法避免等级化,而等级与权力之间又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宗教都会根据每位教徒的功德量或圣洁度,划分身份等级。在这个等级系统中,德高望重者居上。和社会阶级一样,级层越高,话语权越大。在小说中,被卖给阿齐兹为奴的优素福一直称对方为叔叔,而另一位小奴隶卡里尔却始终称阿齐兹为“赛义德”(Sayyid),同时要求优素福也去效仿。赛义德这个词最早指首领,后意为穆罕默德的后代,是对穆斯林贵族的尊称,但直到小说结束,优素福对阿齐兹的称呼都不是赛义德,常以“阿齐兹叔叔”(Uncle Aziz)、“那个商人”(the merchant)或人称代词“他”代替。这一行为表现出优素福对权力的反抗,而这种反抗是通过沉默来实现的,也正符合了优素福“沉默的反抗者”这一形象。
从另一個角度来看,作为一名信仰坚定的穆斯林,优素福应对伊斯兰的教义教规保持虔诚态度,一如卡里尔以及在商旅途中遇到的穆斯林商人们。阿齐兹是穆斯林贵族之一,处于宗教中受人尊敬的地位,每位虔诚信徒自然会对其使用尊称———赛义德。但优素福却极力抗拒这样的称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优素福对于文化身份的抗拒。实际上,这种对文化身份的抗拒是个体对殖民创伤作出的应激反应。在创伤理论中,弗洛伊德把创伤描述为“一种经验,这种经验使心灵在短时间内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办法谋求适应,从而让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紊乱”。② 创伤理论认为,受创主体会“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③ 在那段寄人篱下、任人奴役的生活里,优素福不仅身体受到创伤,心理上同样也伤痕累累。他离开父母和故土,本以为是跟着可靠的叔叔去旅行,却成了奴隶。后来,优素福好不容易遇到了心爱的女孩,却只能眼看着她成为叔叔的妻子,他心中对生活抱有的唯一希望也随之破灭。这一切给优素福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于是他选择抗拒自身宗教文化身份。伊斯兰教教义强调集体性,认为所有教徒真正的归属不是故乡,而是宗教集体。在这种教义的熏陶下,“自我的其它属性被消解,教徒的宗教信仰则成为其唯一的身份标识。”④ 通过抗拒原有宗教文化身份,优素福试图构建一个“他者”的身份,把自己与周遭世界隔绝开,从而构建自己真正的文化身份。古尔纳在作品中常常试图用带有民族或宗教色彩的典故来解决身份认同问题,⑤而其对宗教这一文化身份的探讨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也要归功于他作品中大量引用的典故,其中就包括被誉为“伊斯兰教圣经”的《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唯一的根本经典,《古兰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其中两个重要人物就是优素福与穆罕默德。在《天堂》中,古尔纳借用了这两个名字,并对其进行了反叛性改写。《古兰经》中的优素福被变卖他乡,临艳不惑,却遭到诬陷,身陷囹圄。这段经历与《天堂》中优素福的经历如出一辙,但二者却有着不同的结局。《古兰经》中的优素福最后寻得了自己的光明,《天堂》中的优素福则萌生了加入民兵的想法,前途未卜。如果说《古兰经》中优素福的结局是典型的宗教式结局,那《天堂》中优素福的结局无疑是反宗教式的,体现出古尔纳想要打破宗教文化身份施加给人的枷锁,借此重新定义自己在本土和异邦双重文化夹缝中的文化身份。小说中另一个改写形象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先知,真主安拉的使者,也是伊斯兰教创始者,倡导穆斯林团结一致,不分贫富贵贱,停止内部争斗。但在古尔纳笔下,穆罕默德这一伟大的形象却以一个乞丐的身份出现在优素福面前,是“身形干瘪,声音刺耳的人”。① 这一改写也体现出古尔纳名字隐喻构建的“破”和“立”。通过这两处“借名改写”,可以看到古尔纳对重构文化身份做出的探索,表明古尔纳试图从宗教文化身份着手,探讨殖民与被殖民、构建与被构建的问题。
从描写优素福对文化身份的抗拒,到改写《古兰经》中优素福的结局,再到让安拉使者穆罕默德以乞丐身份出现,我们可以看出古尔纳自身受到的殖民创伤以及其对文化身份构建的看法。仔细研读古尔纳的作品,可以发现他似乎对名字隐喻青睐有加,其大部分作品都运用隐喻的叙事手法,隐晦地将线索藏在人物名字或称呼中。如古尔纳的第三部作品《多蒂》中的主人公多蒂·布杜尔·法蒂玛·贝尔福(Dottie Badoura Fatma Balfour)就化用了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里中国公主的名字,用来隐喻殖民创伤和解的方式。而2020年出版的作品《今世来生》中的哈姆扎(Hamza)则借用了《古兰经》中穆罕默德叔叔的名字。每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融入自己的个人经历,因此要探究小说的写作意图,就有必要对作者的生活背景进行了解。
在非洲东海岸印度洋上,有一座小岛名叫桑给巴尔,在阿拉伯语里意为“黑人的海岸”,后来阿拉伯移民加入,带来了阿拉伯文化,并与土著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斯瓦希里文明。岛上98%的居民都是穆斯林,1948年出生于此的古尔纳也是其中一员。1964年,桑给巴尔发生暴乱,18岁的古尔纳选择离开这座小岛,在肯尼亚停留一段时间后,于1968年作为难民抵达英国,直到1984年才重回故土。定居英国期间,这位流散作家在肯特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长期受到英美文学的熏陶。古尔纳因故土的殖民和暴乱而流离失所,在英国又显得格格不入,这种流散状态和孤独感对他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连古尔纳自己也曾在访谈中表示:“在英国的第一年,我是一个陌生且无足轻重的存在”。② 同时,在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学院的学习经历也让古尔纳对于宗教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将这一认识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天堂》《朝圣者之路》,还是《砾石之心》,抑或是《今世来生》,其各自主人公有着不同寻常的来龙去脉,代表着非洲逃亡流散者的不同类型,都透过多种文化视角来探寻自我文化身份,而构建文化身份正是古尔纳在《天堂》中为读者指明的方向。古尔纳的隐喻手法,有别于其他英语作家的地方,就在于其创作是在吸收消化了欧洲传统文化的精粹后,又返回到非洲本土的物叙述。这种把世界经典与非洲土著有机耦合的能力使寻常作家难以望其项背。古尔纳小说的隐喻手法远不止名称隐喻,其在物叙述和物隐喻方面也有令人信服的表现。
古尔纳小说的故事情节经常围绕一个核心事物展开描摹,从而不易察觉地赋予作品以丰富的隐喻意义。这一点与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1931—)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个关于写作的访谈中,门罗提到:“我不写、也不会写人物的心理状态。……我要进入到人物、或生活里面去,不能不写围绕着它们的其它的东西。”①优秀的作家们正是通过这样的隐喻实现其创作主旨和价值认同的。价值认同一直是非洲作家热衷于探讨的问题,古尔纳也不例外。在《天堂》中,古尔纳用隐喻的方式来探讨直面创伤对自我价值认同的帮助。无独有偶,古尔纳在第二部作品《朝圣者之路》的结尾,也用了隐喻的手法,安排穆斯林达乌德(Daud)去参观基督教的坎特伯雷大教堂,试图从宗教的角度寻求自我价值认同。与直叙相比,隐喻更能给读者更为强烈的感受,引起人们对非洲殖民问题的思考和对非洲殖民史的重视。
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把写作比作“一块砖一块砖的垒砌……最终形成我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②身份认同困境在古尔纳自身经历中有着清晰的体现。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评语中说到:“古尔纳在处理‘难民经验’时,重点放在其身份认同上。他书里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与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生活和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③作为一名用英语写作的非洲作家,古尔纳在英美文学中一直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一直在努力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来探究自己的身份与价值。在非洲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将这样的状态定义为“异邦流散”,即指发生了地理位置的徙移后所面临的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④ 与古尔纳的其他作品不同,《天堂》这部小说从现实与幻想的反差来体现这种被文化孤立的异邦流散感,让我们对于这种“异邦流散”的身份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花园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场景,贯穿整部小说。小说以“天堂”为题,让读者产生一种先入之见,以为接下来将看到一幅“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景象,实则不然。在小说中,即将成为奴隶的优素福跟着阿齐兹到家,一眼就看到了阿齐兹家的花园。“他透过门廊,瞥见了那座花园,一眼就看到了果树、花丛以及粼粼波光”。⑤ “花”“泉水”“果树”都是《失乐园》中用以描述伊甸园的常用意象,象征着生命的美好。自此,这座花园在优素福心中构建出了一个天堂的样貌。在优素福暗无天日的世界里,花园成为其生活的一线希望,使其沉浸于其中。古尔纳多次使用“四面围墙”(walled)和“封闭”(enclosed)等词来形容这座花园,把花园描绘成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而花园里透出的“幽静”(silence)与“凉意”(coolness),让人更是心向往之。从优素福走进阿齐兹家开始,花园就一路见证了他的自我觉醒。离开旧生活后,优素福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阿齐兹家的花园,而在小说的结尾,优素福动身往民兵离去的方向追赶时,最后听到的关门声也是从花园里传来的。
因抵债被卖为奴后,优素福跟着阿齐兹离开故乡,抵达全新的世界。沿途优素福看到的是德军殖民下东非人民的苦难经历——为德国人修路,做计件工作,为来往旅客和商人提行李,工作量不达标就会被德军绞死,且德军施刑绝不心慈手软,完全不把奴隶当人对待,等等。跟着阿齐兹商队在非洲四处游走的过程中,优素福也目睹了这片大陆的衰败。疾病肆虐,迷信盛行,贸易腐败,奴隶买卖猖獗。这地狱般的环境更凸显了那座花园的圣洁,是宛若天堂一般的存在。优素福跟着商队回到阿齐兹家后,便常常溜进花园,在花园里幻想天堂的样子,而花园也成了他心灵上的避难所。但古尔纳并未使这个受伤的灵魂获得片刻的宁静。或许在他看来,逃避并不能让伤口愈合,直面问题才能找到自我,獲得身份认同感。在故事的结尾处,获准在花园里干活的优素福如往常一样走进花园,为女主人祷告,而这次女主人对他示好,被他拒绝,于是从背后抓破了他的衣服,到阿齐兹面前污蔑他。直到这一刻,优素福才意识到,“天堂”再美好,终究不属于自己。就像他的自由,也终究无法由他自己掌控。从小在殖民环境下长大的优素福,从未见过美好的事物,于是把那座花园看作天堂,寄予了自己全部的生活希望。但于他而言,这个天堂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就如同沙漠里的幻象,使其贪恋于美好之中无法认清现实。
小说运用了“花园”这个意象揭示了殖民统治下非洲的现实境况。“天堂”属于殖民统治阶级,而“地狱”的大门则为非洲人民敞开着。古尔纳把“天堂”描述得愈美好,非洲人民的生活就愈显得水深火热。在小说中,被卖为奴的优素福并没有像另一位奴隶卡里尔一样,始终守在奴隶主家里。一次突如其来的机会,让优素福得以跟着奴隶主阿齐兹的商队到非洲各地进行贸易。途中碰到了一个叫哈米德(Hamid)的商人,以养鸽子为爱好。这人会欣喜地跟优素福描述鸽子被关在笼子里的样子,并把它们称为“天堂之鸟”(the birds of paradise)。他还告诉优素福,这些鸽子都是“浑身洁白,拖着宽大的尾羽”,①所有看上去与众不同的鸟都会被处理掉。这些鸽子喻指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人民,而“洁白”则应该是指白皮肤的欧洲殖民者,暗指殖民者想要铲除异己,把非洲完全殖民化,并享受这一过程。这一系列隐喻形象地描述出了殖民者将非洲人民当作玩物的心理,从殖民者的角度来剖析非洲人民在这片大陆上受到的不公待遇,一定程度上也映射出压在非洲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民族中心主义和殖民优越感,侧面凸显了非洲人民所承受的深重苦难。这样的苦痛经历给非洲人带来了巨大创伤,这种创伤主要表现为自我价值认同感的模糊。笼罩在西方殖民主义阴霾下的非洲,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盛行多年。许多被殖民者不仅自己被卖为奴,且世代为奴。他们遭受非人待遇和精神摧残,几乎难以找回自我价值认同感。在“后殖民”时期,通过隐喻手法提醒人们记住苦难历史,记住人类历史上的悲惨一页,为历经苦难和努力摆脱苦难的人们发声,为寻找当下幸福和美好未来的人们提供镜鉴,这应该是古尔纳的小说创作带给我们的重要价值。
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英语文学之根都是英语文学,语言没有发生过变更,文化基本同源,认同无甚变化,连集体无意识都可以共享。印度虽然也曾被英国殖民,但毕竟时间相对较短,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始终没有断层。这几个地区流散作家的形态普遍呈现出单一单维的特点。非洲则迥异,其传统文化早已蜕变,语言早已经被取代,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或地区。所以,当在欧洲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对西方文化和非洲文化都熟稔于心的古尔纳站出来持续精心地书写非洲难民的时候,其意义和价值就立刻凸显出来了。殖民主义是非洲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主题,而古尔纳则抓住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这么多年来人们始终关注却并未深入腠理的难民问题,包括他们的过往、身体的摧残、心灵的伤痛、多舛的人生、无望的挣扎和对于未来始终不灭的美好希冀与憧憬。人类已经进入到后现代化和后工业时代,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已经如此惬意舒适的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在同一个世界的另一端和另一维呻吟、挣扎、哀求、乞愿和期盼,在这种情况下,《天堂》等专门描写上述素材和主题的作品就不乏高度与深度。古尔纳就是这样成功抓住了读者,并成功打开了当下读者的心扉。“现代非洲文学是在殖民主义的熔炉中造就而来的”。② 透过《天堂》这部作品,古尔纳用历史性的眼光,书写了一部非洲殖民史,同时又不局限于殖民历史,而是倾向于用历史隐喻现在,以史为鉴,思考未来。非洲是一片特殊的大陆,除了埃塞俄比亚,整个非洲都曾长期处于被殖民状态。这段历史为非洲带来多元文化,同时也蚕食了非洲本土文化,让非洲人民至今还处于失根状态,处于寻找自身立足点的状态。批判是为了审视。最了解非洲的应该还是非洲人自己,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古尔纳自然是最了解非洲的人之一。古尔纳“以公允的世界主义眼光言说和批判一切的不公”,①在《天堂》中以非洲土著人的眼光来探寻非洲现存问题的根源。借主人公优素福之眼,作品让我们看到,除了殖民带来的经济掠夺、人口骤减和文化蚕食之外,非洲大陆上的部落争斗、迷信盛行以及疾病肆虐也都是阻碍非洲发展的原因。其实不仅是非洲,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遭到殖民主义的迫害,至今仍存在历史遗留創伤。而正视历史、直面创伤,是让伤口愈合的唯一途径。
正如《失乐园》中的撒旦被贬地狱后所说:“一颗永远不会因地因时而改变的心……在它里面,能把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② 《天堂》虚构出了那个名曰“卡瓦”的小镇,且并未提及阿齐兹所处海滨城市的具体位置,因为所处地域不应成为个人身份的决定因素。为此,古尔纳显然是有意模糊地理坐标,构建了一个“去地域化”的非洲世界,以便用更为纯粹的眼光来探索自我身份。“非洲英语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起了各国文化界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③古尔纳获奖后,我国的相关研究立即呈现井喷之势,《文汇报》《文艺报》《生活周刊》《香港明报》《解放日报》等多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文章,从多个角度介绍古尔纳的获奖情况。我国首个非洲文学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首席专家在古尔纳获奖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就接受了十几家报刊的专访。中国文学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涌现出古尔纳研究文章30多篇,《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山东外语教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燕京大学学报》《外国语文》《外语教学》等多家杂志都设立专栏,从创作主题、艺术特色和接受影响等多个维度对古尔纳的小说创作进行阐释,这既说明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之大,也说明我们有时较多地跟风西方学界,还没能完全摆脱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局面。因此,我们仍需增强文化自信和批评自觉。古尔纳虽身在英国,其作品却始终聚焦故土,讲述非洲故事,反映非洲问题,但其写作用语又是英语。这种在“天堂”与“地狱”间的状态,正是这类流散作家的共性,一如南非作家库切和戈迪默,以及与古尔纳同为东非作家的恩古吉,还有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等一众非洲作家,都不约而同地用隐喻揭露殖民创伤,从深层揭橥非洲人民的身心磨难。作为异邦流散和异邦—本土流散作家的代表,古尔纳等非洲作家独特的隐喻叙事和创伤书写拓宽了非洲文学的宽度和深度,其包容性和丰富性也成为世界文学多样性的重要因素。我们关注古尔纳的文学创作,不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文学界的高度认可,而是因为他的创作关注了世界上被多数人忽略了的人群,是因为他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还不能摒弃战争、歧视和伤害,还不能放弃种族间、民族间的成见,还不能放弃站在“文明顶端”高傲地俯视的态度,还不能持有悲悯之心、宽容之心、谦卑之心和大爱情怀。古尔纳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地,取得了文学所企图达到的新的高度。
作者单位:朱振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郑涛,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张翼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