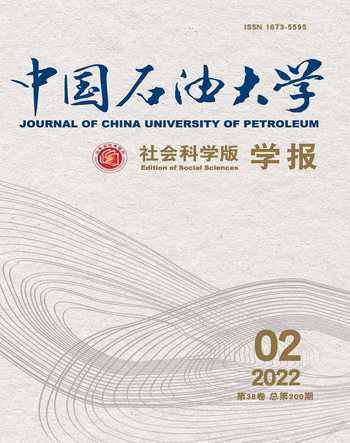从“载体”到“本体”:作为意识形态出场的网络技术
薛永龙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碰撞日益频繁,网络技术不再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出场,而是已然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本体”。当前,网络技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等各个方面,学界对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认识逐渐加深,从先前的“互峙论”“真空论”发展到“内嵌论”,即开始承认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与此同步,意识形态的话语呈现、意蕴阐释以及主流范式也发生了诸多转变,这使得二者在双向互动中彼此耦合的趋势愈发凸显。“技术赋能”时代,虽然网络技术革新给主流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我们的关注点不应一味地聚焦于技术批判,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考察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量技术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危局,从而探寻扭转局面的路径,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建构。
关键词:网络技术;意识形态;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D64;TP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22)03009907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作为一种发端于强烈时代需要的学术概念,意识形态凭借其内涵模糊且外延广阔的特点吸引无数思想家驻足凝望。当法国哲学家特拉西在“意识形态画册”中完成了首幅画作之后,意识形态经历了多学科、多维度的多样描绘,人们对其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也接二连三地发生转变,特别是作为科技的艺术品——网络技术诞生以来,网络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日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使得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变得日常化,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讨论。网络时代,意识形态看似被技术所遮蔽、稀释,这貌似同西方学者提出的网络意识形态“熄灭论”“真空论”“中立论”不谋而合,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意识形态观念迄今为止依然在场。不仅如此,随着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碰撞日益频繁,网络技术不再仅仅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出场,而是已然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本体”。
一、从分离到聚合: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学术论争的演变
网络技术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过渡,由意识形态“载体”向“本体”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讲堪比一场“革命”,即“属性的革命”。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相遇不是一蹴而就的,二者走过了从分离到聚合的漫漫长路,在此道路上,学界围绕二者之间关系的论争不断,大致经历了从“互峙论”“真空论”到“内嵌论”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互峙论”:技术本身同价值理性、主体意志根本无涉
网络技术在初登历史舞台时与意识形态少有联络,或者讲二者一开始就属对立的两端,此种论点是人们以往普遍的共识。之所以如此,与网络技术本身的工具理性有关。网络技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本质是运用软件与硬件的结合去建构一套系统,将世界上分散的人、信息、物品整合起来,实现数据流动下的分享、互动与服务。学者们曾根据几种不同的理论分析得出:无论从技术的理性归属出发,还是从反映现实的真理性判定,技术与意识形态都是水火不容的,技术本身同价值理性、主体意志都是互不关涉的。
首先,持“互峙论”观点的学者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根基,指出网络技术和意识形态分别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范畴。马克思强调,“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2],同时“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这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之源。网络技术作为科技发明的产物,它显然属于科学的一种形态,因此它必然也属于生产力的一种。不仅如此,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统一。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是主体反映客体时形成的观点和思想的集合,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所以网络技术和意识形态在唯物史观的范畴表现上迥然不同。
其次,持“互峙论”观点的学者又提出,即使依照理性的归属来判断,网络技术和意识形态也属于不同范畴。他们曾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来论证其认识的逻辑合理性,认为网络技术不涉及价值理性(大前提),而意识形态是总体性价值的体现(小前提),因此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互相对立的(结论)。也就是说,网络技术遵循工具理性,而意识形态遵循价值理性,二者在理性归属上全然分野。
再次,持“互峙论”观点的学者还从反映现实的真理性角度来佐证其观点。他们引入孔德关于人类智力进化的“三阶段论”指出,意识形态是人类在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的思想产物,此时主体对世界的反映是模糊的、虚假的,而人类要想达到反映现实的清晰的、真实的状态,就必须努力进入自然科学的实证阶段。阿尔都塞后来也提出过相似的论断,他认为科学是现实的真正表征,“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話、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4],同时还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全部批判都意味着它同科学的势不两立。概而言之,持“互峙论”观点的学者从根本上认为技术与意识形态处于不同的起跑线上,二者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也是截然相反的,因此它们本质上是相互对峙的。由于这一观点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所以其在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二)“真空论”:技术的工具属性阻挡了意识形态的投射
随着网络技术在现实中的广泛应用以及学者们对其内在属性探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开始形成另一种认识,即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其实也并非始终是对立的,二者在实践中有时还会出现齐头并进的情形。譬如,作为一种网络技术,算法技术虽然一直充当现代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但当其与意识形态相遇时,不仅其自身的工具理性特点和功能指向被遮蔽,而且会带来意识形态对网络技术的赋权,使得技术“体现出人的意志,彰显出鲜明的价值负载性”[5]。基于此,由于惧怕人们过多谈论技术的价值属性,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网络“价值真空”的观点,指出网络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技术的原生性从根本上阻挡了外界意识形态的投射。
首先,持“真空论”观点的学者认为,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在空间距离上相隔天壤,二者之间不存在流动性,彼此也不可能产生任何互动。具体来讲,学者们认为网络技术创设的是一个虚拟的“非现实空间”,而意识形态生存的地方是现实的物理空间,即主权意义上的实体空间。从这一角度看,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虽然不是对立的,但也绝不可能走向一致。
其次,持“真空论”观点的学者通过观察分析技术的原生特性还提出,网络开辟了一个平等、公开的世界,这一世界摆脱了现实中的各种压迫和歧视,它使不同制度、主义之间的斗争停歇,使激烈抗争的远景逝去,使国家之间、政党之间关于意识形态的喧嚣得以平息。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说,网络没有任何物理界限,它“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6]。质言之,网络空间中不再有阶级之间的对立,在这里不会出现意识形态的踪影。
再次,持“真空论”观点的学者为深化其认识的科学性继续渲染说,网络技术在结构上是“去中心”的,它内部中的无数“节点”没有一个属于“中点”,因此它还是去权威、去意义的。这些学者还指出网络空间是密不透风的“真空地带”,任何主体的意志都无法投射进来。总而言之,“真空论”最明显的理论范式就是否定,即否定网络空间中阶级的存在、意识形态的存在、人的价值的存在。倘若仔细探究则会发现,“真空论”观点中隐藏着特定阶级的政治企图,其千方百计地渲染和深化网络中不存在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降低对手的防御,一面确保自己在技术上永远占据霸权地位,一面又可以在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上夺得先机。
(三)“内嵌论”:技术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在分析网络技术产生和应用的历程时,有学者提出网络技术本身“内嵌着某种价值”,它是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当网络技术被国家权力行为体使用时,当网络技术沦为某种阶级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时,它的“中性”特质就不那么纯粹了,或者说它开始具有了“非中性”作用。这种“非中性”打通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阻隔,从而使网络技术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行为体提升自身综合实力的重要工具,也可以“作为其对外行为的重要手段,对他国进行政治渗透,最终实现政治重塑的战略意图”[7]。
首先,“内嵌论”者从总体上揭露了“互峙论”和“真空论”的片面性和虚伪性。其指出“互峙论”虽然自称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为依据,但它既没有看到生产力理论的与时俱进,也没有注意到意识形态的全貌;而“真空论”则隐藏着政治企图,它大肆鼓吹网络空间中不存在意识形态,其实这种论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要言之,“内嵌论”者认为网络中存在意识形态,且这种意识形态是人为可以干预的,如克里斯托弗·梅所言:
“很多阐释都认定某些技术‘内嵌特殊规则’。就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互联网内嵌着像自由、共同体、平等、利他主义和民主等价值。”[8]
其次,“内嵌论”者从根本上是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技术异化”批判理论的影响和启发。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发现,不仅雇佣工人已经沦为机器的一部分,而且科技变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形式,科技表面看是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实则却是奴役人、控制人的工具。哈贝马斯曾指出:
“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9]
再次,“内嵌论”者找到了网络技术具备意识形态性的历史缘起。通过梳理技术的产生过程他们发现,网络技术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它的设计发明就是为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它根本无法拒绝人类价值的“投射”和人类思想的“内嵌”。另外,网络的“对等通信”“编码解码”等技术中暗藏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念以及掌握核心技术的权力体对霸权的向往和布局。由此可以看出,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不是对立的而是联系的,不是分离的而是聚合的,这种理论上的“聚合”推动着实践上的“耦合”。
二、从互动到耦合:网络技术场域中意识形态出场方式的转变
汤普森曾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10]这一理论开辟了意识形态研究的新命题,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意识形态分析的论域。微观而言,随着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互动的增多,双方之间的确表现出某种“能量”上的流动,当然这也可能是学者们将其视为研究热点后人们不经意间产生的幻觉或者立场先行的倾向。但是,无论是由于外界的干扰还是主体自身意志的左右,有一点是可以引起学者们共鸣的,那就是在网络技术场域中意识形态思想的出场方式发生了转向,其话语呈现由官方化转变为大众化、意蕴阐释由封闭性转变为开阔性、主流范式由控制论转变为生存论。
(一)意识形态的话语呈现由官方化转变为大众化
意识形态工作说到底是去做人的工作,也就是想方设法让每个个体的不同“意识”转化成特定阶级所期望的一致的“形态”。那么,若想达成一致性愿景,政党就必须设法将自身的意识形态映入人们的眼帘、传入人们的耳中、赢得人们的肯定。巧合的是,网络技术的进步让意识形态认同工作不再那么困難,它依靠自己独有的虚拟自由空间,使意识形态的话语呈现由官方转向民间,进而关于意识形态的社会讨论也变得活跃起来,可以说意识形态已变成了“关键词”意义的存在。但需要明晓的是,技术发展引发的话语转向也并非全部都是积极的,在实力非对称的现实中显然机遇和挑战并存。
首先,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除了使技术具有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属性之外,意识形态的话语呈现也发生了转变。毫无疑问,以往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达通常被认为是政治集团和专家学者的专属,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权威性,但网络技术却使得这种局面得以改变。如今在网络空间中涉及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愈发日常化、普遍化、大众化,普通大众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针对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及话题,每个人都能够借助技术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突破了传统的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格局。
其次,虽然网络技术推动了意识形态话语出场的转向,但当我们反观这种出场的结果时,不难看到与“单向度的人”类似的意识形态现象,处于技术附属地位的国家,它面临的更多的将是挑战。在网络空间中,“表面上众声喧哗、随心所欲,背地里却暗藏着一只只无形的手,那就是占据话语优势地位的意见领袖能够形成有利于自己观点传播的‘沉默的螺旋’,诱导网络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11]。具体而言,一旦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发动网络战争,一旦他们利用技术优势对别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其他国家要么缴械投降,将自己的网络主权拱手让人,从此在网络领域偃旗息鼓,要么就只能顽强抵抗,一直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而若想绝地反击,则必须全力冲破技术霸权的牢笼。
(二)意识形态的意蕴阐释由封闭性转变为开阔性
在网络技术的作用下,意识形态的意蕴阐释由封闭性向开阔性转变,人们不再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内涵和外延的框架。与此同时,网络技术的附属品也被赋予了精神属性,网络技术自身在意义上有了叠加,在功能上进行了价值重塑。
首先,意识形态的意蕴阐释由封闭性转变为开阔性,最明显的表现是研究意识形态的领域不断扩展,同时许多意识形态新论题也不断涌现
。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定义意识形态,可自从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識形态”指认为“虚假意识”,并且将一般意识形态描述成观念上层建筑以后,许多学者将此认定为意识形态的概念。沿着这种理路,学者们解读意识形态的方式比较单一化,对意识形态的外延没有实质性拓展。可随着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互动的加强,上述景象有了巨大改观。譬如,在新媒体、文艺和影视等领域关于意识形态的话题源源不断,人们价值评判的标准也大相径庭,这让意识形态的意蕴变得丰富起来。
其次,意识形态还不断搜索有利于自身的网络因素,并对其进行意义叠加,如网络语言被转化成意识形态语言,网络文化被解释为意识形态文化。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意义叠加方式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就网络文化来讲,意识形态在选择时已经注意到它的文化属性在网络中的流动以及它对个体感化的力量,毫不夸张地讲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心理、情绪乃至信仰。
(三)意识形态的主流范式由控制论转变为生存论
在控制论范式处于主流地位的时期,意识形态本身的特征、功能被发掘,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性质差异被揭示,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完善意识形态工作体系奠定了基础。然而,一味地采取强制手段去实行控制,即使暂时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或者满足了某种意识形态队伍壮大的要求,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认同是不可靠的,其所组建的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在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互动中,意识形态的主流范式开始转型,逐渐由控制论转变为生存论,简言之,就是把重心转移到人的生存、国家的处境等问题上。
首先,转向生存论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更加关注主体,旨在寻求一种科技和人文并重的意识形态。网络技术在参与塑造社会的方方面面时,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也进行了重塑,但这种重塑只能是相对较弱的,它不能完全取代人的意志,不然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就会威胁到人的生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割裂科学和人的观点时所说:“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2]撇开控制论不谈,个体在网络中遭受错误思潮的诱导,经受极端舆论的煽动,这些逐渐变成人们经常关注的事情,在技术管理者耳边要求维护人的权利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止。一句话,人只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网络技术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以人为出发点,而不是其他。
其次,意识形态的主流范式中,关于民族国家的生存话题也开始独占一席。习近平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13]当前,面对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冲击,除了不断分析网络意识形态的新影响之外,最重要的是站在国家安危的角度去思考化解之策,这其中就包含着人们对自身生存处境的判断。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转型以及人们对国家生存的关注,实际上体现了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正是国家为人的社会存在提供了可能以及需要的场所,人们只有生活在这个集体中并且关注集体的生存状况,其价值追求和价值创造的活动才能顺利完成。
三、从冲击到融合:作为意识形态“本体”的网络技术开始出场
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的耦合带来了双重冲击。从理论上讲,二者的殊途同归与学界传统的共识存在差异,这让人们不得不对某些基础理论作出新的阐释;从实践上讲,网络技术“非中性”的面纱已经掀开,其“政治偏向性”一目了然。此时,面对技术占有和实力对比上的巨大差距,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更加困难,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但越是冲击不断,我们越能真实地感受到二者的融合,越能清晰地看到网络技术本体意识形态性的时代凸显。
(一)空间管控和功能提升成为国际社会一致关注的课题
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性,首先体现在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的空间管控和功能提升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课题。
当今时代,人类在享受网络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时,也面临着网络空间中错误舆论诱导、主体隐私受到侵犯等诸多挑战。作为共同体存在的网络,其意识形态的空间管控日益成为全球各方一致关注的重点课题。一方面,对网络的空间管控成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早前就制定出统筹性的网络国家战略,旨在首先通过网络技术实现资本增殖的目标,而后利用网络与政治的勾连,谋求霸权统治。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中曾指出:“并不是说媒体就是政治……然而,政治计划和政治人物一旦进入媒体空间,就会按照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塑造了。”[14]可见,对网络的空间管控是资本主义维护阶级统治、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即使像美国这样的技术强国也没有放弃对网络的管控。他们虽大肆鼓吹网络自由,但在践行“网络自由”理念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一边让自己的意识形态自由地在全球流动,一边又阻拦外界的思想文化流向自己的领地。
再者而言,网络空间已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这片高地一方若不占领另一方就会占领,因此在实行空间管控的同时,国际社会还极为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升。与经济和军事不同,网络技术是一种“软实力”,既不具有暴力性,也没有明显的强制性,但它却能够潜移默化地对人施加深远影响,它使得经济落后的国家也拥有“演奏第一小提琴”[15]的机会。正是基于此,当今世界无论哪个国家都特别倚重网络的控制权,通过网络扩大自身意识形态的覆盖面,宣传本国的价值理念,从而实现外界对自己思想文化、公共政策的认同。此外,网络意识形态功能的提升旨在掌握话语权,为了达成这一愿景,国际社会还精准谋划、科学行动,根据话语对象的差异分析其需求,用精准的话语形式和内容贴近对象、感染对象、凝聚对象,从而不断提升自身意识形态话语在国际网络空间中的影响力。在此语境下,网络技术与国家意识形态已经融为一体,网络技术开始具有了意识形态所特有的属性。
(二)核心技术成为主权行为体互相角逐的重要法宝
核心技术乃国之重器,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掌控了斗争的方向和节奏。从历史上看,网络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的,发展中国家所应用的技术,一些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的,一些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购买引进的,因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受制于人已成常态。麦克卢汉曾提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16]。他认为,媒介是人的器官的延伸,媒介的威力大大超越了其所传播的讯息。无疑,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對网络核心技术的把控,这种技术优势也已经延伸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中。可以说,掌握了核心技术就掌握了技术政策的制定权,就拥有了设置国际议程的主动权,就占据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
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在核心技术运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是否掌握核心技术决定着有无制定对外技术政策的权力。“技术具有二重性,技术进步既可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也可以巩固国家安全地位。因此,对外技术政策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17]在制定对外技术政策时,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具有绝对的特权,而没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只能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出于竞争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家更愿意同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相对宽松的技术出口政策,而对于和自己实力相当的国家,核心技术掌控国在技术政策上则表现出既渴望争取其成为合作伙伴,又在合作时保持警惕的态度。
其次,一旦掌握核心技术就拥有了在国际上设置议程的主动权。网络议程设置是技术的一种能力,即网络通过重复性的信息推送、舆论造势来提升某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性,让公众以此作为真理事实和行动指南。
由此可见,掌握网络核心技术也许不能完全左右国际社会对某一具体事件的判断和看法,但“通过选择性信息的传递、议题的设置可以有效地影响和改变国际舆论的走向与评价”[18]。
再次,掌握核心技术也就意味着占据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制高点。网络技术权力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种技术一旦被某个国家掌握,其他国家不但很难在短时间内赶超,就连去插足和模仿的可能性也非常小。从根本上来说,网络技术又是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中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它是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和武器,特别是核心技术,唯有真正掌握方能彻底摆脱霸权国家的控制和封锁。习近平曾强调,我们最大的隐患是网络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个互联网企业即便规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严重依赖外国,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19]。在这种意义上,网络核心技术已经成为主权行为体相互角逐的重要武器,变成了一种政治和权力的工具,具备了意识形态性。
(三)技术逻辑参与并且影响着政治认同大厦的建构
芬伯格在《技术批判理论》中提出:“当社会是围绕着技术来组织时,技术力量就是社会中权力的主要形式。”[20]在他看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技术座驾”中的世界,技术逻辑参与了世界的构造,塑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不仅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逐渐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当今时代,网络技术越来越接近芬伯格关于“实体技术”的阐释,其在与政治权力结合时,已不仅仅是手段和工具,也不只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存在,而是表现为技术本体与意识形态的融合。简言之,技术逻辑参与并且影响着政治认同大厦的构筑,网络技术具备了意识形态性。
网络技术服务于政治认同大厦的构筑,主要源于其在现实社会中政治控制和思想灌输功能的发挥。
首先,网络技术全过程参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用网络技术参与政治意识形态传播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利用技术来左右和控制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容,通过对信息的选择性报道来影响大众的认知和判断;二是利用技术来规范和约束意识形态语言,弱化非资产阶级语言的传播,增加资产阶级语言的出场率,以指示性语言来表达和实现本阶级的意志;三是利用技术来操纵意识形态传播的过程,由于资产阶级有能力对个人、政府机构实行监听和监视,因此其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实际上是透明化的模式运作过程,他们可以在评估意识形态的效度后进行传播的校准。
其次,网络技术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了诸多便利。一是网络技术延伸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范围,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突破了时空界限,真正实现了“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21];二是网络技术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它通过整合文字、声音、图像及视频,让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更加多姿多彩、深入人心;三是网络技术丰富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资源,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模式提供了多种选择,创造出多种可能。
再次,“网络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正在形成。“网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霸权逻辑与网络技术逻辑相结合的产物,依托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资本主义转变推行霸权统治的方式,呈现出从政治控制到媒介控制的趋势,这种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形式,旨在更好地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随着网络技术在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网络意识形态策略实际上已经沦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战略。正如席勒所指出的:“美国的国际传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向人们提供他们迫切需要而又不容易获得的东西。”[22]
最后,在网络时代,反映阶级意志和利益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是寂寞的独白,而是着重运用新型技术手段将自身映入受众的眼帘、传入受众的耳中、输入受众的心坎。基于技术逻辑对意识形态认同大厦的构筑,网络技术与意识形态实现了异向同致并且合而为一,网络技术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属性。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2]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3.
[3]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4]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1.
[5] 武豹.算法推荐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98104.
[6]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7.
[7] 郑志龙,余丽.互联网在国际政治中的“非中性”作用[J].政治学研究,2012(4):6170.
[8]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3.
[9] 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940.
[10]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高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86.
[11] 侯惠勤.深化对于互聯网信息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理论认识——写在《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一书出版之际[J].思想教育研究,2019(3):137141.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8.
[13] 习近平.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M]//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06.
[14]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第2版.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370.
[15]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9.
[16]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17] 黄琪轩.大国战略竞争与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变迁[J].外交评论,2020(3):94102.
[18] 王玉鹏.媒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批判[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5):128135.
[19]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
[20]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18.
[2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9.
[22]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刘晓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101.
From "Carrier" to "Ontology" : Network Technology Emerging as Ideology
XUE Yonglong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collision between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network technology no longer appears as the "carrier" of ideology, but has already become the "noumenon" of ideology. At present, network technolog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 of production, life, communication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gradually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technology and ideology, starting from the "mutual recognition theory" and "vacuum theory" to the current "embedded theory" which embraces that technology possesses the attribute of ideology. Concurrently,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ideological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meaning interpretation and mainstream paradigm, displaying a noticeable trend of a coupled twoway interaction. In the era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the network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ave brought about the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work. However, our focus should not be fully directed to criticism of technology, but rather shift to the more significant facet——its ideological attributes and the techincurred ideological crisis to find a way to reverse the situation and change from passive communication to proactiv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twork technology; ideolog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