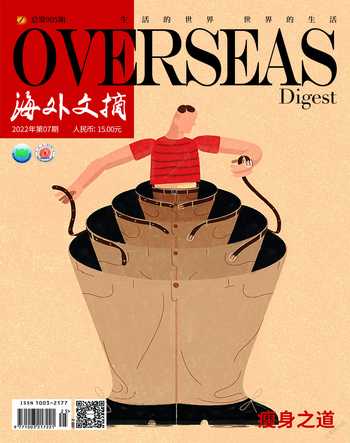末日准备狂:“囤积即正义”
加布里埃拉·凯勒

满满当当的储物架:新冠疫情让多少人成为了末日准备狂?
奥利弗·霍农知道,安全始于稳固的投资策略:一点金银,少量现金,分散持股。霍农住在柏林东部郊区马察恩地区的一个板房建筑区,留着棕色短发,比他的实际年龄37岁要显得年轻许多。
他说,很多末日准备狂看不到个人的日常危机,比如失业或者失去工作能力。“举个例子:我得了椎间盘突出,请了几个月病假,我的老板因此解雇了我。”他说,“这里就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前预防。”
對于这样的风险,霍农的答案是,尽量多存钱,至少要够生活六个月,其中一半是现金,放在家里。他还储存贵金属,将一部分钱投资了有价证券。他以这样的方式为所有状况留足了退路。
“末日准备狂”一词描述的是那些为末日(或者说“粪便撞上风扇那天”)作好准备的人。媒体喜欢将末日准备狂塑造成偏执的暗堡怪胎。他们有的在野外安营扎寨,有的在地下埋藏食物,还有的为天下大乱之日预作准备。自从梅前州“北部十字”之类的右翼群体被曝光后,末日准备狂也进入了负责国家安全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视线。在公众心中,末日准备狂的形象是好战的末日士兵和囤积武器的新纳粹分子。
而这使得准确描述末日准备狂这个群体变得困难,无法既符合事实,又概括其多样性。但如果说到这个概念,你能想到的只有穿着迷彩服、拥有武器库的边缘异类,那就完全错了:末日准备活动早已深入社会大众,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更是如此。
这些末日准备狂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各异,很多都有高学历和超出平均水平的收入。在这个群体最早出现的美国,知名趋势预测者杰拉尔德·塞伦特早在2010年冬就曾写道:“每种新的威胁出现时,都会产生一个聚焦于生存策略的新群体。这样,生存主义原本的‘准军事部队’的刻板印象不断被打破,如今已被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忧虑公民接受……生存主义成为主流。”
在美国,生存主义造就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工业领域。在德国,新冠危机也使得个人采取危机预防措施成为一种大众现象:疫情暴发之初,几乎所有德国家庭都至少配备了一个小储藏间来放置食品和卫生用品。
“一旦开始隔离,就无法再出门”的设想也使得原本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们开始认真囤积物品。他们的冰箱中本来可能除了芥末、黄油、一瓶半空的杜松子酒和一袋马苏里拉奶酪之外空无一物。罐头面包卖家在2020年春封城之初就宣布他们的订单数正快速增长,速食产品和急救装备供不应求,社交媒体中末日准备狂小组的成员数量也呈爆炸式增长。

汉堡街头的顾客:比起武器,囤积卫生纸更重要。
霍农在柏林东部出生和长大,已经成为末日准备狂十年。他总是一个人行动,并不想加入社交媒体中的末日准备狂小组。他说:“因为这些人不只大多右倾,而且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的纳粹。我根本不想和这些人扯上关系。”他靠在自家小房子的沙发上,周围是白色的宜家架子。霍农经营着一家网店,售卖不用塑料包装的天然海绵。在他的博客“城市末日准备狂”上,他为“大城市危机预防”主题写了一些小建议。
新冠疫情暴发后,他看到人们在超市囤积疯抢,就知道他趁早进行储备是对的。“我对人们的反应感到吃惊,因为我原以为根本还没到那一步。”尤其让他惊讶的,是那些为超市货架上的面条大吵大闹甚至拳脚相向的人。“我觉得这十分荒谬可笑,这些人没有头脑的状态让人觉得有点恐怖。”他说,“我看到的是:你其实必须储藏好所有东西,因为在紧急关头,这些疯狂的人会买空一切,还很可能为此大打出手,造成人命。”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末日准备狂的行为似乎有了新的意义。2020年3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为最糟糕的状况作好了准备。现在,人人都是末日准备狂》。英国《卫报》有篇文章的标题是《我们曾嘲笑末日准备狂和生存主义者,直到疫情给了我们沉重一击》。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医院的照片就像末日题材电影里的情节:不堪重负的重症监护病房,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半裸病人,人满为患的医院走廊和病房,穿着防护服的医生,在写字台边虚脱的护士……突然之间,一切都成了现实。
很多人的安全感摇摇欲坠。由于害怕病毒,人们的公共生活已经广泛受限。而且,在封城的最初阶段,人们还不清楚这次危机会对供应状况造成多大的影响:在媒体发出的照片上,茫然的顾客站在空空的超市货架前,绝望的母亲在寻找奶粉,卡车在边境排起数公里的长队。供货困难,人们开始囤积抢购,酵母和厕纸等日常商品数周都没法买到。
战后出生的一代人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之前遇到的问题只有如何在几十种厕纸品类中作出选择。突然之间,对短缺和临时困境的忧虑如此真实,人们突然意识到,在德国,商品流通也可能突然中断,出现暂时的短缺。而末日准备狂们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德国联邦民防和灾难援助办公室出的《无电烹饪:应对日常、野营和紧急情况的50款应急食谱》一书
霍农的储备足够他和女友、孩子生活六个月。在《末日准备一年计划》一书里,他描述了如何在一年间建立起长期储备,需要时刻准备好的急救包中需要放些什么,如何培养能在危机中大展身手的能力,比如烤面包、制作干果、进行急救。“对很多人来说,失业、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会造成恐慌。”他写道,“但是,如果你为家人储备好了足够的东西,知道你可以在紧急状况中存活下来,你就不必担心了。”
很多末日准备狂一直都在改善自己应对危机的能力,对于霍农来说,主要是不断学习金融知识。他自学了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做好预防措施,看了关于小投资者投资策略的视频,听了一些播客,读了相关的书。“这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根本不教的一部分内容,我们的金融教育完全缺失。”他说,“但是,如果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办呢?”对他来说,需要重点应对的不是社会治安体系的崩塌,而是短期混亂或供应短缺。
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考虑大型灾难,比如陨石撞击、火山大爆发或是长期停电,但他表示,最可能发生的是经济危机。“我想,我们正处于一次经济危机的开端,接下来一两年很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极富挑战。”霍农说。
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末日准备狂。
不管是哪种危机来临,霍农都知道该做些什么。那时,他不会待在现在的房子里。他还有另一所房子,目前是他的办公室,他只需步行20分钟就可到达。在那里,他会和女友、孩子和狗狗一起,堵塞好门窗,尽可能不让任何人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他不太担心有人抢劫。“这座房子的好处就在于非常安全,装有无法轻易打开的安全门。”他说。
他是怎么成为末日准备狂的呢?霍农说,他小时候常在森林里漫步,在澳大利亚做背包客时经历过两次海啸。但所有这些并不能真正解释“危机预防”这个主题为何对他来说如此重要。他思考片刻后说:“我这样做,是出于自然而然的人类理性。这听起来可能显得有些自大,但末日准备狂们可能确实比只顾自己和眼前的普通人想得更远那么一点点。”霍农认为,很多人放弃了对自己生命的责任,在遭遇挫折时将过失推给别人,期望别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积极主动、考虑周到的末日准备狂,则和这些无病呻吟、不能独立自主之人恰恰相反。而且,建个小储存库根本不像看上去那么费钱。刚开始,他需要耗费一些精力去搜集需要储藏的用品,但现在他已无需做很多,只用定期更新库存、填满架子。所以,没有时间并非理由。“大部分人都在看电视、刷手机、逛社交平台等事情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他说。
霍农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贫穷,低于中产水平,还有负债。刚开始,他也是得过且过,但孩子的出生让他有了雄心。如今,他的网店十分成功,天然海绵的生意做得很好,新冠疫情甚至让他产品的销量上涨了。但是,他还有很多计划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是,将自己的网店扩展为一个无塑料的卫生用品店。
霍农的预防准备措施已经十分到位,尽管如此,他仍想继续完善。他想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长期目标是在城郊买一块地。霍农说,他性格内向,在人群中感觉不自在,希望能自己种植果蔬,过更加自然的生活,比如在森林里、湖边建一座小房子,获得真正的安宁。
2020年2月购买了意大利饺子罐头、面条和肉脯的很多人,几周之后又撤掉了这些储备。但是,危机已经让很多人对供应链的信任感支离破碎,而以前被嘲笑和轻视的末日准备狂们则感觉自己的观念得到了证实。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末日准备狂,或者说至少在危机初期,我们会有这种印象:为艰难时期作好准备是聪明人的做法。
[编译自德国《明镜周刊》]
编辑:周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