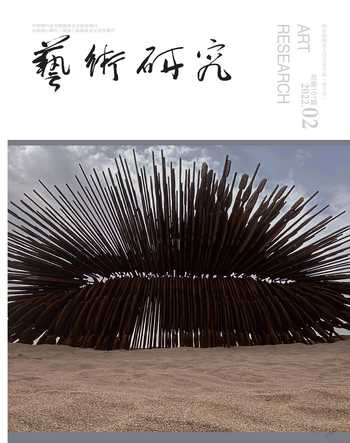文化遗产视阈下藏羌原生民歌口述史的研究思考
邓思杭
摘要:在对藏羌原生民歌这一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时,口述史的相关研究必不可少。在研究中不仅要理清口述史当前现状及主要目标,也需要由此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体系的构设等方面进行更多思考。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应以多位传承人为核心,并结合川西北不同区域、族群、时期的田野信息,由此对藏羌原生民歌的文化形态、传承机制进行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实现其更多维度的研究价值、构设起更为适宜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文化遗产 口述史 藏羌原生民歌
音乐学家薛艺兵先生曾提出关于“原生”民间音乐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体现在它是产生于民间、应用于民间、不脱离‘民间’这个原生环境的音乐;它的音乐风格特征,也是在这个原生环境中形成并与其生成环境相切合的。‘民间音乐’这个概念的内涵,即体现在它的这种‘原生性’”1。藏羌原生民歌,则主要特指在四川省阿坝州、甘孜州一带所流传的、受到藏族与羌族文化共同影響而产生的原生民歌。于单纯音乐形态而言,藏羌原生民歌的旋律、歌词、伴奏乐器都体现出了浓郁的地域民歌风味,是当地民众艺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广义文化形态上来看,藏羌原生民歌更是一种与演唱、舞蹈、戏剧、民俗仪式等紧密相连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在当地人的重要民俗活动、日常生活娱乐中广泛使用,体现出了本地区民众的集体审美精神。
作为藏羌人民生活中重要的综合性文化载体,藏羌原生民歌多个类别项目列入了国家级、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项目不仅成为本地区重要的文化名片,也成为本地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外部业缘介入等所产生的诸多影响,藏羌原生民歌的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传承人、传承体系在当前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许多口传心授的重要文化信息逐渐在当代发展中散佚,其原生性、活态性、真实性都受到了较大影响。基于藏羌原生民歌的当前研究现状、未来研究目标与整体的研究体系窥之,我们不仅要从口述史的研究中拓展现有维度与观照,同时也需打开研究内容与对象视野,丰富研究方法,对其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形成思考,由此推动未来研究体系的构设与发展。
一、研究内容与现状
如果没有深入实际的田野考察、将传承人这一民间文化传承主体作为重要佐证,那么民间文化的历史是不完整的,而口述史正是对原有文献历史的补充,其现场感与真实性决定了其构成了历史多层次背料的丰富形态。2当前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不仅需要对传统文献材料进行补充拓展,还需要关注于其中的多个文化内容层面,并且需要透过研究来思考其传承机制及当下面对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从国家到省、地区对于藏羌原生民歌为代表的川西北少数民族文化聚焦甚多。尤其是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多位国家领导人与省、市领导多次深入川西北藏族与羌族群众聚居区进行实地考察,多次提出要挖掘与发扬本地文化传统、让当地群众的生活实现从解决问题到完成幸福憧憬的积极转变,为实现精准扶贫向乡村振兴而提出了许多要求,其中尤为强调“文化”在这其中能够实现的多维度现实价值。由此可见,无论是基于现实发展趋向还是未来研究要求,我们都急需对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进行详细系统的记录和保护。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以及地区文化研究趋势下,文化遗产视阈下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相关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势在必行。从当前本地区口述史的研究现状来看,除了政府引导完成了藏羌原生民歌的文化遗产普查、申报工作外,还在多个地区建立了相应的传承机制观测体系,同时录制、拍摄了许多宝贵口述史资料,所以基于当前较好的实践案例基础,若我们能基于文化遗产视阈对藏羌原生民歌的传承人完成更为深入的口述史研究,那将会对其文化产生更大的保护与传承意义。
作为文化遗产的藏羌原生民歌从其传承机制上来看,一般更为侧重依赖于传承人的口传心授形式,这样的形式容易受到较大的异变变率及文化冲击影响;将口述史研究方法运用到藏羌原生民歌的保护与传承中,通过记录、录音、摄像等多媒体手段,能够有效地将口头的、活态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转换成文字的、静态的和形象的内容保存下来。同时,借由口述史的调查倾听民众的心声、了解其文化心态,还可以借助社会语境的分析赋予藏羌原生民歌口述史以多层级的文化意义,而在“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意义上亦可对其口述史工作以当下功能拓展,以期完善传承机制和传承人体系之余,对其当下生存、传衍、发展进行深入探究。所以,对藏羌原生民歌传承人口述史进行相关研究在其藏羌原生民歌的传承和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显得极为重要,因为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形态的传衍及保护,亦是使其在当前文化环境中得以活态生存及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向,更是对传承人及当地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及实践文化互惠、产生人文关怀的迫切需要。
结合上述研究现状可以窥见,未来我们对藏羌原生民歌所开展的口述史研究是多个维度的。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维度不仅是基于材料整理与信息记录,还涉及其传承机制等多个层面。藏羌原生民歌的多位传承人曾受到地方政府、研究学者、媒体的采访,也有一些有基于口述史角度对其传承人、传承机制进行详细系统的口述史记录,而从当前口述史研究所需的学科维度来看,这些研究更多关注于藏羌原生民歌的整体文化系统及延展出来的文化形态记录,不仅需要思考整体传承机制的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也需对其发展困境、业缘介入、审美嬗变等情况予以观照。目前,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除了要关注于音乐学与人类学领域之外,也需结合音乐表演、音乐人类学、民俗学、艺术美学等交叉学科知识。换而言之,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既需要“更详细的记录整理”,也需要“更系统的深入研究”,它是顺应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及现实需要的,应结合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现实对其传承人的口述史进行记录整理。尤其是在当前面临着诸多传承困境与现实问题的境遇下,我们可以透过那些容易散佚、濒危、脆弱的口述史的研究,延伸至对传承人、传承机制、传承危机与问题的关注,为其口述史研究拓展多元维度。
二、研究维度的多元及动态拓展
“所谓‘静态保护’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搜集、整理、记录与保存;所谓‘动态保护’指通过口头传承的方式,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长久地’活下来”3。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在传统研究中更侧重于静态保护,而面对着日渐散佚、文化环境变迁、传承机制被破坏等现实境遇观之,我们更需关注于它们的多元及动态拓展,形成从文化空间到个体事例的研究体系。
从整体文化形态来看,藏羌原生民歌包含着民间文学、民间歌谣、传统舞蹈、民俗仪式、宗教信仰等多重文化信息,艺术形式多样、内涵丰富;而从其文化价值上来看,其中所包含的是本地区藏羌民众千百年在此之中所积淀的审美情趣、文化认知、精神风貌;而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藏羌原生民歌包涵着艺术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文化遗产学等多学科内容,具有多维度的学科研究价值。在千百年的口传心授中,藏羌原生民歌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在活态化的文化空间中也孕育出了具有浓郁地域与族群文化特色的审美特征,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由此可见,我们的口述史应在文化遗产视野下构设起多维度、具有现实人文观照、能够发挥应用价值的研究体系,真正拓展其研究维度。但当前以口述史的研究来看,目前大多是以当地政府和文化部门的音像、文字等初步记录整理的原始材料为主,整体上基本还是停留在原始材料的研究,不能满足当前口述史的研究趋向。由此可见,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需拓展其多元的口述史维度,在“动态化”的研究形態下对其开展系统、深度、提炼的具体工作。
需拓展研究维度的多元综合形态与动态化,表明了藏羌原生民歌与其他文化事项的融汇关系(如舞蹈、民俗仪式等),也体现出了研究中需关注的复杂文化动态。所以,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对象范畴应从音乐形态上升至整体文化形态,也要兼顾其中不同的文化角色与文化身份。未来的口述史研究不仅是聚焦于对各级政府认定的藏羌原生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也需要拓展至对其他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譬如一些未获认证的民间老艺人、研习多年的民歌歌手等);不仅只是局限在对演唱者口述史所进行的研究范畴,也将关注到相关的乐师、舞者、仪式主持者、民众甚至参与保护与研究人员的口述史研究;不仅局限在对其旋律、节奏、演唱技法的研究,也应考虑其社会性与民俗性等多学科的口述史研究维度;不仅局限于对老一辈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也应对当前新一代传承人进行多个维度的具体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在活态中的保护,活态主要表现在:技艺存在,传承人存在”4。由此可见,口述史研究需要在其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发挥积极作用,那便需要我们以其文化活态为势,关注于传承人及技艺。以人文观照为本,将传承人、传统文化环境、当前文化环境考虑其中,形成兼顾真实性、原生性、流变性、活态性的口述史研究体系。换而言之,文化遗产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化形态本身,更关照于传承人及其整个文化系统,让它们不仅“活起来”“用起来”,还要在“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应用中使其获得更好的生存发展。从传承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需要拍摄记录下一些民歌的表演技艺、表演流程,在口述史研究中要带有现实人文思考。譬如可以询问一些诸如“现在传承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现在依靠民歌是够能够获得收入,情况如何?”“现在家中有没有传承人或者徒弟?”等之类的问题,以文化遗产的视野对其传承机制、问题、解决途径有更加深入的思考,进而实现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尊重、对文明延续的重视、对民众集体精神的诠释。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藏羌原生民歌口述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是传承人,以及将传承人作为“独立个体”及“文化组成部分”的不同角色定位进行厘辨,然后再针对其文化形态、艺术特征、主体认知、文化遗产传承机制等加以客观角度分析,以口述史等相关理论视角对藏羌原生民歌的文化形态进行阐释。在实际研究中,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表演者、仪式人物、主要受众等参与角色的社会身份含义,在充分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状况之同时,基于客观态度对其文化内涵、精神内涵、传承机制、当前困境等进行分析,进而对其传衍、保护、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同时,关注于这些文化遗产能够实现文化与当地民众之间的互惠,基于人群之间、人与文化之间的互惠关系构建,使相关研究真正关注于人、活态共生、和谐发展,实现其更多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产业价值。
所采用的研究体系既然是多维度的,那么相应的研究方法也应当是多维度的。藏羌原生民歌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主要以人类学的基础田野工作与艺术学研究为源,采用的研究方法可在音乐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美学、民俗学等不同学科方法的引导下,辅以实地调研、专题采访、谱本分析、录音录像等方式对选题的相关研究进行多视角、全方位、多种方法研究论证并获取课题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形成完备的研究体系、实现应有的多维度研究价值。换而言之,口述史的研究要从现有的材料层面深入到理论层面,借助技术手段予以系统存档与推广,以文献数据库建设、网上音像鉴赏等数字化方式助力于文化研究。当前藏羌原生民歌可以借助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的态势,以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口头传统的田野采集规范与数字化建档规程、口头传统数据资源描述模型与著录规则5等方式为源,对现有音像资料、文字资料展开丰富详尽的深入研究工作,并基于数字化的资源及平台优势,提高信息高速检索与共享效率,可使口述史的研究发挥更大的研究优势。譬如:四川音乐学院在线开设的羌族音乐数据库,收录了许多羌族民歌的田野音像资料,这样不仅方便了研究者可以随时在线获得研究资源,同时也对一些濒临失传危机的民歌及口述史资料进行了数字化保护,其应用价值维度也由此获得拓展。
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式发展的背景下,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同时具有多重意义。以口述史去审思这类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及当代呈现之间的关系,对当前所存在部分问题进行思考厘辨并借由艺术批评的语境对其进行分析探究,这不仅可为其当下传承、保护与创新而提供较大助力,也为其当代文化振兴打开了更多的思路。当前藏羌原生民歌因其传承的活态环境受到冲击、原生文化环境受到多元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处于一个异变和濒危状态,所以对其口述史进行采访、整理、梳理显得日趋重要,而由此所产生的研究报告和音频、视频、曲谱、图片等资料不仅对现世具有一定的“抢救性”和“时效性”,这对未来藏羌原生民歌的综合研究可以发挥更大价值。所以,从口述史角度、传承人视野思考以藏羌原生民歌为代表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活态传承”与“当代呈现”之间的关系,找准保护主体在这之中的准确定位以及应当实现的实际功能,构设相应的批评及研究体系,由此寻找到一条兼顾藏羌原生民歌“传”与“创”、实现其当代文化价值及艺术价值的有效途径,并对其平衡机制、批评体系、实践思路的建构进行相关思索探究。前文提到传承人在口述史中的重要位置。藏羌原生民歌口述史源自于人,故其研究的逻辑旨归便是回归民间、“以人为本”,推动藏羌原生民歌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表演实践的双向互动研究,促进文化互惠及人文观照多向互动研究,使其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可以发挥更多地缘优势和实际价值;促进民间艺术家、文化传承人与专业高校、专家学者的交流,以文化视野涵盖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找到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传承危机,寻找到解决桎梏之途,并对其传播推广与活态传承发挥积极意义。较为重要的是,在不影响藏羌原生民歌原生传承体系的前提下,可为其传承机制、传承人体系、相关问题及困难提供更多的研究方案并予以实践,让藏羌原生民歌在“传承”“保护”与“创新”之间获得更好的生存及发展。
四、结语
当前口述史的研究将宏大形态视野延展至微观形态视野,不仅是传统史学研究、文化形态研究、艺术与审美形态研究的拓展,也能够产生更符合现实需要的理论指引及实践应用价值,能够对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发挥更多作用。
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研究拥有较好的材料保存与前期整理资料,但仍不能很好满足当前需求及未来趋向。于此境遇,我们仍需对藏羌原生民歌的口述史拓展研究维度、打开研究内容与主题视野、推进田野实践深度、提高理论高度、观照人文温度,由此进一步完善与丰富藏羌民族的文化研究体系,以期在和谐共存的发展法则中为其实现更多的维度价值,最终使得其口述史研究真正能够为藏羌原生民歌的传承、保护、发展产生更多助力。
注释:
1参见薛艺兵.中国传统音乐的文化处境[C].“中国音乐在新世纪的定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73-91.
2参见马知遥,张家万,潘刚.“非遗”保护前沿问题研究[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179.
3李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声音保护[J].江西社会科学,2007(08):196-200.
4马知遥,张家万,潘刚.“非遗”保护前沿问题研究[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100.
5参见《“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项目简介》[J].民族艺术,2019(2):2.
注: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川西北羌族萨朗与嘉绒锅庄音乐文化比较研究》(17CD191)阶段性成果。
——围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