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非虚构方式写《凉山纪》我毫不犹豫
何万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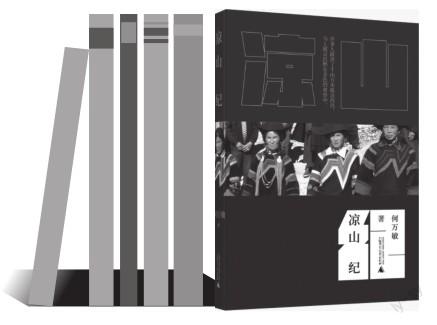
許多文学爱好者对于“非虚构”的深刻印象,竟是来自多年前的一场文坛事件。在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审中,阿来的作品《瞻对》以零票落选,惹得他勇敢站出来,抗议“希望我自己和其他写作者再来参加这个奖项时,以文学之名,受到公正的对待”。此作先前已斩获人民文学奖“非虚构”大奖,有评论家认为这是非虚构写作史上不容忽视的力作。而如今追溯“非虚构”在中国的历程,普遍的看法视《人民文学》2010年开辟“非虚构”栏目为发轫,用时任主编李敬泽后来的话说,“非虚构”不仅是提倡一种文体、一种写作方法,也是提倡一种行动的、介入的写作态度。
如果非要说“非虚构”在中国有多么陌生,也并非事实。《被天堂遗忘的孩子》2009年翻译出版时,《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撰文推荐:“从这部非虚构作品中,我们能感到罪恶前的无助、亲情下的无畏,当然也升华出对职业新闻工作者的敬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年后美国人彼得·海斯勒“纪实中国”的《寻路中国》与《江城》相继面市,则可以用广受追捧来形容了。
几乎与此同时,梁鸿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赢得更多赞誉。“还原一个乡村的变迁史,直击中国农民的痛与悲!”“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倾听农民在新时代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感受农民在新时期的悲欢离合!”读到这样带感叹号的三个句子,作品蕴含的分量大致能猜到。梁鸿看重非虚构是“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
作家蒋蓝直陈非虚构“是反虚伪的真文学”。新近写出《北纬四十度》的陈福民长期从事文学研究,则用非虚构写作“治愈对文学的危机感和焦虑感”。
我写作《凉山纪》时毫不犹豫采用非虚构的方式,当然不是为了去蹭什么热度。事实上那段时间我还阅读过许多其他非虚构作品,挑我自己喜欢的来举例吧:邹波的《现实即弯路》,致力于以社会学与文学的方法描绘现实,曾经写到凉山,试图从文化的角度了解彝族的时候,“却渐渐更多地关注它的社会病,在中国乡村普遍的命运之上,又叠加了这层少数民族的命运”。对善良、温暖、怜悯与执着、动力、勇敢的守望,在晏礼中的《别处生活:20幅平民肖像》中更显得丰富多彩——快递员、卖唱者、乡村医生、矿工、艾滋病人管理者、话剧演员、收藏家、狱警、退伍军人、环保主义者、巡道工,作家用干净的语言、朴实真诚的叙事态度,自由游离的立场,饱满却不经意的情绪流露,复原出现实的浓缩景观。还有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锌皮娃娃兵》《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我还是想你,妈妈》均为上乘之作。
世界的目光总是聚焦于都市的光鲜,高楼大厦任何时候都是蓬勃的标志。反之,四川省西南边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在2020年脱贫以前,一直是中国连片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原因复杂的地区之一,凉山日渐成为“神秘”所在。
作为一个漫游者,我在群山之间的各个角落进进出出,并对由无数高山构成的大地,以及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流域有着不可名状的归属感。当江河之水连同江河切割的山川,从中国的第三级阶梯向第二级跌落时,形成了无比壮阔的景观。“恋地情结”从来都是人文地理的题中之义,分析理解复杂多变的环境对人们生存方式所构成的影响以及多姿多彩的文化——就像高山之巅、蓝天之上的云朵,大地上的人们跟着山转,沿着水走,有时在山上,有时在水边,一直走到以山水形塑生命性格;就像民间流行的野性山歌,仿佛因为离天太近而趋向灵性,甚至一座高山、一块石头、一只飞鸟、一片树林、一阵风,都可以变成奇妙的精灵。
是的,当我把凉山视为“精神高地”之时,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矫情,这里才是心灵的安放之所。
具体到写作动力,我暗自追随的前辈当是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1943年夏天,率燕京大学边区考察团进入凉山时,他才33岁,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两年,血气方刚,踌躇满志。遥远的凉山因其著作《凉山彝家》,被掀开尘封已久的一角。这本书也被誉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代表作”。
闭塞久矣的结果是,关于凉山历史文化、人文地理类的著作乏善可陈,特别是反映早期凉山的堪称奇缺。有几本出自外国探险家之手的,翻译成中文出版,可以想见其实已经与发生的事实相隔了几层。它具有的史料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也促使我必须走到相应的地方去仔细求证一众地名人名的确切,回望过往历史的风云诡谲。强调非虚构的“在场”,既可以将读者妥帖带入现实真相,也是呈现历史往事的一种技巧,并可以将写作者的思想、情感、观点等等隐藏于描述的细节当中,打开一种被遮蔽的事实相貌。
考验脚力的是那些无休无止的道路。蜀道难,凉山路更难。前些年,许多地方根本不通公路,放眼望去,萦绕山中的羊肠小道曲曲弯弯、草蛇灰线。我采访最艰难的一次是在木里县的大山中,美其名曰“穿越香格里拉”,22天的整个行程中徒步多达19天,行走500多公里,直走得人仰马翻。
从金沙江到泸沽湖,从牛牛坝到德布洛莫,从毕摩文化到彝人之歌,我试图以微观性视野来扩大此地的人文历史,填补人们对凉山地理景观与人文历史认知的空白,从而加深对凉山这一偏远地域古老且独特的文化。而这或可增添对广袤中国大地的了解。
沿着前人踏出的道路走来,我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个举足轻重,又颇为有趣的“点”上,只不过文字中表述的“点”并非单个数字的实指。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眼界,汉朝“开发西南地区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行政单位叫作‘道。道是一条直线,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个面。从一条线,慢慢扩张,然后成为一个面,建立一个行政单位……汉帝国的扩充,是线状的扩充,线的扩充能够掌握一定的面时,才在那个地区建立郡县”。尽管横断山东缘的群山叠嶂、江河湍急,形成重重阻隔,对外界事物的好奇一直是推动人类持续寻路与探索的原动力。只要你有过在连绵的山峦或者无垠的旷野目睹道路网络般的延伸,你就会对此深信无疑。
而每到一地,当地人的从容不迫与吃苦耐劳,无疑都成为我在写作中收获的一笔财富。所以我每到一地,如果时间不紧迫的话,我更愿意安心住下来,去听当地人慢慢讲述,获得足够的细节和心灵感悟。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际会都映照着风云变幻时代中一些宏大的叙事。人总是有故事的,無论欣喜与忧伤,都值得娓娓道来。
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碰撞,社会形态由奴隶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即“一步跨越千年”;改革开放后被抛入经济狂飙,贫富反差凸显诱惑与欲望的困境,凉山确实不乏社会观察的素材和样本。尤其对于许多生活在都市的人而言,山中的“异质性”色彩着实令人产生好奇。从传播学角度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发现与着笔只要源自实地采访所得,不仅仅是道听途说或者干脆臆想编造,你所聚焦的那一面就是存在的。真诚的叙述乃至精彩的故事、稍有闪失乃至偏差误读,则依赖于写作者本身的素质和把握事件与人物的能力。
用文学的笔调,以非虚构的方法,追寻普通人跌宕的生命历程和时代的精神状况,一直是我乐于关注的主题。这在一个风行快餐文化的时代,一个游戏、谐谑和解构的时代,肯定并不讨好。我的想法是,具有现代性的现实主义使我们了解到纷繁复杂社会中,烙有鲜明个性色彩的生活动态、生命样本。本质上,写作者和其他人同样处于社会现实之中,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同样是写作者需要面对的,这点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写作者基于长期的观察与表达训练,所得到的反馈一定程度上比常人来得敏感与准确;而一个严肃的写作者还应该苛求以积累的知识建构起来的逻辑听从内心良知的召唤,去观察和描写那些可能被忽略的偏远与边缘、空白与盲区。
由是,凉山这片大地的魅力于我而言正在于此。还是一句话:我用行走的方式和凉山对话,语言也许粗陋却真挚坦荡;我用凝视的方式和凉山相守相望,避免陌生得互不相认,擦肩而过。
《凉山纪》2021年9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其后引起各方反响,也可以说是好评较多。评论家白浩的评价相当中肯:
非虚构关键在于穿过真实后,能触摸到温度和灵魂,这样的真实就不只是皮相的真实,而是抵达本质的真实,是自我的真实,是融入个人体验的活的历史,这样的文本就具有了召唤性。
对于写作,我抱持有生命温度的真诚质感,乐见去大地寻觅生存状态,或许是想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精神的原点。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作者系高级记者,现任凉山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