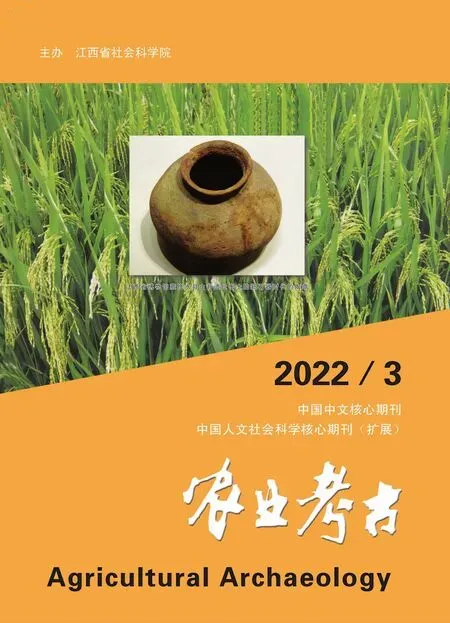人口流动与乡村非农化转型
——基于一个浙北村庄的历史考察
王 荧 沈志忠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乡村的经济史上,以乡村非农化为主旨的改革开放必然成为划时代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的农村经济均是在小农生产边缘徘徊,而改革开放直接开启了乡村非农化的浪潮。此后,中国乡村走上了非农化的道路。
本文试图表明,一个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既缺少深厚农业积累、又缺乏实力雄厚的社队企业的生产队是如何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实现人口流动和收入非农化的。本文以浙江东部的一个村庄——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牛墩村为案例的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时期该生产队利用周边省份基础建设辐射积极输出劳动力实现收入非农化,并逐渐瓦解原先的制度。这种人口流动在集体经济晚期就已经开始,并在20世纪80年代末逐渐发展,至今方兴未艾。
牛墩村所在的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北濒杭州湾,南临曹娥江,从古代海涂开垦开发而来,是历史上著名的浙东海防重镇。沥,意为流,旧时为曹娥江入海处,故称“沥海”。《绍兴县志·沥海所志稿》记载:“沥海所为旧会稽属三十二都。毗连上虞,宋为弦歌乡,元为太平乡,沿至有明为沿德乡,今仍为沥海乡。”
牛墩村位于沥海镇西北,距离上虞县城16.7公里,北濒百沥河。村所在地原本无人聚居,相传沥海一带常遭洪涝,唯该处地势较高,且村民多养牛者,乃是放牧之地,故此名曰“牛墩”。20世纪50至70年代,牛墩村成为一个独立的大队,曾名三联大队,1956年由牛墩、下岸、张家埠三个初级社合并为三联高级社,1958年为三联生产队,1961年为三联生产大队,后因与别的生产大队重名,1981年6月19日更名为牛墩大队(因驻地得名)。牛墩大队共辖3个自然村,128户人家,548人,耕地525亩,种植棉花、水稻、麦类、油菜等。牛墩村是大队驻地,有92户,408人,以张姓为主。据传,18世纪中期,肖金巨商张氏,向今三汇一代开拓水运经营,在附近设埠,货物由此下船,经内河运销各地,故此地日久遂以张氏名姓。2006年,沥海镇根据《上虞市政府关于调整沥海镇行政村规模的批复》(虞政发(2006)13号)文件进行了行政村的调整,牛墩村和邻近两个村庄(九庄村、前倪村)合并,改名为城西村,撤销原牛墩村村委会,新村委会驻原九庄村内,称为城西村村委会。合并后的城西村总人口2612人,耕地面积2246亩,总劳动力1761人,常年外出务工劳动力1048人。2021年春节前后,本文作者以牛墩自然村为调研点,重点对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乡村人口流动与非农化问题进行调研,故本文仍以行政村合并之前的名称,即“牛墩村”为准。
之所以选择该村作为案例考察,不仅因为该村是作者的半个家乡,熟悉且容易获得第一手调研资料,而且因为该村所在区域一直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以及水稻种植历史,保留着农业耕作的传统。不过改革开放之后牛墩村放弃传统农业,实现了劳动输出型的经济转型。牛墩村经历了经济结构完整的转型历程,因此分析这一案例具有典型意义。该案例表明,尽管该村集体经济较为落后,但是,牛墩村通过人口外出流动打工,部分地实现收入非农化,并贴补村庄的农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外出打工成为该村收入非农化的主要途径。这种缺乏工农业积累的贫穷村庄但通过劳动力输出而实现增收的模式,对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以及农民收入增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积贫的农业基础和积弱的工业基础
20世纪50年代,牛墩村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大队,下设三个生产队,隶属沥海公社。在50至70年代,牛墩生产大队的农业基础和工业基础都较弱,难以为村庄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
(一)积贫的农业基础
出于统一安排,牛墩村被划分为棉区,也即全村80%的耕地用来种植棉花,剩余20%的耕地解决口粮问题,同时国家对村庄口粮进行补助。不过,在实际生产中劳动低效率影响了棉花的亩产,因此生产队往往用更多的耕地去种植棉花,进一步挤压口粮地,无法满足村民的正常需求。在改革之前的牛墩村,人们用玉米糊、番薯糊充当正餐,很少有机会吃米饭。在营养摄入方面,牛墩村乏善可陈。有时候人们会摘野菜充饥;绝大多数村民基本和鱼肉等绝缘,甚至在年关时节也难以保证正餐有肉。因此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之前牛墩村在口粮种植和蔬菜供给方面处于贫困状态。
村民在生产队的劳动按照所评的工分获取劳动报酬:男性成年劳动力一天值10个工分,16岁以上未成年男性一天值8个;成年女性劳动力一天值8个工分,未成年女性劳动力不参加劳作,女性劳动力还可以在村办企业中工作以换取工分;孕假以及产假不存在“带薪休假”的情况,不参加劳动不领工分。在1982年重新制定的管理办法中,规定因身体状况而需要安排轻便劳动的,按8折记工。每天收工时,生产队会有一个记分员给各位出勤人员打分,记录在册。每户家庭在年底的时候根据工分量和口粮消耗量与生产队进行结算。
在正常情况下,村民平时不需要现金——事实上也没有足够的现金供他们消费。一旦遇到紧急状况,例如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村民一般向生产队申请借款,而还款的方式依然是用工分折算现金。直到去公社化前夕,人们才决心整顿混乱的财务制度,重新制定了严密的借款、数额、还款制度。例如新的制度规定社员遇到丧事,独生子可借60元,非独生子则按比例不超过60元;社员生病以及医药费,10元以上方可向生产队借款预支,否则不予受理。
从上述粗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牛墩村在当时并没有深厚的农业积累。从1981年第二生产队提供的财产清单来看,该年第二生产队农业收入仅为179.63元,现金是364.96元,而存款的数目是4959.86元。
(二)惨淡经营的社队企业:积弱的工业基础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政策鼓励在生产队基层创办工业,因而牛墩生产大队也开办了一家砖窑厂作为社队企业。该厂坐落在村庄的北面,砖窑厂的员工都来自于村庄内部。其中女性劳动者占据了大部分比例。有时候也会招收一些男性员工。当时,工人们在窑厂工作的报酬并非领取工资,而是记录相应的工分。这些工分连同农业生产所得,年底纳入各个生产队的核算。
牛墩村的社队企业事实上并未给生产队带来利润和资金。这家砖窑厂惨淡经营,效益和利润一直未尽如人意。其原因主要在于竞争激烈而市场量狭小。在沥海镇的诸生产队中,开办砖窑厂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窑厂。很显然,遍地开花的砖窑厂影响了牛墩村这家社队企业的效益和利润,以至于牛墩村窑厂的青砖难以外销。效益不佳使得村庄难有足够的兴趣花费精力和心血经营窑厂,这样更加导致砖窑厂“聊胜于无”。
效益低下、利润惨淡,牛墩村的这家砖窑厂在生产队解散后即遭废弃。因此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牛墩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并不存在雄厚的社队企业基础。生产队的财产构成中,来自工副业收入的贡献微乎其微。
三、人口流动:劳动力征调与外出打工
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后期,牛墩村的人口流动主要有两种方式:被动的劳动力征调以及主动的外出流动打工。
(一)围涂抢险和劳动力征调
沥海镇历来饱受水灾之祸,即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也未见好转。因此在20世纪50至70年代,沥海公社经常抽调大量的劳动力来进行围涂抢险工作。
牛墩村(大队)被要求征调劳动力参加抢险工作。原则上每一户家庭必须出一个男性劳动力参加抢险,但是一些残疾人家庭和劳动力紧缺户可以豁免。每年的抢险工作持续的时间不一,少则数天,多则数周。在集体经济下,征调劳动力参加抢险工作是村民们必尽的义务而无法推脱。因此,虽然抢险工作、防范洪灾是有利于整个沥海公社的公益事业,但是对于具体生产队来说却是一项不小的损失,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生产队的劳动力是紧缺的。上述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观。自1985年起到2000年为止,上虞县决定征收抢险费来代替劳动力征调。此时牛墩村村民们可以资代劳而节省劳动力。一份大约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牛墩村(大队)的部分家庭以资代劳的清单表明,每一户家庭所缴纳的抢险费是这样几项因素的综合加权:家庭总人口以及男性劳动力占据的比例;家庭拥有耕地的数量;是否残疾以及鳏寡孤独。在综合评估后,那一年度每户家庭平均上缴136元抢险费。
这笔抢险费直到2000年才正式取消,而事实上沥海镇早已摆脱了曹娥江水患。因此牛墩村(大队)的劳动力征调贯穿了50至70年代。1985年开始征收抢险费后,牛墩村就可以将节约下来的劳动力用于自由流动和外出打工。同时,20世纪80年代初生产队集体上工制度的解散最终解除了人口流动的外在藩篱。此后,大规模外出务工成为该村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
(二)有限的劳动力流动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另一种人口流动的模式便是小规模的劳动输出。在当时,沥海公社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向每个生产队下达劳动力外出的名额数量。根据这种分配,牛墩村(大队)每年可以获得7-8个名额。这些人由生产队出具介绍信,经沥海公社审批手持介绍信到外地合法地居住和工作。同时人们在出门之前必须将口粮更换成全国粮票,为出远门做好准备。
牛墩村这些村民外出就业的范围比较广泛:在最早年份他们涌入江西支援铁路、开矿和水库建设。这些建筑项目大多是纯粹的体力劳动。当上海开发的辐射到达村庄时,木匠和水泥匠成为主流。不过,尽管属于体力劳动,这些外出村民的收入相比农业生产要可观得多。这些村民如果省吃俭用,则能够为家庭带来珍贵的现金收入。
正因为外出务工的机会珍贵、而收入又相对较高,人选的资格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从有限的访谈材料来看,经常可以获取外出机会的村民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确实拥有一些技术的人员例如木匠、泥匠、水电工等;另一类便是接近生产队权力中心的相关人员,尽管并不具备知识和技术,但也能获得机会。总之,此时牛墩村的人们只有接近权力中心才能获取外出务工的机会。这样的人毕竟在少数,除此之外,其他人则难以获得流动的机会。
然而,劳动力流通涉及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协调生产队劳动力流失后的生产活动。在当时,每家每户出劳动力,记录工分,然后向生产队领取口粮。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所有劳动力都固定在生产队内部这一前提之上的。现在部分劳动力可以自由流通,那么生产队就失去了这些劳动力,然而生产队需要提供的口粮却未因此减少,这样一来生产队(集体)就损失了许多劳动力。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牛墩村发明了名为“交队”的办法:外出劳动力根据一年所缺工分数以现金形式补贴给生产队,之后才照常向生产队领取相应的口粮。例如假设一位壮年劳动力一年的总共工分数大约在200工左右,每一工价值0.5元,那么年底这位劳动力就需要向所在生产队(生产小队)支付100块钱现金,以弥补生产队失去他一年的劳动力。这种方法被村民和生产队广泛接受。至于计算成年劳动力年均工分数和每一工分的价值,根据每一年不同的情况由生产队讨论计算完成,每一个工分的价值也并不固定,大约在0.5-0.8元之间浮动,例如1981年的工分价值就是0.8元。
1978年后村民向外流动打工的机会增多,审批程序也更加简化,大家只需兑换全国粮票即可。因此更多的人谋求外出打工的机会。在集体经济依然存在的前提下,更多的劳动力外出意味着更少的劳动力参加集体的劳动,因此在1982年的春季,牛墩村对工分购买制度进行了改革。在改革后的财政制度中,工分按照农闲和农忙进行计算,春耕和秋收工分价值高;而冬歇期则价格偏低。具体而言:“11月24元,12月20元,1月16元,2月16元,3月24元,4月32元,5月36元,6月36元,7月24元,8月24元,9月36元,10月36元。每年324元。”很显然,1982年的工分单价要比以前高出很多。这是生产队为了弥补劳动流失所做的努力,同时试图提高工分单价而努力将劳动力留在生产队内部。不过仅仅一年之后,“包产到户”和去集体化的政策(村民们称之为解散生产队)彻底撤除了劳动力流动的藩篱。自此之后,伴随着乡镇企业和乡村工业化的大潮,牛墩村的整体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大变化。
四、结语
对于农村和村民来讲,第一产业是基础。然而当前家庭作坊式小农生产无法带来巨额的非农业收入,这就意味着光靠第一产业无法带领农民致富。因此村庄的脱贫与致富必然建立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也即村民要通过多种渠道开发非农收入,改善收入结构,方能充分享受中国现代化的成果。
与很多积累深厚的苏南村庄相比,本文所描述的案例牛墩村,集体经济孱弱,既没有农业基础,也没有社队企业收入作为支撑。所幸此时村庄存在有限的人口流动和外出打工。不过整体制度环境依然是限制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因此有限的外出打工仍然无法根本改变村民的收入结构。不过,很显然,第二第三产业在收入上的优势足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大潮席卷全国之时,牛墩村以劳动输出为主要方式来实现自身的乡村工业化和收入非农化。
在当前全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村庄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每个村庄由于资源禀赋不同,自身所拥有的优势也不同,自然其劣势也不尽然相同。因此只有细致地研究村庄现代化的背景和可选路径,我们才能“因村制宜”,制定出合适的乡村现代化政策,最终实现村庄的现代化以及村民的共同富裕。
①此处数据来自村民阮梦尧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21年2月14日。访谈人:王荧。
②此处数据来自村民潘巧云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21年2月15日。访谈人:王荧。
③此处数据来自村民阮梦尧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21年2月14日。访谈人:王荧。
④事实上全国其他地方村庄也存在一定的劳动力流动,他们也采取用现金购买工分的方法来弥补劳动力的损失,至于名称则不一而足。参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李桂平:《被颠覆的村庄》,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⑤此处数据来自村民何某的访谈记录。访谈时间:2021年2月16日。访谈人:王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