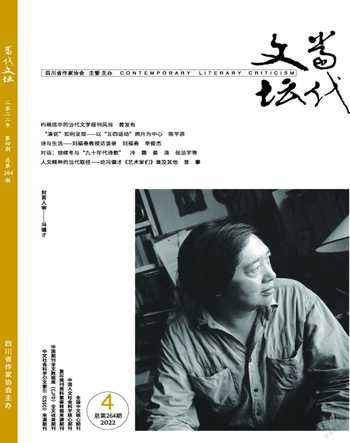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诗学的实践维度
宋聪聪
摘要:学界对海德格尔诗学理论的研究较少触及实践维度,因为海德格尔不仅在谈论艺术时鲜有论及实践,而且在其他著述中也较少流露出对实践问题的关切。但通过与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对比我们发现,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实际上是对亚氏所提出的人的三种活动即理论、制作与实践的继承和改造,存在一个超越了形而上学实践观的实践维度。一方面,艺术与艺术批评,即诗与思都为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实践而服务;另一方面,作为为真理建基并使人成为人的活动,艺术与艺术批评本身就是实践活动,且是最高意义上的实践。
关键词:海德格尔;艺术;艺术批评;《存在与时间》
学界对海德格尔诗学理论的研究很少触及实践维度,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海德格尔不仅在谈论艺术时鲜有论及实践,而且在其他著述中也较少流露出对实践问题的关切。《存在与时间》出版后不久曾有一位青年朋友询问海德格尔打算何时写作一部伦理学,显然海德格尔终其一生也未写作此书。将近20年后他给出的回应是:沉思存在之真理的“这种思想既不是理论的(theoretisch)也不是实践的(praktisch)。它发生在这种区别之前。这种思想之为思想,就是对存在的思念(das Andenken),而不是别的什么”①。容易得出的结论是,海德格尔是在否认他的思想的实践属性,这也成为不从实践角度研究其诗学理论的论据。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考察,“实践”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通常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的二分乃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前者指的是科学认识和研究活动,后者指的是作用于现实的行动,他所要做的不是在形而上学框架下研究“存在论”这样的理论或者“伦理学”这样的对行为的指导性约束,而是超越于这个框架,回到二者共同的本源处去思使理论和实践得以可能的存在本身,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对存在的思念。因此,这样一种思虽然并不属于传统的理论或实践的范畴,但实际上又是对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与超越,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思想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同时超越一切实践的行为。”②因此,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乃是一种超越形而上学实践观的“实践”。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在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中挖掘出一个一直被忽视的实践维度。
一 为了实践的艺术和艺术批评
要讨论海德格尔诗学的实践维度,首先需要确定的是:什么是实践?在1924—1925年冬学期的讲课稿《柏拉图:〈智者篇〉》中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其中他着重讨论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真理的五种解蔽方式中的三种——智慧(σοφία)、技艺(τέχνη)和明智(φρόνησις),他们对应着人的三种活动——理论(θεωρία)、制作(ποίησις)和实践(πρᾶξις)。③理论活动的作用对象是不变的事物,而制作和实践的对象都是可变化的事物。后两者的区别又在于,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实践的目的就是实践活动本身,二者的联系则在于,实践是制作的原因和目的,例如,建造一座神庙这一制作活动的目的并不是建造神庙这项活动本身,而是一座建好的神庙和敬拜神明;而敬拜神明这一实践活动的目的就是敬拜神明。因此,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实践就是目的内在于自身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通常就是伦理和政治活动,而在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中,艺术恰恰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在1934—1935年冬学期的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稿中,海德格尔这样说道:“基础情调(Grundstimmung),而这意味着一个民族(Volk)之此在的真理,源初地经由诗人得到创建。但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的存有,通过思者得到把握、接合并因而才被敞开为存有。而以如此方式得到把握的存有,以民族被带到自己本身面前而成为民族这种方式被设立入存在者的最终与最初的严肃之中,亦即被设立入得到定—调(be-stimmt)的历史性真理之中。这通过国家缔造者对规定着民族之本质的国家(Staat)的创立而发生。然而这一切发生过程有其自己的时间,因而有其自己的时间序列。诗、思、建立国家等力量在历史展开了的时代一齐发挥作用,向前或者向后,并且完全不可预测。”④
在这里,海德格尔提出了存有在民族中发生亦即建立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路线。第一步是由诗人创建出这个民族的基础情调,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真理。“情调”(Stimmung)一词在日常德语中意为“情绪”,但这里所说的绝非浪漫主义所主张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⑤,情调并非诗人的个人情感,而是他从神那里所倾听到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德语中“情调”(Stimmung)与“声音”(Stimme)有着相同的词根,海德格尔借用这一点巧妙地指示出情调之意义。“……而且自古以来/诸神的语言就是暗示。……诗人之道说是对这种暗示的截获,以便把这种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族。”⑥也就是说,诗人恰恰是放下了他个人的情感,而使自己成为神之声音传递给他的民族的通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我们在此只谈论这种艺术),艺术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就像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⑦艺术作品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对神之暗示的暗示。需要指出的是,在海德格尔那里,艺术与诗具有同义性,诗不仅指诗歌,也泛指一切艺术形式:“作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就是诗”。⑧因此,创建出基础情调的诗人不只是诗歌创作者,也包括广义上的艺术家。
而正由于这双重的暗示,基础情调是隐晦不明的,因而需要第二步,即思者對诗中的基础情调进行把握和接合,从而将其中的存有敞开出来,也就是说,将诗人从神那里截获的暗示以一种清晰的人的语言阐释出来。通过诗人和思者的接力,神的语言转变为隐晦的诗语再变为清晰的人语向着一个民族道说出来,诗人和思者也就成为这个民族的建基者,因为正是这传递着和转变着的声音中蕴含着能够为一个民族建基的真理。“神圣者赠送词语,并且自身进入这种词语之中。词语乃是神圣者之居有事件。”⑨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民族之真理、民族共同体之根基不是来自人的创造,而是来自神的馈赠和民族的先驱对这种馈赠之接纳。
但是,诗人和思者的先驱性力量只是为民族建基,还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民族共同体。海德格尔认为,建立民族共同体这一实践最终需要由国家缔造者通过建国行动来完成,诗人和思者的努力正是在为这一行动做准备。思者在诗人创建的基础情调的基础上所构造出来的清晰认识为具体的建国行动提供了纲领,通过这一行动,认识才真正转化为对民族之本质的规定,才真正进入民族的现实之中。由此,诗人、思者、国家缔造者形成环环相扣的链性关系,在民族共同体的建立中共同发挥作用,而他们具体的作用时间和作用效果是不可预测的。这实际上就是柏拉图“哲人王”思想的翻版:哲人指导政治家建立“理想国”,只不过海德格尔在哲人之前加上了诗人这一更为源初性的角色。联系这一讲课的时间恰好是在海德格尔卸任校长职务后不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海德格尔在现实政治实践受挫后在理论层面对其政治理想的表达。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想要建立的国家乃是纳粹政权。相反,这恰恰表明此时海德格尔的思想已与纳粹政权相抵牾。因为如若纳粹政权已经实现了海德格尔的政治理想,那么他便不会辞去校长职务,也不必转而如此这般在理论上勾画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且在大约同时期⑩的黑皮本中,海德格尔对纳粹的不满也清晰可见,比如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把种族和质朴性挂在嘴边的人,认为他们根本上并非纯种也并不质朴11,彼得·特拉夫尼也指出,海德格尔在这一讲课稿中所说的“民族”(Volk)并非一个生物意义上的共同体12。因此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担任校长的政治行动暗示出他曾经寄希望于纳粹就是他所期待的国家缔造者,然而纳粹政权却使他失望,因而海德格尔的政治理想在这一讲课之时还远远没有实现,这也正是为什么他在这次讲稿中会认为荷尔德林所说的“但他们(指德国人,笔者注)对我不再有所需要了”是一句“可怕的话”13并大声呼吁德国人去倾听荷尔德林,从而为建立他理想中的民族共同体做准备。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中,艺术作品并非像康德所说的是无功利的,而恰恰是以现实的政治实践为目标,服务于政治实践。而且,所谓思者对诗的基础情调中的存有的把握与接合实际上就是海德格尔本人在这一讲稿以及其他诸多论文和讲稿中所做的工作——艺术批评,而这一工作正是为了在诗人和国家缔造者之间架起桥梁。也就是说,艺术批评也是服务于政治实践的。由此我们得出海德格尔诗学理论之实践维度的第一个方面:艺术和艺术批评都是为了政治实践。
二 作为实践的艺术
既然在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中,艺术是以政治实践为目标的,那这是否意味海德格尔的艺术观乃是一种工具化的艺术观、艺术并无独立性呢?是否意味着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艺术仅仅有着外在于自身的目的,因而并非实践活动呢?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制作的解蔽功能仅仅在于“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14,因此制作的目的仅仅在于这种外在于制作活动的事物以及它的用途。但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作诗或者说创作艺术作品不是为了制作出某个事物、某种成品,而是对神的谛听。“作为道说(Sagen),说从自身而来就是一种听。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是首先就是一种听。……我们不仅是说这种语言,我们从这种语言而来说话。”15艺术作品不是出于人的创造力,而仅仅出于对神之暗示的接纳,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创作过程与完成的艺术作品是合二为一而非二元对立的,创作的目的就是创作本身,即倾听神言,也就是根本性的语言,而倾听到的语言就是艺术作品。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中,语言被视为存在的运作,而神圣者即为存在的代名词。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不再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制作活动,而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活动。
作为实践活动,艺术是为真理建基的活动,这种建基不只是为民族共同体在国家层面的建立做准备,而且本身就具有独立性。正如海德格尔生前好友佩赛特(Heinrich Wiegand Petzet)写作的《向着一颗星而去:1929—1976与马丁·海德格尔的相遇与对话》(Auf einen Stern zugehen: Begegnungen und Gespräche mit Martin Heidegger1929—1976)一书的书名所暗示的,海德格尔终生追寻的都是同一颗星——存在,也就是真理。在《存在与时间》时期,他认为存在的意义系于此在对存在的领会,因此从此在出发追问存在,由此陷入主体化倾向;1930年代开始为了克服这种倾向他主张回到存在本身,让存在自行显现出来。在这个思想的“转向”中,对诗和艺术的讨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转向”之前,海德格尔关注的是真理解蔽的一面,试图通过此在让真理敞开出来。而在转向之后,他意识到真理除了解蔽的一面之外还有遮蔽的一面,真理除了敞开一个世界,还有遮蔽着自身的大地,但真理隐匿于存在者之中,其本身是无可把捉的,因此艺术作品就作为真理发生的绝佳场所被海德格尔所选中。在这个场所中,艺术家仅仅是真理发生的通道,因而人与真理的关系就倒转过来,真理不再由人所把握,相反,人要臣服于真理为它所用,由此,艺术就成为使真理自身遮蔽着显现出来的实践活动,而由于真理的根本性地位,艺术因而是最高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在艺术作品中真理获得了独立性和支配地位,从而进入一个民族之中,这个民族也就在此基础上被奠基,获得了其最基本的规定性。
然而,这种建基活动不是轻易可以完成的,海德格尔赋予了艺术极为艰巨的使命。按照朱利安·扬(Julian Young)的观点,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出了一种艺术的“希腊范式(the Greek paradigm)”,符合这种艺术范式的艺术作品不仅能够将一个世界从遮蔽中带向前来,并赋予这个世界以神圣性,此外,还能围绕它自身聚集起一个社群。16这种艺术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伟大艺术”,其典型代表就是《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谈论的希腊神廟。“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了那些道路和关联的整一体并同时把它聚集于自己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为人类赢获了其天命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的统治范围是希腊民族的世界。从这个世界而来并在这个世界之中希腊民族才回到自身,完成其使命。”17希腊神庙将希腊神的形象向人们显示出来,规定了一个民族存在的意义,并进而规定了这个民族包括诞生和死亡在内的种种事件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希腊神庙开启了希腊民族的历史。海德格尔将希腊民族这一历史的发生视为西方历史的第一个开端,即存在之真理在西方历史的第一次发生。
但西方历史在这一开端之后很快就走上了形而上学的弯路,且愈发变本加厉,因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的扉页上这样写道:“我们用‘是’或‘存在着’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然而我们今天竟还因为不懂得‘存在’这个词就困惑不安吗?不。所以现在首先要唤醒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的重新领悟。”18这段话包含着双重的紧迫性:一是我们还不理解存在,二是我们甚至根本就遗忘了存在问题。海德格尔的全部探索源起于此。因此他赋予艺术的使命就在于开启西方历史的第二开端,让存在历史再次发生,而要完成这一使命,不仅需要使存在显现出来,而更首要的还在于唤起民众对存在的思念,亦即使民众意识到他们已遗忘了存在。这两方面的使命正是艺术作为一种实践所要完成的。
在现代社会,突出地导致存在之遗忘和存在之遮蔽的乃是形而上学的极端表现形式——现代技术。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称为“集置”(Gestell),词根“stell”在德语中意为“摆布、放置”,指示着技术对人和物所具有的形而上学的支配作用,而“Ge”有“总体”之义,意在强调这种支配的总体性和系统性。现代技术以强力控制着地球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其视为可供处理的对象,甚至人也成为供使用的“人力资源”,因此,人和其他存在者都受到压制,难以自由地显现出来,真理隐匿不现。海德格尔认为,能冲破技术统治、对技术产生抑制作用的正是与技术有着同源关系的艺术。在古希腊,技术与艺术同属于“技艺”,是真理的基本解蔽方式,而现代技术则是异化了的技艺,需要依然保持着原初的非对象性解蔽力量的艺术对其进行拯救。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四重整体(das Geviert)的概念,在艺术中,天、地、神、人四方自由地游戏,无论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还是他人与艺术作品的相遇都不是对象化的掌控或欣赏,而是与天地诸神的共舞,人因此冲破了技术之二元对立的统治,在艺术中达乎自由的境地而成其本质,艺术活动也就成为在技术时代敞开真理领域的实践活动。
三 作为实践的艺术批评
在海德格尔的诗学理论中,不止艺术是一种实践活动,艺术批评同样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同样有内在于自身的目的。艺术批评在亚里士多德所划分的人的活动中所对应的是“理论”。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此处讨论的理论和实践与本文开头海德格尔所言“这种思想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中的这两个词并非同义,海德格尔这句话中所说的乃是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而我们所说的却是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时更为原初的含义。
海德格尔曾专门从词源上讨论过理论一词的意义。他指出θεωρία这个词来源于动词θεωρεῖν(观审),而θεωρεῖν由两个词干组成,即θέα和ὁράω,θέα指的是某物在其中显示自己的外观,而ὁράω意为注视某物,因此θεωρεῖν就意味着注视在场者于其中显现的那个外观,并且通过这样一种视看观看着逗留在这个在场者那里。此外,θεα还可以有不同的重音读法,θεά指的是女神,而在巴门尼德看来,’Αλήφεια(无蔽、真理)就是这样一个女神,因此理论就意味着对真理的有所守护的观审。海德格尔特别指出,尽管在希腊人那里观审之生活区分于实践之生活,后者指投身于行动和生产的生活方式,但在这种区分中,观审之生活尤其在其作为思想的最纯粹形态中乃是最高的行为,θεωρία使事物达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现”(ἐνέργεια)或“隐德莱希”(ἐντελέχεια),即本真在场者的在场状态,因此θεωρία就是人类此在的完善形态。他还指出,理论一词之所以后来流于形而上学的含义乃是因为罗马人的翻译使之失掉了希腊原义。 海德格尔对理论和实践的分析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致的。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和实践做了区分,狭义的实践指的是作用对象为可变事物的伦理政治行为;然而另一方面,理论也是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最高等的一种实现活动”20,因此也可归入实践活动,甚至可以说是最高的实践活动。
那么,具体到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他所做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理论呢?由于理论一词在日常使用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形而上学的烙印,因此海德格尔为自己选用的词是思(denken),并将他的艺术批评称为“思与诗的对话”,意在强调他对艺术作品的思不是一种对象化的行为,而是一种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最为青睐、同时也阐释得最多的诗人是荷尔德林,他将荷尔德林称为“诗人之诗人”21,“思与诗的对话”这一说法也是在谈论荷尔德林的诗歌时提出的。在1951年出版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二版前言中海德格尔指出:“這些阐释乃是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这种诗的历史惟一性是决不能在文学史上得到证明的,而通过运思的对话却能进入这种惟一性。”22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增订第四版前言中,海德格尔又指出:“本书的一系列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研究论文和美学论文。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23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绝不是文学史的阐释,不是将他的生平和作品当作既定的东西去做一种理性的研究,而是出于一种必然性去探寻诗的惟一性。结合前两部分的讨论,我们认为,诗的历史惟一性便是诗所暗示的能够让存在历史建基的神性话语,这种惟一性需要思者将其开解出来,进而传递给民众。
那么,思的必然性又作何解释?思缘何会有必然性?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谈道:“假如人将来能够思存在之真理,则他就要从绽出之生存(Ek-sistenz)出发来思。人绽出地生存着置身于存在之天命中。”24“绽出之生存意味着站出来(Hin-aus-stehen)进入存在之真理中。”25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的动物,而恰恰是绽出之生存,亦即放弃对自己的掌控而归属于存在、从存在而来倾听和道说。作为本质性的生存方式,思与诗一样并不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表达,而是“本身就是原初的、本质性的、因而同时是最终的言说(Sprechen),是语言通过人说出来的最终的言说”26。思与诗一样是为存在建基的行为。正是因为进入到存在的领域,对诗的思才不是任意妄为的随意阐释,而是具有了必然性。运思与作诗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回归到人的本质之中、作为人而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与思也无疑是对人来说最高的实践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海德格尔30年代就开始大量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但“诗与思的对话”这一提法是在海德格尔1943年为自己的教授就职讲座《形而上学是什么?》撰写的后记中才首次出现的:“对于哲学和诗歌的关系,人们大约有一些了解。但对于‘切近地栖居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的诗人与思想家的那种对话,我们却一无所知。”2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思想架构的一种转变:30年代他阐发的是诗—思—建立国家的三重结构,而40年代起就几乎不再谈论国家缔造者和建立国家的行动,转而主要讨论诗与思的对话,其原因可能是二战的废墟挫伤了海德格尔对民族共同体的信心,也推迟了他对第二开端到来之时间的预期。在1939—1941年的黑皮本中他写道:“最早在2300年左右历史可能会再次发生。那时美国主义已经被它过度的虚空消耗殆尽。在此之前人还会向着虚无迈出想象不到的前进—步伐,认不清,也就是说无法克服他的奔跑的空间。”28二战之后他很少再提到“国家”“民族”等字眼,而更多地转向一种等待第二开端在遥远的未来到来的虚静姿态,专注于思与诗的对话来为这一未来做准备,当然,如夏可君所言,这很可能也受到了庄子“无用之思”的启发29。
总之,虽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并未写作伦理学著作,而是转向了对艺术的讨论,但实际上他的诗学理论恰恰是对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人的活动的三方面的继承和改造,改造的结果是使得艺术不仅以实践为目的,而且本身就是实践,并且他的艺术批评也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实践。不仅如此,由于艺术和艺术批评都是为真理建基并使人成为人的实践活动,因此它们还都是超越了形而上学实践观的最高意义上的实践。而海德格尔诗学理论在实践层面存在的问题则在于只关注政治而忽视了伦理,这一点有待后续研究中再继续展开。
注释:
①②242527〔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6、421页,第426页,第396页,第396页,第364页。
③Martin Heidegger,GA19. Platon: Sophistes,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SS.21-64.
④1321Martin Heidegger,GA39. Hölderlins Hymnen “Germanien”und “Der Rhein”,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0,S.144,S.136,S.221.
⑤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⑥⑨2223Martin Heidegger,GA4. Erläuterungen zu Hölderlins Dichtung,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81,S. 46,SS. 76-77,S.7,S.7.
⑦⑧17Martin Heidegger,GA5.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1977,S. 26,S.62,SS. 27-28.
⑩海德格尔全集第94卷收录的乃是海德格尔1931-1938年的笔记,难以确定这段笔记究竟是哪一年,因此大致属于同一时期。
11Martin Heidegger,GA94. Überlegungen II-VI,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2014,S. 173.
12Peter Trawny,Heidegger und Hölderlin oder Der Europäische Moregen,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2004,S.90.
142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1頁,第305页。
15〔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54页。
16Julian Young,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Ar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 65.
18〔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19〔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4-49页。
26〔德〕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7页。
28Martin Heidegger,GA96. Überlegungen XII-XV,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2014,S. 225.
29夏可君:《一个等待与无用的民族——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第二次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9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2022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海德格尔艺术理论的建构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NDQN202YB)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