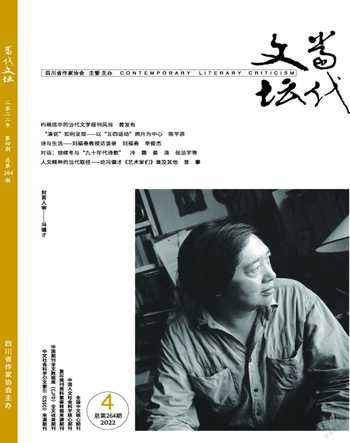从《寻金记》看阿来叙事的丰富性与转捩点
张译丹
摘要:叙事文学所叙之“事”长期被狭化为叙述事件,而使智性的事理、事义被忽视甚或弃置,近年来一些杰出作家突破这种流弊、偏向,让智性元素重返了叙事现场,阿来的最新作品《寻金记》便是其中之一,但这部作品却更矫矫不群,作家对智性的理解与表达并不限定在具体知识或门类学科上,而有着一种新的理性叙事的探索,从三个层面建构了他的叙事的丰富性与重大转捩。
关键词:阿来;《寻金记》;理性叙事
《人民文学》2022年第1期推出阿来的《寻金记》(上)时,其推荐语有“在历史选择的铁律与小说方式的微妙间,写出审美的无穷张力”①,而《小说选刊》在转载时认为“阿来则纯粹依据史料与想象虚构,依然活灵活现,结构工巧,举重若轻”②,虽然二者侧重面不一,但都对阿来这部新作有着极高的评价。我们确实能看到该部小说给叙事文学带来的惊喜非同小可:一方面诉诸于审美想象的张力重生,另一方面诉诸于历史铁律的质实认知。虽然现在还不敢完全肯定,中国叙事文学是否会因这部小说的出现发生自1980年代以来的又一次叙事理性的觉醒或者转捩,但至少可以认为,阿来的这部小说在他自己的创作序列中,是自《尘埃落定》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我们不将《寻金记》纳入一个纯粹的虚构文本的阅读视野,会发现该小说的多重叙事机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同时启动,诸如视点飘移、复线并叙、众声喧哗、复调结构、叙事留白……这些显见的叙事手段之后,到底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叙事理念才让阿来赋予这部作品缤纷色彩和复杂的节奏,并保持着一种不见盈亏的力度、没有过度的铺张,恰到好处地达成叙事的完满?这里,我们有必要展开两个维度的多向性寻觅,一个是阿来的创作进阶,另一个是当代虚构性文本(Fiction)的叙事裂变或涅槃。
在我个人看来,从《尘埃落定》开始,阿来几乎所有的创作都在致力于不断的自我突破,几个显见的转折点分别在《尘埃落定》、《空山》(第一部)、《云中记》中体现出来。成名作《尘埃落定》首先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很高的起点:边缘化题材、差异化人物、自我愚化的叙述人设置以及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致化的语言,与大时代语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同时期香艳而自我絮叨的小说之林中,注入了硬朗而康健、粗粝而率真的生猛元素,在天高地远的野蛮叙事中,自然形成中国西部原野的粗犷文风;《空山》依然沿用藏地题材,以一场山火灾难而引发对消失的文明的反思,其间蕴含着阿来对于母体文化的追问与寻源,有着追求历史大叙事的端倪又不乏个体生命寄身于斯的迷思——对消失文明的追慕、对悲剧性历史的推演,表明阿来有一种构建性梦想,但稍不留意则可能陷入过分满盈的叙事堆砌。因此我认为《空山》的尝试恐怕并未完全达到预想,但这个遗憾在《云中记》中得到完美的补足。《云中记》在《空山》之上建立了一个精神返乡的意象,阿巴这个人物在其符号性之外,被阿来赋予了某种神性元素,在消失的故乡重建了永久的精神家园,其肉体的消失并不代表民族精神的永逝。这三部作品在叙事上除了皆具阿来个人浪漫抒情的风格之外,分别契合着中国当代叙事的诸多走向,《尘埃落定》的意识流手法以及潜意识悖谬性叙事,以个人视角与大众视角之间的差异性张力,支撑起一个荒谬世界里“帅克”式的虚构叙事,在1990年代中国文学叙事突围的大背景下,从“新写实”“新历史”叙事中脱颖而出;《空山》的大叙事梦想,得益于“民族秘史”的启示,有着《白鹿原》般的构造梦想,在荒唐岁月与深山密林的对视中,有着起伏不定的复调式叙事,然而以“空山”命名的整部长篇小说(三部曲),实际上又有意对自己的构建梦想进行了解构;《云中记》从大地出发,从山崩地裂的灾难中出发,这是一场远比山火更为彻底的灾难,阿来的叙事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捩,他的思考带动叙事的笔尖从地表向地心延伸,从大地向天空探索,他把云中村置于山神、树神与天神之间,这是他十年沉潜之后,在21世纪向自然主义叙事的致敬,希望在众神之间寻找到人类新的支点,因此采取了多点密集、散点透视的方式,让整个叙事呈现出巴赫金式的众声喧哗的范式,而阿巴的自我救赎与自我塑形,又像是阿来叙事的最后指归,人的精神复活成为要点。
在简单地给予这样的回溯之后,我们大约应该清楚,阿来小说创作与当代叙事有着或契合或对应的关系,但《寻金记》则跳出了这种关系,虽然现在我们只能阅读到上部,但已经可以感觉到某种挑战式的、引领式的叙事构建和《人民文学》所说的“审美的无穷张力”。当代文学的叙事历险或者叙事探索到了《寻金记》似乎可以真的独立出来被讨论了。这里我们必然遭遇另一个维度的缠绕:中国叙事文学的叙事自足性问题。
自新时期注重形式独立价值的中国式“现代主义”兴起,中国当代文学的文本自足历程走过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岁月,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跨越伴随着各种新探索,贴满各种主义标签的实验性作品成果蔚为大观,从马原的叙事圈套到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从新历史主义到新写实文学,既有叙事的觉醒也有内容取向的超越,直到如金澄宇《繁花》之密集意象、双线叙事,李洱《应物兄》之貌似罗列段子与知识实则击破线性叙事的智性张扬,中国当代叙事文学终于在艰难探索中明白了叙事文学所述之“事”不只是事件或故事。经典叙事学其实早已论讫,叙事“话语”乃有叙述(Narrative)、描述(Description)和论述(Argument)、阐述(Exposition)四大基本方式,并且,这四者在叙事文学中“互为对方服务地运行”,而非“叙述以某种方式对论证占有优势”。③当我们今天阅读《寻金记》时,便能欣喜而清楚地看见,叙事文学的涅槃或归真,除了要有被叙述、描述的事件、事象,还须有同等重要的被论述、阐述的事理、事义等智性元素。
这所谓“智性元素”的叙事,在1980年代晚期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等作品中有著闪亮的表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对象性知识叙事,就是将描写对象之有关属性、原理以及内在逻辑予以充分把握之后形成的、带着知识普及意味的审美表达,在文以载道之外,更多的是文以载理、文以传智。《绝望中诞生》中对地球板块漂移说的挑战和怀疑,以及提出崭新的合逻辑的假说,无疑展现了朱苏进对这一领域的学术分歧、流派分野等等的独特理解,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的智性元素并未在创作界和评论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人们瞩目的主要还是该作品活画出的那个科学迷、地球迷的人物形象及其传奇故事。如今,对于阿来的《寻金记》,阅读和批评的关注点是否也会遗漏其具有转捩点意义的智性叙事,忽视乃至无视其人物和故事不仅依赖其旷达不羁的想象和传奇笔法而有着学问和严谨逻辑的支撑?
创作界和批评界的这种漠视、忽视或盲区是否意味着,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旅程有着美学因素大面积遮盖理性因素的偏向,乃至存在着某种“弃智”的缺陷?是什么原因让在《诗经》里就存在的智性叙事变得那么无足轻重?看看那浑朴的《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其间对星象、节气以及生活随月次、岁次而更的日常科学,有着超乎表象的智性理解,而在现代天文历法还没有诞生的先秦,这样的写作并不是简单的游心寓目,在悲叹命运之际,显然渗透着古人对自然和生命的智性理解,但这样一个理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式微甚至断裂了,特别是从宋代以后及至明清,叙事文学在文体细分的演化过程中渐以通俗化的小说为主流,“无奇不传”的故事及其“游心寓目”的娱情功能日益强化,其智性元素和益智功能日趋弱化;迨至踏入最近百余年的“现代性”和“纯文学”途程,叙事文学虽增益了新军(如影视剧作、报告文学等),其叙事内容和功能却更加窄化,越来越重故事、崇想象、贵经验、主审美、尚娱乐,而将曾经强调的具有教化、识物等功能的智性元素基本上逐出了叙事的伊甸园。这样的“做减法”走势,把叙事文学导入了“漫长的停滞、衰退、缩减、逆变”④的狭路,并“由此形成了我们时代文学最严重的一个问题”⑤。
所幸的是,近年来学界和创作界对这种狭隘的“纯文学”现象和觀念已有反思和反拨,杨义、董乃斌、李怡、陈伯海等学者返本开新地重提“大文学”观并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南方文坛》《当代文坛》《名作欣赏》等文学批评重镇更多次专题研讨了叙事文学表述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创作上则涌现了一批饱含对象性知识的杰作,如麦家《解密》、李洱《应物兄》、王安忆《考工记》、李敬泽《青鸟故事集》、刘慈欣《三体》、徐皓峰《刀背藏身》等,显示出“将被遮蔽和边缘化了的‘知识’重新纳入到文学叙事的角力场”⑥的态势。
此时,我们看到了《寻金记》。但它又与以上作品有所不同,阿来对智性的理解显然不是限定在具体知识或门类学科上,而是一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范畴,甚至如我在前文所提到的最高理性之哲学上,他将现代中国人对财富、生命以及自然神的认识、观念做了一次统摄性的观照,并精心设置了一个维特根斯坦似的“自我毁灭的试验场”,以暗含的希望之不确定性,重启了他对这个民族本性的思索与拷问,对其形成此种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有所观照。阿来在这部作品中有一种对《云中记》之灵魂归宿的延伸性探索,从精神领域重回世俗人间,以深入世俗大地的姿态而仰望哲学的天空。
为了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阿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切片里,构筑了一个丰富的立体空间:以无量河为界、围绕无量山区形成一个笼型的闭合场域。在这个场域内,以一块大金子作为核心线索,穿起了一系列人物的出场与退场(死亡),将一块金子化身为一个能够产生聚合效应的核心,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格雷马斯的“符号的矩阵”,一场有关丢失的大金子的逃离与追杀、隐藏与寻找的大戏,在一个“共时”状态下,以平行蒙太奇的方法被阿来一一展现。
这个场域是一个便于结构的设计,但困难在于,在这个符号矩阵里如何体现其力度的平衡与彼此发生关联和牵制。因为在叙事学里,共时态的困境在于如何与历时发生关系,早期结构主义理论认定共时才有意义而变化没有价值。但没有变化即没有故事、遭遇,也没有力量博弈,情节的发展就被削弱,这显然将文学视为一种静态的并置艺术,又与写作和阅读的历时状态(甚至是线性推进状态)发生冲突。这里,阿来以巧妙的“词典”或“词条”的形式,将人物的轮换叙事设定为整部叙事的推动力,这里的“人物”概念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小说人物”的单一性规定,金伕子、兵士、法王、土匪以及其他各色人等,都具有多重的功效,他们不仅仅是阿来要描写的“人物形象”,还是具有“符号学”意义的结构单体,其轮换叙事也意味着视点的飘移和转换。“它们”是彼此冲突、彼此抵消、彼此依赖的元素,一个单体与另一个单体的关系,以共时存在为起始,聚合在大金子周围,又可能以此消彼长(你死我活)为结束,一些单体从大金子这个聚合体身边永远退出,从聚合过度到耗散。在这个过程中,阿来的“小说人物”由此诞生——他们彼此合作又彼此欺骗,其人性的贪婪与寡情、亡命与艰辛,最后演成无情的利用、占有甚至杀戮。因人物的生死与逃亡、叙述人视点不断的转换,共时性的空间屏障才得以刺穿,平行的叙事轨迹最后都交织在一起,编织成了完整的叙事。
在这些单体之上,有两个恒在的元素像支柱一样维持了整个结构的稳定,一个当然是大金子,它冷漠、高傲,有着无穷的魅力,所有的悲喜剧因它的出现而轮番上演,它有着巨大的财富价值,同时又是一个无言的角色,在它被交换与兑现之前,只是一个彻底的被动体、一个毫无生命的自在的矿物质,但一旦与人群的欲望和梦想结合,就不但是事件的核心,同时又是所有人的灵魂,还反过来左右着他们的命运;另一个是几乎无处不在的刘调查员。准备去前线抗战的他,受命来到这偏僻之地,不期然地和大金子遭遇。他手握重兵高高在上,比大金子还要冷漠,比山林还要广阔,所有的人物都有始有终、有生有死,唯他来去无影、无始无终。这样一个“情比金坚”的狠角色,成为统观整个黄金事件的“上帝之眼”,是故事起承转合的关键人物。如果我们把整个叙事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桔子的话,那些聚合在大金子周围的各色人等的生命线条,就是一个个桔子瓣,大金子则是桔梗,刘调查员是包裹这桔子的桔子皮,有桔皮的圆融、包裹性,又自我成型首尾不分,是一个浑然的“在者”和最高围猎人,决定着整个桔子的成色与皮相,甚至只有他才能感受这急促而危险的生命的呼吸、外界的流风与骤雨,正是他把抗战大叙事带入这个大山深处的生死场,在那些生死追逐、以本能驱动行动的乌合之众面前,让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有了至高的合法性和权威的阐释权。
在《寻金记》里,阿来营造出的这个急迫而传奇的叙事情景,意味着他开始了一种新的叙事突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理性叙事的悄然诞生。
具体说来,阿来在三个彼此呼应和关联的层次里完成了他的叙事的丰富性与重大转捩。
第一,在这个貌似古典传奇的故事里,注入明确的现代理性知识,使一个藏匿与追逐的故事,有了智性的根底而理性化,冷静而收敛的笔调形成了一种文学的新风范,在丛林世界里闪现着义利取舍背后的哲学思考。
小说题材具有天然的西部复杂社会的奇异性和边沿性,那是一个聚集了山林河谷、荒漠甘泉、芳卉毒草、飞禽走兽的奇幻地界,这里像世界边沿又像他们的世界中心,更聚集了来历各异、信仰不同、习性难合的一群人,像聚光灯下的演员又像跟着剧情奔跑的观众,这样一个故事丰满、人物复杂的题材,就算是简单叙写也会成为一部充满传奇的诡谲画卷,其色彩的丰富与奇幻,故事本身的魅力亦可在阿来自己的小说序列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但这尚不足以达成他本来的目的,因此对对象的社会学与哲学性升华就成为必然。
随着大金子的不断倒手,在它流转与迁徙之中,阿来让我们在欣赏其奇诡情节之外,不断遭遇一系列观念性的命题:财富之于个人的意义、黄金之于生命的价值、信仰与财富的权衡、人对物化的抗拒,等等。当一夜暴富、飞来横财成为国人的普遍追求时,对观念的追究显得尤其重要,“人为财死”这古老而笼统的经验,被阿来分解为不同模态的死亡与偷生,旨在告诫人们,他们各自领受的结局来源于各自预支的行为。这不是因果而是人类自身无法突破的牢笼,因而一切的努力都可能是一场自我毁灭的试验。
金伕子吳树林的目的在于讨三房老婆买几十亩地,这大约是传统里普通百姓普遍又执著的梦想,财富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直白简单,而哨兵赵兴旺则一直被自己的运气激励着,所以最初的赵兴旺并不想因此而杀人,还有些微的“行己有耻”的文明意识,在与吴树林的对比中,赵兴旺有更为辽远的梦想和尚不明了的规划,以至于在被追捕中还手下留情不杀追兵,甚至居然可以和汉人村的小嫂嫂春宵一度,且见仁见义,毫不吝啬地给了她金粉、金屑,这春宵一度还差一点成为他未来生活的目标,在怀揣梦想之余有着随遇而安的苟且。他好像是第一个认为金子不过是身外之物的人,和吴树林的简单占有截然不同,甚至对大金子还有着审美的趣味和浪漫的情怀。
法王则认为他代表着神的权威,金子是神的馈赠,所以他必须出手也理所当然。在他的意识里,大金子只属于这片山谷。但正如他感叹的一样,末法时代已经来临,神山即将被掏空。法王一心护佑的并非真正的山的宝藏而是他作为法王的权威,夺回金子或者阻止金子出山,都和神的权威以及他自己的权威有关。但是,阿来从法王角度展开叙写的是,既然是末法时代,一个法王的权威还有什么可以维护的?就像改土归流后,扎西这个千户最后只能沦为山上的土匪一样,他既不能庇护众人也不能保全自己——神权和族权皆已走到末路,他们不过是想借大金子来起死回生,挽留已经远去的威权以及威权下的纲常伦理,回到各自的掌控之中而已。
老丁和阿香经营着古老的黑店营生,他们共同生活且建立起看似相同的财富梦想,妄想着不劳而获天降巨宝,而且是在轮回的套中坚持着这个和打家劫舍并无多少区别的营生。阿香和她前一个死鬼在民国7年就守在这里,老丁出现后,死鬼被老丁干掉,现在和老丁又重复着昨天的剧情……当他们迎来机会之后,同样会经历欲望的煎熬、情理的博弈甚至你死我活的较量,非常手段加江湖道义,让他们得以平和分手各赴黄泉,正如那块被解开的巨大金快。这是阿来在“皆为利往”的时代给了江湖最后的一点脸面。
至于追风马这个从懵懂少年而误入草莽的“土匪”探子,他足智多谋、奔跑如风又经历丰富,他唯一的希望和软肋都是那遥远的故乡和可能已不在人世的母亲,因此阿来给了他历经暗黑苦修屋、无边大莽原的逃离路程,他像一个悬浮的灵魂、无根的种子,总在路上“追风”,得到大金子后他依然像一阵风吹向无可确定的故乡,然后在回家的路上迷失。追风马可能是这群边沿人中的尤其边沿者,正如扎西之前讽刺他“一个土匪居然想着回家”。但是阿来想告诉我们的是“归宿”这个巨大的存在,在不能归去的路上,我们多次迷失。与追风马搭档的是林中犬,这个显然比追风马阴险的家伙,是另外一种人:他虽然面目模糊、身材短小,但在那片密林和山野里能够如鱼得水,靠的是道行和胆量以及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因此作为扎西匪帮的资深密探,他心无杂念、目标明确,当追风马的障眼法几乎骗过所有人的时候,只有他能够察辨细节和风向而果断上路。他的追问是:为什么追风马可以获得大金子而不是我?这是他上路的动力,也是大金子启动的人性恶之一。当他拉着阿香的尸体作为掩护穿越无量山之后,我们更清楚,他善变多疑又利用同道的决绝,显然成为了暂时的赢家,但他尚有不知的是,唯其如此,他将踏入更加迷幻的又一张大网,那无处不在的袍哥堂口正在等着他……这是他越陷越深的人生迷局。
从低级的需求到占有的狂欢,阿来在这个“符号的矩阵”里灌注的理性思考跃升为哲学的追索:所有可能被文学描述的传奇都不是虚空里的迷人云彩,而是应该被纳入俗世的认知环境。当水在漫漶时,谁也无法确定它的性状和形状,只有在一个杯子或其他容器里,被科学分析后才可以得到定性,同样,人的欲望、梦想、生死命数等等只有在社会学眼光的观照之下,才能被认知、被理解。神秘主义不再是奇幻世界唯一的解释,它有着固有的理性路径,而文学则以审美的方式将这个路径铺展开来。康德在18世纪提出形而上学是否成为可能的问题,在更为宽泛的理解里,也就是提出了人文学是否科学的命题,实际上是向整个人类提出了人文学一任自我阐释而不纳入科学认知的后果,可能就是导致人文学长期止步不前或自我重复,根本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在审美狂欢之余,我们面对《寻金记》这样的文本,应当感受到一种哲学的穿刺:我们需要重新修正与世界的关系,必须回到科学地认知世界的路上。
第二,是否存在着宿命的因果,是否存在必须以生命换取生活的通则?阿来带着强烈的质疑和不确定的态度为我们描写了一系列偶然或必然的死亡,这大约可以当成是阿来与读者、也即审美受体之间的一种互动,那些惊心动魄又离奇怪诞的死亡,在叙述里被冷静地处理成“在者”的退场,并形成视点的转换,整部作品则以流动视点的方式,推出了系列人物形象,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多地更多地包容读者面临的有关生死的追问。这是叙述者对读者智性期待的满足。
吴树林是大金子的第一个发现者,也是被“魔咒”加诸其身的第一人,意味着在这大山深处,最基本的财富观以吴树林的摔死而宣告破产,低级需求生发出来的贪婪往往最先被诅咒,这可能就是旧式中国人人争做“人上人”理念的出发点。他时刻提防的赵兴旺没有杀他,但他还是摔下山坡而死于非命。他那可以得到理解的贪欲以终极方式得到解决,这好像是告诫我们,处于低级欲望的层次,其梦想会最先破碎,让我们深度怀疑“一箪食一壶浆,身居陋巷”的现实合理性。富贵之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超越,实在是一个未知数,吴树林不会将大金子看成所谓的资本,仅仅是守着小农经济意识下的女人和土地的概念,想将浮财变成真正的财富而已,但就算如此也得让他以命相拼,和众多拼命的人一样都是“命里没有”的必然结果。但什么是“有”呢?法王应该有么?扎西应该有么?在刘调查员强悍的军力面前,一切该有的大约都不会有了,这是时势和时运交叉作用的结果。
有着“些微”文明意识的赵兴旺,因为一株海棠,因为想确定大金子的重量,被一把斧头砍破脑袋。当阿来以“海棠树与秤”作为赵兴旺生命的最后意象时,就写尽了赵兴旺这样的个体,在审美与实利之间那一点点仅存的心理张力和未来期待,也写清楚了他在汉人村小嫂嫂那里行为的基本逻辑。是的,他本身就像长在蛮荒里的一株海棠。但是,赵兴旺毕竟是一个俗人,因此在他急迫地寻找秤砣的时候,他都快要哭了,他跟所有逐利者一样,为了一个执念而忽略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他看见的秤砣出现时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急切地确认重量——这样,他衡出了大金子也衡出了自己轻飘飘的人生执念和生命重量。
一个被美色和鲜花吸引的逃亡者,能够走出多远?只有像老丁和阿香这样的人,一开始就知道心无旁骛的重要。在阿香的前“死鬼”成为死鬼之前,阿香就明白此生应该安放于何处和此身安放于何处,忍辱苟活和不惜肉身的阿香,以目的论短长、以结果判是非、以利益论高下,有着浪漫情怀的赵兴旺遇见了她,就注定会死于海棠树下。跟所有的目的论者一样,过程或手段之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似乎坚信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一切的死亡都是无足轻重的,客栈像一道江湖的闸门,而他们就守在入口处,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江湖恩怨于他们都是浮云过眼波澜不惊。他们更像两眼发绿的狼,蛰伏在麋鹿们必须经过的路边,等到那致命的一击。如果说大金子的出现于别人都是突如其来的话,阿香和老丁却已经等待得太久了,赵兴旺的出现对他们的来说只是麻木中的唤醒罢了。
但老丁死了,老谋深算的他死于自以为是的骗局,被计中计套走了生命和金子,被寻找归家之路的追风马击断了胸骨,完成了又一幕螳螂与黄雀寓言故事的剧情。阿香使尽解数逃过了无量河,被善追踪辨风向的林中犬捉拿了,两个各怀心思的人组成了逃匿联盟,看起来一切都在逻辑之中,但已经逃离出去的阿香突然提出回到客栈挖取银元之后,这个彪悍而清醒的剪径者就堕入了反逻辑的圈套。一个可以呼风唤雨且拥有大金子的分舵舵主竟然为了几块银元而送命,这么荒唐的“不舍”小利的行为,是自我失败试验场最典型的模型,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小妇人之宿命,前死鬼和现死鬼都没有让她得到应有的升华,她那黝黑的脸和洁白如玉的身体,恰好像一个象征的喻体,让她自我分裂了。直到她彻底死去,那尸首竟成了林中犬通关的工具,一路散发着臭气……阿来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如果科学地看待,生命其实就像一个行进的火车,它只能沿着固有的铁轨前行,路径和终点早就注定,这不是宿命,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它尽管可以花样翻新或者丰富多彩,但那又怎样?当我们看到阿香忍着剧痛的求生哀鸣时,是不是对此有更为深刻的领悟呢?林中犬就这样载着阿香的尸体和大金子走出无量山,但是我们一定知道,他是朝着更深的陷阱滑落,下部一定更为精彩。
第三,阿来一改之前抒情性极浓的叙事风格,《寻金记》表现出独特的冷漠叙述,情感取向以及心底波澜被很好地隐藏起来,我们再也看不見《尘埃落定》里那家园情怀或天地旷达的浪漫,也找不到《云中记》里苦修一般的自我激励,这大约是以叙事的冷峻来表达一块黄金对人类的嘲笑——金钱和财富本来无罪,但占有者或者使用者各自不同的居心投射,让金钱脏污并获得恶名。天底下似乎所有的罪恶都有金钱的影子,所有肮脏的交易都以金钱来完成,但金钱无法自我申辩,阿来就写出黄金不能自我兑换的本质,它还是一块矿物质时,就被一群灵长类动物搬来搬去,并砸死一个又一个搬弄它的人,它隐含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确认。
刘调查员在抗战这个民族大叙事背景下卷入这场恶斗,正如前文提到的一样,他是“上帝之眼”,是唯一可以确证其价值的人,他因为有某种合法性身份和强大的军力而在这场争斗中游刃有余,并借机除掉了扎西匪帮,收拾了令人头疼的法王势力,他个人的冷峻与“无情”以及铁板一般坚定的意志,使他像一架行走的机器,轧过这片山水。这是一种现代秩序的体现,也是川西地区权力倾轧、刘军长一支独大后社会荒漠化的表现,归化、大一统、大局或者刘家天下这样的概念被印在苍白的历史天宇,任何一个走近这段历史的人都不能不异常冷静和万分小心。这不是麦琪家广袤的罂粟园开满诱人的鲜花,也不是云中村白云飘飘的高标祥和,这是一段生命不断被抛掷的历史,因此,阿来是这场野蛮狂放的追逐中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同时精确地释放出关于生命和财富、自然与人文的信息,这冷静叙述的背后是一个求真的科学头脑,这是他叙事丰富性的表现,也预示着他叙事转捩的可能。但我更愿意这样理解,与其说这是阿来叙事风格的转捩,不如说这是他回归事实叙述的表现,去掉了早期某种情怀的干扰,去掉了过于浓密的情感宣泄,他通过《寻金记》找到了世界的内核。一切皆有可能,一切有待时日。
注释:
①《人民文学》编辑部:《卷首》,《人民文学》2022年第1期。
②《小说选刊》编辑部:《卷首》,《小说选刊》2022年第2期。
③〔美〕西摩·查特曼:《术语评论:小说与电影的叙事修辞学》,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④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⑤《南方文坛》编辑部:《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叙事文学——第九届“今日批评家”论坛纪要》,《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文学研究范式转型与‘中国形象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ZW142)
责任编辑:赵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