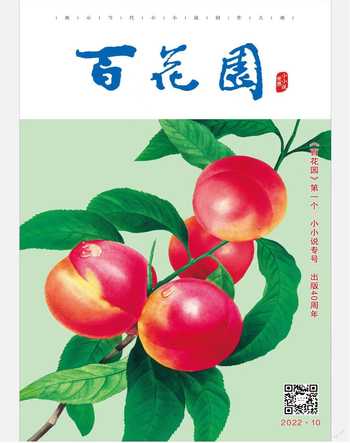文字神圣
张港
地球上,没有语言的民族是不存在的,但是,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文字,这些民族在借用别人的文字。即使是现有的通行文字,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起源的变种。
文字真的神圣。
仓颉造出了文字,“天雨粟,鬼夜哭”。这肯定是神话,但能够流传千年,显然是由于文字的神圣感。过去有“惜字会”,这是文人的组织,每到年终,要将一年内写过字的纸张集中到孔庙中焚烧。写过字的纸,不能随便扔进纸篓,更不可当废品卖掉或擦屁股。纸上有了文字,就不再是普通的纸,就与神灵有关,就得还给神灵。杜甫说“下笔如有神”,说明他写作时是感知着神的存在的。
小小说限定1500字左右,这本身就是对文字神圣的最好诠释,就是提醒写作的人,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珍惜笔墨,淘洗语言。
“淘洗”,可用于沙里淘金,也是由生米到熟饭的必需环节。小小说的文字也需要反复淘洗。
“用手拿起一根粗粗的木棍子,然后再用脚踹开门。”这是某作家的真实文字。明显写了好多废字,浪费文字不说,还把紧张的场面弄松懈了。要是放在小小说里,就得改成“操起棍子,踹开门”,字要少,要用短句,营造出紧张的气氛。
鲁迅曾说,“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宁可把长篇改成中篇,把中篇改成短篇。
我的小小说《海布楞》,写到老安代盼望儿子回来,先写的是“一年又一年”,觉得太普通太没个性,就改成“雁来雁去”。可是雁可以引发多种联想,容易将读者带到偏处,又改成了“草青草黄”,以表达年岁的流逝。“草青草黄”,有了草味,是草原的生活。可是又觉不够,“草青草黄”,由青变黄,是从希望到失望,而老安代是怀有希望的,于是改为“草黄草青”,这是由失望到希望,这四个字才算定下来。这样的修改炼字,给读者的感觉极其微小,但却影响着阅读。“潜移默化”就这个意思。
老师引导:“月亮像不像大大的玉盘?”学生问:“老师,玉盘啥样子?”其实老师也没有见过玉盘。老师读到“鬼子像杀猪一样号叫……”上海学生没有听过猪被杀的号叫,连真的猪都没看过。老师是跟着参考书说的,这样的比喻可以称之“滥喻”。所有的比喻全是因为无奈,最恰当的比喻也不是事物的本质。使用比喻,是文学的重要手段,可是得小心。

我的《村名就叫贼拉犟》,村人初见下放来的老教授的眼镜,这个眼镜片的厚应该怎样形容呢?我先是写了个比喻——“像啤酒瓶子底”,可是一想,当年的乡下人极少接触瓶装啤酒,这样比喻不行。想来想去,最后写“嗬——这眼镜子,上秤盘子,得有半斤”。这才松了口气,感觉这是符合人物的,是有个性的。
用成語是学生的必修本事。可是真的写小说,就得少用,因为成语“放之四海而皆准”,人人可用,处处可用,已经不是针对特定语境的“那一个”。
“遍体鳞伤”,可用,但不具体,最好写哪个部位什么样子:鼻子什么样,嘴巴什么样,左脸、右脸、头发等,一一写来。“鸟语花香”,哪种鸟在叫?什么花香着?成语并没有给出来。“天高云淡”,是抽象的,不如具体地描写。用成语,省事,省字,似乎是写小小说的法宝,可是,我极少用成语。
小小说有时是要“啰唆”的——这简直是反着来,但这恰恰是炼字。
“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看似重复,实是妙笔。
东北过年,孩子能得到叫“磕头了”的小蜡烛。《磕头了》中,“我”将宝贝“磕头了”藏在炕头席子下。胖婶来了,一屁股坐上炕头。胖婶一句一喘,对奶奶说:“我呢……昨天……买了呢……两个萝卜。一个红的,还有一个呢,是青的。一个红的,一个青的。红的呢,包馅儿;青的呢,做汤。喀,喀!——大夫说了,让少说话,说多了伤肺。——我呢,买那两个萝卜,红的大,青的小,其实呢,也差不多少……”
胖婶的话无味而絮烦。用大量文字记下这些,看似浪费笔墨,其实,正写出了孩子担忧小蜡烛被坐扁坐弯的急切心情。这不是废笔。
《狗铃儿》中,“老蹦子”说话,每句只蹦一个字,可是学习发言时,却蹦出两个字,队长表扬他了。队长只有一句台词,是次要角色,即使这样,他的话也得有个性。
队长说:“啊——这个啊——这个老蹦子,发了一个言,发得……很好。还要努上一个力,继上一个续,提上一个高。”
队长的话其实有语病,可是,用于当年的农村队长,却是恰当。
文字是语言的高级层次。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语不惊人死不休。
赵树理等作家自称“山药蛋派”。这么说,是为了突出自然、质朴、通俗的文风,绝非山炮、老土。有一回,赵树理来了兴致,对同事说:“哪位能将我老赵的小说改动仨字,就请吃烤鸭。”就冲烤鸭,说什么也得改他三五个字,“的”“了”总有可改的吧。可是,同事们爱烤鸭更爱真理,一个字也没改——动哪一字都不舒坦。
中学语文一度盛行“扩写训练”:拿来古人、名人的作品,扩而大之。这是最坑人的教学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被扩写成“一轮白日依山尽,滔滔黄河入海流。欲穷明察千里目,更上鹳雀一层楼。”如果这样好,王之涣咋不这么写?难道非让中学生超过王之涣?糟蹋名作,害了学子。狗尾草续貂,毛都不是。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有人以为,把话说明白就行了,以此认定写作并非难事。其实,孔子的“达”,是恰到好处,不长不短,不滞不涩不矫情,不干涸也不泛滥。如宋玉笔下的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辞达而已矣,行文的基本要求,难啊!
写作是心灵难得的独立时光,现代的我们,灵魂被各种各样的不自主支配着,然而,完成一篇好文章,独自端详自己摁键盘的十指,感觉心里甜甜的,然后关上台灯睡觉,梦很美很实。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