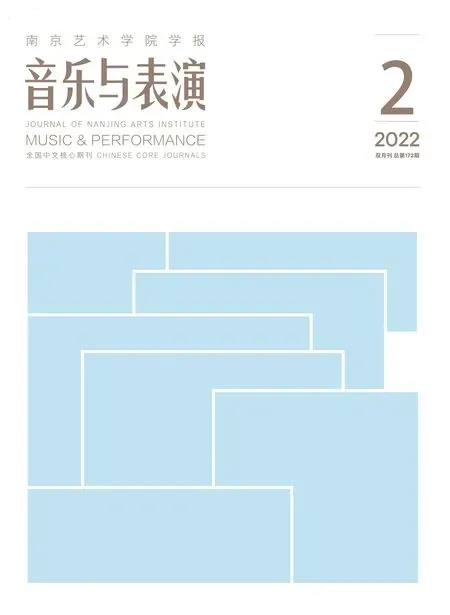音乐、记忆与文化认同
—— 白马藏族地域性“朝盖”乐舞研究
武 斌(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01)

一、自然人文语境中形成的文化认同
任何少数民族的音乐文化都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可知历史文化背景对于族群音乐文化及民俗活动的重要性,据相关文献记载:“少数民族音乐都是以民俗、信仰为基础,脱离了民俗、信仰则很难把这类音乐的意义说清楚;少数民族音乐的这种特点,以及学术上的线索也是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切入对少数民族地区音乐研究的前提。”因此,白马藏族“朝盖”祭祀乐舞活动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地域性族群民俗文化认同的基础。
(一)生态环境下的“共融”
现如今白马藏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铁楼乡和石鸡坝乡,人口大约为2 万余人,以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为主。该地域的水资源非常丰富,并同属于地域性水域之内。在这片聚居区内气候以亚热带山地湿润季风气候为主。冬季长夏季短,昼暖夜凉,昼夜温差大,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春秋温良,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干、湿雨季分明。虽然三地之间都被高山峻岭、纵横河流所阻隔,但是彼此相对临近的地域使得他们依然保持着持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交流与融合。通过查阅地方志资料以及笔者实地的田野考察,可知聚居在两省三地的白马藏族拥有相似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存空间(如图1),这些基础条件为白马藏族形成地域性认同观念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如在“朝盖”祭祀乐舞中多数诵经音乐段末尾音呈三度下滑特征,体现了高山峡谷、河流交错的地域性生态环境对白马藏族乐舞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在“北盖”具体唱诵经文内容中,可知多数关于敬奉和祭祀山川河流、土地等诸神灵的祭文出现在祭祀活动里,如《恭请四面八方神灵》《水神如意经》等。特殊的自然环境促使白马藏族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信仰体系,山川、河流、土地、日、月等内容都为族群的崇拜对象,并最终形成了地域性族群的统一音乐文化认同观念。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C. Kluckholn)所说:“人类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正是这一过程的历史凝聚。”

图1.白马藏族聚居区域分布图
(二)历史渊源中的认同记忆
由于任何族群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变迁,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制度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可知社会历史发展轨迹对族群认同记忆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白马藏族历史以来主要生活在我国的川甘交界处,各地域白马村寨拥有着共同的政治与历史沿革渊源。此地域历史以来就是他们共同的聚居区域,据历史文献记载,汉代以来此区域就已设立氐道管辖(陇西郡的氐道、广汉郡的刚氐道、甸氐道、蜀郡的湔氐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县氐豪杨氏建立仇池国并继续发展。唐朝吐蕃东进以后,此地域就逐步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从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以来,一直到1956 年民主改革,总计长达700 多年的时间里,此地域长期受到土司制度的管辖及影响。可谓是经过我国民主改革以后,白马藏族地区才逐步走向现代化进程。白马藏族聚居区域不仅处在我国地势第一、二阶梯的过渡和农牧交界地带(生态较为脆弱的地区),更是处在我国藏汉文化相互交融和影响的交界区域。这些自然地理因素及历史文化因素等共同构筑了一个既有地域、族群独特个性,又具多元色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族群历史渊源深刻地影响着白马藏族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例如在地域性“朝盖”祭祀乐舞中包含有关于部落战争、族群迁徙、集体狩猎、日常生活等历史场景内容,正是这些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筑造了白马藏族地域性的认同记忆。
二、族群信仰体系中的文化认同
“由于岷江上游地区存活着丰富的民俗信仰文化,包括神话传说、民间传说等,丰富的文化成为理解该区域音乐观念的重要基础和线索。‘把音乐放在文化中研究’的意图在于如何在文化中理解音乐。也就是说,只有对于习俗、信仰、神话、传说等文化内涵有着深入认识和理解,才可能找到理解这一地区音乐观念的钥匙。”内在宗教理念(文化内涵)往往蕴含在外在表象宗教行为之下,这一切所谓的内在“象征性”“符号化”的行为表现会以具体化的形象性艺术呈现出来,例如语言→诵经音乐、肢体动作→祭祀舞蹈等。白马藏族一直以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为主,其中地域性最为殊胜的“朝盖”祭祀乐舞蕴含着族群共同的宗教信仰体系观念,可知族群宗教信仰体系观念是该文化认同的核心部分。
(一)关于“自然”的崇拜理念


(二)关于庙宇神与家神崇拜的认同理念
在白马藏族地区,原来每个村寨都有神庙,供奉着本村寨的保护神、山神、土地神、祖先神等神灵。白马藏族的神庙结构较为古朴,建筑主体多以木梁、青瓦、土堆砖块搭建而成,诸神灵像都为木案绘制并置于神庙土台中央供奉。现如今,只有甘肃文县和四川九寨沟县中多数白马村寨有神庙,而平武白马藏族乡中神庙已随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平武县的白马藏族曾在白马乡火溪沟与羊同河交汇处的山峰下建一座神庙(这座神山为“白马老爷”),之后毁于自然灾害。
在白马藏族神庙中供奉的共同神灵有部族英雄“白马老爷”,据白马藏族民间文献记载:“白马老爷是个神仙,他要从文县赶到四川峨眉山去参加神仙聚会……当他路过白马山寨时,突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崩地裂,房屋倒塌,人畜死伤严重。面对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白马人哭天喊地,但又无可奈何。白马老爷见状,立刻停下来做法术,与恶魔风雨雷电搏斗,直至天亮,使白马寨得免灭顶之灾。但天亮之后,白马老爷由于错过了神行走的时辰,无法前行,就化作一股云烟不见了。眨眼间一座山峰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白马人都说这就是白马老爷的化身。白马老爷就日夜守护着白马山寨,保佑白马人生活健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远近的白马人都要敬白马老爷,从古沿袭至今。”作为白马藏族共同信仰的“白马老爷”,不仅使“白马老爷”形态固化为有形的山峰,还以万物有灵的“灵魂”观念使“白马老爷”聚化为白马藏族部落的守护神。这些庙宇神的崇拜不仅有本土地区的神灵,也汇聚了汉藏文化的宗教神灵信仰。现如今九寨沟县和文县地区的白马寨村落依然保留了敬奉庙宇神的文化形态,并逐步形成了“庙宇”固化信仰内容的文化认同感。虽然平武白马藏族乡已无神庙,但仍以自然形式山神等崇拜守护着“白马老爷”的族群信仰体系文化认同。这种“自然”与“非自然”的信仰形式和内容共同守护着白马藏族对于“白马老爷”的信奉,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敬奉和供养神灵,都是白马藏族对内心深处情感的“释放”与“表达”。
白马藏族地区各村寨的家庭中,多数会敬供每家自己的保护神。家神的画像一般会以布质或纸质呈现并挂于家中客厅的正中央,下面是一个自设供台。家神主要为族群信奉的山神、祖先、英雄人物等,其中家神画像中也有佛教、道教等神灵的出现。在白马寨各家庭中,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家神画像,尤其是在文县和九寨沟县的白马寨落,由于受汉藏历史文化的长期影响,导致宗教文化信仰多元因素的不断深入和融合。如在白马寨家中的家神画卷中有不同的神灵呈现。家神画卷中记写“班氏门中三代祖宗神位”;中间家神画卷中上方左右两侧记写“月、日”,左侧“月”下方记写“斩妖除邪”,右侧“日”下方记写“逢山开路:王布纳麻、羽水龙王、白马龙王、马谷纳麻、圣母娘娘、番神都山、掌印都山、九天圣母、羊纳麻、根山都山、禅衣纳麻”。卷中靠近中下记写“海平纳麻、衣食纳麻、日就高就、山神都山。”卷中最下方记写“妖”,左侧底角位置画一家神排位,供奉神将军及祖先神。家神画卷下置有一供台,摆放着逝世家族祖先的相片,并有香炉等祭供品。从敬奉内容可知,有汉藏文化相互交融的痕迹,如关于伟人的敬奉、佛祖的敬奉、财神的敬奉等。白马藏族对于这些家神的敬奉和崇拜,不仅显示了本土传统文化的地域根基特色,更体现了在社会历史的不同进程中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亲密性。始终使白马藏族宗教体系文化在扎根于原始地域信仰的基础之上,同时又处于一个相对“流动”的变迁状态,这是符合一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因为任何事物都会处于一个相对“变”与“不变”的发展状态。从白马藏族地域性庙宇神和家神的信仰内容可知,虽然不同地区的信仰方式具有差异性,但是都会以一种“有形”或者“无形”的方式来表达族群对庙宇神和家神的认同感,从“个人→家庭→村寨→部落→地域”的神灵信仰延续形式及进程,再到“地域→部落→村寨→家庭→个人”的回馈过程,整个信仰内容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空间运作体系,使得“三界”(即“天界”“中界”“下界”)形成一个无限“可持续循环”的美好景象和空间场域,最终构建起白马藏族地域性多元的宗教文化信仰认同体系。
三、地域性祭祀乐舞中的音乐认同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赖斯曾经提出:“音乐为以往存在或刚出现的认同现象提供符号性的形态,这种符号性的形态体现音乐的内在结构,常构成认同符号的标志性元素,音乐的时间性可以是认同的一个时序逻辑的符号。此外,音乐自身固有的多重属性 ( 旋律、和声、节奏、音色等) 有着标识多重认同之不同方面的能力。”赖斯还以克里斯·沃特曼的一篇相关理论文章为例,引述了如下观点:音乐对形成认同所做出的贡献与用语言术语表达的文化形态所做的贡献是不同的。他认为,jùjú 的表演,外化约鲁巴人的价值,并带来可感知的形式 (约鲁巴人的音乐带来约鲁巴人的身份认同) ,这种互动的民族精神或“情感”是强烈的、充满活力的、嘈杂的、流动的。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理解可知,在“朝盖”祭祀乐舞的形态结构与文化特征分析中,可以更具体和形象地反映出白马藏族祭祀音乐中的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
(一)乐舞结构与进程中的认同感
在白马藏族地区,各村寨每年举行最为殊胜的祭祀活动为一种“面具舞蹈”,各地区都有不同的名称和称谓,如平武厄哩寨“朝盖”、九寨沟“㑇舞”(即“十二相舞”“挫喔”)和文县铁楼乡“池哥昼”。白马藏族举行祭祀乐舞活动的主要寓意为驱除邪恶、鬼怪,禳灾纳吉,祈求诸神灵的庇佑,实现全寨村民平安吉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等。祭祀乐舞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音乐、舞蹈形式和内容,不仅表现出对历史族群传统文化的回忆和追寻,展现出白马藏族古老的文化内涵和理想信念,更体现远古藏区原始文化的精髓和实质。白马藏族祭祀乐舞活动内容不仅保留了“整体性”的结构框架,还体现了各地域的独特文化元素。不同地区对祭祀乐舞名称的解释和所包含的舞蹈类型也有差异,但整体所表达的含义具有相似性和统一性。乐舞活动所展现的“外表——内隐”性结构和实际具体进程可以体现出族群的外在情感文化体验与内隐性的宗教信仰观念,以及地域性文化认同的“趋向性”。
正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也有所述:“结构是系统保持整体性记忆具有一定功能的内在根据,同时,它又是维持系统的不变量,是系统保持稳定性的主要因素。”通过笔者这些年的持续关注和田野作业可知,分布在两省三地区白马藏族的原始祭祀乐舞活动,虽然祭祀的具体形式、内容和过程等方面有所不同、各具特色,如面具形态、庙堂祭祀、舞蹈种类、祭祀音乐和物品等,但是以宏观的视角审视祭祀活动的全貌,可以看出这些祭祀活动主要以恭请神灵、敬奉神灵、迎送神灵等过程祈求得到诸神灵、祖先的保护和庇佑,通过祭祀乐舞的展现达到驱邪逐恶、禳灾纳吉的目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诉求。地域性“朝盖”祭祀乐舞活动不仅拥有较为相似的祭祀结构、进程和文化内涵,其中乐舞内容更具独特的自我表述与族群文化认同。正是白马藏族通过“朝盖”祭祀乐舞活动中的文化表征象征符号表达、传承了族群的历史记忆观念和地域文化认同感。
(二)祭祀音乐中的文化认同
苯教诵经音乐在“朝盖”祭祀活动中,构筑起了一个神圣的外在音乐空间场域。这些音乐具有无穷的神秘法力和象征意义,每一种音调具有不同的法力,例如敬奉诸神灵和苯教护法神尊、禳灾纳吉、降服妖魔的音调。在这种语境之中的苯教音乐,不仅展示出一种宗教的供养形式,更体现白马藏族对苯教文化的认同。
“朝盖”祭祀音乐已成为白马藏族族群记忆、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各音乐要素在活动中的运用,如音高、时值、节拍、节奏、调式、调性等,构建了一个神灵与凡人沟通的神圣场域。根据苯教文献记载,音乐是一种宗教的供云形式,通过音乐使人们的诉求传达给诸位神灵,使其法力显灵,驱除邪恶,保佑人们平安吉祥。
在白马藏族地区的“朝盖”祭祀乐舞活动中,只有平武厄哩寨和伊瓦岱惹寨的“北盖”唱诵经文(多数为原始苯教祭祀经文内容),九寨沟草地乡和文县铁楼乡的“勒贝”念诵“朝哲”词、祭祀咒语等,唱诵音调相对较少。“北盖”和“勒贝”根据唱诵经文的内容来掌控整个“朝盖”祭祀活动的进程,虽然祭祀音乐的整体特征比较相似,但是各地区所展现的音乐元素也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文化特性,如音乐的律动性方面,平武县的祭祀音调较之于九寨沟和文县更具多样性、流动感;节奏、节拍和速度方面,多数吟诵音调为4 拍子也有散拍子出现;上、下滑音和偏音的出现,在不同的祭祀音调中都有出现,有些是表达区域性总体音乐特征的乐段终音下滑,有些是祭祀不同神灵体系特殊乐音的供云形式等。这些情况的出现,多数与念诵经文文本、语音语调、寨落地理位置、历史社会发展环境等有直接联系,不同的音乐形态特征内蕴含着共同的族群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感。经多次实地考察和分析,平武县“朝盖”祭祀活动中的诵经音乐更具音乐性,九寨沟和文县的祭祀音乐缺乏音乐色彩,相对较为“语言化”。下述内容为白马藏族地域性祭祀活动中诵经音乐的文化认同特征:

村寨 四川平武厄哩、伊瓦岱惹寨 甘肃文县铁楼麦贡山、草河坝寨 九寨沟草地乡上、下草地寨祭祀音乐特征三音音列和四音音列为主,如do、mi、sol,la、do、mi,也出现偏音xi音阶三音音列、四音音列以及五声音阶为主,也有六声音阶的出现,如do、mi、sol,do、mi、la 以及 re、fa、la 这三个音构成。四音音列多数以 do、re、fa、la 这四个音构成。二音列、三音音列和四音音列为主, 如do、re,do、mi、sol,la、do、mi,也出现偏音传统的五声调性为主,总体缺乏调式调性特征音域 小字组g 至小字二组a 之间 小字一组c 至小字二组a 小字一组c 至小字二组e旋法结构 旋律线以波浪式进行为主,平稳式进行次之调式调性 传统的五声调性为主,调式以宫调式、商调式和羽调式居多传统的五声调性为主,总体缺乏调式调性特征旋律线以平稳式进行为主,波浪式次之旋律线以平稳式进行为主,偶见波浪式次之节拍单拍子2/4 拍和3/4 拍为主,还有复拍子4/4 拍、混合拍子5/4拍。多数诵经音乐常以交错拍子的形式进行。散拍、单拍子2/4 拍和3/4 拍为主,还有复拍子4/4 拍散拍、单拍子2/4 拍和3/4 拍为主,还有复拍子4/4 拍多采用均分律动的节奏型;多采用均分律动的节奏型;多采用均分律动的节奏型;节奏型images/BZ_108_501_1495_610_1579.png、images/BZ_108_667_1495_833_1576.png、、、、images/BZ_108_1511_1494_1622_1579.pngimages/BZ_108_890_1495_989_1581.pngimages/BZ_108_1074_1495_1216_1581.pngimages/BZ_108_1308_1493_1419_1587.png、images/BZ_108_1715_1495_1824_1579.png、、images/BZ_108_501_1579_627_1657.pngimages/BZ_108_1074_1574_1267_1668.pngimages/BZ_108_1862_1494_2042_1581.pngimages/BZ_108_2080_1494_2181_1581.png语言 藏语、白马藏语 白马藏语、汉语 白马藏语、汉语押韵 腰脚韵 腰脚韵 腰脚韵特征音型 乐段终音下滑,也常见旋律中上滑音与偏音出现乐段终音下滑,乐句中伴有上滑音 乐段终音下滑,乐句中伴有上滑音

“北盖”以“乐舞”供养的形式敬奉诸神灵和本尊护法、满足诸神灵的各种需求,禳解白马部落的各种祸殃以及不顺,调解三界诸神灵之间的“矛盾”以求化解灾难,这些祈愿不仅为人世间带来祥和圆满、利泽众生,更为最终获得“万物和谐统一”的发展态势和美好生活向往而努力。虽然从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来看“朝盖”为原始苯教遗存,但是通过对祭祀经文的解读可知,祭祀道师——“北盖”也是以另一种修习方式——雍仲苯教密宗,获得吉祥圆满,逐步追求更高境界。“北盖”通过念诵祭祀经文不仅使整个白马村寨获得了诸神灵的保佑和祈福、驱除了种种邪恶和妖魔,也使自身的修行从“意念”上进一步达到“无上乘”的理想境界,不断以“菩提之心”感化周围芸芸众生,为“众生的解脱”而努力践行。地域性的诵经音乐不仅为祭祀活动中“人与神”沟通架起一座桥梁,为祈求诸神灵的保佑敬奉妙音供养,更成为白马藏族原始宗教文化的一个象征符号。
“朝盖”祭祀活动的全部进程,器乐音乐伴随着始终。两省三地区所包含的器乐种类大致相同,平武县白马藏族乡使用扁铃、牛皮鼓、铜锣;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勾县草地乡使用大鼓、铜锣、拨、铜号;文县铁楼乡使用大鼓、铜锣、拨、铙。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乐器以合奏为主,也有独奏等形式,例如乐器合奏为唱诵经文、舞蹈、队伍行进等伴奏;独奏乐器扁铃为舞蹈等伴奏。铿锵有力的节奏、节拍和高亢洪亮的音响效果为祭祀活动增添了神秘的原始宗教音乐色彩和文化元素。这些器乐发出的实际声响不仅代表着族群外在的表征形态,更象征着族群宗教信仰文化的认同理念和情感寄托。
据笔者综合分析,地域性的“朝盖”祭祀活动中所用乐器以打击乐为主,乐器合奏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各项内容,只有九寨沟地区的祭祀活动中加入吹管乐器,带来了不同的音响效果色彩。平武县厄哩寨和伊瓦岱惹寨“北盖”使用的扁铃和牛皮鼓,不仅丰富了祭祀活动场域的音乐元素,更增加了原始苯教的神秘色彩。鼓和扁铃(“镶”)是原始苯教最为主要的乐器,象雄语中“洒拉给西挪”是敲神鼓之意,“洒拉克日岗”是奏神扁铃之意。“北盖”在鼓、扁铃和铜锣的伴奏下,唱诵远古的苯教经文,展现了原始苯教祭祀音乐的魅力。苯教文献记载:“此言‘扁铃’之奏法,铃锤向上演奏时,毁灭一切妖魔敌;铃锤这边演奏时,供祭众神情面高;急促用力演奏时,神鬼八域尽收复;扁铃美妙声响时,侍奉使者心中乐,所有知之使者与,冤孽使者平凶气,悲悯使者欲满心。寂息功业有所成,增长功业有边成,怀柔功业有下成,诛灭功业毁妖魔。”九寨沟草地乡和文县铁楼乡的祭祀鼓为大鼓,与平武县白马藏族乡的牛皮鼓不同,更多的融合了我国传统中原的器乐文化元素。演奏鼓的方法以单击为主,配合其他乐器展现鼓声的洪亮与法力,“在广大无边的方域,有无数的音乐,我以敬请展示它,鼓、铃、螺号、筚旺、笛、球鸣木马孔雀美。此乃美妙音调之供云,能断我和无数众生之习气味障,能积大善大德”。在“朝盖”祭祀活动中,打击乐器的音声贯穿整个祭祀活动,器乐音乐不仅带来了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内容,更提升了整体祭祀活动的有序和系统性,为音乐文化内涵的解读提供重要的表现文本和象征性文化元素。
四、地域性祭祀乐舞中的族群记忆与文化认同
据《宗教学通论新编》文献,吕大吉先生认为“宗教是由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四要素逻辑构成的社会文化体系”。那么可知,两省三地区的“朝盖”“池哥昼”和“㑇舞”祭祀乐舞,不仅是白马藏族原始宗教信仰观念、情感体验、行为、制度,以及审美的外在表象化,也是“人—神—鬼”三者之间相互“沟通”关系的重要方式、桥梁和纽带,更是凝聚族群精神文化真谛的一个象征符号。白马藏族祭祀乐舞活动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元素,这些乐舞中既有反映原始社会时期的万物有灵崇拜、图腾崇拜等,又有奴隶阶级、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发展中所产生的相关内容,这也是白马藏族历史文化独特性的因素。现如今,这些综合的祭祀乐舞文化元素要在同一时空中存在和发展,在表现方式上形成不同“时空”的融合与重叠,不仅展现出白马藏族社会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路径,更体现出了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共生共融性以及对族群记忆与文化的认同性。
(一)关于“原始”生活追忆的认同
白马藏族各村寨每年农历正月举办“朝盖”祭祀乐舞活动,主要为了祈求诸神灵的保佑,最终达到“万物和谐”的精神理念。其中的多数祭祀舞蹈都会展现族群先民的真实原始社会生活和场景,表达了白马藏族不忘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如“啥昼”“池母写勒”“帕贵塞”“日傻期”“麻够池”等乐舞,都从不同生活视角记录族群的历史文化事项。通过族群先民狩猎、战争、生活等场景的不断呈现,会持续增强和巩固白马藏族对本族群历史记忆和社会文化的认同。对于部落战争迁徙、战争场面的模拟,使得祭祀乐舞的内容更具古朴性,“池哥”和寨民通过具体的舞蹈动作与祭祀音乐展现先民的历史文化,是一个真实“活态”的历史场景体现。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白马藏族聚居区域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的中心,各原始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断,随着公元7 世纪,松赞干布在藏区统一各部族建立吐蕃王朝后,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张,逐步占领并控制了白马藏族现今的聚居区域,范围在甘川的岷江、白龙江、白水等流域。由于汉藏两军双方的不断交战,使得该地区族群不断深受战争影响。据《旧唐书》记载:“吐蕃于714 年侵唐临洮军时发兵10 万之众,那么加上家眷和奴仆,人数更多。”如此,数以万计的藏兵和家属、奴仆迁居河陇地区,这实际上是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活动,白龙江流域的藏族无疑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与历史环境造就了白马藏族的独特文化,现如今白马藏族通过祭祀乐舞方式表达对族群历史的追忆与认同,体现祭祀乐舞的传承历史文化与记忆作用。
(二)“万象归心”的诸神灵敬奉
“朝盖”祭祀乐舞中,关于敬奉诸神灵的内容纷繁复杂,文章上述内容涉及祭祀诵经音调、器乐、舞蹈类型等,都是对不同神灵的敬奉和供养。白马藏族以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苯教为主,同时在祭祀活动中也会看到雍仲苯教、佛教、道教等信仰内容。在平武厄哩寨和伊瓦岱惹寨中,“北盖”念诵经文为民间苯教的经书,用乐舞形式与诸神灵进行“沟通”,祈求神灵的庇佑,如《祭祀水神经》等,以不同的音调对诸神灵供养。据文献记载:“对神的献祭亦复如此:去祭献时,人是自然的奴隶,献祭归来,人是自然的主人。因此他已与自然后面的神灵达成和解,恐惧和不安被削弱了,人以祭祀和献祭换来了心理的平衡。”再如:“人世的礼所有的功能,是使传统神圣不可侵犯……使因生底欲求而来的积极冲动得到圣化的作用,就得有条有理,于是人心乃得安慰,乃得精神上的完整……宗教便可以战胜恐惧、失望、灰心等离心力,而使受到了威胁的群体生活得到最有力的重新统协的机会,再接再厉的机会。”通过祭祀乐舞的展演,不仅能够从形式和内容上安抚全寨村民的情感体验需要,满足每一位村民的心灵慰藉,更从“三界”神灵体系中求得众神的保佑,重新构建起现实生活与“神界”统一有序、万物和谐的理想境界。白马藏族借助“朝盖”“池哥昼”等祭祀乐舞,把族群对人世间真、善、丑、恶、美的追求与摒弃,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映了族群文化的内核精神以及对敬奉诸神灵文化的认同感。
(三)共同的信仰——驱逐邪恶
“驱逐邪恶”是祭祀乐舞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祭祀道师通过实施相关的法术,驱除全寨的邪恶与妖魔鬼怪,从而至上而下地净化全寨,在新的一年里实现万物和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如祭祀道师用“巴色”制作的“朵玛”“厄”“藏兜”等祭祀物品,以及使用煨桑的供养形式,把这些模拟带有“晦气”的祭祀物品进行消除,驱除邪恶保佑吉祥平安。“人类不但编织用以调整和规范他们社会生活的复杂风俗网络,而且还编织更大的结构来处理宇宙,支配宇宙的力量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问题,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就是这些结构的基础”,现如今融合了多元文化因素的“朝盖”祭祀乐舞,依存在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之中,让这些民间形成的传统民俗活动紧密地与原始宗教文化理念相结合,促进多元文化思想能够更加深入到白马藏族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理性信念中,起到了对村寨人民行为规范化、系统化和意识形态统一化的理想追求。
(四)生命的传承保护与世间的祝福
在两省三地区的“朝盖”祭祀活动中,祭祀乐舞无论从展演形式,还是内容上来分析,展示了对生命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北盖”会念诵《招福功德经》《招福经》等,同样“勒贝”也念诵吉祥咒语,从而保护自身和村寨人民不被妖魔迫害,向神灵祈福纳吉。恩格斯曾说过:“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和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文县铁楼乡麦贡山“勒贝”——班雪仁在“池哥昼”祭祀乐舞中通过念诵请神、送神等咒语和诸神灵进行“沟通”,请求神灵、祖先、家神保佑世人健康平安、事业顺利等,如念诵的咒语内容为:“保佑村寨人民平平安安,老人身体健康,年轻人事业顺利,孩子好好读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切顺利平安,不好的晦气和邪恶统统远离,村寨人丁兴旺等。”白马藏族通过这些超人间的力量形式——“朝盖”祭祀乐舞,使人们获得了来自身体和精神方面的满足,来达到世间人获得幸福生活的目的。
(五)感恩回向与文化认同

结 语
综上所述,分布在不同区域白马藏族的祭祀乐舞活动在整体结构相对统一的文化框架中,也显示了相对独特的不同风格。首先,根据各地区不同乐舞的展演形式和内容可以看出,白马藏族的历史性信仰观念在祭祀乐舞中起着主导作用。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白马藏族生存区域是汉藏氐羌文化融合和交汇的中心,由此形成了以原始苯教为基础的多元文化信仰,在祭祀乐舞中,可以看到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原始氏族部落的图腾、祖先、家神崇拜,以及融合了雍仲苯教、佛教、道教等神灵体系的综合信仰观念。这些信仰元素以跨越时空的融合方式展现出来,勾勒出一幅族群历史社会发展脉络的文化史实,为白马藏族传统乐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活态历史文本。其次,各地域祭祀音乐的风格色彩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区域性诵经音乐的乐段终音下滑成为白马藏族祭祀音乐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平武地区的祭祀音乐明显带有浓厚的原始苯教色彩,音乐中不仅融合了白马藏族的民间音乐元素,还蕴含有古老藏区的传统音乐色彩;九寨沟和文县地区的祭祀音乐整体旋律性较平武地区弱,缺乏五声调式调性感,具有较强的地区音乐风格特点。多元祭祀音乐的文化因素,不仅构筑起一个神圣的祭祀空间场域,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凝聚成族群的文化象征符号,守护着族群寨落的精神文化真谛。最后,祭祀乐舞内容的多样性,塑造了区域性的族群和历史文化认同感。现如今白马藏族生活在河流纵横交错的高山峡谷之中,虽然,地域和行政区域的划分阻隔了各白马村寨的地缘性交流,但是从各地区祭祀乐舞形式和内容的展演方式看,无论从乐舞的动作、队形、面具、服饰、法器等方面,还是音乐文化的象征意义和内涵,都展现出白马藏族远古生活的村寨风貌,以及祈求诸神灵的护佑、驱逐邪恶,从而达到万物和谐的美好景象。
两省三地区白马藏族的传统艺术民俗活动——“朝盖”“池哥昼”“㑇舞”,不仅是白马藏族每年最为重要和原始的殊胜祭祀活动,更是我国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白马藏族的区域祭祀乐舞事项是一个族群、地域综合文化现象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存在方式和“文本”内容是时间与空间的融合、重叠,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有机结合,它不仅全面、深刻地展现区域祭祀乐舞文化的本质与特点,以及地域性族群的历史记忆与音乐文化认同,更揭示出白马藏族古往今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追求理念和核心价值精神。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传承之路,不断地勇于创新和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必将会永远绽放在这拥有5000 年悠久历史文明的中华民族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