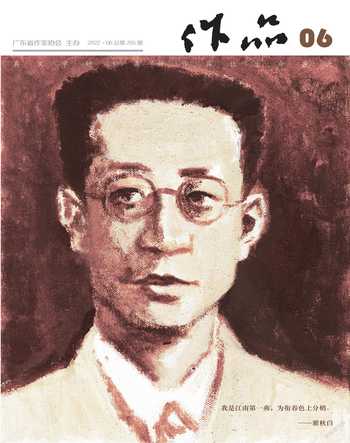高原短篇二题(短篇小说)
墨白
澜沧江畔
下午我们在德钦县汽车站见到旺久的时候,他正撅着屁股修理面包车,他侧身扭头看着我们说,谁?
他说,格桑。
哦……旺久直腰转身,一边去掉满是油腻的手套一边回身看着我们说,去雨崩神瀑,是吗?旺久看我们朝他点头,侧脸看一下头顶的太阳说,今天只能住在尼宗村,明天一早才能去雨崩,有问题吗?旺久看我们点头又说,哦,你们稍等一下,我这就齐。
旺久说完不再理我们,只顾忙活他的。她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他看她一眼说,头还痛吗?她看着他,没说话,但不知怎的她两眼有些发潮。他把手背过去从背包里摸出纸巾来,抽出一片给她一边擦眼一边说,你看你,没过不去的事儿。
她说,往哪儿过?老这样躲藏,什么时候是个头?
他说,那你说怎么办?
她低下头来,不再说话。他抓住她的手,目光却越过山城层层叠叠的建筑物,落在被阳光照亮的山梁上。从山谷里吹过来的风有些凉,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时有汽车的机器声传过来,我们这才注意到旺久已经坐进车里了。
面包车沿着升平镇的坡道往上走,然后又沿着盘山公路往南。旺久一边开车一边推了一下他灰色的礼帽,他看一眼坐在副驾驶的他反问道,飞来寺?在飞来寺可看不到梅里雪山,要转到山坡那边去。
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等从雨崩神瀑回来再去飞来寺吧。
在夏秋多雨的季节,我们果然没有看清被云雾缭绕的卡瓦格博峰,只有最左边的神女峰偶尔在雾纱里显露峥嵘,梅里雪山显得更加神秘。这使我们对前途充满了疑虑,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对我们命运的一种暗示。或许,神圣的卡瓦格博压根就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些身负罪孽的人。
我们心情沉重地沿着修在悬崖峭壁上的214国道往澜沧江的谷底走,希望能早一些到达雨崩神瀑,让神圣的自然之水冲洗我们的丑陋。但我们没有想到,要下到看似近在眼前的澜沧江谷底,还有30公里的路程。旺久一边开车一边嘴里哼着六字真言,峡谷对面的明永冰川偶尔在阳光下对我们闪亮着。在一个岔路口我们掉头往东南走,在接近谷底后,我们又沿着澜沧江左岸的公路往南行,最后在巴久寺前几棵高大的柏树前停下来。旺久打开车门指着其中一棵对我们说,那是卡瓦格博的手杖,当年他插在这里忘了带,后来就长成了这棵树。
在湍急的澜沧江的流水声里,我们惊奇在高原,在这两岸荒凉的峡谷中为何能生长出这么高大的柏树来。在旺久去为我们办理进入明永冰川与雨崩神瀑的门票时,他拉着她围着那棵身上裹满经幡要有几个人才能抱得住的柏树转了一圈。在停下来之后,她心情复杂地看着他,而他充满迷茫的眼睛却看着那棵高大神奇的柏树。她感到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就紧紧地握住。她说,别怕。
他没有说话,也没看她,目光最后移向从远处汹涌而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澜沧江。
过了前面的桥,我们沿着澜沧江右岸的土路来到了永宗村。在叩拜了石锁之后,旺久说,好了,你们已经拿到了朝觐神山的钥匙了。在前往西当村的途中,旺久说,去雨崩神瀑有两条路,一条是从西当村翻山而过,要越过那宗拉卡垭口,另一条是从我们今天住的尼宗村顺着雨崩河往上走。
他说,垭口海拔高吗?
旺久说,3820米。
他回头看了一下坐在后排的她。她说,神瀑海拔呢?
旺久说,3950米。
她看着他说,能上神瀑就能过垭口。
似乎他紧张多日的心情现在有些放松,他说,那就明天回来过垭口。
过了西当村,我们就沿着澜沧江右岸一直往南。路途中,渐渐和我们熟稔的旺久的话就稠起来,他说,你们是怎么认识格桑的?
在丽江。他说,我们乘他的车。
哦,你们从哪儿来?
她看他把目光转向澜沧江说,河南。
哦,很远呢。每年都有各地的人来这里朝觐,有的一路磕长头过来,一走就是几年。
她有些惊讶,要走几年?
是,要走几年,去年就有一个从青海磕长头过来,走了两年,把自己的腿都走瘸了,还是我姑父给他治好的伤。
她有些好奇,你姑父?
对,我姑父。哎……旺久弯下腰来一边系着他散开的鞋带一边说,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姑父是尼宗村的村长,他不但施舍外地的朝觐者,还供养着在村子附近的山洞里修行的人。
他说,那他图什么?
旺久愣了一下,他直起腰来看着我们说,难道别人有困难,我们帮助一下就是为了图什么?他的话仿佛一道篱笆突然从空中落下来横在了我们中间,接下来,旺久嘴里独自哼着六字真言,就不大理睬我们了。在接下来的路途中,他也仿佛变成了哑巴,一言不发。时光在我们的感觉里缓慢地流淌着,就像身边湍急的不知来自何处又流向何方的澜沧江。
那天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尼宗村。但我们并没有见到村长,只有旺久的姑姑在家,屋里还有一个不知来处的穿黄色短褂的僧侣、两个从甘孜来修行的尼姑,她们刚转经回来,正在村长家休整。
在旺久的姑姑准备晚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村里。在村长家门前的路边上,我们看到有一家七口人正在那里搭帐篷,一问,才得知他们是从四川来的朝觐者,在他们身后尽管就是无边的山野,可是他们做起事来仍然悄无声息,唯恐惊动在远处俯视着我们的卡瓦格博山神。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村长才从外边风尘仆仆地回来,同时,他还带回来三个远道而来的朝觐者。
吃过饭后,村长就吩咐旺久安排客人们去休息,一转眼,他就不见了。大家做事的时候,都是那样的悄无声息,心里都各自怀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虔诚。在灰暗的灯光里,一切都显得那样神秘。等我们在旺久的带领下踏着咯咯吱吱作响的楼梯来到阁楼时,在暗淡的光线里,我们看到村长光着背正坐在那里打坐。大家都没敢说话,我们和三个陌生人悄悄在靠墙壁的一边坐下来,众人不论男女睡成一排。在暗淡的光线里,我们看着漆黑的房顶,想着心事儿。他睡不着,就悄悄地起身。她也没睡着,侧身抬头看着他沿着楼梯走下去。片刻,她起身拿起一件衣服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悄悄地来到屋外。在夜色里,她看到他在一块石头上坐着,抬头望着明亮的星斗,神情显得是那样的颓丧。她轻轻地走过去,把手里的衣服给他披上,贴着他坐下来。我们谁都没有说话,寂静的高原无边无际。
夜渐渐地冷起来,她说,回吧,冷了。
他仍然没有说话,她站起来,伸手把他拉了起来。
我们醒来的时候,听到有低声的吟唱声传过来。在晨曦里,他看到村长仍然在那里赤身打坐,只是他的腰间多围了一条被子,他已经在那里坐了一夜了。诵经声是从坐在他对面的那两个身披藏红袈裟的尼姑嘴里发出的。在朦胧的晨曦里,他们就像一组雕像。他发现睡在身边的她不见了,等他悄悄地走下楼梯来到院里,看到她正在看旺久的姑姑煨桑。她对他说,旺久已经起早赶回去了,他下午会在西当等我们。
这让他感到意外。我们走出村长家,看到昨天扎在那里的帐篷已经没有了,那家来朝觐的四川人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住过的地方连张纸片都没有留下,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居住过的痕迹。她转身看着他说,旺久的姑姑说,煨桑是他们每天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
这次他转身专注地看着她说,是吗?
嗯。她看着他说,他们要用桑烟祈求神的下凡。
她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被拥抱的渴望,但他却闭上了眼睛。她从衣兜里掏出湿纸巾来,轻轻地为他擦去了从他的眼角里流出的泪水。
这天上午,村长亲自给我们做了向导。我们发现,同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一样,强烈的紫外线改变了村长皮肤的颜色。我们跟着有着紫红色脸膛的村长,先路过那个环境幽静与世隔绝的雨崩村,最终来到了雨崩神瀑。我们看到雨崩神瀑从悬崖上倾泻而下,在阳光的斜射里升腾。村长来到煨桑台前开始煨桑,当桑烟升起时,村长嘴里一边默诵着祭文,一边绕着插着风马旗的玛尼堆转圈。三匝过后,村长脱下一层上衣,顺着石阶,来到瀑布下开始沐浴。
我们远远地站着,看。她抓着他的手,看着在神瀑下沐浴的村长,喃喃地说,旺久看出你有心事。
他把目光从神瀑下的村长身上收回来看着她。
她说,这瀑布是卡瓦格博神从上天取回的圣水,能消灾免祸。去吧,去洗吧。
她说完,轻轻地为他脱去外衣。
这次他没有拒绝,他顺从地脱去衣裤。在她的注目下,他跟着村长在雨瀑下走动着,他双手举过头顶迎接着从天而降的水流,嘴里发出喔喔的声响。我们知道,藏传佛教的信徒在朝拜梅里雪山之后,作为一种洁净心灵的修炼,必定来到这里沐浴。
他贴着岩壁在水雾里奔跑,围着神瀑转圈,一边转一边喊叫着。这是多少天来她第一次听到他发自肺腑的喊叫,她被感动了,也跟着喊叫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自身的烦恼,和自然融为了一体。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和村长在雨瀑村分手,然后从那里出发,翻过那宗拉卡垭口,前往昨天我们路过的西当村。在西当村那所简陋的温泉招待所门前,他突然注意到门前停放着一辆挂着豫p牌照的越野车。他一看到那个车牌照,就两腿一软坐在了地上。
她伸手抚着他,把他从地上拉起来。
他看着她说,是你干的好事儿?
她没有躲避他的目光,她说,我不想再这样流浪了。
这时,我们看到有两个留平头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招待所门前。看着他们持着警惕的目光朝我们走过来,他的手哆嗦起来,他喃喃地说,这一天终于来了。
那一刻,我们突然感到世界很安静,只有从不远处的澜沧江里流过的江水,发出经久不息的鸣响。
雅鲁藏布江河谷
夜幕降临了,一轮新月悬挂在雅鲁藏布江谷地上空。远远望去,前方被夜空染成深蓝色的南迦巴瓦峰比白天看上去高出了许多。
散去信徒的寺院此时安静下来,只有附近的虫鸣和远处时隐时现的流水声在我们的耳边雾气一样涌动。如果你同我们一起看着窗外通往峡谷的石板路渐渐模糊,也会像我们一样不免焦急。已定的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却因迟迟未归的拉康堪布,使我们制作彩砂坛城的日子一拖再拖。宗科活佛有时会来到已经准备好制作彩砂坛城的木案前,静静地看着我们把粉碎的矿石砂粒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放进不同的白色塑料杯里。尽管活佛面色平和,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他从眉宇之间流露出来的那丝不安。
每到这时,我们就会问活佛,一定要等拉康堪布回来吗?
活佛没说话,但他对我们点了点头。
看着有些驼背的活佛走出房门,我们就忍不住拿起绘制坛城所用的紫铜长条锥形漏斗抚摸着。你想,我们连绘制彩砂坛城时使用的口罩都备好了,可拉康堪布却迟迟未归,这让我们内心的焦急一日胜过一日。
有时,我们会挑起水桶沿着石阶下到江边去,因为那样我们更能接近拉康堪布回归的山路。我们一勺又一勺从湍急的江水里取水,等把水桶注满,可我们仍然不愿离开,我们挺直身子抬头朝山路遥望,渴望着能在山路的尽头看到拉康堪布的身影。
夜幕渐渐降临,虽然我们仍然没有盼来拉康堪布的身影,但脚下湍急的江水却留在了幻觉里,长久地在我们耳边回响。我们坐在窗前,在江水流动的幻觉里突然听出了脚步声,尽管那声音十分轻微,但还是被我们准确地捕捉到了,我们几乎同时喊出,拉康堪布!
我们飞快起身,一边提鞋一边朝门边急走。
在明亮的月亮里,我们果然看到了沿着台阶走来的我们盼望已久的身影。我们快步迎过去,接过他后背上鼓鼓囊囊的帆布包。虽然在夜色里,我们依然感觉到他在经过长途跋涉后流露出的疲惫。
等我们迎来宗科活佛时,铺上的拉康堪布已经发出了节奏分明的鼾声。活佛制止了我们唤醒他的企图,目光最后落到了拉康堪布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上。
我们迫切地说,要不打开看一看?
在活佛的默许下,我们打开了帆布包。除去拉康堪布的一些衣物外,从包里掏出的是一包又一包包裹整齐的植物。活佛读着贴在包裹外边植物的名字,最后亲自动手打开了写着“盖裂木”植物名字的一包。
我们纷纷挤过来,看到包里除去一些枝干和树叶,还有植物的种子。
活佛拿起盖裂木的聚合果,逐个让我们看了一遍说,这个果子里睡着60枚左右的种子,这么多种子组合在一起,像不像我们寺院里的众生?活佛说着晃了晃手中那枚褐色的苞结上带尖的聚合果说,更重要的是,你们看它的形状像什么?
火焰?
对,像燃烧着的火焰。这盖裂木在开花时,花部的温度要比周围的气温高出20摄氏度。
哦,一种神奇的植物。
活佛说,你们要好好地观察,把这个果子的形体用彩砂绘制在坛城中心菩提树的周围。同样……
活佛说着指了一下堆放着的一包一包的植物,在菩提树的四面八方绘制出这些种子的不同形体。从活佛的语气里,我们感受到了他对拉康堪布这次远行收获的赞许。
拉康堪布回来的第二天,在宗科活佛的主持下,我们寺院里举行了简短而庄重的仪式。然后活佛亲自放线,由上下左右和两个对角线切割而成的一个米字,为我们将要绘制的彩砂坛城定位。我们心里都清楚,在南西北东四个方向我们要置放高原落叶乔木的种子,东方是西藏红杉,北方是白栎,西方是高山松,南方是薄片青冈。
拉康堪布打开一包植物对我们说,就是这种青冈,树身高达40米,是我们青藏高原上最高大的树木。你看它的果实,褐色,圆形。这些树木除青冈外,红杉、白栎和高山松都生长在海拔2500米至4000米的高原。特别是红杉……
拉康堪布说着让我们观看,西藏红杉是我们青藏高原特有的植物。
在另外四个方向,我们选择什么种子呢?
雪莲、曲玛孜、绿荣蒿和藏南金钱豹。这些草本植物有的生长在2500米以下的阔叶林里,像绿荣蒿,有的生长在4000米至4800米之间的高山石滩,像曲玛孜。拉康堪布说着又解开一包植物让我们观看,这白色的雪莲,放在西北的位置,西南位置是青色的曲玛孜,东南位置是藏南金钱豹……
拉康堪布又拿起一包植物打开说,这一株藏南金钱豹是我在墨脱境内的山林里采集的,从我们这里往东北方向,然后拐一个几字弯,在雅鲁藏布江的江边。东北位置是绿荣蒿……
拉康堪布又拿起一包植物说,这株绿荣蒿是我在梅里雪山下的明永冰川前采的。绿荣蒿的花有紫色、红色和黄色,但我们要用蓝色的花朵,为什么要用蓝色,你们说说看?
我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上来。
你们出去,看看我们头顶的天空。
我们争相跑出去,当我们抬头看到深蓝色的天空时一下就明白了。
开始制作坛城时,我们把彩砂装进锥形漏斗里,然后使用锉刀在锥形漏斗的齿痕上轻轻地摩擦。只见拉康堪布半跪在宗科活佛画过线的图案中,那支被他使用得光滑锃亮的锥形漏斗握在他的左手里,他用拇指夹着漏斗的顶端用来保持平稳,右手的锉具就在锥形的牙痕上不停地锉摩。我们就这样日夜不间歇地工作。有时我们会听到拉康堪布急促的喘息声,每当那时,他都会停下来,放下手中的锉刀和漏斗,用右手捂着左边的胸口,从他额头上浸出的汗水被日光灯映照得闪闪发亮。我们知道,那一刻,一准是他的心绞痛又犯了。
我们把拉康堪布扶起来,但他推开我们的手说,没事儿。
但我们坚持要给他请藏医来看病,他拦住我们说,真没事儿,我自己知道,就是低压高。
最好到医生那儿用血压计量一量。
拉康堪布说,不用量,低压准在130以上。我的低压一高,头皮就有感觉,一紧一紧的。
那你得吃药。
吃着呢。黄芪、黄精、西洋参外加枸杞子,我每天都泡水喝。真的没事儿,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听他这样说,我们就扶他去休息。可是没过半个小时,拉康堪布又披着衣服过来了。他说,我就是不做,坐在一边也是心静的。
拉康堪布就这样在我们的身边坐下来,看着我们用彩砂绘制坛城。在坛城的最外围,我们要用彩砂绘制出由红蓝绿黄各色组成的火焰圈,以用来阻挡企图侵入神圣洁净法场的不洁之物。火焰圈内的方城,就是由四种落叶乔木和四种草本植物种子的形体组成的八个花瓣构成的圆轮。圆轮的中心,是由蓝色砂粒绘制的由菩提树的花与盖裂木果组成的核心圆。
我们都清楚,我们要用这些植物种子的形体组成诸尊梵文名称的首字母,象征着由722尊佛与菩萨在坛城里聚集,这些种子字具备了佛与菩萨的心要精华,以此生出无上的菩提果,正如植物的种子蕴含了植物全部的生长要素。在真理漫步的地方,我们不停地摩擦手中的锥形漏斗,彩砂像细细的泉水一样通过圆锥尖头上的小孔渐渐流成图案。寂静里,锉刀与锥形漏斗的摩擦就像幻觉里从谷地里流过的潺潺江水,也像寺院后山坡上灌木丛里风经过时枝条摇动的沙沙声。我们不停地把彩砂装进锥形漏斗,让它细细地流出来。我们花费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在时轮金刚灌顶法会来临的头天夜里,完成了彩砂坛城的绘制。
无数的信徒在法会期间,前来参观我们用彩砂绘制的坛城。我们看到拉康堪布每天都跟随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信徒们手摇经筒围绕彩砂坛城转经,他认为这样可以消除一生的罪孽。那埋藏着佛种的坛城,是对我们生命的最终走向圆满的暗示。
在时轮金刚灌顶法会结束这一天,我们精心制作的彩砂坛城,在众多虔诚的目光之下被宗科活佛那双被高原紫外线浸染过的布满皱纹的手毁掉了。由这个神圣仪式所构成的修行过程,让我们从中明白了生命的无常。我们将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世界,并影响我们的一生。
拉康堪布半跪着把我们用来制作坛城的彩砂聚拢在一起,然后装进一个褐色的陶罐里。在寺院通往雅鲁藏布江边的沿途,无数的信徒看到拉康堪布怀抱那个装着彩砂的褐色陶罐,跟在宗科活佛有些驼背的身后,在众僧的拥护下走得脚步蹒跚。
太阳高悬在我们的头顶,远方的南迦巴瓦峰因强烈的阳光在我们的视线里变得有些模糊。
拉康堪布怀抱陶罐立在江边,他让怀中的陶罐慢慢地倾斜,陶罐里的彩砂像一条彩色的细小瀑布流出来,在众多虔诚的目光里随着峡谷吹来的风扬落到江水里。
湍急的江水映射着阳光,又反射到拉康堪布怀中那个倾向雅鲁藏布江水面的陶罐上,像无数破碎的玻璃,在风中刺疼着我们的眼睛。
我们看到,拉康堪布双手把手中的陶罐口朝下举起来,陶罐里最后一丝彩砂随着峡谷里的风在江面上扬起。双手挺举陶罐的拉康堪布就那样站在湍急的江水边,直至他的身躯像一截木桩直挺挺地跌落在江水里。
那一刻,我们没有谁知道在拉康堪布的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突发的心肌梗死还是长久站立由血压的低压升高所引起的眩晕。那一刻,我们看到有无数阳光的碎片从江水里跳跃出来,在我们的幻觉里发出一片无声的尖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