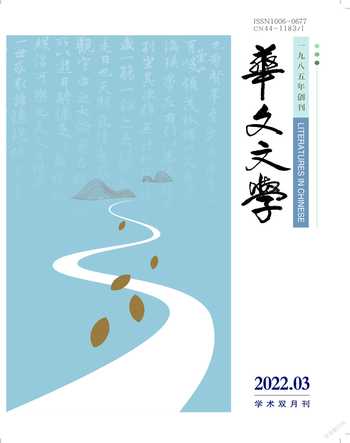宇文所安的征兆诗学与杜诗新诠
胡旻
摘 要:宇文所安于1985年出版著作《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迄今已逾三十载,而学界却仍竞逐其中所谓“非虚构诗学传统”,激论中西诗歌虚实之辨。本文另辟蹊径发掘宇文所安的征兆诗学:中国诗是世界的征兆,诗歌揭示世界之模式。该诗学脱胎于刘勰和刘若愚相关理论,“征兆”关涉气类感通原理,旨在论证诗歌与世界相互感应,“世界之模式”即指中国阴阳观,故诗与世界同构并蕴含二元对比模式。宇文所安据此思路,寻绎杜甫诗歌中“多”/ “一”、“稳定”/ “流动”、“内”/ “外”张力结构,颇具新意。
关键词:宇文所安;征兆诗学;气类感通;阴阳图式;杜诗对比结构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104-07
一、前言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当代美国汉学界久负盛名的批评家,其研究成果一直为汉语学术圈视作可资借鉴之重要参考。若整理写作历程(仅以专书论),可发现其研究方向与旨趣,实有迹可循:早期重点落在唐代诗歌史,代表作是《孟郊和韩愈的诗》(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ü,1975年)、《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1977年)及《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1年)。此后视野则转向广阔的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如宇文所安自述:“近年来我一直将文学史搁在一边,试图精细地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①故此,1985年《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以下简称为《世界的征兆》)之付梓,可视为其学术生涯转轨之重要标识。
自《世界的征兆》一书出版迄今,已逾三十载,学界尤为关注其中所谓“非虚构诗学传统”(以下简称为“非虚构传统”),研究者就此说开展激烈爭辩,有赞同亦有反对。如陈小亮对“非虚构传统”涵义及源流梳理甚为详实,亦指出其不足和局限;李凤亮、周飞则指出宇文所安论述中的种种混淆与错讹。②爬梳前人论述,本文以为,宇文所安“非虚构传统”主张,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想象”两组概念套用于中西诗歌,但强调以读者视角,即中国读者倾向从“真实”与“历史”角度读诗;西方读者则反之,以“虚构”与“想象”为主。孙康宜亦赞同:“宇文所安是在讲读者,讲中国诗‘被读作……’;而持不同意见者却是在讲作者。一方面是说批评方式,一方面是说创作主体,讨论的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③故而,不少论者望文生义为:中国诗歌偏重“真实”与“历史”,而西方诗歌偏重“虚构”与“想象”,分歧与误解因之而生。当张隆溪为“反驳”宇文所安“非虚构传统”,详尽举证中国文学亦含虚构想象元素,④殊不知后者的视角为读者,前者焦点却在诗人创作。
“非虚构传统”固然招惹诸多回响,但此说实无甚高明之处且早已无探讨余地。以中国诠释学传统观之,读者本多偏好“真实”与“历史”,钱谦益《钱注杜诗》更因其“诗史互证”法而扬名杜诗学史,故历代诗歌阐释重史实,本是常理。既为常识,学者或沿波讨源,追索“非虚构传统”之依据,或犯“稻草人谬误”(straw man fallacy),指摘宇文所安扭曲经典,对于整理或借用他山之石,恐怕助益甚微。
回到《世界的征兆》书名,便可发现其中玄机:若学界追逐的“非虚构传统”果真重要如斯,那缘何宇文所安会弃之而采“征兆”(omen)一词?况且该书论及“非虚构传统”议题篇幅占比亦低。故此,本文捻出宇文所安征兆诗学,立为其念兹在兹的核心观点,可简要归纳为:中国诗是世界的征兆(omen of the world):诗歌揭示世界潜在之模式。换言之,诗歌与世界同构,正对应《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此说并非简单强调诗歌与世界之关联,导向“非虚构传统”,而是有其理论渊源、中国宇宙观依据,尤其应关注的是,征兆诗学在运用于诗歌细读时所彰显的启发价值。
二、征兆诗学的理论渊源
就宇文所安实际所论看,其征兆诗学之架构及论述似乎难以称得上周密系统,部分甚至失之零散芜杂(或因宇文氏书写风格)。准此,本文将其主张撮合整理出两大要点:其一,中国诗是世界的征兆。即是说,诗具有预言功能,作为征兆的景物或意象,其含义可由此及彼,见微而知著,延伸开去,如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既是写景,也昭示国势危殆混乱,濒临崩解之状况(因自然与社会人事相感通,容后详述);其二,诗歌亦可显示世界的模式。宇文氏提到:“诗人的意识与诗歌是令潜藏意义和模式显明的手段。”或“诗人的任务是观察世界之秩序,万象纷扰背后的模式。”⑤诗歌或诗人缘何揭示世界的模式?该讲法粗看令人疑惑,实则借鉴与改造了刘勰“文以明道”论及刘若愚文学形上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巧妙利用“文”之多义性:广义之“文”即万物之形状、色彩、声响等属性,即“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⑥;狭义之“文”指文字书写、典章制度等。依此思路,刘氏先是不厌其烦地罗列自然事物或现象:
天之文:“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地之文:“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
动植等之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鍠。”⑦
以上铺陈天、地、动植之形声色,均属于广义之“文”,且为“道之文”即是“道”之显现。同样的逻辑,狭义之“文”,亦为“道”之显现:“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⑧刘勰所言可归结为“文-圣-道”的关系图式。
要言之,《原道》篇主旨追溯“文”之源于“道”:由自然之“文”类推人之“文”,论证二者皆为“道”之显现,便是刘勰“文以明道”论,不过刘氏未就“道”之涵义做清晰解说。
时至当代,汉学家刘若愚重新阐扬此说,将“道”定义为“宇宙原理”,继而提出“形上理论”(metaphysical theories)即主张“文学为宇宙原理之显示”(literature a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并视为中国文学理论之特殊贡献。⑨试归纳并比较三者的说法:
刘勰:文是道的显现。
刘若愚:文学是宇宙原理的显示。
宇文所安:诗歌显示世界的模式。
刘勰所谓“文”泛指万物形状、色彩、声响等性质,亦包括文字书写,但未就“道”做清楚界定。刘若愚因论及文学理论,故将“文”视为“文学”,“道”解释为“宇宙原理”,引申发挥成:文学是宇宙原理的显示。宇文所安则以“诗歌”替换“文学”,将“宇宙原理”更换为“世界的模式”,仅在表述用词略有差异,皆胎息于刘勰“文以明道”论,总体而言异曲同工。不过,刘若愚的形上理论,侧重理论批评(theoretical criticism)层面,缺乏實际运用,宇文所安则踏足实际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将该理论施行于具体诗例。
由上可知,宇文所安征兆诗学,一方面在思路及表述上借用改造刘勰和刘若愚的相关理论,另一方面,宇文氏也对二人之前的某些论述做进一步延伸开拓,如“文”的涵义与功能。诗无疑是“文”之一类,故批评家从“文”之定义切入,实属常见思路。前述刘勰分“文”为广义狭义,即为一例,刘若愚也诠释“文”寓多种涵义:“记号(making)——样式(pattern)——文饰——文化——学问——著作——文学”。⑩
宇文所安则认为“文”的功能在显示秩序与模式:
文,感觉的样式,是某种隐藏秩序的外显。……一切现象透过文而趋于显现,其显现旨在被认识与感觉;只有人心具有认识与感觉自身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文学是外部世界显示的形式。因此,文学成为宇宙显现过程中的完满状态,即充分实现的形式。{11}
先纠中译本错讹,凡原文“aesthetic”,译者皆误解为“美学”。{12}然而该词之基本涵义为“感觉”,何况据其语境,宇文所安引刘勰谈天地之“文”,皆指涉其形、色、声等属性,分明为感觉层面,何来“美学”?再看宇文所安的解释,他援引陆机《文赋》:“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据五臣注:“惟此文之为用,故乃考众妙之理所因而成。”{13}即是说,文之功用在展现众理。宇文氏则将“理”解释为:“诗人认识到内在秩序”,{14}其力证“文”的功能在揭示某种秩序或原理,固然是为征兆诗学所述“诗歌显示世界之模式”张本,但揆度其理论,是不能算曲解。《乐记》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探讨音乐的发生学,可归结为“心-声-音”关系图式,而由“声”到“音”的关键在“文”,正显示由杂乱无章之“声”秩序条理化为“音”之过程。
三、征兆诗学依据的中国宇宙观
(一)“征兆”:气类感通原理
“征兆”原指某事发生前所显示的迹象、端倪或症候。若不纠缠于未来式问题,“征兆”之本质乃关涉两个事物的联系或感应。宇文所安颇为迂回地指出,征兆虽有预言之意,但并非其全部,而是揭示另一事物的方式:
世界是一个浩瀚,不断流变的征兆图,而诗人则是世界征兆读者。正如吉凶之兆向政府显现,揭示出社会状况,诗人同样感知到,世界的征兆是现实的真实秩序。这些征兆并非预言(虽然理解世界运转的人会从中读出将来之事),它们是现时主导结构的潜在标志。{15}
回到中国典籍举例而论,则更易了解。《淮南子·说山》曰:“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16}落叶与瓶冰可视为征兆,二者应和通达季节之嬗变。苏洵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17},以月晕推知风起,由础润推知雨来,见微而知著,不脱感通之理。当然最常见者为政治征兆,如《礼记·中庸》:“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8}灾异祥瑞之征兆可显示国家兴衰。由是可知,“征兆”一词,其背后思路是天人感应或曰气类感通:万物因同气而浑然一体,可相互应和、冥合及交感。故而诗歌亦然,刘熙载《艺概》:“《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19}无论是诗为天地之心或天人之合,抑或宇文所安言“诗歌是世界的征兆”,均旨在论证诗歌与世界之交汇互应,虽表述有异,其揆一也。
此气类感通原理,是理解中国诗学之要诀。情景交融,即视自然景物为内心感受之披露,便为一例。龚鹏程体认到:“感通的原则,正是后世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中国文学基本上是由‘感’形成的:作者感物而动,应物斯感,故有吟咏;作品希望亦能感人。”{20}李约瑟(Joseph Needham)称之为“关联式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21}宇文所安则谓之“感通共鸣”(sympathetic resonance):“作为世界之组成要素,我们不但能共享其波动,亦能了解其秩序和回应。刘勰亦提到联类的能力:世界的任一事物皆是有机整体的部分,由部分亦可揭示整体。”{22}余宝琳(Pauline Yu)亦提到:“中国本土哲学传统大体上视宇宙为一元……在此世界中,宇宙之文(pattern)及其运作机制,与人类文化之间存在基本感通关系。”{23}饶是如此,无论李氏关联式思维,宇文氏有机整体论,抑或余氏一元论,取西洋概念解说中国诗学,终觉相隔一层,反倒是孔颖达语中鹄的:“天地万物皆以气类共相感应。”{24}
(二)“世界之模式”:中国阴阳宇宙图式
征兆诗学谓“世界之模式”,则预设中国宇宙模型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即“意义和模式潜藏于世界之中。”{25}关于该宇宙图式,宇文所安指出:“有两条基本原则支配着变动:相关要素之组合(the formation of correlatives),如阳/火/日,对立要素(counterparts)之组合,如阳/阴、火/水、日/月。”{26}换言之,万象纷陈背后依托两大原理:其一为相关原则,即同类元素归并聚合、同气相求;其二是对照原则,事物遵循二元成对方式,构成无数组两两对照模型,如生死、山水、哀乐、清浊、深浅等。就实际文本分析来看,宇文所安仅运用第一种原则诠释过晚唐诗人许浑《早秋》其一,将诗中“西风”、“残萤”、“玉露”、“早雁”等意象说成相关要素,共同指向由夏转秋的季节嬗变,实在了无新意。概览《世界的征兆》一书其余诗例,则多运用阴阳对照的宇宙图式,故本文也以此为重。
由此可知,宇文所安所谓“世界的模式”,实即中国传统阴阳宇宙图式。“阳”本指日光,“阴”则为背光即阴影。后引申指涉相互对待之两端。《易·系辞上》罗列各种二元对照结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归总为阴阳原则:“一阴一阳之谓道。”{27}
上文曾言及宇文所安谓“诗歌是世界的征兆”,旨在论证诗歌与世界之感通互应,再结合阴阳对照图式可知,诗歌亦映射出类似的对比结构。宇文所安藉此思路,对律诗形式重新解释,主张对仗(parallelism)之工整实为阴阳结构之映照:“对仗联(parallel couplet)并非是‘诗歌技巧’:保守诗歌传统认可的冗余装饰技艺。对仗是自然世界结构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28}此处强调诗歌和宇宙之同构性,并非无稽之谈。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意在说明骈俪对偶的修辞手法,本源于造化成双之理。西方学界亦有类似见解:17-18世纪启蒙运动推重永恒普世的理性法则,其时正值英国文学新古典主义时期,代表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均衡、对称、谨严的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映射了启蒙思潮下秩序和谐的宇宙观。{29}
四、征兆诗学之应用
征兆诗学强调诗歌和世界的同构互通:既然后者为阴阳对照图式,在实际文本分析中,主要任务便是寻绎一首诗所隐藏的对比张力结构。原理虽易知,但施行颇具难度,宇文所安之贡献正在于此,透过其精准高超的细读功力,发前人之未发,下文以两首杜甫诗来演示征兆诗学之应用。
(一)杜甫《旅夜书怀》中“多”/ “一”、“稳定”/“流动”之对比模式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30}
旧注就杜甫《旅夜书怀》解说较为笼统,如仇兆鳌注曰:“微风岸边,夜舟独系,两句串说。岸上星垂,舟前月涌,两句分承。五属自谦,六乃自解,末则对鸥而自伤漂泊也。”{31}仇氏将前两联视为写景,仅做内容勾勒,然第五句“自谦”讲法显然有误,尾联“沙鸥”亦未必自伤。反观宇文所安据其征兆诗学,发掘了该诗贯穿始终之对比模式,就传统解读错讹之处予以纠正。
鉴于宇文所安对此诗的细读篇幅较长,本文仅做节录,其他部分则依原文整理为表格,意在呈现征兆诗学简明扼要的诠释风格,以下先摘译首联细读:
在形式重现中,直觉到差异与对照:那边,众多;此处,独一。那里,稳固之岸;这里,水与流动的世界。那里,柔软、弯折而稳固扎根;这里,僵直而摇摇欲坠地晃动。那里,微小且无足轻重;这里,极为重要。这些对比有其预示意义;它们在对应参照框架(correlative frames of reference)反映出:流动与无尽运动对比于稳固与扎根,孤独的旅人对比于其余安居的人们;处于岌岌可危的正直、名望与高尚,对照于盲从、卑下与庸俗。未做判断;矛盾未解除;一个模式呈现。{32}
考虑到现有中译本与本文理解颇有差异,故有必要就引文做扼要阐说,以正视听。宇文所安之思路,首先由首联“岸”与“舟”区分出两个相对位置之差异:河岸上风拂细草,而舟中桅杆高直,继而导出“多”VS“一”与“稳定”VS“流动”对比模式。其次,据“对应参照框架”,即联想引申展开如下所示:
1. “多”与“稳定”→安居的芸芸众生→盲从卑下的庸众
2. “一”与“流动”→漂泊孤立的诗人→德性岌岌可危
换言之,其联想链条是由自然景物对比模式,转向社会道德价值观之对立:藉细草河岸联想到卑琐无德的庸众,此处或许受《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影响,再由流水、高耸晃动的桅杆(“危”字既有“高”意,又可衍生出“不稳定”、“危险”等意),联想到漫游的诗人及德性衰微。此番细读功力,堪称敏锐独到。论者唯以“儒家道德主义”{33}轻巧带过,恐不晓宇文氏解读堪为知音之言。
再总览此诗揭橥之对比模式,如下表所示:
由表可知,此诗前三联均展现“多”/ “一”与“稳定”/ “流动”对比模式。首、颔两联之对比模式移转,由自然隐藏秩序进入社会价值观矛盾(虽然上述论及透过类比联想链条,可经前两联过渡至道德对立,但此诗展示社会面向实际发生于颈联):众人成见vs. 诗人飘零无依,反衬诗人孤立无援的流亡困境,故“名岂文章著”,意在抱怨他人无识其诗才之明,绝非仇兆鳌所谓“自谦”。孙微也认为此句:“富有酸楚的弦外知音,那就是‘文章’之名乃俗世之誉,而我诗歌之才却一直难有知音。”{34}
尾联“沙鸥”则将诗人从“多”/ “一”张力模式中解救出来:沙鸥在天地间自在翱翔,令诗人心向往之。此说与仇注“自伤”完全颠倒,相较之下,宇文所安讲法更为恰切,若关注此诗对比模式的运动轨迹:前三联的对比模式消弭于尾联,分明暗示诗人勉力克服之前张力结构之困境。由此可见,“沙鸥”意象的感情色彩即便谈不上愉悦,至少是平复释怀,与自伤郁结相去甚远。
(二)杜甫《对雪》中“内”/“外”对比模式
循宇文所安征兆诗学,为《对雪》一诗抉发对比模式,整理列表如下:
先檢视旧注,仍不出散文释义范围:
至德元载十月,房琯大败于陈陶斜。诗正为是而作……此诗中间咏雪,而前后俱叹时事,正是有感而赋雪耳。乱云急雪,对雪之景。樽空火冷,对雪之况。前曰愁吟,伤官军之新败。末曰愁坐,伤贼势之方张。{36}
仇谓此诗为公元756年唐军陈陶斜兵败而作,随即便勾勒大概内容,解读实在无甚新意。又浦起龙《读杜心解》:“非泛咏雪也。上提伤时之意,递到雪景。下借对雪之景,兜回时事。虽似中间咏雪,隔断两头,实则中皆苦况,正足绾摄两头。”{37}强调雪景与诗人情感的对应关系:突出二者皆为“苦况”,但总体表述较为笼统模糊。
《对雪》一诗,描写诗人困坐孤城,而城外则是唐军战败于陈陶,因战事纷乱而使内外隔绝。雪隔断内外世界,景物与时事亦有相通:纷乱的云块、急迫舞动的雪,令人联想到叛乱和战事。再辅以征兆诗学抉发此诗对比模式,则较《旅夜书怀》明朗许多:外部现实世界vs. 诗人内室(心)。宇文所安提醒说:
此诗“内”与“外”主题式对立,实乃中国诗最根本结构。许多诗皆基于外部“世界”与内部“回响”之间的互动,甚至于在之后诗学中,该结构成为中国诗中占比最大的类型。{38}
若其所言确凿,“内”(自我)/“外”(世界)结构及二者之互动,可为今后重读中国诗提供崭新的视角。
回到《对雪》一诗,既然“内”/“外”模式贯穿全诗,二者如何沟通则亟待阐明。内部与外部世界联结,必须跨过边界,此诗却证实障碍不可逾越:
这里有诗人,这里有诗人面对雪的障碍。这是明暗、冷暖的交界,在尚未来临的鲜红春花与雪夜中黑白、阴阳互搏(指“薄暮”——引者按)之间。在这里,观察中的自我面对崩解失序的世界。无物能进入障碍:消息切断无联系,帝国数州倾覆,无物能走出障碍。{39}
再细究全诗运动轨迹:始于首联“内”/“外”对峙,中经“外”(颔联),又经“内”(颈联),最后又回归尾联“内”/ “外”对峙,内外世界终结于难以翻越的障碍,形成无法沟通的张力结构,而诗人在结尾处无言以对,本文将其延伸,解释为书写困境与内外沟通困境之呼应。
五、结语
由前述可见,宇文所安用征兆诗学发掘文本中对比结构,继而重新诠释杜诗,基本达到圆融自洽,令人耳目一新。究其进路,颇近似于结构主义以二项对立(binary opposition)归纳文本深层结构或模式。关于此法,之前学者已有尝试。张梦机根据对句之语义归纳近体诗多达九类对比:刚柔、晦明、人我、巨细、动静、情景、遮表、今昔、时空。如许浑《咸阳城东楼》:“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表刚柔比对,杜甫《春夜喜雨》:“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即显晦明对比。{40}程千帆亦撰文指出诗人常用“一与多的对立统一”{41}结构,诗例如白居易《长恨歌》:“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韩愈《听颖师弹琴》:“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然张、程二氏,仅就对句语义抽绎对比模式,虽无错讹,但其对比浅易,难以联系全诗做更深入发掘。
杨牧关注乐府诗《公无渡河》中“公”即白首狂夫与“河”的对立模式,二者呈现交替反复结构:“公××河,公××河,×河××,××公何(河)”{42},并援引悲剧理论重新阐释此诗,颇具新意。此外,当代美国诗人理查德·威尔伯(Richard Wilbur)评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英译李白《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时灵光乍现:“前两行感觉是留与走的并列象征”{43},此诗既属送别,则“留”与“走”的对比模式恰好切题,比单纯视为写景要深刻许多。
或有论者主张“二项对立”法,机械僵硬,但经前文可晓,方法之运用,端赖批评家功力高低,若仅止于单纯寻觅指认对比结构,必是了无新意,然能结合全诗涵义,做更为深入多层次探讨,则可更新旧解,启发新解。或有论者认为“二项对立”法,仅强调静态对立,不符合中国传统哲学视阴阳乃互补互济,相反相成之关系。本文介绍宇文所安征兆诗学,如发掘杜甫《旅夜书怀》中“多”/“一”、“稳定”/“流动”之对比模式,亦主张对立模式在尾联消解的动态过程,并非一味静态对立。况且即便中国传统强调阴阳关系之动态,亦不废二者之对立。若以非此即彼的观念,言西方则二元对立,涉中国必天人合一,恐怕失之迂腐褊狭。
要之,部分读者对中国古典诗并不陌生,而是过分“熟悉”,常携带读旧诗的程序惯例,反而导致阅读障碍产生,将作品简单化了。诚如宇文所安言:“因为你如果过于相信自己的默契,被先验的印象牵着走,那就往往一叶障目而不知泰山。另外,文学作品并不是越简单越好,总要设法找出其更深的内涵,建立起新的张力。”{44}本文旨在阐明征兆诗学,藉助对比模式重读杜诗,以期该方法可推而广之,对古典诗歌深入诠释有所助益。
① [美]宇文所安:《初唐诗》,贾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页。
② 陈小亮:《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动——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浙江学刊》2012年第6期;陈小亮:《论海外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命题研究的源与流》,《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李凤亮、周飞:《空泛与错位的“非虚构诗学传统”——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文艺研究》2019年第4期。
③ [美]孙康宜:《从捕鲸船上一路走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④ 张隆溪:《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175页。
⑤{11}{14}{15}{22}{25}{26}{28}{32}{38}{39}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 Omen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34,84; pp.19-20; p.77; p.44; p.21-23; p.34; p.83-84; p.86; p.17; p.39; p.38.
⑥⑦⑧ 劉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第1页;第3页。
⑨⑩ [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联经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7页;第32页。
{12} [美]宇文所安:《中國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陈小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3} 张少康:《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16}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50页。
{17} 苏洵:《嘉祐集笺注》,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71页。
{18}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2-1693页。
{19} 刘熙载:《艺概注稿》,袁津琥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15页。
{20} 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21} [英]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陈立夫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407页。
{23}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2.
{24}{27}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第302-303页、第315页。
{29} [美]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1870年至1930年的想象文学研究》,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0}{31}{35}{36} 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29页;第1229页;第318页;第318页。
{33} 陈小亮:《理想的诗歌:中国非虚构诗学对西方文学传统的反动——评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浙江学刊》2012年第6期。
{34} 孙微:《名岂文章著:论杜甫生前诗名为赋名所掩》,《文史哲》2017年第2期。
{37} 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60页。
{40} 张梦机:《近体诗发凡》,台湾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69页。
{41} 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索》,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42} 杨牧:《传统的与现代的》,洪范书店1987年版,第12-13页。
{43} Richard Wilbur. The Catbird’s Song: Prose Pieces, 1963-1995. Harcourt Brace, 1997, p.221.
{44} 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Poetics of Omen for Yuwen Suoan (Stephen Owen)
and 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try
Hu Min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by Yuwen Suoan (Stephen Owen), that was published in 1985,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over thirty years and yet the scholarly world is still pursuing the so-called tradition of non-fictitious poetics in it while heatedly deb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irtual and the actual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By traveling down a different path,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cavate Yuwen Suoan (Stephen Owen)’s poetics of omen that treats Chinese poetry as an omen of the world, with the poetry that reveals its patterns.This poetics, derived from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Liu Xie and Liu Ruoyu, its ‘omen’ related to the principle of sense of air, aims at demonstrating the interactive responses between poetry and the world, with the patterns of the world indicating the Chines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Hence the isomorphism of poetry and the world that contains the model of binary comparisons.Based on this line of thinking, Yuwen Suoan (Stephen Owen) is quite innovative in that he has found the tension structure of manyness, oneness, stability, fluidity, the internal and the external in Du Fu’s poetry.
Keywords: Yuwen Suoan (Stephen Owen), poetics of omen, sense of air, the yin and yang schema, the comparative structure in Du Fu’s po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