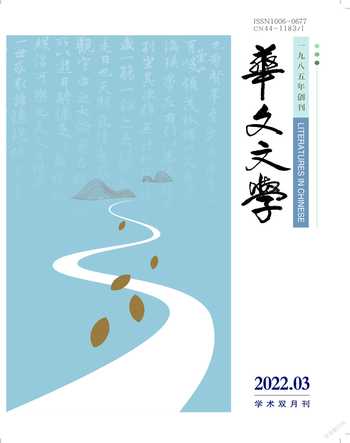《野草》系列刊物与1940年代的文艺领导权之争
摘 要:《野草》系列期刊是1940年代重要的文学期刊,该刊集结了夏衍、聂绀弩、秦似等左翼文化人,在鲁迅之后继续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争取民族解放,巩固左翼的文化领导权,该刊先后集中开展三次批判:一是批判战国策派,弘扬民族主义。二是批评自由主义。在冷战格局下,批判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对沈从文的文艺和思想的批判,介于批判战国策派与自由主义之间。三是积极传播延安文艺思想,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国统区的整风运动。该刊对战国策派和自由主义的批判,是左翼文艺争取并逐步取得国统区文艺领导权的过程,自我批评是左翼文艺权势的内部重构,也是延安文艺思想确立全国性文化与思想领导权的一环。
关键词:《野草》;战国策派;自由主义;领导权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014-12
《野草》系列刊物是指1940年代出版的《野草》月刊①、《野草》月刊复刊版、《野草丛刊》和《野草文丛》。从1940年《野草》月刊创刊,到1948年底《野草文丛》在香港终刊,该刊几乎与40年代相始终。《野草》于抗战时期创刊于桂林,抗战胜利后于上海复刊,后又随左翼文人的南下转至香港,发行地点与40年代左翼文化人的行迹大致相同。该刊编委主要有秦似、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等。撰稿人有郭沫若、茅盾、胡绳、邵荃麟、周而复、林默涵等,几乎涵括了当时主要的左翼文人。此外还有柳亚子和胡愈之等同情左翼的民主人士。学界对该刊的研究不多,在讨论40年代后期左翼文人对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时,也多侧重《大众文艺丛刊》,相对忽略同在香港发行的《野草文丛》。
该刊文章多为杂文,在鲁迅之后继续发挥杂文匕首、投枪的作用。该刊在抗战时期,以弘扬民族精神、批判法西斯为主,抗战胜利后重在揭露社会矛盾,40年代末期则转向传播延安文艺思想,开展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与改造。该刊创刊于抗战相持阶段,彼时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已过,《野草》作为国统区左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文化斗争的作用,是40年代左翼文化争夺并最终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力量。所谓的文化领导权,不是指文艺活动的实际领导权力,而是指文艺的责任使命、文艺话语的主导权及实际的文化影响力。②该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批判战国策派,二是批判自由主义。对沈从文的批判,介于批判战国策派与自由主义之间。三是传播延安文艺精神,进行自我批判,开展国统区的整风运动。这些批判与自我批判,不仅涉及文艺如何争夺文艺领导权的问题,也关系到左翼文艺内部的权势调整与变动。
一、对《战国策》的批判
在《野草》月刊第六期也就是第一卷出齐之际,编者在《编后记》中对第一卷内容做了总结。在谈到该刊的一个常设栏目《斩棘录》时,编者说,“像斩棘录,我们也不希望时作时辍,且专门针对《战国策》。天下的荆棘,只剩战国策了吗?并不然。不过由于学者教授们虽然非‘大政治不谈,但到底还是在拿着笔,稍有辩论,不至于别生枝节而已。”③翻检该刊第一卷可见,该刊确有不少批判战国策派的文字,而且,之后也并未做出多大改变。
战国策派是40年代初的一个文化团体,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同济、雷海宗、陈铨和何永佶,此外还有沈从文、贺麟等。④成员大多為当时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学者。他们受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以及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鼓吹大一统和强力政治。战国策派曾发行《战国策》月刊,并在《大公报》上开辟《战国策》副刊。“战国策派”名称的由来,还在于他们判定当时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指出,“现时代”的意义就在“战的一个字”,“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测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他们不禁要投龟决卦而呼道:这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在他看来,“历史上自成系统的文化,大半都有过了它的‘战国时期”。战国时代的意义,“是战的一个字,加紧地,无情地,发泄其权威,扩大其作用”。战国时代的特征是战争成为时代的中心,“成为一切主要的社会行动的动力与标准”,现代的战争是“全体战”,同时,战争目的不再是割地赔款,而是称霸世界。⑤在战国策派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类似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而被迫卷入到这个世界性战国格局的中国,应该复兴战国精神,以在列强争霸中完成民族国家的再造。
综观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的相关说法,战国策派的主要观点有三:一、战国时代重演论,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认为中国正处于历史从列国阶段进入大一统帝国的阶段。二、崇尚强力,综合尼采的意志论及战国时代士大夫的“六艺”,主张改造宋明以来积弱的国民性,提倡兵文化,提倡“英雄崇拜”,从尚文的士大夫转变为尚武的大夫士。三、宣扬大政治,“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文化上要求综合摄相,文学上提倡民族文学。战国策的这类主张,在抗战的语境下迎合了激昂的民族情绪及膨胀的领袖权威,在当时有一定的现实性,因此不乏支持者,影响一时。左翼知识分子虽对陈铨的民族论和英雄论,曾有一定的认可⑥,但对这种强权逻辑且不乏领袖崇拜的观点,从一开始就保持警惕,而《野草》是较早予以严厉批判的。
《野草》对战国策派的批判,几乎与《战国策》月刊同步出现。《野草》第三期有两篇杂文——《教授们》与《作品与时代》,着力批判《战国策》的观点。其中,李育中的《教授们》针对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对当时战争的定性及其循环史观提出批评。在李育中看来,林同济将日本的侵华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描述为战国时代的重演,无疑是取消了战争的是非之别,尤其忽略了中国、苏联等在抵抗法西斯时的正义性。他认为:“当前有帝国主义的混战,有弱小民族对抗侵略者的生死决战,他却一概抹煞,分不出谁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只会说这是‘热剧。旁观得这样恬然。”⑦林同济对时局的把握,主要是从历史形态着眼,将当时的战争类比为战国时期的诸侯混战,这确实忽略了不同阵营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别,李育中的批评颇为中肯。除了从横向上批评林同济的形态史观外,李育中还从纵向上批评循环史观,在他看来,循环史观是倒退的历史观,它取消了战争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战国策派认为当时的历史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这种循环史观在当时颇有影响,报端时见类似论述。对此,《野草》也及时予以驳斥。如马立业《历史会重演么》就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指出,“宇宙是变动的,历史也是演变的;而且变动的路线是向前进的,不会转圆周,即令有外表相似的事件发生,也根本是不会是重演。原始公产社会不会是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希腊的共和不是今日的‘德莫克拉西,而且现在编《春秋》《战国》高喊‘历史是会重演的的‘大人‘尖头蛮之流,也不会拿树叶来做大礼服。”⑧历史循环论取消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马立业从进步史观批判循环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除针对战国策派的循环史观及其关于战争性质的不当描述之外,《野草》还对战国策派的英雄崇拜、大政治、反对女性解放、大夫士等相关言论和思想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英雄崇拜主要是陈铨的观点。陈铨较为推崇德国精神,他先后介绍“浮士德精神”,强调一种永不停歇的人生观,⑨又介绍叔本华和尼采,推崇叔本华的意志论及尼采的强力意志和主人道德。⑩“英雄崇拜”的观念,综合了意志论和卡莱尔的英雄论。他的《论英雄崇拜》指出,人和物是推动历史的两种力量,而意志是“人类精神活动根基”,“物质对生物,固然有相当的力量,但生物求生的意志,很容易适应物质,战胜物质,甚至于改变物质,创造物质”,因此,“人类的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意志如此重要,那么创造历史的人类意志,到底是多数人的意志还是少数人的意志呢?他显然侧重后者,在他看来,“时势到了某种情况之下,群众的意志,有了某种强烈的要求,这种要求自然可以产生伟大的人物,然而伟大的人物那时也可以不产生,结果历史就成了停滞和紊乱”,即,对于历史发展而言,群众的意志并不是充分必然条件,只有伟大人物的产生才是。“英雄与历史,有双重的关系”:“英雄是群众意志的代表,也是唤醒群众意志的先知”,即,英雄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启发群众的意志”,同时也能代表群众的意志。基于这种英雄史观,陈铨认为“英雄是受人崇拜的,是应当受人崇拜的”,英雄崇拜是高尚的道德行为,不能崇拜英雄的人,是狭小无能的人。但中国因士大夫阶级的腐化,加上五四以来的现代教育,导致人们对英雄缺乏崇拜。如何让人们重新崇拜英雄,在他看来是当时最紧迫的问题。{11}对陈铨的这种英雄崇拜论,严杰人《谈名》着力批判其对少数伟人的推崇,他借鉴鲁迅《战士和苍蝇》的相关说法——“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认为这可以“作医治‘英雄崇拜这种心理病症的药剂”,因为真正的英雄,从近处看也都是缺陷和创伤,跟普通人一样。陈铨过于强调英雄的非凡属性,让英雄显得与“众”不同,忽略了英雄的群众性。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英雄之名,而在于建设合理的社会制度,重要的不是要崇拜英雄,而是“脚踏实地去做人和做事”{12}。对于陈铨所宣扬的主人道德论,琛的《“把船头调转”》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尼采的主人道德,要求强者行动、弱者服从,但就现实而言,“我们目前正是羊,不是鹰”,应该肯定的是弱者的反抗,而不是强者的征服。{13}有意思的是,陈铨提倡英雄崇拜,实际上带有改造国民性的意味,但在国难当头,陈铨所开出的药方,因其弱肉强食的逻辑而受到批判。另外,《野草》同人对陈铨的批评,多是用杂文笔法从逻辑上批评陈铨,而少根据左翼的群众史观反击其英雄史观,不过,左翼阵营的思想史家胡绳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的《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指出,《战国策》“宣传尼采的超人论,英雄论,他们在妇女问题上公然主张三K论,他们公然说,民众只该受支配,供驱使”,认为这是专制思想,“这就是愚民政策”{14}。虽然也没有明确的群众史观,却看到了英雄崇拜对群众力量的漠视这一关键问题。
与英雄崇拜相关的,是战国策派对现代女性运动的异见。陈铨在介绍尼采的强力意志之后,又专文介绍尼采的性别观。尼采认为男性代表力量,女性代表感情。力量主征服和摧毁,而情感则提供慰安,因此,“男子的职务在战争,女子的职务,在给男子感情上的安慰,使他保持战争的力量。”女子的势力“并不在乎她自己的独立的行为,而在乎辅助的行为”。陈铨认为尼采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偏激的地方,但他“分别男女的不同,划定双方的责任,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意见”,认为男女毕竟生物有差,不必强求平等,应该接受尼采基于男女生物差异的本质化区别,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畛域分明的社会分工。陈铨此论是针对“五四”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娜拉”除了离家出走还有更好的方法,这就是接受自己的命运,毕竟“在西方已经有妇女回家庭的运动了”,东方也不妨听听尼采的意见。{15}战国策派另一位较为活跃的人物何永佶(尹及)也认为,男女平等应建立在生物平等的基础上,而近代的妇女运动是舍本逐末。{16}
对这类观点,《野草》同人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批评。余惺夫指出,战国策所谓的生物平等,是以女性承担社会不平等为代价的,缺乏社会平等保障的生物平等只是短暂的幻象,在他看来,“如果叫女性回家或回厨房就可解决妇女问题,妇女问题就根本不会发生,因为妇女本来就在家里,在厨房里的。”即便是建设新的家庭,如果女性地位没有社会条件的保障,单凭夫妇爱等抽象的力量,是难以维系两性的普遍平等的。至于战国策以“大政治”之名,要求女性回归家庭,则更是假政治之名否定女性解放。{17}令狐厚《“女性应该安于生物的平等”论》指出,人类不同于纯粹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类创造了文化,在节烈文化的束缚下,女性连求得生物平等也无可能,女性只有诉诸社会运动,打破既有的文化偏见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平等。他进而指出,女性的解放也是“大政治的斗争”,“但这不是历史的循环或者重演,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由‘大一统进变至战国局面,而是在新的文化底成的前夜,被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間决定的争斗”{18}。令狐厚借用战国策派的大政治逻辑,但将大政治的内涵从国家至上的论调,转换为阶级的斗争,在这个大政治的视野中,女性解放也是题中之意。余惺夫和令狐厚从社会、文化、政治等角度,反驳战国策派的生物平等论,将女性解放从抽象的层面具体化了。
战国策派尚力,对战国时期的士大夫文化极为推崇,针对这种将士族理想化的历史想象,孟超从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探究士的起源和政治行径的本质,他认为张仪、苏秦之流,出发点实为个人主义,其说服帝王的方法近乎“拆白行为”,由此揭示“纵横术”的欺骗性。{19}战国策派从大政治的视野出发,对当时的欧战持较为超脱的看法,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尤其如此,对此《野草》都及时予以回应,如愈之《新策士葬送了希特勒》就称现在不是新战国的时代,而是科学的群众的时代。{20}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二、对沈从文的批判
《野草》在批判战国策派时,批评最为集中的对象不是林同济、雷海宗等史家,而是作家沈从文。沈从文与贺麟一样,只是《战国策》的特约撰稿人,并不是战国策的核心成员,有时他们的观点甚至与陈铨相左。如沈从文对陈铨的英雄崇拜论就持保留态度。{21}他虽只是《战国策》的撰稿人,却在《战国策》上以沈从文和上官碧等笔名,发表了不少作品,对新文化运动及战时文学成就有所批评和反思,这引发了较多的讨论。
《野草》对沈从文的批评,首先也是针对沈从文的女性观。沈从文在《战国策》创刊号上发表了《烛虚》一文,从当时他周边女性缺乏理想和信念的现象出发,批评五四以来的新式教育过于侧重性别解放,忽略了理想教育{22}。李育中《教授们》在批评林同济等人的循环史观之后,紧接着批评沈从文悬的过高,是“在火灾旁边做梦”,忽略中国的社会现实。{23}李育中的批评不仅是针对沈从文个人,也针对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这些文化人常牢骚满腹,为的多是薪金之多寡,分析问题时又过于超脱。
40年代初,沈从文试图重估五四传统。他在《战国策》上发表的文章,如《小说作者和读者》《白话文问题》《新的文学运动和新的文学观》《续废邮存底》等,对流行作品作严厉批评,询唤具有永恒性的“伟大作品”,并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进行历史性回顾和价值重估。他十分看重语体文的价值,《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一文指出,北伐的成功是中国的一大转折,而北伐之所以能成功,则有赖于文学革命,通过在各方面运用语体文这个社会解放、民族改造的工具,“在国民多数中培养了‘信心和‘幻想,因此推动革命,北伐方能成功的”{24}。从国民革命的历程着眼,新文化在现代国民的养成中确实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沈从文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沈从文表彰白话文运动,主要是为批判文学的商业化和革命化,他认为“作品受‘商业或政策‘工具的利诱威胁,对个人言有所得,对国家言必有所失。从商品与政策推挽中,伟大作品不易产生”。至于如何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沈从文认为要在政治与商业之外“选一条新路”,“即由人类求生的庄严景象出发,因所见甚广,所知甚多,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的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25}《小说作者和读者》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作品的功利性,对二十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持否定态度,肯定形式上恰当、“近人情”、有理想性的作品。{26}
反思战时文学的粗制滥造,追求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不只沈从文,当时左翼作家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也在关注这个问题。《野草》对沈从文的批评,并不在于他对流行文学的批评,而在他批评革命文学时流露出的超脱姿态。如署名“琛”的《作品与时代》一文,认为沈从文一味追求抽象的永恒,忽略了作品的时代性。该文认为,沈从文等推崇战国时代,却未认清战国时代的思想正是战国时代的人创造的,“现在的时代,据战国策的君子们说,是回复春秋战国时的‘大政治时代。战国时代的作品是有留传下来的,但并不是生为战国人而为民国人写的作品,恰好正是写着当时。”{27}秦似的《“伟大的捕风”》批评沈从文“把一切世事看作非现实的东西,‘虚空”{28}。聂绀弩的《装腔作势的男人》认为沈的批评未深入辨析具体问题,反而模糊了是非曲直。{29}
《野草》对沈从文的批评,最为集中的议题是他对周作人和鲁迅的评价。沈从文在《习作举例》这个栏目中,列举诸多新文学名家作品,并对作品进行剖析,以便写作者借鉴。他首先推出的是徐志摩,其次是周作人和鲁迅。正是他对周氏兄弟的评价引起了争议。他的《习作举例——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一文称:“周作人作品和鲁迅作品,从所表现思想观念的方式说似乎不宜相提并论。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一个近于恨恨的诅咒。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理性明瑩虚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愤激,易恼怒,语言转见出异常天真。”看似别风格,实则暗喻褒贬。他还认为,“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正说明两种倾向: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后者代表艱苦斗士的作战。同时是看明白了‘人生,同源而异流:一取退隐态度,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大有自得其乐意味:一取迎战态度,冷嘲热讽,短兵相接,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也俨然自得其乐。”{30}对周作人的文章和思想姿态评价甚高,两厢对照,对鲁迅不无批评。
沈从文的这个观点,激起《野草》同人的一致批评。《野草》先后发表《沈从文先生的天真》《从陶潜到蔡邕》《“变节”与“脱节”》《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等数篇文章予以回应,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针对周作人的“落水”,批评沈从文缺乏民族意识,二是沈从文对鲁迅杂文的偏见。
署名“禄”的《沈从文先生的天真》指出,沈从文认为周作人“近人情”,在评价鲁迅的时候,却认为鲁迅“天真”。该文反问,“难道站在周作人对面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人,便没有‘爱,且是没有‘理性的么?”,在该文看来,沈从文缺乏大局观,这才是真的天真。{31}这个批评,看似将纯文学的问题政治化,但在抗战的语境中,沈从文一味推崇周作人确实缺乏大局观。《“变节”与“脱节”》称周作人不是与社会脱节,而是变节。{32}沈从文的观点,甚至引起曹聚仁的不满。曹聚仁也在《野草》上批评沈对周“落水”的维护。他认为周作人已从陶潜的隐,转向蔡邕的投敌,因此,“无论谁替周作人作怎样维护的话头,终不能说出周作人必不能离开北平那圈子的理由,更无从说出他非出卖灵魂不可的理由。”“有人说,现在知识分子事仇作伥,不独周作人一人,你何独苛于周作人而必严加责备?说来还是顾亭林那句老话:人人可出,而他不必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青年导师,文化界的白眉,连敌方的文化人都以为他将清高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应该说出苦茶室)事敌,我们怎可以不加严厉的批评呢!”他不仅不同意有关周作人是退隐的说法,而且认为“应当付之典刑”{33}。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曹聚仁的批评,又引出聂绀弩和宋云彬等人的跟进。聂绀弩认为周作人连蔡邕都不如,因蔡邕所投靠的董卓并不是异族,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这两者之间,谁是谁非,谁正谁邪,尤其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选择哪一条路,是昭然若揭的事”{34}。宋云彬认为陶淵明不全是隐逸,而是对现实不满而然,这继承了鲁迅的看法。不过,宋云彬也称他认同曹聚仁的说法,“目前我们也不需要有陶渊明一流的人物”。但他批评的重点,还不在周作人,而是针对沈从文等京派文人。“我在那篇《呵周》的短文里曾说过:‘处在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保卫民族的斗士和出卖民族的汉奸,还有夹缝可钻,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吗?然而事实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尤其自命为京派教授的,却在到处找夹缝,找第三条路,他们有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不过在他们屡次表示瞧不起‘抗战文艺这一点上,一副尴尬的嘴脸,却有点令人讨厌。我以为与其有这种人,毋宁有几个陶潜,因为他止少对于世事还有点热情,不但‘猛志固常在,而且有时‘终夜不能静的。因为他只是‘托迹于山溪林莽,不是跳在半空中,肩起导师的大旗,挂着知识分子的标签,来向青年们说教。{35}批评沈从文乐于说教,过于超脱。
聂绀弩通过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深入解读,反驳沈从文对鲁迅的评价。沈从文在评价鲁迅时,用的形容词主要是激愤、恼怒、骂世、冷嘲等,聂绀弩虽然认为这是些“不十分表示敬意的字样”,但却并不反驳沈从文的片面,而是沿着沈从文的论断,进一步追问,“如果鲁迅真是一个憎厌人事,感情闭塞,愤激恼怒,骂世冷嘲的作家”,“那么,他的作品会有什么价值呢?又怎能‘自成一格,‘代表一种‘倾向呢?”{36}通过大量的例证,聂绀弩指出,鲁迅的骂世或激愤,都是与具体问题相关,有对是非的具体判断。沈从文反对骂世,反倒是将具体问题抽象化,是不问是非的“各打五十大板”。沈从文仅从风格上对比鲁迅与周作人,看似公允,实则有混淆是非之嫌。因此,聂绀弩认为读者在阅读或学习鲁迅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其激愤,也有看到他背后的热情,尤其是“正视人生的迎战态度”{37}。
从立场而言,沈从文虽然是《战国策》的特约撰稿人,但其思想更为接近自由主义。因此,在抗战结束后,左翼文化人批评自由主义文人,尤其是当时的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等立场或思想时,沈从文也未能幸免。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列为反动文艺的桃红色作家{38}。从上文的梳理可以看出,左翼文化人在40年代初就对沈从文有较为激烈的批评,郭沫若的批评与其说是开先河,倒不如说是对历史的总结。
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抗战结束后,内战旋即爆发。对于《野草》同人而言,民族主义议题逐步让位于左、右之争,该刊面对的问题,不再是统一战线框架中的协作,而是要确立左翼文艺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权,这就要求彻底击垮国民党官方文艺,批判并争取自由主义文人和文艺。
《野草》对自由主义文艺的批判,早在40年代初就出现了。如秋帆的《纪德所成就的》,就对纪德这个著名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有所批评。该文写作的背景是,曾经同情苏联的纪德,在访苏归来后却成了反苏的文化先锋。纪德的《访苏归来》被及时译介到中国,并受到思想文化界关注。对纪德的转变,秋帆指出,“这一点也不应该什么奇怪的。一个自由主义者很难得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以自己的好恶为中心,以个人的荣辱为转移,再加上他的上不沾天,下不落地的阶层性,使他缺乏一个确切的,坚定的政治责任感。他对个人的‘乌托邦负责任,而不对历史的路线负责任,他对个人的游离的情感或‘自由尊严负责任,而不对千万人运命所系的工作和生活负责任。这一个矛盾的枢纽控制了纪德,在他生活认识领域里,无论前前后后,里里外外,造成一个全不统一,全不协调的混乱。”并且指出,“这不是纪德个人的矛盾或疯狂,而是许多自由主义者在这个大时代中难免的悲剧。”当时正值抗战,作者主要还是在反法西斯的世界视野下予以批评。他联系中国的现实,进一步指出,“纪德型的文化人,在中国,北方和南方,都有为敌国的‘王道‘和平做喇叭手的人,清洗这些时代的残渣,是抗战胜利的一保证。”{39}这个逻辑,与《野草》对周作人“落水”的批评,及对沈从文维护周作人的批评是一致的。
《野草》集中批评自由主义文人,是在抗战取得胜利、该刊于上海复刊以后,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胡适、王芸生、朱光潜、曹聚仁、王云五等,问题主要集中在他们的中间路线、超脱的姿态及“政治投机主义”等。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抗战时期,他临危受命开展国民外交,后担任驻美大使,争取国际援助,为中国的抗战做出很大的贡献,因此,抗战胜利后,在归国之际,他的声誉很隆,且国内文化界对他期许甚高。但胡适归国之后,却十分谨慎,不愿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野草》同人对此颇为失望,该刊复刊号就发文称,“更有谁能想到,五四时代的战士,新青年上的英雄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折磨,竟无声息地变成绝口不谈国事的高人隐士了?”{40}不久,胡适放弃之前的中立立场,不顾朋友的劝阻,出席1946年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之后还对该“国大”评价甚高,认为是中国实验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功”{41}。这在左翼知识分子看来,表明胡适已选定立场。因此,《野草》新三期刊载了一组文章——《胡适博士的迷茫》《胡适不办刊物》《胡适之和“好政府”》《论乌鸦》,对胡适的政治主张、前后变化等,予以分析。这些文章认为,胡适不了解“国大”的官僚本质{42},“好政府”只是闹剧,{43}进而批评他背叛其自由主义理念,从不讨人欢喜的乌鸦豹变为白鹦鹉,与曹聚仁一样,有投机之嫌。{44}对于胡适来说,“国大”是一次实验其政治理念的机会,也是自由主义能参与解决时局的良机。但对左翼文化人而言,国民党独自召开“国大”,本身就是对“联合政府”路线的拒绝,而且,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大”并不完整,不具备代表全国人民的合法性。因此,胡适的做法,在左翼文化人看来也就成为自由主义者与当局合作的标志。实际上,当时自由主义者如王芸生就曾抱怨,他们试图保持中立,但常受左右两方的批评。不过,周而复也指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当局而言,是小骂大帮忙,看似中立,还是有偏向。{45}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野草》批判的自由主义多跟美国相关。如邵荃麟《“文明的果实”》就认为胡适在沈崇案中,态度暧昧,有为罪犯辩护之嫌。{46}楼适夷《胡适的妙计》则称胡适是美国的马前卒,“他们的宣抚班是赶在大炮之前的,新大陆之为‘王道乐土,是早经胡适之流普遍宣扬了,加之杜鲁门的漂亮的声明,马歇尔的热心的‘调停,还有一位学者教育家,数十年中国之友的司徒雷登。”{47}颇为激烈地批判胡适的亲美立场。白坚离《周作人胡适之合论》则将胡适与周作人并提,认为胡适是美国新殖民的马前卒,就其人品而言是阮大铖一流。{48}侯外庐《胡适、胡其所适?》称胡适的实验主义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49}当时的国际形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瓜分世界,冷战格局正在形成,中国成为美、苏两个大国博弈的空间,国内的知识分子对此十分警惕。如并不算左翼的曾昭抡,其《青岛杂忆》一文就批判了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因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在青岛驻扎军队。{50}所以,当胡适屡次为美国辩护的时候,虽然事出有因,但也引起诸多批评。郭沫若也对胡适有所批评,他认为胡适等人把美国想得过于理想,美国只是在利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果按利用价值来看,蒋介石的价值要高于胡适。{51}相对而言,郭沫若的批评还算比较温和。
《野草》对胡适的批判,之所以常与美国问题相关,除了冷战的背景外,还在于自由主义者的“中间道路”得到美国的支持,后来演化为“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形成于抗战时期,抗战伊始,国民政府为团结国内力量,召开国防参议会,之后民主党派通过国民参政会等途径参政议政,为抗战贡献力量,抗战后期,中间党派纷纷联合,成为民主斗争中的重要力量。{52}在内战期间,部分组织和自由主义者,一方面寻求在联合政府的框架内解决国是,另一方面试图寻找异于国共的第三条道路。不过,在内战、冷战这种非此即彼的环境下,第三条道路的设想颇有些虚妄。首先,中间力量的形成本身就有共产党的支持,{53}其次,美国对第三条道路的扶持,带着自身的利益诉求,第三条道路借助美国的力量不仅未能真正左右中国政局,反而被拖入冷战的泥淖。
与中间道路相呼应的,是朱光潜、曹聚仁等人的超脱姿态。抗战胜利后,朱光潜等京派文人复刊《文学杂志》,试图延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的姿态与沈从文相近。他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苏格腊底在中国》。前者将人生分为内倾与外倾两种,内倾是静观的,外倾则是行动的,朱光潜对近代的浮士德式进取精神有所批评,认可旁观的看戏式姿态。{54}后者谈人文主义的文化理想,在论及时局时,他虽然批评政治腐败,却对两党均加以指责,对参加政治活动的人也一概予以否定。{55}林默涵对朱光潜看戏的人生观及不做具体分析的批判,均予以批评。林指出:“把世事人生都当作戏,这是那些以旷达自许的名士们常常这样表示的。”“让演戏的人专演戏,让看戏的人只看戏,互不相犯,各得其乐,这样就自然‘天下太平了,显然的,看戏的人永远只能坐在台下看,决不能跳上台去‘越俎代庖,据朱先生说,‘这是一件前生注定丝毫不能改动的事。既然如此,一切变革的企图和活动,不全是多事吗?治国平天下,原是那些帝王将相们的伟业,我们只有张着嘴巴坐在台下看的份儿,几曾见看戏的人跳到台上去演戏呢?这就是了!朱先生的真意原来在这里。”{56}朱光潜强调的看戏,主要是个人的性情和审美观,林默涵则将这种态度普遍化,进而揭示看戏姿态与革命动员之间的矛盾,因此予以批评。他还对朱光潜身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察委员”,却以中间人士自居颇有微词。周而复对朱光潜的民众观有所批评,他认为朱光潜将时局问题归咎于国民性,尤其是民众的“懒惰,因循苟且”,这“既诬赖了中国人民,又把统治阶级的罪恶,全部洗刷干净”。至于朱光潜对国共两党的指责,在周看来也是不问是非的拉偏架,“不分青红皂白,两造各打屁股五十,朱委员多么‘中间啊”{57}。默涵《论“不管闲事”》,针对的是朱光潜对人们在“国大”选举中表现不积极的批评。{58}林默涵认为,朱光潜应该批评的是统治者,而不应是人们的沉默。因为“‘不管闲事,自然不能算美德。但这正是历来的统治阶级所有意造成的。”{59}在《野草》同人看来,朱光潜等自由主义者虽然也看到了问题,但在分析问题的原因时,往往诉诸人性、国民性或其它抽象因素,或不问缘由对国共两党皆加指责,反而忽略了抗战胜利后当局所造成的诸多问题,有拉偏架之嫌。
其实,到了1948年左右,已经不再是天地玄黄了,{60}随着共产党军事的逐步胜利,左翼知识分子与当局的矛盾渐趋激化,留给中间势力的空间不是越多,反而是越少,历史已经走到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了。《野草丛刊》第七期题名《天下大变》,内容也是如此。《从“点将”到“选佛”》从明末的历史出发,说明在党争之际,没有明哲保身的空间。该文意在说明,国民党不会顾及中间势力的超党派性,只会以是否明是非为标准,明是非就会被视为敌对,因此,明哲决不能保身。{61}佩韦《客气过分论》则认为,“政治局势的演变,已到了严重关头。如果不明是非,不分敌友,一律拉拢,貌合而神离,同床而异梦,我恐季孙之忧不在颛夷(臾)而在萧墙之内也。”{62}主要针对当时流行的“斗争过火论”,即认为共产党的土改等政策,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过火。对这类说法,《野草》均及时予以批驳。聂绀弩《诗人节怀杜甫》剖析了自由主义者有关国共治下孰者更自由等说法的逻辑误区。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国民党治下固然不自由,但共产党治下就不见得自由。聂绀弩认为这是以假设替代事实,这种判断中的双重标准,并不符合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理性和实证精神。{63}《自由主义的斤两》也同样批评自由主义者的双重标准,他列举了具体事例,即《大公报》在报道国军从小丰满撤退时避重就轻,罔顾事实。{64}此外,孟超《論蒋干》{65}《谈奴才渣子的技俩——兼论曹聚仁的〈十年观变杂话〉》{66}、申公的《王老板的故事》{67}等,对曹聚仁、王云五的中间路线都有所批评。
到40年代后期,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左翼文化人对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就不仅仅是批评自由主义者的言行姿态和自由主义理念,还对自由主义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向人民大众学习。如胡绳《关于加括弧的“民主份子”》就将农民及其他生产者之外的民主人士称为加括弧的民主份子,意即非真正的民主人士。要成为真正的民主人士,需要“有勇气在向人民大众学习,在和人民大众一起从事斗争中,解脱这可羞的‘括弧”{68}。为自由主义者如何转变指示道路。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四、内部整风与自我批评
《野草》同人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前后期针对的重点不同。前期重在自由主义者与官方、美国等势力的关系,或是自由主义者对现实的隔膜等方面;后期转向讨论更具体的问题,如文艺的大众化,知识分子的人民性及与群众的关系等。这个标准的转移,是与共产党在国统区的影响力变化相一致的,且首先影响的是左翼知识分子对敌斗争的话语结构,随后,这也对左翼知识分子自身提出了要求。
抗战时期,在解放区的整风运动结束后,延安曾派刘白羽等前往重庆传达中央精神。但当时效果并不理想,尤其是胡风等人反应十分激烈,之后他的态度也无多大变化。{69}到40年代后期,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知识分子如何抉择的问题逐渐凸显。而被共产党转移到香港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大众文艺丛刊》等左翼刊物为阵地,适时地从文化和思想层面开展学习和整风运动,确立延安文艺思想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权,{70}不仅进一步批评沈从文等自由主义文人,{71}左翼文化人也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胡风、路翎等七月派的文艺思想{72},及王家康、乔冠华等人提倡的“新感性”等进行批评和清算{73},《野草文丛》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野草》同人大多与胡风关系较好,该刊曾多次发表胡风的文章,{74}该刊编委之一的聂绀弩,与胡风关系颇为密切。聂绀弩的文风很快也遭到批评。林默涵撰文批评聂的《浮生若梦》,认为该作看似曠达实则颓丧,缺乏与现实斗争的勇气。针对《浮生若梦》的消极情绪,他指出:“我没有反对抒情诗,这是谁也不能反对的。但是,同是抒情,而所抒的情却可以大大不同:有人抒的是颓丧的情,有人抒的是刚健的情,有人抒的是个人的忧郁,有人抒的是大众的爱憎。因此,有些抒情诗使人读了有如输进新鲜的血液,从而奋发,振作,更勇敢的投进人民的斗争;有些抒情诗却相反的使人读了有如染上败血的病症,从而消沉,萎靡,心灰意懒,逃避现实。这后一种抒情诗,难道也不该反对吗?而《浮生若梦》的思想,正是属于后一类的,无论如何决不属于前一种。”{75}认为该作思想消极,不利于当时的斗争工作。不过,聂绀弩在海外华人读者中有不俗的影响,当《野草》出现批评他的文章且暂时不登载其作品时,就有海外读者写信前去询问,因此,林默涵等对聂绀弩的批评不了了之,这是由香港这个独特的语境所带来的结果。
聂绀弩之后也自觉学习延安的相关文件,《血书——读土改文件》就是他读土改文件的心得。他对土改文件的评价方式很值得关注,与当时绝大多数人对土改文件的接受方式不同,他是将其当作思想文件阅读的,而且是放在五四思想革命以来的脉络中理解:“五四以来,或者五四以前以来,我们的先觉者(尤其是鲁迅)就高喊思想革命;思想革命决不是只破坏旧的反动思想,主要的在建立新的革命思想。土改文件是自有思想革命以来最正确的革命思想的最辉煌的成果,是那思想的实现的具体明细的纪述。”{76}在他看来,土改虽不是中国革命的最高目标,但土改却是革命的必经之道,只有到了土改环节,思想革命才进入了新的阶段,革命才算有了真正的业绩。
与批评、学习和自我改造相关,《野草丛刊》和《野草文丛》出现了较多有关农民的议题,并开始讨论小资产阶级如何完成从思想到情感的转变。
夏衍的《从“樱桃园”说起》指出,当时“连一些似乎和土地问题永不相干的‘读书人”,“也在纷纷的谈论到分田的事情”。他将契诃夫的《樱桃园》读成中国的时代寓言,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地主将失去土地,知识分子将经历自我革命。对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在于,面对农民这个新兴革命主体,如何从理性认识走向情感上的认同。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出身与地主有天然的亲缘,对地主阶级不仅不恨,反而很同情,小资产阶级的转变因此十分艰难。他的选择是,“咬紧牙关吧,这又是一次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试炼。”{77}
秦牧《论看人》的看法与夏衍类似,“农工阶级所以比小资产阶级健康,主要在于农工阶级和压迫者并无‘血缘。”“从整个阶级来说,农工阶级当然比小资产阶级健康,农民和工人要吃饭,当他拿起工具劳动时,他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智识分子要吃饭,当他拿着笔杆劳动时,他不一定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可能正在干着帮凶帮闲的工作,农民和工人没有饭吃,起来反抗压迫,不管他识字与否,他立刻就接触到革命,智识分子感到苦闷,设法解除,他可能从此接触到革命,也可能完全背叛了革命,这其间,认识正确与否,学习努力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一个不识字的农工可以是一个革命者,一个不肯多读书多学习的半桶水的智识分子却很难做一个革命者,因为饥饿导引农工走向革命,再在革命中接受系统的思想,但仅仅饥饿而没有思想的因素却很难使智识分子走向革命。”{78}
在夏衍和秦牧看来,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于地主家庭,与地主阶级有亲缘关系,因此走向革命存在不确定性。农民则不同,他们的出身比小资产阶级健康,具有天然的革命性,似乎靠肉体的本能就能走上正确的革命之路,小资产阶级的本能不可靠,需要思想上转向革命,才能保证其革命性。这种以出身乃至血缘判断人的革命性的逻辑,十分机械,可以看出夏衍、秦牧等国统区知识分子面对革命大潮时的焦虑。这种机械的阶级划分和革命性论断,以简单明了的方式,翻转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大众、领导革命的命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觉放弃了对革命文化的领导权。
夏衍和秦牧等人都认识到,小资产阶级转向的关键在思想改造,但思想转变却并不容易。正如夏衍所指出的,“近来常听朋友们谈起的所谓思想上转得过来和转不过来的问题。有人说:‘形势变了,政策变了,但是这变化来得太快,我们在思想上转不过来。”因为解放战争的进程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以至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跟不上时代,对于知识分子如何完成思想转变的问题,夏衍以乘车的经验说明在时代列车急行时,“应该是这个人和这个时代与社会保持最大可能的接触”,{79}这样才不会被时代列车甩出去。在他看来,要跟上革命的形势,应该多接近现实,多与人民接触。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秦牧和夏衍的说法还比较拘谨,相对而言,郭沫若就激进得多。他的《尾巴主义发凡》以其常见的夸张方式,表达了自我改造的意愿。他说,“士大夫阶级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做人民大众的尾巴。从前的‘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宁为牛后,无为鸡口。特别是‘牛后,这可具有着极新鲜的意义。牛是最好的一个人民的象征。我们要做牛尾巴,这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跟着群众路线走。”{80}与夏衍抽象地说要贴近时代不同,郭沫若指出,知识分子要完成自我改造,就要放低姿态,甚至放弃身为知识分子的矜持,向群众学习。
五、结语
国民革命之后,国民党虽掌握了政权,文艺的领导权却由左翼文化掌握,40年代《野草》对战国策派、自由主义的批评,是进一步争取并巩固文艺领导权的重要环节。到40年代后期的内部整风与自我批评阶段,《野草》所面对问题的性质从左右之争,转变为左翼文学和革命人的再造,以及延安文艺思想如何确立全国文艺领导权的问题。《野草丛刊》《野草文丛》对延安文艺思想在国统区的传播起着积极作用,国统区的左翼经验由此逐步融入到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这完成的是权势的内部转移,是文艺领导权的重塑。
值得留意的是,《野草》同人大多为杂文作家,自觉继承鲁迅的文化和思想遗产,且与胡风等七月派成员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当邵荃麟、林默涵等在《大众文艺丛刊》批判胡风、路翎等人时,聂绀弩、秦似等并未跟进,他们的重心是自我批评,克服都市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向解放区的工农兵文艺思想靠拢。《野草》同人多为左翼作家,他们对群众的态度从早期新文化人的启蒙视野转向发现群众的革命力量,故他们继承鲁迅精神的重点不在国民性批判,而在其后期的杂文精神。《野草》系作家的文化实践及转变过程,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鲁迅批判传统在全国解放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
① 该刊封面仅题《野草》,版权页则是《野草月刊》。但该刊编辑秦似等人在撰文时,均用《野草》,不加月刊二字。相关数据库和资料集,也多用《野草》,而不加月刊。本文尊重该刊编辑用法,且照惯例,用《野草》。
② 该文的领导权概念,指源自列宁而被葛兰西、瞿秋白等东西方革命者使用的概念,参考葛兰西《狱中札记》(葛兰西著,葆煦译:《狱中札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瞿秋白对该概念的使用,参考李放春:《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
③ 《编后记》,《野草》第1卷第6期,1941年2月1日。
④ 学界对战国策派的研究颇为深入,可参考:宫富:《民族想象与国家叙事——“战国策派”的文化思想与文学形态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路晓冰:《文化综合格局中的战国策派》,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李雪松:《“战国策派”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何阿蕊:《战国策派的美学思想初探——以陈铨和林同济为代表》,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等。
⑤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战国策》第1期,1941年1月15日。
⑥ 李怡:《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龃龉——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其历史命运》,《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⑦ 李育中:《教授们》,《野草》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20日。
⑧ 马立业:《历史会重演么》,《野草》第4卷第1、2期合刊,1942年5月15日。
⑨ 陳铨:《浮士德的精神》,《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
⑩ 陈铨:《叔本华的贡献》,《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11} 陈铨:《论英雄崇拜》,《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12} 严杰人:《谈名》,《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13} 琛:《“把船头调转”》,《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14} 胡绳:《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大众生活》新8号,1941年7月5日。
{15} 陈铨:《尼采心目中的女性》,《战国策》第8期,1940年7月25日。
{16} 尹及:《谈妇女》,《战国策》第11期,1940年9月1日。
{17} 余惺夫:《妇女·家庭·“大政治”》,《野草》第1卷第6期,1941年2月1日。
{18} 令狐厚《“女性应该安于生物的平等”论》,《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令狐厚、秦似均为王力之子王扬(缉和)的笔名。
{19} 孟超:《从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说到纵横术》,《野草》第2卷第4期,1941年6月1日。
{20} 愈之《新策士葬送了希特勒》,《野草》第3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
{21} 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22} 沈从文:《烛虚》,《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
{23} 李育中:《教授们》,《野草》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20日。
{24}{25} 沈从文:《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
{26} 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战国策》第10期,1940年8月15日。
{27} 琛:《作品与时代》,《野草》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20日。
{28} 秦似:《“伟大的捕风”》,《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29} 耳耶:《装腔作势的男人》,《野草》第2卷第1、2期合刊,1941年4月1日。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30} 沈从文:《习作举例——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国文月刊》第1卷第2期。
{31} 禄:《沈从文先生的天真》,《野草》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20日。
{32} 木:《“变节”与“脱节”》,《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33} 曹聚仁:《从陶潜到蔡邕》,《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34} 萧今度:《从陶潜说到蔡邕》,《野草》第1卷第5期,1941年1月1日。
{35} 云彬:《替陶渊明说话》,《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36}{37} 绀弩:《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野草》第1卷第4期,1940年12月1日。
{38}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见荃麟·乃超等:《文艺的新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
{39} 秋帆:《纪德所成就的》,《野草》第1卷第2期,1940年9月20日。该文曾部分发表于《战时知识》(第11期,1938年11月10日)、《鲁迅风》(第19期1939年9月5日)。
{40} 荆风:《胡适老了》,《野草》复刊号,1946年10月1日。
{41} 《京励志社一集会 胡适讲制宪对国大情形表示满意》,《大公报》1946年12月18日,第2版。
{42} 陈闲:《胡适博士的迷茫》,《野草》新3号,1947年1月1日。
{43} 胡明树:《胡适之和“好政府”》,《野草》新3号,1947年1月1日。
{44} 绀弩:《论乌鸦》,《野草》新3号,1947年1月1日。秦似:《胡适不办刊物》,《野草》新3号,1947年1月1日。
{45} 周而复:《北望三嘘录》,《野草文丛》第8期,1948年2月14日。
{46} 荃麟:《“文明的果实”》,《野草丛刊》第6期,1947年12月1日。
{47} 适夷:《胡适的妙计》,《野草文丛》第9期,1948年4月10日。
{48} 白坚离:《周作人胡适之合论》,《野草文丛》第9期,1948年4月10日。
{49} 侯外庐:《胡适、胡其所适?》,《野草文丛》第9期,1948年4月10日。
{50} 曾昭抡:《青岛杂忆》,《野草文丛》第10期,1948年6月20日。
{51} 郭沫若:《隔海问答》,《野草文丛》第9期,1948年4月10日。
{52} 參考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53}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修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97-501页。
{54} 朱光潜:《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文学杂志》第2卷第2期,1947年7月1日。
{55} 朱光潜:《苏格腊底在中国》,《文学杂志》第2卷第6期,1947年11月。
{56} 默涵:《当心拆台》,《野草丛刊》第6期,1947年12月1日。
{57} 周而复:《北望三嘘录》,《野草文丛》第8期,第8期,1948年2月14日。
{58} 朱光潜:《给不管闲事底人们》,《周论》第1卷第10期,1948年。
{59} 默涵:《论“不管闲事”》,《野草文丛》第10期,1948年6月20日。
{60} 郭沫若的文章《天地玄黄》发表于1945年,文集《天地玄黄》印行于1947年。钱理群著有《1948年:天地玄黄》,中华书局2008年版。
{61} 三流:《从“点将”到“选佛”》,《野草丛刊》第7期,1948年1月1日。
{62} 佩韦《客气过分论》,《野草丛刊》第7期,1948年1月1日。
{63} 绀弩:《诗人节怀杜甫》,《野草文丛》第10期,1948年6月20日。
{64} 绀弩:《自由主义的斤两》,《野草文丛》第9期,1948年4月10日。
{65} 孟超:《论蒋干》,《野草文丛》第9期,1948年4月10日。
{66} 孟超:《谈奴才渣子的技俩——兼论曹聚仁的〈十年观变杂话〉》,《野草文丛》第11期,1948年8月20日。
{67} 申公:《王老板的故事》,《野草文丛》第11期,1948年8月20日。
{68} 胡绳:《关于加括弧的“民主份子”》,《野草丛刊》第6期,1947年12月1日。
{69}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统区传播情况,可参考刘奎:《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东岳论丛》2018年第1期。
{70} 本刊同人荃麟执笔:《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载荃麟·乃超等著:《文艺的新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
{71} 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见荃麟·乃超等:《文艺的新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
{72} 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见荃麟·乃超等:《文艺的新方向》,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1948年3月1日。
{73} 乔木:《文艺创作与主观》,载《人民与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1948年5月1日。
{74} 胡风:《“举一个例”》,《野草》第3卷第1期,1941年9月15日。胡风:《一个人和一个世界——路翎作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序》,《野草》第4卷第4、5期合刊,1942年9月1日。
{75} 默涵:《关于“浮生若梦”及其他》,《野草丛刊》第6期,1947年12月1日。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
{76} 绀弩:《血书——读土改文件》,《野草文丛》第11期,1948年8月20日。
{77} 夏衍:《从“樱桃园”说起》,《野草丛刊》第6期,1947年12月1日。
{78} 秦牧:《论看人》,《野草文丛》第9期,1948年4月10日。
{79} 夏衍:《坐电车跑野马》,《野草文丛》第7期,1948年1月1日。
{80} 郭沫若:《尾巴主义发凡》,《野草文丛》第7期,1948年1月1日。
(特约编辑:江涛)
Wild Grass, with Its Magazine Ser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Leadership of Art and Literature in the 1940s
Liu Kui
Abstract: Wild Grass, with its magazine series, is an important literary magazine in the 1940s as it, gathering leftwing men of culture, such as Xia Yan, Nie Gan-Nu and Qin Si, played a fighting role in zawen (miscellaneous articles) subsequent to Lu Xu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magazine, for the purpose of fighting for the nations libe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leadership of the left-wing, initiated three kinds of critiqu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olicy School in its promotion of nationalism; of liberalism and the Third Road in the paradigm of the Cold War, with its critique of Shen Congwens art and thought as something between that of the Warring States Policy and liberalism; and of consciou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by actively spreading Yanan thought of art and literature and engaging in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the Kuomintang-ruled areas. The magazines critique of the Warring States Policy School and liberalism is a process in which left-wing art and literature was struggling for, and gradually gained,the leadership of art and literature in the Kuomintang-ruled areas, with self-criticism being an internal construction of the left-wing powers of art and literature and also a link to Yanan thought of art and literature established as part of the leadership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ought.
Keywords: Wild Grass, the Warring States Policy School, liberalism, leadership
基金項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文艺期刊资料长编”,项目编号:19ZDA278。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10DAC726-9F64-40F7-B4A7-7EDA01BD6F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