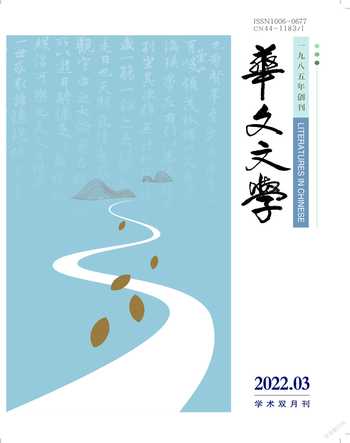作为方法的“盲”
胡星灿
摘 要: 《流俗地》是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黎紫书的最新力著,在书中,作者通过盲女古银霞的生命经验勾勒了马来西亚华族社会及其纷繁历史。其中,“盲”是理解《流俗地》的关窍:首先,“盲”是一种边缘表征,它是主人公所负累的“盲人身份”、“马华身份”、“女性身份”的集中体现,同时,“盲”亦是一种解构力量,它对边缘性的内涵与外延予以审视,甚至消解;其次,“盲”既概括了马华民间社会所承受的权力宰制,同时蕴含着躲避宰制的逃逸路径;最后,“盲”还是当代马华历史“寓言化”的体现,其中容纳着作者对历史的反思。总之,“盲”作为一种方法被植入到《流俗地》中,而通过探寻“盲”的意涵,可以看出黎紫书对边缘、权力、历史等问题的沉思。
关键词:《流俗地》;黎紫书;盲;马华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068-08
2020年,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黎紫书在暌违十年之后,推出了她的长篇著作——《流俗地》。相比于十年前的《告别的年代》,《流俗地》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与转换,它虽然也关注于马来西亚的在地经验,聚焦马华社群的历史过往,但却少了猛烈凄厉,多了“此前少年的包容与悲悯”①。但是,无论是董启章所述的“洗尽铅华、返璞归真”,还是王德威所称的“匹夫匹妇、似水流年的故事”,都只是《流俗地》的表象,探寻小说的深层结构,就会发现黎紫书想要思考与表达的其实远比文本所呈现的要多。其中,“盲”就是理解《流俗地》的重要窗口。在文中,“盲”不仅是故事主人公古银霞的生理状态,它更蕴含着作者对“边缘性”问题、马华民间社会背后的权力结构问题、历史问题的思考。在作者的思考之下,“盲”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能够洞察马华语境,并解决相应困境的方法。
一、“盲”与边缘的表征/解构
毋庸讳言,自马华文学诞生起,“边缘”便是马华作者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黎紫书也不例外。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说中,她甚至一度走向了后现代视阈下所谓的“无边的边缘”(endless marginalities)。因此,《流俗地》对黎紫书而言,无疑是一次回归与超越:一方面,她再次回到了她熟稔并且擅长的领域——一个自足的边缘世界;但另一方面,她没有将“边缘”视为文学游戏的资源或是赚取眼球的资本,而是通过“盲女银霞”,既对边缘予以表征,同时也挖掘“盲”对边缘的解构力量。
(一)“盲”的体验与超越
毋庸置疑,银霞面临着三重边缘身份:盲人身份、女性身份以及马来西亚国族结构中的马华身份。
归根结底,银霞最先面对的是作为盲人的边缘困境,对此,黎紫书也着墨最多。首先,作者突出了盲女银霞的“情之孤独”。银霞的“盲”使她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上学、交友、玩耍,如不是好友细辉、拉祖,她的童年将永困于组屋,然而当二人各自离开、成家后,她又变回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再到妹妹出嫁、母亲离世,银霞注定要寥落此生。即便此后遇到顾老师,但两人也处于不同的视觉维度,对世界的洞察与理解也截然不同;其次,作者描摹了银霞的“生之孤独”。因为“盲”,银霞成为一名德士电台的接线员,每天的生活循环往复,时间也似乎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無。更重要的是,银霞也默认了自己被世界弃绝,她不仅遮掩真实情绪拒绝融入世界,甚至还“自我残疾”——像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指出的“默认权力机制”,主动将自己放置到“另类、异常、边缘化”的位置。②于是,“情”与“生”的双重孤独,使她敏感、自卑、自弃,并最终呈现出“不足”也“无法”被外人道的精神孤独。
但很显然,穷尽“盲”的边缘体验并不是黎紫书的用意,相反,她有意将“盲”作为一种参透“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的视角,并对此加以审视和批判。首先,“盲”的边缘性是滑动的(fluidity),而非恒久固定。事实上,在小说中,银霞和命运的矛盾一直是小说主线,这也暗示了银霞并不屈从于命运,她选择去盲人学校、去德士公司上班,都是彰显其反抗命运的积极力量。甚至可以说,银霞的“盲”所带来的负性价值最终会在她的努力和顽抗中消解;其次,“盲”具有隐喻性与普遍性。银霞固然眼盲,但她内心澄明、向往光明,与此相对,本应光明的外部世界却充满“黑暗”,本应坦荡的人性也无不“溢恶”。更甚至,在《流俗地》漫长的时间线上,作者还突出了历史的曲折回环与现代社会的残忍麻木,这无不暗示了在作家眼中:个体的“盲”不过是一种隐喻,而群体的“盲”、人性的“盲”、历史的“盲”才值得关注;最后,“盲”还意味着尚待经历的生命转机。人世除了苦难,亦有救赎,除了冷眼,还有悲悯,就像王德威所阐释的,《流俗地》终要回答“生命的值得与不值得”③。于是,银霞的“盲”是一种“等待中”的生命状态,是一种静候转机的隐忍态度,这也恰如王安忆判断的“眼看山穷水尽,回眸却柳暗花明”④。
(二)“盲”的介入与重估
除了盲人身份,银霞还兼具马华身份与女性身份,而“盲”的介入则再次重估了这二重身份的“边缘性”。
1. 重估国族与民族。在马来西亚的国族建构中,华族的立场十分尴尬。它通常被排除在国族建制(比如国家文化、国家文学等建制)门外,甚至在国族话语中,它还遭到宰制和“污蔑”,成为“沙文主义”、“单语主义”的代名词。所以,对于华族以及身处马华族群的黎紫书而言,国族一直是一个无法规避的话题,甚至“国族焦虑从上一代到现在都没有减轻。”⑤但有趣的是,在《流俗地》中,国族话题似乎讨论得并不多,这当然可以用王德威的观点“国族大义那类问题早就在穿衣吃饭、七情六欲间消磨殆尽”⑥来解释,但是考虑到黎紫书对国族问题向来的执念,这个观点显然不足以解释全部。
事实上,银霞的“盲”暗藏着黎紫书对国族/民族问题的理解。银霞的“盲”使她无法分别不同民族的显性差异,比如:肤色、样貌、穿着、书籍……。而这些“文化符码”又恰恰是建构一个国族/民族最重要的内核,所以吊诡的地方在于,当一个国家或民族通过历史、文化、知识、宗教、意识形态试图打造一个不可动摇、坚不可摧的“国族”/“民族”神话时,这些神话反倒在一个“微不足道”的盲女面前倒塌,它们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遭到了“盲”的渗透与消解。换句话说,本处于边缘位置的银霞,反倒成为一股边缘力量,穿刺了以“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为工具的国族/民族话语。
2. 重估女性的边缘价值。学界关于黎紫书的“女性书写”研究有很多,但作家似乎反对被定义为女性主义者,她更像是一位对女性有关切、有同情、有吁求的女作家,而不是一位占据“女性主义”资源优势进行申诉、抗议的“代言人”。
而在《流俗地》中,黎紫书进一步将她对女性的关注予以放大。首先,小说毋庸置疑地展开了对“华人女性”问题的关切,这也表达了黎紫书深沉的女性思考。正如陈思和指出的,小说的核心是“华人妇女”的生存境遇问题——她们遭到背叛、强暴、遗弃,几乎没有一位妇女获得幸福,但是黎紫书没有沉溺于女性苦难的诉说,而把重点放在了女性奋斗史、拼搏史的展开上,她强调了华人女性虽身处“边缘”,却向“边缘”借势,并依托“黑暗之力”展开与命运的搏斗。⑦小说中,银霞与顾老师同处电梯间的情节就是一则寓言。当两人处于停电的电梯间时,“银霞这才想起来两人正处身漆黑之中,她说这下可好,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现在你知道我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了’”⑧。显然,这句话点出了两人之间权利天平的不固定性:在现实的(或隐喻的)“黑暗世界”中,处于强势的顾老师所具备的权利机制通通失灵,但相反,本处弱势的银霞却因深谙“黑暗世界”的运行法则,而象征性地占据了强势地位。这也印证了陈思和的观点,不是顾老师给了银霞光,而是顾老师被银霞“驯服”到黑暗里。特别当顾老师随着银霞的描述,在黑暗中想象世界时,银霞如有了上帝创世纪一般的神通:“顾老师依然合着两眼,四周的黑暗坚硬如石,脑中却光影丛生,随着银霞说颜色,颜色便像喷罐里挤出来的彩带四下纷飞;她说形状,各种形状犹如万花筒般在黑暗中奔放旋转,然后黑暗转成白底,横的竖的黑色线条在其上穿梭回旋,不断变形;她说光,便有了光;红黄蓝绿,七彩缤纷的光,四面八方如喷泉涌出。”⑨可见,通过这则寓言,黎紫书概括了她对女性力量的期许。
其次,小说对“女性主义”的展开其实是有限度的。相比于其他女性经典书写对女性身体的、精神的、心灵的深入探讨与开采,黎紫书对女性的理解与爬梳显得相对单薄。比如,银霞在盲人院受到折辱的经验,在黎紫书笔下显得缺乏力道,甚至“盲”还被归因于银霞受辱的主要原因,但是女性所遭受的困境又何止一个简单的“盲”可加以概括。显然,盲人身份作为对性别创伤的总结,反倒证明了作者对女性权力问题兴趣寥寥。此外,顾老师的出现对银霞的女性力量无疑是一种削弱,特别当银霞已然从“黑暗世界”中滋长出生命力量时,实际上任何一种外来力量的赐予对银霞而言皆是干扰。而顾老师的出现,或许也暗示了黎紫书对“女性主义”的建构并不那么自信。
综上可见,《流俗地》通过“盲女银霞”,展开了对马华文学场域里的显学——“边缘”问题的讨论。而“盲”作为一种边缘的象征性表征,同时也被黎紫书赋予了检视“边缘”的力量,在“盲”的透视下,“边缘”的内核与外延重新被定义。很显然,黎紫书对“边缘”的关注,既表现了她对“边缘”的尊重,也展现了她“差异性”(differences)的迷恋。
二、“盲”与“流俗地”的权力结构
《流俗地》作为一部聚焦于“流俗”(马华民间社会)的作品,极大程度地展现了民间世界的丰富性与混杂性。不仅如此,小说还通过“盲”进一步地对“流俗”背后的权力结构予以探讨,此举也印证了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宏论:对日常生活的理解,需聚焦于日常背后的结构性流动,以及“发声线”(辖域化)与“逃逸线”(解域化)的互相作用。
(一)视觉、权力及隐喻
萨特曾用一则比喻指出了视觉与权力的关系:“当听到我背后树枝折断时,我直接把握到的,不是背后有什么人,而是我是脆弱的,我有一个能被打伤的身体,我占据着一个位置,而且我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从我毫无遮掩地在那里的空间中逃出去,总之我被看见了。”⑩诚如其言,“看”是一种力量,它占据主导权,具备先发制人的主动性,而“被看”则是力量的褫夺,它是被动的、从属的,乃至贬值的。无独有偶,笛卡尔的“直觉力”、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的“视觉所及之处,心灵必能到达”{11}、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乃至德里达的“视觉与真理性”{12}都证明了视觉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可以说,在“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中,视觉被赋予了权力,并最终形成了“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价值秩序,一套用以建构从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文化规则的运作准则”{13}。
由该观点出发,就可以发现,《流俗地》的盲女银霞实际上被黎紫书赋予了更深的意涵。银霞因“盲”处于“黑暗世界”,然而这个“黑暗世界”的构筑离不处于光明世界的正常人的参与,因此,银霞的被忽视、漠视、遮蔽,这何尝不是“盲”背后“权力丧失”所造成的。不仅如此,银霞的“盲”还暗喻了被作者称为“流俗地”的马华民间社会。因为民间社会同样缺乏曝光机会、不占据权力资本,所以它俨然就是斯皮瓦克所述的“庶民无法说话”(subaltern can not speak),它与银霞一样同处于一个被历史、宏大叙事、国家话语所抛弃、噤声的“黑暗世界”。换言之,银霞的“盲”成为理解“流俗地”的一个独特视角,“盲”的背后所暗藏的权力结构与价值梯度,在“流俗地”的运行背后同样得以显见。
但是,黎紫书并没有因为觉察到“盲”/“流俗地”背后的权力结构而悲天悯人,正如银霞自由、自如地,甚至可以说游刃有余地生存于她的“黑暗世界”,“流俗地”本身也有一套独立的、成体系的运行法则,这个法则并不会轻易遭到篡改而失效。由此可以看出,黎紫书有意呈现马华民间社会的力量,并且對民间社会的自足之力充满信念:
何为“流俗”?“俗”即日常性。整个小说的分章布局,几乎是以银霞的日常生活为线索的,因此,围绕银霞展开的叙事涉及最为日常的人、事、生活:比如,银霞陪伴于母亲身边,听东家长、西家短,发现马票嫂、大辉等人经历的风雨与世代间的恩怨情仇;又如,银霞经历底层社会中小人物的光辉与溢恶,其中,古道热肠的伊斯迈、顾老师,对盲人抱有敌意的何门方氏,阴暗丑陋的“那个人”……;再如,她还见证了莲珠姑姑的生命变迁,记录了锡都的风雨、华族历史的兴衰。可以说,在银霞的串联下,整个近代马华民间社会的“流俗”面貌徐徐展开。而从“流俗”中,不妨看到,这个民间社会虽然如“盲”一样充满黑暗,但它是隐蔽的、自足的,有着自己的江湖规矩,不受掌控、不被约束,也因此有着野蛮的、迥异于庙堂的力量。
(二)“盲”、流俗地及“神鬼之力”
不仅如此,黎紫书还援用“魔幻现实主义”,进一步挖掘“盲”/“流俗地”的“神鬼之力”。
首先,银霞与文中象神迦尼萨构成互文关系,由此银霞也被赋予了“神力”。在印度教神话中,象神迦尼萨在记录《摩诃婆罗多》时写坏了智慧女神赐予他的神笔,为了完成书写,他折断象牙、以此为笔,象神的自我牺牲精神成为印度教广为颂扬的教义。而银霞的“盲”,也被黎紫书视为自我牺牲的标志,正如文中迪普蒂所述的:“你看啊银霞,迦尼萨断一根牙象征牺牲呢,所以那些人生下来便少了条腿啊胳膊啊,或有别的什么残缺的,必然也曾经在前世为别人牺牲过了。”{14}而牺牲伴随着受难,正如象神自断象牙、独自忍受痛苦,银霞的“盲”也充斥着重重苦难,其中“盲人院受辱”、“童年结束”、“母亲离世”都是苦难的集中体现。很显然,文中银霞与象神迦尼萨形成了互文,两者的牺牲与受难彼此呼应,银霞由此也具有了神性意涵。此外,象神迦尼萨亦象征智慧,而在小说中,黎紫书多此通过不同场景表现银霞的聪颖,她甚至称呼银霞为“人肉地图”、“盲人之光”,文中的迪普蒂也称之为“这真是个迦尼萨大神眷爱的孩子”{15}。可见,银霞已被作者描述成象神在凡间的化身。
其次,银霞通过“盲”打通人间与“鬼蜮”,因此也获得了“鬼力”。在《流俗地》中,黎紫书对马华民间社会的“魑魅魍魉”肆意张扬,她并不忌惮“虚构性”对这部强调“写实性”的小说会构成内在的威胁,也不避讳在以五四精神为宗的马华社群对“驱鬼”的强调远甚于对“招鬼”的重视。之所以大开“鬼门”,是因为作者实难忽视“鬼魅”所蕴含的“死亡神秘之美及生命的艳异风景”{16},更因为“鬼魅”背后暗藏着隐秘的、强悍的、能与宏大叙事、权力话语构成抗衡之力的“鬼力”。
所谓“鬼力”主要体现在银霞身上。因为银霞眼盲,她能看见正常人无法看见的鬼界,同时也拥有了与鬼沟通的能力,比如,大辉家请道士驱鬼时,银霞却听见了女鬼的声音:“银霞却明明听到了,女子的哭声如一缕细烟,呜——呜——呜——幽幽穿梭在那法器的叮咛中,仿佛与那铃声对话,欲断难断,如泣如诉。银霞有点毛骨悚然,手指仍挂在网上。她几乎以为那女子终于会用哭腔诉她的苦,将平生唱成一段苦情的折子戏”{17};又如,银霞有梦游的习惯,她被多次撞见与鬼嬉戏:“银霞当时披头散发,在原地不断兜圈子,还嘻嘻哈哈,像是在跟他看不见的‘人’玩耍。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叫我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宝华心里一寒,以为见鬼。”{18}而正如《尔雅》所述的“鬼之为言归也”{19},黎紫书之所以赋予银霞“鬼力”,是因为她想要召唤那些被历史理性、宏大叙事所冲刷、所遮蔽的人与事,并为它们找准存在的位置。在“鬼力”的作用下,那些“如废墟、如断片”的人与事纷纷“复归”其位,而作为“流俗地”的马华民间社会也因此获得更为可感、可述、可供言说的存在合理性。
不仅如此,正如蔡九迪(Judith T. Zeitlin)在分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时说的:《聊斋》的价值不仅在“志异”,而更在于反思“寻常”世界。{20}当“异”与“常”互相言说时,那么所谓“常”的世界、规范、价值便不再那么绝对且不容商榷。同理,借着“鬼力”,黎紫书构筑了一个“另类”的世界(world of alterity),这个世界也终将成为外部世界的对立面、参照面,进一步促成外部世界的价值更新、权力位移。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黎紫书曾明确表示自己存在“两幅笔墨”:记者的笔法/小说家的笔法——“当记者的时候是站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角度进行采访,目的是唤起更多人的关注;而当小说家的时候就必须主动放低姿态,不能让人感到有主体介入其中。”{21}书写“鬼力”即是一种放低姿态的,深入民间世界的表现。而银霞身上别样的“巫风传统”,既有华夏文明的影子,又夹杂着印度、马来文化的多重因素,这也为我们管窥底层马华社会多元杂处、巫风盛行的真实生活提供了可靠依据。
总而言之,正如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所言的,若要理解日常,则需要捕捉日常背后的“发声线”与“逃逸线”。在《流俗地》中,黎紫书就通过“盲”,即概括了马华民间社会所承受的宰制、苦痛,更指出了它规避、颠覆、逃逸权力辖制的路径,这也显现了黎紫书对马華民间社会极为成熟的理解。
三、“盲”与马华历史的反思
对于马华七字辈作家而言,刺探并重塑“马华历史”一直是他们的创作重心,特别在后学浪潮的探照下,他们更是赋予了“马华历史”破碎、曲折的样态。作为七字辈作家的中坚,黎紫书也曾在《山瘟》《七日食遗》《告别的年代》等作品中反复解构“马华历史”,这也恰如朱崇科总结的:“某种意义上说,大马的华文小说似乎或多或少都会涉及本土华人的历史,这似乎是一种文化抗争,一种宿命,或自我身份的确认,或者也是一种‘感时忧族’的传统延续,也或者是一种耳濡目染的自然流露。黎紫书也不例外。”{22}
而在《流俗地》中,黎紫书虽一如往昔地关注“马华历史”,但相比此前创作,她却从后现代迷障中出走,一改以往的解构精神与戏谑笔法,以“求真意志”介入历史,力图呈现“马华历史”的真切性。于是,黎紫书放弃所谓的“编史超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拒绝“历史的文本化”{23},而是十分坦诚、真挚地书写被大历史遮蔽的小历史,去呈现马华民间社会的真实样貌。
(一)“盲”与历史寓言
在此前介入历史场域时,手握后现代“解构机器”的黎紫书频频遭受诘难,评论者不仅质疑其历史祛魅是否具备必要性,同时还怀疑她的异质性是为了“付与”海外读者的异邦想象。归结原因,因为黎紫书与其书写的历史相隔太远,所以造成其书写合法性的丧失,但反过来,也正因为始终与历史保持距离,她如“女巫”般绚丽夺目的后设技法才能得以施展,这也印证了王德威的观点:“黎紫书其生也晚(一九七一),在她成长的经验里,六十年代或更早华人所遭遇的种种都已经逐渐化为不堪回首的往事或无从提起的禁忌。……他们并不曾在现场目击父辈的遭遇……”{24}。
所以到了《流俗地》,面对自己十分熟稔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和“在地经验”(local experiences),黎紫书具有了言说的合法性,她放下过往历史,转而专注于现世人生。她通过银霞——一个跟她差不多岁数,并且相似度高达七成的盲女,在铺展其生命轨迹的同时,也一路将当代“马华历史”娓娓道來。而如同肖鹰所言:“进入历史,就是在当下自我的存在中,复活历史被时间抽象压抑了的丰富存在,把历史展现为一个活的有意义的存在空间。这就要求个人必须把历史作为自己的命运来承担。”{25}由此可见,黎紫书在记录当代“马华历史”时,已然将之视为自己的使命。因此,《流俗地》呈现出难得的“真”与“诚”。
在“真”与“诚”的驱使下,“盲”成为黎紫书对当代“马华历史”的全新概括。
毋庸置疑,自1957年后,马华族群便开启了被遮蔽的历史。在政治场域,华族阵营一路败退,特别在“五一三”事件后,更是受到宰制,继而触发“寒蝉效应”。相应的,在文化、经济、教育等场域,华族社群也遭到限制。换句话说,在当代马来西亚国家历史中,马华历史始终是缺席的,而诚如詹明信所言:“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6}由此可见,《流俗地》中盲女银霞的生命历程,亦可视为寓言化的历史。
银霞并非天生失明,在她出生以后,曾短暂地看到过世界,因此“以后当人们对我说颜色,说形状,说线条,说光,我都觉得自己能意会,知道他们在说什么”{27}。因为无法辨认外貌,所以她在16岁受到侵犯后只能默默承受,“长那么大,她没有经历过这样充实的黑暗,如同滚烫的岩浆涌入她的嘴巴耳朵胸腔肺叶胃囊……身体成了躯壳,所有的空处都被液态的黑暗填满,迅即凝固”{28}。直到遇见顾老师,银霞才感受到黑暗消散,“眼前的黑暗逐渐被稀释,从一堵厚实的高墙缓缓动摇,变成了雾……她便在如雾的黑暗中被高高举起又被轻轻放下。”{29}可以说,银霞生命的高低起落,与马华族群的曲折命运别无二致。最先开始,马华族群也是“光明”的,只不过最后在各方势力的打压下被迫妥协,至此步入“黑暗”。在马来西亚成立后的第16年,马来华族也经历了堪比“强暴”的“五一三事件”,事件发生后,华族力量旋即缄默。直到2018年马来西亚大选,巫统(UMNO)与国民阵线执政联盟(Barisan Nasional)结束了61年的政权,马华族群才又逐渐看到生存的希望。简言之,银霞与马华族群的命运同声共气、彼此呼应,而《流俗地》描写银霞“盲”的命运、感受与变化,即是对起起落落的马华历史的寓言化表征。
(二)黎紫书的历史观辨析
必须指出,虽然《流俗地》不似黎紫书此前的创作有着强烈的解构历史的野心,甚至它对历史多了“真”与“诚”的介入,但这并不意味着黎紫书的历史观发生变化。事实上,由始至终,黎紫书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悲观的,她更愿意相信历史充满着偶发性和虚无感,就像她在《静思雨》总结的:“只觉‘史’字也虚,而且总思疑历史这卷宗将尽,人类为生命与存在自定义的价值将如一把界尺掉入无极”{30}。换句话说,虽然《流俗地》的解构意识并不明确,但从深层的价值取向看,《流俗地》与黎紫书此前创作无疑是趋同的。
首先,《流俗地》有着消隐历史的倾向。如上所述,《流俗地》的历史是以寓言化的方式加以呈现的,但即便是谈到历史,作者也只着墨了两次:一次是祖屋男人聚在一起,讨论二十年前的“五一三事件”,“这些人见过动荡社会的,谁没经历过当年的五一三事件呢?时隔将近二十年了,大家提起这个仍禁不住脸上色变,对时局愈发担忧”{31};另一次则是文末马华族群对2018年马国大选的反应,“银霞听到满城欢呼,真的就像刚刚射进一球了,同时终场的哨声吹响。”{32}两次书写皆如闲庭信步,并无浓墨重彩地描摹。除此之外,虽然文中也提供了很多历史碎片,但它们都隐藏在漫不经心、羚羊挂角的闲笔、对话、插科打诨之中,并不容易发掘。可以看到,相比之前将历史作为创作的“前背景”(foreground),黎紫书在《流俗地》中却对历史相对冷感。
其次,《流俗地》表达了对“现实”/“历史”之疑虑。毋庸置疑,《流俗地》可被称为“写实小说”,其中流露出的“少见的包容与悲悯”,以及作者对马华“底层世界”的关注,都佐证了小说的“写实主义”倾向。但是不同于传统写实主义小说家对历史现场、现实场景一丝不苟的描摹,黎紫书显然更重视“内在的真实”。众所周知,“真实”是文学表达的主要问题,它来源于现实,却不等同于现实,路文彬就曾指出,“‘眼见为实’之‘实’意指的只是客观之实……而真实则不然,真实依赖于主体,与主体的智慧相通”{33}。换言之,所谓的“现实”不过是依托于“视觉”的盲目的、不可靠的截取与复制,缺乏反思的维度和求索的纵深,因此它未必是真实的。而在《流俗地》中,黎紫书也讨论了这一问题。作家将盲眼的银霞,当作游历当代马华历史的“维吉尔”,这样看似吊诡的操作,却恰好证明了往常的、常见的“现实”与“历史”(过去的现实)充溢着荒谬与不可信。在小说的尾部,黎紫书就再次申明她的观点。当马华族群为大选结果狂欢兴奋时,银霞却显得异常冷静,“她心里一紧,眼前的黮漶黑暗忽然凝聚起来,变得厚实无比,似能反弹出回声”{34},显然她对大选结果是否能改变华人境况是存疑的。与此同时,一只猫不请自来,全文戛然而止,这样的安排也显得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充满着无解与荒诞:
“‘普乃?’她睁开眼睛。
房里先是一片静寂,然后那猫说——
喵呜。”{35}
总之,在《流俗地》中,黎紫书展开了她对马华历史的反思,她没有如往常一样积极地投身历史的祛魅,而是通过“盲”,将历史以“寓言”方式加以呈现。然而,尽管探照历史的方式变了,但她对历史的真实性始终存疑,这也是为什么《流俗地》对待历史颇为冷感的原因。
四、总结
《流俗地》是黎紫书的复出之作,其中既融入了作者对马华民间社会、历史的“包容与悲悯”,同时也隐藏着她对马华社群边缘性、权力结构、历史钩沉等问题的关注与反思。然而遗憾的是,黎紫书未能进一步探索文学性的边界,不仅在技法方面,《流俗地》相比《告别的年代》多少显得平实、质朴,其立意也与她极短篇小说相比缺乏开阔的“世界视野”,这或许与她的创作视野转变有关(由“作者”出发转为由“读者”出发)。总而言之,《流俗地》是黎紫书一次全新的尝试,而该尝试也为“马华文学的成功市场化”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范式。
①③⑥ [美]王德威:《盲女古银霞的奇遇——〈流俗地〉代序》,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第19页,第16页。
②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页。
④ 王安忆:《之子于归,百两御——〈流俗地〉代序》,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第29页。
⑤ 彭美君:《在“文长慎入”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文学吗?专访小说家黎紫书》,见https://theinterview.asia/people/26042/
2021-5-20。
⑦ 笔者从陈思和的访谈中概括得出。
⑧⑨{14}{15}{17}{18}{27}{28}{29}{31}{32}{34}{35} [马来]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407页,第407-408页,第186页,第73页,第108-109页,第97页,第407页,第413页,第458页,第17页,第459页,第460页,第460页。
⑩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26页。
{11} Hans Jonas, “The Nobilityof Sight”, in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4-4(1954): p.519.
{12} [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册,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7页。
{13}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文艺研究》2006年第1期。
{16} [美]王德威:《魂兮归来》,《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19} 《尔雅·释训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年版,第61页。
{20} Judith Zeitlin: Historian of the Strange: Pu Songline and the Chinese Classical Ta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
{21} 根據黎紫书采访得知。
{22} 朱崇科:《论黎紫书小说的“故”“事”“性”及其限制》,《当代文坛》2015年第4期。
{23} Linda Hutche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53.
{24} [美]王德威:《异化的国族,错位的寓言——黎紫书〈野菩萨〉》,黎紫书:《野菩萨》,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5} 肖鹰:《真实与无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26}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桥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30} [马来]黎紫书:《静思雨》,《暂停键》,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33} 路文彬:《视觉主导的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Blindness as a Method: On Li Zishu’s Vulgar Land
Hu Xingcan
Abstract: Vulgar Land is the latest powerful work by Li Zishu, a Chinese Malaysian woman novelist. In this book, the author depicts the complicated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in Malaysia based on the life experience of Gu Yinxia, a blind girl. Blindness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Vulgar Land. First of all, blindness is a symbol of marginality, an epitome of the identity of the blind, of Chinese Malaysian and of women, that is the burden of the protagonis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lindness is also a deconstruction of power as it examine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marginality and even dissolves it. Secondly, blindness not only categorizes the domination of power as borne in Chinese Malaysian society but also contains a path of escape from the domination, and, finally, blindness is also an epitome of allegorization of Chinese Malaysian history that contains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upon it. In sum, blind, as a method, is planted into Vulgar Land, and, through a search fo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blindness, one can see how Li Zishu thinks about issues like marginality, power and history.
Keywords: Vulgar Land, Li Zishu, blindness, Chinese Malaysian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