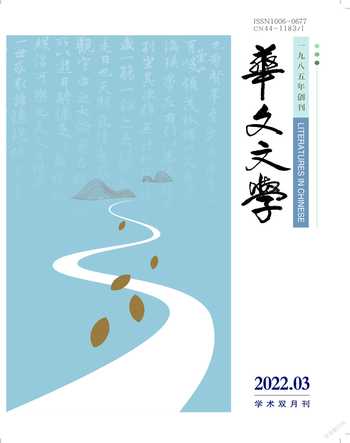迂回叙事中的伦理质询与记忆图谱
张益伟
摘 要:哈南的小说承继了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传统,在技术上惯于使用迂回叙事这一方法,在跨文化视域中讲究介入对民族性伦理的思考的深度,注重挖掘那些隐匿的伦理元素的分布及其跨民族的兼容性。小说以文物、情感为媒,不断开拓中国和日本两种记忆图谱的题材边界,娴熟高超的技术处理使得意绪化、丰盈性、立体性成为小说的风格标识,表现出哈南作为一个小说家具备的极强的艺术感受力。
关键词:哈南;伦理质询;迂回叙事;中国记忆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2)3-0045-09
新世纪以来的日本华文文学,在文学思想资源的开掘和艺术的垦拓方面均做出了不少努力。其中,哈南的小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哈南原名徐金湘,出生于福建莆田,1988年旅居日本。出国前的哈南已是福建作家协会会员,在《福建文学》发表过《又是一个月夜》等小说。由于初到东瀛时身份及职业的转换,他的创作暂停了一段时间。新世纪以来,他又重操旧业,在创作的体量和数量上均保持不断攀升之势。哈南的小说属于现实主义写作范畴。他突出强调叙事艺术的苦心经营,讲究叙事手法的创新,从而让小说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安静感和精到性。他擅长从题材中捕捉叙事的突破口,秉承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以迂回叙事不断介入历史与现实,进行跨文化伦理问题的探索。将哈南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便能从中窥见其写作的丰饶意义。
一、以文物为媒:伦理质询与
认知壁垒的打破
从1988年算起,哈南旅日已逾30年,可谓改革开放后“出国看世界”较早的一批中国人的代表。从计划经济社会输出到国外的这批中国人,大都经受了被现代性文化景观逼视的震撼体验。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声、光、电、影,个体情感记忆中的复杂性与断裂感是那批出国者不得不面对的共同语境。同为福建的作家黄星夜曾在《东京都的福建先生》中描绘过中国留学生黄天民的尴尬处境:“他的东京生活是从银座开始的,可是银座的生活并不属于他。”①荒煤在给旅日作家蒋濮的小说《东京没有爱情》的序言中说:“总之,不要问她们从哪里来,都不过是这豪华世界里无奈漂荡的一叶小小的浮萍,在东京流浪、流浪。东京恋也好,东京梦也好,反正东京没有爱情!”②很多年以后,我们在哈南的小说《猫红》(2018)中,得以看到他笔下主人公成之久的另一种“叛逃式”镜像:“因为他尽量地让自己远离初到日本时的一段艰难日子,想都不愿想起。越是被人认为值得怀念的地方他越是想逃离”。③哈南在日的主要工作是瓷器交易。青花瓷除了使用价值外,其高超的技艺与细腻华美的纹理所表征的古典美学期待,恰好可与日本和服、浮世绘、卡通等符号相抗衡。同时,瓷器也在一定程度上纾解着哈南的文化乡愁,拓宽着哈南愈加开阔的审美视野和学术视野。哈南曾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过文章《日本元青花收藏和研究现状》④,并将青花瓷这一物象放置于社会发展的流脉之中,以小说的形态赋予这一“凝固了的人文理想”⑤更多的想象与考量,进而勾连起特定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史和交流史。
长篇小说《猫红》从跨文化视域呈现了主人公成之久的异国商贸和情感的变迁。小说一方面将成之久的商业探险作为主要题材进行叙事,生成特定年代的经济曲线。另一方面,深入捕捉人物的心靈变迁与伦理观念的浮动与转换,努力掏取和思考一个核心命题:跨民族伦理的兼容问题。民族性伦理一旦形成,便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跨民族交际过程中,伦理的冲突和媾和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差异和冲突会以各种形式体现在人们的生活惯习、历史传统、审美心理、宗族观念、权力规训等不同领域。正如安东尼·D.史密斯所指出的:“无论你留在自己的共同体内,还是迁移到其他共同体中,你仍然是你所来自的共同体的无法改变、不可分割的一员,并且身上永远带着这个烙印。”⑥成之久首先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持有者。他出国前是机关小职员,贷款来日本,最初在中华料理店打工,接着依靠日语翻译过活。彼时日本式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经济神话”,虽然很快就进入了泡沫化时代,但现代性的发展已经十分充分。这一新生场景之于彼时刚从中国大陆走出来的成之久来说,必然充满着诸多探险与挑战。基于十年文革“破四旧”运动的影响,文物符号及其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也跌宕起伏,而正是现代性的崛起才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性产品具有了奇观性与“被凝视”的价值,青花瓷的地位“今非昔比”。成之久的目光为现代性所牵制,他的双眼紧盯着外面的世界。可一旦商业伦理与逻辑对人实行改造,人很容易产生对原初伦理的叛逃意识。成之久与妻子之间的矛盾在小说中得到了细致的刻画。妻子对他的支持和怀疑,对他的妒忌和释怀;成之久抛家舍子后对妻子的背叛和忠实、反抗和无奈等都显示着一个从侨乡出来的人对原初伦理的逃离。他拿着元青花四处寻找鉴定师和拍卖行,询问其真伪和价格几何,甚至少不了从中受骗,也在所不惜。但是让其没有料到的是感情生活一旦渗入到日本伦理之中,诸多潜藏的矛盾便浮出水面了。
随着成之久商业贸易的开拓,他认识了日本女孩惠久美,两人相爱。正是惠久美的出现填补了成之久的异国情感空白,在惠久美这里,成之久一度茫然的伦理选择再度回归到中国传统中来,惠久美以日式伦理唤起成之久内心最为柔软的部分,遂引导他主动回到了中国传统伦理轨道上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成之久的伦理道路走向:从对中国伦理意识的逃离到经受现代性伦理的迷茫,再到回归中国传统伦理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成之久伦理观念变迁过程中,惠久美所代表的日式伦理导向,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传统伦理与现代精神的巧妙组合构成了当代日本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伦理精神”⑦。日本既有着商业层面极为现代的一面,也有着人伦风俗上极为传统的一面。如果说成之久看到的更多的是日本社会开放和经济发达的一面,这一面是现代性对物质繁盛和价值成功学的确认,那么他没有看到的是日本社会传统和保守的另一面。这另一面构成了成之久认知上的偏差和“错讹”,影响他对日本的理解。果不其然,他的计划和“假离婚”方案非但没有赢得惠久美的赞赏,反而适得其反。他试图通过商业成功学来为自己的异国人身份“正名”,迎来的却是惠久美的责难和“当头棒喝”,这对成之久来说,是始料未及的。在情感征途上,成之久原本希冀成为一个凯旋的战士,不承想,却成了一个罪人。小说描写了成之久被惠久美冷落后的忧伤与错愕,惊悸与矛盾,也从叙事者视角对以成之久为代表的中国人心态及日本人心态作出比较,当“假离婚”事件公开后,叙述者说:9DFD329F-1745-4B52-A7FF-7E21086F462B
“日本人在处理这一类的事情时不但不会去自投落网,而且即便是被揭露了也首先得矢口否认——我的记忆中没有这件事——这句话差不多成了日本的流行口语”。⑧
由此看出,成之久的行为与惠久美为代表的日本人伦理心态构成的相悖和冲突。前者着意于对所谓事实真相的呈现,后者则着意用回避和忌讳的姿态面对错误,后者的一种心态固然让创伤很快得到疗愈,让历史变得相对轻盈。但两人之间的冲突与磕绊便也就此开始。以至于惠久美之后的行为和言辞在成之久看来,落落寡欢,难以为继。“假离婚”事件发生后,在惠久美眼中,成之久“是一个不真实的自己,一个不是他的他。”⑨在他们结婚时,惠久美甚至说“我不是跟你结婚的。我是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⑩
“所谓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11}布尔迪厄在论及民族性惯习的作用时,强调了惯习在日常伦理中的生产作用,惯习渗透在包括情感在内的生活的各个角落,构成人们思维运演的组成部分,中国和日本之间惯习的差异以一种隐匿却又无处不在的形态呈现在成之久的情感生活之中。如小说叙述者对成之久行为的一个评价:“在什么事情应该如实交代什么事情应该隐瞒到底上面和一般人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标准。这使得他在许多人都很容易让自己洁白无瑕的地方却沾上了疵点,可是因为他的傻里傻气,在那些其实能够一了了之的地方却往往给自己找麻烦,不让自己轻易地过关。这是只属于他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从表面上看是抹黑了,实际上与欲盖弥彰的意义相反,因为是自己去显露了,有时候反使他有点像是出污泥而不染似的,给人以光鲜的感觉。”{12}成之久自身的感觉不代表惠久美的感觉,在日本人眼中,成之久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则不一定那么“合乎情理”。小说还叙述了成之久对惠久美的宗教祭拜行为的诸多不解和困惑,诸如惠久美多次对观音娘娘像座下一个塑料纸里的小叶片进行祷念,尤其是“猫红之死”一事给予惠久美的冲击,让其行为显得真挚虔诚,却又暧昧含混,“日本人的暧昧同样在惠久美的身上体现着,为了避免触痛对方,经常只在要说的事情的周边做一些暗示。”{13}直到小说最后,成之久似乎都还被“埋在鼓里”,不知道“猫红”除了是惠久美喜欢的一条狗之外,还是他和惠久美的一个尚未出生便夭折的孩子。而惠久美却以惊人的忍耐力守住了这个秘密。这里,我们看到了不同伦理裹挟之下成之久的矛盾,也可以看到惠久美的生活中日本神道观念的积极参与。有学者论及宗教元素所参与的日本现代性过程中的日本伦理构成:“神之道不出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常生活之道就是神道”。{14}成之久之于惠久美来说,显然是惯习和伦理场域之外的他者。惠久美一方面爱着成之久,另一方面却又流露出对成之久的某种超脱和排挤。显然,她是将一种神道伦理具体化到了她个人的行为之中,我们从惠久美形象生成中可以看出神道伦理在日本现实中的持续性存在。
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的伦理观念不但遭遇着冲击,也潜伏着危机。成之久注定是情感世界的溃败者。小说最后描写了其苦心经营的元青花在地震中破碎了,作为古典中国物象的象征,元青花以其伤逝美学隐喻了成之久伦理观念的“落地”与回归,是成之久心性从最高处的一次“陡降”和“坠落”。
小说使用了两条线索展开叙述,用第一条线索描述成之久的商业历险,凸显其悲壮色彩,用另一条线索描述成之久的情感经验,再现他伦理观念的断裂和修复过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成之久对现代化的接受是在一种茫然和未知中边摸索边前行的。他以自身的故事说明了中国传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尴尬境遇。到小说《新宿三丁目》中时,哈南通过一个女性人物的悲剧再次说明跨民族伦理难以兼容这一问题。《新宿三丁目》描写了中国女孩孟茵在日本打拼且殒命的故事。孟茵在国内大学毕业后来日本,弹得一手好琴,舞蹈也让人震撼,曾参加过日本的盂兰盆节活动。孟茵的女儿娜娜因缺乏原生家庭的关爱成为一个“问题少年”。身为单身母亲的孟茵于是活在忐忑不安之中,依赖药物过活,最终吞服安眠药身亡。
与孟茵的“轮廓式”再现形成对应的,是叙事者对孟茵死亡原因的侦破。原来孟茵和日本人加藤在年青时相恋,加藤为了争取和孟茵走到一起,排除了家族的一切阻扰。就在他们即将步入婚姻殿堂时,孟茵告诉了加藤从前的一段经历,即孟茵初来日本时曾在新宿三丁目风俗店工作过的事实,加藤对此无法忍受,提出和孟茵分手。对孟茵来说,她秉承中国女性对爱情和婚姻的尊重原则,正是婚姻的神圣感,驱使她本能地把一個透明的自己托付于对方,这是中国男女之间亲密无间、情感真挚的一种明证。对加藤来说,孟茵的这份“供词”却成了一份“罪证”,成为加藤情感伦理认知中一道巨大的屏障,无法逾越。由此,两人分道扬镳。
孟茵的悲剧是跨文化伦理的差异造成的。感情最终敌不过现实伦理的羁绊和阻隔,这种差异主导的伦理观念让感情不再起主导作用。哈南在小说中强调了现实性伦理秩序和惯习对人们行为的规约,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制约作用十分强大。
二、作为方法的迂回叙事:
用情绪包装情节
李长声曾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论,首先要找出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特色,但人性是普遍的,所以找出衣帽的不同很容易,辨认国民性的不同就不容易了”。{15}对国人而言,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一方面构成了表述的焦渴,另一方面因“那场战争”{16}在其中的充填构成了言日的困难。记忆坚硬如冰,如何撬开言日的困局,在当下的语境中,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难题。在这方面,说与不说的矛盾、说与如何说之间的困境挣扎,构成了文学叙事的绞链。在一定程度上,小说以其虚构属性与想象张力形成了言说的自洽性。相较于日本其他华文作家,哈南虽熟谙日本文化,但他却从不将个人的观念以凌厉的笔法或外向凸显的作法来给予呈述,而是选择一种“迂回”战术。此种方法与儒家“游于艺”的至高境界有着深刻关联,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距离”法,这一点对身为海外华人的哈南来说,另辟蹊径,颇为适用。张悦然说“靠近可以以一种远离的方式来实现”,{17}空间的远隔未必就是记忆的丧失,近距离的细察反而会影响凝视视角的转换,恰恰是两种视角的适当结合,以一种“若即若离”的姿态,方能抵达对“艺”之“真身”的窥视和揣摩。从远距离的观察与近距离的融入之中,哈南不断反省中日文化,并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呈现跨民族伦理观念的差异和兼容性。9DFD329F-1745-4B52-A7FF-7E21086F462B
对哈南而言,情感是人生存的基座,以情感作为中轴线审视人性是一条最佳路径。由此,人的情感底色与倚重、变化过程以及伦常观念使其小说充满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人物的深度自省和思考继承了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布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塑造传统。人物情绪与意绪化的浓墨重彩,又显示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其获得了高超的情感处理技术——迂回叙事。无论是《金戒指》《歪嘴堂官窑》,还是《北海道》《诺言》,他都突出表现人物情感变化的流程,注重拿捏人物的情感分量,经过艺术的调配,这种写作便获得了汪曾祺所说的“要贴到人物来写”{18}的效果。
迂回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前进,而是于曲折的进路中抵达对人物心灵体验的捕捉和描绘。迂回需要不断周旋,对作家语言的处理能力极为考究。在迂回方法指挥下,哈南重视对情势或曰场域的营构,他重视酝酿情势,通过巧妙虚设情势,制造精致的故事装置。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一向重视情节不同,哈南更重视利用气氛的渲染和情感的积累达到对情节的铺陈,从而让情节故事被一种情势包裹着不断向前。在《猫红》中,小说这样描述成之久的情书信笺被前上司的女儿烧掉后的感受:“被烧毁掉的只是一半。另一半却留在了成之久的盒子里。烧毁的理由很简单,连小孩子都会明白。可是得以保存的却是一个很难去把它揭开的秘密,是成之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而且对他来说,烧毁和保存仅仅是一对可以替换的动词,两者之间只有一条十分模糊的界线。因为场合的不同,客观情况的不一样,被烧成灰烬的信笺有时候反而更加容易保存。相反的,你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守着往往只不过是遂了你把他们保存下来的心愿而已。有些东西你不愿意看到它们不复存在,那也只是由于你始终不理解它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因此即便它们作为一种形体被保存下来,而实际上你仍然没有办法理解它们并且拥有它们”。{19}这段描述快速捕捉到成之久彼时内心的斗争状态,被烧毁的信笺寄托着成之久难以排遣的情感矛盾。“烧毁”和“保存”二者之间的辩证斗争正是成之久情感的外化,挣扎与掣肘之后,是一种无奈与超脱。这既符合记忆本身的存储和清除的本质特征,又十分形象地传达出了人物多思的性情。
小说《那一刻你不再担保》充分运用了“担保”一词本身的双重内涵:身份担保与情感担保,突出在日中国人欣欣身份的复杂性。欣欣被日本女孩京子追求着,京子的父亲涉谷恰好是欣欣的担保人。哈南不断调用叙事视角,为了表现欣欣对担保人涉谷的恩情,小说这样描写:“将来是极其遥远的,他恨不得眼前就有一个报答的机会。比如说一部汽车冲过来,眼看就要撞到涉谷身上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欣欣把涉谷拉到了一边;要不就是发生了地震,所有的房子都倒塌了,他却把涉谷压在自己的身子底下,贴贴实实的,让涉谷安然无恙。”{20}为了取悦报恩,欣欣内心的急迫焦渴而又情愿牺牲的心态表露无疑,这种思量可触可感,通过“条件假设”,让情感获得了“空间化”的特殊处理。《诺言》更是将两个成年异性之间的一个诺言描摹得缤纷多姿。“我”与日本女孩伊藤相约一起打乒乓球,事件虽小,却在“我”心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诺言不仅关涉着契约信用,关涉着人格尊严,还关涉着一个异国男人不服输的精神。因此,为了信守诺言,“我”心中掀起种种波澜。波澜本身既是对人性的一种勘探和考验,又增加了人物内省的人文厚度,颇具匠心。为了描述“诺言”这一内在化主题,主人公的心绪和动作的呈现成为实现小说主题的一种外在助推力。“那个看上去有点迷人的诺言彷彿是我在练习场上丢失了之后又重新捡回的一件什么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里,拂去上面的尘埃,想让它从此以后一直发出光亮来。”{21}这个时候,诺言恰如一个小小的珍贵的物件,有了颜色和重量,直击人的灵魂。由此,小小的诺言便显示出巨大的能量。
其次,哈南擅长使用不同的叙事手法和修辞。通过“第三只眼睛”或人称的转换来抵达对人物的描述和形塑,揭示小说的主题。诸如将预叙、补叙、插叙和顺叙进行粘合,从而让不同的叙事空间产生关联作用,进而在一种纵向或者横向的视域中审视人物的情感体验。诸如在《猫红》中,预叙的叙事手法的运用,使得人物成之久不断穿越于个体的历史之中,也让人物成为一个情感的俘虏,似乎被前后左右的情感所胁迫,情感本身足以构成牢笼,让成之久被围困其中,呈现出小说叙事的繁复。这种包含着更高水平的第三视角恰恰证明了哈南对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娴熟调用,也有利于旁观者的美学效应的生产。哈南善于驾驭语言。他的语言可以让沉重或严肃的命题变得轻盈,反之亦然。在几乎无法言说的节点和含混交叉的区域上,他偏偏能够通过修辞将其很形象地给予展示。在考究语言的基础上,哈南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利于表述情感的句式。他继承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叙事方式,“很多年过去了,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22}此种句式用在多部小说中。诸如:
“许多年之后欣欣开始反省的时候,多少谴责了自己的狡诈”。{23}
“多年之后,他的女儿告诉他妈妈曾经对她抱怨过爸爸和机关里的那个女孩子有染时,他的眼前所能浮现的也只有那么一个场景”。{24}
“多年之后,当他回忆起这个已经被证明确实是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场景时,他会情不自禁地把那些电话亭称为自己的办公室”。{25}
“多年之后成之久才从根本上推翻了自己这种想法,并把当时的情景列入了自己最不愿意去回忆的往事之一。”{26}
句式上的这种“过去将来时”让人物前后不同阶段的情感融合在一起,进而呈现出人物情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迁与交织。前后比照,有助于不同情感空间的关联互动,进而也推进了情感效应的传达。
再次,哈南注重对人物情感的张力、情感的空间进行扩容。他摒除极度的张扬,陈述内心的隐曲,创造了一种情感修辞,将感受拉长和延伸,让情感空间不断获得扩容。这一点与俄国侨民作家布宁的小说具有相似性,在布宁的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米佳的爱情》中,布宁充分调用了意绪化和情绪化的策略生成了一个特殊的记忆空间和情感空间,哈南也注重对情感空间的结实打造和精心营构。他熟諳意绪化的暗涌和激荡在人物形塑中的价值含量。可以说,对情感关键节点和触点的准确把握,在哈南看来,远比对外部世界的关注更有效。诸如小说《西村和他的装置艺术》描述雪红和高然夫妇加入日本国籍后,随着儿子西村的长大,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方式也愈来愈简单,愈来愈没有修饰成分,而是直奔主题。小说这样描述他们的交流方式:“那情景就好像他们住宅前面的那一排银杏,在冬天里飘散了所有的落叶,直愣愣地立着,就是有强劲的风,也只是咣咣地吹打在光秃秃的树干上,不会哗哗作响。”{27}在这里,修辞的恰当使用,使得人物的情境和意绪也可触可感,不再是一种难以呈述的尴尬瞬间了。9DFD329F-1745-4B52-A7FF-7E21086F462B
哈南钟情并沉醉于人生的诸多时刻,那些为了摆脱“赖成分”而甘愿让儿子做上门女婿的时刻(《飘逝的红绸巾》),那些伯乐遇到千里马的时刻(《歪嘴堂官窑》),那些少女对初恋无比执着的时刻(《走向童话的世界》),那些老友再见已是陌生人的时刻(《老铺天足金》),那些老人们通过孙女怀念芳华易逝的那一刻(《六岁的时候》),那些对日本人心性进行审察的难忘时刻(《沉默时不能承受之重》)。哈南关注这些珍贵的瞬间和时刻,善于捕捉并以极高的艺术性给予呈现,显示着其艺术感受力的发达。
三、中国记忆:抵抗策略或动员效应
鲁迅曾写过儿时故乡的蔬果记忆给予他的一种深远的影响力,构成他“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28}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作家,哈南的青春时代伴随着十七年文学的生成与布展,受过苏俄红色经典与早期社会主义文化的浸润,革命的浪漫主义式激情或现实主义式悲怆是这“一代人”本来就置身其中的一个共情场域。回首往事,新中国的诞生、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出国打拼,这些记忆图谱转化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中国,另一部分在日本。尤其是第一部分不能“沉默不语”。哈南的中国记忆书写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系列就是知青书写。就“后知青”写作而言,其意义一方面为了揭示创伤记忆所能牵动的社会反思,如梁丽芳从知青记忆书写中解读出的“一场悲剧性的历史反讽”{29},在她那里,揭露创伤所能映射的社会权力的畸形运演和政治效应是一个目标,这一目标关涉着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深度思考。另一方面,知青写作本身的艺术价值值得挖掘,一些学者从思想史和文艺自主性视角不断开掘知青书写更为丰富的意义。有过知青经历的张福貴就说过:“这些记忆的书写仅仅是作为一种审美情感也是有超越性价值的。”{30}贺仲明关注到其中的理想主义信念这一文学功能的推进:“也许应该做的不是对知青文学的理想主义作简单的否定或者嘲讽,而是获得更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31}南帆更是指出了知青书写在“不及物”语境中“某种程度地抵制时尚的覆盖”{32}的效能。应该说,这些研究提供了知青书写阐释的新的路径,开辟了新的空间。对旅居日本的哈南而言,知青书写除了被赋予对个体青春的祭奠和怀想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特殊年代中民间生命力资源的发掘和维护,对传统民间能量的接续和对古老中国理想的呵护。当这些抱负与初衷生成为一种文学形态时,我们便看到了知青书写这一中国记忆的抵抗时间/记忆青春(中国)的功能。
哈南在多篇小说中讲述过知青岁月中的爱情创伤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一律都在青年之际遭遇过命运的重创。《飘逝的红绸巾》通过儿童视角来呈现罗丁及其叔叔罗晓波的青春悲剧。罗晓波因阶级身份在革命运动中被批捕入狱,侄儿罗丁被迫入赘给山里有着好出身(世代贫农成分)的修梅,以求“脱胎换骨”,彻底改变身份,摆脱阶级“烙印”。小说通过罗丁这位少年的视角展开叙事,充满了孩童般的狡黠和诙谐,灵动而又神秘,在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悲剧主题的沉重感和残酷性。小说中一对苦命恋人罗晓波与祝平“假扮结婚”事件使罗丁与祝奇既兴奋又忧伤,因为“他们不但面对着他们所无法抵御的恐惧,他们也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幸福的场面会在一霎间化为乌有,他们更加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会在那么幸福的微笑背后却会有从天而降的悲怆……”。{33}《华侨新村7号》中的淑珠的母亲是曾经被公选出来的美女,却因“成分”问题嫁不出去,虽然她与心上人祖焕相爱,两人却不能走到一起。最终淑珠的母亲自暴自弃,于偶然机会远嫁香港,却又遭遇丈夫英年早逝。当淑珠长大成人代替母亲成为华侨新村7号的新主人时,她竟然遇上了母亲当年的恋人——祖焕这位落寞的老人。小说调动两条线索,在淑珠母亲过去残酷的青春年月与当下新的时空场域间穿梭,将母亲已逝的芳华与祖焕现在的寂寥进行比照,披露一代人青春落幕后的悲怆感。《金戒指》描述了从日本归国的大杉对青春的回忆,一把小提琴牵引他不断舔舐和触摸曾有的青春伤痕。原来,年少的大杉在物质和精神贫瘠的年月,喜欢上了小提琴,这对一家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奢侈的梦想,最关键的是与时代风潮相违背,注定其志向难以实现。而这样被搁置几十年的一个旧梦终于实现,因为球友张超带领他走进了一个让人沉醉的艺术的殿堂。
对哈南来说,青春与激情相伴,与伤痕和缺憾相随。伤痕记忆虽然以人生的惨败作为底色,却显示着生命对外在风暴的抵抗,对自由、纯真情趣的执着追求,这种书写昭示着一代人在时代浪潮中滚烫的生命热度,见证着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的蜕变历程,从宏观到微观层面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和烛照。另外,知青与伤痕书写还包含着对传统的接续和对民间生命力资源的开掘,这一书写呈现了对“共名”大时代中那些矫枉过正行为的检视和审判,同时也在吁请一个古代中国传统的再次降临。
《黄金两钱》聚焦于考察旧时代“主仆”情谊在新时代的命运。小说描述了地主出身的梅芬和仆人英仔“情比金坚”的珍贵情谊。解放前,英仔是地主家出身的梅芬的贴身仆人,解放后,划分成分,英仔翻身做了“主人”,梅芬则饱受坏成分带来的胁迫与冷眼,两人的身份和命运正好来了一个调换。但梅芬和英仔的主仆情谊并不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她们之间的情谊早已化为一种姐妹亲情,久经考验,可以不被任何人任何形势所阻断,这种“主仆+姐妹”式的亲密关系在特定年代中恰恰成为一抹人性的亮色,构成了一道抵抗时代洪流巨变的坚实的堤坝,凸显出传统中国伦理关系中极为坚韧的人伦关系模式,描述了这种模式在特殊形势下的一种“向善”维度的可能走向,从而打破了知青记忆中“儿子打倒老子”、“翻脸不认账”的“向恶”式记忆惯性的钳制,这种模式以其人性的暖色复原古老中国的一种人伦关系模范,折射出哈南对“情”、“义”等传统民间价值的挖掘及其在新时代如何延续的一种思考。哈南重视人文理想的营建和持续,拒绝任何宏大的指向,专注于对民间平凡人物和卑微事物的描述。对民间普通人物生命能量的挖掘,恰恰也印证着陈思和所说的“民间道德”的当代价值:“真正的民间道德是穷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正义、勇敢、乐观和富有仁爱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开朗、健康、热烈,并富有强烈的生命力冲动”。{34}《秦怀和他的藏书》中的秦怀自幼喜欢书籍,并立志做一位藏书家。尽管道路曲折,秦怀却矢志不渝。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秦怀的藏书似乎也藏着知识带来的运气。藉由书籍,秦怀的同学肖兵成为一名作家。秦怀也遇到了一个好妻子,助其逢凶化吉。小说最后描述秦怀梦到自己变成了堂吉诃德,隐喻着他对自由和理想的坚守。9DFD329F-1745-4B52-A7FF-7E21086F462B
张福贵在谈及知青身份和农民身份时,说“这其中倒不是因为其所受苦难多于后者,而在于他们的境遇变化的剧烈和体验的深刻”{35}。在一定意义上,知青记忆本身足以构成一种真实性极强的体验。知青一代的青春与土地、社会、时代有着天然的根生性联结,知青记忆虽然受到时空多维度的牵制,其书写也遵从着记忆筛选和过滤机制的制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书写的“民间性”价值。《老铺天足金》中,年迈的玉华回国去看望发小张加霖和珍英,当知青时,玉华给张加霖和珍英牵线搭桥,成人之美。张加霖曾向玉华借钱去金铺“老铺天足金”打造一枚金戒指,作为求婚的礼物。这次回来,张加霖已离世,珍英患肺癌已失忆,竟连发小玉华都不认识,唯一记得是每天带着1000元钱去寻找早已消失的“老铺天足金”,可快速的现代化建设列车早已将古老的金铺甩在了历史的尘烟之中,其踪迹无法寻觅,珍英只能傻傻的怀念这一消失的风景。对“消失的过去”的打捞和记述寄托着对传统的纪念。与后工业化时代现实主义艺术的“不及物”形成相对的是,哈南的创伤书写充满着原生态气息和对特定现实的想象复原,它能够拨动一代人记忆的琴弦,触摸到粗糙却不乏怀旧的诗意空间。在后知青时代,这些元素恰因其缺席而具备非同寻常的价值。
哈南的另一个中国记忆系列则呈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新变化:中国以其发达、开放、包容的姿态构成了海外华人回归的一个目标。新时期以来的海外华人“回流”、“回归”书写恰如丰云所说“过滤掉了早期回归主题中的道德承担和悲情色彩”,“为华人移民的一种理性选择”,{36}这显示着中华共同体意识对华人离散群体的极大吸引力。作为一种书写现象的“移民回流”,它既彰显着民族性意义的普泛传播,也呈现着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互渗与融合程度,是文化交流的一种理想状态的自然生成,诸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状态的生成则意味着全球文化生态的某种新趋势和新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价值具备了接纳和动员的效能,其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在小说中,体现在华人的行为和思想的矛盾及转变上。首先是跨代际差异化的反思。老一代华人原本想祛除掉自身携带的“中国性”,却怎么也摆脱不了母族文化的烙印,新一代华人却依恋中国,对中国抱有着美好期待,与现实中老一代华人恰好构成胶着对峙的局面。难以纾解的纠葛和困惑构成了华人在日本生活的一个主要代际问题,也是哈南着意于打破“看中国”刻板印象的一次实践。在小说《西村和他的装置艺术》中,陶雪红和傅高然夫妇初到日本时,孩子西村尚不足3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陶雪红夫妇一心期望西村能彻底日本化,为此,他们夫妇从语言、生活习惯、教育理念等方面,对西村进行“日式”改造。但事与愿违。西村不仅没有与中国断裂,反而为中国艺术所吸引,并积極参加宋庄国际艺术展。更让雪红夫妇气愤的是,西村竟找了一个中国女友。西村的一系列行为让雪红夫妇的所有改造计划都泡汤了。中国不仅是他们一家人甩不掉的一种“背景包袱”,更注定要参与他们现在及未来的生活。而在小说《北海道》中,中国女孩洁斐虽嫁给了日本人安藤,却禁不住总是思慕故乡北京,遇到同事真由美并发现其丈夫是北京人后,便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在得知真由美的丈夫正是自己的初恋恋人时,洁斐一时间被双重情感裹挟,处在跨国婚姻的“围城”之中,怅惘之余若有所失。她更在乎的还是中国!
四、结语
哈南的小说写作关注底层华人,并尝试在一种跨文化的视角之中捕捉那些“看不见”的伦理惯习和情感枷锁,这些元素因其内在化于一个民族的内部,不容易被体察发觉;又因其嵌套于日常生活之中,关联着诸多文化心理与习俗的细节。和哈南谦逊低调的姿态相一致,他强调了内向型写作的意义,将个人摆放在一个旁观者的边缘位置上。旁观者的心态恰恰让他能够持续关注一些人们习焉不察的题材,使其注意力投射在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上。张柠曾说:“艺术性的叙事所涉及的事物,必须具有现场感(空间)和历史感(时间),以及由情感态度催生的命运感。”{37}哈南的写作建立在中国发达的民间文化资源和知识传统以及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这一技术传统基础之上,其写作关注人物的情感空间和命运走势,而发达的自省和反省能力又每每使其小说表现出对跨文化区隔间的道德问题的质询,他以平实的语言剥离掉民族性伦理中的“伪饰性”装置,于情感之门的里外做着近身的叛抗与远距的省思,优游不迫。由此,哈南的小说在海外华文文学中便获得了应有的意义。
① 黄星夜:《东京都的福建先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② 蒋濮:《东京没有爱情》,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③⑧⑨⑩{12}{13}{19}{24}{25}{26} 哈南:《猫红》,海峡书局,2018年版,第13页,第114页,第201页,第120页,第114-115页,第156页,第12页,第11页,第3页,第116页。
④ 徐金湘:《日本元青花收藏和研究现状》,《中国文物报》2017年5月2日。
⑤ 张柠:《论作为农耕美学之典范的青花瓷》,《文艺研究》2018年第10期。
⑥ [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
⑦ 徐吉鹏:《传统伦理在日本现代化中的命运》,《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4期。
{11}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58页。
{14} 王中田:《神道教伦理思想的现代阐释》,《日本学刊》2003第6期。
{15} 李长声:《日本人的画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5页。
{16} 卢冶:《为什么谈日本》,《读书》2014第10期。
{17} 张悦然:《较远的观察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第5期。9DFD329F-1745-4B52-A7FF-7E21086F462B
{18}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选集》,范培松、徐卓人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0}{23}{27}{33} 哈南:《北海道》,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第4页,第43页,第267页。
{21} 《香港文学》2019年8月号,总第416期。
{22}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宋瑞芬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8} 鲁迅:《朝花夕拾》,海南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29} [加]梁丽芳:《私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知青一代人的文化震惊和历史反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30}{35} 张福贵:《知青文学的苦难书写与理想主义的价值难题》,《小说评论》2017年第2期。
{31} 贺仲明:《论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创作形态与文学史价值》,《求是学刊》2011年第1期。
{32} 南帆:《记忆的抗议》,《南方文坛》2013年第6期。
{34}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36} 丰云:《漫游在第三空间:新世纪以来新移民小说的主题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7页。
{37} 张柠:《理想是不同类型文学的公约数》,《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责任编辑:黄洁玲)
The Query of Ethics and the Atlas of Memory in the Circuitous Narration: On Ha Nans Fiction
Zhang Yiwei
Abstract: Ha Nans fiction inherits the spiritual tradition of the realist literatur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echnically used to circuitous narration and sophisticated in terms of cross-cultural vision about the depth of thinking in relation to national ethics, paying attention to excav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hidden ethical elements and their cross-cultural compatibility.With cultural relics and feeling as the media, his fiction keeps exploring the border of material in the atlas of two kinds of memo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ts treatment with highly skilled techniques rendering mood, plentifulness and three-
dimensionality signs of his fictional style, displaying Ha Nans strong artistic sensibilities as a novelist.
Keywords: Ha Nan, ethical inquiry, circuitous narration, memories of China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近三十年海外华文作家的乡土记忆与中原文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6YJC751038。9DFD329F-1745-4B52-A7FF-7E21086F46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