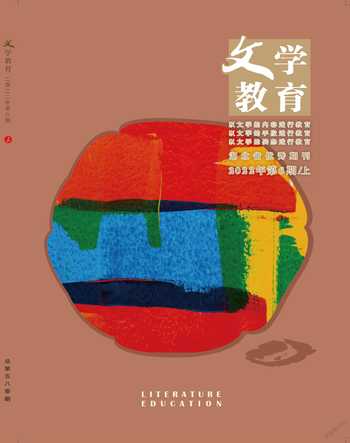《藩篱》中非裔女性从“他者”到“自我”的觉醒
成昕玥
内容摘要:《藩篱》是奥古斯特·威尔逊最为著名的一部戏剧,曾获得过普利策戏剧奖和托尼奖。萝丝·麦克森作为《藩篱》中唯一的主要女性角色,相较于剧中其他角色,不仅在思想上,还在身份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转变。本文基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女性身份,试图解释萝丝如何通过找寻自己的身份,完成“他者”到“自我”的转变,并通过分析她如何获得主体意识并抛弃“他者”身份,论证作为非裔女性的萝丝·麦克森,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奥古斯特·威尔逊 《藩篱》 女性自我意识 女性身份 “他者” “自我” 非裔女性
奥古斯特·威尔逊是二十世纪著名的非裔美国戏剧家,他以描写典型的非裔美国家庭形态和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而出名。威尔逊曾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创作出“匹茨堡循环”(Pittsburgh Cycle),所包含的十部戏剧的背景依次对应二十世纪的每十年。这十部戏剧全部都以匹茨堡地区为背景,描述了典型的非裔美国家庭内部的矛盾,如婚姻关系,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以及社会中的隐性但仍存在的种族歧视。同时,借以威尔逊巧妙的心理描写和精细的语言设计,这些戏剧也表现出了黑人在社会中所承受的种族和阶级压迫。
1987年出版的《藩篱》,作为“匹茨堡循环”中的第三部戏剧,曾获得过普利策戏剧奖和托尼奖,后在2016年被改编为电影。这部著名的戏剧主要围绕1957年一个典型的非裔美国家庭中的矛盾展开。特洛伊·麦克森作为一家之主,靠收垃圾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即使黑人的境遇已悄然改变,他始终认为非裔美国人在社会中遭受着不平等的待遇。所以在剧中,因为自己曾受到过歧视,特洛伊坚决反对儿子科里继续打橄榄球。而本文要讨论的对象萝丝·麦克森则是剧中唯一的主要女性角色。萝丝是一位典型的非裔美国家庭主妇,不仅需要操持家务,还经常帮助丈夫缓和父子和兄弟关系,处理家庭矛盾。当特洛伊坦白自己出轨并且私生子即将出世时,萝丝对待丈夫、家庭和自己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萝丝开始逐渐抛弃家庭主妇的身份。威尔逊给予了萝丝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的权利和抵抗丈夫的背叛的力量。通过她在家庭中身份以及行为上的变化,在某些程度上,萝丝在剧末时已经完成了“他者”到“自我”的转变,并找回了自己的主体性。至此,萝丝·麦克森完成了非裔美国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
以往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威尔逊的成长经历是怎样影响其写作,使其将萝丝·麦克森这样一个典型的非裔美国女性塑造成一个“极端母性的人物”[2](p17)和家庭中“自我牺牲的缩影”[4](p5)。同时,这些学者认为威尔逊赋予了萝丝·麦克森足够的力量,让她能够代表其他非裔女性说出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感受。而其他学者基于女性主义,通过对威尔逊不同剧本中对女性人物的刻画比对研究,分析萝丝·麦克森是“如何通过重新定义女性角色来定义自我”[3](p55),并且追逐自己的梦想和自我实现。尽管之前的一些研究基于女性主义,将萝丝·麦克森的角色理解为——一个重新定义了自己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的非裔美国女性。但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本文将着重探讨罗斯·麦克森如何获得女性自我意识,以及她如何通过寻找“自我”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牛津女性主义理论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Feminist Theory)一书中提到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观下的女性身份观。作者认为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身份被视为是“完全的差异”。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中也提出了“自我”和“他者”[8](p11)这两个相对的术语。在《第二性》中,女性被认为是与男性相比不够自主的人——因为定义和区分女性的参照物是男性,而不是女性本身。因此,波伏娃写道:“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參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8](p11)。很显然,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萝丝·麦克森在家庭中是相对于男性来说的“他者”。同时,“女人的戏剧性在与每个主体(ego)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者”[8](p27)。所以,萝丝在发现丈夫背叛自己后,吐露出内心最深处关于自己如何放弃生活和梦想的想法和感受,并且试图打破现状,逃脱现有处境,寻找“自我”。
一.作为“他者”的家庭角色
在戏剧的最开始,萝丝·麦克森被描述为一位忠诚的妻子和温柔的母亲,她倾尽一切照顾和维护自己的家庭。对她的儿子科里来说,萝丝是一个调和者,总是在帮助调解父子之间的关系。特洛伊的固执己见导致他并不同意科里去打橄榄球。同时,科里也十分害怕并且抗拒他父亲谈论球队招新的事情,因为科里知道特洛伊对此事的消极态度。在第一幕第三场中,科里对萝丝说:“你跟他说招新的事了?”[7](p101)然后继续问道:“他怎么说?”[7](p101)很明显地,科里一直在通过母亲萝丝向父亲传话,旁敲侧击地想知道父亲的态度。接着,在第二幕第一场中,科里虽然已经下定决心与父亲抗争,但在行动实施中,仅仅告诉了萝丝:“我不能退出球队。我才不管爸爸说什么呢”[7](p115)。自然而然,作为母亲,萝丝就变成了那个“跟他说说”[7](p115)的人。萝丝不得不面对特洛伊的不耐烦和顽固反对态度——这样的压力本应该是科里应该承受的。由于科里的逃避,萝丝只能被迫承受压力,充当儿子的“传话筒”和丈夫的“受气筒”。对于科里来说,萝丝更像是一个承受着他不想面对的压力的关系调和者,而这种压力的转移对于萝丝来说也是一种压迫。
对于丈夫特洛伊来说,萝丝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经常提醒丈夫要改变旧观念,勇于打破偏见追求平等,并帮助缓和特洛伊与大儿子里昂和兄弟加百利之间的关系。当特洛伊沉浸于旧时代的偏见中时,她告诉特洛伊:“特洛伊,时代变了。你打棒球那是战前的事了……现在很多有色人种男孩都在打球了”[7](p91)来试图改变特洛伊偏执的看法。此外,萝丝在特洛伊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兄弟加百利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安慰了他。无论是对继子里昂还是特洛伊的兄弟加百利,萝丝都在这段婚姻关系中表现出了她作为妻子的爱和关怀。尽管萝丝为特洛伊做了很多事情,但他们的婚姻关系显然是不平等的。作为一个家庭主妇,萝丝没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因为特洛伊才是那个可以做决定的一家之主。她能为科里做的就只是说服特洛伊签署文件让科里去打橄榄球,这也从侧面说明萝丝在这段婚姻关系中没有做决定的基本权利。在这个家庭中,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特洛伊才是绝对权利的化身,处于支配地位。
不难看出,萝丝在家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男性,而她却从来不关心自己的生活:
特洛伊!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花了十八年的时间,陪你站在同一个地方。难道你以为我就不需要其他的东西吗?你以为我就没有梦想和希望吗?我的生活呢?我自己呢?你以为我就不想见见其他男人你?我就不想去别人家里消遣一下,暂时逃避自己的责任吗?…不是只有你才有需求和欲望…因为我只有这样才能作为你的妻子把日子过下去…[7](p121)
萝丝选择了忽视自己的需求和想法,因为她必须捍卫自己作为妻子的身份。她认为作为一个忠实的妻子,只有她有责任守护家庭,让家庭和睦。路易斯·泰森认为黑人女性总是在努力地维护自己的身份,就像许多早期作品那样,为了家庭、社区和种族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然而,萝丝牺牲自我而去追求的妻子身份,只有在与男性相比时,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和重要性。因此,泰森在书中指出黑人女性其实处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实际上,萝丝并没有独立或者主观性的思想,她在家庭中将自我依附于特洛伊。萝丝对特洛伊说的话证明了她的依附与从属地位——“我把我所有的情感、需求和梦想…都压抑起来。我在心里种了颗种子,我细心地照料它,为它祈祷。我把自己种在你心里,等待着它开花结果”[7](p121)。萝丝也承认:“这是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没让他给我留点空间……我把他的生活当成我的生活,并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这样你就无法分辨”[7](p135)。她自己的话语也表明了她的女性自我意识被妻子的身份所掩盖,将自己的生活埋葬在男性之中。同时,她还被迫承受着来自儿子的压力,以及淹没在家庭中绝对的主体特洛伊制造的身份中。因此,对于男性来说,萝丝处于家庭中的附属地位。所以作为妻子的萝丝在她的婚姻和家庭中处于“他者”的地位——“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7](p11)。
二.寻找女性主体意识的尝试
由于小时候家庭的缺失,成年后的萝丝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你知道我最不希望家庭不完整。我的整个家族都是不完整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爸爸和妈妈……”[7](p119)。因此,萝丝选择将家庭围在藩篱中,以防外部原因导致家庭的分裂。同时,她也将妻子的身份锁在藩篱中,将欲望、需求与主导权以及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隔离在外。
特洛伊的背叛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萝丝发现她花了十八年一直在保护的家庭因为特洛伊私生子的出现而分崩离析。至此,用来保护家庭的藩篱被摧毁,妻子的身份变得毫无意义。丈夫的背叛是萝丝转变的关键点。“但你不再有妻子了”[7]正是萝丝离开特洛伊寻找她作为“自我”的主观性宣言。
萝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寻自我的主体性,向她的丈夫特洛伊,同样也对观众大声说出内心深处的想法:“你总是再说你付出了什么,你不需要付出什么。但是你也索取…你不断在索取…而且还意识不到别人的付出”[7](p121)。
她的话表现出了他对特洛伊的愤怒。此外,萝丝拥有表达她被压抑着的想法的权利,这意味着她敢于找寻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主观意识,而不再甘愿成为一个总是单方面付出的妻子。在戏剧的结尾,她也承认自己曾犯下过错误,“没有让他(特洛伊)给我留点儿空间”[7](p135)。萝丝是清醒的,这是她的第一次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为意识觉醒的标志,能够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对于萝丝这样的非裔女性来说非常重要。
萝丝也终于走出家庭,重新回到自己生活里。她不再总是在家里忙着照顾家人,而是选择去当地的教堂成为一位基督徒。“我把这些蛋糕拿到教堂去,那里正在举行义卖活动”[7](p127)表明了萝丝在教堂有自己的活动,也交了一些自己的朋友。走出家庭,找寻自己的兴趣,认識其他的人,这些都是萝丝身上发生的明显的变化。她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也摆脱了相对于她丈夫才存在的身份意义——妻子。
萝丝做的第三件事是摆脱家庭中男性的支配地位,以求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在第三幕中,特洛伊要求萝丝照顾他的私生子。萝丝答应了他:“好吧,特洛伊......你说得对。我会帮你照顾这个孩子……因为……就像你说的……她是无辜的……你不能因为她父亲的罪过而牵连到她。没有母亲的孩子会过得很艰难”[7](p126-127)。萝丝决定抚养特洛伊的私生子,只是因为她认为孩子是无辜的,她不想让孩子过着没有母亲的艰苦生活,绝不是对特洛伊出轨背叛行为的妥协。特洛伊的请求并不是萝丝答应抚养孩子的原因,因为这是萝丝主观感受下的决定,证明了萝丝正处于自我主观的位置来决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她愿意成为一名母亲,同意再次养育一个孩子。对萝丝来说,做一位母亲是她一直想要的——“生命其中的一个空位就是做一位母亲”。这个私生子是她在获得了自我主体性后,重新地自己养育孩子的一个机会。斯宾德(Spender)曾谈及养育问题,她认为,女性逐渐发觉自己作为生育性别(nurturing sex)正处于社会剥削中;我们的生育正在被男人占有和使用。我们必须面对如何在不否认生育本身的情况下,使自己不再得到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萝丝既不原谅也不认同特洛伊,她自己做出决定养育私生子与男人毫无关联,所以特洛伊的要求并不能构成威胁或是剥削。相反地,这种决定强调了女性生育的权利也是萝丝重新开始的力量。在戏剧的开始,特洛伊是唯一一个在家庭中可以做决定的人,但是萝丝现在已经能够摆脱这种控制着她的生活的不平等的关系。通过抚养这个孩子,她获得了女性自我的决定权。
此外,在拒绝妻子的身份离开特洛伊后,萝丝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特洛伊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她成为了那个教育孩子的家长。“别跟我顶嘴!快上楼换衣服,把那双新买的鞋穿上”[7](p134)。现在萝丝对她的孩子拥有完全的教育权,让孩子服从于她。此外,萝丝说服科里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并进行了一次谈话来教育他:“不尊重你爸爸并不会让你显得有男子气概,科里。你要想成为一个男人,你得自己想办法”[7](p134)。与孩子们谈话去教育孩子这是特洛伊生前常做的事情,这也证明了萝丝通过再次成为母亲而在家庭中获得了主体地位。因为萝丝与特洛伊断绝了交流,并且开始拥有自我的女性意识和决定权,所以她不再依恋任何人或是受到任何人的压迫。自然而然地,萝丝摆脱了她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为主要者,一次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8](p12-13)。正因为萝丝有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放弃了做特洛伊的妻子,她的女性主体意识让她在家庭中拥有了权力,成为了一个与他人对立的主体。因此,她找寻到了“自我”。与此同时,限制萝丝作为妻子身份的藩篱也被摧毁了,萝丝走出了藩篱,获得了自我的女性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萝丝的“自我”并不是完全的“自我”。在经济上,萝丝仍然依靠特洛伊的薪水,住在他的房子里。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裔美国妇女就受到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双重压迫。因此萝丝很难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孩子。尽管如此,萝丝还是在精神上离开了她的丈夫,把她的丈夫变成了一个“没有妻子的男人”。这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非裔美国家庭主妇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威尔逊的戏剧中,萝丝·麦克森与其他女性角色一样,是一位典型的非裔美国家庭主妇。萝丝曾经是一位只会付出,忙于维护家庭的忠诚妻子。她认为用藩篱护住自己的家庭是她的责任。所以她将自己的生活、需求和梦想都埋没在丈夫身上——这造成了严重的错误,让她忽视了自己作为女性的主观意识和精神需求。承受着压迫和“他者”的生活,萝丝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付出是徒劳的。最终,萝丝找寻到了“自我”。她离开了丈夫,放弃了妻子的身份,找寻自己的生活,同时也通过再次成为母亲,在家庭中树立主体地位,确立了独立于家庭中男性的自我身份。至此,她摆脱了在家中从属的地位,从一个依附于他人,承受家庭压力的典型家庭主妇转变成为了一个能够拥有自己生活与“自我”的非裔女性。
参考文献
[1]Disch,Lisa, and Mary Hawkesworth.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eminist Theory.[M].New York: Oxford UP, 2016. Print.
[2]Grabowski, Amelia Tatum. “She’s a Brick House: August Wilson and the Stereotypes of Black Womanhood.”[D]. Gettysburg College, 2013. Print.
[3]Koch, Kimberly Jean. “Negotiating Triple Consciousness for August Wilson’s Female Characters.”[D].Villanova University, 2009. Print.
[4]Shannon, Sandra G.“The Fences They Build:August Wilson’s Depiction of African-American Women.”[J].Obsidian Ⅱ6.2(1991): 1-17. Print.
[5]Spender, Dale.Women of Ideas and What Men Have Done to Them.[M].London: Routledge & Kegan,1982.Print.
[6]Tyson,Lois.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2nd Edition.[M].New York: Routledge UP,2006.Print.
[7]奧古斯特·威尔逊.“藩篱”.Trans.姜波[J].《世界电影》05(2017):86-137.
[8]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Trans.陶铁柱.[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Print.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