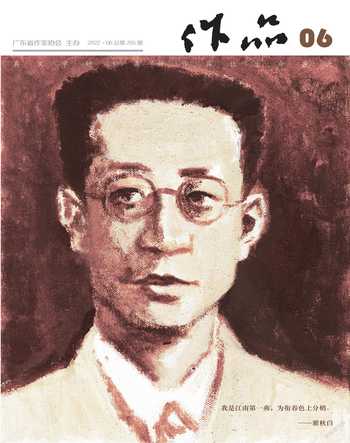太阳风暴
琳达·侯根(美国)
第十一章
第二天,一团黑云般的蚊子从沼泽中升起。到目前为止,我们都很幸运。布氏伸手到衣服包的底部,拿出四顶白布帽子,不停地抖,直到帽檐打开。我笑了,很感激她带来了这些帽子。“你从哪儿弄来的?”我问。看起来有点像野外旅行帽。布氏忙着在衣服中寻找面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就像游猎中的新娘。昆虫被我们温暖的呼吸吸引,落在面纱上。它们的嗡嗡声让我焦虑。我们把手遮盖起来。当蚊子靠近我时,它们的高噪音使我紧张。我挥手,但更多的蚊子紧围着我。
“不用管它们,”朵拉茹日说。“这只会浪费你的精力。”然后她说:“我怎么没想起来,我们这几天应该喝沼泽茶的。”
是的,我记得茶。几个世纪以来,北方人把它用作滋补品和驱虫剂。
“我们忘了,”艾格尼丝说,但她没有说布氏因为急于减轻背包重量,把沼泽茶留下了。
布氏生了一堆比平时更大的火,在火上放了点污泥,我们把木头、草和树叶放在火上,直到烟雾把我们包围。
“我们需要弄到茶叶。”朵拉茹日边咳嗽边说。
我的眼睛流着眼泪。
即使那天我们发现了沼泽茶,它也需要在血液里积累几天才会有足够的效果驱走昆虫。这些昆虫折磨我最厉害,它们带着像电一样的响声向我扑来,找到我忘记遮盖的地方:牛仔裤上的洞,脖子和衬衫领子之间的缝隙。裤腿下开口处。“这是因为你吃了太多糖,”艾格尼丝说。
我听到一些关于驯鹿和人被蚊子弄死的故事,他们的血几乎被吸干,他们为了躲避成群结队的小虫子把自己淹没在水中,被淹死了。
到了晚上,蚊子的数量减少了,布氏就出去采集茶叶的茎秆和叶子。她在独木舟上小心翼翼地划向有沼泽茶生长的沼泽区,随身带着一盏灯,不幸的是,這盏灯提前叫醒了许多昆虫。
她在湖面上移动,湖面银白色,像水银一样重。
蚊子是最古老的生命形式之一。当原始人点燃烟火时,蚊子已经存在了。朵拉茹日说。它们的祖先听过我的祖先的歌曲,她说,当法国人经过这片破碎的土地,唱着情歌和悲哀的民歌时,蚊子已经在那里。当毛皮商人在河流中快速划着桨,上上下下,寻找毛皮,寻找愿意与他们交易的黑皮肤的人的那些年代,蚊子也已在那里。蚊子记得所有的血腥事件。它们记得那些沉入地底下的动物。
有时我自己也能听到,这些孤独而悲伤的歌曲穿过树木,从毁灭的河岸上传来。在那些歌声背后,我听到了我们自己低沉的歌声,那是土地的歌声,通过它的守护人诉说着。有时,我也能在狼的歌声中听到祖先的声音。
我们一动不动,让烟雾缭绕着我们。第二天,为了保护我那过于娇嫩的皮肤,也为了消除被咬后的刺痛,我采取了涂泥的办法。傍晚,蚊子和成群的黑苍蝇如阴影,乌云般依附在帐篷上。我感到羞愧,比起熊、狼,甚至狼獾,我更害怕它们。有一天晚上,我们彼此看着,面纱上覆盖着活的、黑色的蚊子,脸上沾着泥浆,手上戴着手套,我忍不住笑了起来。笑声很有感染力。艾格尼丝说,“这不好笑,”但她也笑了。
在我们的旅程中,布氏像岛屿上盛开的百合花,一开始试探地,细微地,最后坚定地绽放。她需要这个地方和所有的水,好让她在其中吟唱,好让她有足够的空间伸手。水和天空是她窥视超越这个世界的窗口。它们是一面镜子,她看到自己,崭新的皮肤、手、大腿。她以前被皮肤、房子、岛屿和水束缚。现在没有边界了。在黑暗处,在深深的树林里,她跳慢步舞,与大地交谈。有几个晚上我坐在篝火旁,她背对着更深的晚霞向我们走来,或坐在岩石上,或像动物一样悄悄地向树林移动。时间从她身边流逝。她的眼睛温柔。她想着一生中经历过的事情:背叛,罕娜造成的无法治愈的创伤,还有失去了我,她所需要的,使得她变得坚强、孤独。
我听见艾格尼丝在帐篷里唱歌,用古老的语言喃喃自语。
艾格尼丝现在更强烈地想念着那只熊,即使没穿大衣,她也对它说话。朵拉茹日唱起低沉的歌,听起来像是风。她能读懂流动的水,当陆地和无声的迷雾掠过,她看到了我们看不见的。
我醒悟的时间是在斧头、捕猎器、火石和木匠的钉子出现之前。这是我们进入的时间间隔。这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一个时空。我被荒野的魔力迷住了,接近了没有人能说出名字的地方。一切都融合在一起。黑暗和光明没有明显的区别。水和空气变成了同样的,正如水和土地在创造的沼泽汤中融为一体。在我们经过的清澈的水中,水底的岩石只有几英寸深。鸟儿游过湖泊。所有这一切都是分不开的。独木舟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皮肤。我们穿过了绿叶、菰米和灯心草。当我们经过时,在长满睡莲的小湖里,小小的青蛙从叶子上跃入水中。
有眼睛在我们周围,透过树林和雾凝视着我们。也许是陆地和生物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打量着我们。聆听夜晚,在我们能看到的地平线之外,还有另一条地平线。这都是蕴育着故事的土地,是神行走的土地,是人旅行的土地,他们渴望与无限空间成为一体。
我们充实而有力,带着所经历的,默默漂浮着。朵拉茹日说:“是的,我们一直在迷失中。”我们划过茂密的灯心草和沼泽,水很浅,船桨都触到了水底。
我们变得像动物。我们以部落的方式互相倾听。我立刻明白了,感到很自如。和祖母们在一起没有孤独。以前,我的人生中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对人生的任何认知。现在我们,四人,都有同样的眼睛,朵拉茹日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说“这边走”,我们本能地顺着她弯曲的手指前进。
途中,我从未感到迷失。我有一种新发现、一种开放的心情,就像我们在池塘里发现的小小的、透明的卵在孵化。我俯身看它们。生命已经在它们体内移动,像眼睛或心在跳动。我们经过崖壁,崖壁上绘有红色的古代驼鹿和熊。这些画不是人,而是神灵,画的。
有一天下雨了,我们在雨中继续前进,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被水浸黑的树干,没有闪光的岩石,甚至没有低低的云盘旋,或在湿漉漉的,滴水的树枝间盘旋。我们独木舟下面的水和我们头上方的水没什么区别。
过了一个又一个湖,一个又一个岛。我们静静地沿着一条平静的河漂流。那是个郁郁葱葱的季节。花粉飘过,像黄色的雪落在水面。我微笑着回头看了看布氏和艾格尼丝。“朵拉茹日,”我说。“太美了。”
在河的尽头,水流入一个湖泊,我们来到灰色的石墙旁,墙上有画,有红的,有黑的。是驼鹿和狼獾。“看,”我说。我停止了划桨。一团雨云过去了,我们很幸运,岩石的墙壁湿漉漉的,可以看到狼獾长了翅膀。在干燥的空气中不能看见,这些翅膀等待着水来暴露。还有一只白色的鸟,现在能看见了。“什么样的人,”我大声问道,“有这样的憧憬?”
“你的族人,”朵拉茹日说道。“和我的。”
在水下面有更多的画,能看得见。
“水一定涨了,”朵拉茹日说。
真的。我们的桨碰到了树的顶端。陆地上的许多树木被淹了半截。它们站在水里,生着根,像沿水面生长的灌木。还剩一天的行程,我们决定在岛上的高处扎营,这个被淹没了一半的岛值得好好看看。
我脱下衣服,想顺着画墙游过这片水域。
“小心点,”艾格尼丝说。
进到水中,我冷得喘不过气来。水比以前冷。很清澈。在水里,被淹的土地完全正常,草随水流,而不是随风,摇摆。在淹没的树木间可以看到一条小道。
我游到画壁前,睁着眼睛潜了下去。我从未见过这样清澈而深邃的水。我想起布氏有一天站在水前,用她梦幻般的方式说:“两份氢,一份氧。”当我在水中时,明白了这些简单的元素是如何结合后成为第三种东西的。
鱼画在石墙最深处。在它们上方,几只红色马鹿站在那里,像海底森林中被折断的一根小树枝。它们准备从石头上跑开,淌过水。我忘记了呼吸或游泳,又一次处于出生前的状态,似乎有腮裂。在那一刻,我回想起自己是鱼。我是氧和氢,鸟和狼獾。这一切都涌现在那一刻。从那以后,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定义那种感受。我和我的许多母亲都迷失在天空、水域和银河系中,我们栖息在一个行星上,它如此小,被其他世界的转动隐没。
我离开水,闻到了烤兔子的味道。艾格尼丝因为晚餐有新鲜的肉而高兴。我站在火边,拧干湿漉漉的头发。“你从哪儿弄来的兔子?”
布氏在用她的头发绑一只苍蝇。“我假装没在打猎,”她说。“注意点,安吉珥。你把我弄湿了。”
“告诉我。你怎么弄到的?”我知道她是怎么捉兔子的。她设一个圈套,用细绳、细树枝和一枚钉子。
“俄克拉荷马州也有这样一个地方。”布氏看了看四周。“石头上画着熊。没有人知道。它们在森林里。”她把头发盘成一个圈。“我叔叔住在那片森林里。有一次,他看见三十只熊一起穿过森林。他说,它们咆哮着,把树都折断了。他吓得要死,想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他想爬到一棵树上。但熊会爬树。他知道有一个山洞,但他能想到的任何地方,熊都能去到。它们如此强大,从森林穿过时,根本没在意人。”
“难以让人相信,”艾格尼丝说。
“我知道。我敢肯定这不是我叔叔编造的。”
艾格尼丝掸去了我腿上的灰尘。“我希望我有我的大衣。”
朵拉茹日私下告诉了我布氏的狩猎技巧。她用一个圈套捉到兔子的。她所需要的只是一根鱼线和一根棍子。
布氏把苍蝇放在一边。它看起来就像一只蚊子。
“我希望这不是一个诱饵,”我说。
那天晚上,艾格尼丝很早就睡觉了。我们其余的人坐到挺晚,聊天。我们把杏干搅进热开水里,艾格尼丝在帐篷里说话。我们关于熊的谈话使得她去寻找她曾经认识的那只熊。现在她正试着和它说话,试着召唤那只从她十二岁起就一直是她盟友的熊。
艾格尼丝没有她的熊皮大衣,就像没有自己的皮肤。她身上剩下的不多的肉看上去有些松弛,似乎随时可能褪去。她每天睡的时间更长了。她说,她被船、睡袋、帐篷,甚至自己的皮肤束缚住了。她累了。我告诉自己这没什么;那是因为她的大衣不在身边。现在她试着用新的方式召唤熊,唱熊歌,跳一种她称之为“熊走路”的隐藏舞蹈,紧闭双眼,虔诚地对熊说话。
看着她,我为她担心。我开始想:如果我们其中一人发生什么事怎么办?没有人帮助我们。这里只有我们自己。
朵拉茹日也在想同样的事,她噘起嘴唇,看着艾格尼絲,她把眼睛挡在阳光下,好看得更清楚些。“也许是神经紧张,”朵拉茹日说,她把我的担忧都说出来了。
“欧洲人称这个世界是危险的,”朵拉茹日说。我想我明白了:他们把自己困在了自我毁灭中,一种最古老的圈套,比绳子和树枝还要古老。他们把精灵从所有的物种、动物、树木、鱼钩和锤子……所有这些都是印第安人的盟友,抹杀掉。以前,一切生物——山猫和女人,捕兽者和海狸——都相处得很好。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不会表达的灵魂、沉默的精神、绝望的心。
“过去的猎人杀死一只动物时,”朵拉茹日说,“他们把动物的眼弄瞎,不让它看到他们对它的身体做了些什么。他们把被杀的鸟的脚绑在一起,这样鸟的灵魂就不会跟随他们回家。他们砍掉熊的爪子,这样熊的灵魂就不会追逐他们。”
但现在,她告诉我,人们被另一种东西困扰着,一种他们无法忘却的,内在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动物和人类不再互相沟通了。”
但在这次旅途中,我听到了世界的声音,听到了我们周围的声音——石头的声音,水流向尽头,鱼鹰抓住鱼,甚至米诺鱼产卵的声音。我听到树根紧紧抓住地面的声音。
“过去,我们可以请其他物种为我们做点事,帮我们找到回家的路,协助我们消除痛苦。它们会帮助我们,”朵拉茹日说。“这是在创世的第十天传授的,”她说。那些对此无知的人是未完成的造物,被永生诅咒,缺乏对生命的了解。他们不具有珍贵而奇特的智慧。
朵拉茹日说,世界的创造是持续不断的。在创世的第八天,人类被赐予了在地球上的位置。她说:“那时,一定有一些人已经漂流了,越过新形成的水域,走向更新的陆地。也许他们记忆力不好,但一定有某种原因使得这些人认为只有六天的创世时间,有一天是休息日,之后创世便停止了。然而,第九天是故事的创作日。故事有很多用途。”故事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工作,什么是善良和爱。她告诉我,有的故事专门指引我们如何摆脱痛苦。另外一天创造蜗牛、蛞蝓、夜行动物、蠹虫、蟑螂。还有创造歌曲和唱歌的日子。“如果那些漂流的人留了下来,他们可能学会了战争的解毒剂。”但他们只听到创造战争的第六天。那一天,盗贼也被创造出来了。
我温柔地看着朵拉茹日,看着她的白发,她容光焕发的脸庞。生活从未如此美好,女人从未如此美妙。
布氏内心深处有某种东西闪闪发光,我想把手伸进去摸一摸,拿出来,爱慕它。她是最近似我母亲的人,坚持每天都是新生的朵拉茹日,是最接近神的人。我的一部分是按照这位老妇人的形象塑造的,从那鹰嘴形的鼻子到浓密而弯曲的眉毛。当她叙说创世的日子时,我相信她说的。
接近傍晚,我生起一堆火,布氏游在平静的水面上,像一只黑头水獭,她浮出水面几分钟,接着滑入冰冷的水面消失了。我注视着她再次浮出水面。她在水里很自如,水是一种元素,它的形状取决于它的容器。她是水。艾格尼丝曾告诉我,有传言说和她睡过的男人认为他们游过她的身体。
那天晚上,我在艾格尼丝的背上抹油。她躺在火炉旁,胸前放着一块布,油在她那黝黑赤裸的背上闪闪发亮。她在温暖中睡着了,朵拉茹日把兽皮盖在她身上,她看上去像一只大动物。朵拉茹日整夜没睡,坐在她身边,时不时地把老雪松木扔进火里,让它散发出烟和气味。
另一天傍晚,我们以稳定的节奏划桨时,独木舟漂进了一道红色的阳光中。朵拉茹日指引我们看另外一些月球和猞猁的岩石画。那些画在陡峭的悬崖上。光线依然明亮,画映在水面,猞猁低头,看着它的孪生兄弟,仿佛它们是第一次见面。它们离开石头,进入水中,水中的倒影活了过来,就像精神与物质的相遇。如此悠久的绘画深深打动了我,感染我继承的、仍然在活动的久远的思维。
艾格尼丝俯身,把手伸到水中,试图把月亮捞起来。她碰到水面,月亮破碎了;猞猁在水中晃动。
阳光在水面形成长长的一条路,一条独木舟在光的路径上向我们移动。独木舟里坐着一男一女,他们是白人。一条白色的狗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在靠近。快接近我们时,一只苍鹭从水边飞起。
“瞧,”朵拉茹日说,“他们做爱了。他们精神焕发。”
我几乎没听到她说的。我挥手,大声喊道。“嘿!”我已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其他人。我迅速从失去的时间和寂静的空间中回到了现实。现在我想要一管口红。“在这里!”我把手指放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如果不是为了保持独木舟的平稳,我会站起来。那两个人也挥了挥手。
他们的独木舟超载了,船的边缘离水只有几英寸。任何动作都能使他们沉进水里。他们看上去太傻啦,我几乎要笑了。第一次,我以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小船队,我们看起来跟他们一样傻,四个印第安妇女,其中一个相当年老,像只鸟,还得我们搬动她,同时她给我们下命令,根据她苍老易碎的骨头深处做出的决定,指挥我们该往哪个方向走。
那条狗站起来叫着。他们的独木舟倾斜得很厉害,有翻船的危险。“坐,泰勒!”那个女人喊道。
艾格尼丝看着两人的金发、白眉毛和粉红色皮肤,默默无语。
这对年轻人,鲍勃和珍,是几天前乘飞机来的。那个男人是个经验丰富的划独木舟的好手,常来这里旅游,他们迷路了。我没有意识到我们前方的陆地和水域发生了变化,也不知道这种变化意味著什么。我以为他只是缺乏经验。
他把独木舟靠近我们,微笑着问道:“这个岛叫什么名字?”那个女人把桨放到膝上,等待着。“我们一定是迷路了,”他说。
朵拉茹日知道他不会理解她通常的回答,即我们总是迷路的。她有足够的理智,没有说什么。
那条白色的牧羊犬摇着尾巴,喘着气。“泰勒。坐!”
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旅行了整整一天,朵拉茹日邀请这对男女同我们一起在岛上留宿。“我们喜欢有同伴,”朵拉茹日说,她观察到我挺兴奋。
“你再也不能通过那条老路绕过塞奈河了,”我们坐在火边时,那男人对朵拉茹日说。“你必须走另一条路。”
“为什么不能?”她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的。路被堵起来了。大臂河已经从上游改道。他们不得不让我们在西边下飞机,以便我们可以换另一段路,可是那一段水路也可能不能通行了。那里几乎全是泥;现在肯定全是泥了。”
我们一起坐在篝火旁,那条白色牧羊犬的头搁在我的膝上,我搔了搔它的耳朵。朵拉茹日反复考虑我们的路途该怎么走。“过那条河有多困难?”她问道。
“你不会想顺流而下吧。”他不想多说。“水流太急。”
“卢瑟,”朵拉茹日呼唤他。那个男人用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她。但是卢瑟什么也没说。也许他保持沉默是因为那对夫妇。他们看上去很吃惊,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环视了一下宿营地周围,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人。
艾格尼丝的举止有些奇怪。她独自一人从灌木丛中出来,朝火堆走去。“他们有点不对劲,”她说。后来,我在湖里用沙子擦洗罐子时,她尽可能大声地悄悄说:“那两个人是食人族。”
那天晚上,她对他们说:“你们是食人族,不是吗?”
那男人和女人笑着不理她。她惊恐地盯着他们的脸,他们仍然彬彬有礼。他们假装没注意到。毕竟,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在这些破碎的,被水分裂的土地上会发疯的。
那个男人对布氏说:“前面有一处沼泽地着火了。”
“有多远?”
“从这里可以看到烟。”他指过去。我们都往那边看。我们只看到空中有一道蓝色的光,气体燃烧完了。
朵拉茹日朝这对男女笑了笑。“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要住在荒野里。”这个女人的皮肤是贝壳的颜色,出奇地苍白,好像她一生都被保护着不受光线的伤害,她穿着黑色衣服。
“太好了,”朵拉茹日的黑眼睛充满了喜悦。“我要回家去安息。”
那个年轻女人沉默了。我能从她脸上看出,她认为我们其中有人疯了就已经够糟糕的,现在又出现即将来临的死亡。
那天晚上,布氏做了菰米饭和炸面包,我们和他们一起分享了一顿美餐。我想,在食物方面,这对年轻夫妇的差远啦。他们只有新鲜的橙子,我吃了一个,然后盯着其他的,直到他们再给我一个。我没了自尊。如果有必要,我会偷的。橙子是美丽的球形,甜甜的,充满了汁液。
我吃橙子时,艾格尼丝俯过身,凑到我耳边严厉地低声说:“别吃。不要吃他们的食物。”
我希望他们没听到她的话,但他们听到了,他们不时面面相觑。艾格尼丝显得很害怕,对我压着嗓子,强调好几遍:“我是当真的。”
那个年轻女人紧张地环顾四周,好像在密谋逃跑。当我们睡觉时,这对年轻人吵起架来。伴随着艾格尼丝的鼾声,我听到隔壁帐篷里的对话,“那些女人都疯了。”
“她们只是老了,”那个男人说。“她们没事。顺其自然吧。”他想留下来,即使没有别的原因,我想,他也想能够回去后讲讲关于我们这几个女人的事,包括我,那个脸上有伤疤,头发是红色,黑皮肤的女孩,我们带着毛皮和朵拉茹日,乘着过时的独木舟漂流。
那个女人一直在哭,她生气地说:“她们完全疯了。如果你现在不走,我就要回家了。”
没过多久,我就听到了帐篷桩、金属的碰撞声和衣服拉链的声音。到了早晨,这对年轻人,他们的狗和橙子都不见了。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呢?”布氏边说边看了看他们搭帐篷的地方。她显得很失望。艾格尼丝松了一口气。我把独木舟推下水,跨进舟里,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然后,我进入了那个空间,那个专为我和朵拉茹日创造的空间。
我们在水里划了一段距离后,朵拉茹日转过身看着我。她笑着说:“那个女人完全疯了。”
据说,很久以前,食人族就是这样出现的,他们从水里出来,从地平线划过来,就像鲍勃和珍那样。
从前,據说一男一女乘坐一艘人皮船从深海浮上来。他们出现在一道光中,越过地平线。这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他们想吃人。这个女人生下了一对双胞胎——战争和饥饿。他们有一只白色的狼。
他们说,是狼獾救了他们。狼獾把那个女人从捕猎陷阱里救了出来,做了两个皮袋装他们称为饥饿和战争的凶残婴儿,喂他们浆果和肉,然后把他们送给了人类。
在见到那对年轻男女后不久,在我希望有口红之后,我再次感受到奇异和荒野,就好像我们根本没有和其他人相遇过,好像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人。艾格尼丝继续用熊的语言说话;朵拉茹日说,“绕着这个弯道转。”布氏又一次隐退到她自己的世界里,一个取之不尽的,动物的世界。我们四个人中,我是最稳定的。我的双脚,即使不是稳稳踩在地上,也离地面很近。
我们在往东北方向行进。在我们前面,正如那个年轻人所说的,沼泽地里燃烧着泥炭火。布氏用手挡住阳光,看着灰色的烟雾和升起的热浪。它已经燃烧了一年多,来自地下的气体为火焰提供燃料。
从烟雾和热气的后面,传来青蛙催眠的叫声,那一起一伏的叫声像是沼泽中生命开始时心跳的节奏。乌鸦飞了起来,叫着,好像它们是烟雾的声音。火是有生命的,是一种红黑两色的动物,生长在丰富和腐朽的地下,是从落在地下的古代植物和昆虫中发出的火花。飞蛾飞向它。
烟味刺鼻,刺眼。我们绕着它兜了个大圈,穿过一片浅沼泽地,芦苇又高又暗。微风吹弯了青草,发出一阵嘶哑的声音。我跨出独木舟,踩进泥里,拉着朵拉茹日沿液态的泥往前走。朵拉茹日直视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你觉得艾格尼丝病了吗?”
“小心树枝,”我说。我费劲地走在泥水中。
一根树枝差点撞到她。她躲过了。“你觉得呢?”
我好多次有过同样的想法。我朝艾格尼丝瞥了一眼。她看起来面色苍白。“我想她只是累了。”
我没有注意到艾格尼丝是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现在,她看上去精疲力尽。她的脚踝肿了。腿部有一块皮肤裂开了,有液体渗出,好像被水浸透了一样。但她没有抱怨。
布氏也不时在观察艾格尼丝,我们来到一块陆地上,她说:“我们在这里呆一天休息下。”她把独木舟拖上陆地,根本不顾及我们是否有任何争论。布氏确信,我们离“北屋”不远了,这表明我们回到了人类中;我们离目的地不远了。“我们已远远超过期限了,再多一天也没什么。”
我收集木柴生火。幸运的是,那天阳光明媚。有大量的干树枝,马上可以燃烧。艾格尼丝跟着我。“我帮你,”她说。她气喘吁吁的。
“没关系,祖母。我自己行。”
我走得很慢,她免强能跟上我。我们走进了一片树林,她对我说:“听着。”她迟疑了一下,搜寻贴切的词句。“听我说,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希望你们让我躺在狼和鸟的身边;你能做到吗?”
我端详着她的脸,什么也没说。
艾格尼丝没有扭头看我。“这就是我的愿望。”
“好吧。”我折了几根枯枝,弯下腰,笨拙地捡起。我把其中两根递给艾格尼丝,又捡了一些抱在胳膊里,树木散发出浓郁的树脂香味,我们回到了宿营地。
“她在那说些什么?”当艾格尼丝听不见的时候,朵拉茹日问道。
我放下木头。
“我看见她跟你说话了。”朵拉茹日看起来很担心。
我划了一根火柴。“没说什么,”我说。我改变了话题。“我要洗几件衣服。你需要一条干净的连衣裙吗?”我们在北屋会遇到很多人,我想穿件干净的衬衫。
我密切关注着艾格尼丝,避开了朵拉茹日锐利的质疑目光。
朵拉茹日几乎没睡。母爱使她变得坚强,她坐在火边,守着熟睡的艾格尼丝。她把海狸皮盖在女儿身上。老妇人抚摸着她。
在睡梦中,铁锈色的根绕着我长成了一个圆圈,形成了新的球茎和连在一起的块茎,然后分裂,增殖。第一个绿色的嫩芽向亮光移动。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红根。一定是红根。”第二天早上,当我描述这段经历时,朵拉茹日说,“我不能肯定。但如果你梦到了,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她眯起眼睛看着艾格尼丝,“附子草,也需要。”
我跪在一盆温水旁,想起了给朵拉茹日指明旅途方向的祖先。我的生活在亚当肋骨之前,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我无从知道的限制。我没想过会有人靠做梦找到自己的路。在这个土地分开了水的地方,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事情,可能别人会认为是原始人的迷信。这怎么可能,来自自己土地的人,在那里生活了数万年,能与神灵交谈,能听到大地的说话声和动物的言语。北方的猎人都很杰出。即使是现在,他们也会梦见猎物的位置并找到那个地方。难道他们都错了吗?我不这么认为。
古老的世界在我心中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感觉,就像人的眼睛将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将图像翻过来,然后看到真实现象。
我们又碰到了那两个男女。艾格尼丝怀着不祥的预感看着他们。“他们在跟踪我,”她说。他们见到我们也不高兴,也没有想到会再遇见我们。他们对半夜离开感到羞愧和尴尬。
“你们迷路了吗?”那个男人问布氏。他来过这里。他知道是自己迷路了。他看着布氏,希望她会应答是的。她把手伸进包里,拿出一张地图。这一次,她明确地知道她在哪里。在遥远的南方天空中,泥炭火冒出的浓烟形成了一片灰色的云。如果他们在有浓厚烟雾给他们指路的条件下仍然迷路了,那么他们没多大希望能够冬天在野外生存。
他们把独木舟划到布氏旁边。我向他们划过去。布氏在一张地图上指出了他们所在的位置。
那里的水是深绿色的,有藻类和植物。布氏把地图的两部分拼凑在一起让他们看路线,泰勒朝水里喘着气,准备跃身去捕快速从水面滑过的水虫。我没敢對它说话;它会激动得掀翻他们的独木舟。
“我们兜了个圈子。”他毫不犹豫地说了声谢谢,便掉转独木舟出发了。
“等等,”朵拉茹日在他身后喊道。“你有铅笔吗?”
他把手伸进衬衫口袋。他的笔挂在一张信用卡上。布氏尽量克制着不笑。
“谢谢你。”朵拉茹日拿起笔递给我。“你有纸吗?”她问他。
他看着他的同伴。她的嘴唇薄薄的。她摇了摇头,没有。她急着要走,也许很高兴我们没问为什么他们半夜走人了,我看得出她太累了,没有力气去翻找文件。布氏递给我一个纸袋。
朵拉茹日说:“等一下。”她向那个男人伸出一根骨瘦如柴的手指。“画吧。把你梦见的那棵植物画出来,”她对我说。
我画着植物,那个男人从我们身边划开,又慢慢划回来,又慢慢划开。我画完后,说:“就是这样的植物。”然后把那张牛皮纸袋递给朵拉茹日。
“你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植物?”朵拉茹日把画递给他。“它以前就生长在离这不远的上游。”水面的光反射在他的皮肤上。
“泰勒,坐!”
那个男人仔细看着那幅画。“是的。”他说,在这点上,他显得很有见识。“是的,我敢肯定我见过。不是今年,前两年我见过。去年这种植物长在离北屋更远的北边。靠近花岛。来,把笔给我。”他画的地图显示了一个有许多小岛散布在水中的地方。
“我知道这些岛在哪里,”朵拉茹日说。
他在地图上标出了两大块相连的土地,并写上“花岛”。然后,这对年轻人很快地说,再见,向南划去。看着他们离去。白毛狗回头看着我们。阳光下,女人的金发泛着白光。
“艾格尼丝需要这种植物,”朵拉茹日对布氏说。“我们得去那里。”
这一串小岛很远,在我们的路线之外,但我希望不会太远。
接近塞奈河时,我们不得不放弃绕过它的计划,通往它的一些水域现在成了泥浆,独木舟无法通过。即使河水很急,我们也得冒险。这条河本身是两条河的力量,大臂河被改道流入塞奈河。这增加了我们旅程的距离。
我们靠近塞奈河时,地面发生了变化,有许多岩石和颜色更暗。我们感觉到从河里吹来的微风,一开始很柔软,但那是它欺骗性的低语。更近河边时,风变冷,变猛烈,连这也是一种欺骗性的喘息。事实上,河水震耳欲聋,几乎无法通行。我们到达河边时,看到它直冲而下,超载的水量,河水流过的某些地方,墙一般的岩石和陡峭的悬崖束缚了激流。两条河流的水被挤成一条,超出了它可承受的深度和宽度,猛烈撞击堤坝,向上蔓延到河堤外的其他地方,把岸上的树木都冲倒了。
布氏说:“这不可能是塞奈河,”她摇了摇头。有些地方,泥泞的褐色河岸被冲走了。她看起来有些虚弱。我惊慌失措。
布氏关心细节,试图了解这条河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土地和水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是一个谜。如果他们把大臂河改道,就像那个男人说的,那意味着前面的某些水域被封闭,其他水域被淹没了。布氏试着从大局看问题,似乎不可能。她查看着已经留在她记忆里的地图,似乎她可能错过什么地方。她弄清地形,预测会发生的情况。我们看到因为河流没能流入原来的目的地,有些陆地被淹没了,有些水域变成了泥滩。
塞奈河的响声如此震耳,在它之上什么也听不见。“它生气了,”朵拉茹日说。我俯身去听。“河流是生气了。两条河都在发怒。”河水强烈吼叫着,她说,声音这么大,听起来像大地在裂开,在狂怒。
“跟我来,安吉珥,”布氏说,她朝塞奈河走去。风猛地从水面吹过来。撩起布氏披在肩上的头发。她沿着河边走,毛衣被吹得紧贴身上,她希望顺河走一段路后能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一个弯道或有岩石的河道旁,我们能找到河流平静的地方。抵挡湍急河流的岩石墙很高,大部分地段连空手步行都不可能到达水边。更不用说带着船和一个虚弱的老妇人了。所有的地面都被苔藓和水花弄得很滑。我们转身往回走。
“这路行不通,”布氏说。“从这往下,都像这样。”她看起来忧心忡忡。“我们不能从这条河走。”她摇了摇头。她的话,被咆哮的水声淹没。
朵拉茹日朝布氏点了点头,她的白发被吹到了脑后。“可以,”她点头表示。是的,我们可以做到。我们要沿河行进。老太太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冒水的风险。除此之外,唯一的选择是掉头回去。谁知道我们身后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现在它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地方,因为建了水坝,我们划独木舟的地方的水都干了,不能通过。不仅如此,如果掉头,就得逆流而行。
迎风站着,我和布氏面面相觑。我们应该回去吗?我们都想知道。我们可以否决朵拉茹日。我们显得绝望,我们的眼神有疑问。我们谁也不知道答案。“应该”之类的逻辑已经不存在了。一切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无法回头。不是因为距离,而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已走得太远。我们不再是离开亚当肋骨时的女人。至于我,以前是我的那个女孩不可能在雨中划船时,似乎如没下雨一样,也不可能在潮湿的苔藓上宿营。之前曾是我们的那些女人永远不会在夜里自信地唱古老的歌曲,也不会与在森林里行走并允许我们进入森林的精灵交谈。曾经是我的那个女孩永远不会知道幽灵是如何像雾一样悬浮在水面,永远不会听到我们路过的这片土地的故事,也不会让自己沿着一条在任何地图上都是错误方向的小路前行。
现在我们的手臂强壮,我们能够用陆地的语言、水的语言、动物的语言,甚至我们彼此之间比较困难的语言,表达。我进入水和沼泽,被它们改变了。我梦到了草药,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的,比如能治愈关节炎的植物,我记得丰盛、持续的创造。
正是因为了这一切,朵拉茹日要与奔腾的河水谈话,与河水白色而浑浊的泡沫,它的氢和氧交谈,说服它让我们安全通过。她在我们的注视下完成了她与河水的交谈。
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说我们不害怕,那肯定是撒谎;如果我们说我们完全相信朵拉茹日,当她坐在河边对河说话时,那也是撒谎。我们只能看到她的嘴唇在动。我们什么也没听到。但过了一会儿,她朝我们点点头。“它会让我们通过的。”她大声说,这是最后的结论。在我们把独木舟放进凶猛而湍急的河水之前,朵拉茹日做了个祷告,张开手,把烟草扔进河中。她闭着眼睛,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一种尖锐的歌声。我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我只看到她的歌声被风吹过的河水带走。但我能看到她声音很强大。当烟草消失在水里时,我没有信心,但我照朵拉茹日说的做了。
我的独木舟先下水,它一碰到水,水流就想把它吞没。我抓住它,双臂颤抖着,浪花打在我身上。我看着布氏把朵拉茹日抱起来,在齐膝深的水里把老太太抬向晃动的独木舟。我已经浑身湿透了,我在发抖,即使是在很浅的地方,强劲的水流推着我的腿。我用尽全身力气站在那里,稳住独木舟,布氏把朵拉茹日放进舟里。艾格尼丝吓得脸色苍白,两腿在水里叉开。她注视着岩石周围翻腾的激流。即使在很深的地方,也能看出水下有岩石。她曾是那个在河流中无畏的人。她摇摇晃晃地坐了下来,紧紧地抓住衬衫的脖领,好像这样可以防止冷水渗透她的皮肤,但她,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已经湿透了,她的头发披到她的脸和脖子上了。
然后,布氏跪在独木舟里,好像在祈祷。她试图划桨,但突然间,布氏的独木舟不见了,在我还没反应过来之前,我们已跟在她后面,往下落。我尖叫起来,虽然没人能听到。就连朵拉茹日也显得很害怕,而她就是那个确信我们能挺过去的人,那个与水达成,不管是什么,协议的人。她紧紧地闭着眼睛。她的身子更低地倚靠在独木舟的深处。有岩石撞击船底的声音。我害怕得心怦怦直跳。完了,我想。如果我们不成功,肯定会被淹死的。我们遇到了要使我们的独木舟侧翻的漩涡和旋流。冰冷的水不断地砸在我们身上,湿透我们的头发,使我们的皮肤冰冷。我试着划桨,但胳膊疼痛。有那么一会儿,我正好赶上了水浪,独木舟飘移,似乎进入空中,转弯,然后落下来。河水带着残骸、垃圾、废弃物。我害怕撞到漂在河中很长的,还带着绿叶的树干。我根本没有希望停下来或减速。我想,这两条河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对方。我们被相互打架的河水掌控。我们任它摆布。我想起约翰·哈斯克告诉我的,要抓住水流,驾驭它就像骑在一只动物身上。我放松了,屈服于重力和它的流动,让我的臀部随它一起移动,而不是对抗它。就像骑马,哈斯克会说。
我尽力注意躲避那些會扯住我们的柳树和树枝。在短暂的几秒钟内,河水开始变得平缓,当我们快速驶过山丘和树丛时,河水又变得危险。我们穿过阴影,耀眼的阳光,所有一切如此之快地闪过,我们看不到鸟儿是如何沿着河的边缘飞起来的,只能看到其他所有东西和我们一起落进冰冷、浑浊的水中。在一些地方,河变窄了,水蜿蜒流向新的方向。我们挺过来了,我们经过的一些地方,河岸坍塌了,被扯断暴露的树根散发着泥土的气味,伸向河里,好像要阻止我们去北方。我们经过烧毁的树林,穿过黑暗,通过片片泥泞和淤泥,被带到了急流的尽头,是神的力量带我们通过的。也许是朵拉茹日的话救了我们,到底什么话,布氏和我都希望能听见并记住。也可能是纯粹的运气。我们四个,浑身湿透,喘着粗气,从水里爬出来,躺在坚实的地面上,又冷又累。就连朵拉茹日也使尽全力,跟我们一起闯过来了。过了一会儿,浑身湿透、肌肉紧张的朵拉茹日说:“那些女人都疯了,”接着大笑。她使用了一种计谋。她承认,但不告诉我们是什么。也许与她成交的不是水,布氏说:“毕竟,她达成了一项非凡的交易。”她不愿说她拿什么来交换的,但显然,是神灵带我们通过的。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