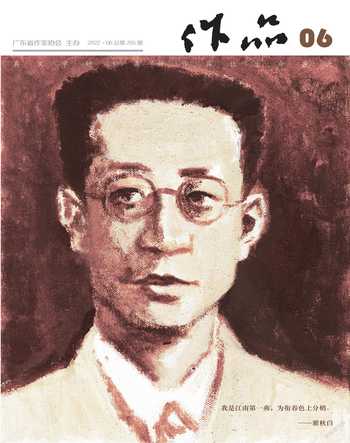绕地游
推荐语:张怡微(复旦大学)
为《红楼梦》做续补是很困难的,傅晓勇气可嘉。小说行文流畅,较为努力贴近原著讲故事的风格,另辟蹊径,为一对女性主仆补充了番外的故事。娇杏谐音“侥幸”,所谓“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作者为她的个性赋予了“勇敢、聪明、忠心”的优良品质,实际上也为主仆情义做了新的假设。封氏反而因此跳脱了原著时代的限制,显示出女性特质的脱俗潜能。学昆曲的设计稍显刻意,可能是为了扣住小说题目的曲牌,以示百转千回、命运起伏。奇梦通灵的设计带有民间故事的教化色彩。
此次改编若能写得更大胆些会更有看头。尤其是娇杏(侥幸)、英莲(应莲)、霍起(祸起)的命运错位,女性命运在原著的最终结果都是薄命。若要改命,需要续作者有更为深邃的、有力的认知和书写。“娇杏”是不是运气好?她是不是知道自己是运气好?她和封氏心灵相通互助的深层逻辑是什么呢?都有许多故事性有待开采。总而言之,作品清新、流畅、慈悲,作为《红楼梦》副线故事的补充,是有趣的写作尝试。
话说那甄士隐随疯跛道人归去之后,其妻封氏恨得直咬牙,因靠在父亲家里,成日里吃穿用度、应酬洒扫已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叨扰,每天出门寻夫不便再动用娘家家丁。幸而身边两个旧日的丫鬟还算忠心,一个大的十七岁,名唤娇杏,小的如今才七岁,是捡来的,叫个芳娘。那一年生了女儿英莲,人人都笑她是老蚌生珠,坊间的几个娘儿们甚至讥讽她是白费力气,费尽千辛万苦终究还是没能得男,可她自己却宝贝得紧,觉得这是菩萨念她一生未做过坏事,赏给她的一颗掌上明珠。
那年四月二十六,她去庙里给送子观音娘娘还愿,在路上捡到了这一襁褓孤女,因觉得有缘便将她抱了回家和自己女儿一起将养,思忖着来日待英莲出嫁时给她做个陪嫁丫鬟。只可惜,如今英莲不知下落,独留下个芳娘,有时候恍惚间,封氏想起女儿来也只能把芳娘揽在怀里,死命地哭上一通。再说这娇杏,也是当日还在苏州十里街的仁清巷甄府就用老了的人,虽则只是一个丫鬟,却是最贴身的人,从小受封氏的调教,这几年来同样的汤汤水水浸淫着,她倒学了不少待人接物的才能。再加上这丫头生性机灵、快嘴,两下里一结合,行事便带了些外面男人的果敢。可她到底也只是一个女子,每日受了自己的央告以买线为由出门去寻人,一双小脚走两步歇三步,回来时额头上猪油似的蒙了一层密汗,身上的衣裳也是被汗浸湿得不成样子。最难得的是如此的奔波劳累,她竟半句埋怨也无,封氏冷眼看着,心里也对这丫头生出几分敬意来。
这一日,娇杏回来时谨慎地拴上了房门,拿出一炷香捧到封氏面前,说是冷崖山上青云庵里一个老僧听了封氏寻人的缘故,怅然感慨良久,将这一炷香赠予了封氏,名为梦遇香,夜里在房中点了,便能在梦里得见想见之人。封氏听了这话半信半疑,但别无他法,因心中实在是有太多的话想要问一问那负心汉,只得照做。这一夜点了香,封氏坐在床上却始终难以入睡,只得拿了蒲扇扇着风,呆呆地盯着那帐子上的花纹。上面绣的是碎点子月季和一些条形的枝蔓,它们促笼在一起连成了一线,规规整整的却难免有些板滞。这样的花纹在苏州城里早五年前就不时兴了,现下住在父亲家里,虽则没受太多明面上的苛责,但将心比心,兄嫂他们哪里又会真的心里不存芥蒂?单单说上次芳娘去嫂嫂院子里,说是跟那入府来唱的小戏子们玩耍,回来时小脸上却多了五道鲜艳的红印子。封氏知道他们是碍于情面不好跟大人计较,便拿小孩子作法。当日士隐还在时,若遇到这样的事,他们好歹还会顾着姑爷的面子略赔上些笑脸,现在独剩她一个出了门子的女儿没脸皮地赖在这里,境遇已真真如履薄冰了。也不怪兄嫂薄情,她虽然生在大如州,可自十七岁嫁到苏州去,就已经成了甄家人,这几十年来在那江南水乡的旖旎与温婉中泡着,她也早已把他乡当作了故乡。
封氏盯着那帐子上的花纹,想起当日新嫁,苏州城内的新鲜玩意儿简直让她迷花了眼,听昆曲,游名园。闲时便支了绷子在房中练习女红,请了两个水儿一样毓秀的绣娘来府上教习,夜里她试探着把刚绣好的一个鸳鸯戏水的槟榔袋拿给士隐看,在晶莹的琉璃灯下,那人笑得乱颤,直把她揽进怀里轻轻地拍着:“夫人刚开始学习苏绣,竟已得了些神化,怎的这水鸭子身上长着这么几根鲜艳奇异的毛啊!”封氏知道是在打趣她,便不理會,拉了帘子歪在床上生着闷气。士隐走到床前来,敲了敲她的肩膀:“夫人,睡了?”
“夫人,睡了?”封氏侧过头来,发现甄士隐不知何时到了床前,头戴乌青色混元巾,手执一麈尾拂尘,颈上却挂了一青团大小连成串的佛珠。僧不僧,道不道,那手虽苍老得很,血管子嶙峋地搭在肉上,但又像是一副晴天收起不用的伞骨,带了些刚凉,也有点笃定的意思。封氏怔了一怔,待回过神来,已一把将那人扯住。“狠心的爷们儿,当日去时你怎么不知会一声,我在街上多番打听,才知道你是被疯道士骗了去,你们去的到底是哪个道观啊?怎的你还戴了这样大的一条佛珠?难不成去的不是道观而是佛寺?”那人扫了扫拂尘,镇定地回答:“既非寺庙,也非道观。常言道释道是一家,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只要诚了心、解了意,就可心安,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吾乡及无乡。所以我去的地界不是这尘世中所在,乃太虚幻境是也。”
封氏啐了一口:“既是这样好的一处所在,你又看破了红尘,合该死在那里才是!怎的今日又到我这儿来现世?要说这红尘,我也看破了,可难道人人都学你这样抛下家人跑了不成?可怜我这一生没个儿子,四十岁上生下个女儿还被那天杀的狗奴才霍启弄丢了,原是我的命不好啊!”那人对答:“非也非也,不是你的命不好,实乃我们人是这天地间最污浊之物,无论男子女子、王侯将相抑或是贩夫走卒,自打娘肚子里出生那一日,便注定了是要在这世间受苦受难的。如今我的劫数已尽,一朝受了度化到了个再无苦难的好地方,只是他们说我虽已悟道,但根基太薄,派我下世来助你造业,成就了一番功德之后才能位列仙班。”
封氏坐正了身体:“你已不在这世间,自是不能领会这世间的苦,如今你快要得道成仙,若当真还念着我们的夫妻情分,我只求你一件事,帮我多生些银钱来使用,到底不让父亲兄嫂他们轻视了我去!”
话说完,只见立着的那人却笑了:“罢了罢了,想来是你还未入化境,我多说也是无益。其实你当下的困境抑或是将来的困境,甚至是寻找英莲的下落,都离不开一个‘贾’字,去找那姓贾的人便可迎刃而解了。尤其是英莲,日后她会住到京城的国公府贾家,只是你现在去寻她也是寻不到的,必定得等她入了那火坑,享了富贵,受了苦楚之后才算功德圆满。”封氏听到话里提及英莲的下落,想起这多年的心病来,又是笑又是哭,踌躇了好一会儿,待要说话时,却发现甄士隐早已不在房中。她急得下床摸索,慌忙中打翻了立在床前的白瓷夜壶,再看那房门紧闭,从屋里面拴上了锁,八仙桌上供着的梦遇香也已经烧尽,方知竟是做了一场梦。
第二日,封氏唤了娇杏来房中说话,谈及昨夜的奇遇,二人都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那梦中人所说之事是真是假,但是细细地推究起姓贾的人,竟只想起来当日那在葫芦庙里借住的穷儒生贾雨村来,难道要找他吗?只是如今他人身在何处都未可知,又谈何求助呢?正疑惑着,忽而听到外面街道上响起了鞭炮,还有唢呐声、人声、马声、衣裳摩擦声、鞋袜踏地声此起彼伏,一阵盖过一阵。这时从二门上传来了消息,说是新晋本府太爷今日上任了。封氏命娇杏出门去,仍旧以买线为由打听那新太爷的来历。
不出一个时辰,娇杏踉跄着跌进封氏的房间,脸上竟还带着些桃色,问她话时,却忸怩了起来。封氏说:“何故做出这样一副不爽气的样子来,没得惹人生厌!”
娇杏见封氏心急,怕她再生了肝火,便朝她福了一福:“夫人容禀,我出了门听到街上的人说新晋的太爷本贯湖州人士,姓贾名化,心里便猜着了七八分。接着又挤进那人堆里朝他的大轿上望,发现那人當真是曾经住在咱们仁清巷葫芦庙里的雨村先生!”封氏疑惑起来:“当日雨村先生来家时,一向只在外面厅堂或者书房里和老爷说话,你是里面的人,从未见过他一面,怎的说你还能认出他来?”这话说完,二人都不言语,略沉默了一会儿,只见那娇杏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夫人恕罪,按理咱们的确是不到前头书房去伺候的,只是当日莲姐儿还在时,老爷和夫人都宠爱她,要什么便给什么,奴婢自小受老爷夫人的恩惠,怎能不对她尽心?那一日,她听小厮讲老爷书房中的芍药开得正艳,便吵闹着要去摘。奴婢经不住她缠磨,想着这会子正是午休的时候,书房中应当没人,便大着胆子走进书房去摘花。这一进去,刚好就碰到了雨村先生。奴婢见他饶穿着敝巾旧服,但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又有一对剑眉心眼,实是一副大丈夫的气度,因此,虽则只见了一面,倒把他的长相记到了心里,想着若来日嫁作人妇,必定得是他这样的人。恕奴婢斗胆,如今夫人在娘家寄居,日子过得艰难,奴婢每每想到这里都觉得痛心。我愿领了夫人的命令去他府上伺候,好歹替您多挣些面子,权当是报答您和老爷这多年的恩惠了!”
封氏听了不免动容,赶紧扶娇杏起来:“好孩子,你竟有这样的壮志,倒真心教人佩服,也好也好,你这样做既是成全了自个儿,也是成全了我啊。”说完娘们儿两个又哭了一场,说了些日后的憧憬,这些自是不消再讲。晚饭后,封肃也来到封氏房中,转述了自己白日里被新太爷请进府上所叙的几句旧话。封氏听了,忆起当年,心中泛起无限的愁悲,但也暗自庆幸那贾雨村大约并不是忘恩之人,知道她和娇杏所筹谋之事估计能成,这天晚上她一宿无话。
第二日大半天的辰光封氏都在琢磨着,该寻个什么由头把娇杏塞进那贾雨村府上去。晌午过后封肃却传来了好消息,说是太爷寄了一封密书来要娇杏。真是应了坊间的那句俗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封氏正欲答应,又想到这娇杏终究只是一介奴仆,身份寒微得很,若是去了太爷府上不一定会有多好的前程,可能最多也就做个通房的丫鬟,这于她于己当下的处境都无多大的益处。因此传了消息过去,说这娇杏虽则只是一个丫鬟,但模样品性都是出挑的,成日价行事说话又都很妥当,如今一时半会儿竟有些离不得她。但是太爷既然肯写信来要她必定是一番诚心,自己也不能不成人之美,只是不想她再做那洒扫挑洗的累人活计。现下自己愿意收她做个养女,倘若能让她以甄家庶女的身份嫁给太爷做个二房便是极好的了。不多时,那边便传来了消息说正有此意,此事算是讲定了。
这天夜里,封氏把娇杏的手搭在怀里,不知说了多少掏心窝子的话,又流下多少眼泪,最后拿出自己的一只碧玉手镯套在她的手上,趁天黑将娇杏用一乘小轿送了过去。她知道,这天过后,从此便又是新的一番天地了。
那娇杏虽然并不是一等的美人,但也算是生得水灵,又难得的有一副玲珑的心肠,再加上当日在仁清巷的缘分,一入府便得了太爷的宠爱。新婚夜,贾雨村将她搂在怀里说起当年在甄府花园的那一场邂逅:“一般丫鬟见了外客总是腼腆的,可你却不同,足足又回望两次,由此便知道你的情意与胆识了。当日刚进这大如州城,坐在那大轿子上倏地就瞧见了你的身影,这样说你可能不信,我一下子就记起来你是当日那个采撷芍药花的女子了,回去思虑再三还是决定厚了脸去向你家夫人要人。现下你果真成了我的人,当日在那花园里的情分如今到底是接续上了。”
娇杏听他讲这番话,不由得感慨起这世间的因缘之事果真是难料,心里却也略略存了些不服气。但一闭上眼,眼中立刻浮现出今后在太爷府的锦衣玉食的生活来,便也渐渐地将这不服气给放下了。待这一年冬至时,那封氏入太爷府去看望娇杏,见她身子沉重、小腹隆起,便知她也是将要做母亲的人了。自此,娇杏也更得太爷的怜爱,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一水儿地朝她房中送,说是助其养胎。第二年初夏,娇杏产下一子,一时间在太爷府上风光无两,难得的是她果真没有忘本,明里暗里地给那封氏不少好处,封氏的日子也就在她的庇护下略微过得松泛了些。可另一边那太爷府的正房夫人却有些坐不住了。
初时,那小丫头娇杏被一顶坠着紫流苏的粉色轿子抬进府来,虽是娇艳,但到底有股子小家子气,上不了台面,虽然美其名曰是娶作二房,但那规制哪一样是照着娶二房的规矩办的?就是她那点寒酸的嫁妆中也只有一只碧玉的手镯还算精巧,看得出是江南工匠的手艺,其余的便跟那街上寻常人家嫁女差不多的行头了,因此她从没把这丫头放在眼里。可不承想那狐媚子的本事竟这样大,日日缠着老爷进她房中,现在她生了儿子,竟真把自己当个角色起来,成日价向老爷要这要那,不知眼里还有没有她这个大太太。因此,她便隔三岔五地叫那娇杏进房中听训,只是那娇杏先前从未过正经被人伺候的好日子,如今被贾雨村当成宝贝一样地供着,难免也生出几分不逊与骄傲来,便时不时地在言语上有些顶撞。那夫人见她并不听训更加气愤,于是说起当日她嫁进来,一没有经过父母之命,二没有媒人相看,再来那趁着黑夜里送进来的规矩实在是不合礼数,扬言要将她休了重新再给老爷找好的来。
娇杏深感形势危急,自己却不知该如何应对,便传了封氏进府上来说话。封氏泪汪着眼听完娇杏眼下的艰难,忽记起青云庵老僧送的那炷梦遇香来,当日点了那炷奇香,夜里果然梦见了想见之人,那梦中之人言语之间所谈及之事一半都是未来的事情,她向他求助帮忙改善处境,便给自己出了个去找姓贾的人的主意,也是因为这个才有了这接下来的许多故事来。现下何不再上一趟冷崖山寻得那老僧,讨些香来,夜里梦了甄士隐,向他再求一求妙计,就是求不得妙计,问一问他咱们将来的光景究竟如何也是好的。娇杏听了拍手叫好,立即称了些银子拿给封氏,说自己刚生产不宜出门,请她雇一顶软和的轿子亲上冷崖山去找那老僧。封氏听了赶忙答应下来。
回家收拾了一番,封氏便雇了一顶小轿往那冷崖山上来。这山虽则名字听起来有些料峭险峻,实际却只有两百来仞高。不过,若真要抬那么大个人一步一步地移上去,也少不得要花些功夫。
此时已到了六月,正是盛夏时分,封氏离了拘谨繁冗的娘家,又穿过热闹的市街,来到这山清水秀的郊野,心情甚是和畅,眼前的树木长得蓊蓊郁郁,耳边又尽是鸟语、蝉鸣。她朝那日头从树叶间隙处投下来的无数流动的碎光点子看,似乎已经听到了那日光穿透树叶之声,紧接着,又好像听到了山风从地上卷起尘土之声、轿夫们豆大的汗珠子从颈上滑落之声,甚至是有一种她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也变得清晰起来。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声音,她并没有细细去探寻,只是她感到似乎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听过这样的声音了,颇有些亲切之感,而且它并不浓,淡淡的,像是一种快乐,但分明又有一种忧伤在里头。
就这样徜徉着,轿子不知不觉间已抬到了青云庵的门口,她缓缓地下了轿子,往那庵里走过去。寺庙并不大,除了正殿大雄宝殿、两侧的钟鼓楼、以及后院的禅房外并无多的殿宇,封氏看到这番场景,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只是行到那禅房后面,却发现有一片竹林生长得格外好,一径呈一种晶透的碧色。封氏看到那竹林下有一老僧正在闭目打坐,瞧他那唇下一缕疏朗的山羊胡子,颇有些仙风,便知这正是那位送香的高人了。
封氏双手合十朝那僧人行了一礼,便问:“敢问您可是那位曾经送过我们家梦遇香的师父?”那僧人听了这话无半点迟疑,说一句“正是,”但并未睁开眼睛。封氏听了不免激动,正欲将自己的来意向那僧人禀明,却见他笑了一声:“施主不必多说,我知道你的来意,当日送你那梦遇香是念你生性良善却一时多舛,因此便送香助你,实际那通灵的事情最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不仅要有香做助力,也须人的心虔诚干净。只是人这副躯干内有十之六七都是水做,既是水做,那便有无穷的形态与变化,每一时都不同。就好比你今日来这竹林之下找我,我们一期一会,殊不知此时我已不是彼时我,此时你也已不是彼时你。所以这梦中通灵的神力彼时你可有,此时却未必能有。施主还是请回吧,若到了一个好时机,自然就会再次梦上了。”
封氏听了并不十分懂,但恍惚间却生出几分怅然,唯唯诺诺地应了便下山去。她并不信那僧人说的等待时机之语,但却信这世间万物大约都有某种不可知的力量在运行。待下了山,她忽又想起了那一片竹林。人人都说竹子是最高洁最安静的植物,拿来比作君子最相宜,殊不知那竹子根能在地底下盘根错节,别有一番繁荣。所以虽则那竹子长高长低长歪长斜,全得凭雨水和风的态势,但一旦到了那地底下却又是新的一番世界。
她封氏也像那竹根,并不是个逆来顺受的。如今娇杏的日子不好过,连带着她在娘家也受了不少冷落,本想着能借着娇杏的东风多多积些钱财,好歹能置下一个小院让自己搬了出去,现在也是不能够了。不由得哀叹,自己本有一个好夫君,却弃她而去,本有一个乖女儿,却失了踪如今不知是死是活,如今年事已高,都不知还有几年活头,却日日战战兢兢过日子,百年之后为她披麻戴孝的人都不知有没有。这样一想简直感今后的日子是一片漆黑,真真到了绝境。既然那老和尚说做梦通灵要等待时机,那就只能另想别的辦法。
这一日,封氏下了山,并未往封宅走,进了一药铺抓些药材再略坐一坐便径直进了太爷府。没过几天整个大如州街上便听到了那太爷府里的大太太突染急病的消息,有人说是因为贪嘴吃了两种相克的食物,也有人说是误把某种凶猛的药材掺进补品里一并吃下了,还有的传得更神,说是因为做梦梦到黑白无常来接她,第二天清早一醒便生了急病。
芳娘将这些话学给封氏听的时候,她正在房中哼着《牡丹亭》里的一曲《绕地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她并不接芳娘的话茬,只问她:“我唱得如何?”芳娘声音脆脆的:“夫人唱的我也会唱,我虽年纪小不解那词儿,但想来必定是极美极隽的意思了,夫人唱出来的时候舌头一定都舒服极了吧!”
封氏听了不免怔了一怔,想不到她小小的年纪竟能说出这样的话。又说:“前些年咱们还在苏州的时候,我时常请了昆曲班子里的角儿来家里演唱解闷儿,当日最爱的便是这《牡丹亭》,你今竟能有这般不俗见解,我送你去学昆曲如何?”
芳娘又答:“我愿意学,只是咱们从苏州过来还留下的统共就两个人,娇杏姐姐早已离去,现下就独我一人陪着夫人,怎可只顾自己而抛下夫人不管呢?”封氏见她答得得体,心里欣慰,又想到若是英莲还在,估计也是这样的贴心巴肉,可能比她还更伶牙俐齿些呢,只是为何那梦中人说必定得等她成年后才能寻到她?想到这里封氏不免落下几滴泪来,独自一人进房中呆坐着。
这一进,封氏便再也不曾出门。等过了些时日,她又托人弄了一座佛像在房里供着,日日地烧香祭拜,有人去看她时发现她的眼角总是有泪,竟不知是被那烟熏了还是因为太过伤心。封府里的太太媳妇们这才想起先前那甄士隐刚走时,人人都跑来宽慰她,可她却偏偏一滴眼泪也不流,大家讨了个没趣便走了,回去之后再谈起她都说她不值得同情。如今,那甄士隐已走了不少日子,她却像是突然开了窍,成日里在佛祖面前哭,她的心肠到底是软了下来,使人觉得可亲了一点。由此便又有些人觉出她的好来,三不五时地也来房里陪着她哭,只是她们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哭她男人,还是在哭自己。大约是哭自己吧。
就这样,再不出半年的时光,那太爷府的大太太终究是殁了,娇杏因生男有功,又借了甄家的身份,勉强可以上得了台面,便得了太爷府老夫人的恩准做了续弦。爱屋及乌的太爷更是赏了封氏百金,说是感谢她这许多年来对娇杏的悉心调教,还要上禀朝廷,为她挣一个节妇的名号,作为本府千万女子的表率。这消息一出,本地各家官宦子女和乡绅淑女都入封府前来贺喜,封氏在娘家也渐渐地抬起了头。
这一年的春节又热闹了起来,等开过年,她便拿着贾雨村赏的钱在城里另找了一处干净的小院带着芳娘搬了进去。人生第一次,她靠着自己挣下了一处宅院,虽然小,但终究是自己的。封氏在这座小院里自由地吃饭,自由地睡觉,自由地闭门谢客,也自由地宴请嘉宾,只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一些寂寥。此时她便依稀地回忆起当年在姑苏城中那段繁花似锦的好时光来,但记得并不清楚,好似那些人那些事竟都是上一辈子的了。这时候便想起那夜做梦,甄士隐说人人生来都是受苦的,当时她觉得说得不好,这世上也许还有未曾受苦之人,而且他那样的讲苦难讲超脱,分明就是一种置身事外的姿态,哪里懂得这身在其中的滋味。可是,如今想起,竟觉出几分意思来。
第二天天刚亮,忽又听得外面鞭炮声响,又是同当日一样的唢呐声、人声、马声、衣裳摩擦声、鞋袜踏地声此起彼伏,一阵盖过一阵。她开门问了才知道,原来是那太爷贾雨村已经被参,今日顶替他的新太爷上了任。正踌躇着,发现娇杏进了院门来,她已是一身素净简朴的村妇打扮,刚准备给她设茶,那娇杏却扑通在眼前跪了下来。
“夫人,娇杏今天是来辞您的,我们老爷现下被革了官职,正打算出去游历几年,我受了他的嘱托要带着一家老小往原籍湖州祖宅去了。夫人不必为我挂心,想来我这一生也是够的,托了您的倾力相助才得以过了两年安乐富贵的日子,虽是短暂,却也知足。这只碧玉手镯是当日我嫁进贾府时您赏给我的,如今我要走了,娘们儿两个也不知这一世还能不能再见,请您再收回这只手镯,权当留个念想吧。当日那大太太死得不干净,是你我为了自保才不得已造的孽,风水轮流转,如今我自己也跟着老爷一起倒霉了。只是我并不怨天,想来这些都是我的报应,如今我脱了一切钗环替她抚养遗子孝顺公婆,权當是赎罪一二吧。”
封氏听了不免鼻头一酸,却再也流不出泪来。从此,她闭门谢客,整日只与芳娘作伴,闲时也叫她捡那昆曲里词曲清雅的来唱,听得也并不入神。只是常怀念起自己那日坐在软轿子里上冷崖山,盛夏炎炎,却有绿树成荫,地上卷起来的热空气经那山中古树的抚摸,变得凉爽非常。果真是风光丽丽,疏朗气清。可是,当初那样好的景色,那样徜徉的心情竟再也未曾有过了。
话说另一头,这一年秋天,苏州城内几乎人人都被一个京城来的贾姓公子的派头所折服,说是因家里盖园子,现下正在城中四处聘请教习、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其实,这聘请教习、置办乐器行头两事倒还容易,只是在采买女孩子上却发了难,因是说买了去是要给贵人听戏的,所以必得要挑那模样好又有天赋秉性的,相看了不少发现不是模样不够就是品性太俗,因此便托了许多人帮忙推荐。一时间,城内许多府第里的小丫头子心里都热络了起来,个个清晨起来吊嗓,练习形体。
等过了中秋,封氏家的大门被一苏州口音的男子敲响,开门才发现是那许多年前带着英莲逛灯会的旧日家丁霍启!那霍启一进门就跪倒在地再也不肯起来,说是当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不敢回府便趁夜逃出了城,一边逃一边替人做些短工竟一路跑到了湖湘,因从小在水乡长大,水性较好,便在那洞庭湖一艘渔船上做起了水手,这一晃许多年来竟也平安地过了。只是这一年年的看着船上诸位同伙都渐渐地成了家,他因为不会说那边的土语又无根基却很难找到相宜的,这才慢慢想起自己家乡的好来。因此,自今年春上,他决定再也不能躲下去了,自己闯下的祸总是要自己来承担,于是等那边过了端午划过最后一次龙舟后,便日夜兼程地顺着江往苏州过来。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到甄府谢罪,等到了仁清巷却发现已无半点当年的痕迹,一问才知道旧日主人遭了殃,已到大如州投奔亲戚来,他几经辗转,这才寻到了封氏的家门,今日既已认了旧主,便决心不走了,下半辈子愿当牛做马以赎当日之罪。
封氏见他说得恳切,其间又有许多跟自己当日在那太爷府做过之事相似的心境,未免将心比心,先前想要问狠治罪的火便灭了大半,给他看了茶,叫他站起来说话。问他刚从苏州过来,那城内可有什么新闻,霍启便说起那京城贵公子采买女孩子一事来。这时,封氏脑海里当日那一场梦中的场景又再次闪过,便问霍启那贵公子姓什么,说是姓贾。她心里感叹,果真是姓贾,又是姓贾,但也知道,这次说的便一定是那梦中人所说的贾家了。因此便唤了芳娘出来见客,命她当着人面唱一曲《绕地游》。那霍启听了连连称赞,又问她,可还记得怎么说苏州话,答说记得不详细,封氏说这不打紧,等入了京城必定得是说官话了。
封氏从床头的小匣子里拿出那只自己送给娇杏又被送回来的手镯,轻轻地要往芳娘的手上套:“好孩子,你先前说想学昆曲,今日就让你霍大爷带去苏州找那个贾公子吧,这原是上天就注定下来的缘分。想着你和你娇杏姐姐与我,咱们三个虽是主仆,但这许多年来却是你们两个支撑着我走了下来,这些年我犯了不少罪过,造了许多孽,如今也该是去赎罪的时候了。就像你霍大爷一样,虽是隔了太久,但终究还是要迈出这一步,想来佛祖在上,将来也不会不护咱们平安吧。凭你的天赋和模样一定能被那贾公子选中,只有一样,我嘱托你,咱们莲姐儿日后可能也要去那里头跟你做伴呢,到那时你若是见了她,替我问一句可还记得她亲娘不曾。”
说完便又拿了手绢来抹泪,但其实这动作是做给人看的,她知道自己早就没有泪了。那芳娘先听到封氏要她去苏州以为是赶她走,正欲哭着求情,后又听她提起赎罪什么的,想起这半年来夫人日日在佛前求饶,虽不知她是犯了何等大错,但一定是对她来说极其重要的了,再加上又提起莲姐儿一事,便知兹事体大,必定是推辞不得了,便强忍着泪水接下了那只玉镯,再拜了三拜,终究还是于第二天随霍启启程去苏州了。
于是封氏便收拾好行李,朝那冷崖山青云庵上走去。
责编:周三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