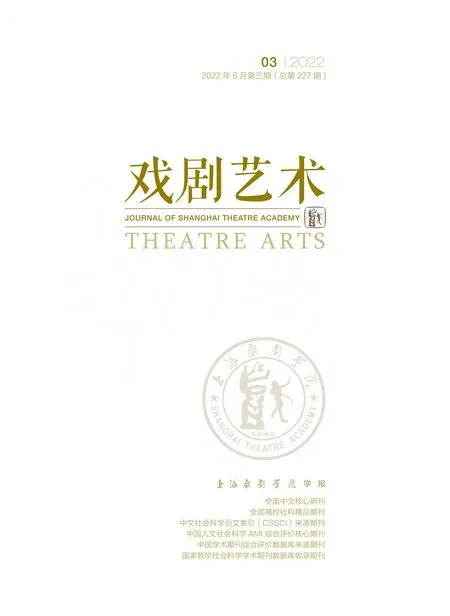勾栏新探
陈佳宁
勾栏是宋元时期戏剧表演的重要场所,早已引起学界的关注,时至今日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现观学界对勾栏的探讨,廖奔先生主张的“栏杆说”较有代表性。他在《中国古代剧场史》一书中提出,勾栏的本义是曲折的栏杆,由于唐五代时的表演区都是一个四方台子,而在台子的四周围有栏杆,“人们因为台子围有栏杆而称它为勾栏,进而又借称作演出棚的名称”。此说一出,得到不少人支持,如康保成、薛瑞兆、麻国钧、李纯等学者皆持此见,并对“栏杆说”予以不同程度的补充。但也有学者对“栏杆说”持怀疑态度,如黎国韬师《勾栏新考》一文,从语源学、民俗学、建筑学的角度切入,提出我国西南地区的干栏式建筑才是“勾栏”的来源,二者的形制如出一辙。
前辈学者主张的“栏杆说”和“干栏说”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如“栏杆说”认为勾栏是围有栏杆的表演台,宋代时用于借称演出棚,但演出棚和栏杆之间有何关系,为何要用“勾栏”一词称呼演出棚,支持此说的学者并未予以解释。又如,“干栏说”主张勾栏的棚式结构源于西南地区的干栏式建筑,但作者没有举出任何干栏式建筑影响了中原建筑的证据,这一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勾栏在宋代的真实面貌。
一、 勾栏的形制
笔者在整理宋代的戏剧文物时,发现了几则重要的石刻砖雕,均是艺人在栏杆之内表演歌舞戏剧,这很有可能就是宋人对勾栏的反映,现将其披露于此。
第一则石刻出土于四川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是南宋墓葬,石刻中雕有一座弧形栏杆,栏杆内有六人在表演乐舞,从左至右: 第一人左手托扁鼓,右手持杖击打;第二人托杖鼓于左肩上,右手执杖击打,左手拍击另一侧鼓面;第三和第四人为舞者,她们双膝微屈,上身微俯,双手抬起作舞蹈状,对应起舞;第五人侧身回首吹奏横笛,第六人双手于右胸前执拍板。(见彩页图1)
第二则石刻也出土于四川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泸县宋墓》认为它反映的是戏剧演出的情况。石刻中雕有一座弧形栏杆,栏杆内有二人,左侧一人头部残损,面向右侧,双手置于胸前,上身微俯作施礼状;右侧一人左臂下垂,右手伸出袖外指左侧之人,似让对方免礼。(见彩页图2)这二人的动作在宋代其他反映戏剧表演的文物中十分常见。比如,四川广元市四〇一医院出土的一块南宋石刻中即有类似动作。廖奔先生认为其所表现的正是宋杂剧的演出场景。再如,苏汉臣《重午戏婴图》中亦有一人作揖、一人似作免礼状的场景。康保成先生指出,图中五位儿童正在进行杂剧表演。这说明,作揖行礼是宋杂剧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动作模式,由此推及泸县石刻图像也是对杂剧演出情景的反映。
第三则文物为两块杂剧砖雕,出土于重庆大足区龙水镇明光村磨儿坡宋墓,是绍兴三十年墓葬,位于M2墓室左右两侧壁龛。由于学界尚无人提出这是一组杂剧砖雕,现将其具体情况叙述如下。先来看左侧壁龛的砖雕,此砖所刻四人位于栏杆之内,左起第一人戴头巾,身着交领袍服,左手下垂,右手持一长形物体,疑为木杖;第二人为女性,头梳瓜瓣形,挽高髻于头顶,两臂下垂;第三人戴无脚幞头,身着圆领大袖袍服,左手握右袖,右手拇指与食指置于口中,作打唿哨之状,模样诙谐滑稽;第四人戴无脚幞头,身着圆领袍服,左手持笏板于左胸前,右手臂下垂,表情严肃。(见彩页图3)再来看右侧壁龛的砖雕,此砖刻绘的栏杆形制与左侧相似,栏杆内站有五人,皆身着圆领大袖袍服,从左至右: 第一人头戴软巾,右手持一鼓,左手做击鼓状;第二人戴无脚幞头,双手持筚篥吹奏;第三人头戴软巾,双手握笛吹奏;第四人戴无脚幞头,双手握拍板作开合之状;第五人戴无脚幞头,手鼓夹于腋下,带挂于颈上,手拍鼓面。(见彩页图4)
这两组砖雕位于壁龛两侧,一左一右相对,二者之间恐怕不无关系。笔者推测,右侧可能是伴奏乐队,而左侧是杂剧表演。原因一,这些乐人所持乐器与宋杂剧的伴奏乐器相当一致。鼓、笛、拍板是宋杂剧表演必不可少的乐器,这块砖雕中有二鼓一笛一拍板一筚篥,这些乐器完全符合宋杂剧乐队的基本配置。原因二,左侧砖雕所刻四人可与宋杂剧脚色一一对应。第一人手持木杖,极有可能是用来击打副净的砌末,此人当为副末;第二人是唯一的女性角色,无疑是装旦;第三人打唿哨的动作是副净打诨时的常见科范,此人表情滑稽,在四人中最为突出,当为副净;第四位手持笏板,与装孤色的形象较为吻合。结合乐队乐器和人物形象来看,这两块砖雕表现的正是宋杂剧的演出场景。
第四则砖雕出土于重庆大足区龙水镇明光村磨儿坡宋墓,此砖同样刻有一座栏杆,栏杆内站有三人,从人物形象观之,恐怕也是杂剧表演的场景。左起第一人戴展脚幞头,穿圆领袍服,手持笏板于左胸,是典型的装孤色扮相;第二人戴牛耳幞头,穿宽袖长袍,左手持右袖,右手指向前方说笑,表情滑稽,据延保全《副净色及其文物图像小考》研究,牛耳幞头是杂剧院本里副净色的常见装扮,此人当为副净色;第三人戴头巾,颔首站于一侧,在宋杂剧的脚色配置中,最不可缺少的是副净和副末二色,此人应为副末。(见彩页图5)
这四则文物反映的信息,大致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它们均出土于宋代墓葬,第一、第二则是南宋时期的石雕,第三、第四则的具体时间更加详细,是在南宋绍兴年间,这些文物既然出自宋代墓葬,它们反映的内容无疑是宋代社会的情景;其次,这批石刻砖雕中均刻有栏杆一座,在这座栏杆之内,或是乐舞表演,或是杂剧表演,说明这座栏杆与演出的关系相当密切。结合这两点以及前辈学者主张的“栏杆说”进行推测,恐怕石雕砖雕中的栏杆正是宋朝勾栏的舞台。之所以将文物中的栏杆定义为“勾栏的舞台”,而非“勾栏”,一是因为,上述文物展示出来的场景只有表演区域,并非勾栏全貌,直接将其视作勾栏实属不妥;再者,勾栏是棚木结构在宋元文献中频频可见。如《东京梦华录》称:“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又如《繁胜录》记载:“常是两座勾栏,专说史书,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背做蓬花棚,常是御前杂剧。”而且勾栏还有不少带“棚”字的别名,也可说明这一问题,如《南村辍耕录》提到,“有女官奴,习讴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几,棚屋拉然有声”,此处将勾栏称作“棚屋”;又如《五灯会元》称“四衢道中,棚栏瓦市。畐塞虚空,普天帀地”,此处勾栏被称作“棚栏”;再如《般涉渊·哨遍·嗓淡行院》有云,“倦游柳陌恋烟花,且向棚阑玩俳优”,这里勾栏又被叫作“棚阑”。由此可见,勾栏绝非是一座栏杆围成的表演台这么简单,其整体是一种棚式结构,上述文物所能反映的内容只是勾栏中用于表演的舞台。要想得知勾栏全貌,就必须从“棚”切入。
“棚”字从木,说明这是一种由木材搭建的建筑,其形制与中国古代常见的建筑——“阁”十分相似。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称:“《苍颉篇》:‘棚,楼阁也’;《通俗文》:‘连阁曰棚’……今苏俗谚语曰‘搭棚’,盖空中楼阁之谓。”唐代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也有类似的解释:“《通俗文》:‘连阁曰棚’,棚亦阁也。”正是因为棚与阁的形制相近,小学家们才会以阁释棚。除了文字学的阐释外,“棚阁”还能作为一个词语出现:
讽帝令都下大戏,征四方奇伎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万数。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而罢。
应诸街坊通车牛外,即日或有越众迥然出头,牵盖舍屋棚阁等,并须画时毁折。
高二丈以上,每一丈每一功各加一分二厘功;加至四丈止,供作并不加;即高不满七尺,不须棚阁者,每功减三分功。
结合以上两点来看,棚与阁的建筑形制是高度相似的。民国时期建筑学家乐嘉藻在《中国建筑史》提到,阁大概始于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较早出现的高层建筑之一,至于其形制,“凡所谓阁者,皆具有一层木材,下空而用其上之义。故两层以上之建物,其上可以居人,而其下则空者,名之曰阁”。既然“阁”是架木而起的双层建筑,“棚”的形制大致也是如此,即下层以竹木为支架,所用者只有上层,这与朱骏声所说的“空中楼阁之谓”完全一致。但一种建筑的形制并非一成不变,要想得知“棚”在宋代的具体形制,除了追溯其历史渊源之外,还应寻找宋人记载作为支持:

建康王枢密德言纶云: 乡人王上舍,以政和六年元夕,与友同出府治观灯。三友登山棚玩优戏,王独在棚下,不肯前。
又有瓠羹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呇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
第一条史料中“剪五色彩为层楼”说明人们用竹木编制的这种棚由两层构成,单层建筑不会以“楼”称之;第二条史料中“登山棚”“在棚下”两个动作表明棚沿袭了此前双层结构的建筑样式;第三条史料提到的“山棚”,是官府在元宵节搭建的一种临时舞台,供市民娱乐,但这条史料描述的并不是山棚,而是仿造山棚形制而建的店铺门首的“枋木及花样”。之所以选择这条史料,是因为《清明上河图》就绘有这种“枋木及花样”,通过它的形制,我们就能得知山棚的大致样式。(见彩页图6)
仔细观察《清明上河图》中正店上方的木式小彩楼,是由竹木直接在店铺门楼上搭建而成的,共有上下两层,下层由竹木纵横交错结缚搭起,作为彩楼的基础,上层是建筑主体,由竹木搭成许多三角样式,装饰有彩布做成的各种花样图案。李俊锋《宋代山棚形制和作用初探》、刘涤宇《宋代彩楼欢门研究》等论文指出,这种小彩楼就是《东京梦华录》所说的“枋木及花样”。“枋木及花样”的模仿对象是山棚,说明山棚也是这样的双层结构。只不过店铺门首的彩楼是为装点门面、吸引顾客而建,没有实用功能,而山棚还要用于“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踘,踏索上竿”等伎艺表演,这就要求山棚的第二层必须稳固结实。前引《岁时广记》和《夷坚志》的两条史料已经说明,宋朝的“棚”继承了前代“重屋”的结构,是一种两层的建筑物,山棚的形制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宋朝“棚”的具体情况——下方以竹木为支撑,上层才是建筑的主体。“棚”的建筑形制在传世的宋画中也多有反映,如《风雨山水图》(见彩页图7)、《长桥卧波图》(见彩页图8)等画作中,在水岸边或山石间绘有小屋一座,由竹木和茅草搭建而成,下方以竹木为支撑,上方是房屋主体,建筑结构和取材都较为简易。由此可见,“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棚”的形制明确以后,勾栏的样式就不言自明了,它也是下层由竹木支撑、上层为剧场的棚式建筑,而“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等多种造型的勾栏,其原理和店铺门首的小彩楼很是相似,下层由竹木扎缚稳固,剧场所在的上层可搭建成莲花、牡丹等各种造型,就像山棚如何结缚花样全凭店家心意是一个道理。进入上方的剧场后,才能看到由栏杆围绕而成的一座舞台。本文对勾栏形制的推论基本已经完成了,幸运的是,笔者在元明文学作品中还发现了两条材料涉及勾栏,与本文的考证结果较为吻合:
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妇人时,果然是色艺双绝。
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第一条材料出自《水浒传》第五十一回,这段故事描写的是雷横进入勾栏观看白秀英演话本的场景。《水浒传》讲述的宋江起义发生在宋徽宗时期,虽然最终成书在元明之际,但作为一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其中记载了诸多宋代史实,不容忽视。在这段情节中,雷横和李小二要进入勾栏必须“入到里面”,说明勾栏是一座封闭剧场,观众必须进入其中方能观看表演。“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一语更是道明,勾栏的本质是棚式建筑。《庄稼不识勾栏》“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表达了同样的含义,这位庄稼人交费后才进入勾栏门,可见勾栏是封闭性的场所。这条材料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说明这位庄稼人先需爬上木坡才能进入勾栏,勾栏很有可能是一种双层建筑,由木坡连接一层和二层,勾栏门设置在一层木坡口。雷横进入勾栏后,“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可知勾栏内分为舞台和观众席,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观众在座位上观赏。而且观众席的位置有等级之分,雷横所坐的“青龙头上第一位”显然是上等座,价格较高,故而白秀英索要赏钱时,“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表明自己忘带银钱后,白秀英说道,“头醋不酽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这都表明雷横所坐之位是勾栏中最佳位置,价格也最高。而杜仁杰笔下这位庄稼汉的位置就很普通了,“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他显然坐在层层包围的人群之中,位置一般则价格低廉。
至此,笔者已大致勾勒出勾栏的形制,其外形是一种由竹木支撑而起、覆有屋顶的棚式建筑,一层仅起到支撑作用,二层是用于表演和观看的剧场。勾栏内部分布有舞台和观众席,舞台由栏杆围绕而成,宋元的艺人们便是在这里表演歌舞伎艺、杂剧院本的。
二、 勾栏的命名
勾栏的形制问题得到解决后,随之出现的疑问是,这样一种建筑为什么要叫做“勾栏”呢?换句话说,勾栏得此名称,是因为其舞台由栏杆围绕而成,还是因为它是一种棚式建筑?不少研究过勾栏的学者曾对“勾栏”的语义进行过溯源,不妨先予以简单回顾。持“栏杆说”的廖奔先生认为,“勾栏的本义原为曲折的栏杆。‘勾’者,曲折也,或勾连也……‘栏’者,栏杆也。梁人顾野王《玉篇》:‘栏,栏槛,以木为之。’”同样持“栏杆说”的黄大宏补充道:“许慎《说文解字》收‘阑、闲、槛、栊、楯、柙’等字,均源出‘阑(栏)’,段玉裁注‘阑’曰:‘谓门之遮蔽也,俗谓栊槛为阑,引申为酒阑字,于遮止之义演之也。’实即门槛,显然是指横木。”持“干栏说”的黎国韬师有不同意见:“汉语中的栏字本来是指一种植物,与栏杆、剧场等建筑物都扯不上关系……栏字与建筑物开始建立联系,乃在于它被用为译语的时候,因为南方壮侗语族‘房子’的发音为[lan],翻译成汉语就是这个栏字。”
从这番对勾栏的讨论不难看出,“勾”字仅是一个前缀而已,对“栏”字的阐释是解读“勾栏”的关键,“栏”究竟是“栏杆”之意,抑或“干栏”之意,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勾栏”源流的认识。有鉴于“栏”之字义的重要性,笔者对“栏”进行了文字学的考察,发现“栏”字的本义是一种植物,《说文解字》未收此字,《说文解字注》有云:“按《考工记》: 以欄为灰……欄实曰金铃子。可用浣衣。从木阑声。郎电切。十四部。按庄子非练实不食,或谓即欄实。”而表示“栏杆”之意的本字是“阑”,《说文解字》云:“门遮也”。段注补充:“谓门之遮蔽也,俗谓栊槛为阑……于遮止之义演之也”“此云阑槛者,谓凡遮阑之槛,今之阑干是也”。可见“阑”最初是用于遮门的阑槛,阑槛与栏杆都是横木,形制相似,于是“阑”也可指“栏杆”。在语词发展的过程中,“阑”之“栏杆”意假借为“栏”,“栏”也具有了“栏杆”的含义,这一现象在汉魏就已出现:
槛车,上施栏槛,以格猛兽之车也。
拘拦: 汉成帝顾成庙,有三玉鼎,二真金炉,槐树悉为扶老拘拦,画飞云龙角于其上也。
亦防而特耸方中,岂见其崇高?果缺栏槛而临阽危,或乏嶂蔽而当缺陷。
这几条史料中的“栏”表示“栏杆”之意显而易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提到“乃用栏为阑槛俗字”。本字的字义混入借字,甚至完全被借字取代而致使本字不用,这在文字演变中十分常见。如“鱻”字本义是“新鱼精也”,即鱼肉鲜美之意。“鲜”的本义是“鱼名”,自汉代开始以“鲜”代“鱻”,“鲜”从此具有了“鲜美”之意,而作为本字的“鱻”却被废弃不用了。再如“阙”的本义是“门观也”,后来“缺”字的“器破”之意假借为“阙”,“阙”的字义得到扩大。“阑”与“栏”也属于这种情况,二者本来各有其义,在汉魏时期,“阑”之“栏杆”意假借为“栏”,“栏”的字义得以扩大,于是,“栏”从汉代开始就与建筑配件“栏杆”产生关联了。
但黎国韬师认为,干栏式建筑大概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一时间点远早于“栏”与栏杆建立关系的汉代,所以“栏”与建筑建立联系是从干栏式建筑开始的。然而问题在于,即便干栏式建筑早已有之,但它一直存在于西南蛮夷之地,并未有实证说明它在汉朝之前已进入中原,遑论干栏式建筑对中原建筑产生影响了。且黎师提到的记载干栏的史料也可作为佐证,《魏书·獠传》《梁书·林邑传》《北史·獠传》《通典·边防·獠》《旧唐书·陀洹国传》《新唐书·南蛮下》《唐会要·南平蛮》《岭外代答·蛮俗条》《蛮书》《太平寰宇记·窦州·风俗》等篇目无一不是与南方夷族有关,直到唐宋时的文献仍然只有“南平蛮”“蛮俗条”等条目才记载干栏式建筑,这说明,干栏式建筑恐怕长期只在西南一带流行,在中原地区本已十分罕见,如此一来,就更谈不上对中原建筑有何影响了。因此,“栏”字不可能指干栏式建筑,它只能被解作“栏杆”了。
“栏”字既然表示栏杆,那么勾栏的得名就是因为其舞台由栏杆围绕而成的缘故。但这并不能说明,棚式结构在勾栏的命名过程中就毫无作用,前文曾提到,勾栏在宋元并非仅此一名,它还有“棚屋”“棚栏”“棚阑”等多种称呼,特别是“棚栏”“棚阑”这两个词语,能格外突出这种剧场的建筑特点,何为棚栏?即棚中有栏也。这不是将勾栏的外部和内部特征都表述得清楚明白了吗?但这一名词在宋元几百年间并未成为剧场的通用称呼,后来更是被废弃不用,反而以偏概全的“勾栏”一词被使用得最多,一直流传至今,为何历史会选择保留“勾栏”却废弃表意更加精准的“棚栏”呢?其中原因也很简单。棚栏是宋元新出现的词语,专指市井之剧场,而勾栏一词从汉代的“扶老拘栏”开始就已经出现,时至宋代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有无数文人吟咏过有关勾栏的诗词,如李颀有“云华满高阁,苔色上钩栏”,王建有“风帘水阁压芙蓉,四面钩栏在水中”,李商隐有“碧城冷落空蒙烟,帘轻幕重金钩栏”。在文人的描写下,勾栏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名词,其文化和历史底蕴远非新出的“棚栏”可比,故而宋代文人在记述瓦舍中的剧场时,多数情况下会选用古雅的“勾栏”。反观“棚栏”,使用此词的文献全为散曲这类俚俗的文体,在诗词笔记中根本看不到它的痕迹,可见它是市井百姓对剧场的称呼。
在剧场定名的数百年间,“勾栏”因其古雅诗意而被文人士大夫偏爱,最终得以保留,表意更加精准的“棚栏”等词却被淘汰。在今人看来,以舞台指称整座剧场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实际上这座剧场最终定名为“勾栏”,是多种名称角逐的结果,在历史文本的书写过程中,文人士大夫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
三、 勾栏的演变
勾栏之“栏”是栏杆,至此已经讨论得比较清楚了,勾栏如何从普通栏杆转义为剧场,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康保成先生曾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见解,他认为汉译佛经和佛教寺院是发生转义的关键环节,在佛经中就有将勾栏称作游艺场所的史料,此文一出,就有黄大宏先生撰写《勾栏: 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范例——对康保成〈瓦舍勾栏新解〉一文的质疑》一文进行商榷,他认为康先生使用的几处关键材料存在误读,提出勾栏演变为剧场还是源于中国固有的文化。笔者认为黄先生的观点很有道理: 一方面,康先生将佛经中的勾栏解释为歌舞厅、音乐厅的确有牵强之处;另一方面,汉成帝时就有“扶老拘栏”的记载,而佛教是东汉传入中国,佛寺修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方才兴盛起来,将勾栏演变的源头归根于佛教,未免有些太晚了。因此,我们还是从中国古代的传统建筑中寻找栏杆与表演场所之间的联系更为妥帖。
梁思成曾解释过“栏杆”在建筑中的用途:“栏杆是台,楼,廊,梯,或其他居高临下处的建筑物边沿上防止人物下坠的障碍物;其通常高度约合人身之半。栏杆在建筑上本身无所荷载,其功用为阻止人物前进,或下坠,却以不遮挡前面景物为限,故其结构通常都很单薄,玲珑巧制,镂空剔透的居多……在古代遗物中,我们所知道最古的阑干,当推汉画像石及明器。”据梁思成所述,栏杆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它是汉代以来多层建筑物中必不可少的部件。也正是从汉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在楼阁等多层建筑物的栏杆内表演歌舞百戏的现象。
汉代出土的明器里,有多座陶楼反映了当时贵族观赏乐舞的情景。如1989年出土于运城市北古村的汉代乐舞陶楼(见彩页图9),共有三层,在第一和第二层的栏杆内均有三位乐人,其中两人吹奏乐器,一人作舞;又如1977年河南项城县出土的东汉三层绿釉陶百戏楼(见彩页图10),底层四周设有栏杆,栏杆内有三个俑人排列成前一后二的三角状,前一人正在表演跳丸,后两人持排箫伴奏;再如1976年出土于安徽涡阳大王店的东汉绿釉陶楼,此楼分四层,第二层是表演乐舞的场所,左右后方封闭,前方有栏杆围绕,五个伎乐俑正在表演。汉代的乐舞百戏陶楼并非个例,在国内多地均有出土,此种陶楼通常有三四层之高,外层有栏杆围绕,乐人们站在一层或二层的栏杆内表演歌舞百戏。不过廖奔指出,“人们往往指这类陶楼为‘戏楼’,这是错误的。它们并不具备后世戏台的性质,设想一下,如果在楼上演出,让观众从楼下观看,视线就会被遮断。其实这类明器是贵族地主楼居歌娱生活的反映,表现的仍然是室内厅堂式的演出”。从廖文的表述来看,陶楼上表演乐舞是否为写实场景尚存争议,如果确为写实,栏杆内的这片场地就已具备了舞台的性质,但若不是写实,而是基于现实生活的一种创造,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乐伎在楼阁栏杆内表演乐舞是汉代十分常见的现象,所以时人才会将栏杆内表演的这一行为抽离出来,安插在陶楼之中。陶楼上的表演写实与否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但无论为何种情况,据此认为栏杆和表演场所在两汉时期就已产生联系,应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魏晋六朝时在楼阁栏杆内表演乐舞的现象并未中断。从文物的角度观之,大致沿袭了汉代陶楼所表现的场景,若说栏杆和表演场所的关系在六朝时有何发展,最重要的一次进步非梁武帝所创熊罴案莫属了。陈旸《乐书》卷一百五十绘有熊罴案的示意图(见彩页图11),图中用于演奏的平台呈方形,有台阶上下,平台四周围有木质栏杆,这座熊罴案是可移动的,在有演出需要的时候搬出,摆放在需要安置的地方,不用时就可撤去。在楼阁栏杆内表演乐舞,难免受到建筑物的束缚,不能随地进行,梁武帝将栏杆从楼阁中分离出来,使其围绕一方平台,成为独立的表演场所,这才有了熊罴案的诞生。但使用独立表演台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整个南北朝仅此一例,多数情况下乐舞百戏还是在楼阁建筑的栏杆内进行表演的。
或许是受到熊罴案的影响,进入唐代以后,栏杆终于脱离了建筑物的束缚,发展为专用于表演的栏杆式舞台,这代表着,栏杆与表演场所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莫445号窟南壁绘有盛唐壁画一幅(见彩页图12),画中有一座平台,前方围有栏杆,栏杆内站有六位乐伎,从左至右分别演奏横笛、箜篌、直项琵琶、排箫、笙、横笛。与之相似的,还有莫12号窟南壁的一幅晚唐壁画(见彩页图13),图中是一座带屋顶的舞台,屋顶下方有四根柱子作为支撑,左中右三侧有栏杆围绕。舞台中间是五位儿童,身着红衣或绿衣相间而站,中间为舞者,正在跪蹲而舞,左右两侧各有两位伴奏者,位于左侧的红衣者吹箫,绿衣者击打拍板,位于右侧的红衣者吹笙,绿衣者弹琵琶。这两窟壁画反映的内容相当珍贵,172窟中的平台显然是独立的,它不再依附于任何建筑,是单纯由栏杆围成的一座表演台,而12窟所绘内容直接是一座比较成熟的舞台了,舞台主体是由栏杆围绕而成,并配有屋顶、立柱等附件,其形制即使与宋元时舞台相比也毫不逊色。
在唐代,栏杆不仅是舞台必备的配置,即便是划地为场的艺人们,也会在市井的空地上搭起一座由栏杆围绕的简易舞台。莫85号窟窟顶东坡的晚唐壁画绘制了市井中的百戏表演(见彩页图14),艺人们以三根竹木作为支撑,用青布幔作横栏,缠缚起一座三角形的简易舞台,内有三位儿童表演,一人头顶竹竿,一人在竹竿中部单腿侧立,一人立于顶部;栏外左侧是两位伴奏的乐伎,白衣者吹笛,红衣者击打拍板,右侧是说话人,栏前围坐有观众。与之相似的还有莫61号窟南壁的五代壁画(见彩页图15),艺人用竹木和白色条幔围起舞台,中有两童子立于竹竿上;栏外有六位乐人,两位站立伴奏,一位手执拍板,一位吹笛,另外四位席地而坐伴奏,所持乐器左起为: 横笛、拍板、排箫、洞箫,站在右侧的说话人正在挥臂说唱。划地作场的表演由于观众和艺人同处于平地上,有时距离过近难以分开,势必会影响演出,于是艺人们用布幔作栏杆围成舞台,栏内表演,栏外观看,如此便不相混了,市井艺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搭建舞台,显然受到了栏杆式舞台的影响,由于他们平时四处作场,携带竹木栏杆颇为不便,于是吸取了栏杆式舞台的核心特征,以便携的布幔作为“栏杆”就可以缠缚起一座舞台。宋代路歧人在室外作场时,仍然会使用这种方式搭建简易的舞台,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党进)过市,见缚栏为戏者,驻马问:‘汝所诵何言?’优者曰:‘说韩信。’进大怒,曰:‘汝对我说韩信,见韩即当说我,此三面两头之人。’即命杖之。”党进骑马路过街市,看到有说话人“缚栏”表演,便驻马询问。可见此人并不在勾栏中,而是划地为场,以布幔为栏缠缚起一座舞台,这种“缚栏为戏”的形式与上述唐朝的情况显然是一致的。
这四幅壁画中,两幅为固定舞台,两幅为简易舞台,它们都反映出唐朝已经出现了栏杆式的舞台形制。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有不少学者都曾以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图为例,论证栏杆与演出场所之间的关系,天宫伎乐图中的表演场地的确是由栏杆围绕而成,但它们的本质还是宫殿或佛寺的一部分,并不是专门为演出而设的。因此,天宫伎乐图反映的内容还停留在栏杆与演出场所产生关系的初级阶段,性质和汉代陶楼没有太大区别,它与上述四幅壁画反映的栏杆式舞台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唐代勾栏完成了由栏杆向舞台的过渡,而它在宋代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栏杆式舞台被搬入棚式建筑,完成了由舞台向商业剧场演进的最后一步。宋代勾栏形制已在前文阐述,如果说还有什么疑点,可能就是栏杆式舞台为什么进入的是棚式建筑,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建筑,这其中有什么特殊原因,又或者恰好是一种巧合?
宋代棚式建筑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便于拆卸、安装简便,每当有重要节日时,官府便会在京城内扎结乐棚山棚,供市民游乐,这在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
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踘,踏索上竿。
十六日车驾不出……寺之大殿,前设乐棚,诸军作乐……诸门皆有官中乐棚。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
六月六日州北崔府君生日,多有献送,无盛如此。二十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
其赐宴殿排办事节云: 仪銮司预期先于殿前绞缚山棚及陈设帏幕等。
棚这种建筑易于搭建也易于拆卸,在元宵节、正月十六、崔府君生日、皇帝生日时等特殊节令时,官府会在多处搭建乐棚山棚以供表演,节日结束后则拆卸下来,以待下次使用。黎国韬师曾提出,勾栏是一种临时性的舞台,“在瓦市内建造一个永久性的舞台显然不如搭建一个临时性的棚式剧场划算,假使瓦舍不再用于商业集市用途,勾栏棚的材料也可以拆卸到其他地方,继续建造另一个临时的戏剧舞台”。这一推论是极有可能的,勾栏设置在瓦舍之中,瓦舍尚且“来时瓦合,去时瓦解”“易聚易散也”,是一种流动的集会场所,瓦舍之中的勾栏又如何能以固定剧场的身份长期处于一地呢?可见宋人考虑到了棚这种竹木结构的安装拆卸远比砖石结构简便得多,很适合搭建临时性剧场,但仅仅具有这个特点还不够,毕竟就地搭建单层建筑会比竹木支撑的双层木棚更加容易,这就涉及棚的第二个优势,对地势和场地大小的要求较低。从前引的《风雨山水图》等两幅宋画中不难发现,棚可适应的地形范围极广,在山坡、水边等地理条件并不优越的地方,也能搭棚而起。勾栏的搭建是追随瓦舍的所在之处的,瓦舍不一定每次都会选址在土地平坦宽阔的地方,而且,一座瓦舍内设有多座勾栏,这意味着经营勾栏的商人还要在瓦舍内部竞争搭建场地,有时难免会碰到地理位置不佳、地域狭小等问题,这就要求勾栏必须具备因地制宜的能力,在山坡上、水岸边、窄小处都能搭建,而由竹木撑起的棚便可以满足这些要求。比如,在有坡度的地方,调整竹木支架的长短和木板的薄厚,就能使木棚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在狭窄的区域里,先将竹木在小范围内撑起,再于高处搭建较大的木棚,就能解决地面狭小的问题;在水中搭建勾栏就更不在话下了,具体情况参考水阁形制就足矣。由此看来,宋人选择棚作为安置栏杆式舞台的场所是经过多番考量的,棚既易于搭建,又能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经营勾栏的商人携带一捆竹木便能追随瓦舍的所在之处进行搭建,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比棚更加适合建造临时性剧场的建筑样式了。
至此,我们已经大致理清了勾栏从栏杆演变为剧场的整个过程。从汉代始,就出现了乐伎在楼阁栏杆内表演乐舞的情况,这是栏杆与表演场所产生关联的第一步。六朝时梁武帝发明了熊罴案这一专为演出而设的舞台,这意味着由栏杆围成的演出场所已经有了从楼阁建筑中独立出来的趋势。时至唐代,演出场所终于脱离了建筑物的束缚,发展为专用于表演的栏杆式舞台。在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社会背景下,栏杆式舞台进入棚式建筑,从此勾栏成为真正的商业性剧场。
结 语
勾栏是宋元戏剧表演的重要场所,早已得到学界关注,积累的先行成果虽然不少,但至今未有定论。本文考察了勾栏的形制、得名、演变等内容,是对勾栏展开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探讨,解释了前辈学者未曾涉及的问题,如演出棚和栏杆之间的关系,为何使用“勾栏”一词称呼演出棚等等,辨析了前辈学者在勾栏问题上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此外,本文的研究或许可以结束“栏杆说”和“干栏说”的论争。二说均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对。勾栏之“栏”的确是从栏杆发展而来,但并不是整座剧场就是由栏杆围绕而成,这是“栏杆说”存在的误解。勾栏的整体是棚式结构,与西南地区的干栏式建筑的确十分相似,但勾栏的棚式结构是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棚阁发展而来的,没有文献表明它与干栏式建筑存在关联,更不能认为勾栏之“栏”是“干栏”之意,这是“干栏说”的问题所在。
早期戏剧的发生时代距今较远,我们在研究中难免会陷入文献史料缺乏的困境,对勾栏的考察亦如是。前辈学者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无不是用力甚劬,虽将与勾栏相关的文献史料发掘殆尽,但仍未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果,由此可见,早期戏剧的研究单纯依靠传世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尽量发掘“第二重证据”,通过文献与文物的互证,或能解决早期戏剧研究的许多难题。